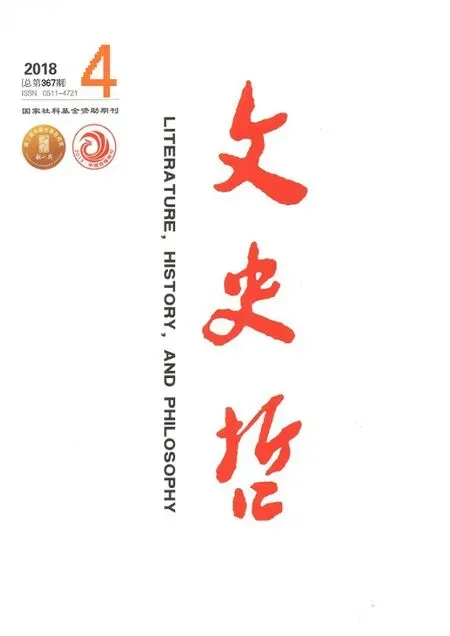郭象独化说新解
——兼与维特根斯坦的相关观点比较
韩林合
郭象的哲学体系是以对《庄子》文本的创造性解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如果说庄子的哲学体系的起点是其道论的话,那么郭象的哲学体系的起点则是其对庄子道论的创造性解构。正是以这样的解构为基础,郭象提出了“独化”说,并以该学说为基础构建起了其复杂的哲学大厦。
一、庄子之道
庄子所谓道究为何“物”?为了令人满意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首先看一下庄子究竟赋予了道以什么独特的特征。按照《庄子》的描述,道具有如下主要特征。第一,道无形、无声(因而又被称为“无”),窈冥(深远难测)、昏默(昏暗沉寂),绝对绝待、独往独来。第二,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说,道均是无穷无尽的。进而,我们根本不能用久老、高深之类的词汇来形容它。第三,道生天地万物,因此它自身不可能是由任何事物生成的。而且,任何事物的毁灭都是由道造成的,因此道本身不可能被任何事物所毁灭。更准确地说,“生成”和“毁灭”之类的说法根本不适用于它。第四,在生成万物之后,道作为它们的本性和命运(所谓“性命之情”或“本根”)而继续支配着它们。因此,道又被称为“物物者”。第五,道不仅生成万物,而且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第六,道是严格按照“虚静恬淡寂漠无为”原则生成和支配万物的。故此,我们完全不能用“仁”“义”“巧”“戾”等等词汇来形容它。
笔者认为,如上意义的道实际上就是作为整体的世界,因为作为整体的世界恰恰也具有上面所描述的所有特征。第一,作为整体的世界当然也是无形无声的,因为只是对于其内的事物,我们才能有意义地说它们具有某种形状,或者具有某种声音。同样,作为整体的世界也可以说是窈冥、昏默的,更可以说是绝对绝待、独往独来的,因为按照定义它包含了所有存在的东西。第二,无论从时间上说还是从空间上说,世界都是无穷无尽的。我们不能用久老、高深之类的词汇来形容它。第三,表面上看,世界之内的任何一个事物都是由其内的某个或某些其他事物生成的。但是最终说来,所有事物(包括天和地)都是由作为整体的世界生成的。因此,它自身不能说是由它之内的任何事物生成而来。更准确地说,“生成”和“毁灭”之类的说法根本不适用于它。第四,在生成万物之后,作为整体的世界作为它们的本性和命运继续支配着它们。也就是说,所有事物最终都是由作为整体的世界生成和决定的。第五,作为整体的世界或宇宙当然无所不包,也可以说无所不在。在此,作为整体的世界无所不在,意思并非是说它作为一个部分或成分而存在于所有事物之中,而是说通过其部分或成分的处处存在,它间接地存在于所有地方。正如当我说我面前的一棵树S存在于它的所有部分所占有的所有空间位置上时,我的意思并非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个体的S存在于这些空间位置上,而是说通过其部分在这些空间位置上的存在,作为一个完整的个体的S间接地存在于这些空间位置上。第六,作为整体的世界也是严格按照“虚静恬淡寂漠无为”的原则生成和支配万物的。它不与物交故而与物无逆(这是因为它绝对绝待),也可以说它一而不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通常所谓变化是指发生于世界之内的诸对象之间的一种事项,而世界整体则是唯一的),进而它也不可能存“心”去做任何事情,我们便也不能用“仁”“义”“巧”“戾”之类的词汇来形容它的所作所为。
在此,我们不应当将世界整体简单地理解为物和事的总和,而应当将其理解为某种巨大的事实结构。同时,由于从现象层面上看世界中的事物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中,我们也可以说道就是作为整体的物化过程。而且,就其本然状态而言,作为整体的世界(简言之,世界整体本身)根本无所谓物与物、物与事、事与事的区别,因此也无所谓化与不化的问题。显然,庄子的道所指的只能是这样的世界整体,而非通常的心智所了解的充满各种各样区别和变化的世界整体——所谓现象世界。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庄子又将道称作“至一”(“大一”或“太一”)。所谓“至一”指无所谓一还是二的存在状态,进而指超越于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样的区别乃至任何区别的存在状态。
出现在《庄子》中大多数地方的具有哲学意义的“天”或“天地”,通常代称世界整体本身,因而与“道”同义。如此这般的道概念,在庄子的哲学体系之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实际上,正是世界整体本身的一些独特特点(绝对、绝待、永恒等等),使得与其同而为一的至人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或消解所有的人生问题。

二、郭象对庄子之道的消解
首先,郭象消解了庄子所宣称的作为万物的创造者和支配者的道。他断定根本不存在创造和支配一切事物者,因为如果存在着这样的东西,那么它必然或者是无,或者是某一个特定的事物。但是,无显然不可能拥有创造和支配任何事物的能力,而任何特定的事物又不可能创造和支配万物万形。因此,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存在创造和支配一切事物的道。基于以上逻辑,郭象认为庄子所谓道只能是至无:
世或谓……形待造物者。请问:夫造物者,有耶无耶?无也?则胡能造物哉?有也?则不足以物众形。(《庄子集释·齐物论》,第105页)*本文所用《庄子》、《庄子郭象注》、《庄子成玄英疏》,均引自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后仅随文标注书名、篇名、页码。
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庄子集释·齐物论》,第51页)
此故是无不能生有、有不能为生之意也。(《庄子集释·庚桑楚》,第718页)
无也,岂能生神哉?不神鬼帝……不生天地。(《庄子集释·大宗师》,第226页)
知道者,知其无能也;无能也,则何能生我?(《庄子集释·秋水》,第522页)
……至道者乃至无也。(《庄子集释·知北游》,第673页)
如果道是至无,不可能拥有创造万物之功,那么庄子为什么总是对之申说不已呢?对这个问题,郭象的回答是这样的:庄子之所以一再地谈到道或无,是为了让人们明白生物者无物而物自生、自有的道理。他说:
窈冥昏默,皆了无也。夫庄老之所以屡称无者,何哉?明生物者无物而物自生耳。(《庄子集释·在宥》,第348页)
无有,故无所名。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于至一,非起于无也。然庄子之所以屡称无于初者,何哉?……夫无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乃所以明物生之自得,任其自得,斯可谓德也。(《庄子集释·天地》,第383页)
在一些注解之中,郭象甚至干脆将道等同于物之自生、自有、自得、自因等等,泛而言之,即物之自然或自尔。由此,便有了“自然之道”这样的说法:
夫达者之因是,岂知因为善而因之哉?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故谓之道也。(《庄子集释·齐物论》,第71页)
类聚群分,自然之道。(《庄子集释·德充符》,第201页)
道在自然,非可言致者也。(《庄子集释·知北游》,第646页)
明夫至道非言之所得也,唯在乎自得耳。(《庄子集释·知北游》,第666页)
从上文我们看到,庄子不仅认为道生万物,而且认为道遍在于万物之中。郭象否认造物主和支配者意义上的道的存在,认为道即至无。在道即至无的意义上,郭象是认可道的遍在性的:道无所不在,而所在皆无。其曰:
道焉不在!言何隐蔽而有真伪,是非之名纷然而起?(《庄子集释·齐物论》,第63页)
冥然无不在也。(《庄子集释·齐物论》,第81页)
言道之无所不在也,故在高为无高,在深为无深,在久为无久,在老为无老,无所不在,而所在皆无也。且上下无不格者,不得以高卑称也;外内无不至者,不得以表里名也;与化俱移者,不得言久也;终始常无者,不可谓老也。(《庄子集释·大宗师》,第226页)
若必谓无*参见成玄英疏:“无者,无为道也。”(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662页)之逃物,则道不周矣,道而不周,则未足以为道。(《庄子集释·知北游》,第662页)
明道不逃物。(《庄子集释·知北游》,第662页)
关于道之遍在性,郭象当然还可以给出另一种更为可取的解释:道即自然,而物皆自然,所以道遍在于万物之中。例如:
任其自然而已。物皆自然,故至一也。(《庄子集释·缮性》,第490页)
夫无有何所能建?建之以常无有,则明有物之自建也。自天地以及群物,皆各自得而已,不兼他饰,斯非主之以太一耶!(《庄子集释·天下》,第959页)
我们看到,庄子的道最终说来是至一,即不包含任何区别的世界的本然状态。在上面引述的相关注解中,郭象是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理解庄子所说的至一状态的:万物尽管从数上说是彼此有别的,但是在自得其生、自然而然这点上是一样的;未有物理之形的万有之初。
三、“独化”说的提出
在坚决地否定了创造和支配万物的道的存在之后,郭象对万物产生和变化的最终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断言万物最终说来均是自生自灭自成自毁自变自化的。此即其“独化”概念的意义之一。
首先,我们看一下万物的最终来源问题:万物最终源自于无吗?从前文我们看到,无不可能有创生万物之功。那么,万物可以源自于某一个特别的事物(比如阴阳之气、天地)吗?但是,我们要追寻的是万物的最终来源,这时还没有任何通常意义上的事物(有形之物)。郭象认为,万物的最初状态是未形之一,即至一。就这个至一来说,我们不能问它从何而来的问题,我们只能说它是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的。那么,接下来的有形之一即第一个事物(或许是元气)是如何生成的?郭象的观点是这样的:我们不能说它是由无创生的,也不能说它是由至一创生的(尽管它的确始自于至一),最后当然也不能说它是由自己创生的(因为这时它还不存在)。因此,万物最终说来只能是不知其所以生而自生的。郭象偶尔又将这种独特意义上的“自生”称为“独生”或“独尔”:
大块者,无物也。夫噫气者,岂有物哉?气块然而自噫耳*这句话谈论的是有形之一即世间第一个事物(元气?)之产生。。物之生也,莫不块然而自生,则块然之体大矣,故遂以大块为名。(《庄子集释·齐物论》,第47页)
此天籁也。夫天籁者,岂复别有一物哉?即众窍比竹之属,接乎有生之类,会而共成一天耳。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天然耳,非为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岂苍苍之谓哉!而或者谓天籁役物使从己也。夫天且不能自有,况能有物哉!故天者,万物之总名也,莫适为天,谁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此天道也。物皆自得之耳,谁主怒之使然哉!此重明天籁也。(《庄子集释·齐物论》,第5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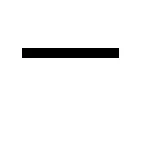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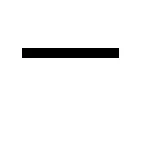
此所以明有之不能为有而自有耳,非谓无能为有也。若无能为有,何谓无乎!一无有则遂无矣。无者遂无,则有自欻生明矣。任其自生而不生生。(《庄子集释·庚桑楚》,第706页)
郭象不仅认为根本不存在创造和支配万物的道,而且进一步认为万物彼此之间也没有任何因果依赖关系。在这种意义上,万物也是自生自灭自成自毁自变自化的。此即其“独化”概念的另一种意义。显然,这种意义上的独化更其极端。
对于这种意义上的独化,郭象给出了如下论证。如果事物之间有因果依赖关系,那么我们或者要承认有第一因即造物者,或者要承认因果链条是无穷无尽的。但是,不可能有造物者,因此须承认因果链条无穷。这就意味着我们永远找不到事物的真正的、最终的原因。因此,还不如从一开始就否认因果关系的存在,转而认为万物均是自生自灭自变自化的。而且,如果承认事物之间存在着因果进而依赖关系,那么这会导致人们偏爱其所依赖的东西,这样便会导致人们之间的争斗。因此,最好放弃事物之间有所谓因果进而依赖关系的想法。
如果说任何一个特定的事物既不可能是由无或道创生的,又不可能是由另一个事物创生的,也不可能是由自己创生的(因为此时它还根本不存在),那么其生成就只能是不知其所以生而自生的结果。而且,任何一个特定的事物的变化的情况也是一样的,这样的变化既不是由无或道造成的,也不可能是由另一个事物造成的,更不是由自己造成的,而只能是不知其所以然而自然的结果。郭象曰:
彼,自然也。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者,即我之自然,岂远之哉!凡物云云,皆自尔耳,非相为使也,故任之而理自至矣。(《庄子集释·齐物论》,第56页)
言天机自尔,坐起无待。无待而独得者,孰知其故,而责其所以哉?若责其所待而寻其所由,则寻责无极,〔卒〕至于无待,而独化之理明矣*按照通常的看法,影子依赖于有形之物而生,而且其坐起也取决于后者。郭象认为这样的流俗看法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影子根本就无所依待,是独生独化的。在此,他给出了如下论证:假定影子之生、之坐起依赖于相应的有形之物,那么该有形之物之生、之坐起又依赖于什么东西?这样,我们不得不没完没了地往下追问,总是不能找到影子之生、之坐起的真正的原因。因此,我们最好放弃这样的追问,进而坚定地放弃事物间存在着因果依赖关系的看法,而是一开始便承认影子进而世间万物均是独生独化的。。若待蛇蚹蜩翼,则无特操之所由,未为难识也。今所以不识,正由不待斯类而独化故耳*在此郭象作出了如下论证:表面上看(或者说从常人的角度看),蛇之行要依赖于其蚹(蛇腹下的横鳞),蜩(即蝉)之飞要依赖于其翼。如果影子与相应的有形之物之间的关系类似于蛇之行与蛇蚹、蜩之飞与蜩翼之间的关系,那么该关系之依赖性质并非是难以识认的。但是,这种依赖性质恰恰是难以识认的,因此这两种关系是不一样的。进而,影子并非依赖于相应的有形之物,而是独生独化的。郭象本人当也不承认蛇之行依赖于蛇蚹、蜩之飞依赖于蜩翼,而是认为它们均是独生独化的。。(《庄子集释·齐物论》,第10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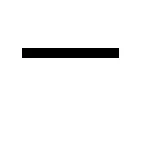

虽张毅之出,单豹之处,犹未免于中地,则中与不中,唯在命耳。而区区者各有所遇,而不知命之自尔。……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则一生之内,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动静趣舍,情性知能,凡所有者,凡所无者,凡所为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尔耳。(《庄子集释·德充符》,第184页)
明物物者,无物而物自物耳。物自物耳,故冥也。物有际,故每相与不能冥然,真所谓际者也。不际者,虽有物物之名,直明物之自物耳。物物者,竟无物也,际其安在乎!既明物物者无物,又明物之不能自物,则为之者谁乎哉?皆忽然而自尔也。(《庄子集释·大宗师》,第223页)
郭象之所以反对自因说,是因为他坚持这样一种奇特的事物观:一个事物在某一时间点上的存在(比如昨天之我)从数上说根本不同于其在另一时间点上的存在(比如今天之我)。他说:
夫无力之力,莫大于变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趋新,负山岳以舍故。故不暂停,忽已涉新,则天地万物无时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为故;舟日易矣,而视之若旧;山日更矣,而视之若前。今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复今我也。我与今俱往,岂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觉,横谓今之所遇可系而在,岂不昧哉!(《庄子集释·大宗师》,第223页)
这样的事物观,再加上某一事物之变化原因不能来自他物的观点,使得郭象不可能坚持如上意义的自因说。进一步说来,这样的事物观实际上根本就排除了通常意义上的变化概念*参见如下注文:“物之变化,无时非生,生则所在皆本也。”(《庄子集释·庚桑楚》,第711页)。因为通常意义上的变化是以相关的事物的历经时间的数的同一性为前提的,而郭象恰恰不承认这样的同一性的存在*参见拙著:《分析的形而上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章第1节。。那么,郭象自己究竟是如何理解事物的变化的?毕竟,在注文中他毫无顾忌地讨论到了变化。笔者认为,当他正面谈论变化时,他是这样理解变化的:变化就意味着比如一个特定的事物在一个特定的时刻丧失了一个性质,而在接下来的时刻一个与之极为相似的并且与之有着某种特定的时空连续性、某种非依赖的协变关系的事物拥有了一个新的性质。
一些解释者甚至还将如下意义上的自因说(或内因说)归属给郭象:万物均是因自身的原因而产生的*冯友兰、汤一介、王晓毅等均主此说(参见前引书)。汤用彤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便已经正确地指出了郭象并不坚持这种意义上的自因说(参见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84、191页)。。这种观点似乎有着充分的文本根据,比如前引《齐物论》注似乎就明确地断定了这点:“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不过,按照我们前文的解释,此处所谓“自生”并非是说万物均是因自身的原因而产生的,而是说万物均是不知所以生而生的。泛而言之,万物均是不知所以然而然的:它们均不知所以生而生,不知所以化而化,不知所以有而有,不知所以得而得,不知所以成而成,不知所以取而取,不知所以知而知,等等。按照郭象的习惯用法,所谓不知所以然而然即自然。相应地,不知所以生而生即自生,不知所以化而化即自化,不知所以有而有即自有,不知所以得而得即自得,不知所以成而成即自成,不知所以取而取即自取,不知所以知而知即自知,等等。请进一步参考如下注文:
道,无能也。此言得之于道,乃所以明其自得耳。自得耳,道不能使之得也;我之未得,又不能为得也。然则凡得之者,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掘然自得而独化也。夫生之难也,犹独化而自得之矣,既得其生,又何患于生之不得而为之哉!故夫为生果不足以全生,以其生之不由于己为也,而为之则伤其真生也。(《庄子集释·大宗师》,第229页)
以上注文中的“自得”即“自得此生”之略语,请比较《庄子集释·天地》注文:“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难,而犹上不资于无,下不待于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营生于已生以失其自生哉!”(第383页)显然,“自生”也为“自得此生”之略语。《大宗师》注文中的“我之未得(即未得生),又不能为得也”、“然则凡得之(即得生)者,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掘然自得而独化也”清楚地表明:郭象所谓“自生”或“自得此生”不可能是在字面意义上使用的,即不可能意味着万物均是自己创生自己的。
因为我(在此指任何一个人,进而也可指任何一个事物)是不知所以生而生的,即是自生的,而自生是自然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也可以说我是自然而生的。由此看来,我与自然是不能分立的。此即前引令人费解的注文“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者,即我之自然,岂远之哉”之意义*引文出自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齐物论》,第56页。其中,“我自然生”为“我自然而生”之略语,语出《秋水》注(《庄子集释·秋水》,第522页)。就字面意义来说,“自然生我”这种说法显然是不适当的,参见《知北游》注:“谁又先阴阳者乎?吾以自然为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尔耳。”(《庄子集释·知北游》,第673页)。
因此,认为郭象坚持自因说完全是望文生义。实际上,郭象根本就否认因果关系的存在。按照他的观点,最终说来或者说本质上说来,世界中的一切事物均是没有任何原因地(包括所谓外因和内因)——或者说掘然(突然、忽然、诱然、欻然)地——生成和变化的。
四、“独化”说之困难及其消解
郭象的这种事物观显然是完全违背人们的常识理解的。按照通常的理解,事物之间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依赖关系的,而因果关系即是其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为普遍的一种。那么,郭象是如何消解其理论中的这个困难的呢?我们知道,因果关系是一种依赖性的协变关系:作为原因的事物中的某种变化,导致了作为结果的事物中的某种相应的变化。郭象虽然否认事物之间有依赖或决定关系,但是他并不否认事物之间有某种意义上的协变关系:如果一个事物发生某种变化,那么另一个事物就发生某种相应的变化。郭象将这种协变关系称作“相因”、“俱生”。在此,“因”当为因任、因应、因顺、因循之因,而非原因之因,因此并非意指引起或依赖。请参考其关于“罔两待景”的议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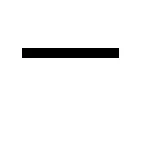

虽手足异任,五藏殊官,未尝相与而百节同和,斯相与于无相与也;未尝相为而表里俱济,斯相为于无相为也。(《庄子集释·大宗师》,第24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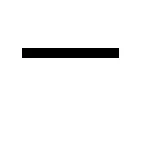
在有些地方,郭象的相关观点变得甚为极端。他甚至认为世界中的任何一个事物的存在都极大地关乎另一个事物的存在(特别是人之生)。因此,如果任何一个事物不存在了,那么所有其他事物的存在(至少是人之生)都跟着成问题了(因为其存在的完整的理由链条不复存在了);如果任何一个事理没有得到实现,那么所有其他事理的实现(至少是人生之理之实现)就会成为不可能(因为其实现的完整的理由链条缺失了)。他说:
人之生也,形虽七尺而五常必具,故虽区区之身,乃举天地以奉之。故天地万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无也。一物不具,则生者无由得生;一理不至,则天年无缘得终。(《庄子集释·大宗师》,第206页)
那么,如何解释事物之间的这种普遍的非依赖(“非待”)的协变关系?在上面的注文中郭象是以这样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的:任何一个特定的人或物均是由所谓五行(也称“五常”)即金木水火土构成的,而五行又是天地万物的构成元素,因此任何一个特定的人或物的存在均与任何其他事物的存在有着非依赖的协变关系。
这个回答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其所给出的论证显然是不成立的。我们不妨另行给出如下回答:给定两个事物,如果其本质之中便包含着它们彼此之间的非依赖的协变关系,以及它们与其他事物之间的非依赖的协变关系,那么这些其他的事物的本质之中必定又包含着与另外的事物之间的非依赖的协变关系,如此类推,以至无穷,所有事物按照其本质便必定处于普遍的非依赖的协变关系之中。
不过,真正说来,或者说最终说来,事物之间的这种普遍的非依赖的协变关系是无法解释的——这是不知所以然而自然的事情。请看如下注文:
物有相使,亦皆自尔。(《庄子集释·则阳》,第806页)
按照郭象的独特用法,“自尔”意即自然,进而意为不知所以然而然。此注文进一步当可这样来理解:这种协变关系——进而所谓“相为”、“相使”或“相与”——最终源自于相关事物的内在性质,构成了它们之本性(或本质)的一部分;而本性之事均是不知所以然而然的。
郭象将世界中的诸事物本质上所处的这种复杂的协变或俱生、相因关系——进而“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关系——称作“玄冥”或“玄合”。他认为,这种玄冥之境构成了独化的最高境界——所谓“独化之至”。
通常意义上的独化之境不一定就是玄冥之境,因为独化之物可以是彼此冲突的,而玄冥之境则是充满内在的和谐的独化之境。而郭象意义上的独化之境,必定是玄冥之境:
卓者,独化之谓也。夫相因之功,莫若独化之至也。故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独化也。人皆以天为父,故昼夜之变,寒暑之节,犹不敢恶,随天安之。况乎卓尔独化,至于玄冥之境,又安得而不任之哉!既任之,则死生变化,惟命之从也。夫真者,不假于物而自然也。夫自然之不可避,岂直君命而已哉!(《庄子集释·大宗师》,第220页)
意尽形教*此句意为:“暖姝者”心里想到的全是有形的教化之事。,岂知我之独化于玄冥之竟哉!(《庄子集释·徐无鬼》,第759页)
人们通常认为,在郭象的“独化”说与其“逍遥”说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因为独化意味着无待,而常人之逍遥却以有待为前提。在笔者看来,这种看法是对郭象相关说法的误解。我们知道,郭象严格区分了圣人的无待逍遥与常人的有待逍遥。因为圣人无心、无我、无物,所以能够绝对地安命,与物无不冥、与化无不一,或者说无所不因,无所不乘,所以他能够无所不成——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更准确地说,在任何情况、任何条件下)均能够成功,由此他便进入了无待逍遥之境。就常人而言,他们不可能像圣人那样做到玄同彼我,他们心中不能不装有各种各样的区别。但是,只要他们能够做到无分外之心,安于自己的命运或性分,冥其极,守其分,那么至少就此说来万物的区别对他们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甚至于就不存在了——此时可以说万物均齐于性足或自得(即得其真性或自然)。这样,他们也能够获得逍遥。不过,这种逍遥全然不同于圣人的逍遥,是有待逍遥,因为其真正的实现最终还是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而最终说来只有圣人才能够提供这样的条件。为了让常人能够获得逍遥,圣人(严格说来,圣王)所能提供的相关条件也甚为简易,即:无条件地尊重常人各自的本性,任其自能,任其自为,不随意干扰之,此即老子所谓“法自然”(语出自《老子》第二十五章),也即其所谓“无为”(语出自《老子》第二、三、十、三十七、三十八、四十三、四十八、五十七、六十三、六十四章)。因为完全没有外在的干扰,所以常人乃至万物最终说来便能够按照各自的本性而自行、自动、自为、自化、自长、自成;进而,因为万物本质上说来彼此处于普遍的非依赖的协变关系之中,乃至本来就是相为于无相为、相与于无相与的,所以常人这时便能获得其各自的逍遥的条件,从而进入自得的(进而自由自在的)逍遥之境。
因此,郭象所称的常人的这种有待逍遥之“有待”,实际上完全不同于通常所说的有待,进而也完全不同于其“独化”说中所否认的事物之间的因果依赖关系,而是相当于其所理解的“相因”或“俱生”。因为从一方面说来,圣人为常人所提供的逍遥条件并不是其逍遥的原因,而只是构成了其预设或根据(可以说二者之间所存在的是某种非依赖的协变关系);从另一方面说来,看似(即表面上看来,或者说在没有进入逍遥之境的常人看来)构成了常人乃至其他有生命之物之逍遥的原因的那些事项(比如列子在空中行走时所依赖之轻风,大鹏展翅飞行时所依赖之厚风),实际上本来就分别内在于常人的本性和相关的事项的本性之中。这也就是说,郭象之有待“逍遥”说与其“独化”说并非像许多解释者所认为的那样相互矛盾。
按照郭象的“独化”说,万物本质上说来均是(或者说均应当是)独化于玄冥之境的,均是俱生而非待的,即使影外微阴与影子、影子与有形之物之间也是这样的。此即其著名论断“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所要表达的意思。人本来也处于这样的状态;而且,按照其本质人也应当处于这样的状态。对于常人来说,这样的状态构成了其有待逍遥之境。但是,常人恰恰背离了这样的状态,因为他们均不安于性分,认为事物均是相依相待的。因此,他们总是挖空心思地寻求相为、相与、相使,结果使得自己和他人均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相反,至人或圣人则认识到了世界的真相,认识到了万物本质上说来均是独化于玄冥之境的,均不是互相对待的,甚至于根本就没有我和物的观念,因而能够随顺万物万化、万事万变,进而达至无待的逍遥之境。这样的逍遥之境便是绝对绝待的玄冥之境——此即郭象所谓“绝冥之境”(也即庄子所谓“无有”、“无何有之乡”、“无何有之宫”)。就常人来说,当他们在圣人的“帮助”下进入了有待逍遥之境时,他们便再次独化于玄冥之境了。请参考如下段落:
然庄生虽未体之,言则至矣。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死生之变,而明内圣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绰,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义之所适,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芒。至〔仁〕极乎无亲,孝慈终于兼忘,礼乐复乎已能,忠信发乎天光。用其光则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长也。*郭象:《庄子序》,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3页。
夫尧之无用天下为,亦犹越人之无所用章甫耳。然遗天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下虽宗尧,而尧未尝有天下也,故窅然丧之,而尝游心于绝冥之境,虽寄坐万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遥也。(《庄子集释·逍遥游》,第35页)
五、与维特根斯坦相关观点的比较
在前文中,我尝试对郭象的极端说法“一物不具,则生者无由得生;一理不至,则天年无缘得终”给出了一种解释,并且还对其进行了某种论证:给定两个事物,如果其本质之中便包含着它们彼此之间的非依赖的协变关系,以及它们与其他事物之间的非依赖的协变关系,那么这些其他的事物的本质之中必定又包含着与另外的事物之间的非依赖的协变关系,如此类推,以至无穷,所有事物按照其本质便必定处于普遍的非依赖的协变关系之中。在给出这样的解释和作出这种论证时,笔者参考了维特根斯坦的相关说法。
按照前期维特根斯坦的理解,世界是事实的总和。事实首先分析成基本事实,而基本事实则是最简单的事实结构,其核心特征是互相独立,彼此既没有必然联系意义上的因果联系,也没有逻辑结构上的联系。如果我们继续对基本事实进行分析,我们得到的将不再是事实,而是对象。无论从结构上说还是从构成上说,对象都是最简单的成分。它们是世界的最终的结构元素或构成元素,或者说实体。正因如此,它们不可毁灭,永远存在。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们根本就无所谓存在或不存在,因为所谓存在就是最终的元素的相互结合,而不存在或毁灭就是最终的元素的彼此分离。那么,这样的对象是如何构成基本事实的?维特根斯坦认为,诸对象之所以能够相互结合构成基本事实,并非是它们之外的某种成分(某种形式的黏合剂)使然,而是因为它们内在地包含着如此结合的可能性。一个对象所内在地包含的与其他的对象的结合可能性,或者说有其出现的所有那些基本事态,构成了该对象的内在性质或本质。
由于对象是永远存在的,一些对象的存在,甚至于一个对象的存在,就意味着所有对象的存在(这也就是说,作为世界乃至整个逻辑空间之结构元素或者说实体的所有对象必是始终共同存在的,缺一不可)。进而,因为一个对象内在地包含着它与其他对象的一切结合之可能性进而才会有其出现于其中的所有基本事态,所以给出了一些对象,甚至于给出了一个对象,就意味着给出了所有基本事态,进而所有事态,最后也就意味着给出了包括现实世界在内的所有可能世界(即整个逻辑空间)。由此便有维特根斯坦的如下断言:
每一个物都决定了(bedingt)整个逻辑世界,可以说,整个逻辑空间。*[奥]维特根斯坦:《战时笔记》,韩林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32页。从上下文来看,该评论也可译作:“每一个物都以整个逻辑世界——可以说,整个逻辑空间——为条件。”(在此,“条件”意为根据或理由,而非指原因。)这样的断言与郭象的相关说法亦若合符节。

夫事物之生皆有由。夫事由理发,故不觉。(《庄子集释·外物》,第82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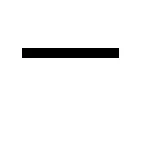
在此,郭象似乎区分了原因和理由,认为事物之生成和变化无原因,但有理由。一个事物之生成和变化的理由即与其有着非依赖的协变关系的诸事物(更准确地说,即其性分或理分)。而且,天地万物之生成和变化的理由(或根据)的链条是有终结的,其终点便是所谓至理,即这样的道理:天地万物均是自然而然的,或者说均是不知其所以然而自然的(因而此终点绝非通常所说的造物者)。事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就一个事物来说,这种与其他事物的非依赖的协变关系本来就构成了其本性之要素,而本性之要素均是自然而然的,或者说均是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与理由的链条不同,人们通常所谈论的原因的链条则是没有终结的,是无穷的。按照上面的解释,郭象所喜欢使用的“不知(其)所以然而(自)然”之类的说法所涉及的当只可能是根据或理由。
在一个事物之生成和变化的根据即与其有着非依赖的协变关系的诸事物均内在于其本性之中这样的意义上,郭象自然可以接受如下说法:事物均是“自本自根”(《庄子集释·大宗师》,第225页)的。但是,如果将“本”、“根”理解成原因或来源,那么郭象则不接受这种说法。请比较如下注文:“欻然自生,非有本。欻然自死,非有根。”(《庄子集释·庚桑楚》,第70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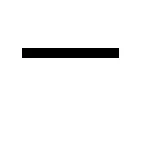
最后,正如前文所言,圣人为普通人所提供的那种逍遥条件(任其性分)显然不可能是其逍遥的原因,而只能看成此种逍遥的根据,或者说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