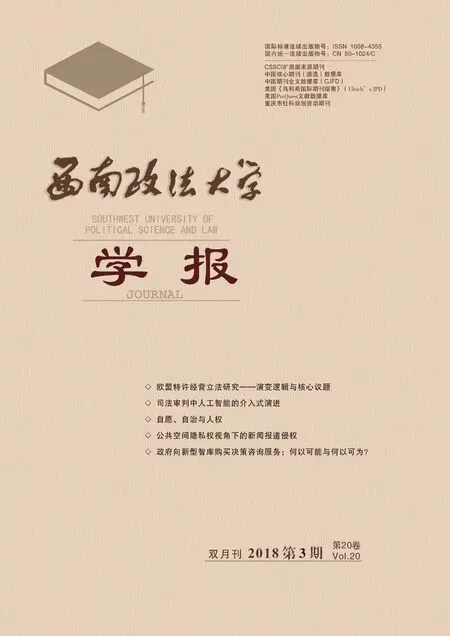侵权损害完全赔偿原则之新阐释
(南京大学 法学院,南京 210093)
一、问题的提出
侵权损害赔偿领域学说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观点层叠不穷。由理论源头俯视开来,似乎乌云密布,令人眼花缭乱,难以理清侵权损害赔偿的要义。学界通说认为,在侵权损害赔偿领域应当秉持对受害人救济的理念,遵循完全赔偿原则,运用“差额说”的损害计算方法,通过“全有全无”的方式来确定侵权损害。然而,随着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传统模式在对受害人的救济和对加害人的平衡两端都出现了新情况。在具体案例中,因为因果关系证明的难度,受害人往往不能得到救济;而因为客体的偶然高价值性,加害人赔偿后往往陷入生计困难。因此,对完全赔偿原则的否定之声开始出现,其中呼声最高的当属“概率因果关系”“损害酌减制度”和“动态系统论”,但是三者是否真能承载起修正或替代完全赔偿原则的重任呢?
我国民法学理论研究中没有放弃“拿来主义”方法,主张直接借鉴比较法上有益的经验,以此来变革或修正我国民法上的相关制度理论*借鉴比较法是我国现阶段民法研究的一个主要方法,但是借鉴的限度为何?本土化如何展开?这些问题亟需结合我国现有实证法和判例进行展开。。诚然,从解决问题的方向上来看,该种方法确实有可取之处,但是从本土的适应性和解释论的妥当性来看却稍显不足,往往会出现矫枉过正的现象。针对侵权损害完全赔偿原则,我国学界对之已经形成检讨的思潮,但是究竟是重新换一件“衣服”,还是打上几个“补丁”,却莫衷一是。因之,下文主要的任务是,在梳理侵权损害赔偿范式转变的基础上,对相关修正方式进行全面反思,并以此为契机,对我国侵权损害赔偿原则进行新的阐释,以期能对司法实践和理论发展有所裨益。
二、侵权损害赔偿范式的转变
(一)“损害填补”下的传统模式
《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针对侵权行为揭示了加害人负有填补损害的责任,其判例也一致认为,损害赔偿是旨在使受害人能够再处于如同损害行为未曾发生的情况[1]。《德国民法典》第249条对损害进行了一般性规定,认为应恢复到损害没有发生之时的状态[2]。整体把握来看,法国法的判例和德国法的明文规定,均确立了对受害人之损害进行填补。英美法虽然在表述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也依然遵循着上述恢复到损害未发生之时的理念[1]16。在“损害填补”思想的主导下,比较法上确立了完全赔偿原则,德国法更进一步采纳了蒙森(Mommsen)所确立的“差额说”,认为损害就是受害人在侵权事故中所损失的利益,而利益乃是受害人的财产状况,也就是侵权事故发生与没有发生侵权事故所形成的差额[3]。针对差额的确定,德国法上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观点。《德国民法典》生效不久之后,“差额说”就被认为是一种简单的“算数运算”,也就是确定物品的货币价值,损害赔偿的确定是通过两次状态的货币价值差来确定的[4]。但是德国法院却认为,“差额说”实际上是与货币价值无关的算数运算,应当进行规范控制,必要的时候还需要进行修正*相关判决理由论述参见:NJW 1987, 50.。尤其是在一些损害无法通过简单的状态差额来确定的时候,例如使用价值的减少、非财产价值的损失等。出于上述考量,德国法在“差额说”的基础上发展出“规范补充”理论,来弥补损害赔偿法上的不足,德国法称之为双轨制[2]Rn.22。但是无论学说如何进行修正,德国法仍然在坚持着“全有全无”的完全赔偿原则,只要是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原则上应当予以救济,恢复到损害未发生之状态。
其实传统理论的完全赔偿原则,并非是“全有全无”四个字所能涵盖的,其更加核心的内容应当是,只要和加害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损害,就应当获得赔偿。因此,与其说完全赔偿原则是损害层面的问题,不如说它是因果关系层面的问题。根据因果关系“等值理论”,如果没有加害人的行为,损害就不会发生之时,那么加害人就应当对该种损害承担责任。虽然“等值理论”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存在一定的缺陷,需要通过替代因果关系、超越因果关系和累积因果关系等理论来弥补,但是它仍然可以作为作为确定损害赔偿的第一步。但是“等值理论”对于责任的认定显得过于宽泛,其仅仅对责任判断具有过滤作用,如果不对损害进行限定,那么加害人必须对受害人所有的损失进行赔偿。为了不让加害人承担与其侵权行为不成比例的责任,也避免责任过量对加害人造成不利,合理的限制责任显得极为必要[2]Rn.104。因此传统理论区分了责任成立和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前者主要来确认行为和损害之间是否具有关联,而后者则用来确定赔偿责任的范围。根据自然法则,无边无止境的损害和加害行为之间均可能存在因果关系,而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就需要对此予以限制。传统理论针对责任的限制,发展出“相当因果关系理论”,认为只有和加害行为存在相当性的损害,并且处在法规所保护的范围内,才可以获得赔偿[2]Rn.107。
传统理论在处理损害赔偿范围之时的核心要素是因果关系,在处理技术上,实际上是加害行为和损害交互的模式,而因果关系则担当着桥梁的作用。以一个观察者的视角来审视侵权损害案件,最先呈现出来的是加害行为和损害。对于加害行为的理解,基本上通过确认是否违反相关义务,并辅之以作为和不作为的区分,可以清晰地呈现出加害行为的具体轮廓。而对于损害则存在不同的情形,如果是间接损害,因为间接损害本身具有弹性,需要通过因果关系来确定损害的范围,该种损害实际上是抽象的,由法官根据可预见性和相当性来确定损害到底应该是多少。而如果是直接损害,或者说是具体权利的损害,此时损害虽然也具有一定的弹性,但原则上均是先确定具体权利前后状态的差额,再判断具体损害和加害行为之间进行是否具有相当因果关系,是否属于法规所保护的损害。传统理论饱受诟病的“全有全无”模式,主要是在积极损害层面上所体现,也就是说在加害行为和损害之间,判断是否存在相当因果关系,如果因果关系的概率超过50%(有的国家可能要求更高),则认为加害行为和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该损害就应当得到救济[5]。而如果加害行为和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是49%(或者更低),此时不能认定因果关系的存在,因此对于损害全部不予救济。除此之外,传统理论仅仅考量侵权损害赔偿内部要素,而不考虑相关外部要素,侵权行为的特殊性、加害人和受害人自身的经济情况、损害的超巨额性和加害人的违法性程度等均不再予以考量。加害人必须对其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但是其也仅仅赔偿其造成的损害,这应该是传统理论最好的表达。
(二)“多元考量”下的变革模式
传统理论具有很强的体系完美性,也能适用于绝大多数案件,但是在某些特殊案件中,却显得捉襟见肘,难以给出让人满意的答案。现代侵权法不仅仅主张以救济为损害赔偿的价值,还认为公平、惩罚和弱者保护等均为损害赔偿的价值归宿。侵权完全赔偿原则在现代民法中,在三个层次上受到挑战:第一个层次是内部因素的“反水”;第二个层次则是外部因素的“攻击”;第三个层次是内外部因素的重新整合。
首先是内部因素的“反水”。因果关系理论认为,与加害行为有相当性的损害应当全部赔偿,与加害行为不具有相当性的损害则无需赔偿,该种处理方法在概率因果关系理论兴起之后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学者们认为,因果关系为51%之时,全部需要赔偿,而因果关系为49%之时,则全部不予赔偿,是极其荒谬的[1]105。在反思的大潮下,一种全新的理论似乎呼之欲出,这就是“概率因果关系理论”。20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的法学教授Joseph King提出的“生存机会丧失理论”和美国加利福尼亚法院在“Sindell v. Abbotts Laboratories案”中所确立的“DES-市场份额责任”,即为概率因果观点的典型代表*参见:Joseph·H·King. “Reduction of Likelihood” Reformulation and Other Retrofitting of the Loss - of - a - Chance Doctrine[J].The University of Memphis Law Review, 1988:492-493;Supreme Court of California, Sindell v. Abbotts Laboratories, 607 P.2d 924, 936 (Cal 1980).。“生存机会丧失理论”是指,如果医生谨慎地治疗,则患者的存活概率为80%,而因为医生的过错行为,导致患者最终的存活概率为70%,并且患者最终没有存活。此时如果按照传统理论,很难认定医生的过错行为和损害之间具有相当因果关系,因为医生过错行为下存活概率仍然有70%,而即使医生谨慎治疗,患者的存活概率也仅为80%,此时是否需要赔偿,以及如何确定赔偿额,都是理论难点[6]676。“DES-市场份额责任”则是孕妇服用了一种名为DES(Diethylstilbestrov, 己烯雌酚)的保胎药,多个厂家都生产了可能导致胎儿出生后患癌症的保胎药DES,无法确定孕妇究竟服用了哪一家产品。此时按照传统的共同危险理论,采取证明责任倒置,在各个厂家不能举证之时,由所有厂家承担连带责任,但是法院认为该种操作不恰当,而是按照市场占有率判决了比例责任*参见:Supreme Court of California, Sindell v. Abbotts Laboratories, 607 P.2d 924, 936 (Cal 1980).。在这些案型的反思中,学者们认为必须重新审视因果关系和损害的概念,通过概率因果关系理论,跳出“全有全无模式”,因果关系的概率是多少,加害人就应当赔偿多少损害。
其次是外部因素的“攻击”。完全赔偿原则和自然的个人无限责任密切相关,原则上个人需要对全部债务进行清偿,传统民法中只存在少数例外,仅仅出现在劳动法和交通事故法领域,通过保险的补偿来限制个人的无限责任。然而,司法实践中经常会发生与“天价车案”或者“未成年人侵权案”相类似的案件,从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内部因素来看,损害是由加害人造成的,无论是过错还是因果关系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仍然坚持让加害人承担全部责任,易于让其陷入生存困难之窘境,于法价值的考量上,着实存在不妥*参见:朱斌,林智.雅阁撞劳斯莱斯敲定赔35万个人赔18.8万[EB/OL] .(2012-02-07) [2018-03- 15].http://auto.sohu.com/20120207/n333996951.shtml;韩泽祥.任丘两女童玩火致木材市场“火烧连营”[EB/OL] .(2011-12-01) [2018-03- 17].http://roll.sohu.com/20111202/n327612782.shtml.。比较法上各个国家或地区也均注意到了上述问题,法官在处理案件之时,原则上会对上述因素予以考量。新近更有许多国家在司法和立法中确立了“损害酌减制度”。例如,在德国法中,虽然《德国民法典》中不存在“损害酌减”条款,但德国法院并不会出现让个人承担超过其支付能力范围的无限责任,因为德国宪法在强制执行等领域对自然人给予了保护[2]Rn.14f。瑞士法和我国台湾的相关“法律”则采取了与德国不同的模式,其在民法规范中对“生计酌减”制度予以了规定,如《瑞士债务法》第44条第2款和我国台湾“民法”第218条均认为,如果损害非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赔偿额如果对生计产生重大影响之时,法院可以减轻其赔偿额*《瑞士债务法》第44条第2款规定:“如损害赔偿义务人并非以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损害者,且将因给付损害赔偿而陷于窘困之状态者,法官得基于此等理由,对于损害赔偿义务进行酌减。”我国台湾“民法”第218条规定:“损害非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所致者,如其赔偿义务人之生计有重大影响时,法院得减轻其赔偿额。”。此外,比较法上针对未成年人赔偿问题,也对完全赔偿原则予以了限制。早期《德国民法典》中并不存在对未成年人责任限制的条款,学术界认为这应当属于联邦宪法法院的任务。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具体案例中认为应当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保护,在裁定中,认为应当借助于《德国民法典》第242条诚实信用原则来限制未成年人的责任*相关具体案情解释参见:NJW 1998, 3557.。在德国2002年债法改革之时,改革委员会对《德国民法典》第828条进行了修正,认为在汽车、有轨交通工具或悬空缆车的事故中,已满七周岁但未满十周岁的人无需承担责任。
最后是内外部因素的重新整合。内部因素重新整合的观点认为,只要确定了相关机会存在的概率,或者确定了因果关系达到一定程度,即可在此基础上综合考量其他因素确定行为人的责任范围[7]172。该种观点在理论上又划分出两个阵营,一种认为侵权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应当打破传统因果关系的门槛,在个案中通过被侵害利益保护力度、行为正当化程度、因果关系贡献度、过错程度等要素的综合评价,来确定损害范围[8]155。另一种则认为侵权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不应当打破传统因果关系理论的筛选功能,其他因素仅仅应当在责任范围初步厘定之后发挥作用,综合考量以确定最终需要承担的责任[9]61。上述两种观点,在立法上最典型的体现就是根据过失程度来确定损害赔偿范围。采赔偿数额与过失程度相符原则的立法例肇始于受自然法影响的1776年《普鲁士联邦法》,以及1867年《荷兰民法》[10]309。现今采取该种立法例的主要有《瑞士民法》和《奥地利民法》,其中《瑞士债务法》第43条第1款规定:“就所发生之损害其赔偿之种类及规模,由法官决定之,法官须就案例情状及过失之规模评断之。”《奥地利民法》与上述思想一致,也认为损害赔偿范围,取决于损害赔偿义务人的过错程度。我国民法中并不存在上述明确规定过错程度对损害赔偿产生影响的条文,学者们主要探讨分析的是《侵权责任法》第26条、第27条和《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2条第1款所确立的“与有过失”制度。学者们在该条的基础上认为,传统的完全赔偿原则的适用只取决于受害人的损害,而未充分考量行为人的过错程度,存在一元单极化评价的不足,而“与有过失”所揭示的“损害取决于过失程度”的理论很好地兼顾了加害人和受害人主观层面,有助于实现法律的实质正义[7]161。
(三)范式转变的评析
损害赔偿范式的转变,实际上是损害赔偿理念转变的外部表征。早期损害赔偿法注重“损害填补”功能的实现,秉持加害人的行为和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之时,就应当对其所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民法在损害赔偿法领域,不仅关注损害填补,还逐步导入了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比例原则。损害赔偿法在一定程度上担负着实现社会正义的功能,尤其是实现矫正正义,因此多价值的融入必然导致损害赔偿理念的转型。通过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内外部考量,打开损害赔偿完全原则的枷锁,确实符合侵权法发展的趋势,但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是否可以通过内部的自我修正,避免枷锁的完全打开?如果真的要突破传统,又需要在多大程度上摒弃?不得不承认,完全赔偿原则在理论的发展上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如果全面否定完全赔偿原则,又有什么理论能重新建构起损害赔偿法大厦呢?单纯的摧毁不应是法学研究的方向,反思后的修正和重构才是学者们应尽的义务。学者们所支持的新近理论,其外部形态上确实向我们展示了良好的正义区分理念,但是在具体操作上,相关制度价值到底如何,可适用性如何,这些都是需要反思的。
三、完全赔偿原则的修正与反思
(一)概率因果关系
传统理论在因果关系上坚持“相当因果关系理论”,认为加害行为和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相当性之时,加害人需要对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关于相当性的认定有不同的标准,但是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至少要达到盖然性以上的程度。不可否认,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也只能通过概率对未来的状况进行预测。在法律因果关系的确定上,由于时间的复杂性,因果链的漫长性,人们预测因果关系的难度也不断地增加,再加上法律关系的体系越复杂,因果关系就变得越宏观,判定的难度也就更大,司法实践中针对某些特定案件,想要调查清楚因果关系的具体程度就存在更多困难[11]。尤其是在环境侵权、医疗侵权和产品侵权案件中,由于技术的复杂性,因果链的不确定性,让受害人承担证明责任,证明加害行为和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比较法上许多国家采用降低证明标准的方法,以此来缓解受害人举证的压力,而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6条也确立了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倒置。但是该种方法,仍然存在缺陷:一旦降低证明标准或者举证责任倒置,加害人也很难举证免责,这就等于把因果关系不明的全部风险转嫁给了加害人。虽然加害人在多数情形之下是强势主体,但是不恰当地加重其负担,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加害人仍然会将损失再次转移,该种做法反而增加了社会成本,阻碍了经济的发展[12]。
无论是DES案例还是“生存机会丧失理论”都揭示了因果关系的不确定性,或者说加害行为和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达到相当性要求,而此时如果仍然坚持对损害全部赔偿,显然加重了加害人的责任;如果认为因果关系相当性不足,让加害人不承担责任,似乎又难以发挥侵权法的救济功能。比较法上针对上述情况,发展出概率因果关系理论,并进一步衍生出比例责任。最为典型的如《瑞士债务法》第43条第1款规定:“就所发生之损害其赔偿之种类及规模,由法官决定之,法官须就案例情状及过失之规模评断之。”*对于《瑞士债务法》第43条第1款,在教义学上有的学者认为其是概率因果关系理论的基础,有学者认为其是动态系统论的基础,这也正是该条的弹性所在。因而在瑞士法上损害并没有严格限定为具体权利的差额作为损害,法官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对损害的规模进行酌定。虽然瑞士法仅明确提到了过失对损害规模的影响,但在实务中并没有仅仅限于过失。瑞士学者认为,法官在确定实际的损害赔偿额时,不仅仅只考虑过错程度,否则会陷入一方面强调救济,另一方面又强调惩罚自相矛盾的局面[13]Rn.24。因此针对该条,瑞士法在实践中也会考虑过错之外的其他因素,而其他因素在何种程度上影响最终的实际赔偿额确定,则由法官综合考量来决定。就此瑞士法虽然表述为法官可以对损害范围进行裁量,为法官在特定情形下突破“相当因果关系理论”提供了教义学支撑,但是损害范围的确定,仍然是将各个因素统合到因果关系理论中来解决的,否则损害的确定缺乏正当性基础。只不过,瑞士法接纳了加害行为和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可能性是多大,加害人就应当赔偿多少损害的观点,所以瑞士法对损害的分析上仍然需要找准着力点,而担当该着力点的理论应当是概率因果关系。
德国法中并不存在类似于瑞士法的明确规定,而且《德国民法典》第823条和第826条,确立了权利和利益区分保护的模式,原则上侵权法保护的客体是权利,利益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给予保护[12]。损害的具体计算,需要根据具体客体的不同状态下的差额,此时如果仍然坚持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对于加害行为和整体损害的因果关系只会产生“有”和“无”的判定,不存在概率因果关系适用的空间。德国学者为了克服上述障碍,在类推《德国民法典》第830条第1款第2句“共同危险”案型的基础上,结合《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87条,法官在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对损害的数额进行自由心证,因而德国法可以借助程序法对损害重新界定[6]682。在损害自由心证的基础上,再引入“概率因果关系理论”,从而能够突破传统的“全有全无”模式,在特殊案型下,通过对损害进行规范性评价,对加害人予以合理救济[15]。不难看出“概率因果关系理论”实际上是通过对损害和因果关系的重新定位,突破了传统理论的束缚,在仍然坚持侵权责任构成理论的基础上,对损害进行规范性评价,重新审定损害的内容,以及损害的范围,为因果关系的可能性和相应损害的对应性打通媒介。
那么现在需要反思的是,“概率因果关系理论”和传统的完全赔偿原则冲突吗?以及损害赔偿是否需要通过“概率因果关系理论”全面打开?上文提及,完全赔偿原则最核心的要义应当是,与加害行为有因果关系的损害都应当予以救济,与加害行为没有因果关系的损害则不应给予赔偿。“概率因果关系理论”并没有偏离上述要义,其相较于“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反而更加强调对和加害行为有因果关系的损害应当进行赔偿。“相当因果关系理论”认为,当加害行为和损害之间的关系符合条件说,并且符合相当性判断之时,就应当予以赔偿,忽略了一部分具有因果关系但无法达到相当性的损害,从这个角度来看,“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并非是“完全赔偿原则”的完美贯彻者,反而遗漏了一部分需要考量的损害。相反,“概率因果关系理论”在特殊案型中,并不囿于“损害差额说”的限定,而是对损害进行规范性评价,由法官根据因果关系的概率来确定相应的损害,仅赔偿和加害行为具有概率因果关系的那部分损害,从这个角度,其反而更好地贯彻了完全赔偿原则。
而针对是否有必要全面引入“概率因果关系理论”,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笔者认为没有必要。传统型侵权,原则上因果关系并不能完全通过概率来呈现,很难像理论设计那样精确到某个具体的数字,如果贸然全面引入概率因果关系,反而会增加司法实践的操作难度。根据法官对案件的事实查明情况,如果符合相当性,加害人则应当对损害承担责任,而如果不符合相当性,则无需承担责任,此种选择,符合人类认知的价值判断。只有在法官认为案件因果关系相对复杂,并且能够以概率衡量的情况下,通过自由心证,并且论证说理之后,才可以引入“概率因果关系理论”,借助相关条文对损害进行规范性解读。同时该种比例因果关系就算在上述特殊案型中,也应当仅仅作为一种补充,在概率达到盖然性之时,没有必要仍通过概率来确定责任,应当重新回到相当性之判断。正如我国台湾学者在处理因果关系不明案件时主张的做法:如果可能性超过一定比例之时,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甚至只要达到51%以上之时,此时是就无需按照比例责任来确定赔偿范围,而应当直接全部赔偿[16]。因为在人文科学领域,要求某个因果关系论证达到100%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达到90%也是很困难的,如果加害行为和损害之间已经具有盖然性或者高度盖然性,此时没有必要再引入概率因果关系。画蛇添足,反而削弱对受害人的救济,影响侵权法预防和救济功能的实现。
(二)损害酌减制度
虽然侵权损害赔偿本身应归属于救济层面的问题,不应包含对加害人的社会照顾,但是司法实践中,如果严格贯彻完全赔偿原则,可能会导致部分加害人陷入生存困难,同时也会偏离社会公平之理念。高额的债务可能使加害人面临生活之窘境,以至于无法继续维持生活,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43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5条均规定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民事诉讼法》第243条第1款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5条第2项:“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下列的财产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所必需的生活费用。当地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必需的生活费用依照该标准确定。”。但是该种措施并不当然消灭债务,如果被执行人日后重新获得财产,仍然需要被执行,其实这样并没有缓解债务人生活窘困之情境。除此之外,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一些案例,加害人如果对损害全部给予赔偿,并不会陷入生活之窘境,但是却会出现违背社会公平之理念,如“好意搭乘案”和“见义勇为案”等。“好意搭乘案”是指甲应乙之邀请驾车带乙一同前往乙家聚餐,行程中由于甲的疏忽发生车祸,使得乙遭受重伤产生损害*参见:陈章群.“好意同乘”发生交通事故 搭乘者的损失谁赔偿?[EB/OL] .(2016-06-28) [2018-03- 18].http://news.sina.com.cn/o/2016-06-28/doc-ifxtmses1326621.shtml.。而“见义勇为案”则是指甲见义勇为救乙,但是在施救过程中因为自己之过失导致乙人身和财产遭受损害*实务中经常有人见义勇为,由于施救行为不恰当导致被救人财产和人身损失,比如手表或者衣物毁坏。。虽然案例中甲本属于好意施惠和见义勇为的范畴,但是因甲的过失造成损害,甲的行为和损害之间因果关系,因此甲应当对全部损害予以赔偿。但好意施惠和见义勇为毕竟是社会所鼓励之行为,如果行为人从事上述行为之时,存在过失造成相应的损害,仍然让行为人承担全部损害,似乎并没有将社会所鼓励的行为和一般加害行为区别对待,无法与社会公平之理念相符,不利于鼓励“好意施惠”和“见义勇为”。因此,较为妥当的做法是,在考虑具体案情,以及加害人和受害人经济状况的基础上,由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予以适当酌减,方能符合社会公平理念的需要。
损害酌减制度其本质定位不应当是侵权责任本身所产生的问题,有学者将损害酌减制度扩充自整个损害赔偿领域,以之所谓损害的规范性评价命题来展开,其存在一定的不妥之处。比较法上无论是《瑞士债务法》第44条第2款,还是我国台湾“民法”第218条均规定,如果损害是赔偿义务人非以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并且如果给付赔偿会导致加害人陷入困窘的境地之时,法院可以径行酌减,从该层面来看,损害酌减并非是规范层面对损害的评价,而是例外性地对不合理的赔偿责任予以限制[10]370。荷兰法要相较于瑞士法和我国台湾的相关“法律”走得更远。《荷兰民法典》第6编第109条仅将损害酌减限定为“全额赔偿会造成无法接受之后果”,其损害酌减的适用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充,因此荷兰法上不仅仅可以包含“生计酌减”,也能容纳“公平酌减”。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荷兰法也仅仅是赋予法官在特定情形下酌减的权利,并非作为一项义务,仅仅为法官用来处理例外情形的案件。近代民法中,大量严格责任不断被确立,过错责任和严格责任并存的局面已经形成。严格责任侵权往往伴随着大规模侵权的发生,如果仅仅借助于《破产法》来实现对严格责任者的衡平,那已经是杯水车薪,难以缓解加害人消亡的危险。损害酌减制度的确立,可以较好的缓解严格责任侵权所导致的巨额债务和破产危险。
那么损害酌减制度是完全赔偿原则的例外吗?德国法早期在限制未成年人责任之时,多次恳求联邦宪法法院对宪法进行解释,并以此为基础来限制未成年人的责任承担。德国宪法法院最终认为,应当根据《德国民法典》第242条诚实信用原则,对未成年人责任进行限制,以体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2002年德国新债法改革之时,对《德国民法典》第828条第2款进行了修改,在特定的领域对未成年人的责任予以限制。比较法上许多国家或地区则选择了一个更加直接的方式,在其民法典中对“损害酌减”制度予以规定,有的国家规定了“生计酌减”,有的国家既规定了“生计酌减”,又规定了“公平酌减”。针对见义勇为的损害减免,比较法上还确立了一种“违法性阻却事由”的立法模式,如《德国民法典》第680条,针对紧急无因管理救助人的责任表述为“惟有故意和重大过失可以归责于管理人”。《日本民法典》第698条和我国台湾“民法”第175条也采取了类似于德国法的规定,认为除非有故意和重大过失,其他情形不承担责任。祖国大陆新近出台的《民法总则》第184条也采取了上述模式,直接免除了救助人一般过失和重大过失的责任。上述通过“违法性阻却事由”来免除责任的模式,虽然便于操作,但是稍显弹性不足,不利于个案考量。比较法上还有国家或地区采取了另一种模式,如《意大利民法典》第2030条规定,紧急无因管理,也就是见义勇为情形下,根据救助人的特殊情况,法官可以降低其因为过失所承担的责任。《法国民法典》第1374条和《瑞士债法典》第420条则采取了与意大利类似的方法,赋予法官酌减的权利。
但是所有的上述规定模式并没有一般化的趋势,仅仅是作为例外的规定,而且也没规定法官有义务依特定之情形予以酌减,仅仅用“得”,或者“可以”来赋予法官考量选择权[17]351。损害酌减制度本身并不涉及损害赔偿制度,其仅是损害赔偿法外部的考量制度,出发点是宪法所确立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以及自然法中“公平正义”原则的现代化,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应当保障上述权利和价值的实现,司法判决也应当考虑到上述权利和价值的维系。从这些角度来看,损害酌减制度并非是完全赔偿原则的否定,其仅仅是在完全赔偿原则基础上进行的修正,在承认完全赔偿原则正当性的前提下,针对某些特殊或者极端的案件予以外部矫正。也正是因为需要坚持完全赔偿原则,才要在外部发展出损害酌减制度,本质上属于自然法和公法对私法的介入。
(三)动态系统论
针对完全赔偿原则在某些案件中结论的缺陷,学界有一种理论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完全赔偿原则展开了攻击,并且担当其建构的角色,这就是“动态系统论”。“动态系统论”是奥地利学者威尔伯格提出的,其以损害赔偿法为例,展示了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动态的责任基础。在个案中,根据具体出现的各个要素数量以及丰富度来进行综合考量,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8]164。该种思想被奥地利学者考茨欧在《欧洲侵权法原则》中广泛应用,无论是在保护利益的范围(第2:102条)、责任范围(第3:201条),还是在注意义务的认定(第4:102条)上,都采用了“动态系统论”的方式*相关条文表述可参见:欧洲侵权法小组.欧洲侵权法原则:文本与评注[M].于敏,谢鸿飞,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在受比较法的影响下,我国学者也开始主张引进“动态系统论”,并以此为契机对完全赔偿原则进行解构。有学者认为,个案中应当由弹性的价值评价体系来确定损害的范围,通过构成责任基础的全部价值的不同强度来实现法律效果的弹性化,突破“全有全无”模式[8]172。在此基础上,学者们认为加害人的责任范围取决于裁判者对于过错、违法性、因果关系等责任构成相关要素的综合考量和整体评价,通过弹性化法效果来实现法律适用的精准化[7]173。而具体运用“动态系统论”的方式又分为两种,第一种直接跳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或者将相关要件当做要素,运用“动态系统论”对损害进行规范性评价,构造出损害和损害额的区分[18]。第二种则并不主张跳出传统的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在要件内部运用要素发挥作用,或者在责任构成之后,对损害通过“动态系统论”进行二次确定[9]61。
不可否认“动态系统论”确实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其在比例原则的辅助下,展现出民法所追求的公平正义,为我国大部分学者所支持。但是需要谨慎的是,如果只是追求法效果的弹性化,或许通过原则或一般条款来实现价值的自由法学,相较于“动态系统论”更能吸引学者。因此,一直以评价法学自称的“动态系统论”并不意味着在给出一定的考量要素后就听凭判断者去自由判断,“动态系统论”本身也追求法的安定性,主张通过评价来实现基础评价[19]。但是如果在立法上不对侵权责任构成要件进行具体规定,将损害的范围、类型的界定完全交给法官,极有可能导致判例不统一的后果,其复杂、灵活的程度,大大超出了我国法院所能允许的限度*有关学说的观点参见:王利明,周友军,高圣平.中国侵权责任法教程[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77;葛云松.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与一般侵权行为条款[J].中外法学,2009(5):730.。除此之外,第一种对动态体系的运用,已经跳出损害的基本限定,不受因果关系约束,完全将损害上升到规范评价,其在没有条文约束的情况下,很容易游离为自由法学。此外,动态系统论所强调的要素评价,每一个要素的选取,每一个要素的评价,都是十分复杂的,并不存在统一的要素类型谱,完全靠法官在个案中发挥作用,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综合评价,其渗透着法官的自由心证,说理论证部分难以统一,反而加剧了个案的不公平。
而针对第二个层次使用“动态系统论”而言,如果其仅仅是在要件内部进行要素判断,其完全是在辅助传统理论,传统理论也是需要结合多方面因素考量,来确定某个要件是否成就,并在要件成就的基础上推导出法效果,就此而言该理论并未超越传统理论。而如果单纯的对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中的过错要件进行单独特别评价,如《瑞士债务法》第43条第1款和《奥地利民法典》第1324条均认为赔偿范围应当与过错程度相符,损害的数额首先确定,其实是损害赔偿的上限,过失的程度大小,将用来决定损害赔偿酌减的幅度[13]Rn.838。该种操作实际上混淆了主观过错和因果关系的功能,近代欧陆民法主观过错层面对损害范围确定的可预见性已经被移植到因果关系层面,通过相当性理论发挥作用,如果再次将损害范围的确定回归到主观过错层面,可能需要理论的重新建构[20]。在没有重新建构之前,在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基础上,通过确定赔偿额上限,再通过过错程度和其他相关因素来确定具体的赔偿数额,其尽管彰显了侵权法的“预防功能”,但却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救济功能”。瑞士就有学者批评道,如果在侵权损害赔偿上,损害赔偿取决于加害人的过失程度,事实上将损害赔偿和刑法的形式结合在一起,回到了惩罚和损害赔偿不分的状态[13]Rn.831。
此外还需要谨慎的是,如果在侵权责任构成的基础上,重新利用相关要素对损害赔偿范围进行确定,还存在二次评价的可能性。无论是过错程度,还是违法性程度,其在侵权责任是否构成之时,已经在因果关系相当性的判断上发挥作用,过错程度越大、违法性程度越大,因果关系相当性程度也就越高。如果在责任成立的基础上,再次引入过错程度的判断,加害人因为过错程度较低,就仅需对一部分损害承担责任,受害人将会因为加害人的过失程度较轻无法获得赔偿。在此情况下,会造成受害人需要自己承担加害人无需承担的部分,这对于在个案中根本不存在过失的受害人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13]Rn.830。我国学者一般会利用《侵权责任法》第26条、第27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1款所确立的“与有过失”制度,来论证过失程度对损害赔偿额的影响[7]160。该种论证存在不恰当性,“与有过失”制度主要是建立在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关系上,其本身是损失分担条款,而不是“损害赔偿和过错程度相符”条款。该条款主要是解决加害人和受害人对损害发生均具有过错时,原则上加害人和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需要承担全部责任,但是受害人对损害发生也具有因果关系,也应当承担全部责任,二人和损害的发生具有共同因果关系,二人均需对损害承担责任,此时内部责任外部化,没有必要进行一个繁琐的给付再偿还的过程,直接根据双方的过错比例来确定最终的赔偿额,该种思想也并未违背完全赔偿原则[17]310。
四、完全赔偿原则的全新阐释
(一)损害赔偿价值的重申
随着社会的发展,案件的复杂性程度增加,越来越多的因素需要法官予以考量,单纯的确立起原则性的损害赔偿条款必然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在极端案件中需要纳入侵权主体的过错程度、被侵害利益的保护力度、经济状况和因果关系的贡献度来综合评价,但这毕竟是极端案件,缺乏一般化的正当性基础。无论是完全损害赔偿原则的支持者,还是完全损害赔偿原则的批判者,大家所秉持的价值都是公平正义,必须承认公平正义的判断需要借助于价值的类型谱来理清轮廓,但是在不同的案件中,相关价值衡量的位阶本身就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统一地打开完全赔偿原则存在让法官自由裁判的风险。侵权损害赔偿实际上走了一条从以制裁、惩罚为目的——到以损害填补、救济为目的的道路。如果此时,过多的引入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本身以外的因素,虽然形式上是在追求个案的公正,但一旦全部打开之时,必将会破坏法律的安定性和确定性,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难以估量。
完全赔偿原则被冠以“全有全无”名称之后,被一部分学者给妖魔化了,其实原则本身并无任何瑕疵,只是操作方法的处理上,可能让该项原则走向极端。完全赔偿原则最为核心的要义是,与加害行为有因果关系的损害应当全部得到救济。言外之意,与加害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损害不应当予以救济。我国学者在批评《侵权责任法》第87条涉及的高空抛物案件时,认为行为人和损害之间可能没有因果关系,甚至行为人可能没有加害行为,就让潜在的行为人承担责任是十分荒谬的[21]。以此来判断,如果在侵权损害赔偿中,淡化因果关系的作用,通过其他要素的协同来完成责任范围的确定,其正当性基础是否能够得到认同,殊值怀疑。我国学者认为侵权损害赔偿的功能主要有如下三种,分别是补偿功能、预防功能和惩罚功能[17]25。必须承认,侵权法必然对侵权行为进行预防,对欺诈销售的侵权行为进行惩罚性赔偿,以及维护行为的自由,但是上述功能仍然不能上升到和补偿功能并驾齐驱的地位,也无法做为一个基础价值屹立于侵权法中*这里需要注明,因为文章在相对传统的领域反思完全赔偿原则,并没有对惩罚性赔偿进行展开,但是必须承认惩罚性赔偿制度和完全赔偿原则也存在较大关系,笔者拟另文展开。相关介绍也可参见:朱广新.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演进与适用[J].中国社会科学,2014(3):104.。如果过分地关注加害人的主观程度,淡化因果关系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使民法和刑法区分规制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因而,原则上虽然被告行为的性质和严重程度与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的判断相关,但与损害赔偿额的确定无关[22]。
完全赔偿原则所匹配的“差额说”并不一定要求将前后两个结果机械地相减,也不意味着所有事实上的损失都需要进行赔偿。虽然新近有学者提出,应当对损害进行规范性评价,但其实规范性评价也并不是什么新的命题,因为法律上的损害,从一开始就需要进行规范性评价[2]Rn.23。规范性评价一定程度上仅仅是一个流行语,并没有创造任何新的价值,其本来就贯穿在损害的确定之中。因此“差额说”实际上也是在因果关系相当性的规范评价下,来确定加害行为和损害具有相当性。损害的范围,并非一定是全部损失,在补偿功能的视角下,加害人造成了多少损害,就应当予以多少赔偿。在传统侵权中上述理论并没有受到挑战,但是随着新型侵权的不断发生,一方面侵权客体价值的高昂,另一方面因果关系难以判断,对传统侵权理论提出了挑战。“概率因果关系理论”和“损害酌减制度”逐步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但是这两项理论制度仅仅是完全赔偿原则具体化和外部修正,并非构成对完全赔偿原则的冲击,侵权法的补充功能仍然是未来发展的主题之一。因此在侵权损害赔偿领域,仍然应当坚持完全赔偿原则,并辅之以“概率因果关系理论”和损害酌减制度进行体系性建构。同时必须承认我国在立法上并无比较法上类似于瑞士法的直接规定,应当属于制定法的漏洞,因此需要解释论上进行构造,此时公平责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就可以发挥作用了。
(二)公平责任原则的引入
司法实践中有些案件的因果关系由于其侵权本身的特殊性难以查明,如医疗侵权、产品侵权和环境侵权等。这些侵权并不像传统侵权那样,存在典型的具有现实危险的加害行为,其从属于特殊侵权,无论是在归责原则还是因果关系层面都与传统侵权存在差别*参见:Supreme Court of California, Sindell v. Abbotts Laboratories, 607 P.2d 924, 938 ff. (Cal 1980);Supreme Court of Hawaii, Smith v. Cutter Biological Inc., 823 P 2d. 717, 724 (1991).美国法院适用概率因果关系也主要在特殊侵权中进行适用。。如果在这些侵权行为中,对于损害和因果关系的理解仍然坚持传统理论之时,受害人和损害结果之间不具有相当性因果关系,因而受害人难以得到救济。而如果为了救济受害人,不加区分地将证明责任倒置给加害人,加害人自己也很难举证证明自己和损害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此时仅可以确定加害人和损害之间具有部分因果关系,但是这种因果关系只是一种概率性呈现,无法达到相当性标准。在个案中,如DES案件和“生存机会丧失”案件中不予救济又显得十分不合理,因此有必要对损害和因果关系进行重新理解。上文介绍了比较法上通过法官对损害的自由心证,以期引入“概率因果关系理论”,这对我国侵权法来说实有借鉴的必要。
我国《侵权责任法》和《民事诉讼法》在条文上,既没有瑞士法实体领域的法官对损害的规模确定的条款,也没有德国法在程序法上确立的法官对损害自由心证的条文。但是,需要注意到,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条并没有采取《德国民法典》823条和第826条一般条款的模式,而是参考了法国法宽泛的保护方式,《侵权责任法》第2条也明确了我国侵权法的保护范围并不仅限于权利,而且还延伸到利益。因此在我国侵权法中引入“概率因果关系理论”,并没有传统大陆法系国家的障碍,主要有两条可供选择的路径。第一条是通过对《侵权责任法》第6条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中的因果关系和损害结果重新解读,由法官对损害进行相应的规范性评价,以引入概率因果关系。第二条则是通过原则性的条款辅助,在特殊案件之时,借助于特殊的侵权法基本原则,有条件地引入概率因果关系。在笔者看来第一条有全面打开因果关系理论的风险,在我国司法环境下很容易坠入自由法学,在没有案例制度的基础上,不宜贸然全部变革。第二条路径则相对比较折中,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4条确立了公平责任原则,其对于特殊案件,因果关系未达相当性,而结合具体案件特殊性需要救济之时,可以对损害进行酌定,引入概率因果关系理论来确定具体的损害*我国其实已经有学者在其他条文上注意到公平责任条款的作用,如杨会博士在论证安全保障义务人补充责任正当性之时,就运用到公平责任原则。(参见:杨会.论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补充责任的原因[J].河北法学,2013(7):92.)。
《侵权责任法》第24条确立了公平责任原则,虽然在条文的标注和适用范围上一直存在争议,但该条文在填补法律漏洞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学者已经发现我国的公平责任原则和德国法上的公平责任原则存在差异。(参见:张金海.公平责任考[J].中外法学,2011(4):758-773.)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公平责任原则是无过错损失分担的条款。(参见:杨代雄.一般侵权行为的无过错损失分担责任[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3):96-106.)当然我国也有学者反对公平原则作为一项归责原则,认为其仅仅有损失分担的作用。(参见:程啸.侵权责任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110.)笔者认为,公平原则在侵权法里实际上有“润滑剂”的作用,不应当仅仅停留在传统的轮廓,应当在“特殊案件”中发挥法律解释和续造的作用。。按照传统理论,加害行为和损害之间因果关系没有达到相当性之时,本来无需赔偿,但是在个案中如果不给予赔偿,不符合社会公平之理念,因此需要引入公平责任原则进行辅助解释。在特殊案件中,尤其是因果关系判断相对较为复杂的案件中,应借助公平责任原则,降低因果关系相当性的标准,对损害进行重新划分,以此引入“概率因果关系理论”。在这里公平责任条款实际上发挥的是类似于《瑞士债务法》第43条第1款和《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87条的作用,并以此为契机进行漏洞填补,在不破坏法律统一性的前提下,实现个案保护。但是需要谨慎处理的是,我国人民法院应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案例制度,针对特殊的案型,建立统一的指导案例,下级法院原则上应当参考上级法院在特殊案型上的操作,如果下级法院要突破上述限制,应当进行充分论证说理,充分考量各方面因素。
(三)诚实信用原则的引入
如上文所述,存在一些案件,虽然加害人和损害之间因果关系明确,按照传统理论应当予以赔偿,但是出于生计之需要或者出于社会公平之理念,不应当让加害人全额赔偿。比较法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构建了“损害酌减制度”,以此来规范损害赔偿高昂致使加害人难以维系生存需要和侵权赔偿导致社会公平破坏的情形,有的国家或地区虽然没有类似的条款,但是可以借助于判例或者原则性规定予以合理限制[23]71。虽然我国《侵权责任法》并没有对“损害酌减制度”进行明文规定,但是我国新近通过的《民法总则》在第7条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同时在第184条还确立了“好人条款”,认为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不可否认,上述条文和典型的损害酌减规定还存在较大差异,但是结合《侵权责任法》第1条开宗明义所确立的侵权法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精神,从保护个人的生存发展,以及维持社会公平的角度来看,我国司法实践应当在现有条文的基础上,通过解释论在侵权法中确立损害酌减制度。
在侵权法中,如果加害人的行为导致了巨额的损害赔偿,此时让加害人支付赔偿额,将会导致加害人重大生计困难,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有必要构建生计酌减制度。从比较法来看,基本上呈现出三种模式:第一种低度控制模式;第二种中度控制模式;第三种高度控制模式。低度控制模式是指,仅规定法官可以在特定的事由上予以酌减,但没有具体规定事由;中度控制模式是指,规定法官应考量某些事由,但是同时辅之以弹性的要件;重度控制模式是指酌减事由被严格限定在特定的事由上[10]351。自比较法来看,轻度控制过于宽泛,法官裁量权过大,有流于一般条款的风险;重度控制模式,仅将“生活窘迫”或者“生计重大影响”作为酌减的要件,于条文的弹性度不够,无法彻底弥补完全赔偿原则的不足。比较法上,荷兰采取的是中度控制模式,其在《荷兰民法典》第6编第109条规定了损害酌减制度,认为应当考量责任的本质、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当事人双方的支付能力和全额赔偿将造成无法接受的后果等因素,该种中度控制模式既保证了要件上的弹性,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酌减事由,不至于让法官陷入自由裁判不当的误区为各国所效仿。我国在没有条文的基础上,应当通过诚实信用原则的导入,构建类似荷兰法中度控制的模式引入损害酌减制度*我国司法实践中其实已经接纳了“公平酌减”制度,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第18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意见(试行)》第18条和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中院《关于处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有关问题的座谈纪要》第14条均确认了“好意搭乘”案件中,应当适当减轻好意施惠人的责任。。
从酌减类型上,我国侵权法中应当确立“生计酌减”制度和“公平酌减”制度来弥补完全赔偿原则的不足,但是这种补充需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并不是对完全赔偿原则的全面干预。首先,应当明确损害酌减是法官的一项权利,而不是一项义务,法院行使酌减权之时,并不受当事人申请的约束,只要有充足理由均可以进行酌减。其次,在酌减的幅度上,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酌定,但是不能完全免除加害人的责任,因此我国《民法总则》第184条“好人条款”的法效果确定上,不具有弹性,一律免除救助人的责任,恐有失偏颇[24]。最后,在损害酌减的限制性条件上,比较法上有将故意和重大过失排除的立法例,但是从损害酌减条文是为了保护加害人基本的权利和维系社会公平的角度来看,侵权法中基本人权的保护的价值应当高于惩罚价值,故而我国侵权法在综合考量的基础上不应一概将上述加害人排除在外[23]70。《侵权责任法》第20条规定针对侵害人身权法益无法确定的损害之时,法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酌定,第22条对精神损害赔偿进行了规定,上述条文均可以对受害人痛苦予以综合救济[25]。在财产利益领域,虽然没有条文明确规定法官可以适当酌减,在特定情形下,法官结合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也可以对赔偿额进行酌减。同时还应当注意,该种酌减应当是法院行使公权力的体现,当事人并无申请酌减的权利,仅能提出相关事由,供法官裁量之用。法官在适用酌减制度之时,需要进行充分论证,综合考量加害人债务情况和未来经济收入的可能性等因素,最终决定是否酌减,以及酌减的幅度。
五、结语
完全赔偿原则在现代民法中确实受到了多维度的挑战,但是在以“填补损害”为目的的侵权法功能体系下,该项原则并没有表现出退让,仅仅是以一种内外部自我完善的姿态出现。侵权法的预防功能和惩罚功能,虽然在现代侵权法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并没有上升到和补偿功能同等的地位。受学界所赞扬的“动态系统论”由于其自身的内在缺陷,不足以承担起重构损害赔偿法的重任,其仅仅能在既有理论的内部发挥补充作用。“概率因果关系理论”和“损害酌减制度”为损害赔偿领域带来了新的视域,完全赔偿原则通过内部自我修正和外部制度辅助,能够较好的容纳上述理论。我国侵权法领域一直贯彻完全赔偿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尚能合理平衡加害人和受害人的利益,需要注意的仅仅是在特殊案件中强化公平责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的辅助作用,以此来修正和弥补僵化地使用完全赔偿原则带来的不足。JS
参考文献:
[1] 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15.
[2] Oetker.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BGB § 249[M].München:Verlag C. H. Beck, 2016:Rn.11.
[3] Johannes W. Flume. Beck’scher Online Kommentar § 249[M]. München:Verlag C. H. Beck, 2017: Rn. 37.
[4] Stoll.Begriff und Grenzen des Vermögensschadens[M].Karlsruhe:Verlag C. F. Müller,1973:16.
[5] 韩强.法律因果关系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09.
[6] Stremitzer. Haftung bei Unsicherheit des hypothetischen Kausalitätsverlaufs[J]. AcP, 2008(Bd.208): 676-698.
[7] 郑晓剑.完全损害赔偿原则之检讨[J].法学,2017(12):157-173.
[8] 叶金强.论侵权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J].中外法学,2012(1):155-172.
[9] 邓辉,李昊.论我国生计酌减制度的构建[J].研究生法学,2015(3):52-63.
[10] 林易典.论法院酌减损害赔偿金额之规范[J].台大法学论丛,2007(3):305-384.
[11]Spindler. Kausalität im Zivil- und Wirtschaftsrecht[J].AcP ,2008(Bd.208):284.
[12] Posner.Economic Analysis of Law[M].5th ed.New York: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98:209.
[13] Roberto. Schweizerisches Haftpflichtrecht[M].Zürich: Schulthess, 2002.
[14] 方新军.权益区分保护的合理性证明[J].清华法学,2013(1):135.
[15] Wagner.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BGB § 830[M].München:Verlag C. H. Beck, 2017:Rn. 67.
[16] 陈聪富.因果关系与损害赔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04.
[17] 王泽鉴.损害赔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18] 王磊.论损害额酌定制度[J].法学杂志,2017(6):112.
[19] 解亘,班天可.被误解和被高估的动态系统论[J].法学研究,2017(2):46.
[20] 李中原.论侵权法上因果关系与过错的竞合及其解决路径[J].法律科学,2013(6):99.
[21] 周永坤.高楼坠物案的法理分析——兼及主流法律论证方法批判[J].法学,2007(5):48.
[22] 彼得·凯恩.侵权法解剖[M].汪志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22.
[23] 徐银波.论侵权损害完全赔偿原则之缓和[J].法商研究,2013(3):65-73.
[24] 陈甦.民法总则评注[ 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1321.
[25] 周友军.我国侵权法上完全赔偿原则的证立与实现[J].环球法律评论,2015(2):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