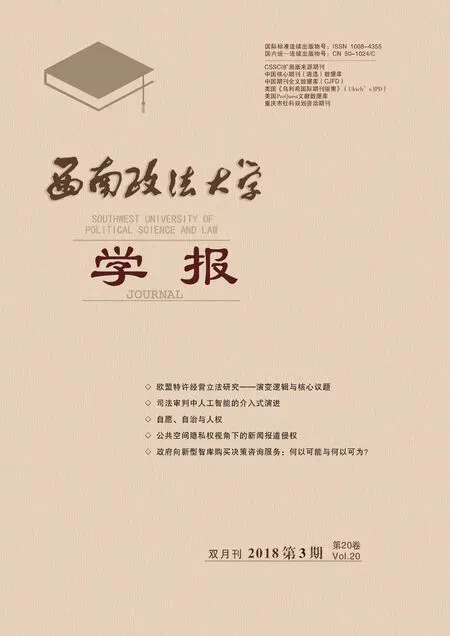“先行行为引起作为义务”的限定
(武汉大学 法学院,武汉 430072)
一、引言
在我国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理论的通说中,先行行为是作为义务的形式来源之一。先行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是指由于行为人的行为而使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处于危险状态时,行为人负有以采取有效措施排除危险或防止结果发生的特定义务。例如,成年人带小孩去游泳,负有保护小孩安全的义务;交通肇事撞伤人而使被害人有生命危险时,行为人有立即将受伤人送医院救治的义务等[1]。行为人具备履行能力而不履行此等义务,不避免、不阻止相应危害结果的发生或者容忍其发生的,构成特定犯罪的不纯正不作为犯。
稍加对比我们就会发现,游泳活动只具有一般的、抽象意义上的危险性,而交通肇事则直接侵犯了人的身体、生命或者公私财产法益。通说没有说明,为何将上述两个例子同等对待,即二者何以皆能引起作为义务。其背后的根本问题在于,通说未能令人信服地给出先行行为引起作为义务的具体判断标准。由于“危险状态”几乎无所不包,如果仅以是否引发危险状态作为引起作为义务的条件,则先行行为在范围上将无法限定,这势必导致不纯正不作为刑事责任的泛滥。鉴于此,我们有必要为引起作为义务的先行行为塑造教义学上的限定标准。这正是本文的主旨所在。但在此之前,笔者拟从思想根源上简略讨论先行行为引起作为义务的缘由,以期为深入认识先行行为类型的作为义务夯实基础。
二、先行行为引起作为义务的思想基础
客观地看,作为特定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侵害或危险)结果既能由行为引起,也能通过与行为无关的危险事件产生,并能使行为人作为保证者承担防止危险现实化的责任,因而可以说,结果是认识不纯正不作为犯的逻辑起点,正是结果回避的需要引发了对于作为的期待。不过,以刑事制裁为后盾的刑法规范不能要求一切人去看管一切人的安全和利益,否则就是以一种本质上迥异于责难积极作为的方式侵犯个人的自治和自由。所以,谁负有作为的义务或者谁可能成为不作为犯罪的行为人,就成了最为关键的问题。在直观感觉和公平观念上,唯应期待那些与结果存在某种关联的人担负防止结果发生的义务。传统观念认为,这种关联要么是基于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要求,要么是出于先行行为所致的危险状况或者紧密个人生活关系中的协助必要。
在此,因果关系不是不作为犯的决定性问题。自然意义上的因果关系阙如并不意味着法律不能惩罚不作为。当有理由期待行为人救助他人而他却不施以援手,评价的规范基点就不在于结果如何引起,而在于行为人不阻止该结果的实现。那么,以不存在因果关系为由,反对将结果归责于不作为,形同无的放矢;而试图另辟途径以证明因果关系的存在,则如掩耳盗铃。后者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当数准因果关系论,即:“如果行为人实施相应的作为可以避免损害后果发生,那么行为人不作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就存在一种类似作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效果联系,这种效果联系并非现实的因果联系,而是一种假设的因果联系,即准因果联系。”[2]327准因果关系论的致命缺陷体现在关于因果关系的认定过于泛泛,以致具体事实的刑法意义是否经过这一判断毫无差别。例如,眼看小孩跌入水池并在水中挣扎,小孩的父亲和其他旁观者均未予救助,根据准因果关系论,这位父亲和旁观者的不作为都与小孩的死亡结果存在因果关系。但这对后续的犯罪认定没有任何作用。所谓“假设”说到底就是“无”,我们当然不能对于一个不存在的东西要求什么。
所以,就作为义务与因果关系两者的关系而言,是作为义务决定因果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决定作为义务。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是从作为义务反推出来的一个虚幻的观念形象,人们借此消减对于无归因之归责的担忧。其实,不作为犯评价的真正重心在于行为人凭什么对一个不由自身造成的结果承担责任。脱离了特定人在社会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根本无法说明作为义务。对特定角色的社会期待限定了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成立范围。构成不纯正不作为犯罪认定前提的,不是自然的因果关系而是社会的角色关系。
以上结论对于先行行为的认识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第一,先行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是认定特定作为犯罪的前提,而不是引起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之作为义务的根据。第二,既然评价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关键在于对社会角色的期待,刑法教义学就必须实质性地考察值得期待的理由,以便合理阐明由先行行为所引起的作为义务。当今德国刑法学界的通说主要是从机能的视角来分析保证人地位的性质,并在此基础上将保证人地位区分为保护者保证人地位和监督者保证人地位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的保证人地位分别对应着保护义务和保证义务。保护义务意味着,如果行为人让他人的法益处于自己的保护之下,那么他就必须要保护好该法益,使其免受危险。保证义务的核心思想则是,行为人由于创造或者支配了危险源,他必须阻止其产生损害性的作用,也就是说,他必须对此种来源的危险进行监督,使其不至于现实化[3]。基于先行行为而生的作为义务属于一种保证义务,亦即阻止自身行为所创设的危险现实化为侵害结果的义务。
可以说,先行行为引起作为义务的思想基础在于,谁创设法益侵害的危险,谁就应该防止该危险现实化。值得一提的是,一个表现为作为的行为在实质上已包含了一个未避免结果发生的补充性的不作为,在行为及其引起的结果完全可由作为评价之处,这个补充性的不作为就失去了意义。同样,只要先行行为之后的不作为在规范上未超出先行行为的犯罪构成,整个事态就应该直接以先行行为所构成的犯罪来评价,而没有必要再行考虑相应的不纯正不作为犯罪。
应当看到,防止先行行为创设的危险继续发展为现实侵害这一思想为先行行为引起作为义务提供了思想上的依据和原初的理由,但其本身却无法充当是否引起作为义务的判断标准,因为我们不可能认为源于任何行为的任何危险都能引起作为义务。于是,我们必然需要探讨更为细致可行的标准。这又涉及两个方面:其一,什么样的先行行为有可能引起作为义务;其二,当先行行为与其创设的危险呈现何种关系时,作为义务才告成立。相应地,下文将从行为的角度与行为和危险之关系的角度分别论述先行行为引起作为义务的限定标准。笔者要提前说明的是,关于这两个角度的论述会存在重叠之处,但其不能相互取代。对此,下文结语部分将作进一步的交代。
三、行为的限定:合法先行行为的排除
在文献上,先行行为指的是危险的前行为。至于何种举止称得上危险的前行为,则是一个极富弹性、具有广阔解释空间的问题。如果“危险”泛指一般意义和抽象意义上的危险,那么其可能会完全抽空“前行为”的实质内涵,导致先行行为的范围无限放大,进而引起作为义务的泛滥。我国通说对“带小孩去游泳”的危险评价便是一例。事实上,该通说混淆了保证人义务的类型,将原本属于由自愿接管脆弱法益而产生的保护义务误解为由先行行为所引起的保证义务,从而不得不把“带小孩去游泳”之类的合法行为解释为先行行为。依此逻辑,先行行为包括具有社会相当性的一般生活行为。例如,有学者认为,基于汽车驾驶的一般风险,即使合法驾驶而发生交通事故,驾驶人也对具有生命危险的受伤人员负有救助义务[4]。但这值得商榷。一方面是因为,如果法秩序允诺人们为一定行为的同时,又基于行为可能产生的危险对行为人附加作为义务,其规范前后矛盾自不待言,更严重的是这将实质性地取消国民的行动自由。另一方面是因为,既然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与相应的作为犯罪适用同一刑法条款,就不能只要求作为犯罪的实行行为具备类型化和定型性,或者要求对作为进行客观归责的条件尽量细化和严密,而在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认定中毫无限制地将引起作为义务的先行行为回溯至任何日常举止,否则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则。
所以,主流观点强调,先行行为必须是违反义务,并因而导致法益遭受侵害危险的行为*参见:NJW 1973, 1706;林钰雄.新刑法总则[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405.。这其中理应包含义务违反关联的要求。义务违反标准旨在将合法行为排除在先行行为之外[2]334,而义务违反关联标准则拒绝把不能视为由义务违反而造成的危险(即损害扩大的可能性)归责于先行行为。
例如,甲遵照交通规则驾驶汽车,乙突然闯入行车道。甲回避不及,将乙撞成重伤。事故发生后,甲径直驶离。乙未及时获得救治,流血过多而死亡。在此,只要甲充分履行了谨慎义务,乙的死亡结果就不能归责于甲的行为,故甲不构成交通肇事罪(过失犯罪)。又如,甲以40km/h的速度驾车行驶在限速30km/h的居民区道路上,与骑自行车的乙相撞,致乙危及生命的重伤。甲明知乙急需手术,但他却没有停车抢救,也未呼叫急救医生。乙随后死亡。事后证实,即便甲当时在限速内行驶,也无法避免与乙相撞。对此,尽管甲未履行谨慎义务,但由于在合法替代行为之下也避免不了事故的发生,甲不构成交通肇事罪*德国《刑法典》关于交通肇事类犯罪的规定不同于我国《刑法》。德国学者认为,此两例中的甲均不构成“过失杀人罪”。。
但问题在于,甲是否具有保证人地位,进而就其故意的不救助成立不纯正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在第一个例子中,难以认为甲的合法行为能够引起作为义务。因为,“一个人以合乎义务的行为对他人造成危险,在规范上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关系不比意外事件更为紧密:无论相关人员是撞在石头上,还是与我无干地撞在我身上,抑或我(并未违反谨慎义务地)使他绊着,以致他不幸摔倒,并需要避免进一步伤害的救助,都一样是意外。”[5]除非具有特别的理由,任何个人都不应该对意外造成的伤害承担刑事责任。在第二个例子中,甲虽然违反了谨慎义务,但碰撞及发生构成要件结果的危险并非产生于义务违反行为,应该对来源于先行行为的作为义务加以否定,否则就是为了导出保证人义务而重复利用已被排除归责的行为,这是一个奇怪的做法。甲的先行行为和乙的死亡结果业已经过(不构成)犯罪的评价,况且先行行为也无以说明甲的作为义务,所以不能将乙的死亡结果归责于甲后续的不作为。就德国《刑法典》的规定来看,只能以第323c条第1款意义上的“未施救助罪”来评价两个例子中甲的不作为,即基于一般团结义务应该作为——不是阻止乙的死亡而是救助他人——而不作为的行为。
按照以上分析,正当防卫行为不能成为作为义务的来源。理由在于:一方面,刑法上的正当防卫条款容许正当防卫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不法侵害人的伤亡,也就是说,正当防卫人在特定范围内实施的行为是合法行为。另一方面,不法侵害人既然将自己置于违法的境地,就应该独自承担因制止其行为而引发的风险,更何况,倘若要求正当防卫人避免不法侵害人的进一步伤亡,无异于赋予不法侵害人高于一般人的特权,因为当一般人在完全无罪责地(比如因自然灾害等)陷入身体和生命危险时,任意第三人无须为其承担避免伤亡结果的作为义务。尤其在我国《刑法》意义上,根据第20条第3款无过当防卫的规定,如果认为正当防卫能够引起救助不法侵害人的作为义务,则会造成处理结论的不均衡,即当防卫人直接杀死不法侵害人时不构成犯罪,而一旦“手下留情”不当即杀死不法侵害人反而会因为不作为而构成犯罪。
难题在于攻击性的紧急避险中。当避险行为造成无辜第三人的法益损害时,避险行为人有无阻止法益损害继续扩大的作为义务?对此,通说认为,虽然紧急避险行为得以正当化,但是这种正当化是与一种利益权衡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权衡应当对被害人的利益给予最大的照顾[6]582。原因在于第三人只有照料性的忍耐义务,即一种社会成员牺牲自己的少许利益来拯救陷入危难的其他成员的社会连带义务,这种为维系最低限度社会团结所需的义务仅在避险行为人所保护的利益明显优越于所牺牲的利益时才具备正当性。这不仅意味着紧急避险中严格的限度条件,也意味着,当原本不过当的避险行为造成第三人法益损害扩大的危险时,避险行为人必须采取措施阻止更为严重的后果出现。例如,因遭遇雷暴天气而破窗进入他人房屋躲避的人,有义务封堵破损的窗户以防止屋内的财物遭到进一步的破坏,否则(在其他条件也满足时)他将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毁坏财物罪;为避免致命车祸而将汽车猛然拐入人行道并撞伤行人的司机,有义务把伤者送往医院救治,否则(在其他条件也满足时)被撞者加重的伤情或者死亡结果将归责于这名司机的不作为。
但是,仔细分析后,我们会发现前述观点经不起推敲。这是因为:第一,尽管无法否认紧急避险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但不纯正不作为犯罪评价和非难的重点不在于此。“一个完全不带有价值判断的因果关系,不能构成对刑法评价的连接点。”[6]573-574正因为如此,合乎注意义务的先行行为与由其引起的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才退到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地位,从而使作为义务的判断标准奠基在先行行为是否符合规范期待这一基础上。第二,既然可以接受合乎注意义务的先行行为不引起作为义务,也同样能够拒绝一个完全合法的紧急避险行为引起作为义务。第三,退一步说,即使认为在紧急避险中受到伤害的无辜第三人只有最低限度的团结义务,由其承担扩大化的结果并不公平,也不能反推出,把这种结果归责于避险行为人的不作为就是公平的。因为一个由合法的紧急避险行为引起的结果几乎等于由意外引发的不幸,避险行为人最多只应该承担基于社会团结所需的连带义务,即德国《刑法典》第323c条意义上的一般救助义务。至于我国《刑法》应不应该设立类似的一般救助义务以及在何种范围内以何种方式设立等,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四、行为和危险的关系限定:客观归责
如前所述,主流观点认为,先行行为是违反义务的行为。但是,义务违反标准并不足以完整说明“先行行为引起作为义务”,因为它没有考虑由先行行为所创设的危险的性质。所以,德国刑事司法实践上不仅要求源于先行行为的保证人地位以违反义务为前提,而且要求违反义务的先行行为必须创设(可能)产生构成要件结果的紧密危险*相关案例,参见:BGH NStZ 1998, 83; BGH NStZ 2000, 414.。这种“义务违反+紧密危险”标准的问题在于:第一,就像在德国著名的“皮革喷雾剂案”*该案的具体案情、判决结果及相关分析,可参见:孙运梁.以客观归责理论限定不作为犯的先行行为[J].中外法学,2017(5):1369-1370.中那样,义务违反标准有可能仅以纯客观的义务违反,即客观上出现法益损害的结果为已足,这会导致合乎谨慎规范的先行行为也能引起作为义务。第二,“紧密危险”的标准不够明确。于是,理论上开始借用客观归责理论来进一步限定危险,即只有当先行行为所创设的危险能够进行客观归责时,源于先行行为的保证人地位才告成立。这实际上把先行行为和由其创设的危险都置于了更为系统化的教义学检验之中。例如,旅店老板在轻微的雷雨天气把他的一位客人锁在店门外,致使后者遭遇雷击而受伤,虽然旅店老板的先行行为违反合同义务,但并没有因此而创造引起结果的紧密危险,即可以进行客观归责的危险,因此他不是保证人[7]。也就是说,引起作为义务的先行行为除了违反义务以外,还必须创设引起结果的紧密的可以客观归责的危险。
(一)作为义务的成立:客观归责于先行行为
因先行行为类型的作为义务本身源于刑法范畴,不同于来自民法等刑法以外法律领域的义务,这种作为义务的原因也必然只能在刑法意义上的先行行为中去寻找,所以保证人地位在此不得不依托于对先行行为所创造之危险的评价。如果这种评价采用客观归责的标准,则先行行为类型的保证人地位与先行行为所创造之危险的客观可归责性基本同生同灭。同时,根据主流观点,在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客观行为构成上,结果的客观可归责性是一个与保证人地位平行的要件。那么,客观归责理论在先行行为类型的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认定中就发挥了两次作用:首先,将危险归责于先行行为(保证人地位的成立);其次,将构成要件结果归责于不作为(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成立)。
我们有必要将前述两次客观归责的过程区别开来。有学者认为,对于损害结果来说,先行行为必须具有可归责性,“我们之所以承认因先行行为而推导出来的保证人地位,并非由于行为人实施了任何一种在先的行为客观上导致结果的发展,而是因为在先行为对于构成要件的结果而言具有可归责性,因而具有了探讨其不作为可罚性的基础。”[2]335这一主张实际上是将构成要件结果直接归责于先行行为,试图把不纯正不作为犯罪认定的两个步骤合二为一,从而一步到位地解决先行行为类型的不纯正不作为犯罪问题,具有很强的误导性。所以有学者不得不澄清说,“单独看先行行为,它本身并不是该当构成要件的行为,以先行行为为义务来源的不作为犯罪中刑法关注的重点是创设风险之后维持却不去降低该法所不容许的风险,而非创设风险的先行行为本身,……先行行为与构成要件行为(实行行为)不是等同的,应当进一步厘清先行行为的危险、不作为的危险与客观归责理论危险规则之间的关系。”[8]156,157先行行为意义上的客观归责要解决的只是保证人地位问题,也即“先行行为引起作为义务”的问题。
根据客观归责理论的通行主张,只有当行为所创设的风险实现于构成要件作用范围内的结果时,该结果才能归责于行为人。相应地,可以将客观归责理论区分为三个阶层:风险制造、风险实现和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这三个阶层内部又各自存在多项细化的规则。将这些规则(修正地)运用到先行行为归责上,可以形成如下一些具体标准:第一,总体来说,先行行为引起的后果(包括损害扩大化的危险)应当对行为人在客观上是可归责的,即先行行为创设或者增高了风险,且该风险实现于蕴含着损害扩大化危险的后果之中。第二,创设了可容许的风险时不构成先行行为类型的保证人地位。第三,欠缺对后果的预见可能性排除先行行为类型的保证人地位。第四,欠缺结果回避可能性(义务违反关联)不构成先行行为类型的保证人地位。第五,超越规范保护目的不构成先行行为类型的保证人地位。第六,被害人自我答责排除先行行为类型的保证人地位[9]。可以看出,客观归责理论列出一系列具体标准,旨在深入考察先行行为与其创设的危险的关系,然后将某些情形排除在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先行行为类型保证人地位认定的宽泛性和任意性。
以德国《刑法典》第315c条规定的危及公路交通安全罪为例,其构成要件的充足不以发生现实侵害为前提,仅要求给行为客体带来明显而尖锐危机的具体危险。因此,违规驾驶汽车导致的伤亡结果无以评价在危及公路交通安全罪之内。假设甲违反规定在道路上超速行驶,与骑自行车的乙相撞,导致后者重伤且最终死亡,就先行行为引起作为义务而言,可依据客观归责理论进行如下分析:甲明知超速驾驶可能导致危及生命等重大法益的交通事故(即具有预见可能性),但依然为之,因而创设了不允许性风险,且该风险确实已实现于对乙的伤害之中(即不允许性风险的创设和实现);乙的行为没有任何瑕疵(即被害人无须自我答责),如果甲也照章驾驶,则碰撞完全可以避免(即具有义务违反关联性);他人的生命、身体或者贵重物品的安全恰好是危及公路交通安全罪的规范保护目的(即未超越规范保护目的)。基于此,可以把乙需要救助的现实归责于甲,甲因而处在了保证人地位上。倘若乙及时获得救助本可避免死亡,而甲却对此放任不管,那么(在其他条件也满足的情况下)甲需要对乙死亡的结果承担不作为的刑事责任。同样,行为人将不会游泳的被害人过失地撞入水池之后,在具备救助能力时却冷眼旁观,任由被害人挣扎至死的,(在其他情况也满足的情况下)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
如此看来,原本用于客观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的客观归责理论经过一定程度的修正后,的确可以作为先行行为类型保证人地位之刑法教义学上的检验标准。在客观归责理论的视角下,一般违法行为、过失犯罪行为和故意犯罪行为皆有可能成为先行行为,也即皆有产生作为义务的余地。客观归责理论的重大意义在于,它表明了仅当先行行为和构成要件结果存在某种规范上的关联性时,先行行为才引起相应的作为义务,而这种作为义务的成立也需要经过一系列具体规则的精确检验。例如,当甲超速行驶将乙撞成重伤并导致后者昏迷后,甲无论如何不对乙身上的钱包安全(即不被路人“顺走”)承担作为义务,因为从规范期待(规范保护目的和答责原则)的角度来看,甲只须为他自身行为所引起的后果及扩大化的损害负责,这就将由先行行为所引起的作为义务限定在了相对合理的范围。
(二)客观归责理论的借鉴意义
在客观归责理论引入之前,我国刑法学界存在两种判断先行行为类型保证人地位的有力学说,即支配说和紧迫危险说。
我国刑法学者黎宏教授早在1997年就提倡从行为支配的角度来说明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他主张:“在研究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时,必须考察两方面的因素:一是事实性的因素,即行为人对危害结果发生的因果关系能现实性地具体支配。二是规范性因素,即法令、法律行为,职务或业务上的职责等通常意义上的作为义务发生根据。”[10]168-167就先行行为而言,在事实性因素的认定上,不仅要求支配行为的存在和开始,即先行行为人于先行行为发生之后介入后续的流程,实施了救助被害人的行为,而且要求对最终结果的排他性支配;在规范性因素的认定上,先行行为是一种法律行为,因而是产生作为义务的规范性根据[10] 168-171。这一观点并不可取,理由如下:首先,以介入排他性支配行为来说明先行行为引起作为义务,实质上等于否定了先行行为类型的保证人地位,这与作者承认先行行为类型保证人地位的主张自相矛盾。其次,法律行为是人所实施的能够发生法律效力、产生一定法律效果的行为,先行行为一般是受意志支配和控制、能引起相应法律效果的行为,因而一般是法律行为,但这并不足以成为刑法作为义务的规范基础,就像自由意志行为或许能产生其他法律上的效果,却不一定都要进入犯罪构成评价的视野一样。
鉴于此,黎宏教授后来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修正,他认为:“只有在行为人主动设定了对法益的排他性支配时,才可以消除不作为和作为之间的结构性差异,进而将该不履行作为义务的行为视为作为,按照作为犯的条款处罚。这种排他支配的设定,既可以通过行为人中途介入面向结果的因果进程的方式,也可以通过行为人制造并支配面向结果的潜在危险的方式。……在采用先行行为的方式时,行为人仅仅是实施了导致法益面临危险的先行行为还不够,还必须维持该侵害法益危险最终变为现实侵害结果。”[11]1588例如,“引起火情和导致他人受伤,都属于行为人的先行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具体利益造成的危险’,当时,没有其他因素的介入,行为人对该危险的明显增加具有排他性支配,因此,在该危险最终演变为实害结果时,可以说,行为人的不灭火或者不救助行为和放火罪、故意杀人罪的作为行为等价,构成不真正不作为犯。”[11]1590这样,黎宏教授就将其支配说从“介入救助行为”的视角转换到了“维持、放任危险增加”的视角,从而使“支配”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但随着这种变化,支配说在先行行为类型的保证人地位方面完全丧失了它的限定功能。
支配说的根本缺陷在于“支配”的可随意解释性。如果把先行行为之后维持和放任危险的行为也理解为“支配”,那么,所有在先的行为都可能引起作为义务,而且处在先行行为后的现场中的任何人都对后续的危险具有支配性。但这样理解“支配”难说恰当,更遑论排他性支配。德国学者许内曼认为,先行行为人的支配只存在于过去,对于先行行为之后的发展则未显示出现实性。在不作为的时点,先行行为人其实与任何一人无异,仅拥有一种以防止结果出现的可能性为标志的对事态的潜在支配。换句话说,当先行行为完成以后,行为人实际上已将后续的因果流程从其支配领域排除,所以,从存在论上说,他便只如任意第三人那样面对接下来的事态[12]。在山口厚教授看来,对侵害结果原因的支配是产生作为义务的实质根据,但“在因措施错误而致发生危险以后的阶段,很难说行为人支配着导致结果的原因”,因而在此意义上他赞同将先行行为从作为义务的发生根据中剔除[13]。
张明楷教授支持紧迫危险说。该说认为,使刑法保护的具体法益面临紧迫的危险是先行行为成为作为义务来源的实质根据,先行行为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将产生作为义务:第一,对刑法所保护的具体法益造成了危险;第二,危险明显增大,如果不采取积极措施,危险就会立即现实化为实害;第三,先行行为人对危险向实害发生的原因具有支配[14]。该说从先行行为所创设的危险出发,探讨作为义务成立的可能性,比支配说更为可取,但其一大弊端在于,将合法行为也作为引起作为义务的先行行为,无疑不当扩大了先行行为的范围。其次,该说忽略了先行行为和构成要件结果之间本该具备的规范关联性。例如,驾车行驶的甲撞翻乙驾驶的微型货车,致乙昏迷,周围群众上前哄抢货车中的物品,甲未加阻止。根据紧迫危险说,甲的行为在客观上使乙的财产面临紧迫危险,甲应当履行保障货物安全的作为义务,否则构成盗窃罪。但这难以令人接受。因为先行行为必须违反正好服务于相关法益保护的谨慎规范[15]。也就是说,对于保证人地位的成立而言,除了结果和违反义务之外,行为人必须通过其先行行为创设引起侵害结果的紧密危险,而这一危险的创设就体现在行为人对于旨在保护相关法益的规范的不予重视中*参见:BGH NStZ 2008, 276 (277).。最后,紧迫危险说还“分享”了前述支配说的缺陷。
比起支配说和紧迫危险说,客观归责理论在判断先行行为类型的作为义务上更具优势。周光权教授在评价客观归责理论的方法论意义时指出,客观归责理论建立了一套正面判断和反向检验交互进行的检验标准,用多重规则确保检验无所遗漏,凸显了评价的层次性和充分性[16]。对于先行行为引起作为义务而言,客观归责理论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刑法教义学上的严密建构和精细化检验,使得先行行为所产生的危险、危险与构成要件结果的关联、危险与规范保护目的的关系等在体系中各得其所,也使得对先行行为类型的作为义务的认定由事实向规范逐步推进,从而保证了判断步骤上的有序性和结论上的妥适可能性,避免了评价上的挂一漏万和走向极端。这是支配说和紧迫危险说所无法做到的。在我国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教义学上,完全可以用客观归责理论取代支配说和紧迫危险说,使其成为先行行为引起作为义务的判断标准。
(三)关于重复评价的释疑
如前所述,按照客观归责理论的检验逻辑,一般违法行为、过失犯罪行为和故意犯罪行为皆有可能产生作为义务。但问题是,当先行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已然处于(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范围内,能否再以相应的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对其评价乃至处罚?根据许玉秀教授的观点,当先行行为与后续的不作为所侵害的法益相同时,如果承认先行行为的保证人类型,则等于承认任何作为犯皆可能同时成立一个不纯正不作为犯,这就相当于把先行行为人看成防止结果出现的保证人,从而认为其具有制造危险和防止危险的双重身份[17]。如此,则每一个作为犯都会受到双重的否定性评价和过度的制裁。不仅如此,在受侵害法益不是同一法益的情况下,为了让先行行为导致的另一法益侵害也能获得足够否定性评价而承认先行行为的保证人类型,往往需要将先行行为的因果流程分成两段来分析,从而造成因果流程被重复评价的现象。因此,许玉秀教授倾向于否定前行为的保证人类型,反对将先行行为当作不作为义务的来源*除了对重复评价的担忧,许玉秀教授还认为,“既然依据前行为保证人类型的法理所拟制出来的不作为,在归责流程中或者毫无意义,或者和结果加重犯互有重叠,则前行为保证人类型犯在归责类型上即显得不太重要,而且不是无法替代”,并提出了取代前行为保证人类型的具体方案。(参见:许玉秀.当代刑法思潮[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677,693-701.)。
但是,许玉秀教授的这一分析在结论和思路上都存在疑问。首先,从评价的对象来看,对先行行为进行一次(作为的)评价,然后对由其引起的损害的扩大化进行一次(不作为的)评价,二者所针对的不法内涵和责任内涵是不同的。这在先行行为和后续的不作为分别侵害不同法益时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甲本意只是要烧掉乙的房子,但在起火后却发现房子里有小孩的呼救声,甲眼看着大火吞灭一切而无动于衷。甲的纵火行为与其后续的不救助行为完全可以分开来评价。即使在先行行为和后续的不作为侵害同一法益时,评价的对象也不同。例如,甲出于疏忽将乙锁在屋内,但当他发现被锁的人是自己平常厌恶的乙时,决定“锁他半天”,不为其开门。甲最初只是纯客观地剥夺乙的自由,但当其对事态有了明确的认识以后,无论是其行为上的不法性还是主观上的可谴责性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于同一事实可能存在不同侧面的不法和罪责内涵,所以判定是否重复评价应以不同侧面的不法和罪责内涵是否重复为标准。更何况,先行行为与后续的不作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难以作为同一事实看待。其次,从评价的结果来看,如果先行行为是过失行为而后续的不作为是出于故意的话,则过失行为就被视为是辅助性的或者得以评价在故意不作为之内的,因而最终在总体上评价为故意的不作为犯罪;如果先行行为是故意行为而后续的不作为是出于过失或者故意的话,则最终在原则上评价为故意的作为犯罪。这是竞合论所要解决的问题。最后,先行行为是否引起作为义务是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符合性上的问题,而究竟是以先行的作为来评价犯罪,还是以后续的不作为来评价犯罪,则属于竞合论上的问题,那么,从竞合论反推构成要件符合与否的做法,似乎在分析思路上前后颠倒,倒果为因,殊不可取。
因此,在认定先行行为类型的保证人地位时,应该将先行行为是否引起作为义务的判断与不纯正不作为犯所涉及的竞合问题区分开来。因主题和篇幅所限,笔者在此暂不探讨竞合论的相关问题。
五、结语
在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教义学发展过程中,既有全盘否认先行行为能够引起作为义务的观点(以下称“全盘否定论”),也有主张先行行为乃作为义务的唯一来源的观点(以下称“唯先行行为论”)。“全盘否定论”的主要理由如下:其一,因一种并不能准确界定的防果义务而承认先行行为类型的保证人地位,会破坏构成要件的保障功能和罪刑法定原则。其二,先行行为虽与结果存在因果联系,但却无法为刑法上不作为的归责提供基础。其三,先行行为与任意第三人无异,对行为之后的因果流程只具有潜在的支配。其四,先行行为引起结果的危险已通过先前的作为责任而得到充分评价[18]。不过,这些理由并无足够的说服力,“全盘否定论”也从未获得广泛认同。首先,诸多犯罪构成要件从形式上看是对作为的表述,但完全可将不作为解释于其中,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至于如何准确界定由先行行为所引起的防果义务则如同刑法规范的解释一样,有赖于刑法教义学的精耕细作与合理建构。其次,先行行为和构成要件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在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构造中确实无足轻重,但先行行为所创设的危险却足以为后续的不作为归责提供初始动因、思想基础和有力支持。再次,虽然先行行为人对后续的因果流程只具备“潜在的支配”,但鉴于对危险的创设和危险扩大化的放任,其与在场的任意第三人实难等量齐观。最后,在一些情形中,先行行为的犯罪构成难以完全评价后续的不作为。例如,行为人因为疏忽大意而失火,在火势完全可控的情况下却任由大火蔓延,最终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的,仅以先前的过失作为来评价犯罪肯定不充分。此外,从刑事政策的角度而言,在先行行为引发法益侵害危险的场合,先行行为人是最有可能也最应当承担结果回避义务的人,由此而肯定其保证人地位也符合人们最朴素的正义观。与“全盘否定论”不同,“唯先行行为论”认为,只有行为人自己在不作为之前设定了向法益侵害方向发展的因果关系,才能成立不纯正不作为犯[19]。如前所述,这种从因果关系视角来论证作为义务的思路不值得借鉴和采纳。
既然如此,承认先行行为引起作为义务,并对其进行合理限定就是更为可行和更切实际的选择。这一限定当从行为角度和行为与危险的关系角度着手:就前者而言,应该将合法行为排除在能够引起作为义务的先行行为之外;就后者而言,当先行行为所创设的危险能够客观归责于先行行为时,作为义务才告成立。在客观归责理论当中,创设不允许性风险的行为未必都是违法行为,一些客观上可归责的行为只有经过违法阻却事由的判断以后才能最终排除其违法性。就先行行为引起作为义务而言,定位于构成要件论的客观归责理论难以对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合法先行行为发挥限定作用,因而有必要在客观归责理论之外单独探讨合法行为能否引起作为义务的问题。所以,上述两个角度的讨论各有价值,在对先行行为类型作为义务的合理限定上不能相互取代。JS
参考文献:
[1] 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8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69.
[2] 王莹.先行行为作为义务之理论谱系归整及其界定[J].中外法学,2013(2):325-346.
[3] Hilgendorf, Valerius.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M]. 2 Auflage. München: C.H.Beck, 2015:196.
[4] Joecks,Miebach.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StGB. Band 1. [M]. 3 Auflage. München: C.H.Beck, 2017: § 13, Rn. 123.
[5] Ransiek. Das unechte Unterlassungsdelikt[J]. JuS, 2010(7):585-589.
[6] 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总论: 第2卷[M].王世洲,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7] Frister.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M]. 4 Auflage. München: C.H.Beck, 2009:268.
[8] 孙运梁.不作为犯中客观归责理论的适用[J].清华法学,2016(4):148-161.
[9] 孙运梁.以客观归责理论限定不作为犯的先行行为[J].中外法学,2017(5):1351-1376.
[10] 黎宏.不作为犯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11] 黎宏.排他支配设定:不真正不作为犯论的困境与出路[J].中外法学,2014(6):1573-1595.
[12] Schünemann. Grund und Grenzen der unechten Unterlassungsdelikte, zugleich ein Beitrag zur strafrechtlichen Methodenlehre[M]. Göttingen: Verlag Otto Schwartz & Co., 1971:316.
[13] 山口厚.刑法总论[M].2版.付立庆,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92.
[14] 张明楷.不作为犯中的先前行为[J].法学研究,2011(6):136-154.
[15] Kindhäuser,Neumann,Paeffgen. Strafgesetzbuch[M]. 5 Auflage. Nomos, 2017: § 13, Rn.43.
[16] 周光权.客观归责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兼与刘艳红教授商榷[J].中外法学,2012(2):225-249.
[17] 许玉秀.当代刑法思潮[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676.
[18] Hillenkamp. 32 Probleme aus dem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M]. 8 Auflage. Berlin: Luchterhand Verlag, 1996:233.
[19] 日高义博.不作为犯的理论[M].王树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