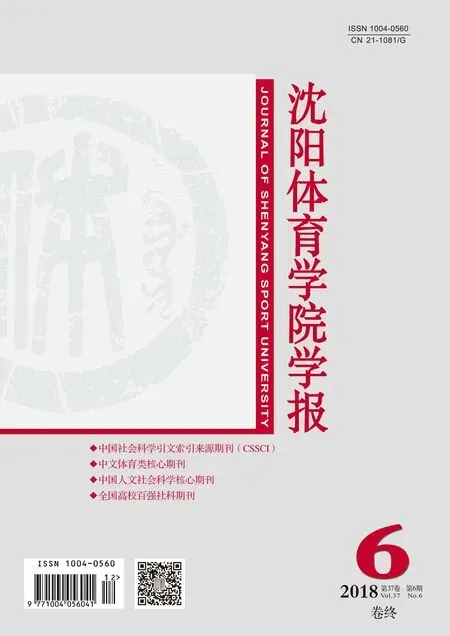中国武术“以意释气”的身体哲学解读
李 丽,张再林
(1.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体育部,陕西 西安710071;2.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710049)
如果我们对中国武术的古典文献进行深度梳理的话,可以发现在浩瀚如烟的武术著述之中,“气”无疑是一个最为频繁出现的哲学概念。如拳谱中“气遍身躯不稍滞”“气如车轮,腰似车轴”“气宜鼓荡,神宜内敛”“练气归神,气势腾挪”等,不一而足。其中不仅揭示出了“提气运用”之法,而且彰显出了“气变成形”之功,尤为重要的是最终都有力地揭橥出了“一气流行”之道。凡此种种,“气”可谓是一个足以贯穿中国武术文化的核心关键词。可以确证地说,这种核心的文化地位正是体现在武术之“气”不仅是一个关乎运动机制与关系演化的关键词,而且还是一个关联着人格特征与精神气象生成的全面性思想概念。
应该承认,也正是“气”所具有的这一“复杂及多元”的文化特质,使得其内在之意并不是那么清晰可见、直接相通,理解起来多存在着歧义、多义等难以进行客观解释的文化现象,这也是人们谈“气”色变以及学术困惑的主要原因。基于这一点,笔者将一改思想史中所贯穿的就“气”论“气”、以“气”释“气”的思维惯习,尝试以身体哲学为理论背景,以“身体意向性”“身体思维”“气化身体”等理念为切入点,从“意”的视角去解读“气”的文化意义,由此提出了“以意释气”的理论观点。对照这一观点,我们可以发现不论在中国哲学,还是具体在武术哲学,“以意释气”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切实可行的,这从“气随意动”“以意迎气”“以意导气”“意气相合”等彰明较著的观点中可窥其一斑。
易言之,一种与“意”同旨的“气”之发现必将使中国武术“气”的概念重获青春,彻底摆脱其固有的原始神秘主义而走向更为真实的文化面貌。这一学术理路的尝试,不仅可以视为对武术之“气”的经典思想的有力提撕,又可以视为是一种“返本开新”的方式,为武术“气”之深义揭橥出其意犹未尽和别有洞天的新内涵。
1 武术之“气”:一体多元的哲学概念
1.1 “气”与“劲力”的运用之妙
武术人之所以坚持“气”与“劲力”二者的密不可分,主要是因为两者都以最终共同服务于技击之功的掌握与提升为其根本之旨。例如,太极拳讲究“哼”“哈”“嗨”三气,以“金刚捣锥”来讲,有人认为是跺脚,其实不然,这样的理解是不对的,它强调的是放松,不仅仅是“形”上的放松,更为重要的是“气”上的放松,以“气”来配合。例如动作往下,配合的是“哈”;动作往上,配合的发声就是“哼”。反之,往上要“哈”就泄气了;“气”往下松配合“哈”,“气”则不会往上返,这里所体现的正是武术功夫中强调的“敛气”。正所谓“大凡运气之法,在乎气,而气之虚实全凭小腹下运之”,也即拳家常说的“气沉丹田”,否则气上浮于胸,会导致步不稳而拳乱。
著名武术家门惠丰先生指出:“对呼吸进行有意识的训练有一些方法,概括起来就是提、托、聚、沉。动作往上的时候则顺势提气,提也是一种劲力,意在重心升高,是为了升高重心后的一种劲的运用,便于发力。‘气’提起来还要稳住,托住,托就是使气息保持稳定,不散乱,这两个字都是向上动作的方法。动作向下时就是‘聚’‘沉’了,意思是讲,先把意念沉入丹田,再把气向下沉,在这里,沉的过程就是聚的过程。一言以蔽之,这样的呼吸目的是为了达到技术要求的一种体认要领,它们是为劲力的发放而做准备的。”[1]
无疑,这种“气”与“劲力”的运用之妙在中国武术思想史上其意义既深且巨。正所谓“拳之根本,在于气,不可乱出。苟或乱出,则如大力之人,多有一遇对敌,力转不能以自伸,所谓气阻力闭,而无循环相生之妙也。”[2]所以“气”是力足的基础,是劲力生发之根本。不过,这一“气”的功夫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努力做到拳经中所强调的:“但须练之于平日,早成根蒂,方能用之当前,无不坚实。不然,如炮中无硝磺,弩弓无弦箭,满腔空洞,无物可发,欲求勇猛疾快,如海倾山倒,势不可遏,必不能也。此炼形炼气之最紧者,谨之秘之。”可以说这是对“气”与“劲力”内在关联的最好解读。
1.2 “气”与“形势”的互证之法
古代拳谱中讲:“形合,则气不牵扯;形不合,则气必濡滞。”可以说这是对“气”与“形”二者之间最为凝练,也是最为深刻的解读与阐明。孙禄堂曾反复训诫说:“练拳时要从其规矩,顺其自然,外不成于形式,内不悖于神气,外面形式之顺,即内中神气之合;外面形式之正,即内中意气之中。故见其外,知其内,成于内,形于外,即内外合而为一。”[1]耐人寻味的是,这里共同遵循的道理到底是什么呢?古人所给出的答案其实正是“合”的义理体现。
例如在方法论上强调的“腰要往前低,而周身之气,需往下腹沉,做到上虚下实”,唯此才能做到“下步自能坚固紧密矣”,它强调的是“上下周身”与“气”之合。除此以外,行拳走架之时还强调:“转关有一定之势,接落有一定之气,无悖谬,无牵扯矣。盖势之滑快,气之流利,中无间断也。一有间断,则必另起炉灶,是求快而凡迟,求利而反钝也。”它强调的是“起承转合”与“气”之合。再如《面部五行论》中强调:“凡一动之间,势不外屈伸,气不外收放,面上五行形象,亦必随之相合,方得气势相兼之妙。故收束势者,气自肢节收束中宫,面上眉必皱,眼包收,鼻必纵,唇必撮,气必吸,声必噎,此内气收而形象聚也。展脱势者,气自中宫发于肢节,面上眉必舒,眼必突,鼻必展,唇必开,气必呼,声必呵,此内气放而外象开也。”[2]这里强调的是“面部五行”与“气”之合。
所有这一切使我们发现内在之“气”与外在之“形”唯有做到“内气随外、外形内合”,才能真正理解“气聚则离明得施而有形,气不聚则离明不得施而无形”的哲思之道,才能真正做到“盖形以寓气,气以催形,形合者气自利,气利者形自捷”,以及“练气练到至处、尽处、无以复加,则功成圆满,真气充足,气一收结,气止血聚。血者,华色也。气血不行,肌肤随气,收贴于骨,五行真气,尽现于外,各随所禀以呈”的互证互摄之境。
1.3 “气”与“练养”的契合之机
《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气论及身体观》[3]中提出“物之时与秩序,依于物象而有;而物象又依气之息散,即气之流行而有”以及“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等气化观点。显而易见,这是一种杨儒宾先生所谓的“节宣其气”“身体应感”的经验养成。为了进一步说明“气”与“练养”的问题,不妨读一读虽未在武术著述中得到相应的重视但却具有着十足意义的《苌氏武技书》[4]中的《中气论》一篇,其写道:“盖动静互根,温养合法,自有结胎还原之妙。俗学不谙中气根源,唯务手舞足蹈,欲入元窍,必不能也。”意思是讲习武者若能理解并做到动与静互为根源,气与势融为一体,练养得法,自可使精气神凝聚而达“结胎还原”之妙。文中还写道:“炼形炼气,动关性命,其气之统领,气之归着,可不究哉。”意思是讲,不论是从灵活之身势来看,还是从巧妙之技法来看,妙合而成主要源于“气之聚也”的练养思想。归根到底,唯有对“气”与“练养”的内在隐秘进行鞭辟入里的认识与理解,才能真正地达到“武备如此,炼形以合外,炼气以实内,坚硬如铁,自成金丹不坏之体,则超凡入圣,上乘可登,若云敌人不惧,尤其小焉者也”的功夫境界。
值得注意的是,《三尖为气之纲领论》更是对“气”之练养具体到了“三尖”部位。内容写道:“‘气之纲领,气之归着’,是以‘三尖’为结聚点的重要学理。何为‘三尖’?就是人体头、手、足三个顶尖之处。例如‘头’与‘气’的关系问题,文曰:‘头为诸体之会,领一身之气,头不合,则一身之气步入矣。’为什么会有这一穷神之化的观点呢?这是因为‘头圆像天,为诸阳之会,为精髓之海,为督任交汇之处,统领一身之气,阴阳入扶,全视乎此。此处合,则一身之气俱合,此处不合,则一身之气俱失。”[1]三尖中的其他两尖同样如此,它们既是内气运行的统领,又是内气激发的归着点,还是练形与练气妙合而成的契机所在,更是一种不无至胜之谛的体现。
1.4 “气”与“精神”的融摄之径
《礼记·祭义》中“气也者,神之盛”一语道出了“气与神”之间的内在关系。无独有偶,苌氏武学之中也明确提出了“气力之根本在于聚精会神”,如在《聚精会神气力渊源论》中提出:“神者,气之灵明也,是神化于气。气无精不化,是气又化于精矣。”“神必借精,精必附神,精神合一,气力乃成。夫乃知气力者,即精神能胜物之谓也,无精神,则无气力也。”“盖人之生也,禀先天之神以化气,积气以化精,以成此形体。既生以后,赖后天水谷之津液以化精,积气以化神,介于丹鼎,会于黄庭,灵明不测,刚勇莫敌,为内丹之至宝,气力之根本也。”以及具有统摄性意义的“武备如此,唯务聚精会神,以壮气力。但不知精何以聚,神何以会,殚毕生之心力而漫无适从也”等明辨明审之论。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精神合一,气力乃成”“神以气会,精以神聚”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武术的内在奥秘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姿势之外有姿态,姿态以外还有心态,心态之外还有心气,心气之外还有神气,神完气足,才是太极”的至理名言了。在这里,不得不提及“身法八要”中的“提顶”一项,它要求头直目正、顶悬身拔,这样有益于气血运行、气血通泰流畅,唯此才能有“满身轻利”之感,始能聚精会神、专心一致,才能做到“形如搏兔之鹘,神似捕鼠之猫”等招势气象。正所谓“形神气志,各居其宜。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其位,即三者伤矣”[5]。总之,“神”与“形”之间多了“气”这个层面,更有利于我们考察和表述生命现象以及精神现象的联系和区别,解析上也更为精细了。
2 武术之“意”:生命意向的身体表达
《论中国武术的“意”》一文中指出:“‘意’作为中国武术的灵魂所在,主要表现在通过外在的技击表象来传达武术技击之本意;通过艺术化的表现手法展示武术理想化的技击意蕴;通过‘有意’到‘无意’的过程转变而达到一种‘出神入化’的至高意境。”[6]这一总结性的分类对武术“意”的阐释,可以说不无意义且具有一定的见地。然而较为遗憾的是,对于武术“意”的概念与特征还缺少哲学高度的解释与定位。
2.1 “心之所念”的身体意向性
归根到底,“意”字从“心”,此“心”并非彼“心”,而是一种梅洛·庞蒂式的“走向世界”的身体之“心”,一种张再林先生所谓的作为我身体“原动力”的“身体态度”“行为指向”之心,可以说这与处处时时强调“得于心,应于手”的中国武术是不谋而合并深深相契的。因为在中国武术中不仅有着“捶心自出,拳随意发”“心之发动曰意,意之所向曰拳”的旨要之义,也有着“势势存心揆用意,得来不觉费工夫”的经典提撕,更有着“意者,心之所发也,是故心意诚于中,而万物形于外”以及“仔细留心向推求,屈伸开合听自由”[7]的至理论断,不难看出中国武术正是在“意”的作用之下实现了“心之所念”与“心之所指”的身体指向。这里的“意”作为一种“能在”式而非“实在”式,以其“可能”适成其“本能”,以其“潜在”适成其“现在”,以其“内生”适成其“外成”,以其“非心非身”适成其“亦心亦身”的方式,建构着现实的一切。也“正是这种‘意’的存在,为我们架起了一道生命之桥,使我们生命中分离的思和行、身和心连为了一体。”[8]这是一种“身体性知觉”、一种“身体意识”的存在。涉身其中,我们虽不假思索,但却可以“用身体知道”。
可以说正是在这一“心之所念”的“意”的牵引之下,武术之身体才会“融会贯通,感官合一,才能达到‘上下相随、前后相连、内外相合、左右相应’的不同方面的呼应、搭配与整合,整个演练过程呈现出了一种‘相互涵摄’‘循环论证’的运行轨迹。”[9]从发生学角度来看,“心之所念”的“意”的优先性,最终把习武者的身体动作引向了最佳的位置与空间。另一方面,“从意向对象和意向行为看,意向性既涉及意义赋予,也涉及意义阐明。”[10]正因如此,在具体的一招一式之中,我的身体总是被具体的某一任务而牵引,并且“我的身体朝向它的任务存在。”以至于“哪里有要做的事情,我的身体就出现在哪里。”[11]这一切体现的正是一种真正的“心之所念”的直觉主义的认知精神,彰显的是一种身体哲学式的“彻底经验主义”的认知观。
2.2 “念即是行”的身体意向性
尚济在《形意拳技击术》中指出“心,指人的思维器官;意指人的思维活动,形之于外就体现为人的精神气质。内中意一动,则精神振奋,目有光芒,整个神气能将对方罩住,如猫之捕鼠、鹰之攫兔,斯之为心与意合。内中意念一齐,刺激了植物性神经,各内脏一起积极活动起来,推动了循环系统进一步改善,一部分平时不易开放的毛细血管得以开放,气感便油然而生,自觉脐下温暖,这便是意与气合。一旦打出拳式,动作指向何处,气便随之而至,力也即随之而至,意帅气,气催力,这就叫气与力合。”[12]可以说这是一种“由内到外”的身体运行逻辑;是一种“精神所到,仿佛有一线精气,随心之所思而运行”的能动和受动二而一的关系思维。正所谓“拳术至练虚合道,是将真意化道至虚至无之境。不动之时,内中寂然空虚,无一动其心,至于忽然有不测之事,虽不见不闻,而能觉而避之。”[13]凡此种种,对于时空性质的把握以及攻防性质的合理转换,正是“心之思”“意之动”的昭然若揭。
《灵枢·本神》写道:“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由于其把心的念想活动等同于“意”,又由于把这种“意”的内容视为志向之“志”,从而为我们明确地推出了对心的一种意向论的解读。“意”是行之始,其中之“意”更多地理解为作为“行之始”的生命欲望,而非仅仅理解为“识之始”[14]的意识意向。《易》把“意”视为动而未形的生命之极。刘宗周提出了“心无体,以意为体”“意则心之所以为心也”,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这种“欲行之心”“行始之意”在中国武术中体现的更是淋漓尽致,如形意拳谱中“气能顺乎意,意由专一而顺乎心,则得乎常心而神发智矣,此成和之极功也。气若何而顺乎意?始于善练,进于善养。善练善养,则气浸顺乎意,意浸专一而不外驰。久一则寂,寂则廓然而心正,心正者神自清,故能感而遂通,应而不藏。”[15]究极而言,这种“感而遂通”的“念即是行”的直觉性的“不二之悟”正是一种“智性”[16]的身体思维方式,一种“反身而诚”的直觉性体验。
3 武术中“以意释气”缘何得以可能
3.1 “意”与“气”均具有目的性属性
中国武术中有“内外三合”之说,即“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为内三合;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为外三合。”有趣的是,为什么在内三合中会有“意与气”合?在这里绝不是无中生有的武术理念,而是经由武术人深思熟虑、不断反思不断淬炼的思想产物。我们可以对其进行更深一步的学理分析,如“要知用力用意乃同出于一气之源,互根为之,用意即是用力,意即力也。……要知意自形生,力随意转,意为力之帅,力为意之军,所谓意紧力松,筋肉空灵,毛发飞涨,骨生锋棱,非此不能得意中力之自然天趣矣[17]。”又如在试力之时,所强调的“需意不使断、神不使散,轻重操持而待发,动一处牵全身。气力一致,归于虚灵沉实而圆整,上下左右前后不忘不失”[17]。“意气领先聚力量”,所谓“意、气”是指组织、协调和统筹、整合内外各种力量的生理和心理机制;其操作意义在于借助本体感觉的反馈信息对自身活动进行调控。
阮纪正先生指出:“人的所有动作、行为,当属在意识控制下通过主客互动的那种从静走向动之目的性运行;这里的工程学之意义在于目标探寻、任务界定、组织调配、过程控制,由此所有操作在原则上也就势必是要意气领先的。”[18]它所彰显的不仅是“以意领先、以气运身”“意到、气到、劲到”操作上的程序安排,而且又是对“意气君来骨肉臣”内部系统组织分工协作的总体性要求。王乡斋先生也曾指出:“习拳平时用功,常使神气聚而不离,如站桩之时,自神不外驰,意不外想,精不妄动,气不轻浮,神不乱游,无站桩之形,而收其实效,则有不可思议之妙。”凡此种种,不论是行拳走架,亦或是试劲发力,还是站桩修性,“意、气”都呈现出了某种内在的一致性,都以一定的目的性为其操纵逻辑。
3.2 “意”与“气”均为可能性之存在
“气”是事关运动趋向的基本方式,是事态发展演变的基本动力,是整体性把握的综合性评价。“气”无形却可感,且能化无形为有形,它通过身体运行而构成一切、渗透一切、充斥一切,自始自终在不断地运动变化着,它既可以是一招一式的个性集中,也可以是整体套路演练的综合表述。然而,武术“气”概念不是虚无缥缈的、不着边际的,它是武术人实践理性的结晶,是对武术本质规律的一种思辨与抽象,是传统思维模式与习武者切身结合的产物。不可否认,“气”以其混融的特性保持着通透一切、左右一切的实践功效,具有着巨大的整合力与包容性。所以,武术人喜欢以“气”去指称、描述一些不可理解甚至于玄妙莫测的问题,以至于常常被古人冠以“判断慧根有无”“描绘灵感无定”的理论特点,属于中国古代学术中常见的那种能触发多向联想的形象概念。这一多向联想之“气”为一种生生不息的可能性之道,而非现实性之道。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文化特性不仅体现在“气”之中,同样也体现在“意”之中。
例如拳经中写道:“尽此一口气,向火烧脐轮”,意思是“闭口鼻之气,以心暗想运心头之火下烧丹田,觉似有热,仍放气从鼻出脐轮,即脐身田”。可以说这一经典隐喻醍醐灌顶般地使我们领悟到了“意”“气”之间的内在可能性以及交互之道。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从“夫所谓聚气结球,行至某处者,全属以意设想,此即修道家炼气成丹之要法也”“成和之修,必由于顺。形顺乎气,气顺乎意。意之专一者为志。志以湛静顺乎心,心者,神智之所宅也”“呼吸者,则谓之调息也,息调则心静,息外无心,心外无息。欲得息外无心之妙,必须真调息,息调则心定,心定则神宁,神宁则心安,心安则清静,清静则无物,无物则气行,气行则绝象,绝象则觉明,觉明则性灵,性灵则神充,神充则精凝,精凝而大道成,万象归根矣”[19]等等中感知到这种可能性之道,以“显则聚,隐则散”的形式推荡出了妙乎神乎的身道世界。
3.3 “意”与“气”均以类似方式生成
这一类似方式的生成,即是一种“内生外成”的实现方式。“意”和“气”二者皆为无形,然却可感,且能化无形为有形;它们通于一切、充斥一切、渗透一切,而且自始至终在不断地运动转化,二者如能各得其宜,方能呈现出顽强的生命力。武禹襄《十三势行功心解》中对于这一“内生外成”的意义表达最为透彻与全面。例如,其中的“以心行气,务令沉着,乃能收敛入骨”,这里的“心”是意念精神之总称,指的是一招一式应以精神意念为主,驱使其气,即每一开合之中,开时必须意气达于手指,合时必须意气通于脊背,而后达足跟,在如斯线路中,将全身之筋伸直行之,则自然沉着而有缠劲,其气就自然而然收敛入骨髓矣。又如其中的“以气运身,务令顺遂,乃能便利从心”,意思是讲用功即久气能随意而运动,则身之运动为意之运行,其根乃在心,因以心行其气也,所有屈伸起落,务须曲线缓和,毋使身手内发生棱角之病,是为顺遂。如此则身可从气,而气可从心矣。
更为有趣的是,其中的“意气须换得灵,乃有圆活之趣,所谓变转虚实也”一句要义,更是直接道出了“意气”二者的合一。杨澄甫认为:“每一动作,其身手均有主宾之分,如能随机换意互为主宾,意之所至气即随之,是谓之灵;意左则左为实,意右则右为实,能如意而倒换之,意气不滞住某一点,是谓之活;内中顺遂,是谓之圆;能保顺遂以倒换,亦即虚实之变化也。”不得不提出的是其中还有着“先在心,后在身,腹松气敛入骨,神舒体静,刻刻在心”的“心与气”亦或是“意与气”的注释,意思是讲凡走架子应做到“心为令,气为旗,腰为蠹”,做到以心意为本,身体为末,即以心行气,以气运身之谓也。以心行气,在意不在气;若注意在气,则意为气所击而生滞也,盖神速而气慢;欲练气合神,必须意在精神,不在气之本身,然后神能导引其气变为神,则气随之功可得矣。读着这些洋溢着诗思的话语,不难得出不论是中国古代身道的“显微无间”的幽冥之说,还是中国古代生命哲学的“体用不二”的阴阳理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思想的共鸣。
3.4 “意”与“气”均具有本体论的形式
如上所述,“意”与“气”都以“内生外成”的方式而存在。然而以这种方式而生成的东西实质上正是对“道”的追寻与表达。例如“意”与“力”的操持问题,在《拳经拳法备要·用力》中有着较为经典的论说“周身用力,逐一细推。头如顶千钧,颈如搬树转,下颏如龙戏珠而挺出,肩膊如铁,浑坚而徒来,前手如推石柱,后手如扯拗马,前脚如万斤之石压,后脚如门闩之坚抵赖,臀如坐剪夹大银,身如泰山无可撼,此周身用力之妙,摹神设想之巧者也。”[2]虽说是在讲“周身用力”之道,实际上更是一种对“意所向也,心之所之”这一“意向性”“取向性”之道的身体表述。“夫意,气之导也,气体之充也。以气为剥,而亦以气为取。行无所事,而遂其自然,意之所至,气之随之。”“理可详者,气之意也,意其意而不一,斡乎乾而能常,浮乎坤而能长,运而二无穷,生之而五方,化之而无边,因之而无强。”[20]
实际上对于“气”而言更是如此,正所谓“夫气之性,元是活动运化之物,充满宇内,无丝毫之空隙;推转诸曜,显造物之无穷。不见其滢澈之形质者,为空为虚;惟觉其陶铸之常行者,为道为性。欲求其所以然者,曰理曰神。”[21]所以气之体用由积累而得以验,气之运化须实践而得以证成。“万端变化,皆由气之蕴蓄,相推迭旋,亦乘气之活动。”《气学》虽然是从宇宙之气来谈万物变化之道,实际上对于中国武术而言更是如此。正所谓“夫气者,力也,拳家之根本”,为什么成为根本?主要是因为“气足则力亦足”,如《拳经·气法指要》中论道的“紧闭牙关莫开口,开口气泄力何来;须知存气常充腹,杀手休将气放怀;回转翻身轻展功,灌通筋骨壮形骸;终朝练习常如是,体质坚固胜如铁。”歌诀中的气运神化既精深又幽玄,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窥见他们的精神境界和思维运作方式,而且可以把握其内在的“一气运化”之身道。它与“道”的理化相应,因为“气之变动成乎理,气成理的过程也就是气运化的过程,理意味着这种运行的有序性,气通过变化的运行而成乎理,也就是理由隐而显的过程,而理显现出来的过程就是气运行有效性的表征”[22]。
4 中国武术“以意释气”的文化意义
一旦我们将武术中的“意”与“气”进行互释,我们就会发现两者之间不仅具有着相同的学说宗旨和运行模式,而且更为有意义的是它既可以对武术之“意”进行内涵解读,同时又可以对“气”进行内涵诠释,可以说具有一石双鸟之功。“而这种以‘意’释‘气’不仅与中国古代诸子的‘意’‘气’说遥相呼应,而且也以一种‘近取诸身’的方式使长期以来‘气’的扑朔迷离、难以诘致的面目得以真正澄清,并使时下对‘气’的种种解读的偏颇与误解一扫而空。”[23]这也就意味着“意”与“气”在武术中实质上是一体的,也就是说对于武术之“意”的说明恰恰正是对于“气”的说明。
4.1 构建“以意释气”的哲学话语体系
所有这一切,使我们全面而深入地看到了在中国武术的传统身体观之中,“意”“气”往往以相提并论、合二为一的方式进行着理论的阐释与身体的表述。可以肯定的是,“意”“气”一体的话语体系无疑已经成为了功夫修炼的哲学反思,而且是高度哲学化的反思。如“以意导气,不加丝毫气力、丝毫色相,意到手到,意止手止,使气纯养归根,以气为本。有急有徐,有刚有柔;机息渺茫,动则万变;不固执以求气,不着相以用力;神乎神乎至于无形,飘乎渺乎至于无声。”[24]总的来说,“神乎神乎至于无形”的“意气一体”功夫境界在管理学和行为学上的意义正是在于目标管理、计划实施和过程调控、组织保障,它涵盖了操作过程中的目标取向、信息反馈、精神控制的心理活动和信息传递、能量配置、运行调谐的生理机能的两个方面。两相比较,“意”与“气”的论述如出一辙,其内在关联可以说已经呼之欲出了。
有趣的是,不仅在中国武术中,而且在《黄帝内经》中更是对其极力标榜,它所强调的“得气”与“气至”实际上都与“意”密切相关,其中“‘得气’说明经气的‘自我调节’功能已被诱导或调动起来;‘气至’则反映了阴阳之气‘各守其乡’的调和状态。”[25]不难发现的是,不论“得气”中的“自我调节”,还是“气至”中的“各守其乡”都是以“密意守气”“必一其神”为其根本旨要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意”“气”之间其实有着统一的枢纽,这个枢纽使得感官作用的意义相互渗透,合为一体,所有的分殊成为“一性”的有机之分化。在具体操作上,它突出了心主神明、意为统领、气遍身躯、劲贯四梢、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神态自若、意动形随几个方面的分工协作与协调整合。可以说在西方哲学的语言里找不到像“意气一体”那样能够把武术人的实践智慧、技艺和行为主体的精神境界融合一体的概念,它已经带动与丰富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资源。
4.2 开显“意气一体”的功夫论思想
正如刘宗周指出的“‘意’是心中本有的支配后天念虑的最初意向”的那样,对于中国武术而言,这种“意”则是一种身体意向性之“意”,它是对技法应用,招式演练等有经验型的“随感随应”的意义主张。实际上这一““随感随应”的意义主张是与“气”密不可分的,我们已经得出,不论是“得意求气”也好,还是“气以迎意”也罢,二者实非可分解之物,而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东西。这是因为,“气”同样为一种“身体意向性”的有意义性的主张,正如王夫之所宣称的那样,“盖气者,吾身之于天下相接者也”。也就不难理解,武术之“气”为有“意”之“气”,恰恰在于“气”作为吾身与天下“相接”“相及”的性质。令人不无诧异的是,这种“相接”“相及”的性质,实际上与身体现象学中“身体意向性”的概念所指上是一致的。对现象学而言,这里“意”“气”所指的意向性,既涉及意义赋予,也涉及意义阐明。这里的意向性不仅赋予了经验以意义,而且深深地奠定了武术技击的坚实依据。
正如充满诗意的“吞身如鹤缩,吐手若蛇奔,活泼似猿猴,两足如磨心,若问真消息,气穴寻原因!”这一经典隐喻所言,“象形取意”已经与“气”的目的属性以及可能属性紧密相连,并呈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这是一种独特的身体体验,这种经验因进入了不可思议之境,因而与世俗的经验绝然不同,其功夫只有落在“格拳穷理”上面,才能真正做到“意气一体”的“一体之感”,这是一种功夫论思想。正如戴国斌教授指出:“这一‘格拳’‘穷理’的过程就像探测器一样,它们是对外侧变化后自我行动的调整,它不仅是对身体敏感性的训练,也是对应对策略与应激举措等行动方式的习得。”[26]由此出发,也就不难理解“意”“气”合一的过程,实际上正是一种探究拳术原理,从中获得智慧感悟心得,其“体、用、造、化”得以具体实施的探索过程。它最终走向的则是一种“意气一体”的“互参律”“和合律”相互融摄的功夫世界。
5 结语
一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气”是中国武术的核心概念。而在中国讲“气”,则首先是哲学的“气”。不可否认的是武术之“气”源于哲学之“气”,然而又有着自身的特点。这种自身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气”与“劲力”、“气”与“形势”、“气”与“练养”、“气”与“精神”等互证、互摄的内在关联上。除此以外,也是最为重要的,则是体现在“意气一体”这一哲学概念的文化意义上。可以说其内蕴的哲学方法和运行规律是中国武术必须作为自身的基本要素加以吸纳与转化的。这是因为我们必须要持有这样的观点“理论整体的价值取决于对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上有无进步,是否在进行或者包孕着有意义的探求。”[5]对于“以意释气”的理论阐释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期许,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武术研究者的共识,共同为别开生面地揭示出武术文化的内在奥秘、创造性地转化武术文化的思想资源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