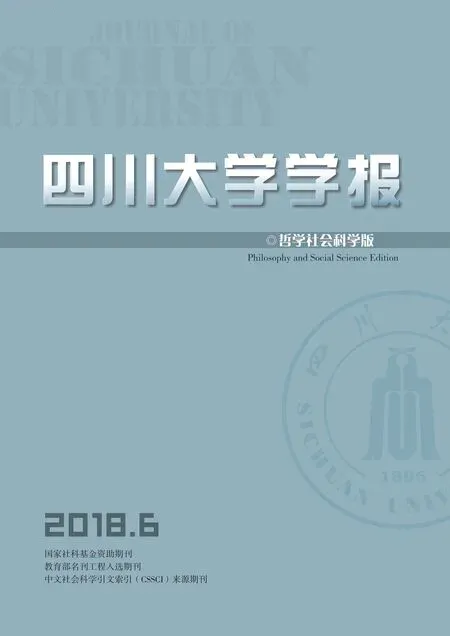“中国文化走出去”语境下跨文化传播的基本问题
——以“龙”和“Dragon”为例的词语文化轨迹探讨
王晓路
目前学界对中国文化“走出去”多有讨论,其中一个重要的议题是,无论送出去的是何种内容以及采纳何种呈现形式,语言都是不可或缺的确定性要素。实际上,经过近代已降的百年变迁,中国日常生活与学术语言,均已发生了巨变。大量的经由翻译或改写的外来表达不断融入到汉语表述系统之中。在今日讨论“中国文化走出去”之时,认真审视构成当代中国文化意象和思想性陈述的话语方式,探索其中一些基本词语的跨文化转换路径,就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本文拟就此进行讨论。
一、语言生成的文化轨迹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话题。语言在人类的伊始阶段就与其生存方式密切相关。当时采纳语言符号进行交际主要是出于集体生存行为的需求,“像人类这样行动迟缓的动物,只有依靠集体合作才能在严酷的自然淘汰中幸存,寻找食物、躲避野兽,早期人类的任何活动都需要语言有意识地做出规划和安排”。*夏明心:《人、超人、“神”:认知革命,让人类更强》,《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38期,第152-153页。虽然远古的口语形态已经不可考,但在人类自身的能力中,语言无疑最能彰显其特点,诚如吕叔湘先生所指出的,“语言是人类的创造,只有人类有真正的语言”。*吕叔湘:《语言和语言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第1页。人类群体从口语到文字符号的创造和扩延,不仅构成了各具特点的语言系统,将自身的经验抽象并铭刻为表意性符号进行传递,也使特定群体拥有了体貌之外最为重要的文化同一性(cultural identity)。*See Alan Bullock and Oliver Stallybrass, eds., The Harper Dictionary of Modern Thought,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7, p.298.有关中国文字书写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参考Lingchei Letty Chen, Writing Chinese: Reshaping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此书讨论了大中华区语言书写的文化问题,包括华裔文化现象等。对于文字的功用,柳诒徵先生曾说过:
文字之功有二,通今及传后也。草昧之世,交通不广,应求之际,专恃口语,固无需乎文字。其后部落渐多,范围渐广,传说易歧,且难及远,则必思有一法,以通遐迩之情,为后先之证,而文字之需要,乃随世运而生。吾国之文字,实分三阶级:一曰结绳,二曰图画,三曰书契。是三者,皆有文字之用,而书契最便,故书契独擅文字之名。[注]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第25页。
在这段话中,“范围渐广,传说易歧”点出了文字书写符号产生的缘由。在人们针对语言文字起源的研究中,法国思想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其名著《论文字学》(DelaGrammatologie)中提出了独到的观点:“使手势变成言语的社会距离扩大到变成缺席的程度,正是在这时,文字成为必要。”[注]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409页。加粗为原文所有。德里达的主旨并非去探索文字起源的一般性史实,而是要以从口语到文字书写的现象来支撑自己的一个重要思想,即通过论证文字书写的在场与缺席以构建其直指西方逻格斯中心主义的解构思想。因此,语言自诞生伊始,不仅与人类的生存需求直接相关,使人们拥有必须的交往技能,而且其发展也与人类的社会文化和思想认知同步深入。语言的这一神奇作用是其他任何文化形式都难以替代的。因而不难理解,在中国现存的文献中多见对文字创造的想像性说明,以突出其神秘性力量,如许慎《〈说文解字〉序》中所言,“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注]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53页。以及《淮南子》中“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注]高诱:《淮南子注》,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第116页。的说法。类似的对文字神秘性的膜拜态度的表达,在纬书中更为丰富,如《春秋元命苞》:“仓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刚。龙颜侈哆,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及受河图绿字,于是穷天下之变化。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治百有一十载,都于阳武,终葬衙之利乡亭。”《龙鱼河图》:“黄龙附图,鳞甲成字,从河中出,付黄帝。”[注]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90、1150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而将文字与万物、文章乃至民间生活关联最为紧密的论述当属刘勰的《文心雕龙·练字》:“夫文象列而结绳移,鸟迹明而书契作,斯乃言语之体貌,而文章之宅宇也。仓颉造之,鬼哭粟飞;黄帝用之,官治民察。先王声教,书必同文,輶轩之使,纪言殊俗,所以一字体,总异音。”[注]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43页。这一段话从汉字创作的传说过渡到文字的统一及特点,可以说是对汉字的社会文化功能最为简要且清晰的说明。
由于人类群体在各区域发展方式迥异,因此历史文化的复杂性也往往体现在各自不同的语言上。各区域的群体在其最早的地理定位时期,一般都有两种大致相同的生存方式,一为适应性,亦即其生存须适应其外部条件;二为创造性,亦即在此条件下创造持续生存的可能性,二者构成了自然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主要发展路径。[注]有关“自然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两种分类方式,参见劳思光:《文化哲学讲演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vii-viii页。但需要提及的是,这两种发展方式均与语言的生成和演进同步。由于不同的语言带来了交往的困难,所以如何跨越语言羁绊以达到有效交流就成为语言文化领域中的重要内容。实际上,各个文化区域对于人类为何没有使用统一的语言有着种种传说,例如最著名的巴别通天塔的故事以及上帝命名说:“亚当取名的故事将语言的起源阐释为某种在我们周围罗列事物的方式。第二个故事解释了为什么‘整个地球’没有使用‘同一种语言和同一种言语’。因为上帝为了束缚人类,故意以此来‘困惑’大众。”[注]P·H·马修斯:《缤纷的语言学》,戚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6页。由于各群体的生存经验不同,各国语言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都不同程度地留下了各具特色的语言文化轨迹。其中,中国早期对文字书写的统一就是文化史中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它不仅使自己的语言文字作为整体得以延续,形成了文化认同,而且可以说是世界文化史中的奇迹。这一现象也为国际汉学家所注意:
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文明都记载了人类的活动,但是只有中国文明保留了自己完整的文字特点并延续到了现代。它拥有六千年的文字史,这使其异常独特。……这归咎于中国的书写系统,这些令人着迷且神秘的词汇,几乎每一个都内含了历史、文学、艺术以及民间的智慧。[注]Edoardo Fazzioli, Chinese Calligraphy from Pictograph to Ideogram: The History of 214 Essential Chinese / Japanese Characters, New York,London, Paris: Abbeville Press-Publishers, 1987, p.9.
因此,语言与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着一个互为结构的关系,语言在其社会进程中不仅发挥了无可估量的文化作用,同时也构成了最为凸显的文化特征。这是因为,“语言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有关系”。[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卷9,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238页。换言之,语言本身亦是文化难以分割的一部分。由于每一种语言都附带了与其密切相关的文化标识,后者又往往构成文化象征,所以语言的魅力和复杂性也正在于此。
二、语言表意的文化线索
不同种类的语言文字,其共性之一是多围绕文字的形、音、义之间的交织关系展开,而其中历史沿革的方式,尤其是技术条件以及与其他文化的交往融合,会使不同的语言系统具备一定历史阶段的文化独特性。例如,中国早期文字的书写系统就与铭刻等技术条件密切相关,这一历史相当漫长。经考古发现的“楚帛书”和“汉帛书”等古代书写材料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而竹简则从战国沿用到魏晋时期。由于当时书写成本居高,中国古代汉语中的一音多字、一字多义、字功能大于句法等特点是一种历史性使然。汉语文字的发展,与书写工具、文字载体以及印刷技术的逐步改变有关,包括雕版印刷和近代从竖排改用横排印刷的历史,也与社会文化的发展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特别是外来文字的不断进入有着密切的关系。概言之,语言文字的特点多与其外部确定性条件密切相关。而中国语言及书写文字的简约特点又最能表达古代中国人对天、地、人的观察和解释,因为对世界万物而言,以少总多、以简驭繁、语简意远、虚实相生、境生象外等方式不仅是最具诗性的表达,同时也是最能使读者通过有限的文字符号接近事物本身的途径。《易经》《老子》《庄子》等文献中都有大量极富特点的中国语言观。中国古代律诗本身的意象特征,也是充分利用了汉字以象形为基础的特点,这一点也为西方学界所看重。[注]See Pauline Yu, 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其他相关的论著还有:James Y.Liu, 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Stephen Owen, 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可以说,中国古代诗论中的诸如“语贵含蓄”“言有尽而意无穷”等对文字表述的美学追求源远流长。[注]参见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81、688页。而且重要的是,这一语言体系亦与中国思维方式以及思想世界直接相连:
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古代中国文字的象形性,还应该注意的是这种象形性延绵不绝地使用及其对古代中国思想世界的影响。……以象形为基础的汉字长期的延续使用,使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始终不曾与事实世界的具体形象分离,思维中的运算、推理、判断始终不是一套纯粹而抽象的符号,中国文明的连续意味恰好就在这里。[注]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1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7页。
就语言变迁的线索而言,在汉魏之后,汉语的书面语与口语逐渐分离,致使词汇的差异开始增大。至晚唐五代,诸多文献,例如《六祖坛经》和敦煌变文等材料,都出现了大量的所谓非正统表达,其中尤以寒山诗表面浅白,实则意在言外的表达具有代表性。[注]See Robert G.Henricks, The Poetry of Han-Shan: A Complete,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Cold Mountain,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另参见关于寒山诗研究者斯奈德(Gary Snyder)的重要论著:Joe Haper, ed., Gary Snyder: Dimensions of a Life, San Francisco: Serra Club Books, 1991.其实,汉语的历史变迁与扩容除了自身的社会文化的演进,包括科举等文化制度之外,还与一些文化事件,如佛教进入中国,利玛窦(Metteo Ricci)、理雅格(James Legge)等众多西方传教士对西学和中国文献的双向翻译和论述,乃至近代从日本和欧美不断引入的表达等密切相关。[注]See Jonathan D.Spence, 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 Viking: Elisabeth Sifton Books, 1984;Benjamin I.Schwartz,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The Belke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S.Robert Ramsey, The Languages of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John DeFrancis, The Chinese Language: Fact and Fantasy,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4.例如,当时在佛经翻译中往往借用“格义”等策略,使得汉字获得了扩容,“用中国哲学术语(主要取自《老子》、《庄子》和《易经》)来表述佛教观念,这是‘格义’常见的解释”。[注]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李四龙、裴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67-268页。上述的文化事件、跨文化交流、译介以及改写活动不仅使汉语增加了诸多词汇,而且在欧洲形成了新的学术领域,即基于语文学并针对文献进行研究的传统汉学(Philology-based Sinology),[注]有关科举制与汉语发展之间的关系,参见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汉语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有关基于语文学的欧洲传统汉学,参见David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1.有关汉语词汇与现代汉语的发展,参见Philip J.Ivanhoe, ed., Chinese Languages, Thought, and Culture: Nivison and His Critics, Chicago: Open Court, 1996.只是进入近代之后,这一基于文献的西方汉学传统才开始发生现代转型。[注]参见王晓路:《中国大陆汉学研究范式问题:回顾与反思》,《国际汉学》2015年第5期,第5-10页。
汉语的发展犹如中国文化一样,既有一个不断与周边交往和融汇的历史性进程,也有其自身持续的演化。[注]参见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序。另参见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2页。事实上,自宋代至清代,从黄河流域迁徙至长江流域的群体逐渐增多,交通规模、生产方式和日常生活样式与中古时期相比,业已完全不同。城镇规模的扩大,钱币的改变,店铺、作坊及行会等商业活动与地方戏曲、方言使用范围的蔓延、茶楼说书、章回体小说的产生等社会文化现象汇流,成为这一时期特定的文化形态。这无疑对语言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口语词汇开始大量进入文学,而且其中的双音词汇的表达日趋明显。语言的丰富与成熟也使中国学术的脉络日益清晰,我们今日所谈的六艺、诸子、经学、黄老术、玄学、理学等都与语言的发展阶段相关。[注]参见林尹:《中国学术思想大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总之,历史有多种线索和细节,对任何一种历史对象的探寻首先需要梳理多重线索进行历史还原,将一些表面上没有直接关系的历史支流连接起来,以重新审视那些未被写入历史主流的“低音”,因为这些线索可能恰好是历史的汇流之处。“在这里谈‘低音’并不是在提倡‘复古’或者是对传统模式毫无保留的回归。我所要说的是一种‘重访’(revisit),重访许多近百年来被新思潮压抑下去的学术论述、重访许多被忽略的面相、重访一些基本的问题、重访一些近代保守主义者为了回应新派所作的过当的扭曲、重访近代主流论述形成之际发生的重大分歧的过程等”。[注]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3-4页。文化交往史与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界非常看重的。就中国文化与外部世界的交往而言,欧洲一些大学,如荷兰莱顿大学的系统研究成果值得特别重视,例如他们以比较眼光对中西文化交流史进行了专题研究,其重要成果之一《历史事实、历史批评与意识形态:全新比较视野中的中国历史编撰学与历史文化》[注]Helwig Schmidt-Glintzer, at al., eds., Historical Truth, Historical Criticism and Ideolog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cal Culture from a New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eiden: Brill, 2005.就是一部值得重视的成果。
毋庸赘言,语言随着群体的社会生活变迁而不断产生着变化,在经验复制和知识共享的学术活动中,语言都是其中不可剥离的构成性要素。人们无论是对现存文献的把握抑或解释,还是对自身的认知和领悟进行言说,都需要对语言本身的意指以及语言背后的涵盖范围有比较确切的把握,亦即需要对语言本身以及语言文化进行系统的研究,“事实上,每一门科学至少包含了一种语言内容,即会涉及与其理论和观察有关的语言”。[注]Adam Kuper and Jessica Kuper, eds., The Social Science Encyclopedia,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5, p.371.因此,在语言与文化并置的历史进程中也逐渐形成语言自身的学术系统。近代国人对新知的需求、语音统一之官话的体制化实施、白话文运动、大众传媒的兴起,尤其是摄影及画报所带来的图像世界等各种历史事件,都使中国语言发生了深刻和持续的变化。而移民和迁徙也使汉语的使用范围扩至各大洲的众多区域。实际上,这一历史变迁一直呈阶段性发展,西方汉学界就对中国在16至19世纪的史实做了相当多的历史发生学解读,例如D· E·莫基洛的名著《16—19世纪中国与西方的遭遇》[注]D.E.Mungello, 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 1500-1800, 3rd Edition,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9.就是这一分支领域的代表作之一。
今天,使用汉语的范围已不可同日而语。汉语及其所承载的文化随着中国高速发展,不仅是国人认识和传播自身价值体系的工具,也是国家之间理解和沟通的重要桥梁。由此,汉语及汉语文化上升到了国家形象和文化战略的高度。今日中国对自身文化的对外宣传以及对外国优秀文化的引介,均会涉及许多具体的语词使用及其跨文化转换问题。这些词语所附带的文化内涵以及在翻译转化过程中的不等值特征,不仅涉及当代表达的跨文化理解和诠释,而且其重要性直接关乎当代国际文化间的互识、国家形象、文化特质等诸多重要问题。因此,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语境中,跨文化传播中的基本问题之一首先涉及基本词汇转换的有效性,因为对这些基本词语的表层翻译或自我认定不仅会造成不同层度的误读,而且可能导致某种文化误解的后遗症。在此,本文仅以最具中国文化象征意义的“龙”为例加以说明。
三、语言转换的非等值特征:“龙”与“Dragon”
在中国文化中,“龙”是最具象征意义的文化想像性的图腾,同时也是最具“神力”的象征物。“《说文》十一:‘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据此,则龙盖神物。古者神人多乘龙。……《易》曰:‘云从龙。’又曰:‘飞龙在天。’”[注]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第117页。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所谓“四灵”,即《礼记·礼运》中所谓“麟、凤、龟、龙”,其中的“龙”不仅为“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善变化能兴风雨利万物的神圣动物”,而且“飞龙在天,大人造也。(《易乾》)”又将之比喻为皇帝。[注]参见《辞源》(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962页。中国“龙”的相关说法也为西方学者所认同:
龙是中国最为复杂和多级的象征, 它结合了几乎所有神话和宇宙观。“龙”(long)内涵了多种杂糅的存在,与西方观念所不同的是,中国龙是一种吉祥的创造物:象征阳性力量和富饶。从汉代(206BC-AD220)开始,龙也象征着皇帝,即天子(the Son of Heaven)。[注]Wolfram Eberhard,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Symbols: Hidden Symbols in Chinese Life and Thought, Trans.from the German by G.L.Campbell,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6, p.83.
这一认知也反映在一些权威的百科全书中,如《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说明:龙是“中国神话中的神异动物。传说能隐能显,春分时登天,秋分时潜渊。又能兴云致雨,后成为皇权象征。历代帝王都自命为龙,使用器物也以龙为装饰。但远古传说中龙可驯养。帝舜时董父、夏孔甲时刘累和师门都能驯龙。龙还可以供人乘驾。《山海经》记祝融、夏后启、蓐收、句芒等都‘乘雨龙’。另有书记‘颛顼乘龙至四海’、‘帝喾春夏乘龙’。前人分龙为四种:有鳞者称蛟龙,有翼者称应龙,有角者称虬龙,无角者称魑”。[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卷5,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367页。显然,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中,由于对于自然现象的不理解和敬畏,各文化区域的群体都以不同方式借助一些想像进行象征性解说,继而使自身的文化形象合法化,这无疑依靠了语言本身所承载的解释和联想功能。“人类发明语言,与其说是为了沟通,不如说是为了解释”。[注]杜君山:《历史的细节:技术、文明与战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第1页。于是,人们出于历史阶段的认同需求,往往对同一文化象征物进行不断的解释,从而在不同时期的历史转述中获得不同的文化编码,形成文化形象的固化,以适应并发挥出不同的文化认同功能。于是,各文化区域中的神话传说以各种方式不断进入区域群体的集体无意识中,逐渐成为区域整体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不难理解,各文化区域在其早期社会进程中,均有一些类似的巨型怪兽的传说,只是所呈现的具体形态、行为以及附加的文化寓意各不相同而已。这些神话传说往往通过意象形成特定的表述形式和认知形式,所以,“神话是一种基本‘象征形式’,类似于语言,是对世界的回应,从而创造世界。然而,与语言不同的,至少与语言哲学不同,神话不是知识的,不是散漫的,而是典型的意象的。它是表达我们经验的基本的、充满感情的、没有中介的‘语言’”。[注]查尔斯·里夫斯:《神话理论与批评》,周丹、王晓路译,迈克尔·格洛登等主编:《霍普金斯文学理论和批评指南》(第2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第1043页。所以,一些基本词语是进入文化编码和文化记忆的关键,对于这些基本文化词语,在后期的跨文化诠释中都有一项历史还原的基础性工作,而非是表层的或自我认定的“等值”,这是跨文化传播有效性的前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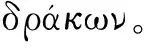
最早将中国人的龙观念介绍给欧洲的,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这些介绍集中体现于金尼阁(Miclas Trigault)整理出版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1615年)。利玛窦在手稿中一般将龙写作Dragoni,有时写作Dragone。1616年,金尼阁的侄子小金尼阁(D.F.Qiquebourg-Trigault)将此书译成法文时,一律将龙译作Dragon,这大概是中国“龙”与西方Dragon的第一次完整对译。[注]施爱东:《中国龙的发明:16—20世纪的龙政治与中国形象》,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10-11页。
由某种象征物联想到群体和文化特性,一直是跨文化理解中的难题。人们在一种所谓地理区域的信仰系统的分割方式中,总会采纳截然对立的或以一概全的方式对其他文化进行想像性,甚至是偏见性述说。[注]See Jonathan D.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and London: W.W.Norton & Company, 1990, Part 6, Chapter I,“Western Images of China”, pp.132-136.欧洲对于中国乃至中国文化的理解就大致经历了最初的神秘感、想像到晚清时期的鄙视阶段。大卫·马丁·琼斯的重要著作《西方社会与政治思想中的中国形象》[注]David Martin Jones, The Image of China in Wester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New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1.对这一历史线索的分析、描绘,可以说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其间,中国“龙”的吉祥含义被逐渐转换成皇帝支配性的身份象征到后来又成为整个国民的“猪尾奴”等贬义指涉,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注]参见施爱东:《中国龙的发明:16—20世纪的龙政治与中国形象》,第五章“辱华词汇‘猪尾奴’的递进式东渐”。只是这种对中国文化从迷恋到嘲笑的转变在近代的发生相当快速,就连美国当年最著名的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 Williams)本人也感到惊异,“1845年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回国时,注意到这样的变化。1833年他去中国时,虽然有关中国的信息匮乏,但美国人仍然痴迷中国。耶稣会传教士的记述、神奇的《一千零一夜》故事和中国商品上田园牧歌的形象,这一切协同作用,给美国人的民族意识里灌输了这样一个理念:中国别具一格、令人神往、美妙无比。然而回到美国时,卫三畏却惊诧地发现,公众舆论的中国形象一落千丈了。在十来年的时间里,曾经令人倾慕的中国人却成了被嘲弄的对象”。那一时期正是满清政府与欧美各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特定历史时期,所以这一观念转变的历史语境相当复杂,其中既有国家发展的历史阶段所形成的对外部世界认知的改变,也与当年信息的输入和媒体的刻意宣传不无关联。如1876年美国费城承办了万国博览会(世博会),当时在一种以大机器为代表的工业文化氛围中,美国及欧洲人对当时中国馆展出的传统手工艺产品除了依然感到好奇之外,也增加了鄙视心理。在当时媒体的报道中,中国展品在欧美人眼中已然失去了早期的那种异国情调式的东方魅力,“一个记者认为,中国馆象征中国人缺乏‘往前的冲劲’。他认为,这个严重的缺陷妨碍了中国加入面向未来国家的大家庭”。[注]以上引文参见约翰·海达德:《中国传奇:美国人眼里的中国》,何道宽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年,第179、317页。其实,对非我族群的文化认知都有一个从自我文化立场出发去想像的进程,中国对其外部世界的理解过程亦如此。例如,中国将外国人与“鬼”关联,当与《山海经》这类文献所描述的异族形象不无关系,而中国古人对一些地理方位及其方位群体以“狄”“夷”“蛮” “戎”等词汇加以归类时,也都有一个认知的历史过程。当年一些传教士进入中国进行实地考察时,大多是从自己的信仰出发而非从中国文化形成的自身条件去理解中国文化,如“利玛窦和夏尔都很了解中国。他们通晓中国文化、接受汉民族生活习惯。而对发达的华夏文明,他们并未采取一种殖民主义的征服态度或者野蛮地改变中国人的信仰。但至少根据基歇尔的看法,利玛窦和夏尔去中国是为了让中国人明白,中国文化是更古老的埃及——基督教文化的糟糕‘译本’。而他们所负的使命就是把中国带到西方科学创造的奇迹面前”。所以,中西二分法的观念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中国和欧洲这两个伟大的人类文明就分别落到了欧亚大陆的两端。在争取第一的对抗中,中国对欧洲提出挑战,两者各有胜负,就生活的优雅程度、伦理学、政治学而言,中国胜于欧洲;而在抽象数理科学、形而上学方面,欧洲却是遥遥领先”。[注]翁贝尔托·埃科:《他们寻找独角兽》,蒯轶萍、俞国强译,乐黛云、勒·比雄主编:《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8、11页。但是,深入研究过中国科技史的李约瑟对此却并不认同,他对于所谓普遍性和优越性有着清醒的认识:
在西欧以及欧洲体系的美洲的许许多多人深受所谓精神优越感之害。他们坚决认为只有他们自己的文明才是唯一具有世界性的文明。他们对于其他人们的社会文化思想和传统一无所知,所以觉得理所当然地应该把他们自己的思想意识和传统习惯(无论在法律、社会民主或政治体方面)都强加给其他的人民。[注]李约瑟:《四海之内》,劳陇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第1页。
因此,唯有深入了解某一文化,才有可能避免一些有意或无意的误读。当中国“龙”在英文论述中被反复转换为“dragon”而又缺乏必要的解释之时,文化误读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其实,这一类文化专属词语,需要借用拼音方式进入言说,即用表层为拼音文字符号的形式进入跨文化的语境中是有必要的,在此基础上再进行语境化的阐释,使之逐渐得以被领会和接受,因为,在这些词语被认可之前,以斜体(为避免与其本国语拼写相混)的拼音方式一般会在西文阅读经验中产生陌生化效果,对于这样的“新词”,非母语读者会比较注意,而且也必须借助于相关解释才能贴近该词的文化内涵,以此避免某些误读。需要注意的是,其中阐释的有效性相当重要,也是跨文化传播中的难点所在,所以需要进行专项的工作,其意义是对文化的基本代码进行历史性还原的同时建立有效的跨文化话语单位。在这方面,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也做过一些尝试。他在《中国文学思想解读》[注]Stephen Owen,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583-596, “Glossary”.一书中,专门采用附录的形式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些术语以威妥玛拼音方式进行了对照处理。最值得称道的工作当属当代西方学界两本权威的文学工具书,其一是《新普林斯顿诗歌与诗学百科全书》,撰写者将此书中“中国诗歌”(Chinese Poetry)和“中国诗学”(Chinese Poetics)所涉及到的专门术语,均以现代汉语拼音方式呈现。[注]Alex Preminger and T.V.F.Brogan, et al.,eds., The New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Poetry and Poetic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187-200.中译参考《中国诗学》,祝远德译, 王晓路校,载《东方丛刊》,2004年第3期,第21-26页。其二是《约翰斯·霍普金斯文学理论与批评指南》,几位著名的西方学者在论述“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时,对其中的专门术语也采纳了现代汉语拼音形式。[注]Michael Groden and Martin Kreiswirth, eds., The Johns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 Criticism,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46-159.中译参考《中国理论与批评:1.前现代诗论;2.前现代小说和戏剧理论》,王晓路译,载迈克尔·格洛登等主编:《霍普金斯文学理论与批评指南》,王逢振等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第299-312页。由于这两部工具书的影响很大,所以其中以汉语拼音呈现的专门术语获得了重视。前面提到过的工具书《中国象征词典:中国生活与思想的象征》,不仅采纳了现代拼音,还注明了相应的汉字,如“Dragon-Long-龍”。[注]Eberhard,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Symbols,p.63.概言之,此类基础性的工作十分有必要,这是因为,“文化的基本代码(那些控制了其语言、知觉框架、交流、技艺、价值、实践等级的代码),从一开始,就为每个人确定了经验秩序,这个经验秩序是他将要处理的,他在里面会重新找到迷失的路。而在思想的另一端,则存在着科学理论或哲学阐释,它们阐明了为什么一般来说存在着秩序,它遵从什么普遍规律,什么样的原则能说明它,为什么是这个特殊秩序(而不是其他的秩序)被确立起来了”。[注]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8页。
结 语
在当前的历史语境中,“中国文化走出去”无疑会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若干基本范畴和命题,[注]相关的一些工作西方学界正在进行,如A.C.Graham, Studies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ical Literatur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这本论著在探讨中国传统哲学时,专门就中国传统哲学命题和术语进行了现代转向研究。而语言依然是其中最为基本的问题和最为基础性的工作,“不管人们如何理解,语言问题也许从来就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问题。但与今天不同的是,它过去从未像现在这样渗透到形形色色的全球性研究领域以及在意向、方法和思想体系方面千差万别的话语之中”。[注]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第7页。需要注意的,进行此项工作并不是对中国历史文献的单一重访,而是需要思考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关联。因此,我们在深入研究中,除了需要继续挖掘这些元命题和范畴的丰富内涵之外,也必须通过跨文化视角深入探讨这些命题和范畴的命名、诠释与接受问题。而唯有在学理的层面上进行引介,方能在特定的知识范围内建立起学术共享的基础,以达到平等对话,与此同时,才有可能使之成为对话方认真对待的文化经验和话语陈述。对此,学界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透彻的把握,包括样本、筛选以及方法等一系列工作,这关系到中国文化的持续发展以及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的脉络与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