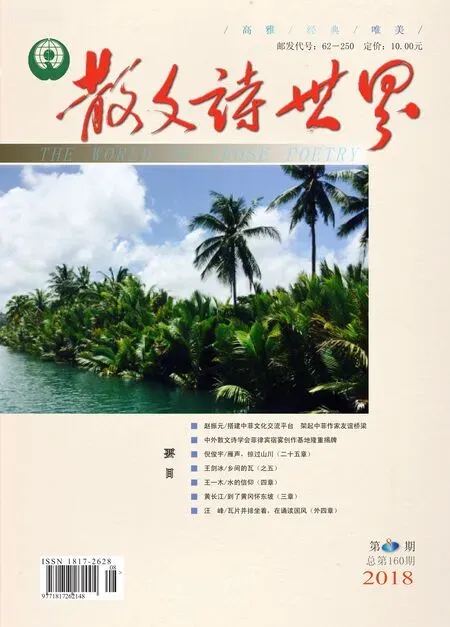瓦片并排坐着,在诵读国风(外四章)
江西 汪 峰
左腿搁着右腿,我是说乡间两条交叉的小路。我是迈左腿还是右腿呢。黄昏的时候,我像萝卜一样拱出泥土,探望着这样一个有着传统色彩的乡村,我是说我的乡村情结。要有柿子树,因为毕竟是冬天了,光秃秃的树枝上有那么几粒亮色。每一颗都像从院子的胸腔里跳出来,有着欢蹦乱跳心脏的农民兄弟。当然还要有土墙,土墙这东西像棉袄一样。我们中国人,几千年,都靠这个棉袄。土得掉渣了一些,但适用。总有老人坐在墙下,像慢时光。当然也有玉米、辣椒,这一连串的亲戚,靠在土墙上,把阳光纳进鞋底。他们是乡间的明星,已成传统的老歌,唱的人少了。再少,还有人听,还有人在自身的温暖中耳语般敞开。都这个时候了,我还保持一本正经,像一个会左顾右盼的石头,把自己的目光缩在坚硬的衣领里面。碰见喜鹊就恭喜,碰见乌鸦就口渴。碰到一条摇尾巴的狗,就扔过去,溅湿一大片狂吠。
屋顶。瓦片并排坐着,像先生领着学童,风一吹就摇头晃脑,它们在诵读国风。幸福就像痛苦一样,幸福是短头发,痛苦是长头发。黑压压的。重而黑的瓦,重而黑的国风。被翻晒、腌制,阳光母亲一样,低着北方的头侍弄着南方。瓦片割破的手指,淌着血。瓦片碾着骨头嶙峋的痛。瓦片腾跃着龙鳞。炊烟知道种树,就在瓦片上往上长,往远处长。知道梅花骑马来了,知道白雪在老树上抖动。知道月光就是大蒜门口遇到的芫荽,长得郁郁葱葱香气扑鼻。鸡与鸭是一朵花和另一朵花,它们暂时还固守在笼子里向你温柔地抛媚眼。痴呆了一夜,转眼在胡须里住了下来,霜就老了。
村庄被一条路牵着。晃晃悠悠。一头牛在夕阳的余光中,背上没有笛,只有老迈的皮,闪着宁静的光。
石板路
我喜欢那种被碾着的感觉。被独轮车碾着,在身体的痛处,开一道深槽。我喜欢二胡的感觉。两根弦吃进松香,沉沉的流水,溢满街巷。我喜欢承担,少年的欢愉,老人的哀愁。当然,我承担较多的是时间的悲欢。还有身体里的裂纹。阳光和月光在木窗中剧烈摇晃。春天和秋天,泼下的颜色很浓。必须收起马背和弓弦,在你面前放下沧桑。必须的,雪花代替菊花,如果我还有用,就应不断用匍匐来偿还对你的亏欠。吹吹打打,狮吼龙吟,或者雨水和青苔漫浸。从喧闹到孤寂,或从孤寂到喧闹,总是积水的二胡声。今日,我把二胡架在老街。等于把一条内心的河流引入:沉下去的是斑斑驳驳,浮上来的是日月星辰,是咸咸淡淡。
水 井
哎,睡不着就不睡,一万年都睁开眼。在故乡落脚生根,永远是喜悦扩散出涟漪。
哎,我背着水井走路。月光在上,八千里路云和月。我背着骨头和木柴,燃烧和熄灭。
但水井不走。母亲的目光是井水。洗得我火烧火燎,洗得我彻骨之痛,洗得我体无完肤。
哎,邻家妹妹的眼里也有一个井,太深重了,我二十年前扔下去的水桶,现在都没有拎上来。
石拱桥
扁担一样,一头挑着故乡,一头挑着异乡。在头顶还顶着一个月亮或一个太阳。这样说着,脚下还踩着一条河流。这样说着,有一头牛经过石拱桥,牛背上有牧童和短笛;这样说着,还有一架花车经过石拱桥,手推花车的壮小伙子手臂上的肌肉结实,滴着汗,而花车上有一个红棉袄的姑娘哼着温软的哩曲,脸上红扑扑。这样说着,还有一个人会经常站在桥上,她的脸和泥土上的裂纹差不多,她的白发像炊烟一样在晚风中摇曳,她的目光因向远方凝望得太久而被晚霞烧红烧伤。这样说着,石拱桥和桥上的一切都会成为影子,会被风吹进河里,几经岁月的沉淀和漂洗,变成了一幅深藏在心底,挥之不去的风俗画。
茅 草
故乡河畔狂长激情的茅草,身体被猛烈地摇晃,直至大地或黄昏在剧烈地倾斜。
我为什么想到茅草?我为什么想到信江河畔吹笛的人?他那么深入,每一次吹奏,都如从水底走过,这个饱经风霜的人,最后茅草缠身。
哎,在孤愤中写作,我应该去赞美,而不是用明晃晃的刀去砍杀。时间是锯齿,这不,我又被砍倒一大片。
哎,野雀是茅草的伤。它一飞一掠都像从茅草中划过,最终会入驻寒风的洞口。
这世上,总有一种声音是难受的,因为我被割伤了。所以要用笛声惊动河流,要逼迫野雀纵跃、茅草返青。
该沉到水里的就沉到水里,该打捞上来的就打捞上来。故乡可以养育茅草,我也可以,这不,手指拨弄茅草,手指就是茅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