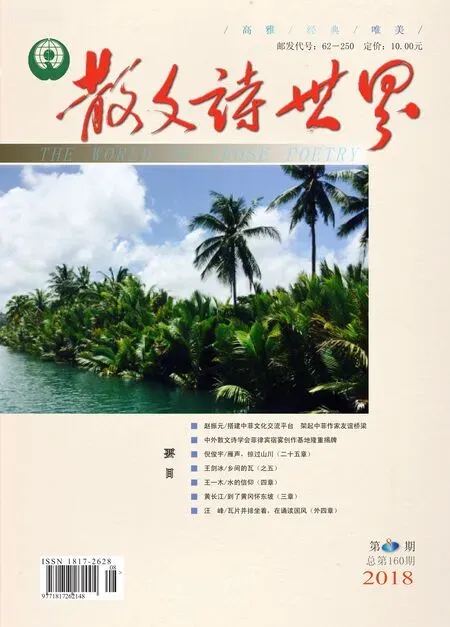烈日灼心
甘肃 孟甲龙
一
砚台上的墨痕和铁锈殊途同归,异乡人归去来兮,篡改了龟壳上记载的家暴史。
留声机磁带倒转,做了背井离乡的导火索。
穹顶之下,是大地编排出的十四行春江花月,是八百里曲觞流水,是我写满母爱的羽扇纶巾。
生活的秩序和齿轮倾轧着童年的车祸事件,无数次逃避,逃避一日三餐,逃避柏油马路,危机解除后又归于桑梓。
经常想起被货郎人践踏的女孩、野草、白衣蝴蝶和一句诗——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
睡前故事没有逻辑,自然不具备量子力学和哥德巴赫猜想的魅力,只是提及了行吟诗人词根深处的一点乡愁,亦或族谱里失去作用的金科玉律。
光阴的骨骼被露水淬炼成日渐崩坏的世界。
在故土,人们拒绝膨胀的所有形式。
在故土,两袋糯米的肾脏从未走出荒诞情节,只有丰腴青春退出了日程,缩成微小斑点,却是我的核心梦境。
在故土,阳光没有私心,修缮着亲人的高低床。
二
奶奶死前父亲找来医师,可本草纲目终究抵不过一场大雪的喧宾夺主。
暴雨降临,牧羊人在机械表的催促下更显臃肿。
蚕蛹在三十七度的培养箱里弹奏命运的交响曲,也效仿着一片桑叶的唯心主义。
妹妹夭折的第二夜,父亲呼天抢地,招来阴阳师,驱鬼降魔,剔除了附属在茅屋的虫蚁,剔除了附属在厨具的细菌,剔除了黄土诅咒。
长夜是绝佳的痛,长夜是故乡在一根根白发上老去,长夜是回家的路。
迎亲马队沿着河西走廊跋涉,姐姐,嫁在西北以北。
梦中问故人,磨坊里的姑姑是不是剪断了贫瘠的脐带,把农作物的长势嫁接在大数据的胶带上,勾勒出家族的走势图。
用生理盐水洗净手术刀,切开一盘车厘子,奶奶说生活的引力无形间带给自己半生困惑,比如七个孩子。
给杂草和蚱蜢加持,重复祖先的求雨术,唯一的麻木感并非别墅区的绿色地带,而是消失的爱人和今夜白露、故乡明月。
三
背叛土地的高脚楼插入眼眶,毒虫漫步在走廊,母亲没有追逐它们,我也不躁动,和垂体旁的良性肿瘤一起游弋旷野,一起走进伊甸园。
用青花碗赡养猫、老鼠、长蛇、蜈蚣和儿子;用泪水给父亲的农具洗澡;用果脯、啤酒、鹿肉安慰流浪人。
尘埃折射出复活的伊索寓言,和天下人通信,子夜的霓裳脱落以后,清澈露珠必将灼伤我的眼球。
惊慌流窜的星子只会安居在羔羊出生时的木槽,比如我,只会安居在一尘不染的墓地,或半亩方塘。
蛰伏于白色画板的天光云影,照亮了游子回家的路。
让月光暴晒玉米粉和高粱籽。
星辰和呓语藏在词本,银簪以嫁妆的名义被人供奉,屠戮时光二十四遍,我才爱上遒劲风声和温柔的雨,并和枯叶拥吻。
墙上的油画里一群马在歌颂森林,决绝者摘下野果喂养它们,顺势而为温习了进化论,不再惧怕贫困。
我脱下流苏裙与守夜人交谈无神论、色欲、创世纪,交谈冰川时代,交谈村里八个光棍的未来。
要么戴上面具隐居在浅黄弹壳里,要么和狐狸一起睡在木桌上,沉沦着呻吟,沉沦着长大。
我的卡带里只有浓烈乡愁,在子规的喉咙上演游子吟,最后回归于家的副本。
铅笔在书桌上等待主人,续写石头记和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四
贫瘠伙同盛夏把剩余的蔬菜一饮而尽,盛满萝卜汁、玉米粉的炊具也将生锈,也将溶解于忏悔录。
向死而生做了虐心小说的主语,大与小都在逐渐消亡的途中,过程不重要,而结果肯定是关于一首《天涯歌女》的舍生取义。
妄想不能解决外界与村庄的利益冲突,因为社会主义比泪水更迫切,比土地更理性。
孤独比做爱绝妙,不能反驳轻核聚变、重核裂变,物理笔记除了相对论引领的骤雨狂风,还有关于诗与远方的断片。
爷爷遗留的财产只有木质马车和铁犁,却是子孙的新宠。
拆解乡愁,衍生出更年期的活色生香,泼洒在羊肠小径,做个研究学术的专家,编造生活里最淫秽与荒谬的部分。
哮喘声是时代的病灶,也是剥落杏花春雨的幕后推手。
异地求生,命挑在指尖,险情山水收养了猎狗,只能偷偷回忆越过雷池的麦苗和大脑里趋之若鹜的归属感,我没有回家的路。
五
拉卜楞寺溶解了多少善男信女的滚烫欲望,比如牧师讲过的良人未归,比如站街女的叫卖声。
性冷淡不再是病变的美丽称呼,为了避免灵魂被玷污,我刻意绕过风情酒店把初始热忱完整无缺地保存在一页乡愁的宋体字。
黑色玫瑰与彩虹桥格格不入,流浪人把捡到的石头回赠予乌鸦,我的田园没有碑文和皇家守卫军。
把祖传了三个世纪的舍利子变卖成铜币,给祖宗修葺墓碑,刻上墓志铭——如此洁白,至高无上。
亲人不忌讳名中重复的字,除了不可篡改姓氏,任意平、仄声字都能入谱。
灯影在时间的齿轮里摇滚着;牵引异乡人的绳索在暮色里缠绕着;道路两旁盛开的芍药在雨夜狰狞着。
远方爱人是否也如我一样,借着血的温度野蛮生长,借着血的温度慰藉夜行人的喜怒哀乐。
吊坠镶嵌在《百年孤独》,如我沉默寡言,如我上善若水,如我潦倒无名。
凌晨三点发现花未眠,香气溢满青木地板,又流进茶几上的汤勺,折射出最尖锐的饥饿感。
以空无、碟片、唱机为食材,烹饪光年,我知道,母亲的泪水才是唯一的现实。
六
一抔黄土正在被都市淘汰。
在故乡,潮湿的火种也能胜任主宰命运的王,我也会酣睡,和偷运诉状的判官狼狈为奸,娶了妻子。
依旧不敢给母亲倾诉遇见的万状惊恐。
藤蔓推动日历的电轨,砖块扑灭了最后一束火焰,哪天才能挣脱缚茧,飞到油菜花海。
黄雀趁着月黑风高,吞食了一只迷路,亦或寻食的螳螂,行动触发了灶台上捕鼠器的开关键。
九月授衣敷衍了种子,亲人带来故乡山川,闪烁着泪水般的银光。
看不懂符号学、简谱、宫商角徵羽以及刺绣在衣领上的麦垛图。
稳婆偷偷告诉我一个秘密:母亲曾经分娩下畸形胎儿。
把颠沛流离磨成纵横灯火,不玷污每一页诗,不惊扰寡妇,不染指成名作家的复制品,不浪费生命。
明天的旅途依旧可爱,南开的绿皮火车走了,恋期未满,爱人就死了,疼痛触手可及。
伏案疾书,狼毫剥落光鲜,案牍承载着时光鳞片,我也监守自盗,说了虚假情话。
七
暮色跌进沟渠,伴随着预言涅槃。
时间妥协了不安分,肌肉开始萎缩,透析结果表明,白细胞正以次方的形式递减,指纹、耳膜、睫毛、脂肪与唾沫也一一告急。
秋风甚嚣,吹干了长满栀子花的坟茔,我奔跑在草丛用单调行动制造隐秘乡愁,不提前预支锐利事物——麦芒,佯装出富裕状态——牧羊人。
冥币、神性不仅是恩宠之物,更是故乡的一阕悼亡辞。
痛觉长短不一,性生活砸开了身体封条,经年铜镜沿着反射弧照亮锁孔,我不能拉开火柴盒,成为点燃秸秆的始作俑者。
淬火煅烧,直至吻痕成为艺术,把处男情节献给田园诗人。
骨骼在炊烟中精美绝伦,青灯之下,我想起了母亲松垮黄布裙下干瘪的乳房,在土炕上摇摇欲坠。
生命很空,又空得不透彻,依旧有蝉噪、犬吠、马嘶,与枯竭睡意。
狼毒花压弯了风声,和牧童短笛合二为一。
八
无数个黄昏,我驻足在二分之一广场,欣赏淹没星群的重金属歌曲,效仿流行乐者,欣赏给故乡带来耻辱的脱衣舞。
夜莺划过中央大街的上空,击沉了飞机,我在火灾现场找寻童年,找寻经历过夭折和蝗灾的旧时光。
蜘蛛网把烧焦的尸骨带到脉状街道,供路人欣赏和朝拜。子夜透明,川菜馆酒肉发霉,火车站门可罗雀,又如腐烂掉的公交车。
丰富剧本再也排练不出感人乡愁,抑或恐怖故事、虐心细节,抽屉装满了咖啡伴侣,爱它雪般洁白的样子,开水灼伤后,饮下三杯,压制住思念的神经。
黎明公平,分娩下一份祭祀和十二份悲天悯人,没有违法乱纪,却摧毁了一个物种的基因。
传教士为羔羊诵经,坚信有神论。
泪痕撕碎了银河系,使我恍惚间坠入暗河,再临摹一次母亲的红唇与手指,悲怆、辽阔、冷艳、突兀,生下游子后,任凭春风吹皱一生芳华。
九
寒冷可以迟到,但从不缺席。
重排枯藤老树的化学元素:钙、钾、氩、氯、硫。
夕阳灼伤一根麻雀的翎羽,我为“父母在,不远游”沉默,沉默如火,沉默如月光逃回田野。
白色枯叶坠地破碎,容不下阴冷天空的卵子、优雅的草、曦月的微光。
鱼传尺素,给心爱的姑娘寄去锦书,告诉她我熟知与陌生的拉市海风暴。
铺在青石巷的白练是嵌入大地的锥子,雕刻下过路人的碑文、咒语、喟叹。
协约空空如也,在垃圾堆露出冰山一角,晒干身子,挣扎出土,回归故乡。
饮一杯几年离索,为青春祭祀,茶水与酒等于少不更事?对,等于少不更事。
和大地一起缅怀过去,做个好孩子,歌颂晨光,歌颂真实的,虚构的,消失的,存在的,硕大的与微小的一切事物。
在城市的雾霾里写一部家族的兴衰史,以烈日灼心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