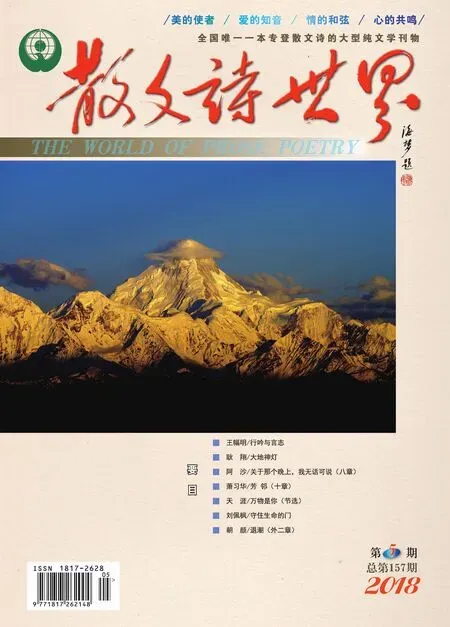守着你直到坚硬的光阴变得柔软(外一章)
甘肃 李 萍
1
这几年,我提着我的影子,深居简出在你的生活,偶尔与风窃窃私语,除此之外,我是沉默的。
有时候,我装扮成一个书生的模样,站在你的窗前,挑灯的微醉里,体味你双眼迸发的柔情。
阶前的心事,像雪粒在簌簌滑落,体内奔跑的欢喜,用世上最贵的显影粉,圈出你。
弯腰就能捡起你的目光,还有初次遇见时的无可奈何。
有些遇见就是这样唐突的。
2
唐突是个令人释然的词语,所以我有理由在任何时候,用爱举了一粒石子扔向回忆。我听得见石子落在往事中的“噗通”声。
一只飞鸟被声响惊吓,如同我的忧伤。那些忧伤是与你逃不了干系的。
我借着飞鸟展翅的无奈,用左手写出“爱”的第一划,然后用右手写下“情”的最后一划。
于是,伤感的情怀在大雪纷纷的清晨被滑倒。对于“爱情”的笔画,我了然于胸,想封笔,自此不再写关于爱情的半笔。
你一定感觉得到,因为我在风的耳语里读出了你的吻。
3
桃花在一个冬日的夜里开了,娇艳欲滴的夜色,微醉雪意。
于是,我也醉了。我在醉意中醒来,翻阅千年的诗页,还迫不及待地在一杯咖啡如一滴洇开的墨里,让装帧过的江山,留白很多。
那些留白是极为昂贵,平平淡淡叠加的回首里,依恋是曾经,也是未来。
陶醉的依恋,热烈的未来,在相随的分分秒秒里沉湎爱。
爱是劫。劫也是爱。
我的期许里,我想我会记得时间的歌,令你的拥抱变得生死相依。
4
我自然记得草香的味道,你或许已然忘记,或许你比我更深刻。
一些怨恨和介意让“爱情”的字眼变得密密麻麻,想要嫁给风的夙愿一直醒着,只有出嫁,才会在草香里闻到你的呼吸。
一些微小的记忆,小得不能再小的记忆,甜蜜、幸福、明亮、饱满如西画,叮叮当当作响的爱,在挪步,一步,两步,三步。
第四步开始跌跌撞撞,凌乱解释了忐忑。
我只想做个霸王,占据你的江山。
5
一个沉闷的午后,相思潜藏在檐下的石阶里。估计你在昏昏欲睡。
穿越是我的强项。我在你的时光里策马扬鞭,驱赶零下二十度的寒冷。
我要点燃你,所以我无所顾忌地钻木取火,洗劫你视野里所有的光。我只愿让你刻骨地记得我。
彻夜仰望也是我的特长,在爱的专场演出里,我宁愿腐朽,也会让生死不渝的你依旧光鲜,依旧香甜。
此刻,风是极简的。
那么就有理由拥抱。
6
我的文字里的村庄,你是村长。
另一种真实里,你突围着我的骨血。你一直在我心上的,故而声线变异也是情有可原的。青草样的日子,在一只火烈鸟啄食阳光的雨天,村口的炊烟是我写的情书。
我不会退缩,善良的月光,会读懂我。
木格子窗上,贴满爱的光线腾跃的故事。一个细节又一个细节,我都很深情。
窗前墨绿的是什么呢?我不去看都知道,那是栽植的相思。
安静是粗茶淡饭后村庄的福分。我有十万个理由不走,也不会先走,一直守着你直到坚硬的光阴变得柔软。
我至今在向着草原的方向静默
1
某个冬天的清晨,零下二十度的寒冷里,我的草原依旧绿着。天蓝,云白,草绿,牛壮,马健,羊群珍珠一样散在绿毯上。
我把你送我的红纱巾打成蝴蝶结,绑在头顶,拽扯着你的目光,把你从遥远一把拽入草原,并给你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扎西。
扎西的确是个好听的名字。转着经桶褶皱积满风的老扎西,穿着藏袍没有洗脸跑来跑去的是小扎西,还有健壮如牛打马而过的年轻的扎西。很多个扎西组成的陌生里,在尤为显眼的白帐篷里,我把你放置。
一只并不温顺的狗守着你,守着我的草原。我生怕你被卓玛的微笑掳去。
2
我真的害怕你被掳去,所以我用糌粑和酥油茶拴着你,偶尔在糌粑里加点咖啡,让你不至于忘记诗和远方。
我舍不得你去牧羊,我愿意用草色喂肥你的灵魂,让你服帖在空旷里。
于是,我挤奶,我打酥油,我拌糌粑,我还用一双草原上独一无二写过散文诗的手,把新鲜的牛粪抹在草尖上,让黑黝黝的土地借着绿绿的草儿熏醉富有。
一天,两天,几天后,牛粪片花被草儿托举着,干瘪,轻飘。
留一些素白给草原,于是风在晨昏变得狂躁,把不满甩来甩去,遇到羊儿也不心疼,碰见牛儿毫不留情。最后在一朵格桑花的温柔里服帖。
人世间的所有,在安静里服帖,在服帖里安静。
我的红纱巾,给草原的冬天打了个结,还给一些秘密也紧紧地绑上蝴蝶一样的结。
3
有时候,我跟着草原上最老的阿奶纺锤,一个个欢喜与忧伤被蓄入,与羊毛拧成一股,而后不停地旋转。
有时候,我把奶渣晾晒在经书上,让我的渴慕在虔诚里轮回。
有时候,我把羊骨头扔给野地里的狗,打发不属于异乡人的春天。
还有我感到焦虑的时候,也会把背水桶弃在记忆的岸边,赌气地跑到山顶上亮几嗓子,招惹一些勇敢的鹰来偷听。
更多的时候,我把草原与大海串联又并联后,沉默又沉默,直到一只草原鼠与旱獭拱手作揖留住它们的盛夏时,我才会剥离自己,把一些空洞植入鹰不能抵达的高地。
那是神的领地,那是爱的领地,那是洁白与神圣并存的领地。
4
一场大雨之后,我丢了草原。你绑架并束缚了草原的青春,还有秋草的爱情。
于是,我在所有的绑架中迁徙,开始在钢筋水泥构建的气息里挤奶,拌糌粑,燃桑烟,背水,纺锤。
我无法在人流中超度,无法在所有的颠倒里豁达。
我只有静默,静听一些合唱从记忆里承载的炊烟。
黑帐篷,白帐篷,我沉湎一个故事的纷纷扬扬,如雪一样覆盖草原后的安静得意和张扬。
最初的欢喜与敌意,在某个冬夜彻底坍塌。我无法容忍的颓废最终在一朵冬花的灿烂里嚎啕大哭。
我束手无策,在挣扎,在绝望。
终于,在立春的子夜,我携了喧嚣的巨款和灯火通明的夜晚潜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