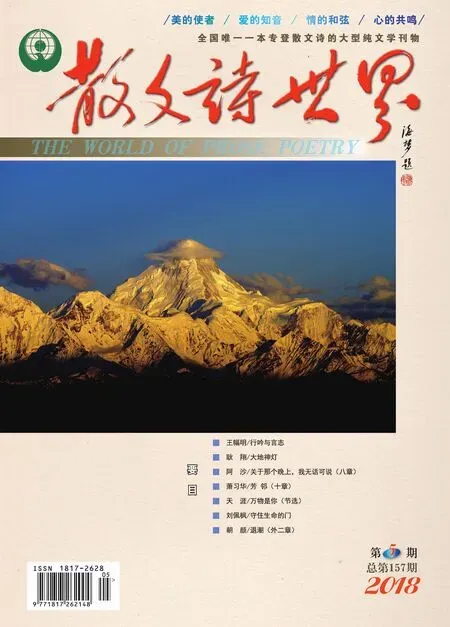关于那个晚上,我无话可说(八章)
四川 阿 沙
大凉山往事
在大凉山,光着脚,吃坨坨肉。
酒干了三大碗后,峡谷的月亮就开始散发光芒。
我听不懂来自远方毕摩的诅咒,又无法弄清人世的真相,我有一把生锈的枪:它可以对准任何一个人的脑门。
在大凉山,穿一条四色裙,就可以漫山遍野地打马奔跑。
也可以观察荞麦和燕麦,它们的生长季节不同。大雁飞过的时候,就要开始做荞粑,炒荞面。
我渐渐体会不出人和人之间的快乐。
在大凉山,有时在夜里,我会躲在查尔瓦里偷偷哭泣。
夜晚冷得像一块冰。这时我就知道,我无法忘记失去的所有。
曾经我写下过多少豪言壮语,现在却禁锢在山里。
最后我深陷于湍急的大渡河。或许我还要在河边垂钓,即使一无所获。
或许我还要生一炉火,丢两个洋芋。
等听见哔哔啵啵的声音,就知道山林即将燃起熊熊大火,气势汹汹,几天几夜不能扑灭。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我还是无法不去怨恨,当初是谁给了我一条黑色的查尔瓦,当初又是谁让我明白了痛苦。
梦
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关于我最深的一个梦。
他驼着背走路,指节粗大。他穿一身破牛仔,下巴蓄一撮稀稀拉拉的胡子。
他出现在梦里的时候,我的耳旁就刮过一阵风。我知道凯撒大帝死去了,亚历山大向我走来。
在梦里我们并排坐在田埂上,风拂过。我们并排坐在田埂上,风拂过,他抽起了烟。
关于那个夏夜,我不敢再说什么,我竟爱上一缕风。繁星漫天,山头是冷的,即使走很多路,喝很多酒,抽很多烟。我们停留在上个世纪的炊烟里,烟囱吐出长长的白烟。
比一只萤火虫的死去还要洁白,他抓住了我的翅膀,教我如何飞翔、如何降落,我把我学会的技能用于跳过一条浩瀚银河。
在那个梦里我们并排坐在田埂上抽着烟,我不记得那是1997年还是它的下一年,我们直抵生命的最初界限。
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风吹过,但我记得我们并排吐着烟圈,在那个1997年或是它的下一年,我与他在一列火车上分别。我们一个往北,一个向西,夕阳拖着残缺的尾巴大口大口吞噬,直到山洞遮蔽了光线,饕餮消灭了盘中餐。
没有一个梦是关于他神秘的身体,正如没有一个微笑是关乎我的内心,在厚厚的防线之外,我们拿起枪,拿起刀,狠狠地向生命的沉重砍去。
没有人提醒我开始与结束,在那个吹风的1997年的夏夜,或是它的下一年,他背着行囊走了,而我为他拔了34根白发。我们唱歌或是跳舞,啊,那一年终于过去了。
曾经,你锁住了我的青春
有时候,孤独是一座没有出口的大山,暮色比往日更缓慢一些才降临。每当那时,我一个人坐在二十七楼的阳台上,吹过二十七楼的风,有些硬,像无影的刀。
多少次,我在梦中祈祷,求上天让我忘掉过往。因为曾经,你锁住了我的整个青春。
摘下一棵水草,它摇摆的身姿,告诉我,他们热热闹闹地在河里结婚生子。日出,日落,一生便这样结束,轻柔如一片羽毛,一粒尘埃。
我不得不使自己变得规矩起来:为你,那迟来的拜访。
再次见到你的时候,不知为何,你已满头白发。你向我轻轻地抱怨,如婴儿饮泣。这些年翻过巍峨大山,蹚过汹涌大河,却从不曾看过我的眼。
因为你,它已遍布浑浊。
你记起了曾经的誓言,可是,它已无任何用处,我渐渐学会了如何看一只丹顶鹤优雅地独舞,或是溪边一只水鸟,任何一只水鸟的生老病死。它们诞生在水中,终将往水中去。
曾经我涉足过一片淳朴的土地,它的名字叫蓝岭河谷。多么优雅,与我不同。在夕阳渐尽、炊烟缭绕的时候,我已把自己的魂交与她,从此,我带着自己浑浊的魄,带着剩余的生理和原始欲望,毫不在乎余生,潦草地活在这个世上。
子夜终于来临,你走后,我便只能习惯黑夜。我不知道任何事情的真相,就像一只愚钝的水鸟,分不清爱与恨,更分不清接受与逃离。只记得,那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我内心轻盈地在原上跳舞。
南方的城
要是有一辆飞跑的摩托,我就一直往南开。
那年的官渡古城,城门一开一合,你从未知里向我走来。
我不知道在菩提伽耶,佛对你说了些什么。慢慢煎熬的热忱,拯救我——如拯救残破的帝国。
你在不知道何处的北方,那生满锈的老铁轨,是一个四四方方的牢笼。热气会捂住你的脚,如你的手抓住我的脉搏。
你对我说世界上根本没有鬼神,只有批判的尽头和看得见的命运。在某一刻你为我敞开。
我不知道这雾气弥漫的山顶是不是有霞光,我的眼泪飞满山坡,我被托起不可遏制地上升。
不对,你说得根本不对。哪里有尽头,只有触不到的时空。
你已老去,我正年轻,不理解如浩瀚银河。
什么都别再说,我从没想过你。
悼三月
在三月,我喝金色的啤酒,抽焦炭含量高的烟,背着沉重的铁甲穿梭。
我没有灵巧的手,又碰巧遗失了蔚蓝的眼神。
我的爱情在云水湖的上空飘摇。
在三月,我想倚靠一棵大树。攀登层层梯田而上,夕阳就充满整个荒芜。
追求是枉然的,在已经过去的三月。东风一吹过来,悲伤就失去了理由。我还踏着薄如蝉翼的步伐,怕一惊动,就被你剪成两段。
我们的距离是一整个三月,而三月,就这样过去了。
关于那个晚上,我无话可说
其实我真的无法告诉你,关于那个晚上,我已无话可说。
你从一团漆黑中向我走来,一步一步,像逐渐逼近的一颗星。
那晚夜凉如水,天上有无数颗星。我的身边还有一颗,拉着我的手。
关于那个晚上,我能说的只有呼啸的大风。山腰上闪烁的灯火,红红绿绿的,那是我脆弱的胸膛。
星星,我坦言我从没见过那么多星星。像无数只眼睛看着我,那眼睛里全是水,水里又全是眼睛。
妈的,除此之外,我知道关于那个晚上,我已无话可说。
我曾经爱过一个住在草原上的人
我曾经爱过一个住在草原上的人,他以捕猎为食,跨马为座。你可能不知道那匹马有多彪悍,我可以告诉你们,它的汗是宝红色的。
一开始他不知道我无以为家,最后他竟变成我唯一的港湾,这听起来有点可笑,可这都是真的。
我有时跨坐在马背上,整个脸贴着他的后脖颈,我的头发被风吹得全往后倒,我的手紧紧地抓住他的衣服。每当那时,他就会说一句:驾!像是在喊我的名字。
这个住在草原上的人,他有长长的盘起的头发,厚实的胸背,和标准的高原红。他只会说康巴语和四川话,他看我的眼神直愣愣的。
后来情况大变,我离开了他。走之前他紧紧地拥抱着我,我们在马上飞奔,穿过了树林、小山与河流。
他的胸膛是滚烫的,他的泪水也是滚烫的,只有他的手,很冰。他告诉我所有的花都叫格桑花,正如所有的男人都叫扎西,我嫁给任何一个男人,都如同嫁给他,扎西。
我是坐飞机走的,他的马再快也赶不上。我在云上,他在云下。即使他抬头望再久,也测算不出天空的高度。
再次看见他是在城市,他剪了头发,穿着和我们一样的衣服,只有两坨高原红没有变。他说他来找我,拿出他的苹果手机,让我加他的微信。他转发了一些哗众取宠的东西,那一刻我真的没有什么能对他说的。我知道那个扎西一去不复返了,可是扎西说他还是扎西,一直都是。
生命树
我知道,我不过是一棵树而已。
树有树的使命:落地生根,开枝散叶。
但在那天,宁愿干旱至死,也不允许自己沾一勺水,怕自己酝酿出眼泪。同样地,在那天,即使连根也要拔起早已枯干的脑海——只有这样,我才能重新来过。
啊,我可不能再想念任何人。
我曾将身体发肤,随意让北风宰割。这种糟蹋自己的方式,结果证明,毫无用处。
不过,现在好了,我终于可以重生,不带着任何前世的记忆。
作为一棵新生的树,就要坚守树的使命,茁壮成长,慢慢修炼。
明日修炼到即使面对你的爱人,面容也毫无畏惧,即使你在我面前,也不生妄念,我就彻底长成了一棵成功的树。
想当年,甚至还想过去死,但最终还是捱了下来。
而现在,没有你,又能怎么样呢?我一样开花结果。像其他所有正常的树木那样。我要辛勤地为自己工作,努力将不多的光阴抱紧。那时我将懂得,我是一棵经历了世事的树,不必为谁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