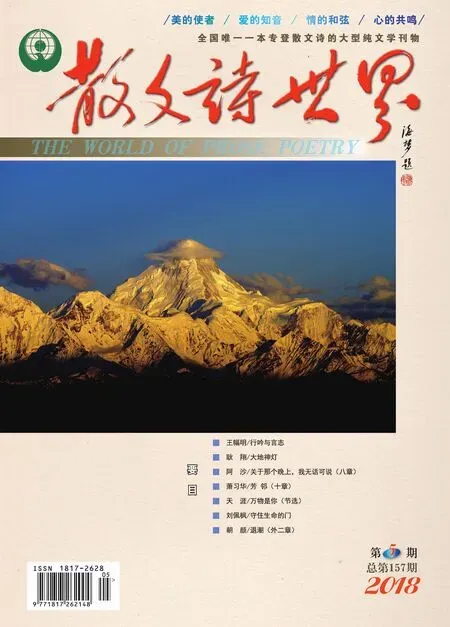杨通散文诗四章
四川 杨 通
一场大雾中的尘世物语
饮完酒的空瓶子,像是一个隐喻。
雾那么浓,谁都不肯吐露一只候鸟的去向。仿佛醉过了头的星星,蜷缩在自己深奥的辞典里,静观送葬的队伍,借着微弱的火把,把本就无序的生死走得更加深远和潦草。
生活,并不缺少阳光与花朵、风霜和雨雪。而滴水观音、万年青、风信子、龟背竹,这些有毒植物,暗自成长,我们总会盲然无顾,误碰误食。
鉴于此,我们需要学会身无长物,有口皆碑,船隐东岸,马归南山。如寺庙阶前的一炷香,燃尽红尘万丈。如菩提,低眉,无语。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何必有芒刺,与尖锐。
旧时光里的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被一株衰草带进圈养枯叶蝶的寂寥画框。
我们饮完了奔走相告的酒,生命只剩下无处接头的空瓶子。
路,断了上线与下线,失去了暗号,昨夜的狭路相逢不能共享魂魄。何处有佳音,何处是爱人咳嗽声的轰鸣?我们带着病体残躯,走在光阴涣散的末路上。
死亡,并不是什么隐喻,就是饮完酒的空瓶子。苍茫遍野,举目无亲。
在梦里抬头的稻草,拖泥带水,模棱两可,恰似灰飞烟灭后被濡湿的尘埃,与我们黎明时分不见彼此的泪水与哀愁,有某种雷同的虚构。
虽有薄光浸透纸背,却相看两茫然。
听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雾这么浓。虫子们很自私地约定:睡懒觉。
月亮假装死了,太阳也是。诱使溪流迷失于天地的混沌。让饮完酒的人,醉在幽暗的空瓶子里,仿佛隐姓埋名的临渊悬崖,潜伏在人间的隔壁,等待,有朝一日露峥嵘。
蛇皆已冬眠,冰凉的皮肤下面是埋藏毒液的寝宫。即使是身怀绝技的盗宝者,贸然进入,也逃不过九死一生。
而那些忍痛逝去的亲人,至今仍然没有找到能够从这场大雾中走出来的解药。他们似乎越来越听不清楚我与守墓人略带伤感的轻声对话——
雾散,寒流退。时间也许会再一次把我们这些囊中之物取出来,恢复光明的身份,还原尖硬的棱角,唤醒春天,在旧日的伤口上,发新芽,开新花。
冬天的私语
被一场大雪遮蔽了棱角,我暂时不再锋芒毕露。我的马蹄止于驿站,我的鸟翅降至低空。
我和时间都累了,坐在堤岸上,与垂下头颅的柳树一同专注于思考……
我内心的江河看似断了流,其实它们只是在冰下小憩。
我像蛇一样蜷缩着,对自己说:“让爱冬眠一会儿,醒来后,再叫你。”
我的身体在风中摇曳,像羊蹄甲的叶子,举着的绿,仍然宽厚。
我的天就要晴了。
我呼叫着麻雀,在地上铺晒阳光,让准备婚礼的蝼蚁们出洞扫雪,不再湿脚。
我的山坡上,到处都有不知名的野花在顽皮地开放。
天气这么寒冷,她们却可爱得令蝴蝶们因为敬畏而心生疼痛。
我的阳光还在。
没有什么悲伤的事,可以动摇我被照耀。
我与昨夜失眠的人推窗对望,看见彼此灵魂的星光,繁茂而璀璨。
我坚守着苍茫的后缀词——光,或者芒。
我的生命虽然免不了半途而废,死亡却能引领我坚持到最后。
我可以借助自由地飘,完成彻底陨落。
在黎明前又一个离世的人,是我乡愁里走不尽的亲人。
但是今天,他是我接收到的最不幸的消息。
我们都有还来不及卸载流行在歌声里的故乡便被荒草埋没在路上的命运。
我在墓园里栽满了耐寒的冬青树、多梦的夜来香。
等不到未来。或许明天,春暖花开,融雪煮酒,这里便会高朋满座。
我的小路上仍然有生动的溪泉;我的山林中仍然有肃穆的寺庙;我的日子里仍然有温暖的炊烟;我的大地上仍然有繁衍生息的牛羊和车辙;我的诗行中仍然有万念从善的晨钟暮鼓。
我优秀的纸笔墨砚,屯着激情暗涌的万水千山。
我的黄昏有圆满的落日。
神是宠我的。他说:如果你不肯掉光身上枯败的叶子,我就再为你吹一阵风。
我期待,在爱人深厚的银装素裹里,完美地熄灯。
我的生活仍然有沉重的梦想。
我把我搭在光阴的弓箭上,射向你篝火朗朗的庭院、沏茶洗砚的桌案。
我是一封渴望穿越寒冬腊月的情书,碰不到你桃之夭夭的红尘,就不能化爱成灰。
冬天,万物退避,万事撂荒。
悲观者心生寒凉。
但尘世风光尚好,人间只是换了一个频道。
如果你仍能感觉痛苦,“就必须忍辱负重,以保证头脑不被淹没在水中”。
所以我说,我没有再厮守无聊的孤独,因为“我与其他的东西私订了终身”。
一朵梅花懂我,低头,偷偷笑了。
春天,在远方披荆、拨云、攀岩。我暗恋她的曲折、昂扬、陡峭。
三月的尾声,或逝春者的流言
一
我还是没有学会时间教给我的耐心,接受生活的煎熬。
所以,我还不能够安静下来,撂事听风,涉穹赏月,举手谢客,闭门造车。画窗外繁花盖世,写大地鸟声入梦。
二
花叶坠露,逝者如斯……
我已厌倦从前的牛皮纸信封,那些装进去的对爱情最亲密的私语,再也找不到辛勤而负责任的邮差帮忙投递。
如今的送信人,没有相思的单车,也不带春天的邮戳。
三
济身良木,我已是一瓣粗糙的落英,被风扫掉了名字,被雨洗去了足迹,被春天逐出了温润的怀抱。
月色漫漶。我又疑是万家灯火泼出的药渣,一身糟粕和余孽,不知道还能不能化泥为肥,再次遇见芳草丰美的根。
四
月如刀,燕剪柳。请撕开你心的封口,抽出我曾经的诺言,读一读爱是否依然烂漫,看一看蓓蕾们是否仍然在蠢蠢欲动。
匍匐于春天,我思念和冥想你的枝蔓,是否还在争先恐后地觐见你——我废墟里孤傲的王。
五
这偌大而庞杂的春天,我何时才不再迷路。我的马蹄上缠满了蝴蝶,它们绊住了我的行走。
我的心,被蜜蜂蜇得好痛!
你在花丛中放肆的璀璨,让我瞭望你的目光,乱了针脚,无所适从。
你让我的春天,越来越虚幻。
六
落草为寇,蹚水为侠,已不是我的黄金岁月。
春闲时,请把我从你的藏品中取出来,擦擦灰尘和锈迹,洗去曾经的耻辱和荣光,还原我青春剑气上最真实的青铜时代。
如果,我是纵横在你春天深处的一件雕塑,请刻上芳菲不朽的座右铭。
七
灯下有诗书,案上即乐园。
孩子们的嬉闹,跳跃着童话的斑斓色彩。
写字的老人,再一次写掉了自己寂寞的芳华。
一声鸟鸣掉在新沏的茶盏里。
春色氲氤,风筝荡漾。
天亮了。黎明的草场撩开躁动的衣襟,盛满往事里夕阳行色匆匆的余辉。
八
美,是春天用来赏赐众生的。
不管气候怎样下烂药,今天的蝴蝶和蜜蜂都要倾巢出动。
即使名花仍然只开富贵的主,卑微的人,也要抓一把风雨回来。
让我们在这个欲念蓬勃、目不暇接的春天里,只热爱属于自己的那一朵小野花。
九
三月即尽。
骤然炽热的阳光,一下子就毁掉了春天的日历。
整理衣橱,原来准备穿给春天的服装,还来不及上身,花儿们就迅速离开了。这是一件令人伤感的事,仿佛等了一生的你,在我认为该来的时候,却悄然从墙外走了过去。
十
生活教给我的耐心,已无处可用。
时间继续煎熬我所剩无几的春色。
春天一岁一岁地来,我一年一年地旧
我错过的某些行走的瞬间,正是岁月的刮刀在一点一点地剔除我温室之树上的花骨朵。我与光阴的故事也随着钟摆的移动在慢慢老去。
是的,这些年我一直在生命的辞典里检索健康、安宁、快乐、幸福和爱情的定义。来不及邀请你数天上的星星,大雁就疾速地飞过了秋天;来不及陪着你看大地上的烟火,阳光就坚决地融化了积雪。
春天又来了,我仍然无所适从。
仿佛一岸芦苇独自白了头,心上江水的流逝越来越缓慢。闲登孤山寺,追赶万物的脚步也已接近老态龙钟。
怀抱一野黄昏的苍凉,我在梦的月亮上钻木取火,锻打纯银的手镯,成全一枝玫瑰的姻缘。而我又一次在草叶上看见了泛滥的白霜。
爱情的自留地,颗粒无收;生活的桌面上,一片虚空。
清晨醒来,一砚淡墨里屯满了虫豸们的轻声尖叫。
时间的笔尖刚打算在生命的草纸上阐释阳光或雨露的来意,便被折花人弄断了诗情画意的线索;梅花等不到潇洒地凋谢,便预见了自己枯萎的末路。
谁将引领我们背诵共同的台词:“与其坐等死亡,不如自己走向它。”
命运沉浮,生死交替,已不是某种“经久不息”的征兆。这一切,似乎都与春天无关。
“有些时候死亡并不是最恶毒的”,唯有“鲜花能照亮最黑暗的角落”……
我不由自主地感觉到“春天让我更陈旧”,却意外地听见排箫里的天籁之音:“人生苦短,说谎太浪费了”。
在偌大的春天里,我们习惯了只是一件被任意放置的小摆设。
你提示我,时间过去了那么久,几乎忘记了还要再为春天写一首诗。
我相信过,“有你在,就有丰满的新鲜空气”;有矜持着逾墙而走的花香,我们最终会拥有彼此。
而时间——不朽的权杖,注定要更改我们两小无猜的初心。
谁说的,对于一个看惯了繁花的人,春天显然是多余的。依我看,雏燕翻新柳,也不一定是必要的。你看,今年的桃花还是要一如既往地开在别人家的后院。悲伤总是难免的。
别怀疑我是一个对美背信弃义的人。我只想远远地站在春天的侧面,等那些我曾经暗恋过的人们,经过我。我要试一试,还可不可以继续爱上你。
但是,现实并不喜欢我在光天化日之下恣意妄为地冥思苦想,想风雨的身世为何总是阴郁的;想那棵树为何要放弃做有用之材;想“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想“我喜欢你”、“我喜欢你跟你没关系”。
春天一岁一岁地来,我一年一年地旧。
我在时序的运转中学会了逆来顺受。我手无寸铁。不得不把自己裸露在无灯无光的夜晚,交给啄木鸟用于针对失眠症的治疗。
冬雪融退,春风来袭,百鸟和鸣。我喝我的酒,我贪我的杯,我醉我的醉,我痛我的痛。不问繁花绽放,不问星斗移转,不问我的心能否安憩人间的美好。我对流浪者说:我既不是你生活的苟且,也不是你的诗和远方……
今夜,我不贪新瓦,只恋旧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