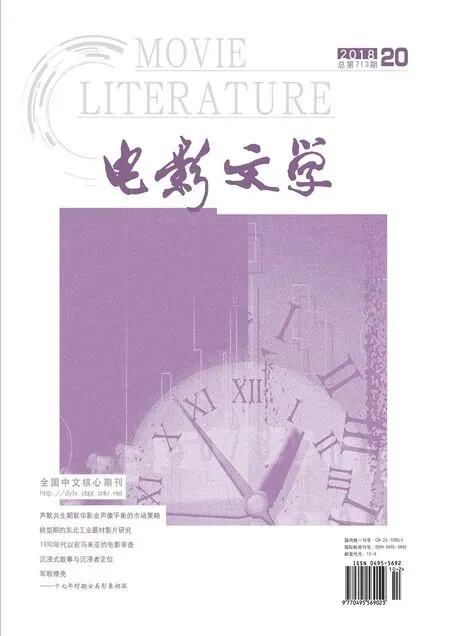《归来》的情感与镜头表达
王佩佩
(吉林艺术学院,吉林 长春 130000)
张艺谋是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从摄影师入行最终转型成为导演,他的作品在视觉呈现上有着摄影师对画面的精雕细琢与严苛要求,镜头语言往往成为分析张艺谋电影作品的主要入口。电影《归来》被看作是导演张艺谋回归文艺片的重要作品,在深耕商业电影多年之后,张艺谋舍弃了商业电影的视觉奇观和浮夸隆重,再一次回归到他擅长创作的抒情文艺片当中。电影《归来》取材自严歌苓小说作品《陆犯焉识》中的一个段落,更多的是关于小说故事的衍生,讲述了陆焉识在“改造”多年回家以后的故事。影片以情感叙事贯穿始终,情感真挚纯朴,感人至深,尤其表现出张艺谋在镜头语言方面的匠心独运。于是,分析镜头语言与叙事方式成为解读电影《归来》的情感表述的主要途径。
一、情感基调
电影的情感基调是艺术创作的核心,喜剧或是悲剧都有各自不同的艺术结构,在确立不同的情感基调以后才能够向上铺展影片的艺术结构,我们甚至可以将情感基调的定位看作是确立电影全片的核心与根基。在张艺谋早期的艺术片创作生涯中,与其他第五代导演一样,剖析中华民族的历史根性与民族心理成为创作的重点,透过1987年到1999年张艺谋创作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和《我的父亲母亲》等作品不难看出,张艺谋也始终在坚持这方面的艺术创作,几乎所有故事的缝隙里都透出了民族心理的一部分,主导所有故事的也都是这些民族性格。然而,张艺谋在这些艺术张力十足的故事背后,又将其中牵扯不断的情感脉络梳理得十分清晰,虽然闭塞,甚至难堪、不公平,但是每一个故事背后流动的都是中国农民最朴实的情感,每一个作品都有最真诚的情感基调,使故事从头至尾流动得顺畅淋漓,令人感同身受。
对电影《归来》而言,虽然张艺谋的电影改编是基于小说最后一章的最后一句话,从陆焉识回家以后的故事谈起,但是他从“陆犯焉识”的故事中提取的情感基调是准确而深沉的。严歌苓在《陆犯焉识》中书写了大量的关于20世纪中国的“文革”历史,故事虽然集中在冯婉瑜和陆焉识二人坎坷的人生故事上,但是背后的“文化大革命”作为庞大的故事背景是密密麻麻融入小说故事当中的,严歌苓也在书写小说故事内容的时候着墨颇多,其目的是让读者深刻地感受到“文革”时期的疯狂,以及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拉扯着冯婉瑜和陆焉识的命运。可以说,小说《陆犯焉识》的叙事基调和情感基调都是灰色的。
但是,导演张艺谋在改编的时候深入“陆犯焉识”的故事本身,从中提取了深厚的情感,为影片铺垫了厚重的情感基调,让小说故事原本布满灰色的情感内容中填充了一丝温暖的亮色。张艺谋在电影《归来》中更为集中于冯婉瑜对陆焉识的执着,以及陆焉识对冯婉瑜的绝对情感,二人之间的感情有着超越时代背景的明亮和温暖底色。于是,张艺谋的电影改编被很多人诟病是避重就轻,刻意地为了电影审查和电影市场做出的一种妥协,但究其根本,冯婉瑜和陆焉识的情感是张艺谋更想好好表现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也是更值得表现的部分,“文革”时期深入骨髓的“冷”与冯婉瑜对陆焉识的情感的“热”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张艺谋电影改编的“避重就轻”显然是他回归自身文艺片创作的出发点,回归到了最初同创作《菊豆》和《我的父亲母亲》等作品一致的情感创作核心中来。
因此,电影《归来》并非一部痛斥“文革”时期的绝对的批判性作品,导演张艺谋在架构故事的时候,给予了冯婉瑜和陆焉识个人情感故事更多关注,令该片成为一部书写人间温情的优美作品,这份带有温度的情感基调也主导了影片的叙事铺陈和镜头语言等多方面的艺术创作方式方法。
二、抒情方式
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创作各不相同,但是他们作品的共性是对于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的畅快书写,无论是激昂的热血创作,抑或是含蓄内敛的书写,其中主要书写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实感,而抒情方式的不同也决定了电影作品的艺术表现形式和艺术表征的不同。由于张艺谋是电影摄影出身,他在进行电影创作的时候更加坚持的是内敛的情感书写,希望透过电影画面的设计和镜头的运动带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甚至是时常用隐喻的画面处理方式来表现人物的情绪情感,这些都并非简单的电影美工可以处理的部分,需要电影导演对镜头画面和故事情感有高度的心理敏感度和艺术敏锐度,从双重角度入手去开发这类故事的情感脉络。于是,《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就是为了讨一个“说法”不惜走上了诉讼的维权之路,在当时的农村那样的关系型社会,秋菊的做法是出格的,甚至是常人无法理解的,让秋菊坚持走完这条路的一方面是中华民族性格中的倔强和坚持,看似“冥顽不灵”的秋菊有着中国女性的不屈脊梁和坚忍品格;但是另一方面是秋菊与丈夫的情感,秋菊对自我认知的启蒙,她坚持人与人之间并不能是这样随便伤害如此敷衍的,“讨一个说法”实质上是情感高度升华的外部表征。在《我的父亲母亲》当中,张艺谋同样以这样含蓄内敛抒情方式书写着母亲与父亲的浪漫纯真的爱情故事。进一步,张艺谋隐忍式抒情方式的外部表征,正是电影镜头画面的精雕细琢和隐喻式表现。
在电影《归来》当中,冯婉瑜和陆焉识的爱情故事令人唏嘘,“文革”时期虚化为一个大背景笼罩着片中故事里的每一个人。在陆焉识被抓走的日子里,冯婉瑜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不堪精神的重负患病失忆,不再认得这个自己日日等待、夜夜盼望归来的丈夫,即便是在“文革”结束后,备受摧残的陆焉识得到了平反,顺利回到了这个自己日思夜想的家中,冯婉瑜却将自己看作是陌生人,丝毫没有接纳自己的意愿,甚至有着深深的排斥和厌恶情绪。亲人近在咫尺而形同陌路,明知道冯婉瑜每天等待的依旧是自己,却因为精神创伤而无法相认,无论是命运的嘲弄也好,还是时代弄人也罢,这种“意外的重逢”其中透着辛辣的讽刺性和悲剧意识。
但是,如果我们观察电影《归来》的镜头语言和画面设计不难发现,相对于这份沉重的悲剧性,导演张艺谋想要表现的是冯婉瑜和陆焉识这份跨越漫长岁月积淀出来的厚重情感。影片大量运用了逆光镜头,在室内击打出灰尘颗粒弥漫在空气中,勾勒出斜着射入窗户的光线的形状,同时将人物安置在这种凸显肖像性的光线当中,一方面表现出岁月的漫长;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人物情感的浓烈,以及坚守的这份执着。此外,大量的室内场景中,导演张艺谋运用了大量的近景特写镜头,尤其强调从室外投向室内的光线,人物周围虽然处于黑暗当中,但是面部是明亮的。一方面令观众的视线更加集中在人物面部表情和行为活动,放大人物情感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将人物和时代的位置关系有机地表现了出来——即便是时代背景再黑暗看不到尽头,人物内心的光亮才是真正引导一切的东西。毫无疑问这种镜头对于情感的表现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加含蓄,也更触动人心,这种镜头表现情感的书写方式也是张艺谋曾经多年深耕的艺术创作手法。
三、情感主题
最初的电影没有声音,完全依靠画面的视觉反差影响观众的观影心理,给人以情感共鸣和感官刺激。于是,没有声音的电影似乎是电影最原始的也是最应当具有的基本形态,声音是辅助表现的艺术手段,画面和镜头语言才是一部电影最根本的艺术表现工具。在电影《归来》当中,人物台词寥寥,导演张艺谋更多的是利用无声的镜头画面展现人物,并且以此为常态进行影片的创作。在陆焉识归来之后,影片大量的情节是重复的,叙事空间和视觉空间都集中在冯婉瑜和陆焉识的这个不是很宽敞的小房间里,窗外永远有着温暖的光线照进来,室内始终升腾着烟火气,光线经常将人物反打出轮廓,似乎是在刻意将情感隐藏,却又在画面和镜头的轮动过程中满溢出来。
电影《归来》的情感主题是要高于小说原著的历史主题的,“文化大革命”虽然给冯婉瑜带来了无法治愈的精神创伤,也给陆焉识带来了一生都无法弥补和原谅的悔恨,但是相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人们精神的摧残和生命的侵犯而言,冯婉瑜和陆焉识的真挚爱情是更加令人动容的,尤其观众生活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物质社会当中,影片进行的精神层面的书写更为触动人心。在陆焉识离家的这段岁月里,冯婉瑜没有丝毫改嫁的心愿,一心一意等待着丈夫归来,她心中始终相信无辜的丈夫会回到家中,清白和正义是属于好人的,但是日子过于漫长,时间摧毁了她的意志,没有摧毁掉冯婉瑜心底对陆焉识的爱情,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份执着的情感,在精神世界已经垮塌的情况下,冯婉瑜是无法坚持到陆焉识回家的那一天的。而陆焉识在备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以后,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平反回家,面对自己的却是无法相认的妻子,而他却选择不离不弃留了下来,在痛苦的折磨之后依旧能够选择漫长的等待和未知的痛苦,陆焉识对冯婉瑜的真挚爱情可见一斑。
于是,大量的近景镜头呈现了冯婉瑜和陆焉识“素不相识”的生活细节,每次陆焉识陪着冯婉瑜到车站去接那个“永远无法归来的自己”,镜头都从温暖的暖色切换到了冰冷的冷色调,每一次接送似乎都有一丝希望,但是画面的冰冷隐隐地告诉观众势必又要落寞而归。大量的重复的生活化的镜头反衬出冯婉瑜和陆焉识爱情坚守的伟大,观众一次次地透过镜头看到冯婉瑜和陆焉识虽然同在画面当中却无法相认的画面场景,一次次地感受到张艺谋导演将情感书写到镜头中的深意,影片的情感主题也在每一次的特写镜头中得到了升华。此外,二人的女儿丹丹为了实现梦想的决心也是影片潜在表述的一部分,她的梦想是纯洁的不可侵犯的,即便是冒着生命危险回到家中的父亲也无法侵犯她的梦想,丹丹在充满阳光的家中舞蹈的场景是影片的经典镜头之一,丹丹的不懂事正是因为自己对梦想的坚持,而时代却狠狠地给了她一巴掌,人物的命运和时代的勾连不言而喻,但是梦想的伟大和纯粹我们不能去否定。
四、结 语
导演张艺谋通过电影《归来》再一次回归到了自己的“安全地带”——文艺片的创作当中。一方面观众认为张艺谋避重就轻地改编《陆犯焉识》的方式具有投机性,另一方面观众又无法否定张艺谋从这个极具时代底色的故事中提取的情感是如此感人至深,冯婉瑜和陆焉识的爱情故事才是影片想要表述的重点。张艺谋将自己多年对镜头和画面的支配调度能力完全用在了《归来》的创作当中,人物的情感正是像影片画面中弥散在空气中的温暖光线一般,时时刻刻地温暖着观众的内心,也正是导演张艺谋在那个充满黑暗的压抑的时代历史中挖掘出的一抹人性亮色,冯婉瑜的失忆正是对爱情的最高形式的悲剧书写,同时也是最感人至深的表述方式。
——论严歌苓长篇小说《陆犯焉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