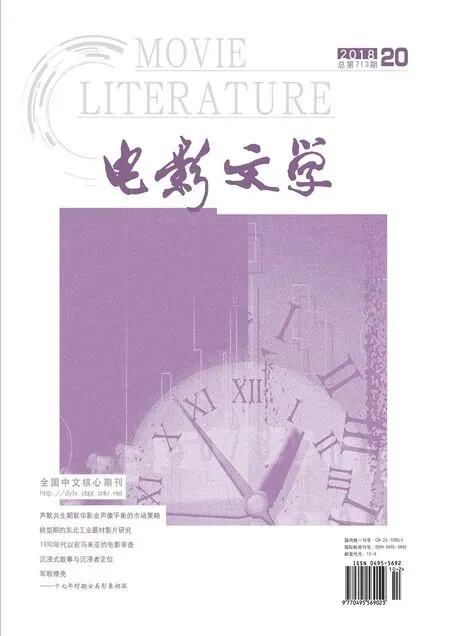弥散的景观:类型弱化的武侠电影及其叙事内核的延展
张 梅 李建伟
(1.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 艺术传媒学院,重庆 401520;2.北京电影学院,北京 100088)
一、武侠电影:类型的弱化与叙事语境的变异
武侠电影是最具中国文化标杆的类型电影,就像美国的西部片,成为一种不断被言说的神话结构。武侠电影以独特的诗意演绎着中国人的武侠梦,展示着中国人对侠义精神某种集体无意识的渴望。因此,在中国电影史的重要发展节点,武侠电影总是扮演着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凝聚全球华人文化心理的重要作用。但是新千年以来,内地电影产业的市场化和近20年的高速增长中,过度的商业开发和大众消费,以及武侠电影创作人才的青黄不接等主客观原因,武侠片正面临类型弱化与叙事语境变异的危险。近五年内地取得高票房的类型片,大多是喜剧片、军事动作片、奇幻与魔幻题材的影片,还有像《我不是药神》这样触及现实的现象级电影。而武侠片虽时有创作,但引发现象级的关注、掀起观影热潮的却微乎其微。
自1920年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任彭年执导《车中盗》《荒山得金》以来,武侠电影便以其天然的叙事使命和“惩奸除恶”为核心母题,触发武侠电影的跨时代创作。在经历漫长而不断丰富的发展历程后,武侠电影逐步形成以“尽忠”为核心的报主主题、“尽孝”为核心的复仇主题、“尽善”为核心的除恶主题。其类型片的叙事模式也被固定为善恶二元对立。随着时代发展,“侠”与“武”的表达内涵出现一些新的内容,但其核心价值观和创作程式始终是内部稳定的文化结构。正是这一稳定的结构在一定时期符合社会集体无意识的需要,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以香港电影为代表的武侠文化,其类型活力、市场和文化召唤能力,长期占据着主流视野。进入新世纪,武侠电影一时又成为国产大片制作的重要题材。尽管像《卧虎藏龙》(2000)、《英雄》(2002)、《功夫》(2004)、《叶问》(2008)、《一代宗师》(2013)等影片产生高影响、高回报,但其类型特征和叙事范式早已支离破碎,大部分武侠作品都沉浸在自我表达的叙事语境。学界把这类武侠作品称为“新武侠电影”,但这与之前香港的“新派武侠电影”全然不同,前者主要表现在——创作者更多元、主题表达更私密、审美志趣更个人化的武侠世界。
比如王家卫的《一代宗师》讲述近代中国武林的文化脉络,呈现的是个人表达的情感空间;侯孝贤的《聂隐娘》以考究的舞美,试图还原一个真实质感的大唐图景和古典文学的诗性气质;而徐浩峰的《箭士柳白猿》《师父》则是将武侠电影从戏剧的仪态式表演和视觉欺骗的剪辑中解放出来,实现真实的“交手式武术”,还原武术在近身搏斗中呈现人体自然的心理和动作反应。徐浩峰的作品尽管主题也不乏深刻,但导演显然更热衷于改造传统武侠电影的美学范式,试图不遗余力地要建立一个新武侠电影世界的视觉体系和风格标记。
因此,在近20年的武侠作品中,我们清晰地看到,武的暴力呈现,侠的情感表达,惩奸除恶的二元叙事法则尽数被消解。这种消解,主要还是后现代的消费主义、游戏狂欢,导致整个传统文化的历史性断层。武侠的叙事时空被现实阻隔和悬置,进入一种网络时空的虚拟——玄幻、仙侠网络小说与网络影像的传播,在游戏对抗中宣泄暴力,同时消解了文学和影像建构起来的武侠文化的“侠”,当下武侠电影对现实价值观的抽象和乌托邦梦想的寄托,很难再引起观众的情感认同与类型吸引。
二、弥散的景观:武侠电影叙事内核的延展与内化
近年来的武侠作品,在叙事语境中融入社会现实中某种个体存在的隐喻,传统武侠所建立的精神信仰开始转向世俗的烟火——武侠世界的人物不再是江湖之远,而是真实地走进人们的生活,呈现为一种“诗意的渐隐和现实的渐显”。
(一)“诗性”武侠的凋零与现实转向
新世纪以来,诸多武侠电影以及根据神话题材改编的电影,于大时代的推动下,快节奏的生活荡涤着人们对“旧日武侠情怀”的消解,注入更多大众娱乐性的现实期待。比如《悟空传》《捉妖记》《绣春刀:修罗场》。在《绣春刀:修罗场》(2017)中,主人公沈炼既有身份低微的官差的冷酷,也有习武之人的某些狭义甚至仁慈。从两部作品的人物性格设置可以看到,很多时候他身不由己,在巨大的政治权谋中,他只能是一个现实的中庸主义者。在传统武侠作品中,侠客的行为并不受体制与环境束缚,“纵千万人吾往矣”的无惧无畏,甚至有些不谙世事的莽撞与刚强而感性的意气,是其诗性浪漫的表意核心,比如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的乔峰。而这部影片,即便主人公沈炼最后的反抗也并非侠之“大义”,而是来自与女主北斋的“小情”——人们不再相信有人会为了高于自身的利益而甘于牺牲、奉献,但英雄为红颜一怒,反倒是可信的。同样的故事时代背景设置,《绣春刀:修罗场》与20世纪90年代的影片《新龙门客栈》的侠风侠情形成鲜明对比,传统武侠主人公永远是家国大于儿女情长。在这跨时代的文本对照中,传统东方诗学之崇高、信仰、浪漫的“侠客”精神,让位于迎合当下观众唯一具有行动说服力的爱情。
(二)被拆解的武侠叙事能指
诗意的武侠电影的文化结构和叙事空间虽已渐次散落,但其侠文化的核心要素以现实指涉和意指作用,散落在更具活力的叙事语境中。武侠的本质是抚慰与宣泄,而非欺骗。时代在变,焦虑、恐惧也在变,现世人们需要的侠客已不再是历史时空的替天行道,而是以武犯禁。这个“禁”也包括在敏感的意识形态背后,有敢于违抗和逾越一种体制的枷锁的“游侠”精神,就像新好莱坞的《邦尼与克莱德》《末路狂花》,对现有体制的某种集体无意识反抗。观众的这种隐秘的心理尽管在主流院线大片中是很难实现的,但是在武侠作品中却可以改头换面实现某种情感宣泄,比如姜文的新片《邪不压正》深层的讽刺意味,以及“屋顶飞奔”的剧情设计,象征对自由的极度渴望。
不难发现,近年国产电影的叙事主旨,许多冠以军事战斗、社会犯罪、动作冒险标签的影片,实则都暗含某种侠义精神的诉求。如《老炮儿》(2015)、《湄公河行动》(2016)、《战狼2》(2017),以及2018年现象级影片《我不是药神》《动物世界》等影片。虽然从题材和类型划分上它们均不属于武侠电影的范畴,但通过拆解武侠电影的核心叙事构件,这些影片从价值观重塑、叙事逻辑、人物性格、现实折射,毫无疑问将武侠电影中的侠义叙事内核移植到一般类型片,或将一种正义与伦理、终极坚守的朴素价值观注入一般类型片,塑造与大众亲和互动的平民英雄。
(三)弥散与内化:武侠精神的跨类型表达
以“技击动作”为主视觉呈现的《湄公河行动》《战狼2》,两部影片在叙事主题上极为相似,都将反恐、爱国、惩恶、英雄主义融为一体,满足了受众的多重心理诉求。对照武侠电影叙事规格,两部影片都浓墨重彩地展现了以武术格斗实现侠义任务的叙事初衷。《湄公河行动》中,正义的主角面对恶势力,以暴制暴,以武制武才能伸张正义、维护国家尊严;而《战狼2》中,主人公冷锋被塑造成一个孤胆英雄的角色,这种人物在中国类型片中还是比较少见的,尽管《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也是这样的英雄,但他还是脱离不了集体主义的意识规训。冷锋也是如此。不过,冷锋的形象打破了把退役军人设置为黑道杀手形象的惯例,脱离军队的集体束缚,人物可进一步拓展狭义精神的叙事空间。从这一点来说,国产电影由于意识形态主导的体制审查等特殊原因,孤胆英雄的人物很难在当下文化语境中实现,但导演吴京通过军事动作片,以国家正义与爱国主义之名,恰到好处地找到了发力点,平衡了受众与意识形态之间或隐或显的多重矛盾。
《湄公河行动》和《战狼2》,在特定的叙事空间实现了现代行侠的主体叙事,看似是在伸张国家正义的大旗下以军事题材为原型的类型创作,但其叙事元素与主题内核,却符合了武侠电影的创作逻辑。特别是吴京长期从事武侠影视剧的拍摄背景,而另一个来自侠文化作为亚社会形态的香港导演林超贤,他们两人都潜移默化地受到武侠电影创作思维的影响,才有侠义精神的弥散与跨类型表达。
如果说《战狼2》《湄公河行动》的武侠特征是动作电影叙事规律使然,那么以冒险、游戏为标签,有着浓厚现实主义色彩的《动物世界》(2018)就大不相同了。这部影片在叙事逻辑上完全符合武侠的精神,但主题清晰地表达了现实残酷与理想坚守的二分世界,叙事没有着重探讨复杂人性的意图,主要以故事本身的惊险和刺激为吸引点,但可贵的是这部影片在整个故事中突出一个朴素的价值观——不忘初心。抛开故事吸引,影片之所以获得观众认可,还是在于当下个人信仰与理想双重失落的年代,小人物郑开司始终坚守初心,其行为包裹下的人物内心,具有一种当下特别缺失的“少年纯真”与“少年侠气”,正是这种青春热血的“少年气”的核心价值召唤,观众找到了自己心中的“少年时代”。影片将寓言与游戏感交织,以动画形象“小丑”作为郑开司理想人格的象征,实则表达了主人公内心的渴求,他是一个典型的“小镇青年”,他的坚守与其说是度人不如说是度己。这样的英雄或说这样的“侠客”,让大众更信任也更能受到心灵的抚慰。
同样,2018年的现象级影片《我不是药神》,在文本内外的互文叙述中,也同样蕴含了武侠电影的精神内核,由此也彻底令“侠”走出了墨守成规的历史语境,赋予了其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不是药神》主人公程勇的转变是鲜明的,从开始以药谋利到被病人们激发善心无偿供药,再到最后冒着坐牢的危险走私送药,在人性与现实的博弈中,程勇充分展现了一个“药神”应有的作为与初心。正是程勇的这种同情心,才使所有超脱现实功利的武侠精神有了原动力,才使魔幻的“药神”变成现实的“药侠”。影片在喜剧的外壳下,表达的则是残酷的社会现实与人性光芒,这才是这部影片具有强大情感召唤的根本原因。
三、结 语
中国的武侠电影是一种民族记忆的文化结构,同时也是一种现代神话原型,尽管这种类型片还没有像美国西部片一样,具有如此牢固的内在结构和外在形态,不易被其他类型片所兼容,但当下无疑是中国武侠片最不好的时代,同时也可能是下一个最好时代来临之前的黑夜。不管中国正在工业化的类型电影未来如何发展,武侠电影以及武侠电影的创作思维和叙事逻辑,在其他类型片的开发中,总是以某种现实需要和诗性品格坚挺地存在着,形成一种鲜明的弥散的景观,而这种景观不仅仅存在于特殊题材,更会扩散到一般题材中,它传递的是真正属于中国文化最民族性的价值观,最终会内化为中国电影最具特色的文化品格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