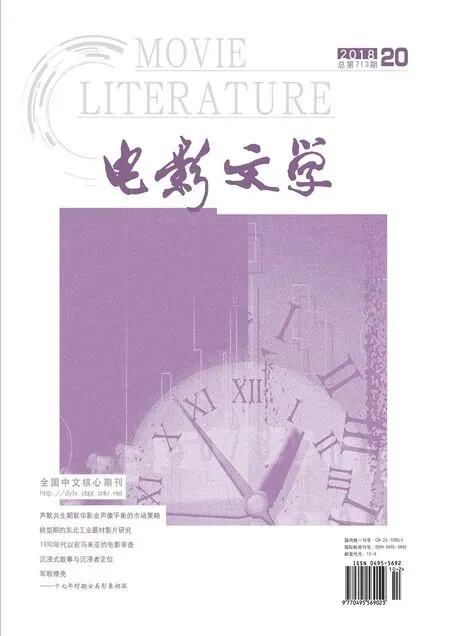论电影《燃烧》对村上春树小说的改编
张 静
(防灾科技学院 文化与传播学院,河北 三河 065201)
由韩国导演李沧东执导的《燃烧》在2018年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亮相后,成为戛纳场刊评分最高者。这部电影改编自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烧仓房》,原著中许多精彩的对话都保留在电影之中。一般多认为小说表现了高速发达的资本主义是如何毁灭了那些无足轻重的美好事物,《燃烧》却进一步丰富了主旨,伴随着形而上的哲学思考,表现出更为丰满且复杂的社会现实与人性困境。
一、人物形象和社会环境更加具体丰满
《烧仓房》全文不足一万字,总共出现了三个日本人物,而且这三个人都没有名字,只是被叫做“我”“她”“他”。“我”是一个普通的作家。“他二十七八岁,高个子,衣着得体,说话斯斯文文。表情虽不够丰富,但长相基本算是漂亮的那类,给人的感觉也不坏。手大,指很长。”“他开一辆通体闪光的银色德国赛车。对车我几乎一无所知,具体无法介绍,只觉得很像费里尼黑白电影中的车,不是普通工薪人员所能拥有的。”而“她”不知从哪里来,最后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她很“单纯”——什么年龄、家庭、收入,在她看来,纯属先天产物。她无论什么场合都能倒头就睡。“她在待人接物方面以无念为宗。”村上春树人物模糊化、虚实结合的叙述手法让这篇小说可供想象添加的空白很多。
在电影《燃烧》中,三个主要人物则成了韩国青年,被赋予了不同的出身经历、经济情况和性格情感。钟秀是来自朝韩边境的坡州农家青年,母亲在他小的时候就离家出走。钟秀大学毕业于文艺创作专业,致力于成为小说家,但为生活所迫整天忙着打零工,尚未提笔写东西。电影一开始的时候,他父亲正惹上了官司,被判刑一年零六个月。惠美和钟秀曾是坡州同乡,她因为欠了很多卡债,被家人赶了出来,住在一间朝北的阴暗小屋子中。她喜欢自由的工作,偶尔做街边促销模特赚点钱。在惠美妈妈那里,女儿是一个满口谎言的人,“她可会编故事了,编得不漏痕迹。”当钟秀听惠美说她在学哑剧时问她想当演员吗?惠美回应道:“演员是谁都能当的吗,只是觉得好玩而已。”“只要好玩,我什么都做。”影片一开始,她就计划着远赴非洲旅游。BEN外表英俊、风度翩翩。开着保时捷跑车,住在富人区的豪宅里,参加教会活动,在健身房跑步,周末一家人会在美术馆聚餐,谈笑之间其乐融融。
可以见得,电影在人物形象具象化的过程中,阶级差异与对立被明显地呈现了。原著小说中的“我”是一个有家庭、有房子的小说家,也算得上是中产阶级。而在电影中,钟秀是一名最底层的搬运打工仔。当钟秀问BEN是做什么工作的,BEN说他的工作就是玩。这时候的钟秀不免哼的一声,明白无误地表现出了他的嫉妒与不满。最终,钟秀杀死BEN,更像是一场阶级的突围与报复。《燃烧》中的三个韩国青年是导演精心设计的具有超越意义与观念的人物形象,代表着阶级的缩影,也代表了不同的生存状态。
《烧仓房》中没有关于日本社会环境的描写。这篇小说写作于20世纪80年代,从其中描述的那么多的年轻的富人,“做什么的不知道,反正就是有钱”来看,似乎反映的是日本正处于泡沫经济巅峰之上的社会时期,富裕而空虚的年轻人开着跑车,自在旅行,带着美妞,抽着大麻,然后每隔两个月烧掉仓房,“浇上汽油,扔上擦燃的火柴,看它忽地起火——这就完事了,烧完十五分钟都花不上”。
而《燃烧》的背景则设置在当今韩国,高楼栉比的城市,灯红酒绿的酒吧,车水马龙的街道,欲望男女就生活在首尔大都市之中。小说中被烧的“仓房”变成了欠发达韩国农村中比比皆是的废弃“塑料大棚”。钟秀打开的电视中正播报着新闻,上面说韩国社会青年失业的问题急剧恶化。而钟秀就是失业浪潮中的一员,他作为大学生却在四处找零工。这样的人物设置反映了韩国阶级分化严重的现实矛盾。钟秀的村子每天都可以听到边境上朝鲜对南的政治广播。虽然半岛局势紧张和本片的主题没有多大关系,但可以显示在个体人生的困境与迷茫之上政治的荒谬性。
二、添加了福克纳《烧马棚》中的父子关系
相比于原著小说,电影中添加了钟秀父亲这一人物形象。
钟秀有一个躁狂症父亲李龙石,这位父亲曾经是坡州中学成绩第一名的学生。早年服过兵役,去中东打过仗,拿到过一大笔补偿金。但他却拒绝投资房地产,而是回来搞起了畜牧业。产业失败后,自尊心极强的他留下了愤怒调节障碍的病症,喜欢大发脾气,妻子因此抛家弃子而去。后来,他因压不住自己的脾气,对办事的公务员挥舞椅子,虽然无意伤人,却使对方拇指骨折。事情发生后,只要苦苦哀求,写反省文就可以缓刑,但他却死活不肯,也不听律师的话,最后被判了刑。
这个父亲形象乃是来自福克纳1939年创作的短篇小说《烧马棚》。在电影中,导演曾多次提到福克纳——福克纳是钟秀最喜欢的小说家,因为福克纳小说中写的生活很像钟秀自己的。听说钟秀喜欢福克纳之后,BEN也在咖啡馆里阅读《福克纳短篇小说集》。而且钟秀父亲是搞畜牧业的,家中有一个马棚,里面养着一头孱弱的小牛。这些情节设置都在向福克纳《烧马棚》致敬。在《烧马棚》中,落魄穷困的佃农父亲阿伯纳性格暴力,他解决人和人冲突的办法就是点起一把火烧了别人的马棚。他十岁的儿子沙多里斯迫于亲情为他父亲做了伪证,但他希望父亲能就此改过自新。但当父亲又一次不顾他和母亲的劝阻执意要去烧毁少校家的马棚时,小男孩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失望与愤恨,跑去少校家告了密。最后,他逃离了家庭,“天马上就要亮了,黑夜马上要过去了。他从夜莺的啼声中辨得出来……何况太阳也就要出来了”,等待他的是光明而充满希望的新生活。
福克纳小说中的儿子沙多里斯内心充满正义感、渴望稳定和安全,钟秀也是一样。钟秀和父亲“心中总是充满愤怒”不同,他心思细腻,富有同情心。他去拜访一位前辈为犯事的父亲想办法。他为父亲写请愿书,四处请求乡亲们签名。他很负责任地去喂一只从未现身的猫。他在牛棚里挥汗如雨地收拾牛粪,当小牛犊被卖掉时,他充满了不忍。他毫不犹豫地为十六年不见的母亲还高利贷。惠美失踪后,他费尽周折地去找惠美的同事、母亲,还去了哑剧学校,努力打听惠美的下落。
但在小说中,善良的儿子最终选择了背叛暴力的父亲,逃离了家庭。因为沙多里斯相信公平和正义,本能地认为少校家代表着秩序与规则,而父亲的放火代表着邪恶的破坏。他最后选择告发父亲,其实就是选择了后天法律和规则社会,而不是先天血亲。而在电影《燃烧》中,富有同情心、念过大学的钟秀,最终却继承了父亲的愤怒和暴力,选择了自我复仇。父亲什么也没有留下,只留下了一匹孱弱的小牛犊,还有一箱子整齐锃亮的匕首。钟秀卖掉了那头小牛,拿着父亲的刀具杀死BEN。电影中有好几处镜头是钟秀父亲被庭审的场面,钟秀在旁听席上孤零零的身影显得十分渺小。钟秀对复杂的法律、冗长的辩护似乎没有任何的信任。这也是他认定BEN杀死惠美之后,不去诉诸法律而是选择自我复仇的原因。父亲曾经让他烧掉母亲的衣物,童年那场熊熊烈焰曾多次出现在他的梦境中,原来那种破坏性的、毁灭性的大火,被证明是最好的工具。最终,他正是用火这一武器烧掉了BEN的尸体和跑车。
福克纳的《烧马棚》是文学名篇,李沧东能在众多文学作品中,将《烧马棚》拈出,将之与村上春树的《烧仓房》完美嫁接,反映了其对东西方文坛强大的掌握与理解能力,也大大丰富了电影中男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揭示了他最终行为的心理轨迹。
三、设计出具体情节坐实了对烧仓房的猜疑
在她神秘消失之后,“又一个十二月转来,冬鸟从头顶掠过。我的年龄继续递增。夜色昏黑中,我不时考虑将被烧毁的仓房”。村上春树的小说便这样余韵未了地结束了。读者可能会去继续猜测“仓房”到底是什么,可能有人认为那只不过是一个年轻人在吸食大麻后的胡言乱语罢了。因为在小说的一开篇,她就给我表演了“剥橘子”的哑剧,她说:“总之不是以为这里有橘子,而只要忘掉这里没橘子就行了嘛,非常简单。”在小说中,我认为“简直是说禅”“我因此中意了她”。哑剧,就是把不存在的东西当成了存在。我把烧仓房当成了杀人,是否也是一出我想象中的哑剧呢?
而在电影中,惠美也表演了这个剥橘子的哑剧。电影完整地复制了小说中这个情节,说明哑剧“剥橘子”有重要的隐喻作用。但相比于小说的戛然而止,电影接下来设计了一半的情节来证实钟秀必须忘记他家周围实实在在的仓房,因为BEN烧的不是仓房,而是杀死了惠美。
首先,电影中增加了一只猫。一开始惠美要去非洲旅行,钟秀负责照顾惠美的猫。但这只猫一直躲藏起来从未和钟秀谋过面。但当惠美消失后,BEN家里却平白多了只猫。当钟秀试探性地叫了惠美猫的名字“Boil”。小猫似乎很熟悉这个名字,一下子就温顺地跳进了钟秀的怀里。这无疑让钟秀五雷轰顶,他证实了他的猜测——惠美的确被BEN 杀死了,惠美的房间是被BEN收拾干净的,而且BEN带走了惠美的猫。
而且,电影还在BEN卫生间里添加了一个神秘抽屉,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女性的饰品。当钟秀发现这其中也有惠美的腕表时,更加验证了BEN烧死的是惠美而不是塑料大棚,而且,这样死在BEN手里的女性还有很多。BEN甚至还用惠美“像烟一样消失了”的话来暗示惠美是被烧死的。再者,惠美消失后,BEN又有了一个新女友。新女友和惠美一样年轻漂亮,做着底层的工作。BEN同样带新女友去见他的朋友们,新女友和惠美一样在卖力表演以求融入诸人。BEN同样面带微笑,打着哈欠。这就暗示着,这个新女友很可能就是下次将要被烧的“塑料大棚”。如此一来,在影片后半部分导演设计出了具体的情节,一步步坐实了钟秀对于烧塑料大棚的怀疑,这都代表着李沧东对村上春树原著小说的思考与诠释。
另外BEN 家中走廊尽头有人体骷髅形状的装饰画,还有蹲踞着的神兽雕像,BEN在做饭时说他喜欢制作“祭品”,及其BEN戴上隐形眼睛,郑重其事地为新女友化妆的场面,也颇有献祭的仪式性。这未尝不是导演对韩国社会近年来邪教横行、屡有漠视生命事件的现实影射与反思。
四、将主旨上升到对大小饥饿的探讨
电影中还出现了“Little hunger”(小饥饿)和“Great hunger”(大饥饿)的揭示,这是导演试图用哲学性的观念,来展示三个主人公的生存状态。
惠美对钟秀说:“非洲卡拉哈里沙漠里有一个布希族,听说对于布希族来说,有两种饥饿的人。Little hunger和Great hunger。Little hunger 则是指一般肚子饿的人。Great hunger是为生活意义而饥饿的人,我们为什么活着、人生有何意义—— 终日探寻这种问题的人,布希族认为这种人才是真正饥饿的人。”于是为了见一见这些“Great hunger”的人,她带着微薄积蓄去非洲旅行。后来,惠美在BEN的朋友面前跳起了布希族舞蹈。双手平朝下面,就是Little hunger,把双手举到上面,朝向天空就是Great hunger。在钟秀家院子里的夕阳下,惠美再次裸身跳起了Great hunger之舞,并且动情地留下了眼泪。
钟秀是生活在“小饥饿”之中的,他开着父亲留下来的泥迹斑斑的小货车,干着体力劳动,他没有时间写他的小说,而是一直在工作。惠美首先是一个被Little hunger所困的人,她住着狭小的房子,没有稳定的工作,欠着还不完的卡债。BEN最后对钟秀说:“据我所知,惠美现在一分钱都没有。”而在电影中,更让惠美痛苦的是Great hunger。钟秀说家里出了点事,惠美毫无反应,钟秀奇怪地说:“不问出了什么问题啊?”惠美说:“问题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嘛。”Little hunger总是存在的,那就不用去管它了。所以,惠美没有把钱去还卡债,而是千里迢迢去非洲旅游,去人迹罕至的地方看落日,看着血一般火红颜色的晚霞,她泪流满面。她做的这些看起来莫名其妙的事,都是为了安抚她内心的大饥饿。所以她哭着说:“我也好想像那晚霞一样消失掉,如果能像最初就不存在那样消失掉就好了。”惠美抽完大麻之后在夕阳下的那一段裸舞,是一组完整的长镜头。她不断地向着天空举起双臂,那是布希族的大饥饿之舞。正因为惠美在穷困潦倒中还在追寻人生的存在意义,所以在BEN看来,她才这样“有意思”。可以见得,惠美和韩国电影中一贯塑造的复仇女性、女权女性、欲望女性都不一样,显示出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意味。
和原著小说一样,电影中的BEN物质上很富有,丝毫没有Little hunger的困扰。钟秀嫉妒地对惠美说:“他年纪轻轻过上这样的生活,悠闲地到处旅行,开着保时捷,在豪宅里面煮意面,像盖茨比,不知在干什么却很有钱。谜一样的年轻人。”但他同时也在抽大麻,甚至玩着每两个月烧一次塑料大棚的危险游戏,这说明他精神上的空虚幻灭。他烧塑料大棚只是为了听那“骨骼深处响起的贝斯声”,这里的“贝斯声”可以理解为精神上的满足,也就是Great hunger的满足。他和钟秀最后的谈话中说:“钟秀你好像太认真了,认真就没意思了。要享受才对嘛。要在骨骼深处响起贝斯声,才是活着。”这句话听起来似乎语重心长。
在原著小说中,我的经济情况不明,“她”是一个穷光蛋,“收入实在微乎其微,不足部分似乎主要靠几个男友好意接济”。而他“做什么不知道,反正就是有钱”。但村上春树并没有直接提到大小饥饿问题,电影中却重点把握了这两个名词。如此一来,与其说三个年轻人处于不同阶级,还不如说三个年轻人处于不同的饥饿状态。这就涉及了人的存在与生命的意义问题,一定程度上将本片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
五、设置了钟秀杀死BEN的结局
村上春树的小说全文没有高潮和矛盾冲突,也没有结局。她失踪后,我每天早上仍在五处仓房前跑步,那些仓房依然一个也没被烧掉。“冬季的鸟们在冰冷的树林里啪啦啪啦传出很大的振翅声,世界照旧运转不休。”村上春树擅长用“一种轻的方式讲述那些生命之重”的叙述,让原著小说极其寂静且平淡。
而在电影中,钟秀执着地追寻BEN烧的“仓房”究竟是什么,最后他认定“仓房”就是惠美,他愤怒地将BEN杀死,并烧掉了犯罪现场。影片最后出现的火光冲天成为全片的高潮,这时候响起了深沉的贝斯声。BEN被杀死似乎大快人心,观众在电影的最后似乎得到了悬疑告破的满足。但这个结局同时也经不起推敲:如果惠美只不过是“例常消失”而已,BEN其实是无辜的呢?BEN死之前的最后一句话:“惠美在哪里?不是说和惠美一起来吗?”似乎他认为惠美还活着。毕竟猫对名字的反应说明不了什么,BEN卫生间首饰盒中有惠美的手表也有很多种合理的解释,那么钟秀做的岂不是一场肆意妄为的谋杀?
在原著小说中,村上春树提到一个“同时存在”——“的确未尝不可以称之为同时存在。一个我在思考,一个我在凝视思考的我。时间极为精确地刻录着多重节奏。”在小说中,惠美或者死了或者没有死这两种结局是“同时存在”的。而在电影中,除了这种不确定的“同时存在”外,导演李沧东又加上了第二重“同时存在”——钟秀真的杀死了BEN吗?或者钟秀只是在进行小说创作,毕竟他杀死BEN 前一个镜头是他在惠美房子中写小说。这就使得电影比小说多了一出巧妙悬念,导演这里把现实、猜测、创作三者融为一体,让本来扑朔迷离的剧情更加惹人猜想。
如此以来,电影中虽然将人物具象化,又添加了许多坐实钟秀猜测的情节,但现实和虚幻、存在和消亡还是无法清晰地划分界限,电影就在声影变换中,让观众再次深刻地迷惑,从而引导观众思索人生与人性。
——青年记者“走转改”水墨画般的村庄书写着别样的春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