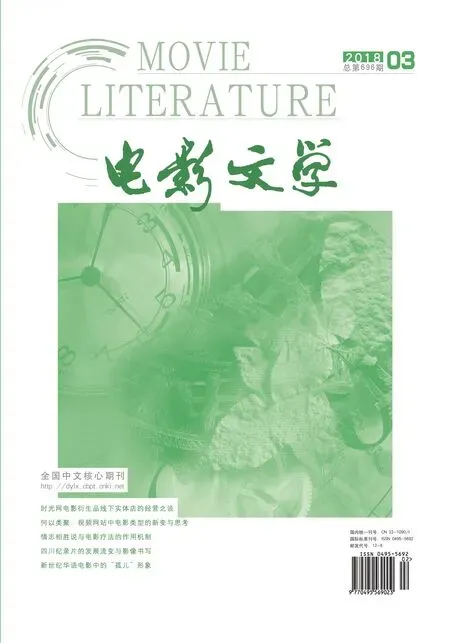《萨利机长》个人价值之外的人文关怀
刘 虹
(云南农业大学 外语学院,云南 昆明 650201)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萨利机长》(Sully
,2016)可以说是一部典型的伊斯特伍德电影,但又是一部“非典型”的灾难片。在传统灾难片中,灾难的发生往往是电影叙事的高潮,而灾难片产生的令人感到恐怖、凄惨和惊慌的景观则作为电影最主要的观赏点而被大量运用视觉特效进行表现。而《萨利机长》则在保留了伊斯特伍德一贯冷静、简单的叙事风格和沉稳的镜语设计的同时,并未对灾难惊心动魄的一面进行过多渲染。相对于刺激观众的视觉心理,伊斯特伍德更重视的是电影传递出来的人文情怀。一、人生存价值的重视
在人文情怀中,最首要的便是对人的重视。人文主义诞生的过程便是人类对自身价值和尊严进行认识,以及对人应该享有的自由、权利等进行追求的过程。例如,康德就曾提出,人是“客观的目的,他的存在即是目的自身”。灾难片之所以具有魅力,正是因为人处于危险的境地之中,并且人在这样的环境下迸发出了生命张力。观众一方面同情和怜悯银幕上处于悲剧、压抑氛围中的受难者,另一方面又感叹于他们在灾难面前表现出来的生命活力,包括对自我的救援以及对他人生命的关爱、重视。
在《萨利机长》中,人文主义品质体现得最为明显的便是主人公萨伦伯格(昵称为萨利)。电影改编自2009年的全美航空1549号航班迫降的真实事件。当时的空客A320在从纽约的拉瓜迪亚机场起飞不久后就遭遇了鸟群的撞击,出现了双发停车(两个发动机引擎因为损坏而同时熄火)的严峻局面。机长萨利此时相当于驾驶着一架几十吨重的毫无动力的滑翔机,且飞机之下就是人口稠密的纽约城区。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萨利果断决定在哈德森河面迫降。而在此之前,大型客机水面迫降全部以机毁人亡告终,只能有少量的幸存者生还。而在萨利的操作下,飞机上的155个乘员全部生还。这一次空难也被称为“哈德森奇迹”。
萨利始终高度重视每一位乘客的生命,在迫降时,他就已经尽量选择了靠近渡轮的位置降落,这直接导致飞机在落入水面后仅仅4分钟,就已经有周边的船前来救援。在这一次紧急迫降中,尽管萨利在水面迫降成功,但是河水很快就涌入机舱,飞机上的全体人员在机体彻底沉入河底时只有20多分钟的逃生时间,机组成员需要迅速指挥乘客离开飞机。此时的萨利机长从容不迫地穿着制服,指挥乘客站到机翼和橡皮艇上,用自己的镇定安抚乘客。而他自己则实践了“最后一个离开”的行为准则,在离开之前,萨利两次检查机舱,在大腿深的冷水中确认所有人都已经离开,自己才走。对于萨利来说,尽管时间有限,但他所要做的就是完成自己的工作。在迫降结束之后,萨利还反复要求确认是否找到了155个人。电影为了突出萨利对生命的重视,加入了两个细节:一是萨利在医院得知无一伤亡后,眼中闪烁着泪光,随后萨利走到窗边给自己整理了一下飞行员领带;二是萨利在去到宾馆住下后,从钱包中掏出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一次延误也要好过一次灾难”,这张随身携带的字条代表了萨利作为一个机长的深沉责任感。
如果电影仅仅是突出萨利在灾难面前的恪尽职守和技术过硬,那么电影的人文深度还是不够的。在电影中,以“反派”面目出现的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实际上也是一个从另一个角度来关注人的生存价值的角色。电影中当萨利赢得所有人的感激和颂扬时,运输安全委员会委员们却始终以咄咄逼人的姿态质疑萨利的处理方式,坚持通过电脑数据的模拟以及虚拟飞行来试图证明萨利没有听从塔台的意见返回拉瓜迪亚机场或降落在另一个机场是错误的、冒险的决定。从表面来看,萨利拯救了他人,成为炙手可热的英雄,但是却无法回家,甚至有可能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数十年的飞行都被这208秒的迫降否定,这是荒诞的。双方的争执成为电影叙事的主线。也正是在双方的据理力争中,伊斯特伍德安排了数次闪回,让观众不断接近事件的真相,也慢慢走入萨利的内心世界,在平缓的叙事节奏中带起了张力十足的节奏。尽管当观众处于萨利的立场时,容易对运输安全委员会感到不满,然而伊斯特伍德所想表达的却是,作为一个第三方,安全委员会表现出了成熟公正的追责态度,并不为媒体所动摇,而坚持运用各种手段还原事故现场,在打捞起发动机后,发现自己的数据错误后又真诚地向萨利道歉。正是这一国家机关反复地追究细节,执行制度和流程,才有可能避免更多更惨重的,有可能威胁更多人生命的灾难发生。这样一来,电影中的矛盾双方都被统一到尊重生命、对抗死亡这一人文精神上来。
二、人性光辉的展现
《萨利机长》中,空难成为一面镜子,人在空难之中被置于生死考场上,能够在这一命运临界点上表现优越者,自然散发着善良、勇敢等人性的光辉。在空难之外,还有如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也同样是恐怖的,同样会给人类带来损失与悲伤。但是在灾难情境中,人类表现出利他的、舍己为人的品质,有别于动物性的人性代表了人类的尊严。
《萨利机长》中,在听证会上,当人们夸赞萨利拯救了大家时,萨利曾表示,之所以能出现“哈德森奇迹”,并不仅仅是机长的功劳,这个奇迹属于全体机组成员,包括水面的救生艇船员、纽约警察局,以及一百多名乘客自己。电影中也对这些角色进行了充分表现。副驾驶斯凯尔斯始终保持镇定并且听从萨利指挥,积极配合萨利的工作,先是尝试重启引擎,随后查阅处理手册。其他的机组成员对于机长也是无条件地信赖。在听到萨利的“准备撞击”的广播后,空姐们就迅速出来维持机舱的秩序,始终大喊着“Stay down”让旅客保持趴好低头用力的姿势,在打开机舱门后一名空姐的脚受伤,乘客大呼“水里有血”,空姐依然让乘客先行撤退,自己最后才在萨利之前撤离。而地面上的搜救人员也反应迅速,轮船船员马上向飞机靠拢,而搜救队的蛙人在看到落水乘客时为了节约时间甚至在没戴氧气筒的情况下直接从直升机上跳水救人。乘客们在这种紧张时刻也没有过于慌乱,而是井然有序地站在机翼上等待救援,主动帮助身边的妇女和小孩。换言之,当萨利在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时,其他人也在尽忠职守。正是所有人的团结一心造就了“哈德森奇迹”,否则单凭萨利一人之力,是无法保证155名人员全部生还的。这些都闪烁着人性的光辉。与之类似的还有如约翰·拉菲亚执导的《10.5级大地震》(10.5,2004)等,电影中急救室的护士、总统的幕僚长、州长的女秘书以及地质研究院的女博士等,也都在地震来临时选择忽略自己的个人烦恼,坚守各自的岗位。
在美国电影普遍崇尚塑造出类拔萃的超级英雄时,《萨利机长》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让观众看到普通人同样可以成为英雄式人物。电影中将个人能力发挥到最大限度的角色是萨利,但是萨利本人的表述却是否认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一直保持了在荣誉面前的低调,不认为自己单枪匹马拯救了全飞机的人。电影结尾的字幕所赞颂的也是“纽约的骄子们”。在对普通人进行表现时,《萨利机长》也表现出了一种去精英化的戏剧化的倾向。相对于《10.5级大地震》中科学家、学者、政客等依然属于精英阶层的人物不同,《萨利机长》中乘客的面目是模糊的,给予较多戏份的父子三人也只是因为急着打高尔夫才临时上了这架客机的普通乘客。伊斯特伍德无意在乘客的身份和个人遭际上制造戏剧性,这正是为了让这一类人的形象更接近作为普通人的观众。另外,萨利以及其他人所做的努力并不是传统个人英雄主义叙事中违背国家制度束缚的,他们的“壮举”恰恰是在严格遵守制度、规则和传统道德的情况下完成的。可以说,《萨利机长》以一种非个人英雄主义的方式,满足了人们的英雄情结。《萨利机长》的人文价值也正体现在这里:超级英雄中的英雄典型模式是不可复制的,而萨利机长组织的这一次逃生尽管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却是一次可以被学习和借用的正能量,尤其是经历了“9·11”伤痛的纽约人,在正面临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美国人看来,“哈德森奇迹”的力量是强大的、令人振奋的,会有更多的普通人铭记这件事,从中获取经验。这其中就包括在生死关头对美好人性的保持。
三、社会与人关系的思索
人是生活于庞大的社会之中的。人文主义的诞生本身就证明了新的精神生活内容和思想形式是来源于新的生产方式的,正是西方中世纪的封建生产方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传统的教会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时,主张重视世俗的文艺复兴运动才得以产生。因此,当我们用人文视角来审视一部文艺作品时,有必要关注该作品对于人类身处的社会的刻画。《萨利机长》的一个值得称道的地方就在于,伊斯特伍德能够跳出灾难,以灾难为一个切入点,让观众看到一些现实景象的剪影,从而对灾难之外的社会问题进行反思。
例如,在飞机迫降之后,与安全运输委员会对萨利的严肃审查不同,媒体迅速将萨利包装成一个国家英雄,无论是纸媒抑或是电视等媒体,包括纽约街头的大屏幕,全是对萨利的正面宣传,萨利去酒吧也被认出,酒吧甚至为他发明了“萨利酒”。而这种宣传是违背萨利本意的。在萨利看来,他只是做了分内之事,而媒体的这种包装给予了正在等候调查结果的萨利极大的压力,使萨利做了媒体报道他是骗子的噩梦。媒体之所以出现这种对英雄的狂热,很大程度在于媒体要迎合民众的需求。电影中无数次提到2009年还没有发生过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情,而当时还是1月15日,民众有着因为战争、经济等造成的焦虑感。萨利的紧急迫降成功慰藉了民众的心,因此媒体马上塑造了一个供民众崇拜的英雄,他们围堵在萨利妻子的家门口,干扰了萨利妻女的生活。又如替单身妈妈亲吻萨利的化妆师,表示恨不得把酒店都送给萨利的酒店经理等,都是这种民众的代表,而这些都让萨利无所适从。又如安全运输委员会对于萨利的苛求,如QRH检查单的检查顺序等,体现出的是一种僵化体制对人安全和尊严的戕害。在灾难没有伤害到人之后,人类却有可能伤害到人类自己。这无疑是值得人反思的。
灾难对于绝大多数观众来说毕竟是有一定距离的,但是社会症结却是无处不在的。伊斯特伍德所揭示的种种社会乱象,使《萨利机长》更为深刻。
艺术是人们将现实生活升华、转化为审美的过程。在电影艺术中,影像帮助观影主体进行思想的释放,走近艺术,再进一步改变观影主体的思想、情感甚至是创造力。这也是大量具有高层次人文情怀的电影的美学作用。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老骥伏枥,于近90岁的高龄推出新片《萨利机长》,电影以机长萨伦伯格以及“哈德森奇迹”为中心,让观众重新认识了这一次空难。更重要的是,电影通过对人类生存价值、人性光辉乃至人在当前社会遭遇的诸多问题让观众对于当代生活以及人性有了新的感悟和体验。经由伊斯特伍德塑造出来的萨利机长形象,激发着人们对于理想人性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