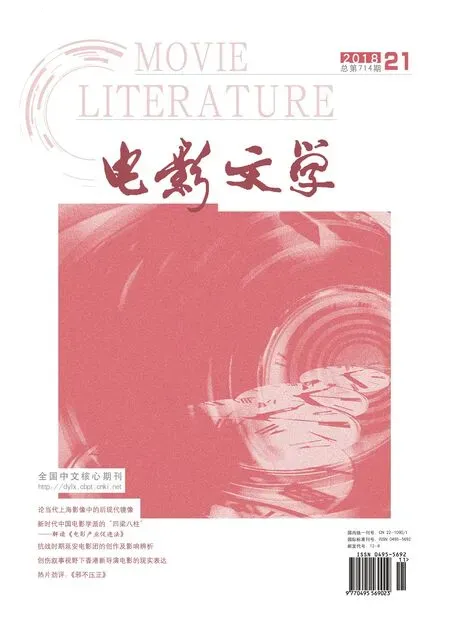《米花之味》:傣族乡村的诗意救赎
赵 敏 袁智忠
(1.大理大学 文学院,云南 大理 671003;2.西南大学 新闻传媒学院,重庆 400715)
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疆,是众多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又与东南亚多国接壤,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多元文化生态格局。20世纪“十七年”时期是中国电影发展的黄金时期,在云南拍摄完成的少数民族经典电影众多,从《五朵金花》《阿诗玛》到《摩雅傣》《青春祭》,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光彩的一页。新世纪以降,我国电影产业发展迅猛,涌现了大量的商业类型电影与美国好莱坞电影正面交锋。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经过数十年的市场化磨合,也逐渐从体制变革的阵痛中复活过来,开始主动适应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的新语境。鹏飞执导的傣族题材电影《米花之味》是他继《地下香》之后的又一部长篇之作。影片以独特的傣族乡村风情、温暖人心的画面表现和不乏幽默的细节设计,被评为“平遥国际电影展新生代单元最受欢迎影片”,院线上映后收获了不俗的票房和较好的口碑。
一、叙事:遵循诗的逻辑
“诗意电影以诗的逻辑确立自身的影像和叙事结构”,以画面为主要媒介“表现如诗歌一般的富有意境的电影效果”,常打破固有的语言符号类型和影像习惯,思想表述含蓄而感性,变确定性为不确定性。近年来,诗意美学风格的代表之作有《路边野餐》和《长江图》,诗歌以独白或字幕的形式垂直切入故事,打破了电影常规的叙事逻辑,赋予影片别样的韵律美感,将过去与现在、幽冥与现实杂糅。《米花之味》在云南傣族乡村取景拍摄,其画面具有诗意的景观之美——温暖明媚的阳光下,田间微风徐徐吹来,将处于中缅边境的小村庄描绘成现代化建设缝隙中的“诗意栖居地”。留守儿童的主题也被处理得随意而含蓄,叙事漫不经心,结局具有开放性,以诗的逻辑将故事呈现。与20世纪80年代同样拍摄于傣族乡村的《青春祭》相比,《米花之味》少了一些时代与命运强加于个体的无奈之感,多了几分活泼和轻快,配合当地非专业演员的方言土语以及自然融入故事的民族风俗,使电影洋溢着傣族乡村的“原汁原味”,细节设计不乏幽默。
舒缓的情节节奏和弱化的叙事逻辑往往被认为是诗意美学的风格表征,由此决定了诗意电影对矛盾冲突的处理较为克制,人物的悲喜之情不会肆意爆发。当返乡的叶喃看到女儿吃完东西不收拾、学习成绩倒数、沉迷于手机游戏和网吧,甚至养成了偷盗的坏习惯时,愤怒的情绪无法通过训斥和说教来排解,只能用沉默的让步取代,伤心之情被轻描淡写地掠过。情与理、是与非、对与错,希望女儿自己去感受和领悟。心灵产生的距离正好为诗意的表达提供了心理空间,冲突因地理距离而起(母亲外出打工),又通过心理距离稀释。饰演叶喃的英泽表演纯熟稳重,将母亲对孩子的愧疚、无奈、包容、爱等多种情绪细腻地交织展现,在情绪处理方面趋近于“不急不躁的东方诗意美学”。平凡的生活琐事和普通人的烦恼都借由诗意的镜头语言娓娓道来。请山神、点佛灯、拜石佛等宗教元素的适当融入,既是当下傣乡生活的真实写照,又能够满足大多数观众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神秘期待。
然而按诗的逻辑来书写,在诗歌与叙事两种艺术形式之间频繁跳跃必然会带来整体的割裂感。若以诗意来统筹全片,对于留守儿童这一社会问题则着墨过多,结尾处好友喃湘露的死更是无比沉重。若以反映留守儿童问题为主要目的,则影片只是隔靴搔痒,并未触及问题的核心,即母亲离家的必要性及对孩子成长的影响缺乏应有的思考和讨论。米花在傣族乡村是一种较有特色的食品,“米花之味”以甜味居多,如果日常生活是酸甜苦辣各种味道的混杂,那么在叶喃回乡的日子里,面对女儿的各种心理和行为问题,即便身在如诗画般优美的家乡,心中的甜味也基本是缺失的。
二、画面:色彩造型与偷窥视角
影像作为一种视觉为主的艺术形式,画面造型是其特色,常通过色彩、光影等视觉元素来完成人物情绪的烘托和主题思想的隐喻。基耶洛夫斯基的《蓝白红三部曲》借用色彩对情绪的唤起,通过叙事将各自所代表的寓意逐一表现:“蓝——自由、白——平等、红——博爱。”用形象的色彩符码勾勒出主题的轮廓,加深思想深度。在国内,学摄影出身的张艺谋对色彩表现也有精致的追求,以《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英雄》《长城》《影》为代表的一系列电影形成了张艺谋特有的色阶造型艺术,深具思想隐喻性。在云南拍摄的《米花之味》得益于自然景观色彩的高饱和度,镜头里满是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和黄灿灿的菜花田,使画面充满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伦理之美。
《米花之味》的宣传海报设计精良,暖暖的阳光下身着傣族服装的母女二人在菜花田中露出甜美的笑容,大面积出现的明黄色是无法被忽略的视觉标识。黄色往往能够激起观众一系列积极的情绪体验,例如《我的父亲母亲》中黄灿灿的菜花田是丰收的预兆,也是父亲母亲年轻时甜蜜、幸福和欢快的标识;《满城尽带黄金甲》中的黄色又是财富和身份的象征。但是在《米花之味》里,这些与黄色相对应的积极情绪体验,对于中缅边境傣族乡村的留守儿童喃杭来说,恰是她心灵深处的渴望。虽然有外公照顾,每个月靠着母亲寄来的生活费衣食无忧,可我们仍旧无法将喃杭定义为“幸福的孩子”。正如山神附身的阿婆说道:“米花变味了!”米花究竟应是何种滋味?影片想阐释的内容“多”而“重”,母女关系、留守儿童、家庭教育、乡风振兴、死亡、宗教……小而轻盈的米花能否承受得住?影片最后母女二人在石洞中共舞的段落,完成了心理层面的和解,也是宗教皈依的形象化显现。在精神分析理论的观照下,山洞既是傣族乡村的信仰之源,也是对母体子宫的隐喻,母女间的“爱恨”回到最原初的状态——共生,返归自然天真的心性和自由洒脱的状态。
电影观众的缺席通常被认为是“在场”,全知视角下故事与观众容易产生身份认同,窥视体验在黑暗的观影环境中得以发生。鹏飞在《米花之味》的镜头设计中,突破性地使用了主观窥视镜头,将留守儿童对于亲人爱的渴望和自己内心深处的自卑呈现出来。例如,喃杭面对母亲的归来表现得十分冷漠,用被子蒙住自己,只露一个小洞出气,镜头模拟了从小洞内向外窥视的主观视角,无论母亲怎样轻言细语,喃杭都不肯掀开被子看一看桌上的零食和隐喻着大千世界的礼物——地球仪。又如,喃杭在网吧通宵游戏,母亲默默地等了一夜,回来的路上没有半句责备,此时导演再一次使用了主观镜头,模拟喃杭从汽车后排向前窥视的目光,小心地捕捉着母亲的情绪反应,十足一个做错事的孩子,愧疚和不安之情无法掩饰。据导演鹏飞讲述,在拍摄《米花之味》之前他在傣族乡村与当地居民同吃住,深入了解傣族人的生活,对当地的留守儿童问题有深刻的理解,才能在拍摄的过程中积极探索,努力丰富境语类型,力求突破少数民族电影既有的形式与风格。
三、救赎:留守之殇与伦理之惑
随着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工作的不断推进,少数民族宗教伦理呈现出世俗化的趋势,佛教的教义与当代社会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渐趋近,成为规约当地民族日常行为的共同准则。西藏和云南都属于高原,生态保持相对完好,人与牲畜、自然和谐共生,再加上有不少“神山”“圣湖”分布,自古就被看作离天最近的地方,观众对高原地区充满了无限神奇的审美想象。于是,在融入了藏族和傣族元素的电影中,寻求心灵救赎似乎成为一个既定的母题。《转山》《七十七天》《冈仁波齐》《寻找罗麦》《这儿是香格里拉》都在去往藏地的过程中寻求自我内心的安定。《青春祭》中下乡到傣寨的女知青通过与当地傣族姑娘的相处,实现了女性审美的觉醒。
让下一代过上更好的生活,成为“不得不”背井离乡的广大农村父母进城打工的动力之源,也造就了“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物质相对宽裕以亲情缺失为代价。喃杭对突然回家的母亲十分不习惯,不愿正视母亲的关爱,更不满其日常的责难,关爱和埋怨的情绪相互撕扯,母女二人摩擦不断却又无力改变,渴望救赎。《米花之味》的救赎具有多重指涉的特点,溶洞中母女二人在佛前共舞的造型设计极具宗教仪式感,既是对好友喃湘露离世的祭奠和超度,又是母女在佛像面前放下心里的矛盾,回归理解和互爱的表征,同时整部诗意风格的电影通过优美的自然景观和娓娓道来的温情故事对银幕观众进行了一次心灵洗涤。石佛洞中的石钟乳有水滴落,几百年来汇聚成潭,是傣族自然崇拜的体现和心灵归属地的隐喻。傣族人自古就相信“天有天神,地有地神,江河有水神,植物有植物神,太阳有太阳神……”在神灵面前,人心应该是坦诚而没有丝毫掩饰的。
诗意是《米花之味》所遵循的逻辑和镜头表现特征,但诗意的“漫不经心”、感情发散或心灵漫游也为叙事和主题表现带来了过多的不确定,甚至产生困惑。从叙事的严密性来看,影片的一些重要情节缺失,所埋设的伏笔和疑问一直没有给出答案。叶喃在城里的工作是什么?又为何辞职?村里人在背后说她“尽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这是直接关系到人物道德品性的重要伦理问题,不能被省略。若真有“勾当”,叶喃没有资格站在道德的高度去评判女儿的说谎、偷盗行为;若只是村里的闲言碎语,则应在适当的时机还其清白,同时也反映了傣族乡村乡风不正的伦理问题。另外,在许多信仰佛教的少数民族地区,寺庙是神圣的象征,不容亵渎。喃杭虽是“问题少女”,可为何会堕落到偷寺庙里的钱?电影并没有就她对钱财的急迫渴望做出解释。有了精心安排的“能指”,却没有清楚明确的“所指”,或者说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具备明晰的逻辑指向性,使观众对影片的理解处于迷失、困惑的状态。
四、结 语
“讲好中国故事”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媒体人提出的新要求,在中国电影走向国际化的今天,繁荣和复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近几年中国电影市场飞速发展,一些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虽然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改变,但面对激烈的商业票房竞争,仍不具备市场优势。故事老套、人物形象刻板化、拍摄水平拙劣、营销推广意识不强、缺乏资金和专业团队等是此类电影普遍面临的困难和症候。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米花之味》能够抓住“留守儿童”这一当下的敏感话题,同时坚守心灵救赎的民族宗教母题,通过聘请高水准的摄影和音效制作团队,进行较为成熟的商业推广和运营,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艺术性与商业性的结合,获得了不少观众的认可。虽然在伦理叙事方面《米花之味》还存在一些不完满,但导演鹏飞在风格上大胆创新的勇气和精神也为新时代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打破老旧的“民俗—歌舞—景观”程式,实现多元风格提供了又一种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