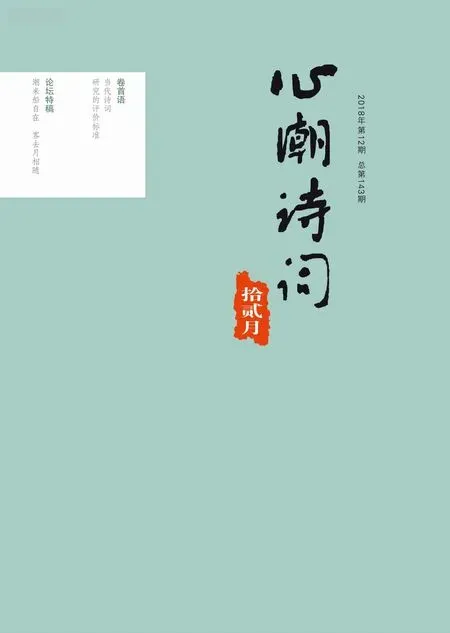变生新体成沧海 不废江河万古流
——散曲俗趣之风的传承与变奏
一、散曲俗趣之风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形成
散曲一体,在元代发展成熟,相比于唐诗的庄雅、宋词的婉媚,它主要的风格特征则是俗趣(皆就总体而言)。俗趣之风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元代广大汉族文人被社会抛弃之后,从思想意识、人生态度、文体选择和表达方式上都形成的一种反传统的叛逆思潮。以“元曲四大家”为代表的文士,普遍选择曲作为泄愤述志的书写工具,语言运用和题材选择皆弃雅从俗或化雅为俗,表达方式上则放弃传统诗词的凝练庄雅、含蓄婉媚,而一变为通俗明快、庄谐杂出、妙趣横生,简言之则为俗趣。就其实质而言,是元人叛逆的时代思潮的结晶。这当然主要是就北曲而言。
二、散曲俗趣之风的历史演变
元曲中北曲的俗趣之风一旦形成,这种在继唐诗、宋词之后兴起的中国古典诗歌的第三大诗体便宣告成熟。于是,中国诗坛由诗的曾经一体独大,到诗与词的二水分流,最终形成诗、词、曲鼎足而三的发展态势。曲文学以俗趣为美的风格,也由元、明、清而及于当代,虽然在明代有南曲的兴盛,并以清雅的风致转而向词体回归,但以北曲俗趣为美的主体特征始终得以坚持。到清代政治大一统局面形成之后,文学全面复古,因散曲文学并不古雅,遭遇冷落,由此纷零不振。直到晚清以迄民国,在国势飘摇中,散曲文学再次振作,其俗趣之风在姚华、陈栩、周梅初、吴梅、卢前、孙为霆、凌景埏等人手中得到延续。
三、散曲俗趣之风的现代传承与变奏
1949年以后,人所共知的原因,人们曾一度不知散曲为何物,幸而赵朴初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散曲作品《某公三哭》,把谐趣之风发挥得淋漓尽致,这又重新唤起人们对散曲的文体记忆。文革结束以后,在百废待兴的文艺春天里,散曲也渐渐在枯枝上抽出新芽。以萧自熙、羊春秋、丁芒等为代表的一批曲家,以散曲写时代感愤、写城乡生活,将散曲的俗趣之风带进二十一世纪。一方面是散曲俗趣之风的正宗传承,另一方面是散曲俗趣之风的别体变奏。这种别体变奏,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以丁芒为代表所倡导的“自由曲”;二是把俗趣之风融入诗词后的别开生面。如聂绀弩、杨宪益、启功、李荒芜等前辈先生在特殊时代环境中不约而同地以俗趣为美的诗词创作,继之而来的是周啸天、李子等人的诗词,亦为其流衍。
四、散曲一体的当下兴盛
进入新世纪后,长期被遗忘的散曲一体,出现井喷式发展,有几个新的现象值得关注:
一是散曲从有史以来的个人自发写作,进入到有组织的社会集体活动。自1991年中国散曲研究会成立,开始关注全国的散曲创作与理论研究,到2004年全国第一个省级的散曲创作组织山西黄河散曲社成立,再到2008年,湖南潇湘散曲社、陕西散曲学会又相继成立,紧接着广西、贵州、北京、安徽、江西等省市也先后成立了散曲创作组织。到2010年,挂靠在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下面的散曲创作室成立;2015年,挂靠在中华诗词学会下面的散曲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华诗词学会郑欣淼会长兼主任);仅就散曲创作而言,便有了两个全国性的组织及多个省级组织。这些组织对当下全国散曲创作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组织和引领作用。
二是有了专门的散曲刊物。2005年,山西黄河散曲社的《当代散曲》创刊;2011年,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的《中国当代散曲》创刊;2017年,中华诗词学会散曲工作委员会的《中华散曲》创刊。此外,还有《中华诗词》《湖南诗词》《陕西诗词》等刊物,也都先后辟有发表散曲的专栏。
三是有了网络新媒体的便捷传播。如“中华诗词论坛·中华散曲”“中国散曲研究会”“全国散曲工委”“北京散曲”等等网络平台,可以快捷地发表和传播散曲作品。
四是有了散曲理论工作者的关注和支持。从2005年以来,一直到2015年底,在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散曲研究会在组织散曲理论研究的同时,也一直把组织和指导全国的散曲创作正式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从组织建设、理论指导、作品推广、曲家宣传等方面,曾做过不少工作。散曲研究会一些专家的理论著作,有效地指导了曲家们的创作。这里还要特别提到,近年来罗辉先生花大力气、下大工夫编纂的《新修康熙曲谱》,也即将为散曲创作提供更多方便。
因为有了作品发表的方便,有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推动,有了中华诗词学会的宽阔平台和影响,尤其有中华诗词学会以郑欣淼会长为首的学会领导们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中国散曲创作,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兴时期。优秀的曲家、优秀的曲作、优秀的曲集不断涌现,传统的格律体散曲和自由曲竞相发展,俗趣之风融入诗词之后的新体变奏等等,都使得散曲一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展示出五彩斑斓,大有沧海横流之势,给人“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繁盛之感。
五、几点感想
第一,要尊重诗、词、曲三体各自的审美特征,更要容纳不同体式风格的相互渗透与融合。诗、词、曲三大传统诗体,就其在文人之手定型之后的出身而言,大致可以说诗是庙堂的,词是花间的,曲是市井的。所以,在旧时代文人眼里,它们有雅俗之分、贵贱之别。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诗体的尊卑观早已淡化,积淀下来的则是人们对于不同诗体特征的认知与接受,比如诗的庄雅、词的婉媚、曲的俗趣。我们对于不同的诗体,既要用不同的审美眼光去打量,同时也要容纳不同体式之间的互相渗透与融合,这一点很重要。有人主张要肃清聂绀弩、启功的“浅俗”诗风,有人曾经在网络上对周啸天的获奖诗歌大肆攻击等等,都是仅守其正,而否其变,固守一隅,而不知汇通之故。
第二,诗、词、曲三体的社会认可度,诗最高,词次之,散曲又次之。这种状况的形成,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一则局限于体制高低贵贱的传统偏见,二则因散曲以调侃讽刺见长不适合歌功颂德,三则因学校语文教育中对曲之一体的长期忽略,由此造成大众对曲的陌生, 这不利于传统诗词的全面发展和共同进步,我们一定要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予以改变。
第三,比较而言,曲以其语言的通俗、题材与风格的不拘、表达的直接明快和体式的灵活等草根特色,故最接地气,其发展前景,未可限量。依我个人的看法,它极有可能在吸收和融汇传统的诗、词以及新诗各体之优长之后,在传统散曲的母体上脱胎换骨,从而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大众化的格律体诗歌,而传统的诗、词、曲则渐渐地成为小众。但无论小众与大众,都将在未来的诗歌发展时空中并行不悖,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万古不废!
第四,就当下曲之创作与批评而言,创作突飞猛进,批评则相对滞后。批评滞后,也严重影响到曲的学术传播和社会认知。对于创作的学术批评,犹如舞台演出的聚光灯,只有被聚光灯照射到的人物,才能成为中心和主角,才能引起观众的集体注目。在新世纪领时代风潮的前辈作家中,如萧自熙、羊春秋、丁芒、常箴吾、李旦初等人,成就卓荦不凡,是应该被理论批评的聚光灯充分照射的时候了,还有湖南的周成村、北京的南广勋、陕西的徐耿华、山西的张四喜、刘江平、折电川等人,不谦虚地说,还包括四川的笔者本人,也都应当受到学术关注。可惜的是,因多方面原因,散曲理论批评甚少关注当下,目前还只能是活跃在创作舞台上的人各自拿着手电,不时你照我一下、我照你一下地向观众亮相,从舞台上空照射下来的具有历史穿透性的这种学术聚光灯,它的光芒的发出,似乎还要假以时日。但我坚信,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良性互动,共同推进诗词曲全面发展的日子,是终究会到来的。
——读《元散曲通论》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