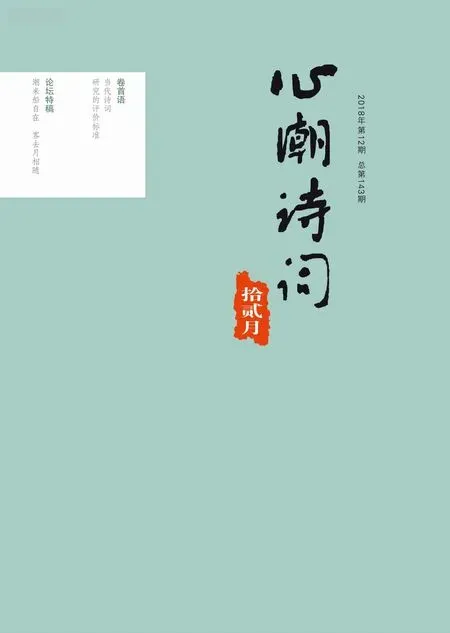大雅正声与时代精神
——为诗词创作中的歌德派正名
“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李白诗句)。诗的时代,诗的国度。复兴大雅,重振正声。对于中国当代诗词的创作及研究,凡有志于此道者,都具一定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这是一种价值取向在两个方面的不同表现,一方面是诗学,一方面是诗教。诗学目的在于诗的自身,诗教目的在于诗的外部。一个是审美的标准,一个是功利的标准。两个方面、两种表现,两种不同的批评方法,孔夫子早已为之定下规矩,并且创立一整套中国式的原则。
一、新诗与旧诗:胡适与毛泽东
中国诗坛,在二十世纪着实热闹了一番。尤其是胡适的出现。1916年,胡适的新体白话诗发表。中国诗坛从此增添了一个新品种。之前,自三百篇以后的古、近歌诗,一统天下;自胡适出,才有另一品种,以相对举。一个是新体白话诗,一个是旧体格律诗。简单讲,一为新诗,另一为旧诗。新诗与旧诗,从此以后,就在诗坛争胜。我将这段历史划分为两段,两个六十年,两个甲子。并且为之下了断语。第一个六十年,从1916年到1976年;第二个六十年,从1976年到2036年。只就旧诗而言,第一个六十年,死而复生;第二个六十年,生而复死。而新诗呢?毛泽东主席说:“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此前如是,此后又如何?
但我的这一断语,是从主席那里学来的。这是一种文学语言的描述。
二十世纪中国诗坛,新诗与旧诗,在其发展、演变的第一个六十年,胡适与毛泽东,两位领袖人物,其开天辟地的历史贡献将永载史册。
(一)胡适与“胡适之体”
1.半阕《生查子》及其创作灵感
胡适喜作《沁园春》,在其明确挂上招牌的二十九首歌词作品中,七首寄调《沁园春》。以下所录,为其中一首。其曰:
弃我去者,二十五年,不可重来。看江明雪霁,吾当寿我,且须高咏,不用衔杯。种种从前,都成今我,莫更思量更莫哀。从今后,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 忽然异想天开。似天上诸仙采药回。有丹能却老,鞭能缩地,芝能点石,触处金堆。我笑诸仙,诸仙笑我。敬谢诸仙我不才。葫芦里,也有些微物,试与君猜。
歌词附小序:“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是我二十五岁生日。独坐江楼,回想这几年思想的变迁,又念不久即当归去,因作此词,并非自寿,只可算是一种自誓。”这是自寿,也是自誓。这一年的四月十六日,另有同调歌词题称:誓诗。此前所作,其谓“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在于破解对于诗歌创作的一种传统观念,对于破旧的宣誓;此时所作,其谓“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乃对于立新的宣誓。破旧好理解,立新可就甚费斟酌。请留意歌词煞拍的语句:“葫芦里,也有些微物,试与君猜。”就是说,我老胡倡导“文章革命”(文学革命),到底有何奥秘?诸位老兄,包括新诗、旧诗的朋友,有谁猜得出来?
到现在,新诗界的朋友猜不出,可能也没人猜,同样,旧诗界的朋友也没人留意这一问题。但是,我猜着了,早在二十年前,就知道老胡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能知道吗?什么药?不就是收到他在不久之后所出版的《尝试集》里面的那些“微物”吗?比如,《希望三首》:
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希望开花好。
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
急坏种花人,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
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
这三首“诗”,写于1921年10月4日,在北京大学任教职。时年三十。见《胡适的日记》(1921年10月4日)。载北京《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1922年7月1日)。收入《尝试集》。语言学家赵元任曾为之谱曲。这是旧诗还是新诗呢?从字面上看,没人说是一首旧诗,是一首词。一首怎样的词,一首由半阕《生查子》所构成的词。三个半阕,构成一组联章。
由半阕《生查子》所构成的“诗”,这就是胡适葫芦里所藏的“微物”。怎么样?知道胡适想干什么吗?他想提示新诗界的朋友,用填词的方法作新诗。《生查字》,双调。四十字。上下片各两仄韵。格式与五言古绝相仿。胡适拿来,砍去一半,留下一半,即据为己有。成为自己谱写歌词的一种独特方式。
那么,胡适用半阕《生查子》作“诗”的灵感从哪来的呢?从陈衡哲女士那里来。胡适《寄陈衡哲女士》一“诗”有云:
你若先生我,我也先生你。不如两免了,省得多少事。
这首“诗”,写于1916年11月1日,在哥伦比亚大学。时年二十五。载同日日记。谓不必以“先生”相称,是否有亲近之意,未可知。但有一事可以肯定,对于女士《咏月》,老胡颇极赞赏,以为“绝非吾辈寻常蹊径”《致任叔永书》说明老胡的试验,应与女士所作相关。
陈衡哲《咏月》诗云:
初月曳轻云,笑隐寒林里。
不知好容光,已印清溪底。
2.为新体诗创作寻求生路
胡适与陈女士相比,才气及情致,均大为不及。胡的一百首,也抵不过女士一首。陈女士所作,乃偶一为之,非同胡适,做“文章革命”(文学革命)。就其主观愿望看,应当还是一首诗,五言古绝,而仍非词。不过,这一故事,揭示了一个秘密:借用半阕《生查子》之句调谱写新词,以填词方法作新诗,这是胡适为创造新诗体所进行的一次有意识的“尝试”。
除了半阕《生查子》,这是大量填制的词调,此外,《西江月》《临江仙》《鹊桥仙》以及《好事近》,亦曾填制。而对于《好事近》这一词调,则特别兴趣,所填制篇章之数量,仅次于《生查子》。其《小词》(“好事近”调子)有云:
回首十年前,爱着江头燕子。一念十年不改,记当时私誓。 当年燕子又归来,从此永相守。谁给我们作证,有双双红豆。
这首词写于1929年2月13夜,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时年三十八。载《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收入《尝试后集》。江头燕子当为其遵母命所娶之妻江冬秀。明确标榜“好事近”调子。基本上依循《好事近》格式填制,字数、句法都不变,尤其上下两结,皆为上一下四句式,颇能突出词调特色。但在平仄安排上,个别字声有所违拗,上下两仄韵,一为四纸、八霁,一为二十五有、二十六宥,亦不同韵部。此小小突破,当为所谓解放词体之必然结果。
胡适的“尝试”,目的在于为新体诗创作解决形式问题。正如黑格尔所说,文学创作的成败在于,能否找到合适的形式。1924年,闻一多的实验,亦为着解决形式问题。新诗的不成功,关键就在于找不到合适的形式。胡适是位洋博士,外面有什么新奇的形式,诸如十四行之类,相信都会拿来,但他还是在老祖宗的库房里找。说明,自家的器物,还很好用。但他不明说,又放进《尝试集》,作为新诗放行,起了一定误导作用。就是让你猜不着。所以,将近一百年,他为新体白话诗所做的努力,尚未引起学界的注意。拙编《胡适词点评》于1998年12月于香港出版,行之未远,又于2006年7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胡适词点评》(增订本)。“点评”有“代序”,题称:“为新体诗创作寻求生路”。特别揭示胡适的这一良苦用心。
3.旧文学之不幸与新文学之可悲哀
胡适的创作,立足本土,就地取材。其所作”尝试”,究竟成功不成功呢?这一问题尚有待历史的检验,而只就外部情况看,他的破与立,无论新与旧,却好像都有点不讨好。他将词体拿来,分拆开了,为新体诗创作留下示范,新诗界朋友不领情;他对于旧体所采取的各种破坏的行为,旧诗界朋友也不满意。
有关胡适及其始终皆未能适的各种现象,确实有趣。多年前,我曾为文叙说自己的观感。其中一篇题称:旧文学之不幸与新文学之可悲哀。而副题则云:二十世纪对于胡适之错解及误导。载香港《镜报》一九九九年五月号。文章说:“旧文学被当作死文学,白白挨了一刀,新文学之作为活文学,活得也并不怎么精彩”。而老胡则始终不明白:胡适?胡适?为什么到头来还是一个,胡适之?
不过,他在破与立当中所体现反传统的精神,对于诗界革命,无疑也曾产生一种推进作用。值得探究,作一公允的评价。他的另外两首《沁园春》,一着眼于文章革命,一着眼于世界革命,堪称时代的新声。标举文章革命者,立题“誓诗”,前文已引述。其词曰:
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日落何悲。我闻之曰,从天而颂,孰与制天而用之。更安用,为苍天歌哭,作彼奴为。 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
这首词写于1916年4月12日,在纽约哥伦亚大学哲学研究部杜威门下攻读哲学。时年二十五。载上海《留美学生季报》春季第一号(1917年3月)。作者称,题目叫做“誓诗”,“其实是一篇文学革命宣言书”。其攻击目标为五百余年来,“半死之诗词”(《尝试集·自序》)。于题材方面,即反对“无病生呻”,反对伤春、悲秋,而主张乐观,主张进取;于体制方面,即尝试以白话入词,对原有之格局规制进行重构。故以为下半首(下片)为《去国集》之尾声,《尝试集》之先声(同上)。
另一首《沁园春》题称:“新俄万岁”。题下附小序:“俄京革命时,报记其事。有云:‘俄京之大学生杂众兵中巷战,其蓝帽鸟衣,易识别也。’吾读而喜之,因摭其语作《沁园春》词,仅成半阕,而意已矣,遂弃置之。谓且俟柏林革命时再作下半阕耳。后读报记俄政府大赦党犯,其自西伯利亚召归者,盖十万人云。夫放逐囚拘十万男女志士于西伯利亚,此俄之所以不振而‘沙’之所以终倒也。然爱自由谋革命者乃至十万人之多,囚拘流徙,挫辱惨杀而无悔,此革命之所以终成,而新俄之前途所以正未可量也。遂续成前词以颂之,不更待柏林之革命消息矣。”其词曰:
客子何思,冻雪层冰,北国名都。想乌衣蓝帽,轩昂年少,指挥杀贼,万众欢呼。去独夫“沙”,张自由帜,此意于今果不虚。论代价,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 冰天十万囚徒。一万里飞来大赦书。本为自由来,今同他去,与民贼战,毕竟谁输。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狂态君休笑老胡。从今后,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
这首词写于1917年4月17夜,在哥伦比亚大学。时年二十六。载北京《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1917年6月1日)。收入《尝试集》。以时事入词。有关事件之本末,小序已讲得十分清楚。上片记述俄京大学生革命事迹,下片借十万囚徒获赦,赞颂自由与革命。大题材、大感慨,颇能增强其体质;可为“文章革命”之范例。
这是一百年前的作品,如在今日,和一众革命诗词排列在一起,相信亦不遑多让。周策纵着《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五四运动史》),对于那个时期的人物及事件,有专门的研究。他曾有文章指出,毛泽东《沁园春·咏雪》受到胡适的影响。胡适词发表在前,如受其影响,亦无庸讳言。
以上是胡适在中国诗坛第一个六十年所作贡献。以下看毛泽东,其于中国诗坛所创立的样板及其领导地位。
(二)毛泽东诗词中的毛泽东
1.胸襟、抱负与气象
1925年晚秋,三十三岁。毛泽东作《沁园春·长沙》,一展胸襟与抱负,词云: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湘水楚天,钟灵毓秀。这首纪游词,是毛泽东登上诗坛的第一首歌词。旧地重游。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表现青少年时代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抱负。
1934年至1935年间,作《十六字令》三首,云: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自署创作时间是“1934―1935年”。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三首,四十八个字,推敲了一年。三首小令,歌咏对象是山,也是人。韵味郁浓。咀而嚼之,齿罅生香;百读不厌,名副其实。
1935年10月,四十三岁。走完长征最后一段行程,即将到达陕北。登上岷山峰顶,毛泽东写下《念奴娇·昆仑》云: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马克思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与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历史的结果就是;最复杂的真理,一切真理的精华,(人们)最终将会自己了解自己”。
《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毛泽东了解马克思与孔子的大同,谓“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歌词所表现的不仅仅是一种胸襟与抱负,而且是一种气象。乃气象,而非一般的气魄,或者气概。读此词者,应特别留意到这一点。
一九三六年二月,四十四岁。毛泽东作《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歌词作于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此词于10月7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曾轰动一时,并即引发中国词坛上的一场政治较量。
概言之,中国诗坛第一个六十年,胡适倡导“文章革命”(文学革命),为着新文学,他所作“尝试”,所有建立,都为着解决新体诗创作的形式问题。其对于旧体,较多的是破坏作用。但这六十年,新诗不成功,该怪谁呢?怪新诗自身,不听老胡的话。
2.民歌、古典与新诗
毛泽东主张内容与形式并重,民歌、古典、新诗并举,具建设性。颇具深远意义。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中国诗歌出路问题的讲话。曾说:“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方面都提倡学习,结果要产生一个新诗。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这段话,有个共同目标,新诗、旧诗,于今仍须记取。
二、易好与难工:暴露黑暗与歌颂光明
第一个六十年代表人物:胡适、毛泽东。第二个六十年,群龙无首。暂时找不到代表人物。第一个六十年,如再划分得细一些,可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分界线,再行划分为两个时间段。第一个时间段,民国阶段。三十余年,属于新诗、旧诗各自的创造期。相关问题,有待文学史家给予评说。这里着重说第二个时间段,共和阶段。二十余年,新诗、旧诗,皆进入破旧立新阶段。目标一致,而表现各不相同。这里只说旧诗。两个事证,可知大概。
(一)歌德派及其书写模式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是二十世纪中国诗坛第一个六十年的共和阶段。这一阶段,新诗、旧诗,相关书写,基本上都以歌德派的形式出现。新诗暂勿论,以下是旧诗的两个事证。
事证一:“毛主席诗词”及“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
1963年12月,《毛主席诗词》出版。1964年初,山东大学高亨教授《水调歌头》盛传一时。这首词颇具毛诗作风。据称,有人当面问过毛泽东,以求证实。毛听后哈哈大笑。说:词写得不错嘛,有气势,不知谁写的。查实为高亨所作,《人民日报》即花边框起,重新发表,为正视听。词云: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扫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 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
但是,陈明远就不够好彩(运气不好)。他的《沁园春·咏石》,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将其误当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传播,之后又说他冒充,坐了几年牢。其词曰:
璞玉一方,切琢无疵,磨砺发光。岂怡红公子,命根维系,梁山好汉,天道周行。烈火难熔,狂风不倒,迸出齐天大圣王。传千古,数几多宝库,龙窟云冈。 谁言铁石心肠。有热血沸腾涌满腔。任离合悲欢,无求德色,嬉笑怒骂,皆为文章。上补青天,下填沧海,焚身裂骨自刚强。了此愿,亦不枉平生,非梦一场。
这首词,咏物言志,雄健豪爽,颇有毛诗气派,难怪红卫兵误传。为着纪念这段历史,特将其载入《当代词综》(第四册第2012页),以为备忘。
相关篇章,之所以容易被混淆,甚至被误认,说明相互之间必定有许多共通之处,诸如题材内容、叙述方法以及语言风格等等,而且,这一些在某一历史阶段似乎也已形成一定套数。此类现象,文学史上也曾出现。例如辛弃疾与刘过,刘学稼轩,词多状语,作出来的词,与稼轩很相像,有位老前辈就曾怀疑,刘是辛的枪手。其实,那是不可能的。前阵子,网上流传,主席《沁园春·雪》,出自胡乔木手笔。胡的女儿已出来代为否认。无论如何,那是学不来的。因为身份不一样,胸襟也自不同,更不用说气象。
事证二:说人家是修正主义,自己不比人家修得更加厉害。
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胡乔木所作《水调歌头·国庆夜记事》有云:
今夕复何夕,四海共光辉。十里长安道上,火树映风旗。万朵心花怒放,一片歌潮直上,化作彩星驰。白日羞光景,明月掩重帷。 天外客,今不舞,欲何时。还我青春年少,达旦不须辞。乐土人间信有,举世饥寒携手,前路复奚疑。万里风云会,只用一戎衣。
这是胡乔木的得意之作。但其中有不少重复的字,如十里、万里、万朵,还有两个复字,我觉得并不纯熟。字面上缺少锻炼。编纂《当代词综》,不录此词,而录另外的篇章,计十篇。但他不同意。说:我的那几首《采桑子》说愁,其实是诡辩;另有几首反修,现在我们不比人家更修。为什么不选我的《水调歌头》?
胡乔木的事证说明,诗词创作紧跟政治形势,与时俱进,但有些时候,时势的发展、变化,既不可预料,又不由自主,不能不跟,也不能跟得太紧。
以上二例,应可见歌德派书写之一斑。作者圈子很小,作品亦不多见。仍然处于模仿的阶段。
(二)老干体及其书写模式
第一个六十年的共和阶段,诗词创作,尤其是诗词的发表,还是少数人的行为,多数人的创作基本上仍在地下进行。1976年,进入第二个六十年,旧体诗创作从地下转向地上。和第一个六十年相比,第二个六十年,最明显的特征是,政治上的两个凡是,赋予诗词创作重大的历史使命。诗词创作的意识形态化,令得诗词界亦出现两个凡是:凡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都会写诗词,凡是平反昭雪都要发表诗词。诗词界两个凡是的出现,一方面对于诗词创作及相关诗词活动有一定推进作用,另一方面也令得诗词创作有点泛滥成灾。
1.马背与台阁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解放军某部团长唐伯康提出“中华诗词”这一概念,并编纂《当代中华诗词选》。这是以中华诗词为标榜的第一部诗词总集。1989年8月,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其间,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学会由一批尚未退下岗位或者刚刚退下岗位的老革命、老干部带领,从无到有,迅速拉起队伍,创建阵地。此后,老干体一词,就在诗坛流行。老干体与歌德派一起被捆绑,都被纳入台阁派的书写范围之内。即使某些并不在台阁,或者曾在台阁已离开台阁的作者,同样被纳入台阁派的书写范围之内。其范围之广,队伍之庞大,可以想见。
2.挑战与应战
在这一背景下,昔日的歌德派以及今日的老干体,既迎来新的挑战,也面临着新的困境。1987年5月31日(端阳节),中华诗词学会在北京成立。第一任会长钱昌照,借出北兵马司胡同十七号作为学会会所。筚路蓝缕,终于为传统诗词创作开辟了一片天地。钱昌照谢世,周谷城接任会长。面对眼前局势,曾为感叹:“暴露黑暗易好,歌颂光明难工。”诗词创作除了勇于向固有观念说不,“莫再谦称传谬种,敢将敦厚育英才”(周谷城诗句),在实践过程中,树立正确的观念,仍须于诗词历史进程,总结、吸取经验与教训,包括对于概念、意象运用所出现的经验与教训。这就是所谓探本与溯源。
第二个六十年,已去掉一大半。中国古典诗歌由第一个六十年之死而复生,在第二个六十年,到达2036年之时,会不会让生而复死的预言实现?昔日的歌德派以及今日的老干体,必将产生一定的作用。有关歌德派以及老干体,为何还要在其前头加上个昔日和今日的修饰语呢?其实,就所描述的对象看,并无特别用意。只是表述上的一种小小的变化,亦非技巧,因为歌德派和老干体,实际上是同一个概念。于歌德派前头加上昔日二字,说明乃古已有之,并非今日之所独创;于老干体前头加上今日,表示乃今之新名目,同样并未否定其旧时已有。昔日与今日,在这里并无专门的指向。歌德派和老干体,其来龙去脉,得失利弊以及发展前景等问题,同样是目前所当面对的问题。
三、近源与远源:歌德派的今天与明天
正如上文所述,歌德派和老干体,尽管都是共和以来的新名目,但寻根究底,亦都有其来历。而作为新名目,其于共和期间的出现,大都带有贬义。例如,歌德派,已成为文艺界乃至文化界对于歌功颂德一班人的称呼;老干体,亦已成为诗词界对于一班退休或者还没退休的老干部所作诗词的称呼。做法皆甚未妥。故此,我说歌德派和老干体的近源与远源,将其置之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考察,既为着认识其作为诗六义中之一义的真面目,带有正本清源的意思,亦为着总结、吸取历来以诗六义进行创作的经验与教训。
对于共和期间所出现的歌德派和老干体,应当正面直对,无须回避。相关作者有勇气以歌德派自居,以老干体自命,乃自信心的表现,值得赞赏,值得支持。我遇到多位有此自信的诗人和词人,很受鼓舞。2002年,在澳门举办“大雅正声与时代精神”学术研讨会,就曾呼吁:“对于新的大雅正声,现代的雅与颂,包括言王政之大雅与小雅以及美盛德之各种颂歌,应当有个合适的评价。”呼吁:“将历史与现状联系在一起,对于雅与颂进行综合考察。既从现代的角度,对于传统的大雅正声进行科学的分析,评判其地位及影响,又从传统的角度,对于新世纪的大雅正声进行历史的关照,评判其现状及前景。用一句比较新潮的话讲,那就是传统的现代化和现代的传统化。”时间过去十二年,相关话题仍未过时。
(一)传统风、雅、颂的历史定位及创作经验
1.比重及定位
传统的风、雅、颂,在历史上早有定论。诗三百当中,十五国风一百六十篇,大雅、小雅一百零五篇,周颂、鲁颂、商颂四十篇。三种体裁或者式样,各有一定比重,各占居一定地位。有所偏重,而又无所偏废。几千年来,就是这么一种状况。
比重牵涉定位,说明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问题。也是在十几年前,一位朋友主持诗词丛书出版工作,曾征询意见,我告以“控制数量的方法保证质量”,亦希望重视相关数字。有感于此,与诸生言诗,也曾说及,现今诗多好少,或者说写诗的人比看诗的人多,诗界之第一要务,须将孔夫子的“四个可以”加上一个可以,成为“五个可以”。这就是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还得可以删。这应当是个大前提。有朋友一年一部诗集,除了备忘以外,可能还得承担一定风险。
以下说诗六义问题。这是传统风、雅、颂创作的整体经验。诗六义包括风、雅、颂与赋、比、兴,对于乐歌创作而言,包括写什么和怎么写两个方面的问题。风、雅、颂,说的是题材问题,包括内容范围及题材要素。用当时的话语讲,是大政事和小政事,以及风土、习俗;用现代的话语讲就是天文、地文、人文以及事理、情思、物景。一个属于题材范围,一个属于题材要素。或者说,一个是自然物象,一个是社会事相。赋、比、兴,说的是体裁问题,包括乐歌式样及表现手法。用当时的话语讲,是赋笔白描,还是比兴寄托;用现代的话语讲就是叙事,并于叙事过程说情、言志。
2.“生民”的典范
“生民”,这是诗大雅中生民之什的其中一篇。诗篇歌颂周民族第一祖先后稷。从其奇特的出生说起,再列述其文武之功,并以配天。谓其所有,来自于天。其全部事业,一地一天;即对地种谷,对天祭祀。乃一组大型宴会上的雅歌,叙事长诗。为周朝开国史诗。堪称大题材、大叙述的典范。
史诗的制作,以人配天。人与天,相距遥远,究竟如何追配?“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这是先贤所开示的方法。在时间与空间上,由近与远的推移与转换,达致通天的目标。
3.曹操与陶潜的经验
(1)曹操《龟虽寿》,从个别到一般的提升。曹操诗云: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神龟、腾蛇,各有所长,亦各有其局限;老骥、烈士,各有局限,亦仍然尽其所能,不愿意停止。这一切,属于个别事物,个别现象。盈与缩,寿与夭,福与祸既在于天,亦在于人。只要调养好身心,同样可得久长。这是一般的道理。
从个别到一般,从具象到抽象,达至咏志的效果。以具体物象咏志,而非以概念。于具体物象,体察物理,加深对于久长与短暂,包括天道与人事的认识。颇堪效法。
(2)陶潜形、影、神,由诸身到诸物的推移。
陶潜《形影神》三首,其序称:“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三首歌诗,包括《形赠影》《影答形》以及《神释》。分别歌咏形、影、神,乃以自身的存在及存在的形式以追配人、地、天,而后托体山阿,实在通天的目标。其近与远的贯通与联想,同样也值得效法。
(二)二十世纪风、雅、颂的扭曲及错位
二十世纪,时事多变,对于文学问题,把握不定。20世纪80年代以来,言路放宽,注重独立思考,但是容易走极端。原来只允许歌颂与赞美,为政治服务,现在不愿意当歌德派。作为传播文化、推进文明建设的高等学府及学术研究机构,在一般情况下,似乎也只是着眼于风。将风当作文学主流,喜欢讽刺,喜欢揭露与批评,不喜欢雅、颂,以为歌德派。这应是一种偏废。
就题材的处理看,当代歌德派以及一班老干部的诗词创作,叙事、言志,大多以天下为己任。言大政事,一人与天下;言小政事,诸侯与诸侯。以天地为背景,展现历史上的人物与事件。诸如毛泽东《沁园春·咏雪》就是这样大题材、大制作。以眼前的物景与物景下的人和事,直接以配天。
除了在题材上,于为时、为事的同时,也为自己,仍可在时空位置上,于大与小以及远与近等多个方位,进行调整,寻求深长、远大之旨,亦可望与天相配。
(三)二十一世纪风、雅、颂的创造及归位
两个源头,胡适、毛泽东以及诗三百的雅与颂,于近与远,均已为展示方法与途径。而只是就近的讲,步入新世纪,元亨利贞,万物资始,今日歌德派,现代的雅与颂,于吸取两个源头资源的过程,仍然需要做些什么呢?以下三事,似当留意。
其一,内容与形式,始创与守旧。
孔夫子提倡“述而不作”,朱夫子将其解释为始创与守旧。以之阐发诗词创作的相关问题,应可作如下表述:内容须始创,形式宜守旧。内容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形式相对稳定。中国古典诗歌既然是古典,就得遵守古典的游戏规则,认认真真玩一玩。形式不能变,不能够轻易突破。无需做出许多花样。比如新诗韵等等。
其二,对立统一,相辅相成。
从文学材料分配与组合的角度入手,上片布景、下片说情,一句话就能读懂全部宋词。正与反的组合,构成二元对立定律。柳永的程序化,将词的创作,推向数码时代。李清照正与反的组合,揭示易安体的秘密。辛弃疾正话反说、反话正说以至于无正无反、亦正亦反,无穷变化,令人应接不暇。阅读宋词,两个字,正与反,切须谨记。
其三,词才与词心,感觉与认识。
秦观的两句话,“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千百年来,博得多少小姑娘的芳心。而最令乃师吃紧(担心)的却是另外两句话,“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因后者所呈现的是一种状态,无法抵赖,而前者却不一定就是心底里的话。乃词才,而非词心。文学作品是作得让自己都有口难辩好呢?还是说了等于没说好?至于“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和“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二者相比较,一个重如泰山,一个仅仅是一种感觉。相信也有明显的区别。文学创作亦各有各的抉择。
总而言之,新世纪的风、雅、颂创造,仍须遵循老祖宗所制定的原则,诗学与诗教并重,审美与功利兼顾,各就各位,共同为复兴大雅,重振正声,做出各自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