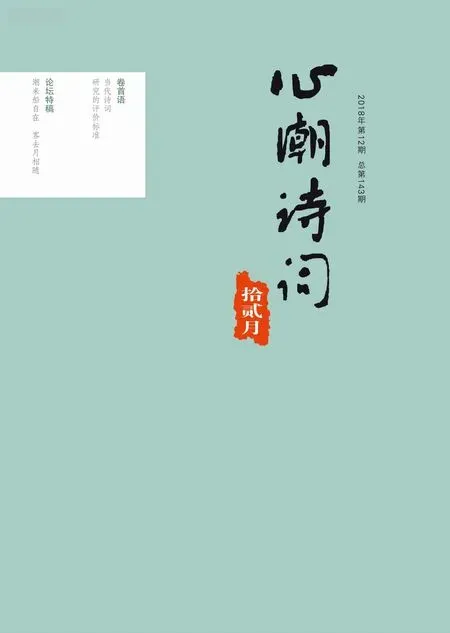当代旧体诗入史,全靠作品说话
前不久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第一期“开明论坛”研讨的话题是“当代旧体诗的入史问题”,我认为谈论这个话题,是具有前瞻性的。以前多次听到四川大学文学院前院长曹顺庆提到这个问题,即诗词是否应该进入现当代文学史,诗词界称之为“入史”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是要靠作品说话的。任何一个体裁,只要产生有生命力的作品,即会受到关注、产生影响,积淀下来,所以完全是靠作品说话的。而不是靠某一个人,不是靠一个学术权威来决定这个事情。因为我看到当代诗词产生了这样的作品,所以我个人认为当代诗词的“入史”,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时间问题。
在2015年8月召开的中华诗词学会换届会上,有一位“五四”以来有影响的新诗人屠岸,在会上发言,要言不烦。他说,当代文坛有一个奇特的现象,这个现象在世界文坛上,在世界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就是古代文体,半死半生。“半死”是指文言文,因为它基本上退出了文学创作的领域。“半生”是指诗词,呈现了一种复兴状态。作者和读者的热情都非常高。不仅仅在首都,有中华诗词学会这样一个全国性诗词组织,国内各个省份及地市州,以及港澳台甚至海外华人聚居地,都有诗词学会这样的组织。各地的诗社多如牛毛,很多人都在写旧体诗词。旧体诗词这一形式,并非只有毛主席才能驾驭,事实上很多人都会玩。一个古代的文体,在现当代这么活跃,不断地产生出好的作品,而我们现当代文学史没有反映这一现象,没有反映当代文坛的这一奇观,当然是“残缺的文学史”。
鲁迅先生在书信中讲过一句著名的话,他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这句话广为流传,其实是断章取义。因为后面还有一句话:“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就是说,以后如果不能在唐宋人的诗词外增添新的东西,就干脆不要写。你翻不出“如来掌心”,写出来的东西只是唐诗宋词的味道,那我们就不如直接读唐诗宋词。而我要说的是,现当代诗词之所以有未来有希望,就是在于有人翻出了唐人的掌心。我最初也曾相信“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这句话。但毛泽东诗词提供了一个例外,因为作品本身和传播力量的强大,几十年中几乎把其他声音都覆盖了。而且毛泽东诗词确实起到了承前启后、衔接传统的作用。特别是毛泽东的词,水平是相当高的。新中国建立以来,很多人对诗词的热爱,都是从读毛泽东诗词开始的。不过,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虽然那时也有别的人写作诗词,甚至水平相当高,但是缺少发表的平台,故不为世人所知。比如四川大学中文系已故的曾缄教授,他写六世达赖传奇的《布达拉宫词》,以易传之事,为绝妙之词,有声有色,可歌可泣,越过吴梅村《圆圆曲》,直攀白居易《长恨歌》的水平。他意译六世达赖情歌中的两句:“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如今已万口流传,不亚于任何唐诗名篇。即将问世的《中华诗词集成·四川卷》就是以曾缄《布达拉宫词》开头的。
很长一段时间内,像曾缄这样的诗人是默默无闻的。当代诗词压抑的生存状况,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由于思想解放,环境宽松,才得到了彻底改观。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诗人,其作品翻出了唐人掌心。影响比较大的一个是聂绀弩。我读到聂绀弩的《散宜生诗》,感到非常的兴奋。觉得他真正写出了这个时代的感觉,时代的精神,而又那么地衔接了传统。他的题材是古人想不到的题材。他写劳动改造,把挑水、搓绳、掏粪这样的题材,写入七言律诗,而又写得非常到位。比如说挑水,第一句像打油诗:“这头高便那头低”。但第二句就扳回来了,“片木能平桶面漪”,一个木片儿就把桶面晃荡的水捣平了,水就不会溢出来,这叫深得物理,而且有更深的象征意蕴。他的对仗也非常厉害,经常搞一些你想象不到的东西。“青眼高歌望吾子”,这是杜甫的一句诗,现成的拿来就是。对句是“红心大干管他妈”,这是当时流行的话语,看似不能入诗的话,和古香古色的“青眼高歌望吾子”,硬是对得天衣无缝。“望吾子”对“管他妈”,“妈”跟那个“子”,“吾”跟那个“他”。对仗拆分到了单字,你看了眼睛都瞪大了,这真正是翻出唐人掌心了。
我写旧体诗就受到聂绀弩的影响。只是他写七言律诗,我写七言歌行,脱胎换骨的一首诗是《洗脚歌》。起初我不知道洗脚是怎么回事,有学生请我去洗脚后,我才知道有洗脚房的存在,同时我也搞懂了,《史记》里面写刘邦接见来献策的郦食其,为什么一边洗脚,一边接见,弄得被接见的人十分生气,竟与刘邦对骂起来。以前没搞懂,洗脚几分钟可以搞定的事,为什么要洗那么久呢,竟惹得对方生气。去过洗脚房才知道,这叫做“足按摩”。原来刘邦那个时代,就有足按摩,这件事引起我浮想联翩,进入形象思维的状态。所以诗一打头就说:“昔时高祖在高阳,乱骂竖儒倨胡床。劳工近世闹翻身,天下久无洗脚房。……”
诗歌创作,无论新诗旧诗,都是这样的:第一,你一定是受到了一件事情的触动,有时候不只是一事端,可能是好多的事端使你受到触动,甚至你也说不准是哪件事触动了你,就成了“无端”(如李商隐诗)。但一般的情况,是一个事端触动了你。在诗里面,你不一定直接说这个事,你可能借端托喻,加以变形;第二,引起了浮想联翩,而浮想联翩就是形象思维的状态。
梁代文学家萧子显,在《南齐书》的文学传里面讲了八个字:“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就是说,文学如果没有创新,没有变化,就不能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作为,这实际上与前面提到鲁迅先生那段话,是同一个意思。而当代诗词之所以站得住脚,就在于它有了这种新变。举个例子,一位女诗人(叫甄秀容)参加“红豆杯”诗词大赛,那是一个爱情诗的大赛。她写出了两句诗,广为流传:“夕阳一点如红豆,已把相思写满天。”这两句诗,是不比唐代诗人差的。不是说王维写出了《红豆》,其他人就没办法写了。另一个年轻的北京诗人(叫高松)写了一首送别的七言绝句,第三句是“说好不为儿女态”,这就是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的意思,彼此说好了,分手的时候不要作儿女之态。殊不知其末句却是:“我回头见你回头”。这个也翻出了唐人掌心,写出了想不到的好。作为一个诗词的研究者,我看到这种诗,就感到很兴奋,就会情不自禁地到处宣传这样的诗。
当代诗词创作也有误区,例如一说传统诗词,有人以为就是近体诗词,一说就是格律。关注的就只是平仄粘对之事。但刚才提到的一些作者,更加重视诗词的意趣。林黛玉说,果然有了意趣,不修饰也是好的,当然,修饰一下就更好了。广元有一个年轻诗人(叫何革),写了一组《岁末杂感》,第一首是这样写的:“忽南忽北似飘蓬”,开头这一句是人都能写,但第二句就不是别人能写的了:“话不普通人普通”。这个话就很有意趣,很有味道,意思是作为四川打工仔,普通话说不好——“话不普通”,是个平凡的人——“人普通”,这语言既浅近,又耐人寻味。又如,现时流行起同学聚会,江油有个诗人(叫丁稚鸿)写同学会:“渭北江东总忆君”,这句话化用自杜甫赠李白的“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接下来是“时光已抹旧时痕”,这个大家都能写。关键是后两句,不是别人能写的了:“同窗相会无高下”,同窗相会怎么会没有高下呢,最后一句解释了:“都是呼名叫字人”。原来作者抓住了同学会的一个特点,就是任何人在老同学面前,都是不好摆谱、不好端架子的。
言归正传。旧体诗词在新文化运动中被边缘化,陈独秀有一个“三大主义”,胡适有一个“八不主义”,我认为他们是有道理的,并没有错的。我经常说一句话,旧体诗被边缘化,应该由写旧体诗的人自己负责,谁教你把旧体诗写作当真写成了“旧体”呢?谁教你没有新变呢?陈独秀称之为“铺张的”“陈腐的”,胡适称之为“模仿古人”“滥调套语”,这一类的批评没有错。今人提倡复兴诗词者,想掉过头清算陈独秀、胡适,那就成了反攻倒算,我非常不赞成,我反对这样一种理念,即认为旧体诗词就是要“为往圣继绝学”。比方说宋词的曲调都不知道了,教人填词还在那里辨四声分清浊,刻舟求剑。作为学术研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在创作中,这样的墨守成规有意义吗?田晓菲女士认为,新诗的出现改变了旧体诗的写作。其实也就是给了旧体诗以生机。
当代网络诗人曾少立提过一个口号,值得注意,那就是写当代诗词要注意吸收新的审美因子。不要一说到激动,就是“唾壶击缺”,你现在到什么地方去击唾壶,哪里还有唾壶,唾壶乃是古人的痰盂,击唾壶也不卫生。还有“扪虱而谈”,今人谁和你扪虱而谈。那些典故成语,让它保留在古人诗词里好了。今人都住进单元房了,你还在“独上高楼”,一读即令人生厌,感到太隔。有这样的创作理念,所以曾少立的词就做得很好,他写的《风入松》,我认为比吴文英写的还好。“红椒串子石头墙,溪水响村旁”,这个景色你可能也会写,但“有风吹过芭蕉树,风吹过那道山梁”,这个别人不一定能写了,这叫语语可歌。以下的“月色一贫如洗,春联好事成双”,对仗也好。“月色如洗”与“一贫如洗”迭加,“春联成双”与“好事成双”又是迭加。
在旧体诗入史这个问题上,有一个文学史观的问题,还有一个诗词观念的问题。而当代诗词研究,我相信一定会成为一个学术增长点。说实话,在唐诗宋词研究上,你要找学术增长点很难,除非是你有很深的功力,可以把别人挖的井挖得更深,或者掌握了新材料,你可能有所发明。但如果仅仅就文学研究文学,那就很难出新。而当代诗词研究还处在起步的阶段,填补空白就可以成为学术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