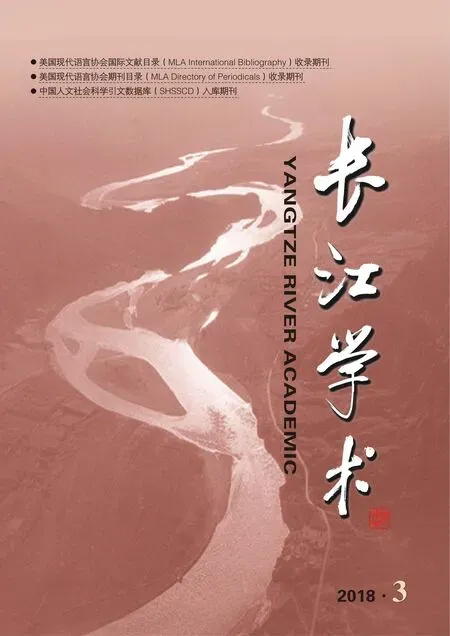歌剧《白毛女》与“讲故事的人”
王 鑫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白毛女”故事的起源,来自河北地区的乡间传说,而后以新闻报道、报告文学与小说的形式被记录下来。然而,真正让“白毛女”家喻户晓,收获世界赞誉的是1945年开始公演的歌剧《白毛女》。中国传统戏曲的现代改革,“从延安戏改、50年代旧戏改革及60年代初期的现代戏运动”,直至“样板戏”,此间,“白毛女”的故事一直以歌剧、地方剧种、芭蕾舞剧等形式被进行“再创作”。“白毛女”的故事,经过数十年的文本变迁与“再解读”历程,以故事的思想意涵、情感投射、社会价值,贯穿于中国现代战争历史的民族记忆之中。
本雅明在1936年对“讲故事的人”这一正在消逝的文艺群体,进行过深入分析。几乎和他写作《讲故事的人——尼古拉·列斯科夫作品随想录》处于同一时期的“白毛女”的传说,以及其借助“歌剧”形式所不断延续的“故事”生命,恰恰契合了所谓“前现代”社会中“讲故事”的特征与价值。由此,“讲故事的人”所汇聚的理论视野,成为探讨故事“白毛女”的歌剧创作与传播的理论基点,在创作形式、文本意涵与感知距离的层面上,为理解歌剧《白毛女》的经典化价值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入口。
《白毛女》艺术作品的发展轨迹,可谓贯穿了整个中国现代革命史,故事的讲述形式多样,情节内容也演变不衰,其艺术生命力甚至延伸至新世纪。需要说明的是,在《白毛女》漫长的文本变迁史中,为叙述方便,本文主要将讨论对象的时空背景设置在20世纪30年代末到50年代中期,即初始的“白毛女”民间传说,与影响深远、具有奠基意义的《白毛女》歌剧。选取这一阶段的“故事讲述史”,主要是基于形式与内容层面的考虑。思考形式的“秧歌剧”,或更准确地说“歌剧”,是否是“传说”得以扩大、故事得以流传的关键?因为其中涉及“秧歌剧”改革,所以,“鲁艺”为什么选择“歌剧”来表现“白毛女”?延安时期秧歌剧改革的成功案例不在少数,但影响最大、成就最高者为什么是《白毛女》?这在它的故事线索与思想主题方面是否可以寻得解答?
一、集体经验与创作形式
本雅明所提出的“讲故事的人”,是伴随着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的来临而逐渐消亡的文艺创作群体。在“技术复制时代”与媒介信息逐渐泛滥的社会,独一无二的创造价值被压抑,缓慢形成的集体经验遭遇贬值,所以,隐匿在人类文化传统中的故事及其讲述历史也行将逝去。以现在的历史观去回望本雅明的悲观论调,可以发现他对所谓“前现代”的追忆,以及对“现代”的怀疑。然而,同时处在前现代向现代过渡时期的中国,物质与技术水平发展相对落后的延安及解放区,恰恰是很大程度上符合“前现代”表征的社会。信息封闭、交通不便、识字率低、科技落后,这些都为口头文学的发展与流传提供了条件。“白毛女”的故事,正是以“人们口口相传的经验”作为“汲取养分的源泉”,在中国本土的民间艺术资源中上下求索,以集体讲述、群众鉴赏、共时参与的方式,创造出如此具有变异性与适应性的文艺作品。
本雅明认为,“一个讲故事的人总是扎根于人民的”,而一个杰出的故事往往表现出“一种集体经验”。同样,首先作为故事的“白毛女”,源于河北山区的民间传说,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多个版本,诸如鬼怪迷信的故事、地主淫逸腐化的故事,以及歧视、欺压妇女的“王滨说”,和与此类似的“任萍说”等等。“白毛女”的传说,首先因民间口头文学的特性而具有传染性、变异性、开放性的群众基础与传播动力,在此基础上的文本演变,更是根植民间伦常传统中的巫术、神鬼等神秘崇拜,或如本雅明所说的“膜拜”。“白毛女”的传说也因其礼俗色彩而映现出浪漫意味,内蕴着文学改编的艺术潜力。因此,基于这一民间传说,《晋察冀日报》的记者李满天,在歌剧《白毛女》出现之前,就曾发表报告文学《白毛仙姑》与小说《白毛女人》。然而,在抗战时期河北乡村的特定时空背景下,小说文本并未充分发挥出舞台戏剧的口头传播特性,更无法凝聚群众的集体经验。1944年随“中外记者团”前来延安的记者赵超构曾写道:“据我个人在延安各书店的观察,文艺书籍中,印得最多,或者说销得最好的,是秧歌及其他通俗读物……”
1944年“白毛女”的故事随在外演出归来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流传到延安,而后又在周扬的主持与动员下,成立了歌剧《白毛女》创作组。“西战团”成员邵子南首先创作出诗剧《白毛女》,但由于诗剧的强烈诵读性质,挤压了舞台表演的发挥空间,故而组织贺敬之等人重新构思剧本。其中,周扬“发现”或揭示的“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重要主题,为歌剧《白毛女》注入了思想动力。参与歌剧《白毛女》的创作队伍,是在戏剧系主任张庚的具体领导下,由贺敬之、丁毅主笔,王彬(后改名王滨)组织创作与讨论,丁毅刻写油印,马可、张鲁、瞿维、李焕之、向隅、陈紫等人作曲,张庚、王彬审定,王彬、王大化、舒强导演,许珂舞台装置,王昆、林白、张守维、凌子风、吴坚、邸力、赵起扬、陈强、王家乙、李波、韩冰等主要演员,以及“鲁艺”全体文艺工作者与观剧群众共同组成。
这个人数众多的创作组,仅仅是歌剧《白毛女》的预演阵容。且不谈往后的修改、增删、改编过程与人员更迭,仅作为“献礼”于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公演前,在“鲁艺”的多场预演,就开始广泛采纳观众意见,逐渐扎根群众、贴近现实。在党校礼堂公演后的第二天,《白毛女》创作组收到中央书记处的修改意见,几天后再次来人转达了周恩来的相关指示,为原本的故事主题注入了清晰的时代背景与政治预言。公开演出后,创作组收到的信件与《解放日报》转来的批评文章,计40余件,共约15万字,主要就内容问题提出改进意见。1945年10月,歌剧《白毛女》走出延安,在张家口等地表演,并参考了当地文艺工作者和观众的意见,再次进行多番重大修改,强化了渐趋明朗的社会转变,凸显出人物情绪与经历的革命色彩。正如贺敬之的回忆,当年他“坐在观众中看戏,散戏后夹在观众群中听他们谈话,最无拘无束,最真实宝贵的意见常常在这里听到”,有时,他们也会“直接访问观众,包括干部、群众”,由此观之,“群众是主角,是鉴赏家,是批评家,有时是直接的创造者”。
和其他文艺传播方式不同的是,当舞台戏剧剧本创作完成后,它接下来面向观众的时刻,仍是整个戏剧创作中颇为重要的一环,也由此开启了故事的流传。看戏,是一个观众共时性参与的集体活动。在集体中,观众的情绪容易被导向极端,出现崩溃、狂欢等种种外化可能。面对本就拥有群众基础的传说改编的歌剧《白毛女》,观众的“共情”感与代入感被激发,凝神观看的同时,往往呈现出一种“松弛”的状态。曾奔赴解放区采访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1948年妇女节前夕途径彭城时,曾观看歌剧《白毛女》。据他回忆,当时至少有两千人在初春的寒夜里,围着临时搭建的戏台等待演出。由于演员情感真挚,音乐舞蹈的配合纯熟,当晚几乎所有的观众都潸然泪下,其中有位老大娘,甚至放声哭泣直至终场。即便是人生经历与中国民族历史没有共鸣的域外记者,也坦率承认,当时“他感动得几乎要哭了”,但却已经分不清自己是被剧情感动,还是在观剧气氛的渲染下受到的情绪影响。
本雅明认为,被讲述的故事越是能表达出群众的声音、揉进集体的经验,故事就越加具备传播效力,而这就必然需要一种“松弛”的观剧状态。听觉与视觉的松弛状态,会导致两个反向的极致。其一,如同“讲故事的祥林嫂”所引发的听众的麻木与厌倦状态;其二,是与变化、活跃的经验相融合的“忘我”境界。歌剧《白毛女》的艺术形式与处理技巧,使观众得以在松弛的观剧状态中,形成“信任”的心理前提,进而抵达“忘我”的审美境界。松弛的观剧环境导向凝神与“忘我”的同时,也会诱发憎恨等极端情绪的发泄。曾饰演黄母的李波就常常在路上被小孩儿们追着指骂,甚至被扔石子。黄世仁的扮演者陈强就曾在演出时,被气得发抖的老大娘扇过耳光,被乡亲们扔来的水果砸成“乌眼青”,甚至被新兵上膛的枪口瞄准过。
歌剧《白毛女》所讲述的“故事”和凝聚的经验,不仅是一个“母题”式的传说,更是集体智慧与艺术创造的结合体。在音乐方面,它为了贴近故事原型的时空背景,在河北民歌《小白菜》、山西民歌《捡麦根》、河北花鼓、河北梆子等民间艺术资源中寻求灵感,更在剧本细节与人物表现上反复揣摩。作曲家马可为营造出人物的反差感,讽刺性地将“满口仁义道德、吃斋念佛”的黄母的唱腔,配以象征其精神虚壳的“佛曲”。《白毛女》的艺术处理,将曲调创作、唱腔设计以及演员的声音表演,融合为立体生动的听觉记忆。同时,延安戏改后的演员扮相,不同于以往旧秧歌的丑角化,而是在真实再现的基础上适当美化,结合道具、化妆、服装、舞台美术等方面的日趋精良,丰富了视觉审美的呈现,也内化为观众的色彩记忆。共时性集体行为的观剧活动本身,也将其中或屏息凝神、或捶胸恸哭的环境气氛与欣赏状态,化归为集体的情绪记忆和身体记忆。口头文学的传播方式,对“记忆”有很高的要求,通过“记忆”,方使故事在历史中不断流传。由此,上述所有的感官记忆,再次经由架高的戏台、无法复制的真人表演、化妆扮相的陌生感与距离感,映现出其他艺术形式所不具备的仪式性,使《白毛女》故事的讲述更为具象、充满实感,将民间集体经验的智慧与力量发挥到了极致,也就此使集体经验整合进入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记忆之中。
二、“实用关怀”与文本意涵
就“鲁艺”文艺工作者所改造的“秧歌剧”而言,“旧秧歌”是脱胎于中国乡村民俗传统中的一种集体性自发参与的娱乐活动。旧秧歌多以“闹剧”的形式,抒发农民的生活态度与情感表达,其中不仅有“插科打诨”的笑料,甚至存在“飞眼吊膀的低级”趣味。当然,这种“藏污纳垢”式的外化表现,用现代意识可以被理解为,这是他们对底层社会处境与被压迫地位的消极反抗姿态,也是对农民生活状态的自嘲、情感压抑的宣泄。但是,在战时客观环境中的文艺创作,必然会选择借助这种受众基数庞大的艺术形式,来承载更加符合社会现实需要的思想主题与时代教益。在这样的前提下,“鲁艺”开始对“旧秧歌”进行改造也成为必然。
“骚情秧歌”所指涉的旧秧歌,与改造后的“新秧歌”在两个层面上存在明显差异。其一,涉及秧歌的社会功能。这里的“骚情”概念,取自它特定的方言含义,即示弱讨好、献殷勤、“拍马屁”,反映了过去农民对地主的软弱奉迎态度,及其无奈苟活的生活状态。但是,这种传统农民的思想意识,在张扬社会与政治诉求的前提下,毕竟是消极无力的,亟待被意识形态规训,进而被改造为与此相对的“斗争秧歌”。由此,新秧歌便开始强调农村新人、社会新事物、革命新希望的积极态度与反抗意识。其二,指旧秧歌中具有调情色彩的隐秘想象与情感宣泄。这种倾向在新秧歌中被大量简化与净化,以此形成了“严肃秧歌”的成功转型,但它仍在一定程度上对民间礼俗秩序中的文化情愫有所保留,对乡间伦理道德持尊重态度,并在人物的情感表现上时有出现某种缝隙般的设计。
由此观之,新秧歌主要是在美学形式、情感限度、时代背景与社会功能的角度,对传统旧秧歌进行改造。但是,为了不损失秧歌活动原本的观众群体,新秧歌的改造力度并不激进,加之战时社会氛围的影响,部分农村群众开始萌生参与社会现实的愿望。由此,新秧歌非但没有损伤传统秧歌的情感线索,还顺势合宜地运用故事情节来传达思想主题,进而提炼、抽象出时代感与社会价值。歌剧《白毛女》正是在“有情”与“有用”的层面上,成为延安戏剧创作实践中最为成功的作品。
歌剧《白毛女》的情感意涵丰富,爱恨情绪激烈,“有情”几乎贯穿全剧,诸如浓烈的亲情、革命的激情、乡邻间的同情、隐性的爱情、坚定的爱国情、乡村秩序中的怀旧情愫,以及对恶霸地主彻骨的仇恨等等。故事的情感性正是乡村农民真实经历的映现,将民族的沉疴与痛楚寓于其中。基于真实体验与集体经验的歌剧《白毛女》无疑调动了观众的情感释放,他们号哭、诉苦、咒骂、动武……然而,正如前文所说,《白毛女》的故事感染力,打破了“亲历者”共鸣的限制,致使域外记者贝尔登也深受感动,这恰恰证明了“有情”的渗透力是如何击溃“民族国家”的界限,得以抵达普遍适用的人性情感深处。
新中国成立初期,歌剧《白毛女》在世界多地演出,收获许多国际奖项,也吸引了国外剧团改编演出,来自国际社会的肯定与接受,主要原因之一在于“白毛女”故事情感的感染力。黄世仁的扮演者陈强,和黄母扮演者李波都有回忆文章谈到,他们在国外表演《白毛女》,从来没有观众给他们二人献花,在维也纳的一次演出,终场时甚至有观众强烈要求“不要给他献花!”情感的张力不仅仅依托共同的战争记忆、创伤历史,更是因为其故事主题的多面性。在全世界的文本书写中“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群体普遍存在于作家笔下,反抗压迫也是经久不衰的主题,他们甚至也可以将《白毛女》中的阶级压迫理解为伦理道德的缺失等等。
讲述一个杰出的“故事”,需要充溢着真挚的、人性普遍的情感力量,以“有情”支撑立意,但这仅仅完成了故事的一半。本雅明认为,“实用关怀是天才的讲故事的人所持有的倾向”,故事的“有用”性往往寓于伦理观念、实用建议以及谚语或警句之上。在这个意义上说,“有用”则支撑起杰出“故事”的另一半。“有用”的故事,要求与社会生活相关联,“有用”的经验,更需要满足群众的集体心理需要,且易于总结、记忆、复述、传颂。正如《白毛女》剧本的多次改动,不仅要符合群众的集体经验,更要对农民的固有思想意识有教育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改动就是预示时代发展方向的,“黄世仁应当枪毙”的中央指示。后来田方明确转达了周恩来的建议:“目前日本帝国主义很快就要被打败,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会降为次要矛盾,而国内的阶级斗争必然要上升为主要矛盾。因此,在解放区如何教育发动千百万农民为自身解放而斗争,就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然而,这种预言性或者时代性极强的思想指导,以及周扬式宏旨的贯彻,都需要在故事发展的细微处层层渗透,细致处理人物革命性转变的思想基础。比如,大春的每次出场几乎都是一个表现其革命性思想的机会,递进式的革命透视,最终必然会指向加入八路军的革命选择。再如枪毙黄世仁的决定,一方面以群众的呼声来明确表达,一方面也在区长的耐心劝导、顺应民意、依法行事中,显示出革命权威的合法性。由此,社会题旨借用歌剧形式的口头艺术特质,珍藏于群体的集体记忆与集体经验之中。同时,在歌剧表演开放与流动的漫长创作历程中,其思想主题也在不断发生变异、吸纳、适应,进而积淀为承载着丰富意蕴的故事。赵超构曾写道,解放区秧歌队下乡宣传卫生的一次表演,被那里的乡亲评价为,“你们的秧歌比从前的好”,因为句句“有用”,“旧秧歌中看不中用”。当然,仅以“实用”的社会教育功能,来界定秧歌剧的高下必然不符合所谓“文艺”的标准。真正具有艺术生命力的作品,一定是在漫长的时间距离审视下,仍然绽放熠熠光泽,在变幻的历史中,依然汇聚深远意蕴的文艺产物。由此,当我们仅就歌剧《白毛女》的基本故事单元来看,便会明显发现其丰富的文本意涵,是建基于故事的多重线索,并在实现了“有情”与“有用”相结合的前提下,情节环环相扣、线索复杂明晰的智慧创造。
以自然伦常的角度来看,由于杨白劳的饮恨而死与“小白毛”的降生,这个关乎生死的故事无疑被笼罩在神圣与严肃的气氛之下。在神秘文化的层面上,逃往深山的喜儿与接下来的鬼神、祭祀、诅咒、凶吉等情节要素,满足了观众对于未知的幻想与“膜拜”情结。从人性情感的抒发来看,亲情、爱国情、悲悯情怀都被投射其中,相对较弱的爱情作为隐线,尚未充分释放。另外还有对欲望的书写,如黄世仁的施暴;以及对脆弱情感稍稍露头但被“及时”遏制的想象,如喜儿对自己被娶进黄家一闪即过的念头。从道德角度观之,故事场景的精心设置突出了压迫群体对民间伦理“神坛”的亵渎,如新年抢人、书房施暴、孕期谋害计划等。从革命反抗的社会教益来看,表现在第一幕中“偶然”提及的红军、大春等青年的反抗姿态、村中众人对“改朝换代”的预感、对黄世仁的审判,以及喜儿得救后众人高声唱出的那句“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逼成鬼的喜儿,今天要变成人”。
三、艺术“光晕”与感知距离
歌剧《白毛女》的创作模式开启了一种被称作“流水作业”的先河。在总负责人张庚的领导下,剧本创作组成员通力协作。贺敬之每写完一场戏,作曲组便立刻开始谱曲。审定完成后,丁毅投入接下来的刻写印制。接着,导演执导演员试排,每一幕完成后再总排,并邀请群众观剧、批评,意见再反馈到贺敬之那里予以修改。这整个链条俨然是一项“手工艺术”的创制过程。不断修改、增益、衍生、流传的“白毛女”故事,如同张庚所言“捏面人”的生动比喻,呈现出一件手工艺术的诞生。如同一件艺术品,由“透明的薄漆在一个缓慢的过程中层层相叠”;最杰出的故事便是“最准确地描绘出由不同的人的复述层层相叠的那种完美的叙述”。也正因为集体参与艺术作品的生成,造就了故事讲述的复合性、多质性与可阐释性。
本雅明认为:“人的感知的构成方式——即它活动的媒介——不仅取决于自然条件,而且取决于历史条件。”对艺术作品的感知,是与历史环境息息相关的,以故事“白毛女”的传播和接受历史,可以看出,创作者与鉴赏者的思想意识内在于社会政治之中。歌剧《白毛女》经历着持续的创作与吸纳过程,在当传统的口头文学遭遇现代化的冲击时,讲述传统的故事不再满足群体思想意识的需要,那么它便会建基于“另一种实践——政治”。张庚曾就《兄妹开荒》的例子,说明了主题性与历史感在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兄妹开荒》这部秧歌剧固然清新单纯、热情活泼,但是,剧中人物的情感遭遇是“平淡的”,革命斗争力量是“微小的”,思想转折程度是有局限的。如果把它放在一个更为艰难的社会环境中,它的思想与感情力度定会更加深刻,所以,社会的困境更能将人物“最隐秘的本质显现出来”,也会让文本在历史长河中呈现出不衰的生命力,而在这一点上看,《白毛女》无疑是成功的。
“白毛女”故事的源头,首先来自纯粹的神鬼传说,包含朴素的道德劝诫色彩。这个脱胎于民间礼俗的传说,在八路军于晋察冀建立根据地之后,发生了改写,原始版本中鬼魅般的“白毛仙姑”成为革命的象征,是积聚了农民集体苦难的对象,借以表达最具深刻意义的斗争与反抗思想,达到发动群众投入自我解放的社会功能。1949年后流传海外的“白毛女”开始关注并凸显爱情的主题,将情感的释放作为吸引观众、感染观众的主要内容。50年代末期的“白毛女”则在其每次改写中层层深化劳动人民的坚强意志,人性的柔软与情感被革命口号所淹没……感知的方式与距离,时刻影响着观众的思想。其中,“历史条件”的坐标,更是现代社会中的观众难以摆脱的“无意识”,而这种“无意识”也同样倒映着70年后读解《白毛女》的我们。
对白毛女故事的感知,和其生成历史一样,在不同的时代与环境中被纷繁呈现。故事讲述中所承载的主题越是清晰、明朗、宏大,它就越容易早早被时代抛弃,而最为有效的解决方式至少依靠两种力量的组成。在审美艺术创造过程中,讲故事的人自律、灵活地对文艺资源进行借用,直至创造出自足的艺术样式,并积淀出通行的、普遍适用的道德教益。我们可以假设,即便没有周扬式宏旨的思想高度,“白毛女”的故事仍旧能够被讲述与流传,其承载的道德劝诫价值可以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中延续。但是,走向现代化的社会不会是稳定的,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开放,要求故事的讲述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它的变通性,可以依托经验打造某种寓言式的想象空间,如中央书记处的指示对《白毛女》的介入。另外,在社会生活与意识形态氛围中,每一个首先作为社会人的艺术家,开始体会现实的需要,在集体无意识中领悟与规范思想的表达。诸如当时周扬的高超政治理解力,可以说是令《白毛女》主题宏大、影响深远的主要原因。往后歌剧《白毛女》的数易其稿,也是其迫切适应群众需要、传达时代声音的表征。
群众的感官记忆与文化记忆,就《白毛女》的传播结果来讲,其时代主题的表达只会更为深入他们的思想肌理,内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但实际上群众对它的喜爱程度,非但没有减退,反而跨越时代与地域的限制,生发出更为深远的效应。在这里,对故事“白毛女”的不同感知方式,正是集体经验凝聚与意识形态渗透的统一,并在时代与社会发展中得以持续适应、变异、改写的结果。故事的讲述需要我们处在一定的距离之外进行观照,“隔着一定距离望去,你会看到,那讲故事的人所持有的非凡而质朴的轮廓在他身上凸显出来”,“显现出来”。或许正因为这样,才能触及故事的整体,甚至在其中感悟到时代的映现。
与小说文本和新闻文本不同,集体参与的《白毛女》戏剧创作,一直是一个开放的文本。它的开放性不仅依托于读者的阐释,更体现在集体“再创作”历程中,不断满足自然、伦理、历史、社会、政治、人性等多方面的感知角度。小说需要借由读者对文本的“再解读”来延续它的生命,因为它一经作家创作完成,便开始面对读者,以读者对小说的阐述行为参与社会,此间的交流与审美是孤独的过程,而非集体经验的凝结与流传。新闻文本则诞生于信息时代,它如同“琥珀”一般记录了真实的瞬间,但也“屈服于那一刻”,所以,“新闻报道的价值无法超越新闻之所以为新闻的那一刻”。而杰出故事的讲述,则是在传统的艺术审美形式中,结合“有用”的教益,维持集体的经验与记忆。“故事”的教育意义是“耗不尽的”,“即便在漫长的时间之后还能释放出来”。歌剧的艺术形式与丰富的文本意涵,在“白毛女”的故事之上完成了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作为传统艺术的《白毛女》是其得以富于“光晕”的底色,它通过自然神圣的艺术形式而具有“膜拜价值”;而在强化社会政治功能之后,处于特定历史坐标的观众,在意识形态的信仰中,同样会生发出另一种意义上的“膜拜价值”。正是这种复合的“膜拜价值”,赋予了歌剧《白毛女》以本雅明意义上的所谓“光晕”或“氛围”(Aura)。
《白毛女》的创作与流传历程,以及其经典化价值,为中国革命文艺提供了崭新的资源,并在其文本生产的内部形成了一个自足的链条。它由口口相传的传说开始进入群众的听觉系统,并在复述与流传中集聚集体经验,以戏剧表演的方式启用群众的所有感官系统,在松弛的状态中走向狂欢,并化作身体记忆与文化记忆,进而在与现实社会需要的结合中,反复感知、适应时代、汲取教益,最终再次化为人人口中相传相诵的传说。被意识形态借用的歌剧形式,为参与历史书写与民族认同的“白毛女”,寻得了最为契合的表达,得以实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