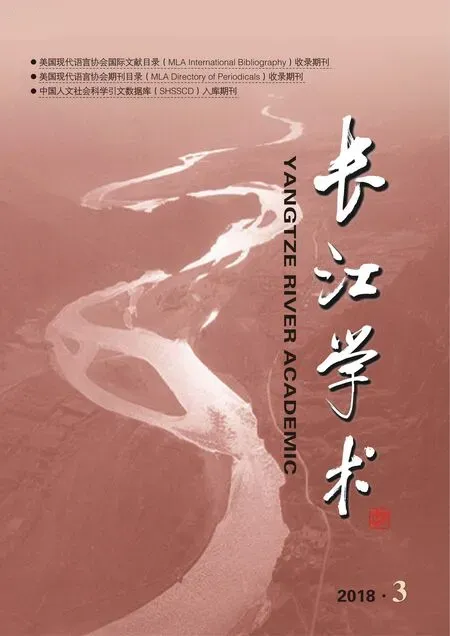《三里湾》中的“孝文化”
惠雁冰 左雨浓
(延安大学 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在当代文学史中,赵树理的《三里湾》是第一部表现农业合作化题材的长篇小说。对于这部小说的解读,以1980年代为界,大致呈现出两种风貌。前期研究多集中在小说“相当广阔地表现了今天农村的复杂斗争”“显示了农村新生活的风光”以及“引人入胜的魔力”等方面,主要以俞林、周扬、傅雷为代表。后期研究集中在“以村庄为主体的文学叙事范式”“显性文本与隐性文本的分离”“情感化特征为主的乡村治理结构”等方面,主要以贺桂梅、赵卫东、许梦陶为代表。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学界在两个时期对《三里湾》的评价侧重。上述研究对整体认知《三里湾》政治主题、叙事范型及文本的内在矛盾有重要推动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三里湾》与以“孝文化”为主体的乡土文化传统的深刻关联。而这一点,恰恰是赵树理小说“民族化”风格的显在表征,也是《三里湾》这个文本具有经典性、重读性的重要因素。
一、以家庭为原点的“孝”文化
在中国文化的形态谱系中,传统伦理文化不仅是本民族文化的结构性组成部分,同样也是本民族文化的核心元素。中国自古以来就以人伦规范为重,并以人伦为圆心辐射性地建构了个体与家庭、社会、国家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一种与“同心圆波纹的性质”相类似的文化现象。而这一文化现象的精神根基就是以家庭为原点的“孝文化”。
据史料记载,我国的孝文化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父系氏族时代,当血缘关系趋于稳定,且社会物质生产资料有所剩余时,人们由对神或图腾的祭祀崇拜转为对祖先亡灵的孝祀崇拜。自此,“孝”的观念开始在中国文化中逐步显现。《尚书·虞书·尧典》中记载,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舜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出现最早、最典型的孝子形象,虽然他的父亲、后母及弟弟都想置他于死地,但是他仍不失子道,长年如一日地孝顺父母,友爱弟弟,其孝行为后人所称赞。相传奴隶社会时代,舜在执政期间提出“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足见“孝”的内涵已有了较为明确的所指,并开始由一种笼统的观念性的范畴转向一种谐和家庭关系的个体的自觉意识。再从出土的甲骨文会意字“孝”来看,从老省,从子,释意为年幼者搀扶年长者,足显“孝”的本意及历史渊源。
封建时代,“孝文化”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充分的丰富与发展,它作为人伦道德之首一直规范着人们的语言行为,熔铸在人们的精神心理之中。春秋战国时期,管仲所著的《管子·形势解》提到:“孝者,子妇之高行也……父母慈而不解,则子妇顺……子妇孝而不解,则美名附。”《管子·五辅》也提到:“为人子者,孝悌以肃。”管仲认为孝敬父母是为人子女的崇高行为,子女尽孝也会获得良好的声誉。《论语·学而》有云:“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里仁》有云:“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看来,孔子也认为人只有先做到孝才能再去完成其他事情,且劝谏父母要柔和,尽量顺遂父母的意志。《吕氏春秋·孝行览》言:“务本莫贵于孝……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这里,“孝”又被提升到万事之根本的地位,正所谓百善孝为先,一个人如果具有孝德,那么天下都会跟随他。此外,《尔雅·释训》也有“善父母为孝”之谓。这些留存在各个古籍中的“孝”话语不胜枚举。秦汉之际,“孝文化”以《孝经》的形式独立成书,成为全民必须研习、践行的至上理论。汉代“以孝治天下”,《后汉书·荀爽传》载道:“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唐时,唐玄宗亲自为《孝经》作序,上至国家帝王,下至平民百姓都将行孝当作开蒙之要务,是万事之纲纪。南宋时,清朝康熙年间秀才李毓秀所作的《弟子规》道:“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元时,郭守正撰写《二十四孝》,细述了各个朝代孝子孝女的故事。
同时,“孝文化”的盛行,不但在中国节日体系中催生了行孝的节日,如七月半盂兰盆会、九月九重阳节等,而且成就了名门大家的家训家规,如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明太子太保刑部尚书林俊的《林氏家训》、宋代朱熹的《朱子家训》等等。
由此可见,“孝文化”渗透在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烙印在民族的精神基因上。对此,钱穆先生在其著作《文化与教育》中说道:“中国文化就是孝的文化。”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也指出:“一,中国文化自家族生活衍来”;“二,伦理处处是一种尚情无我的精神,而此精神却自然必以孝弟为核心而辐射以出”;“三,中国社会秩序靠礼俗”。在论及中国“孝”问题时,黑格尔也写道:“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的确,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本质就是“孝文化”。伦理道德与社会组织形态同时产生,作为德之首的“孝道”因此与家庭、政治、宗教、法律息息相关。不论是在宗法制的旧时代中,还是在当下的民主现代社会里,“孝”道这一基本人伦不可偏废。以父母为例,以反哺之心爱护他们,以敬畏之心尊重他们,以赤诚之心忠于他们,以理解之心顺从他们,这本是“孝”文化的题中之义。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我们要墨守成规,甚至没有原则。对于传统孝文化的精华部分我们理应承传弘扬,而对于其中那些阉割人性、禁锢思想的不合理部分,我们也理应剔除反诘。
二、《三里湾》中青年男女的“孝”选择
《三里湾》反映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山西晋东南地区的合作化运动,可谓一部典型的问题小说。作品紧紧围绕三里湾的扩社、开渠两个重要事件及村中几对年轻人的婚恋生活问题展开描述。而婚恋内容则是小说情节结构的主线,也是文本思想主题得以生活化呈现的重要载体,所有影响到“开渠”“扩社”等生产关系调整的矛盾与斗争,无不通过婚恋的归属问题得以搅动与平复。有意味的是,这些处在婚恋中的青年男女,其行为与心理又莫不与孝文化有着微妙的关联。下面,我们就小说中的几个青年形象做具体阐述。
首先,我们来观照范灵芝这个形象。灵芝出生在干部家庭,她的父亲是位老党员、老干部,是三里湾的村长,同时也是一位半脱离集体生产的个体农民。母亲则是一位温婉良善的农家女。她自身也是初中毕业、工作上进的青年团员,任三里湾的扫盲教员,又在村上的农业合作社里担任会计一职,在作品中扮演着进步的农村新女性角色。她积极参加党团工作任务,在帮助玉生完成农具模型测绘过程中起到了理论指导的作用。在面对爱情的选择上,她勇敢示爱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社里奉献的玉生。在意识到自己以“有没有文化”来评判一个人的价值这种错误思想后,她能及时进行自我反省。凡此种种,都塑造出一名聪慧能干、沉着冷静、热情自信、谦逊自知的知识女性形象。
不过,细读文本,我们就会发现灵芝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孝文化”的元素。在她和马有翼两人讨论如何说服范登高和马多寿入社的问题上,灵芝和有翼决定各人给各人的爹“治病”。在她看来,她家入社是势在必行的。当有翼提出争取自己父亲入社相当困难时,灵芝给出的建议是:“不论他理不理,你们长期和他说,或者能争取到叫他不得不理的地步;要是说到最后实在不能生效,为了不被他拖住自己,也只好和他分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灵芝对待入社问题的态度颇为强硬,方式也比较粗糙。在他俩争论彼此为争取自己家庭入社所做的努力时,她更是伶牙俐齿予以反击,直到有翼无话可说。在得知有翼为菊英的吃饭风波作证而犹豫不决时,她准备去找有翼谈话,赵树理对她做了这样的描写:“灵芝的脸上仍然冷冰冰竖着两道眉,平时的温柔气象一点也没有了。”
然而,有意味的是,灵芝对待落后思想和行为都会毫无保留地给予谴责,但在劝谏父亲入社、摆脱资本主义思想这件事上她表现出的则是截然不同的态度。灵芝有意向父母隐藏她争取全家入社的意图,更多的是寄希望于党组织来帮助父亲入社。她旁敲侧击地询问父亲有关支部会议的开会内容,借此来给父亲灌输入社的思想。她小心翼翼地从不正面与父亲发生冲突,更不像指责马有翼的落后行为那样指责父亲不入社的“走资”行为。在父亲终于要入社但又纠结家中两匹骡子是卖掉还是一同入社这件事上,灵芝更是耐心柔和地给父亲解释骡子一同入社的益处,并分别站在社里和父亲的角度有理有据地劝说父亲,巧妙化解了父亲的怒气。她从来也没有逼迫父亲改变自己意愿的想法,一直都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这不正是“孝子之谏,达善而不敢争辩”吗?灵芝这种谏而不逆的行为正是她谅解父亲的体现,也是她对“孝文化”的一种理解与选择。又如,当金生提出想把灵芝从他们互助组换到村上社里做会计时,灵芝答道:“这么好一个学习机会,我自然愿意!你能跟我爹说一说么?”灵芝在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后,希望同样征得父亲的同意,这也是尊重父亲的一种体现。但从另一方面而言,虽然灵芝孝顺父母,却并非事事顺从,她的孝还呈现出有选择的一面。作为一个接受了新文化的进步女性,她合理分析思考了玉生家庭的进步力量,于是自作主张决定了自己和玉生的婚姻。她用自己的方法一方面来影响父亲拒绝入社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追求。她知道说服父亲入社任重道远,也知道父亲对此不堪其扰。所以,为了避免与父亲争论走资、入社问题所产生的摩擦,她最终没有选择去父亲房中而是去旗杆院看时间。对此,可能有人认为这是灵芝叛逆的表现,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也是灵芝互相成全的表现。即她主动规避接下来和父亲之间可能产生的冲突,希望父亲想通以后心甘情愿地做出入社的决定,这也印证了灵芝处处为父亲着想的善良愿望。
其次,再看王玉梅这个形象。出生在干部家庭的玉梅,其大哥金生是三里湾的党支书,整日忙碌于农业合作社的大小事宜,恪尽职守,公平公正。二哥玉生则是一门心思为社里的农业生产做各种器具,无私奉献。大嫂勤劳顾家,母亲慈爱和善。正是在这种同劳动、共分享的和谐融洽的家庭氛围熏陶下,玉梅的观念具有比灵芝更为先进、积极的一面。虽然她没有多少文化知识,但生活常识与工作经验无疑相当丰富。小说中,魏占魁这样评价玉梅:“玉梅是个强劳力……不论做什么都抵得上个男人……”作为三里湾村的模范青年团员,她吃苦耐劳,积极参加社里的各项组织活动,在农业劳作中能力卓越,丝毫不比男性差。玉梅在帮满喜给专署何科长找房子时出主意说:“你先到我二嫂娘家去借他们的西房……”“实际上是叫天成老婆替你问房子去!”这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思维更显玉梅的深谋远虑。因长期在社里工作学习,玉梅也比较善于处理人际关系。面对大嫂与二嫂的家长里短,玉梅对大嫂说道;“大嫂你不要动,让她找得来再说!你要先出去了,她还要说是你找着她闹哩!”在自己的婚恋选择上,她更是理智取舍,进退自如。在和有翼订婚之后,她甚有先见之明地提出分家问题与马有翼父母的封建管制问题。在行孝问题上,玉梅同样具有自己的见解:“谁也舍不得把他的爹妈扔了……只要他们老两口愿意跟我们过管保能比他们现在吃得好、穿得好!”何况,“我们又不是怕他们穿衣吃饭,只是不愿意让他们管制……”
由此可见,玉梅的孝是有节制的孝,具有人格平等性、义务互益性与情感互换性,因而更加具有现代性的倾向。为人子女,她自会让双亲衣食无忧,老有所依。只是在她看来,父母与子女彼此都是相互独立的个体,为人父母不应该将子女看作自己的附属品而处处限制,子女有权追求自己的意志与选择。既然双方想要在一起共同生活,那么彼此都要为对方着想。子女确有孝敬老人的义务,但父母也应体谅子女。因为单向输出的爱势必不会长久,久而久之,家庭中的孝关系难免紧张,甚至产生不可弥合的裂缝。而具有互逆性的爱,才是孝道得以延续的重要基础。玉梅正是明白这个道理才会提出分家的要求,她这么做也是为了让“孝文化”在一种更为合理的道路上传承。
相比玉梅和灵芝的进步性,菊英在思想上无疑具有更多的保守性。作为马家的儿媳妇,她常年生活在这个封建家庭中,备受婆婆和大嫂的欺负。尽管她是一名青年团员,但婆婆“常有理”和大嫂“惹不起”是村里出名儿的老封建和泼妇。她们见不得菊英进步也不允许她进步,无奈之下,菊英也只得终日受她们摆布。当然,家中的落后势力固然强悍,但她自身也有其落后性。当女儿玲玲和侄子十成因为两个形状不同的香草袋而发生争执时,明明是十成无理取闹,她做的也只是让女儿一味地忍让退步;当大嫂诋毁自己的名誉时,她还是选择息事宁人、吃亏了事;在解决分家问题上,她也是全无主见,随波逐流,全由别人帮她决策,自己毫无独立意识。与此同时,菊英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她心底对自身的否定。在给金生媳妇诉苦时,金生媳妇问道:“那么你穿的布还是娘家贴吗?”菊英答道:“不贴怎么办?谁叫他们养下我这么一个赔钱货呢?”这是菊英对自己的评价,连她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独立的个体,这也就不难理解她总被婆婆和大嫂她们当作役使的工具了。
尽管菊英是软弱的,但也是孝顺的,只是她的孝是逆来顺受的孝。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独立人格时,她只能按照封建的那一套来尽孝。在与王满喜打扫给何科长暂住的屋子时,他们发现老人“胡涂涂”收藏的旧东西,她嘴上说着“尽是些没用的东西”,可实际上当看到孩子抢着玩时仍旧说“可不要动爷爷的宝贝”。看到王满喜想要扔掉那些东西时,她又说,“在这些没要紧的事情上还是不要得罪这些老人家吧!”家中的各种洒扫杂活、穿衣吃饭都得由她来做,隔三岔五就要给家里磨米磨面。每次回娘家还要为公公和丈夫做鞋,她心中对公婆始终葆有敬畏之心。纵然婆婆大嫂百般刁难,善良的菊英虽有怨言,仍旧一如既往。即使最后她与马家分了家,初衷也不过是想要获得吃饭平等的待遇。
至于袁小俊,则是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农村姑娘。她不是团员更不是党员,是党组织头疼的落后分子。她所有为人处世的道理,都由她的母亲亲自传授。比如对待家里人要刻薄一点,对待外人要圆滑一点,和嫂子怄气,和丈夫撒泼,和公婆分家,目的都是为了能在家里做主,能在家庭中获得话语权。在这个封建气息并未消散殆尽的三里湾,在传统男尊女卑的世俗影响下,女性想要获得尊重与平等哪是一朝一夕就能达成?她牵制玉生,给玉生下马威无非是想要满足她获得独立地位与尊重的强烈愿望,这也算是她向封建传统家庭压制妇女这种恶俗的无理反抗。于是,她便以好吃懒做、刁钻蛮横的搅家婆形象出现在人们眼前。然而,当和玉生的夫妻关系破裂,袁小俊还是会失去家庭地位,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最终让她自食恶果,追悔莫及。虽然袁小俊在外人看来不受管束,但是对于母亲的话她却言听计从。这样看来,袁小俊是彻底的愚孝,她按照母亲给她设定的模样,把自己当作工具,不论是非对错,全然执行母亲的命令。母亲让她把绒衣退还她就立马退还,没有一丝怠慢,让她和婆家人闹矛盾她就闹矛盾,让她离婚她就离婚。在马多寿和马有余商量是否接受小俊做儿媳时,马多寿也说道:“你妈是她姨姨!掌握得了她!”足见小俊对她母亲的话奉若真理。直到她听从母亲的话准备和有翼结婚,却遭到有翼退婚,村里人都把她视为笑柄时,她这才痛感母亲的荒唐,心中开始懊恼,并对母亲难免有些顶撞。不过,这也是她觉悟的开端,作为一个“人”独立思考的开始。袁小俊作为一个被封建传统所浸染的女性,她接触不到任何进步性的指导,仅仅依靠刁蛮的性格来面对生活,以无理的行为来处理事情,她的所作所为,上承母亲的意志,下保自己的生活,然而这一切都是空中楼阁。这也就从另一层面揭示出,袁小俊只有真正意识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后,才有可能获得精神上的新生。
而小说中的另一个青年形象马有翼,则是一个上过中学、接触了新思想的进步青年团员。他的母亲“常有理”是村里出了名的泼妇,父亲“胡涂涂”也是个既传统又惧内的人。他的封建家庭是社里开渠碰到的最大阻碍,也是社里亟待扫除的顽固堡垒。一方面,他在代表着进步趋势的合作社工作,另一方面又在代表着封建势力的马家生活。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虽然渴望自己的家可以走出封建,走向进步,但是又恪守着唯父母命是从的传统,从而使他具有很强的妥协性,也造成了他软弱、犹疑的性格。他希望可以说服父母参加农业合作社,却又说仅凭自己的单薄力量无异于螳臂当车,导致他们家迟迟不得入社;在给菊英吃饭问题作证时,他支支吾吾回答含糊,最后还是在满喜的强烈追问下才说出实情;在被父母的包办婚姻所逼迫时,他没有出面反对,而是选择把自己关在家里和父母怄气;他会因为灵芝生他气、不和他好而伏案哭泣,在听到灵芝和玉生订婚的消息时号啕大哭;当父母让他去临河镇找他舅舅这件事与党支部要求他参加紧急会议这件事相撞时,他一连三问:“可是我爹要我请个假去请我舅舅去!你说怎么办?”“可是他非叫我去不行!”“我回去了,我爹仍然要我去请我舅舅,我该说什么呢?”种种细节,都表现出他矛盾的心理与摇摆的立场。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和父母妥协呢?其实与马有翼内心对父母的孝顺之情有关。他考虑到如果直接反对包办婚姻,一来他的母亲受不了,二来以后不好面对姨姨、舅舅,因此在孝心的驱使下,他用怄气的方式委婉表达自己内心的抗拒,尽可能地压抑自己的个性,也希望父母能够回心转意。他害怕夜里开门黑灯瞎火的跌伤父亲,虽然生着气还是起身替父亲开门。在有翼眼中,父母的平安康健比起他们之间的矛盾摩擦显然要重要得多。他是善良而可爱的,当他得知灵芝订婚后,害怕玉梅也被人捷足先登,于是想要出门去找玉梅。母亲拼命地拦他,他也是很有分寸地用筐抵着母亲,让她不得不退出门外从而防止母亲摔倒。这些细节都是有翼孝心的体现,他在农村长大,自然受到乡土文化传统的熏陶,明白善事父母者为孝的道理。虽然父母思想上的封建残余依旧,但毕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他事事以父母为先,不忍心对父母如此决绝。但是,有翼的孝也是有原则的孝,他虽然小节不保,但大事不亏。最终,他还是鼓起勇气,走出了父母的禁锢,冲破了封建的藩篱,帮助父母入社,引导父母汇入时代前进的大潮中。
三、“孝文化”与赵树理的乡土情结
从小的方面而言,《三里湾》与“孝文化”的内在联系,与赵树理的成长经历与双重身份有关。赵树理出生在一个迷信色彩浓重的传统家庭,祖父祖母信奉“三圣教道会”,母亲和她的娘家人都是“清茶教”信徒,父亲则是个痴心于传统阴阳卦术的人。尽管他们分属不同教派,但都称得上是“善教”,什么“遵王法,敬父母”,什么“不说假话,不欺暗室,不履斜径”。所定教规各有区别,但无一例外都是专门劝人行善施福,助人为乐。身处这样一个家庭环境的赵树理,虽然也习得孔孟之道,但更多接触的是这些鬼神教义或奇门遁甲之术。这些教会教义之所以在赵家相安无事,是因为其中“善”的核心作用。也正因为这些教义与儒学的融合,使赵树理首先是一个深受“孝文化”传统濡染的农民,其次才是一名接受了“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党员知识分子。这一点,从他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达成父亲母亲的心愿就可见一斑。还未成年的他在寒冬里经常要赶着毛驴驮上碳,往返百里地挣几个小钱补贴家用,也因此身体落下畏寒的病根儿。面对父亲养家糊口的严厉敦促,他虽然也心生烦闷,但仍然改变回乡务农的初衷,以第一的成绩获得小学教员的资格,为的就是父母的期许。他的两次成婚也尊奉父母之命,虽然他为第二次成婚曾作出解释:“我对于个人的生活已毫无兴趣了,这样也好,那样也好,我都不在乎。可是家里需要个干家务活的。我自己并不操心这件事,就听任父母张罗说亲。这种态度大概是听天由命吧!”正是在这种乡土文化传统的潜移默化下,赵树理形成了自己温良端方的品格。在其踏上文学之路后,这种内化的品格就逐渐外显为一种饱含温情的叙事风格。
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赵树理熟悉农民生活和农村社会。他写乡村的人情物事,写农民的酸甜苦辣,知道他们爱一边劳作一边拉家常,知道他们农闲时间爱听故事听评书;他懂得农民的淳朴与忠厚,知足与谦卑,也了解农民的偏狭与自私;他同情农民的遭遇和命运,知道农民心中有着发展个体小农经济的想法,也知道他们心中的封建迷信思想依旧根深蒂固。对这一切,他都报以善意的处理。
作为一个党员知识分子,他的愿望就是自己的作品能被广大的农民兄弟看懂,并有所收获。所以,他总是针对农村社会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展开创作,并希望广大农民群众能通过阅读他的小说来改变传统的思想观念。
正是这种既靠近传统、又紧跟时代的创作要求,使他的作品普遍追求一种大团圆式的结局。《三里湾》也不例外,在这部反映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乡土社会走向现代化过程的长篇小说中,不论是进步家庭还是落后家庭,结局都是力求圆满。他没有尖锐地批评传统,与传统决裂,相反是抱着宽容而理解的心态。因为他知道,这就是中国乡村的真实风貌,是中国特有的农民阶层。所以,赵树理笔下生活在三里湾村的落后分子,每个人并非大奸大恶之人,他们只是被传统糟粕所禁锢蒙蔽,他慷慨给予这些人改过自新的机会。尽管在合作化观念植入乡村社会的过程中,小说中的个别家庭开始出现了断裂的迹象,人物也呈现出动态的一面,但赵树理还是给予了善意的弥合,竭尽所能地体现出家的圆融与乡村世界的完整。从这个角度而言,这种“大团圆”结局其实可以看作是“孝文化”传统的文学外溢。
从大的方面而言,《三里湾》与“孝文化”的内在联系,与乡土中国有关。从古至今,中国社会都是以农耕经济为主的乡土社会。因此,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基层乡村社会遵循一种以人伦为支点的“差序格局”,而这种差序格局就是让社会秩序由“己”推波出去,“即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哪一群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由此便有了父子、远近和亲疏。其中,亲子关系自然是其中最核心的环节,相配的道德要素自然是孝悌。费孝通认为:“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正因为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基层,它有着结构稳定、发展缓慢、人人相熟的特点,所以伦理传统在农村的持久力和规约力更加强大。基于这个说法,我们就会发现灵芝、有翼、小俊、菊英他们四人的“孝”,虽然各有不同各有侧重,但总体来说仍是囿于伦理传统的“孝”。不论他们是进步团员还是落后分子,他们仍旧按照乡村差序格局的特点来协调家庭关系,这正是主导着乡村社会秩序的文化传统所影响的结果。正如有翼和灵芝在劝说父母入社的事情上,两人都存在着相同的无奈和阻力,而无奈和阻力的来源是这无法言说并且习以为常的传统威慑力。由此可见,尽管《三里湾》所呈现的已经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步展开的新的历史场景,但小说展现的还是“孝文化”主导着生活秩序的乡土社会。费孝通先生曾在提出“孝”是什么的时候写道:“做子女的得在日常接触中去摸熟父母的性格,然后去承他们的欢,做到自己的心安。”但与此同时,我们又会发现,玉梅的“孝”和灵芝、有翼他们的切入点有所不同,她的孝具有人格上平等、关系上互益的特点。也就是说,她是站在现代社会的角度来呈现“孝文化”的,所以她所表现出的孝意识是具有现代性的。这一现象与三里湾作为中国社会的基层,并处在乡土社会和现代社会开始正面碰撞的特殊历史场景有关。毕竟这一时期是传统伦理文化的效力开始逐渐减弱、现代文化开始生长的时期。这样看来,《三里湾》中几位年轻人对“孝文化”的不同选择与呈现,既体现出赵树理对乡土文化传统的认同与守望,也体现出乡土中国在时代演进的过程中缓慢但有力的步履。
——浅评《入社礼的仪式与象征:关于生与再生的秘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