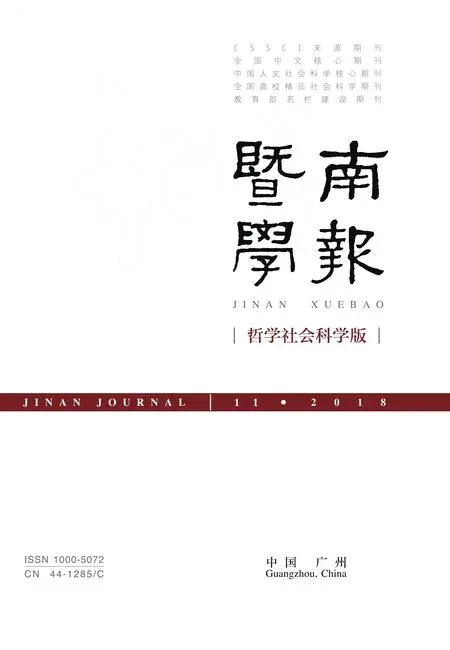戏剧翻译对爱美剧运动的引导和制约
王海瑛
中国话剧的“舶来品”性质决定了戏剧翻译活动在话剧的形成过程中必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中国话剧的发展史上,1917—1927年属于现代话剧的形成期,之前的话剧被称作早期话剧或者文明戏。研究话剧史的论著在讨论现代话剧的形成时,往往都要着重墨介绍外国戏剧的译介和20世纪20年代的爱美剧运动(简称“爱运”)。正是因为“爱运”的开展,早期话剧才得以脱胎换骨,最终发展为现代话剧,所以“爱运”在话剧史上所起的桥梁和枢纽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就笔者所见的文献,最早系统研究“爱运”的论著是张庚的《中国话剧运动史初稿》(未完稿),其中第二章论述了“爱运”产生的理论背景和在上海、北京两地的实践表现及成绩。曹晓乔的《试论“爱美剧”运动》是第一篇研究“爱运”的专论,对“爱运”的历史背景、主要组织体现、理论成就、实践中的缺陷和历史意义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其他较深入的研究还包括:葛一虹(1990),杨新宇(2006),刘方政(2009),张艳梅(2013)等,这些都是著作中的章节。此外,众多戏剧史的教科书都对“爱运”有所介绍。然而,上述文献中凡涉及戏剧翻译的部分,多侧重于史实的介绍;那些专门讨论外国戏剧对中国话剧影响的论著又倾向于从比较戏剧学的角度进行纯理论或纯文学的分析。受制于戏剧独特的“二元”属性(既是文学又是艺术)以及戏剧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质,几乎没有学者尝试从翻译学的角度来考察现代话剧形成期的戏剧翻译与话剧实践的互动关系,而这正是本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戏剧翻译与“爱运”的孕育、产生和发展
本文讨论的戏剧翻译是个广义的概念,包括与之相关的所有人物和事件,即外国戏剧的介绍、翻译、改编、上演和接受,以及外国剧作家、戏剧运动和相关理论的翻译和介绍。
戏剧翻译对中国话剧的产生与发展所发挥的重要影响不言自明。但1917年以前,其影响是有限的、间接的。1907年春柳社在日本选择搬演《茶花女》片段和《黑奴吁天录》正是因为林纾的相关译本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据阿英的考证,现存最早的翻译剧本为1908年李石曾译的《夜未央》和《鸣不平》。但是彼时国内话剧舞台及演员皆在襁褓之中,根本没有上演的可能。《鸣不平》虽于1909年初由春柳社演出于日本,《夜未央》却直到1918年才被药风社搬上舞台。由于早期话剧的演出实行幕表制,没有剧本概念,戏剧翻译的影响力更多体现在对外国戏剧的跨文化改编上。比如文明戏时期的莎剧演出,所据蓝本为林纾译的《吟边燕语》。据郑正秋1919年编的《新剧考证百出》,外国剧目也只占四分之一,且以改编的莎剧剧目为主。
1917年以后的情况则不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戏剧翻译,就没有“爱运”的孕育、产生与发展。
第一,“爱运”产生前文学系统内的知识分子关于建设现代话剧所做的理论探讨在中国戏剧翻译的第一个小高潮中得到具体化和升华。作为“五四”运动主要阵地的《新青年》是这次翻译高潮的引领者。除了众所周知的1918年6月发行的4卷6号“易卜生号”外,同年10月发行的5卷4号也是戏剧专号,刊登了胡适、傅斯年、欧阳予倩、张厚载等关于戏剧改良的文章。宋春舫还给出了《近世名戏百种目》,供从事戏剧翻译的人士参考。事实上,《新青年》从创刊之始就没有忽略过外国戏剧的译介,如自1915年1卷2号就开始连载王尔德的《意中人》(薛琪瑛译),1916年的2卷1号和3号上又连载了王尔德的《弗罗连斯》(陈嘏译)。但是真正掀起戏剧翻译高潮的还是“易卜生号”,紧随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刊登的是易卜生的三部剧作译文《娜拉》、《国民之敌》和《小爱友夫》。随后,《新潮》、《小说月报》、《东方杂志》、《妇女杂志》以及著名的四大副刊《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和创刊于1921年的《戏剧》等杂志都刊登有大量翻译剧本,同期出版的单行本亦不少。“在20年代中国剧坛,有近20个国家的200多部剧作被翻译出版”,译介最多的是英、法、俄等国的戏剧。1917年至1924年,“全国二十六种报刊、四家出版社共发表、出版了翻译剧本一百七十余部”,涉及近20个国家70多位剧作家。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1917—1920年“五四”运动高涨、保守派和改良派为改良新剧激烈论战、翻译剧的发表层出不穷的这几年,舞台上演的翻译剧却难觅踪影。胡适在回答一位主张翻译剧必须上演的读者的来信时很勉强地说,“我们译戏的宗旨本在于排演。我们也知道此时还不配排演《娜拉》一类的新剧”。他内心很清楚,除了天津的南开新剧团外,当时的中国能够胜任现代话剧演出的剧团和演员都还没有出现。
第二,“爱运”产生的直接导火索是1920年10月上海新舞台演出的翻译剧《华奶奶之职业》(简称《华》)惨遭失败,而这是“中国舞台上第一次演西洋剧本”。演出由汪优游主持,剧本以潘家洵1919年刊登在《新潮》杂志上的译本为蓝本,汪将其改为中国的故事,对剧情、人物名称和服装都做了归化的处理。汪认为,这次演出“狭义的说来,是纯粹的写实派的西洋剧本第一次和中国社会接触;广义的说来,竟是新文化底戏剧一部分与中国社会第一次的接触”。演出因为剧本、演员、观众等多方面的原因而失败告终。即便如此,《华》的演出却“标志着戏剧界自身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由文明戏和戏曲界共同发难,将戏剧改良理论主张付诸实施的可贵开端”。
《华》演出的失败引发了众多戏剧从业者对现代话剧建设的深入思考。汪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讨论如何建设新剧,他主张“脱离资本家的束缚,召集几个有志研究戏剧的人,再在各剧团中抽几个头脑稍清有舞台经验的人,仿西洋的Amateur,东洋的‘素人演剧’的法子,组织一个非营业性质的独立剧团;一方面介绍西洋戏剧智识,造成高尚的观剧阶级,一方面试演几种真正有价值的剧本”。汪积极地将设想付诸实践。经由《时事新报》副刊《青光》的主编柯一岑介绍,汪认识了时任《小说月报》主编的沈雁冰。汪请沈为他办的剧社取名,并推沈为发起人之一,“以资号召”,沈提议使用“民众戏剧社”一名。1921年1月,《时事新报》刊登了《民众戏剧社宣言》和《民众戏剧社简章》,民众戏剧社正式在上海成立。《宣言》里明确指出要出《戏剧》月刊“介绍西洋的学说”。后来《戏剧》(1921)创刊号封二公布的社员题名录共13人,排在最前的两位便是沈雁冰和柯一岑。
不久之后,陈大悲将汪所提的Amateur译成了“爱美的”,并于1921年4月20日至9月4日在《晨报》连载了《爱美的戏剧》,该书1922年3月由北京晨报社发行单行本,因为大受欢迎,一个月内印了三版。陈在篇首《编述的大意》结尾列举了自己参考的多本国外戏剧著作的书名,同时坦言,“我起先原想专译《爱美的舞台实施法》,因为这部书专为美国人而作,与中国情形很多不合,不如拿人家先进国底戏剧书做基础,编一部专为中国人灌输常识而且可以眼前实用的书,比较的有些收获底希望”。所以严格说来,这是一本编译的著作,而且以翻译为主。至此,“爱运”以上海和北京两地为中心,迅速波及全国。
第三,“爱运”发展至高潮的标志是洪深改译并执导的翻译剧《少奶奶的扇子》(简称《少》)演出获得巨大成功。1924年1月至3月,洪将王尔德原著《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改译为《少》刊登在《东方杂志》21卷2至5号上。同时发表的还有《改译序录》和《后序》两篇文章。《改译序录》分十节,详细讲解了剧本与小说的区别,剧本如何写实,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区别,剧本的三要素,《少》剧之写实、结构之佳、语言之妙,以及改译为中国故事的原因等。《后序》则解释了话剧演出中仿效和发挥的重要,以及读剧和观剧的区别。两篇文章每一节结尾都附有所参考的外国原著作者及书名。显然,洪不仅改译了外国剧本,还把与剧本相关的重要西洋戏剧理论知识编译成浅显的中文提供给读者和戏剧从业者学习。同年5月,洪执导并参演的《少》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的职工教育馆内前后演出八场,“轰动全沪,开新剧未有的局面”,被誉为“中国第一次严格地按照欧美各国演出话剧的方式来演出的”现代话剧。该剧的演出成功,“标志着中国话剧在舞台实践上真正摆脱了文明戏的羁绊和困扰,终于创造出比较完整的现代话剧的艺术形态”。
由于20世纪初中国的话剧从业者对西方戏剧的了解主要借由日本辗转而来,他们对这种新兴的艺术样式存在种种误读,因此文明戏时期将对话与戏曲表演进行简单杂合的新剧演出很快就走向了衰落。回顾“爱运”的孕育、发生与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正是因为懂英文的译者直接从英文原著翻译和介绍西洋戏剧知识,才使得戏剧翻译活动自1917年以后得以全面展开。这当中不仅有剧作家、剧本、理论知识以及舞台演出技巧的译介,更有翻译剧的改译和上演,这才使得“爱运”在孕育和发展中逐步走向高潮。
二、翻译话剧:文学性与舞台性完美结合的先驱
戏剧性是贯穿戏剧艺术五大要素(剧本、导演、演员、剧场、观众)的核心,包含文学构成和舞台呈现两个层面,二者的完美结合,才是戏剧性的最佳状态。这种对戏剧性的二元认识,直到21世纪初才有学者“从中西戏剧观念的相互参照与沟通中”对其进行了准确的阐释。董健指出,尽管世界戏剧发展史上曾出现过只讲文学性不承认舞台性或者只强调舞台性排斥文学性的倾向,但是这两种倾向所推崇的戏剧作品都只能是“戏剧艺术的畸形儿”。
早期话剧的衰落以及“五四”前夕《新青年》同仁对旧剧的无情批判让新剧建设者们明白了一个道理:辛亥革命的失败使文明戏的发展丧失了核心动力,对于一批未经专业训练、文化程度普遍低下的文明戏演员来说,仅从舞台呈现上做文章,表演流于低俗是必然的结果;话剧想与表演形式颇为成熟、民众基础牢固的京剧和地方戏抢观众,只能先从文学性上发力。文明戏演员出身的汪优游对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汪通过柯一岑邀请沈雁冰任民众戏剧社的发起人,便是想利用沈在文学界的影响力为话剧活动摇旗呐喊而作为“舶来品”的话剧,想在文学性上有所作为,只能借助翻译话剧。
以色列翻译理论家埃文—佐哈尔认为文学是一个多元系统,翻译文学亦自成系统,但往往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当以下三种情况出现时,翻译文学就从边缘走向了中心:(1)文学多元系统依然“幼嫩”;(2)文学多元系统在大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或弱势;(3)文学多元系统出现转折点、危机或真空。20世纪初的中国正好符合第三种情形,随着白话文的推广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开展,翻译文学逐步占领了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受到当时翻译文学系统主流法则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戏剧翻译活动与1917年以前相比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首先,1917年以前戏剧译者群体的构成比较多元化,而这一时期则以文人为主。据笔者统计,1917年以前的译者既有留学生(李石曾、马君武等)、剧人(陆镜若、徐半梅等)、作家(许啸天、包天笑、曾朴等),也有翻译家(林纾、刘半农等)。但1917—1920这几年,刊登在各大报刊上或以单行本发行的翻译剧全是文人所译,完全看不到剧人的身影。《华》的译者潘家洵就是其中一位重要的文人译者。1921—1927年情况略有改观,但总体变化不大。剧人译者仅有田汉、陈大悲、徐半梅、欧阳予倩和洪深,而且他们译剧的数量只占极少数。因为在现代话剧的建设道路上,他们个个都肩负着创作本土话剧的重任,翻译剧在他们看来只是树立榜样和解决剧本荒的权宜之计罢了。
其次,翻译话剧与中国舞台的第一次接触以失败告终,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剧本的选择完全受到了翻译文学系统的左右。汪仅仅关注了剧本的文学性,忽视了作为艺术的话剧演出中的舞台和观众这两个重要的因素。
文明戏时期上演过的翻译剧基本都是仅保留故事情节的改编本,改编者也都是剧人,对于怎样的编剧能吸引观众非常清楚。但“五四”时期话剧译者以翻译文学系统中的知识分子为主,不太重视剧本与舞台的关系,适合中国舞台上演的翻译剧本几乎没有。关于戏剧翻译,胡适明确表示“我们注意的易卜生并不是艺术家的易卜生,乃是社会改革家的易卜生”,“我们的宗旨在于借戏剧输入这些戏剧里的思想”,“在于输入范本”,至于这些“范本”是否适合当时中国的舞台以及如何将它们搬上舞台,就不是胡适等文人所关注的重点了。所以,当汪优游急切地想搬演“范本”时,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他最后无视舞台对观众的需要、选择上演萧伯纳的写实主义问题剧《华伦夫人之职业》(以下简称《华伦》),这又和沈雁冰对该剧的高度推崇分不开。沈1919年曾写了两篇文章介绍萧伯纳,其中一篇是关于《华伦》的,登在《时事新报》上。该文除了介绍《华伦》的命意所在,还将该剧与易卜生的《群鬼》做了比较,认为“易卜生是讲一家,萧伯纳是讲全体——就是社会”。汪读了此文后,从中“得着的教训实在不少”,最后决定将其搬上舞台。汪事后承认,“排这本戏以前,早就料定他不受欢迎的”,“明知他们不爱看这本戏”,但依然上演,“这里头的确有一种冲动发生出来的”。而这种冲动则是源于汪认为新舞台之前演的都是“假新剧”,属于《新青年》同仁所批判的旧剧行列,而《华》才是“真新剧”。
再次,“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系统中直译的策略逐渐替代之前的意译和译述成为主流,欧化的语言为翻译话剧走向舞台设置了新的障碍,洪深借助改译策略重译了王尔德的剧本,并亲自执导和参与《少》的演出,令其“轰动全沪”,成功移除了这一障碍。至此,通过改译和演出西洋剧本,话剧的文学性与舞台性终于在中国的舞台上首次得以完美结合。
《华》剧演出的失败一定程度上源于潘家洵的译本是典型的直译本,存在很多问题,不仅有译错的地方,还有许多没有翻译保留原文的地方,比如一些人名和地名。尽管汪出于文化差异的考虑,将故事改成了中国的,情节上也有些许改动,但欧化的语言本身并未得到修改。洪深改译的《少》则不同。在洪译本之前,已经有《遗扇记》和《扇误》两个译本发表,但洪以剧人译者才有的舞台意识,指出这两个译本的通病在于“按字而索,未能达出言外之意”,“造语别致,非通常习闻之口吻,演员念不上口”,总之是“欠缺神味”。洪强调,文化差异的存在使得观众无法理解直译的剧本,加脚注又不适合舞台演出,“不得已求其次”选择改译,“改译云者,乃取不宜强译之事实,更改之为观众习知易解之事实也”,“地名人名,以及日常琐事,均有更改,惟全剧之意旨精神,情节布置,则力求保存本来”。洪对改译所做的界定成为后来研究的学者开展改译研究的基础。对比原著细读《少》,可以发现,故事的人物和地点全部中国化,剧本中所有带有异域特色的表达全部改成了中国的习语和俗语,译者删去了一些影响理解及演出效果的细节和对话,并增加了许多的舞台说明和细节,目的只是为了帮助观众在最短的时间内理解剧本及其主旨。
借助翻译文学的力量为话剧建设助威的理想正是汪当年想做却没有做到的,洪最终做到了,原因在于他成功摆脱了翻译文学系统直译策略的影响,顺应了话剧艺术对舞台语言通俗化的要求。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改译策略都被当做戏剧翻译的重要策略使用。话剧艺术是文学性和舞台性的统一,位于翻译文学系统的文人译者仅关注话剧的文学性,只有剧人译者才明白,抛开了舞台和观众,话剧就少了一条腿,这样的话剧如何才能独立行走呢?现代话剧在形成期对于翻译话剧的这种既依赖又排斥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本土创作的话剧逐渐增多后的20世纪20年代后期。
三、剧人的译者身份是一把双刃剑
“五四”新文化运动始终有一个“新旧论争”的母题,运动期间,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经历了破旧立新的变革与洗礼,而所有这场变革的参与者都有一个共识:中国的、传统的都是旧的,西洋的、现代的都是新的。当“西洋”与“现代”和“新”画上等号之后,懂英文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无疑是一笔重要的资本,若能翻译西洋的原著,则这个资本的价值更高。具体到自西洋引进的话剧艺术,这一点尤为突出。20世纪初的中国,戏剧从业者普遍文化程度不高,一位接受过新式教育、既能创作又能翻译,既能编剧又善表演的剧人所拥有的资本是显而易见的。汪优游、陈大悲和洪深这三位“爱运”中的关键人物,除了剧作家和演员的身份外,都兼有译者的身份。作为20世纪20年代初比较稀缺的剧人译者,三位的译者身份使得他们在话剧领域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他们的职业发展。
茅盾说“汪懂英文,读过外国戏剧家所作的剧本以及外国名演员所写之‘经验谈’”,但被誉为“话剧界奇才”和“新剧界全才”的汪优游英文到底有多好,我们不得而知。他“生长在赤贫人家”,在上海民立中学读书时学过英文,但是1905年冬天成立文友会后学业受到极大影响,“由优秀分子,一变而为低能儿”,最后不得不转入南京水师学堂。1921—1922年,汪在自己出资主办的《戏剧》月刊上发表了很多翻译的文章,以译介国外的剧作家和戏剧活动为主。他在一篇译文的篇首说,“纸面上的剧本中含的什么主义,自是文学家应当负介绍的责任”,而他想做的是“把近代世界有名的演剧家介绍几位到中国来”。当有读者认为他搜集外国剧作家的笑话编译《西洋的剧场轶文》系列文章没有太大意义时,他回答:“这些笑话大半是由舞台的谬误所酿成的,前人的谬误就是后人的教训”,并总结了十种舞台的谬误以强调他编译该系列文章的指导意义。以上史实再结合汪上演《华》之前并未对潘译本做过多少语言上的改动,潘译本中的误译也没有被更正过来,我们基本可以断定汪本人的英文水平并没有好到可以胜任文学作品的翻译,这也是为什么他译的多是介绍性的文章,并没有完整的剧本。
“爱运”的另一个重要发起人陈大悲则不同。他不仅出身官宦世家,而且“很小就开始学‘蕃话’”(即英语)。陈在上海的新式学堂里完成中小学学业后,于1908年考入苏州的东吴大学文学系。因为酷爱演戏,1911年初陈离开东吴大学加入任天知领导的进化团。经过几年的戏剧实践,他日渐认识到文明戏的种种弊端,1918年2月毅然选择东渡日本,目的是取回戏剧的“真经”。陈在东京戏剧专科学校仅学习了一年多,便于1919年4月中旬回国。在日本学习期间,除少数课坚持听以外,大部分课他都逃掉了,把时间花在了泡图书馆和抄书上,回国时带回“近10箱的书籍和资料”。
从陈1917年10月决定去日本,到次年2月抵达日本,前后仅4个月时间。这期间他还翻译了一部长篇小说。即便他语言天赋极高,几个月内也很难达到精通日语的程度。笔者推测,日语沟通的障碍应该是他逃课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他在图书馆抄的几箱子书籍资料,应该大部分是英文原著。毕竟,他最初是打算去欧洲的,因为那才是新剧的发源地。退而选择日本,除了欧阳予倩等众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朋友强力推荐外,经济原因也是很重要的考虑。
陈出国前就译过英文小说《红鸳艳谍》,1918年初登在《小说月报》上。陈回国后倒是翻译了两篇日本学者的文章并发表在《民国日报》上,但之后发表的所有译作全是英美国家的作品。特别是1921年编译的《爱美的戏剧》,更是从数本英文著作中汲取精华,再附上与中国情形相符的介绍编写而成。陈在翻译《银盒》的《译者序言》里明确提到自己读的是英文剧本,之所以一直想译剧本却不敢译,是因为读别人翻译的剧本时发现“许多话说不上口来”,“还发现许多人类所没有的言语”,自己担心译不好犯同样的毛病,对不起原作者。陈不仅意识到了翻译剧的语言“上口性”很重要,还在文末探讨了关于直译和译述孰优孰劣的翻译策略问题,显然已经是一个很严谨的译者了。
将“爱运”带入高潮的洪深,其英文水平之高,早已是公认的事实。早年就读于清华学校时,洪就“能将英语和第二外语说得相当好”。1914年6月他翻译并主演了《侠盗罗宾汉》,在清华校园出尽风头。1916年洪官费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烧瓷工程,学习之余还创作了英文剧本《为之有室》和《回家》。1919年,洪放弃了实业救国的理想,凭借这两个英文剧本,成功转入哈佛大学跟随奥尼尔的老师著名的贝克(George Pierce Baker)教授学习戏剧,成为中国出洋专攻戏剧的第一人。
如前所述,洪1924年初在《东方杂志》上刊登改译的剧本《少》对于掀起“爱运”的高潮功不可没。尽管此前洪翻译的剧作并不多,但读一读《改译序录》文中关于戏剧翻译的论述,我们就能发现,与同期的戏剧译者相比,洪堪称专家级译者。该文一共十小节,洪在第九节引用了著名翻译理论家泰特勒(Alexander F. Tytler)在1791年就提出的翻译三原则:“一,原文意义,不可错误遗漏;二,声调格局应与原文相似;三,字句尤当如原文之流利。”这三个原则作为翻译标准被后来的翻译理论界反复引用和讨论。国内翻译学界首次公开介绍泰特勒的理论是1950年,而对西方翻译理论的系统译介则迟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洪作为中国20世纪初的话剧翻译实践者,能具有如此高的翻译理论意识,颇令人惊叹。
我们可以从汪、陈、洪三人作为译者的经历和他们各自在戏剧实践活动中取得的成绩之间依稀看到直接的联系。作为“爱运”的重要发起人之一,汪是第一个在国内报刊上引用Amateur一词的剧人。如果当年他能阅读更多戏剧类原版书籍,学习更多的西方戏剧理论知识,而不是仅满足于翻译一些舞台演出相关的介绍性的文字,或许他在现代话剧的建设道路上会走得更远,也不会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退回到文明戏的舞台。
因为编译《爱美的戏剧》,陈获得极大声誉,被爱美剧的信徒“仰为一代宗师”。1922年11月蒲伯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戏剧专门学校“北京人艺剧专”,陈担任教务长。陈在《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章程》的第一章第三条首次使用了“话剧”一词,明确指出“话剧,和西洋的‘笃拉马’(Drama)相当,以最进步的舞台艺术表演人生的社会剧本”。然而仅仅一年之后陈就遭遇了剧专学生的“驱陈”风潮,随后被解除教务长之职,剧专也在1923年底停办了。陈“宗师”形象的幻灭与他的翻译剧本遭到文人无情的批判有着直接关系。1923年8月13日至31日的《晨报副刊》连载了陈翻译的《忠友》。不久就有人撰文以中英对照的形式列举了译文中33条误译,其中不乏一些简单的理解错误。这件事让“一般崇拜大悲的学生从此便对他失去了不少的信仰,尤其是大悲自己的学生”。
对陈而言,真可谓成也翻译、败也翻译。如果当年他不是急着回国,而是加强自己的日语,在日本认真学习几年戏剧专业知识,或许他就代替洪深成了留洋专攻戏剧的第一人,为话剧命名的荣誉也不会被归到洪深的头上,他本人更不会从20世纪20年代“话剧的急先锋”蜕变成30年代“靠着写礼拜六体的小说赚稿费”、“完全被世人忘却”的老人。
洪作为留洋专攻戏剧的第一人,尽管回国前汪就曾在信中表示要和他做朋友,为他将来回国后在剧界活动“效些微力”,但他1922年春回国之后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1923年初他编演的《赵阎王》因为超前了时代而不被观众接受,还有人骂他是神经病。不过这丝毫不影响专业剧人对他的认可,1923年7月洪经欧阳予倩和汪的介绍加入上海戏剧协社,“入社之第一日,古君剑尘即以其排演主任一席嘱洪君”。随着协社的几次公演,《少》剧的改译和演出取得巨大成功,洪终于获得了观众的广为认可。
然而,现代话剧的建设者们始终认为只有原创的作品才能证明话剧的中国身份,才能让话剧艺术在文学系统中占有一席之地。向培良1929年撰写《中国戏剧概评》时,对当时的剧作家一一点评,从陈大悲说到丁西林,唯独不提洪深,在他看来,“号称在戏剧界颇有声名的洪深——其实他的成绩只改译了两个剧本,以后便走到电影界去了”。这一评价显然有失公允,但是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20世纪20年代末大家对翻译剧和剧人译者的普遍看法。洪后来离开戏剧协社加入南国社,也是因为他感到很悲哀,认为自己的努力并没有为自己带来在艺术领域或文学领域中应有的地位,而“因田汉的关系,洪深在文坛上的地位是无形中在增高”。
四、结 语
洪认为将Amateur译为“爱美的”“真是绝顶的聪明”,既译出了业余的字面意思,又凸显了欧美戏剧艺术者对艺术的追求与努力。然而,马彦祥认为“爱运”在破坏旧的文明戏方面成果显著,但在积极建设方面“除了‘非职业的’一点以外,是什么也没有做到”。这一评价过于偏激,但是回顾一下学界对“爱运”的各项成绩总结,我们可以发现,所有的成绩都离不开戏剧翻译。《爱美的戏剧》一书中的理论以翻译西方著作为主,民众戏剧社的成立是借用了罗曼·罗兰“民众戏院”的口号,其机关刊物《戏剧》刊登的理论文章也是以译介为主。北京人艺剧专的成立虽然弥补了民众戏剧社理论与实践脱离的缺陷,但是在其前后持续仅半年多的十九次公演中,以陈本人的剧本和文明戏剧目为主,根本没有西方近代剧的翻译演出,这显然也是其最终停办的原因之一。上海戏剧协社则不同。作为中国早期戏剧团体历史最长的一个,协社在其存续的十多年间一共有十六次公演,除去《少》之前的五次公演和1924年8月的第八次公演外,其他十次公演的剧目全部是翻译或改译的西方戏剧。
事实上,戏剧翻译始终贯穿着“爱运”的孕育、产生与发展全过程。在“爱运”对旧戏和文明戏的批判、对西方戏剧理论的译介、对西洋剧本的翻译和搬演过程中,现代话剧逐步形成。然而,翻译文学系统在为现代话剧建设添砖加瓦的同时,也为其发展带来了障碍。翻译剧《少》的改译和演出正是在挣脱翻译文学系统的束缚之后才得以成功,标志着文学性和舞台性在中国话剧舞台上的首次完美结合,“爱运”也随之走向高潮。“爱运”中的三位主将汪、陈、洪因为积极参与戏剧翻译而获得重要的资本,但剧人译者的身份对于他们在话剧领域的职业发展而言更像一把双刃剑。
翻译是知识传播的桥梁,借助翻译中国才有了话剧这种艺术形式。而“爱运”不仅是中国的戏剧从文明戏走向话剧的桥梁,更是中国话剧向健康发展的道路上前进的桥梁。建在翻译这座大桥上的“爱运”之桥,既受大桥的引导,也受其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