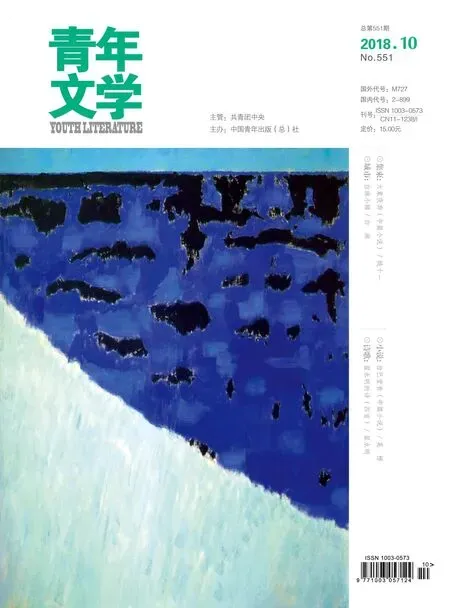逐 影
⊙ 文 / 林晓哲
当是时,民被兵燹,陷穷寇,困征敛,澄公方弱冠,北流于瓯之平阳,无何,继迁永嘉城南,备尝艰难,创业垂统,是为吾族之一世祖也。
——《西河林氏宗谱》
那时候已经没有人听他絮叨了。连他最小的孙子也不听他絮叨了。他独自坐在田埂上,翕动着嘴唇却没有发出任何声响。他的目光掠过缓缓转动辐条的水车,掠过田间一群群忽起忽落的白鹭。当他的目光掠过那几个正在劳作的孩子的时候,他皱了皱眉。他太想去纠正他们难看的姿势了。他张开嘴,干咳了两声,未能咳出喉咙深处的一口痰。他知道他们都不想在这里见到他。他们甚至厌恶他过问今年的收成或孙辈们的饱暖。他们甚至连他插嘴称颂一声当今圣上都要大发雷霆。他不明白他如何成了这个家里多余的人。他常常在被奚落中想起自己的父母。他在年轻的时候离开了当年的家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他不知道他的父母在他离去之后是怎么过的,是怎么没的,是惨死刀下还是寿终正寝。他们一定是没了,不然他们都活到上百岁了。他仿佛看得到他的父母注视他远去的眼睛。那双眼睛和他现在的眼睛一样湿润。
他没有擦拭渗出眼眶的泪水。他没有意识到眼眶渗出了泪水。他的泪水和他一样老迈,风吹一下就干了。他的泪水沾染着潮湿的泥土的气息。他的皱纹把眼睛包藏起来,也沾染着潮湿的泥土的气息。他的银灰的发丝从发髻里蹿出来,和同样银灰的山羊胡子掺杂在一起。他一动不动地坐着,如同一个垒起的土堆。有几只麻雀试图逗留在他的发髻上。他掸了掸发丝,把它们全给赶跑了。他感到有一股怒气从胸口涌了上来。在意识到那一股怒气时,他窘迫地望了一眼他的孩子们。他咽下了那一股怒气。无论如何努力,他都无法咽下卡在喉咙深处的那口痰。
“阿爹,这里用不着你,快归家去吧。”
他不知道自己嘟囔了句什么。他感到自己不是在回答他的儿子,而是在回答一个遥远的声音,或是一个遥远的声音恰好回落在他的嘴里。
“阿爷,你在讲什么?我怎么一点也听不懂?”
那是他最小的孙子。他的小孙子沾染着比他更浓重的泥土的气息。他看着他踢着腿兴冲冲跑来,溅起的水花散落在他的衣裳上。他支吾了一声,揣测方才发出的声音是否是他曾经的土语。他已经有很多年没有用它讲话了。
“太心,你晓不晓得赤岸在什么地方?”
“阿爷,你都讲过无数遍啦,我不晓得,不晓得。”
他的小孙子双手在水田里搅拌,伺机让水浪扑上田埂,埋入他的裤管。有一排失控的水浪唰地扑向他的脸,落在他的颈项和双肩上。他的小孙子诡谲地笑着,扑通扑通地逃开了。那一股被咽下去的怒气重新涌了上来。
他随后听到他那几个儿子“嘎嘎嘎”的笑声。他又窘迫地缩回脖子,揣测方才是否有谁发现了那一股怒气。接着,他抬起头,乞怜似的说:“你们晓得,我要走了,你们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件事?”
他只看到他那几个儿子低着的头,或者撅起的屁股。他又翕动嘴唇。他是循着记忆里的声音翕动嘴唇的。
“那是很久远以前的事情了。
“那天夜里,簇拥的火把染红了整片海岸,甚至潮水也变成赤焰的颜色。将军的人马就是从火把里蹿出来的。是潮水把将军的人马推到了这里。大人们说无论潮水把将军的人马推到哪里,将军都会攻占那里的城池。大人们谁都讲不清将军听命于哪个王子的差遣。或许连将军自己都讲不清楚。大王在世的时候娶了太多的女人,那些女人生了太多的王子,终于把大王的天下也搅乱了。那时候,大人们总是在村口的大榕树下讲闲谈。他们连守城的人马听命于哪个王子的差遣也讲不清楚。大人们总是吵吵嚷嚷,有时还分成两个阵营,各自押上胜败的赌注。他们吵吵嚷嚷的声音会让大榕树的叶子和胡须都摇晃起来。那时候,他们觉着将军的人马只是过客。他们不会带来灾难。只有旱涝才是灾难。
“那时候,我们庆幸的是不用再去学馆念书了。在先生哭丧着脸说科考没了的时候,我们都开心地笑了。科考没了,念书就没用了。我们成天在村口、岸边、山头晃荡,身上沾满了灰尘、泥土、野草和沙粒。阿爹快被我气疯了。阿爹每天忧心忡忡。娘说看阿爹那被雷劈的样子,像是他又落第了一回。
“将军的人马来的第二天夜里,阿爹在后院凿了个地窖。阿爹差家仆——那时候我们家有好几个家仆——把几桶谷藏到地窖里。阿爹说,将军的人马一定会来找吃的,谁晓得他们有多大的胃口?可是阿爹说他还是‘百密一疏’。阿爹说‘百密一疏’的时候我看着挺滑稽。阿爹没有考取功名,可他总是喜欢文绉绉地讲话。几天之后,将军的人马真的来我们家了。他们没有带走我们家的谷,他们带走了我们家的鸡,还带走了阿爹一直舍不得喝的几瓶黄醅酒。
“将军的人马驻扎在离海岸很近的地方。那阵子,一到夜里海岸边就火光冲天,云和礁石都被熏红了,将军的人马东倒西歪地嬉闹着,像过节一样。到了白天,将军的人马就成群结队地出去找吃的,有时,他们还会聚拢到大榕树下,和大人们一起插科打诨。将军的人马看起来不像是来打仗的。他们像是来吃吃喝喝的。他们逮着村里的鸡啊猪啊狗啊什么的就杀了烤了吃掉。他们抹一抹油腻腻的嘴唇,把唾液吐到很远的地方,在‘嘎嘎嘎’的笑声中提起长矛。有一天黄昏,他们排成整齐的队伍,在岸边操练了起来。
“那时候,我们正匍匐在山崖的乱树丛里。我们常常匍匐在山崖的乱树丛里看将军的人马,看他们的铠甲和长矛。没有比这更刺激更有趣的事情了。我们还会为身穿哪一套铠甲手持哪一把长矛发生争执。没有人喜欢一个小士卒的粗布衣,那样很容易被戳死。那天黄昏,我们差点干了一架。我们中最大的伙伴按住我们的头,把我们每个人的屁股都揪了一下。他说:‘小心哨岗上的箭,它会射穿你的脑袋,那样你就死了。’
“于是我们屏住呼吸。我们匍匐着,就像一条条死蛇。天色暗下来了。潮水窜到海岸上,月亮从海上升起来。我从未见过那么大那么圆的月亮。大概是潮水把月亮也拉近了。在我们眼皮底下,又点燃了一个个火把。这一次,火把好像把月亮也熏红了。
“我的心慌得紧,怦怦乱跳。我对大伙讲我想回家。大伙讥笑我,说我打仗了准是逃兵。我们中最大的伙伴说:‘你忘了我们就是来等打仗的吗?看样子,明天一早就开打了,搞不好夜里就会偷袭!’我想了想,想起自己真的是每天盼着打仗。可是我又对他们讲阿爹会担心的。我这么一讲,大伙又开始讥笑我了。接着他们说要移师城门了。从这边的山崖爬到城门口的山崖少说也得花两个时辰。‘你不走就回去。’我们中最大的伙伴撂下这句话第一个爬走了。我只好跟着他们往前走。
“我们没入树林,穿梭在山脊的野路上。月亮跟在我们屁股后,越升越高,现在它不红了,一片惨白。我们踉踉跄跄,边讲边笑,好几次被风绊倒,可谁都没讲自己担心野狗、蟒蛇、大猫的侵袭。那时候,我们是真期待看见一个活生生的人被箭射穿,或者被刀砍成两半,或者头颅离开颈项在地上打滚。鲜血染红了整片城墙。鲜血还从城墙上流下来,顺着护城河流向大海。最后,大海也染红了。
“我们终于爬到护城河外的半山腰。我们离城门大概有半里远,可是不能再靠近了。我们抓了一大把树叶和野草遮在头顶,拥挤在一个小山坳里。我被压在最下层,都快被压扁了。可是我没吭声,因为还没到吭声的时候。我们盯着城墙上一排排长长的火光,盯着火光下一个个昏昏欲睡的士卒。他们真是不要命了,我们可一点困意都没有。我们担心的是,将军的人马会攻打另一个城门。不知道谁说,至少有六个城门。
“天还没亮鸡就叫了。狗也在吠。那些声音让我们心烦意乱。将军的人马逮着村里的鸡啊猪啊狗啊什么的就烤了吃了。我们念叨着,谁家里少了鸡,谁家里少了猪,谁家里少了狗。念叨到狗的时候大伙都伤心了。狗是我们的伙伴。‘那些吃得最多的人会被箭射穿,被刀砍死,头会掉到地上打滚。’我们诅咒道。
“谁晓得后来他们一个也没有死。天蒙蒙亮,将军的人马就走到城门下。将军的人马排了很长时间的阵势。城墙上的人马跑来跑去,准备迎战。可是压根就没打仗。将军的人马排好阵势后,派了一小撮人马跑到城门下溜达了几圈,叫嚣了几声。接着,城墙上的人马开始射箭,他们的箭不偏不倚,刚好射在护城河的河岸上。将军的人马跟着也开始射箭,他们的箭射在城墙的砖头上掉下来,只有几支插进砖头间的细缝里。他们射得真准。我们啐了一口就开骂了,‘这些狗生!’我们朝山下扔石头,可惜太远了,都没扔到。过了一阵子,将军的人马走了,不知道去哪里了,也许是去另一个地方找吃的了。我们觉着无趣极了。现在轮到我们昏昏欲睡了。可是我怎么能安心困觉呢?阿爹还在家门口等着训斥我呢!”
确实,他觉着无趣极了。黄昏时分,他拄起拐杖,从田埂上站起来。天色澄蓝,云彩淡薄,天边居然出现了一轮浅月。他佝偻着身子蹒跚离去。他是背对着浅月离去的。那不是归家的方向,那是离家越来越远的方向。
他走出田埂,回头看了一眼在田里劳作的孩子们。
他以为自己已经走出了很远的路程。他以为自己走出的路程足以使他的孩子们变得渺小。当他发现他的孩子们仍然与猫狗一般大小时怔了一怔。他张望着他的孩子们,想象着他们也抬头张望他——哪怕只有一个,然后叫住他,制止他背对着月亮离去。他想象着与他的孩子们发生激烈的口角。他在激烈的口角中表明最后的念想。
“我就要走了,你们究竟答不答应我一件事?”
可是没有一个孩子抬头。他停留了一会儿。他需要留给孩子们最后回旋的时间。接着,他看到他的小孙子扑通扑通地跑过来。
“阿爷,等一下我,阿爹让我跟你一起归家。”
他探寻着他的小孙子踩过的田埂,那也是方才他踩过的田埂。他揣测着多少年前,是否曾经像他的小孙子一样在田埂上嬉闹。这时,他的小孙子牵着了他的手。他皲裂的手心顿时注入一股绵软的热流。他踌躇地眺望着仍在田里劳作的孩子们。仍然没有一个人抬头。仍然没有一个人发觉他背对着月亮离去。仍然没有一个人关心他生平最后的念想。他赌气地握紧那一股绵软的热流,继续朝前走去。直到发现那些熟悉的身影都已经变得十分渺小,才松开手。
“太心,你晓不晓得赤岸在什么地方?”
“阿爷,你都问过我一千遍啦!”
天色渐渐暗下来。他脚下的路渐渐陌生了。他的记忆被愈来愈黑的夜搅得一塌糊涂。月亮仍在背后。只要背对月亮就一定不会出错。他觉着是月光投射的影子招引着他行进。是的,那时候他是迎着月亮行进的,那时候月光带给他莫大的慰藉。而现在带给他慰藉的却是一个比黑夜更黑的影子。那个曾经在他身后被他忽视的影子。
他的小孙子的步伐越来越迟疑了。
“阿爷,我们是不是走错了?”
“没错。”
“那你是忘了归家的路了吗?”
“阿爷会找回来的。”
他抓紧孙儿的手加快步伐。他的双腿在加快的步伐中不停地趔趄。他在刚踏上一段山路的斜坡时就虚脱了。两边的茅草长得比他的小孙子还高。他的小孙子哭了。他无力安抚,急切地以野狗、蟒蛇、大猫恫吓,这让他的小孙子哭得更加凶猛。
“我要归家!”
他的小孙子撕心裂肺地吼道。树林遮蔽了月亮。树林的影子吞噬了他的影子。他在失去影子的指引后手足无措。他坐下来,耳朵里传来更多的声响。风吹茅草的唰唰声,蚊蝇扑打的嗡嗡声,焦躁的虫鸣声,潺潺流动的溪水声,以及也许来自于鬼神的寻不着根源的异动声。成群的蚊蝇萦绕周围,他不时吐出几只误入口中的蚊蝇。
他拽起孙儿的手继续上路。月光终于从树荫中走出来。他记得走下斜坡,穿过一爿稻田,就会见到村舍,就会见到渡口,就会见到停泊的舟楫。他仿佛听到了“咚咚”“咚咚”的打鼓声。他确实听到了打鼓声。还在下坡时,他就看到远处微弱的火光。微弱的火光侵入他的身体,几乎成为他久违的依靠。
他迎着火光奋力小跑了几步。几步之后,他听到了从田间传来的此起彼伏的狗吠声。一群低矮的黑影挡住了前进的方向。他的小孙子扑到他怀里,差点让他摔了一跤。他捡拾着地上的碎石,把其中几块大的递到孙儿手中。
“别怕,我们有石头。”
他挪动身子,及至和孙儿一起贴到一棵桉树背后。他被皱纹包藏的眼睛终于完全探了出来。他一手横举拐杖,一手握紧石头,时刻准备着,和一群野狗展开一场战斗。
“那时候已经没有王法了。王死了,王的儿子也死一大半了。
“那阵子连天色也变得异常,飓风潮溢之后,又是炎旱,河水快干的时候,一条条鱼跳起来,鱼随即被吃光了,田也裂开了,青蛙像泥巴一样呆板,狗趴在地上吐舌头,母鸡咕咕叫个不停。天地之间什么都干了,没有云,也没有风,万物呈现一派肃杀之气。大人们杀了猪羊,成天烧香求雨,连一滴雨也没有求到。有一天,阿爹回到家,怒怼了我一眼,说:‘看来要把你也祭了,这回龙王是非要吃个大童子不可了。’
“阿爹变得越来越烦躁,总把气撒在我头上。我回怼了阿爹一句:‘龙王还嫌我瘦呢,他要吃肚大的。’我怀揣弹弓,又拣了一把镰刀逃走了。我去找伙伴们了。我们想去山里看一看,能不能找点吃的。那时候,我们每个人都面黄肌瘦了。
“我们什么也没有找到,果子烂干了,鸟飞绝了。我们越走越深,越走越饿。再找不到吃的,就只能啃树叶了。我们太累了,只好躺下来歇息。歇了很久,谁都不想动了,连翻个身都不想。
“那伙流寇,就是在我们歇息的时候出现的。
“那伙流寇统共有二三十人。看起来,他们是逃窜到山里来的。他们衣冠不整,狼狈不堪,脸上、衣裳上、刀枪上都沾满了血。他们发现我们的时候立即神气起来,立即把刀枪架在我们的颈项上,搜我们的身子。我闻到了一股腥臊的气味,那是死去的禽兽也或许是人的气味。我瞟了他们一眼。我只敢瞟他们一眼。他们面目狰狞,目光呆滞,看起来有几天没吃一点物什了。
“那伙流寇为没有搜到一点物什暴跳起来。我真担心他们把我们给煮了吃了。他们合计了一下。他们让我们老实点,让我们带路找吃的,只有找到吃的,才能让我们活命。我们就这样走入两边长满茅草的山路,走回自己的家。我们走得太深太远了,连该怎么走出山路都记不清了。
“那股刚死去的禽兽的气味夹杂着刀锋的寒气,一直挂在我的颈项上。我感到我的人头随时会落地。我感到我的人头已经不属于我了。有一小阵子,那伙流寇放松了警惕,开始说笑,粗野地谈论着想象中的物什和女人。这时,一个伙伴突然改变方向,没入茅草中,朝一条狭小的支路飞奔而去。离他最近的流寇二话没说扔出手中的大刀。大刀没入茅草,只扎进土里。
“‘小贼厮,逮住后看我不宰了你。’流寇骂道,拐入茅草丛抽出大刀。在他回来的时候,流寇头目用刀柄撞了一下他的头:‘把老子的大刀扔钝了,看我不宰了你。’
“那个流寇哈着腰赔笑,掉头去追逃走的伙伴。流寇的头目又叫道:‘还追个屌,把剩下的给老子看好。’
“流寇头目一说完,所有的流寇都用刀柄狠狠地打了一下我们的头。捡回大刀的流寇在我的头盖上猛砸了两下,把我砸得晕头转向。
“落山的太阳伏在我们身前折射出斜长的影子。斜长的影子指引着回家的方向。汗珠从我们身体的每一个毛孔流出,可我们仍在打战。我们谁也不敢瞧一眼谁,谁也不敢瞧一眼流寇,谁也不敢从眼眶里流出泪,或者擤一下挂在鼻孔下方的鼻涕。那时候,我们只盼着快点归家,盼着把流寇带回家里,带走他们想要的任何物什。
“我们终于走到最后一段下山的斜坡。我们终于抬头张望了一眼。我们看到了一片稻田,看到了稻田外的屋宕,看到了从屋宕里透出来的微弱的火光,看到了在屋宕上升腾的几缕灰烟。我们没有看到一个人,连大榕树下也没有一个人。
“我们就这样带着一帮流寇走到了家里。
“……
“次日,逃走的伙伴回来了。他说他一夜都匍匐在山崖上。他看见村里着火了,他以为我们全遭殃了。他说一早听到女人的哭声,他才像得到了抚慰放声大哭,才连忙跑回村里。我们村的大榕树就是在这场火灾里烧死的。再也没有人去大榕树下讲闲谈了。”
他的小孙子依偎在他怀里。他不知道他的小孙子是什么时候睡着的。狗吠声越发猖獗,仿佛在撕咬夜色。他在想是否撇开孙子,投入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时间不多了。月亮来到头顶。他放下孙儿,从桉树背后站了出来。他看到稻田中间闪动着两点火光。火光一摆一摆地急促移动,接着,火光驱散了低矮的黑影,驱散了狗吠声。
“前方谁人?”
他似乎忘记了自己是谁。他只是不停地翕动着嘴唇。火光靠近他时变得十分审慎。他辨识出那是两盏灯笼。灯笼之后是一个壮年、两个后生。
“是个老人。”一个后生说。
“老人家,是迷路了吧?”壮年问。
“看,地上还躺着个小儿郎。”另一个后生说。
“老人家,这小儿郎是你孙儿否?”壮年问。
“这老人不会是得了呆症吧?”一个后生说。
壮年拍醒他的小孙子。他的小孙子一醒来又号啕不止。他双手拄着拐杖,把身体的重量全压在上面,站在风口瑟瑟发抖。他听着他的小孙子抽搐地讲出爹娘的所在。渡口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他将离它越来越远。
壮年抱起他最小的孙子。他拒绝了后生背他的好意。他跟着三人重新上路,走上不久之前刚走过的道路。他为没有纠正孙儿的说法感到悲哀。他思忖着,是否可以缓慢地后退伺机逃走?是否可以告知三人孙儿记错了归家的方向?是否可以谎称他是带着孙儿探亲而不是归家?他所有的念想都未能阻止他跟上三人的步伐,直至一个趔趄摔倒在地。
后生见状,夺过拐杖,不容分说地把他背了起来。后生为了这一刻似乎等待了很久,十根手指使劲掐住他的大腿。他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他贴在后生肩上,抬头望了一眼月亮。他没有看见月亮。曾经在他身后的月亮,竟然在他掉转方向之后,仍然在他身后。他看着三人在地上交错的影子。现在,他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影子。
“老人家,就快到了。”壮年兴奋地说。
他穿过那爿熟悉的稻田,一阵心悸。
“放我下来吧。”他哀求道。
“不行,你不能再走啦。”
后生的手指松动了一下。后生的手掌在他的屁股上摊开,把他的身子往上推了一推。他的小孙子又睡着了。他得自己告诉他们,他所住的是哪一座屋宕。
他想象着他的小儿子站在门口等他,想象着他忍无可忍的叫骂声。他困惑自己为何至今没有死去,他究竟错过了多少次死去的机会。他埋下头,把眼泪、鼻涕和哈喇留在后生的背上。他的呜咽声使三人越发感动于自己的善举。他们一定要把他送到家门口,直至见到他的家人。
他向三人指了指一扇宅门。他没有在门口看到他的小儿子。他想起来,多少年前,这里一片荒芜。
“谁能想到,有一天,将军的人马又回来了。
“这一回,将军的人马还是从海岸上冒出来,还是举着一个个火把。但这一回,将军的人马一夜之间就攻陷了城池,没隔几天,就安插到各个乡社。将军的人马再也不像从前的样子了。将军的人马头裹白巾,颈项露出文身,做什么事都齐齐整整,连表情也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将军的人马也不再抢物什了。他们一遇见生人,还会咧嘴一笑。
“如果不是遇到那个士卒,我们也不会把这支人马和将军的人马联系到一起。那一天,我们正蹲在榕树根上讲闲谈。大榕树只剩下一个榕树根了。士卒走到我们身旁时愣了愣,问:‘这里以前是不是有棵大榕树?’
“我说:‘是啊。’我心想有榕树根的地方当然有过榕树了。
“他说:‘我以前来过这里。’
“他好像陷入了回忆。他一定是想起以前偷鸡摸狗的事情,看起来很羞愧。
“他又说:‘那时你们都在榕树底下讲闲谈。’
“我说:‘那时我们还小,轮不到呢。’
“他又问:‘榕树怎么没了?’
“我说:‘前几年让流寇给烧了。’
“他说:‘以后再也没有人敢烧你们的物什了!’
“我们一点都看不出他是从前满口脏话还会撒尿互喷的人。没隔几天,士卒又带着族长公来到我家里,把我的年纪问了过去,还给我编了号。阿爹问族长公做什么事,族长公说他也不晓得。
“士卒走了之后,我跑到榕树根,想问个究竟。那时候,大伙儿还在关心将军的人马是怎么变样的,是中邪了还是被佛门点化了,还是经受了不可想象的磨炼?大家惬意地在榕树根讲闲谈。大家有几年没这样惬意地讲闲谈了。
“有一天,将军竟然也来到榕树根。将军一来,我们都跪下来磕头。将军没有想象中那样威仪,笑嘻嘻地问寒问暖,还和我们一起插科打诨。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将军的脸,也是最后一次。将军的脸真红,不晓得是喝过酒,晒了太阳,还是特意涂得那么红。快走的时候,将军说,他会上报朝堂,给我们分地,给没成婚的年轻后生分地,‘有了地,诸位就可以讨老婆了。’将军这么一说,我们都笑了。
“隔了几天,士卒带着族长公又来了,让我去大道坦集合,去分地。我就跑大道坦那儿去了,阿爹忧心忡忡地跟上来。阿爹问士卒:‘我可以替吗?’士卒说:‘你太老啦!’娘也跟出来。那时我想,阿爹要是想分地,岂不是要把娘休了?我回头瞅了他们一眼,就进大道坦里了。大道坦里站着很多后生,还有很多士卒围在外面。我才晓得,阿爹和娘进不来。我有些慌,就去找爹娘。可是大道坦上人太多了,我好不容易才挤到边上。我瞥见爹娘的眼眶里噙着泪,就没有喊他们。那时我想,反正我会回来的,是去分地又不是去打仗,地不好,大不了不要啊!
“我们在大道坦上排成一行一行。起先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后来才明白是验身。验完身,就往前走,朝海岸的方向走。从大道坦到海岸,士卒排成一条护卫的长龙。有几个后生慌了,嚷着回家,结果被摁着头押到了海岸。我看见海岸上停靠着很多船。我没作声,一味地寻着爹娘的身影。爹娘被隔在很远的地方。我没寻见他们就上了船。海上的云层压得很低,雾色苍茫,我原以为会落雨,结果船开远了也没有落……”
“阿爷阿爷,后来呢?”
“后来阿爷就来这里了。”
“阿爷,你想回去吗?”
“阿爷想回去看看咧,就是走不动啦。”
“阿爷,我们抬着你去吧!”
“你们知道那离这有多远吗?”
“阿爷,你不是坐船来的吗?我们也坐船去,不用管有多远。”
门闩打开了。他的大儿子从宅门里走出来。
他看着他的大儿子从壮年手中接过他的小孙子,看着他向三人致谢,看着他目送三人离开,看着他把小孙子抱入小儿子的厢房。他的大儿子始终没有看他一眼。他没有寻见他的小儿子和小儿媳。他站在厢房门口又打了个趔趄。在他的大儿子猛地搀扶起他的时候,他吓了一跳。他觉着自己瘫倒了。他的大儿子把他搀扶到床上,直到临出门,才说:“阿爹,就算求你,以后别再出门了。”
他翕动了一下嘴唇,缓缓闭上眼睛,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他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醒了过来的。他不知道自己究竟睡了多久。他的床头摇曳着烛光。他仿佛从摇曳的烛光里看见了许多摇晃的影子。他又翕动嘴唇,比以往更强烈地翕动嘴唇。他众多的子孙一个个把耳朵凑近来,都在倾听他在讲什么,接着又一个个摇了摇头。不久之后,烛火熄灭了。他看着他众多的子孙纷纷跪下来,哭天抢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