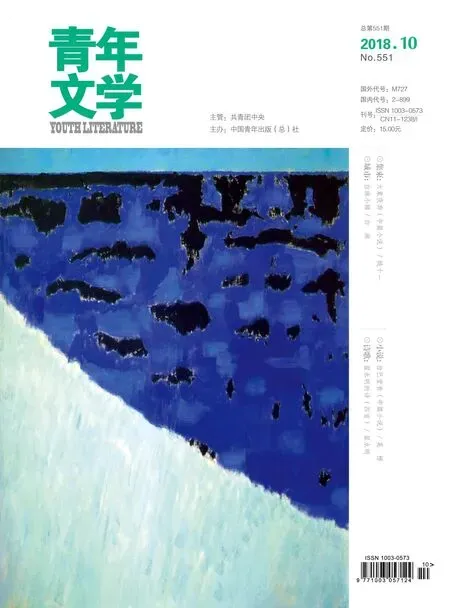直面精神的迷惘与困境
——“浙江新荷计划作家小辑”简评
⊙ 文 / 傅逸尘
浙江省作协作家扶持项目“新荷计划”实施了五年,培养了一批青年作家,在文坛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本次“浙江新荷计划作家小辑”里的六位作者:姚十一、林晓哲、叶桂杰、阿斐、星芽、李慧慧,有八〇后,也有九〇后,他们都在试图直面现代人精神的迷惘与困境。
叶桂杰的短篇小说《蜘蛛》让我一下子想到了一个世纪前发端于美国的“迷惘的一代”,这个词组最初是对美国某一代人的命名与概括,后来这个命名出现在了海明威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的题词中,于是演化成了一个文学流派。《蜘蛛》里人物的成长背景与“迷惘的一代”差异当然巨大,但“苦闷与迷茫”在他们身上的表现似乎有着惊人的相似。《蜘蛛》没有故事,只是写了一个情节,近午夜的时候,两个学生发烧,“我”(叶老师)将他们送往医院,然后分别给他们的家长打电话,让他们到医院来看护这两个学生。刘海望只是低烧,开了药也没吃;另一个学生张建则高烧打点滴,一直在沉睡中。刘海望的家长来了,他一直在咒骂自己不争气的两个儿子,然后又讲述了自己的成功与失败;张建的家长却没来。一伙骑摩托车的在医院外面疯狂飙车,不知跟刘海望是否有关系;刘海望去父亲的小轿车里睡觉时那些骑摩托车的人中有一个被打伤进了抢救室,但没有抢救过来。刘海望不知为什么在他父亲的叫骂声中跑了,刘父的车也开走了。最后,“我”把张建送回了学校。按说,“我”与两个学生应该是这篇小说叙述的中心,但作者没有着重写两个学生,却用很大篇幅写了刘父。即便如此,这两个发烧的学生仍然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通过小说中诸多的细节描写让我感受到,他们在所处的生存环境中是无法健康成长的。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呼应着写了一只蜘蛛,它象征什么呢?蜘蛛给人的印象是很恐怖的,但它又是许多农业害虫的天敌,还可以入药。那么,作者是想说现在的学生看着很不像样,甚至还有许多让人生疑或讨厌的东西,实则不然,他们就像蜘蛛一样,或者是一种整体象征,那么又象征着什么呢?象征我们的生活就像被这蜘蛛的网网住了一样?抑或,根本就没有象征这一说,就是写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什么意义也没有?
姚十一的中篇小说《大象夜奔》是个荒诞作品。在一个叫图山的地方,住在山腰的罗庄人都双目失明,住在山顶的马庄人都双耳失聪,住在山底的牛庄人都说不了话。小说重点写的是罗庄,这里的人天生就是盲人,他们是依靠每年的送神会后由神明赐予的动物来祈求获得赦免,重获光明。可是,神已经十年没将动物恩赐给他们了;因而,一头大象的突然降临,让罗庄人上演了一出剧情颇为跌宕起伏的悲喜剧。罗庄的人们只有领袖罗盲子明白这位不速之客是一头大象,他号召人们做好迎接光明的准备;于是,人们用各种方式来认识大象,接近大象。开始大家都把大象当作信仰一般对待,由专人专门饲养它,给它搭棚子、行礼;但大象并不邃人愿,几次发脾气踩踏死数十人,包括同为领袖级的人物独眼罗很大的儿子,人们转而惩罚大象,通过减少食物让大象瘦小下来。然而,一个叫小六的盲人的突然复明,又重新燃起罗庄人对大象的热情,复明的小六也成为人们膜拜的对象,大家给他送各种礼品,他也经常出入盲人家,不光拿走一两件器物,还带走女人。后来罗庄出现饥荒,罗铁匠等人准备突袭小六,但小六在人们突袭前吊在树上死了,此时的大象也已经奄奄一息。独眼罗很大似乎成了先觉者,喊出了“光明即罪恶,让光明见鬼去吧”的口号,于是罗庄的人们决定杀死大象,然后将其吃掉。小说结尾,第二天一早,罗庄的人们纷纷赶到大象的巢穴时,大象却不见了。罗庄人复明的理想是正常的人性,但围绕着复明呈现出的却是人性的堕落、精神的委琐与人格的矮化;小说着意于对人的欲望,甚至贪婪的批判,即便追求光明的崇高,仍然不能掩饰人性的狭隘与丑陋。这种带有寓言意味的写作,显然是对当下社会诸多症候的一种反讽与批判。姚十一的小说虽然也有较为丰富的细节描写,但这些细节主要局限在写人上,缺乏超越日常性、甚至人性的想象,尤其是在对大象的描写上,显得过于呆板与逼仄。
林晓哲的短篇小说《逐影》,要单纯许多,写一个老人年轻时被抓当兵,后来落户在这里,再也没回过老家。现时态中,他已经老了,却仍然惦念着回老家。儿孙们对他的这一内心的精神理想都很麻木,甚至漠不关心。于是,当孙子奉儿子之命在田间地头上叫他回家时,他却将孙子带向回家的相反方向,奔向了河边的渡口。他们遇到了一群野狗,他想拼死一搏,却被三个陌生人所救,然后被他们送回家。但儿子们对他回老家的愿望漠不关心,他终于抱憾而死。儿孙们生存在现实中,而他的愿望与现实生存无关,他的精神理想便有了凌空虚蹈的意味。小说写得很细腻,很有画面感,语言亦富于诗性。从这个角度讲,李慧慧的散文《那一抹即将消失的亮白色》与林晓哲的短篇小说《逐影》形成反差。散文写老家海边盐田的历史沧桑,以及盐场工人的苦辣酸甜。作者关注的也是人的精神层面,盐场的消失未必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实际的影响,但老味道的缺失却象征着精神与情感的消亡,这无疑是一曲绝唱或挽歌。问题在于,作者写得太实,少了点散文应有的灵动与韵致。《星芽的诗》是与动物的对话,更富于哲理的意味;《阿斐的诗》则是与人的对话,强调的是情感。
这一小辑作品对历史与现实中人的精神的关注让我心生敬意。尤其是当下,人们普遍缺失理想信仰,甚至人格品质也日益低下,这与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理想相去甚远,特别需要用文学与艺术的方式浸润和提升。人们的精神理想与人格品质的高度,关乎民族的存亡与未来。我希望八〇后、九〇后的年轻作家能带给读者一些新的、属于他们的独特的精神理想与文学经验;或者讲述一些带着他们体温与气味的故事,哪怕是为文学性所忌讳的符号化叙述也在所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