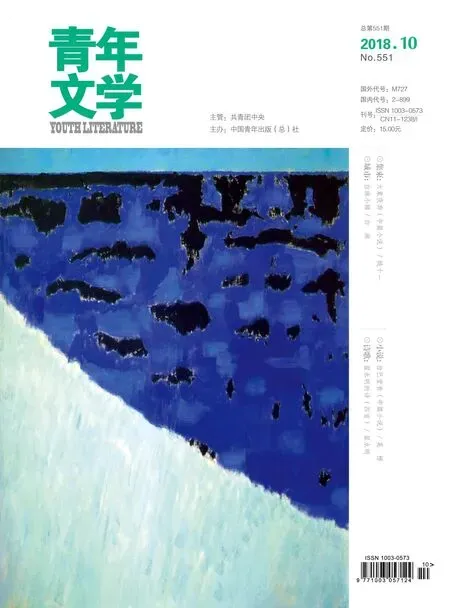吸烟区
⊙ 文 / 邱振刚
掌声渐渐歇了,那个姓丁的公共汽车司机清清嗓子,开始讲他是怎么协助警方,抓住了通缉犯的事儿。他早算过时间,离他坐到台上去,讲他的事儿,还有一个小时。这十来天,他已经把省里的十五个地级市跑遍了,他颇有些庆幸,省城是最后一站,要是第一站就在省城讲,他不知道得紧张成什么样。如今,他有了经验,只消紧盯着主席台沿上摆着的那一排花盆,一眼都不往观众席上看,看不到观众们各式的眼神,心里就会很踏实,圆圆满满地念完他的稿子。
他们这个团的发言次序,是按姓氏笔画排的,他因为姓穆,笔画多,就排在了这个五人报告团里的最后一个。领队说了,今天讲完,明天一早大伙儿就可以回家了。这阵子全省各处做报告,一直吃酒店里的自助餐,开始时还觉得新鲜,后来发现无论哪个市,哪个酒店,都是这几十样热菜凉菜,他早就吃得够够的。老婆做的腊肉蒸冬瓜,炒苕尖,想想嘴里便是一阵发潮。
这就是香烟的好处,嘴馋了,缺觉了,气不顺了,它统统能解决。他摸了摸西服上衣的左右两个内兜,一个里面是稿子,一个是半盒烟。这时,台上的丁司机讲到了他发现车上有个人,大夏天的也戴着帽子,还一直低头背着人,就假装车坏了,停下车,走到车尾看清了那人的相貌。观众席里一片安静,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一看是时候了,就一猫腰,踮着脚下了主席台,快步从最近的门走了出去。
吸烟这件事,上课时他也是这样,上午还好,到了下午,头一节四十五分钟的课上完,他趁着孩子们休息,总得抽根烟。那时,他出了教室,在旗杆下的水泥台子上坐了,燃上一支烟,一边望着对面成片成片望不到头的山,还要把下面一堂课的内容在脑袋里过一遍。等抽到烟蒂了,他这才伸脚踩灭了烟,慢慢踱回教室。教室的门上贴着张课程表,教数学、语文、音乐的,是他,教美术、英语、体育的,还是他。
乍一听,英语是那些山里的学生娃娃最用不着的课了,再说,这两年也有了政策,英语不再是必须要上的课。但他知道,自己的英语发音,是当初上大学时,从外教那里学来的,是很标准的美式发音,学生们只要跟着自己学好了,等日后到了县中,就不会被发音没那么标准的老师带偏了。
他从前到县中上过观摩课,各科都上过。他知道,自己语文和英语都比县中的老师讲得好,反倒是数学,虽然是自己的本行,但因为没那么齐全的新式教具,课上得不够生动。
出了这间多功能厅,他沿着走廊远远一望,就望见了大堂,他脚底下就渐渐快了,脸上不由得漾起了笑。这一阵子,因为在省里到处走,住惯了酒店,他有了经验,知道这样的酒店,一定会在大堂里有块吸烟区。
穿过走廊到了吸烟区,他安心坐下,掏出打火机点燃了香烟,深深吸了一口,这才透过烟雾,朝周围打量着。这个吸烟区不小,有三四张沙发,有单人的,也有三人的,已经零零散散坐着几个男人,每个人都在仰着脸吞云吐雾。他又吸了一口,接着把烟盒摆着茶几上。吸烟的人嘛,总免不了瞄一瞄别人的烟。对于自己的烟,他是有自信的。他不用还房贷车贷,花钱的地方少,再说这几年工资也涨得不低了,学生们呢,他们家里也靠着开农家乐、买卖山货,收入多了,不用他帮着垫书本费,他这才有钱买些好些的烟了。
面前的烟雾越来越浓,他的,旁人的,混在了一起。他扭头看着窗户外面的马路上,已经过了九点,省城的早高峰还没过去,公共汽车,私家车,送外卖的摩托车、电动车挤满了路面,一道道黑灰色的尾气搅和在一起,人行道上的行人,都在捂着鼻子快步走着。他又开始想念山上蓝汪汪的天了。
他把客人一直送到酒店门口,看他们上了出租车,却不愿马上就回到房间里。那所大学给他订住的是套间,还是那种三间的,最外间是会客室,有真皮沙发、高级茶具,墙上挂着五十英寸的电视,中间那间呢,算是书房,给预备着最新款的电脑,卧室在最里面,床大得像篮球场,地毯足有一寸多厚。这样的房间,住起来已经够舒服了,可他因为讲座临时取消了,尽管讲课费一分钱不少,但心里仍然很不痛快。最近这几年,他每逢暑假就会回国,美国大学的暑假又足足有三个月,国内的省会,他早就已经都跑遍了,重要的地级市也去得差不多了。这次呢,这所大学想请他来做次讲座,本来他都答应了别处,想到这是家乡的学校,也就答应了。可这大学呢,两天前有个副校长被查出有经济问题,校内一切非教学的活动都被暂停,他的讲座也就没法再开了。刚才,就是校办主任带着会计来给他送讲课费。毕竟,他是国际知名学者,受过不少领导接见,学校方面不敢怠慢。当然,讲座取消的原因,人家是不会给他这个外人说的,只是笼统地编了个说辞。
他回到大堂,抬起手腕看看表,琢磨着这突然多出来的半天空闲怎么打发。他瞥见有服务员正给吸烟区的报刊架上换了一批新刊,就信步走过去,坐下,拈起了一份杂志。
陈黎?
他刚打开杂志封面,对面传来一个声音。他没想到这里有人认得他,抬头一看,只见对面是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指间夹着支烟,正朝自己笑着。这人西装的垫肩早撑离了肩膀,领带也打得有些歪斜古怪,一个干瘦黝黑的笑脸正对着自己。
但这和气的笑,瘦窄的脸,他却是熟悉的。
你是,穆秉堂?陈黎说。
穆秉堂点点头,拿起烟盒,拈出根烟递给他,说道,刚才你一出电梯,我就认出你来了。知道你忙,正犹豫要不要过去和你打个招呼,你就过来了。
他们是县中同学,从高一到高三,整整三年的同窗。高考那年,陈黎考进了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穆秉堂却只上了本市的师专,学的是数学教育。两年后毕了业,穆秉堂却没去当老师,而是顶替突发脑溢血死在一大摞账本上的父亲,进了县供销社当会计。九十年代初的那些年月里,人人都想当大款,个个都在开公司,满大街都是拎着公文包的人在公共汽车上挤上挤下,看大门的大爷都知道螺纹钢多少钱一吨。他心思也不在公事上了,和一个同事合伙做起了生意。没多久,他就闯了祸,从外地买来的一批化肥卖给本地农民后,被农民举报是假冒伪劣。他被从供销社开除了。他也没当回事儿,还觉得自己终于自由了,当天就买了卧铺票去了深圳。在深圳,他前后待了五年,曾经和很多人一样赚到过钱,可很快又失去了,还被债主雇人打断了肋骨。消息传回老家,母亲急得住进医院,他只得回来照料母亲,就是这个时候,他从老同学那里听说,陈黎有了大出息,大学毕业后考进社科院读经济学研究生,去年毕业了,又公费去了美国念博士。
母亲病得不轻,在进手术室前扯着他的手,求他别去旁处折腾了,好好在县城找个事儿。那时,他在深圳还欠着别人一万多块钱,反正也不敢回去,就答应了母亲。当时,县城的边边上有一所小学招老师,虽然是民办的,但他没别处可去,只得去应聘了。当了几年孩子王,才把当初的欠债还完,这时候,学校里竟有了转为公办的指标,要求是先进。先进不是那么好得的,要有工作表现。他想到了一招,就是去那些家境差、住得偏远的孩子家里家访。正好他班上有个孩子,住在离县城三十里的山里。越远越好,知道了这个消息,他心里还挺高兴,就找了个周六去了。他先坐着长途车到了山下,接着又等了三个小时,才等到回山的老乡,坐着他们的三轮车进了山。
他没能实现当天返校的计划,到了周日深夜才回来。他把自己在宿舍里关了两天,该上的课也都请了假。两天后,校长正要去找他,他走进了校长的办公室,说要辞职,进山当老师。那校长当时就蒙了,停了半晌才叹口气,走过去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如今,二十二年过去了。那学校,由一间土坯房变成了三大间砖房,有了正儿八经的操场,水、电,也早通了,但教师还是只有他一个。这么多年,学生最少时有三个,最多时是十一个。这些年里,这所学校所有的课,都是他一个人教的。
陈黎问,你来省城,是出差?
他嗯了一声,把这个先进事迹报告团的事儿简单说了说,又问,你一直在美国?
陈黎点点头。
他说,我一直在山里当老师,你们都奇怪我怎么会去山里当老师,又怎么会一待就是这么多年吧?
陈黎说,你去山里,是我去美国第二年,后来,有别的同学去美国,我们的确说起过你,都挺纳闷儿。我还记得你刚师专毕业时,去的单位挺不错的。
他说,不光你们没想到,我自己都没想到。其实,当初刚上山,就是觉得那些孩子没法上学,太可怜了,我也没想到会在山里待上二十多年。
他还记得当年上山家访时,那学生家的门上却挂着锁,他不甘心白跑一趟,在门口坐下等。可他等了两个多钟头,抽掉了一整包烟,仍然没人回家。他怏怏的,正要下山赶最后一班车,山路远处出现一支手电筒的亮光,一个五十出头的矮瘦汉子牵着他那学生过来了。他有些纳闷儿,这汉子从年纪上看,在学生的父辈和爷辈之间,相貌却毫不相似。原来,他是本村的支书,算起来也是学生的表叔。他说,学生的父母都去了外地打工,平时衣食都托付给自己照料。支书见他是老师,马上一阵长吁短叹地诉苦,说这村子里,一共六个该上学的娃子,可只有这个田宝,年纪大到能自己去县城上学,旁的娃子,就只能在山里混日子。山里本来也有个学校,可连来几位老师都没留下,最长的待了仨月,最短的一个,站在教室外撇撇嘴,直接就下山了,学校也就这么荒废了。他这晚在支书家睡了,第二天就去另外那几个娃子家里看了看。等看到第三家,还没去看那学校,他就知道,自己下半辈子,指定就交付给这里了。
他说,刚上山头十年左右的时间,山里的确艰苦。说是有个学校,实际上就一间漏风透雨的土坯房教室和一间兼做厨房的宿舍。就连黑板,都是他从山下修路的工地上,找工人要来废沥青在墙上刷的。
陈黎扬脸看着他,说,我上网查过,关于你的新闻真多,有的新闻里说,你有不少学生,各种费用都是你给交的。
他嘿嘿笑了,说,啥各种费用啊,无非书本钱而已,那也没多少钱,反正在山里过日子,自己的工资,想花也花不出去,就给学生买课本,买书包了。他说,自己其实一点儿不亏,学校没院墙,教室墙根下就是菜地,各种蔬菜都有,他想吃什么随便摘,老乡也不肯和他算钱。至于工资,村会计每回都是到了日子就把那一沓薄薄的纸票子给他送来。他基本上左手进,右手就又还给了会计,因为村会计三天两头地要下山进城,他要托村会计给学校带粉笔、练习簿之类。后来,山里的条件慢慢好了,家家户户都开了农家乐,一到假期,每家住满了城里来的客人,也就能供得起自己家孩子读书了。从那时起,他的工资也就慢慢攒下了。他也靠着学生家长帮忙,在自己宿舍旁边建了几间房子,开了农家乐,到了节假日,就陪着天南地北来的客人往山沟里钻。
他就是因为这个机缘,才出了名。
当时有个客人,离开后没几天就带着一个助手回来了,两人一人一部摄像机,硬是跟着他,拍了他两个月。拍出来的那个片子,后来在国际上得了纪录片奖。他看片子时简直惭愧得要死,恨不得把头往旗杆上撞,片子里面把他开农家乐、带着学生在操场上晾晒山里红和葛藤干的事儿都拍了进去。他这一出名,很快,记者从全国各地都来了,都要采访他。他越发惭愧了,他知道,这片山的更深处,还有两个比这里条件更差的学校,那两个老师,在山里的时间比他更长。他嗫嚅着,把这事儿给记者们说了。他本以为,记者会马上扔下他,去采访那些老师,想不到,记者还是围着他团团转。再往后,他得了各种各样的奖,评上了各种级别的先进,还参加了如今这个报告团。前不久,县教委派人上了山,递给他一沓材料让他填。填完表,他就成了公办教师,终于,在二十八年后,他重新成了公家人。
县里还给他补发了工资,竟有八万多块钱。
他说,省城还有好几个同学,田海勇,马婷,朱晓荣,宋爽,都在。
陈黎知道他的意思,摇摇头说,我下午三点就要飞到香港,否则,可以和他们见个面。
他指了指茶几上的手机,说,上山之后,这些年我一个同学没见过,但同学们的情况,我倒是基本都知道。陈黎笑了,说,微信里有咱们班的同学群?
他点点头,说,我拉你进来?说罢他拿起手机,看陈黎脸上有些犹豫,就停了手,把手机放回茶几上。
陈黎知道自己有必要解释一下,就说,自己本来也在大学同学的群和研究生同学的群里,后来都退出来了。因为老有人让他帮忙写申请留学要用到的经济担保信,还有找工作的推荐信。在美国,这些信虽然没直接的法律效力,但是,美国是个信用社会,如果被推荐人和推荐信里的情况不相符,自己是要受影响的。等到真正想推荐自己看好的年轻人时,对方就会怀疑。
他点点头表示理解,又说,我也有个儿子,不过学习不行,凑合着读完了初中,无论如何不肯再上高中了,现在正在外省一个技校学汽修,看来是没机会请你写担保信了。
陈黎说,你结婚的事儿,到美国去的同学,倒是没怎么提起过。你的是儿子?我的也是。
他说,这孩子不是我亲生的,是孩子他妈带来的。
当初,他每逢周末就下山回县城看望母亲,在山下等长途车时,常在路边一个面铺子里吃碗面。那面铺子,是个单身母亲带着一个小男孩操持着,他不赶时间的话,就帮着干点摊煤饼、收拾炉灰的事儿。后来,他母亲去世了,他周末懒得回城,就都在山上过了。有个周六下午,他去一个学生家里帮着修房顶,天黑透了才回到住处,发现四下里都收拾得干净整齐,灶台上还摆着冷透了的饭菜。他还以为闹了鬼,后来听山里人说,见到过山下那个开面铺子的女人去了他那里,里外忙了一整天。那人还没说完,他就偷偷乐了,到了下个周末,他带着一口袋山货下了山,两个月后,就和那女人领了证。
他说,前段时间微信群里好像有哪个同学说过,你儿子挺有出息。
陈黎说,凯文——我儿子叫凯文——去年拿了牛津大学的一个奖学金,去那里读书了。这个奖学金项目还可以,每年全世界才有十来个人入选。
他说,你儿子去那么远的地方,夫人放心吗?
陈黎淡淡一笑,说,夫人嘛,早就分居了,只是赡养费一直谈不拢,谁又都不舍得花钱雇律师打官司,也就一直这么样过。
他觉得有些尴尬,后悔问这个问题。陈黎也想换个话题,就说,你知道秦老师现在在哪里吗?
陈黎说的,是他们当时的语文老师。他想了想,说,当初咱们那一届刚毕业,秦老师不就从学校调到县委了吗?我好像听说过,他也来了省城。
陈黎说,秦老师到了县委后,开始是写材料,后来就变成县委书记的秘书,县委书记官当得越来越大,一路升到省里,秦老师也一直跟着,拖家带口搬进了省城,这些年一直在机关里待着。三年前,秦老师也退休了,去了美国投奔儿子。
他问,秦老师也去了美国?你们住得远吗?
陈黎说,远得很。秦老师的儿子在硅谷的电脑公司里搞研发,一家人都住在湾区,自己任教的那所大学呢,在新英格兰。陈黎看他的神情似懂非懂,赶紧说,这两个地方,一个在美国东海岸,一个在西海岸,在中国就跟从上海去新疆那么远。秦老师的儿子是极限运动爱好者,秦老师在美国适应得很快,也喜欢上了攀岩、狩猎什么的。
说到这里,陈黎拿出手机,划拉了一阵子后找出张照片给他看。只见照片上有两人站在一条河边,河水流得很急,远处是一大片雪山。两人都穿着橙红色的登山服,都被墨镜挡住了半张脸,脸上也都被晒得黑黝黝的。照片上最醒目的,是两人每人提着一条硕大的鱼。
他看了好一会儿才看出个眉目来,笑着说,你和秦老师的衣服一样。
陈黎说,所有的颜色里,橙红色是最醒目的。凡是玩儿户外的,都穿这颜色,为的是万一失踪迷路,便于救援者发现。
这两条鱼,真大。他说。
一个四十磅,一个三十七磅。怀俄明州是全美鲑鱼垂钓的圣地,这种分量,在那儿算是普通的了。
怀俄明州?这个地名,对他是完全陌生的。
陈黎又笑了,说,怀俄明州,是美国人口最少的州,地广人稀得很。黄石公园,你知道吧,中国人去美国旅游必去的景点,就在这个州。他说,前几年有一次年度体检时,他查出患有重度脂肪肝、神经衰弱、颈椎关节炎等一大堆毛病,医生看了体检报告,说他不用吃任何药物,换个生活方式,别整天坐在电脑前写论文就行。正好他也有这个心思,就找了个地产经纪人在怀俄明租了一块地皮,盖了间木屋。那个地方,没自来水,没电,没公路,更没网络,就靠一部卫星电话和外界联系。当初自己就带了一根钓鱼竿,一小袋盐,一箱子野外压缩干粮,开着自己那架小飞机就进山了。那地方最热闹的时候是半夜,因为到处是狼叫。白天反而什么声音都没有,方圆几十里都没个人影。
他说,在那里住的第一天早上,我推开房门后往外一看,哎哟妈呀,吓了一跳,外面到处是狼粪、熊粪。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月,每天就干两件事,白天钓鱼,晚上睡觉。回到城里后再检查身体,体重竟然增加了,尤其是体脂率,比进山前还高了一大截,医生脸色难看得要死。后来我才明白,是因为河里的冷水鱼脂肪含量极高,哈哈哈。
你都有飞机了,多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他说,语气里满是羡慕。
陈黎在烟灰缸里按熄了烟蒂,又摆手拒绝了他递来的另一支烟,说,只不过一架单引擎小飞机而已,只能装两个人,行李舱比汽车后备厢还小,是很普通的交通工具,在美国就连工薪族也买得起。倒是因为考飞行执照必须上够足够的课时,耽误了不少时间。
他琢磨着陈黎刚才的话,心里有些纳闷儿,美国还有那么偏僻的地方?他想了想,从手机找出张照片,拿给陈黎看。陈黎盯着屏幕上那一片被云海包围缭绕的峰峦,眼睛也亮了,赞叹说,风景真美,拍得也好,不亚于专业水平。我在老家也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真不知道还有这么漂亮的地方。
你真有眼力,这就是专业人士拍的。他说。去年有个电影摄制组派了个副导演来山里取景,那副导演吃住都和他在一起,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背着相机出去拍晨雾。后来,副导演下山前告诉他,已经把照片发给了导演,导演很满意,过段时间整个剧组就会上山来拍电影。他等了半年,也没等到人,最后,副导演给他来了邮件,说有个邻省的森林公园出了赞助,电影就在那里拍了。
他说,你在美国,算中产阶级了吧。
陈黎点点头,算吧,但比秦老师的儿子差远了。
他有点不明白,说,他不也是给老板打工吗,难道比大学教授还有钱?
陈黎说,秦老师儿子有那个公司的原始股,现在市值上千万美金呢。按说他都实现财务自由了,手里股份换成钱的话,几辈子都花不完,可如今还在设计芯片,完全是出于兴趣。他去年卖了点股权,在佛罗里达和法国戛纳都买了海边别墅,就是给秦老师养老用的。
他说,秦老师真有福。陈黎沉默了几秒,又接着说,过几年,自己可能要搬去香港长住。
你要从美国去香港?他问。
陈黎说,不是移民,光是去担任教职。我下午去香港,就是和对方谈具体待遇的。这几年,从美国去香港教书的,挺多。香港的大学,给教授的薪水比美国还高。在美国,哪种水平的教授能拿多少薪水,基本上都是明码标价的。香港给这些从英美国家来的教授,薪水会比原来高很多。更关键的是,香港和大陆的联系也更紧密。中国大陆是现在全世界机会最多的地方,尤其是这几年,大陆有不少大型国企,还有一些民企都在积极并购海外企业,这种时候就格外需要我们这样有海外背景的经济学家提供意见。
机会,这样的词儿,前几年还能让他心里动一动,如今,他早没了这心思。现在,他最大的心思,就是把大山深处那两个学校“并购”过来。要不然,那两个学校的老师年纪都大了,学生随时可能失学。那个近点的学校还好办,可那个远一些的,因为和自己的学校分属不同的地级市,事情还不好办。
其实,他不光操心哪个学校办不下去,要是有学生自己不想上学了,他也是惦记着的。每年刚过完春节,从初五开始,他就在山下长途汽车站转悠,看有没有他的学生坐长途车去外地打工。有一次,有个学生铁了心不再读书了,索性从另一条更远的山路下山,绕道进了县城。他得了消息,跑去县城的火车站找人。他万万没想到,在候车室里找到的,竟然是他最看好的学生,其实,这学生两年前就从他手底下毕了业,如今县中上到了初三,凭他的成绩,半年后考上县中的高中部,肯定没问题的。当时,那学生正蹲在候车室暖气片跟前吃桶面,一看见他,吧嗒一声,桶面连汤带水都摔在地上。他看着那学生,责备的话,劝告的话,都噎在嗓子那儿,还没说话,就哭了起来。那学生就和他一块儿哭,眼泪一滴滴落在地上那堆面里。后来,那学生还是走了,过了几年,这学生给他发邮件说了在外地上了自考,就快要拿到专科文凭了,他这才觉得心里安生了很多。
陈黎看他有点走神,轻声说,等你做完报告,咱们一起吃个午饭?酒店顶楼就是个旋转式自助餐厅,我住的是套房,能拿房卡带个人进去吃饭。
他回过神,摇摇头,说中午会有省教育厅的人请我吃饭,我本来最怕和不熟悉的人吃饭,可他们说我是这个报告团里唯一一个教育口的人,再说我也想趁着这个机会问问,能不能让旁边那两个学校的学生,来我这个学校上学。
陈黎听他把山里另外那两个学校的事儿说了,琢磨了一会儿说,你们不是不在一个市吗,这恐怕不容易。
他说,是啊,按照现在的政策,学生的学籍是跟着户籍走的,不鼓励他们离开户籍所在地去上学,即使最后能有个上学的地方,到了升学时也不好办。
陈黎说,你现在这么有名,你的话,对那些管教育的人应该管些用。要是我的话,就聘你当那个学校的校长,公章也交给你,这样一来,那几个孩子,虽然实际上在你这里上学,学籍还在原来的学校,真正的问题不就解决了?
他越听,眼瞪得越圆了,说,这么好的主意,我怎么没想到!你对国内的事儿,还真熟悉。
陈黎见他激动得脸上泛红,也有些得意,说,我常关注国内的情况,再说,也常听秦老师说国内的事儿。
他的手机响了起来。他低头看了看屏幕上的闹钟图案,说,哎呀,该我去讲了。陈黎拿出张名片,塞进他西装上衣口袋,说,多联系啊,说不定我哪天还要去你那里住几天呢。
有空回去看看吧,县城和乡下,变化都挺大的,咱们学校,变化最大,以前就一个楼,现在一大片!他说着,挥了挥手,快步沿着走廊往多功能厅走去。
陈黎望着他的背影,见他脑后的头发已经相当稀疏,想起这些年,有过几个当初的同学去美国出差时和他见面,每次都聊起穆秉堂,对于他在山里一待就是这么多年,都说没想到。他自己当时也说过,“老穆说不定早后悔了”。这几个同学,都发展得不错,否则也不会有去美国的机会。但是,他们都有后悔的事儿,比如当初应该跟那个而不是这个领导之类。现在,陈黎知道了,和他们不一样,穆秉堂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哪一步后悔过。想到这里,他心里有些嘲笑自己那时的多虑了。
穆秉堂在走廊尽头消失了,他把心思转回到自己身上,打算回到房间收拾好行李,简单吃个午饭,就去机场,搭乘那班飞往香港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