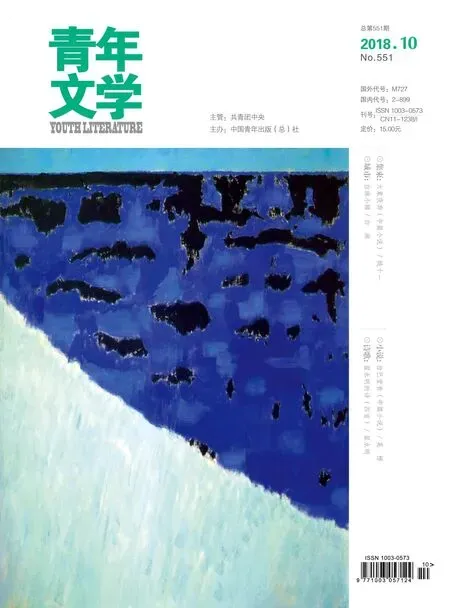蜘 蛛
⊙ 文 / 叶桂杰
那天晚上,我依稀记得洗漱完毕后正要发微信给妻子问问家里情况,一个电话打来了。是同事。又是那个同事。我把手机夹到耳朵和肩膀之间,坐到椅子上,脚抬到桌面上,对着台灯用指甲锉锉脚指甲盖。窸窸窣窣,窸窸窣窣。
“什么事?”我问。
“喂!喂!听得见吗?”手机里喊。
“你说吧。”我说。
“喂!喂!叶老师,听得见吗?”手机里喊。
“你说……你说呀……快说!”我说。
“你的学生刘望海又发烧了。很虚。你快来。马上来。”手机里继续喊。
“几度?”我问。
“嘟嘟嘟嘟……”我听到手机里传来拖鞋走在楼梯上的踢踏声,但是没人回应我了。
我从窗户望出去,只见在楼下的街道上,一辆摩托车从耳朵背面很远的地方开过来,轰鸣声渐强。我把手伸出去试探气温,时间已是夜里十点多了,天很黑,空气很冷。窗外街道两旁的路灯怪异地瞪着眼睛,射出疲软的光。几个小混混在五金店门口叼着烟。五金店的卷门拉着,二楼的房间亮着灯。一个上身赤裸的男生从阳台往下看。
“你要穿几条内裤啊,去你妈的!”下面的人嘻嘻哈哈,骂骂咧咧。他们的声音在空荡荡的街道上显得特别响。骑摩托车的男生用前轮一遍一遍地拱着行道树。摩托车哒哒哒地闷响,树下栽着大葱的泡沫箱被轮子碾碎。沾了黑土的轮子在水泥地上画出一个爆炸形状的图形。
我把身子从窗户上收进来,穿衣,围脖,套裤子,勒皮带。我俯身拎起运动鞋的时候,一只毛茸茸的黑棕相间的条纹蜘蛛从鞋里面爬出来,在鞋面上停顿了一下,大概是被鞋带绊住了。然后它旋转了一个钝角,溜走了。
我被这个意外吓了一下,想要换双运动鞋。想想又算了。我坐着套好鞋,猛地跳下床来,眼前白亮亮的,顿时闪过蜘蛛被踩扁、体液四溅的画面。我的心脏一紧,约莫是受到了刺激。我迈开脚步,越走越快。每次鞋子着地,我都感到脚底下毛茸茸的,水淋淋的,黏糊糊的,同时耳朵里响起吱吱吱吱、带着腥味的声音。
“呀呀呀呀呀……叶老师来了。你看叶老师终于来了。我就说你们的叶老师肯定会来的。他怎么会不来呢,他肯定会来的……”在男生公寓的一楼大厅里,同事兴奋地攥住我的衣角。
刘望海套着一身羽绒服,瘫坐在板凳上,身子软在墙角。我看他两手努力地撑住大腿,脑袋垂在脖子上。同事说他已经39℃了。按照我的经验,不可能。
“值周领导知道吗?”我问。
“知道。陈校长刚来过,说是让我在这儿看着他。他去女生公寓巡逻了。回头还会来的。陈校长说……”同事说。
“联系过他爸了吗?”我问。
“联系了,他说马上就来。他爸是热心肠,才打了五个电话就打通了。他爸说他还在下山的路上,到了县城,马上就赶过来。他爸说……”同事还要说,但是我很不礼貌地打断了她。
“什么时候联系的?”我问。
“多久前联系的?”我纠正了我的问话。
“一个半小时了吧。”同事说。
我看了一眼我的同事。她察觉到我看她的目光,有些惊讶,张开嘴打算要辩解什么,却又不知该说些什么。她多半意识到自己哪里做错了,却又不甚清楚。我摸摸刘望海的额头,有些烫,或者说,不很烫,或者说,很不烫。我的脑子里一团糨糊,形容词和副词搅成了一坨烂泥。他的身子有些发抖,可是我也在发抖。这一楼的大厅实在太他妈冷了。
“怎么样?”我问他。
“很难受,想吐。”刘望海说。
“等你爸来了带你回去吧?”我说。
他很吃力地点点头,却又摇头。
我硬是让他重新量了体温。38.5℃。或者说还差一点。我心里哼了一声。
“要不先回床上躺着,说不定被子捂捂就好了。我给你再找条被子。”我说。
“我跟我老爸说了,我想去医院看看。”他说。他说完就发抖,使劲儿抖,把凳子摇得吱嘎响。
我叫了120。
我掰开大厅的玻璃门,锁门的铁链哗啦啦响,然后咣当一声掉在地上。我踩着铁链乒乒乓乓地走出公寓楼。外面一片漆黑,犹如鸿蒙未判之时。公寓楼后面靠着连绵的大山。山上多有坟墓,夏天的时候坟上会闪烁磷火。山与公寓楼之间是一个露天的游泳池。游泳池的水是从山上引下来的。但现在游泳池是干的。两年前的一个夏天,学校食堂的一个女员工在非开放时间爬进去游泳。然后,滑进了深水区。然后,然后就没然后了。同事们将她捞起来的时候,她的身体胖得像一头猪。
我点了一根烟,吐了两嘴。陈校长打着手电过来了。我递了一根烟给他。他没要。我就知道他不会要的。我就把烟架在耳朵上。他问我刘望海怎么样了。我说没事。他说哦。他把手电筒的光束透过玻璃门在刘望海的脸上扫了扫,然后问:“叫120了吧?”我说是的。他说:“那就好。救护车来了,你带他去看看,我再去教学楼转转。”
我没回答他,因为一口浓烟含在我嘴里。我用鼻腔徐徐地喷着烟,望着他手电的光在水泥地上一左一右地摇,然后就摇出了校园,溶解在校外的夜色之中。我把烟从耳朵上摘下来,放回烟盒子。
我就知道他是不会要的。
快到十一点,救护车开进了校门。两个医生把刘望海搀进车。车内的灯光很暗,空间很逼仄。医生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也许说过,但我没听见。我的意识被浓重的睡意胶住,那根烟并没有弄醒我。我是第一次坐救护车。去年的一个冬夜,我女儿生了一场大病,全身盗汗。但是我不在家。我妻子独自一人骑着电瓶车带她去医院。那时候还下着大雪,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层。她的电瓶车在雪地里翻倒了。那以后,妻子一个星期没跟我讲过话。
救护车开到校门口,摁了五下喇叭。保安披着大衣,迎着寒冷走过来,敲敲车门。我摇下窗户。
“是我。”我说。
保安伸长脖子,往车厢里探探,说:“又是这个胖子呀。”
“怎么?”我说。
“刚没多久他还说要出去呢,我没准许,差点让他溜了。”保安说。
“这也不是第一次了。”我说。我不想多说。我太困了。强悍的睡意快要把我掀翻了。
“是的。这也不是第一次了。”保安说。保安摇摇头,收紧棉大衣,走回保安室。然后铁拉门移开,救护车开出校门。
我盯着刘望海,刘望海望着我。我感到脚背上痒酥酥的,仿佛有只蜘蛛爬过。我心里一毛,于是把脚板抽回来。我低头去看,原来是刘望海的鞋子踩住了我的脚背。“对不起,老师。”刘望海说的时候,脸上发出狡狯的笑。他把笑收住了。他以为我没看见。但我什么都清楚,只是我太困了。
车开出没多远,一个电话打来。是我的同事。又是那个同事。我敲了敲驾驶座后面的挡板。救护车停下来。
“什么事?”我问。
“喂!喂!听得见吗?”手机喊。
“直接说!”我说。我差不多是吼着说的,但我并不想吼。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吼出来了。
“张建是你们班的吧?他也发烧了。”手机里喊,“高烧。你们快回来,把他也带去。”
“几度?”我说。
“嘟嘟嘟嘟……”听到拖鞋在楼梯上的踢踏声。
两个医生同时把目光投向了我。我又敲了敲驾驶座后面的挡板。喇叭鸣响。铁拉门打开。救护车开进了校门。铁拉门关上。我给张建的父亲挂了个电话。电话一直响,没人接。我给他母亲挂了一个电话。电话响了很久,终于接了。
“您好,我是叶老师。”我说。
“什么事?”手机里人声嘈杂,伴随一片清脆的声音。
“喂!喂!听得见吗?”我说。
“你谁呀?”手机里哗哗哗响。
“您好,是张建家长吗?”我说。
“是——自摸!”手机里传来欣喜若狂的尖叫,手机从我手心跳出去,在皮椅上发出“嘟嘟嘟嘟”的哀鸣。
我在家长群里发了条微信:请张建父母马上联系我。急!急!
张建穿着薄薄的秋装校服,身体止不住发抖,像个筛子,牙齿打着磕,嘴唇发紫。我摸了摸他的额头,很烫,非常烫。同事说他有39℃了。按照我的经验,可能还高一点。我们把他从板凳上扶起来的时候,他就像一抔细沙要从我们指缝间流下去。我们把他架到车旁,他挣扎起来,大喊大叫。
“你说什么?”我问他。
“我不去医院。老师,我不去医院。”张建气喘吁吁,声音混沌。
“为什么不去?”我说。
“我躺床上,被子捂捂就好了。”张建说。
“我妈说生病了,被窝里闷一闷,出点汗就好。”张建说。
“我明天就会好的。”张建说。
“我不去,我不去医院。”张建挣脱我们,像一根细细的沙粒线流到了地上。
“都烧成这样了,还说不去呢。”我们把他扶起来,弄进了车。我把车门砰的一声关上,示意驾驶员出发。张建还要抗议,但是被我摁住了。我的脑子变得清醒,回光返照似的,白天的威严已有所恢复。
“必须去。”我说。
救护车一驶入街道,就打开了警报器。街上没人,也没车。警报是多余的,在这个寂静而寒冷的冬夜。但是没有警报,车里的人更是多余的。从村路拐进县道的时候,一辆摩托车一声轰鸣从后面追上来,然后稳稳地与救护车保持同样的速度。我透过车窗望出去,那个坐在摩托车后面的年轻人正冲着我们的车厢挥手。在他后面,还跟着长长的一串。它们紧紧地跟着,不急也不缓,保持相同的车距。每辆摩托车上坐着两个人,坐在后面的,有的挥手,有的打口哨,有的甚至扶着驾驶员的后背站起来。它们高大的轮子在地面上疾驰,哗——快一下,哗——慢一下,像潮汐似的,听得我脑海里一浪翻出一浪。
我望望刘望海。刘望海垂着头,嘴巴抿着,嘴角上翘,想笑。
我又给张建的父亲挂了个电话。
“嘟——嘟——嘟——”
“喂!你谁呀?”
“您好,我是叶老师。”
“嘟嘟嘟嘟嘟嘟嘟。”
我重拨。
“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
我又重拨。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您好,我是叶老师。”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您好,我是叶老师。”
“您好,我是叶老师。”
“您好,我是叶老师。”
……
刘望海的父亲赶在我们前头到了医院。我们从救护车上下来,刘父也从车里钻出来。他那辆黑色的大众,轮子和底盘沾满泛白的烂泥巴。刘父从呢大衣里掏出一盒软盒中华和一只打火机,一瘸一瘸地向我走来。
“叶老师,真是辛苦你了。我那兔崽子没一天是省事儿的。”刘父笑着,给我递了一根烟。急诊大厅门口的灯光很暗,抹在他嘴上,黑黑白白黄黄红红,一口烂牙。
我把手一挡。“我不抽烟。”我说。
我们把张建从车上搀下来,刘望海自己跳了下来。我扶着张建,刘父带着刘望海,我们进了急诊大楼。
刘望海低烧,医生开了一盒药。刘望海揣进兜里,不吃。张建高烧,医生开了三袋注射液。我举着输液袋,把张建带进了输液室。
药水在输液器里一滴一滴地滴下来,速度很慢。我把张建的校服拉链拉到领口,衣摆塞进裤子。我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椅子是成排成排的,冰冷,生硬,令人反胃的绿色。
输液室里人很少。一对老夫妻,老头挂水,老伴儿陪护。
刘父从外面走进来,一瘸一瘸。刘望海跟在后面。刘父坐到我旁边。整排椅子砰地塌了一下。
“唉唉,真是兔崽子,一点点毛病就来事。”刘父说。刘父把一条腿架到另一条腿上,指着刘望海:“你那点点头疼脑热,床上躺一躺就得了,用得着来医院吗?”
刘望海不吭声,笑笑。他从他父亲衣兜里把手机掏出来,坐到墙角的椅子上埋头玩。
“不舒服总是要看看的。”我说。
“小洞不补,大洞受苦。”我说。
“我像他那么大的时候,什么大病小病没经历过,几回去过医院?从小到大,我打过十次针吗?十次都没有。我操他蛋的,养了这么个兔崽子,没一天不欠揍。”刘父说。
好像很生气。
“这个同学怎么样?家长还是联系不到吗?他哪里人?”刘父问我。
“凉州人。”我说。
“关机了。”我说。
“他们知道我的电话。”我说。
“阀门厂上班呢。”我说。
“赶过来要一个半小时呢。”我说。
“早就没车了。”我说。
“出租车都没有。”我说。
我看了看时间。“十一点四十七分了。”我说。
“哦。哦。哦。”刘父说,“我那年也是跟他妈在阀门厂上班,把他哥一个人撂在老家读书。都没个照应。”
我没回应他。我在专心给妻子发微信。我说我在医院。我说输完液可能很晚了。我说女儿怎么样了?妻子回复说,你说呢?我说我不知道。妻子没回。
“我那大儿子,也是个兔崽子,就没让他老师省心过。有一次撬开他奶奶家的锁柜,拿走了两万块钱。连着五天不回来,把他奶奶急的。”刘父说。
“去网吧了?还是KTV?还是台球室?”我敷衍着。他大儿子的故事,我并不想多听。我累了。我想闭闭眼。
“头两天叫了一帮同学到国际娱乐城,后头几天,没钱,就在网吧过夜。”刘父说。
“哦。都这样。都这样。”我说。
“在网吧熬了三个晚上,实在没钱了,就骑着电瓶车回家了。在一个三岔路口,撞在了一辆运沙石的大货车上。”刘父竖起手掌,同时用另一只手的小指头猛地戳到那只手掌的下面。
“后来呢?”我说。我说完就后悔了。我不想再讲话了。
“还说什么后来呢。像我一样呗。瘸了一条腿。”刘父注视着张建的输液器。药水一滴一滴地滴下来。刘父眉头皱起来,想必回忆起了什么。刘父说:“一人高的车轮从他的大腿上轧过去。医生问,要腿,还是要命?我儿子说,要腿。但是我私下跟医生说,要命。”
刘望海一跳一跳地走过来,两只手放在嘴巴前哈气取暖。
“老爸,车钥匙呢?这里太冷了,我去车里暖和暖和。”刘望海说。刘父用他那条瘸腿很别扭地踹了儿子一脚。刘望海顺势向后跌坐在地上,唉哟唉哟地喊疼。
刘望海说:“老爸,你下手也太狠了吧?哎哟喂……”
“你学学人家的吃苦精神。”刘父指着张建。张建把低着的头略微抬起来望了望刘望海,又低了下去,埋得更深了,几乎要嵌进胸口。
“他哪里吃苦了?”刘望海捂着膝盖,还不肯起来。刘父站起来,跨过去,又是一脚,踢在他屁股上。“还不快滚。”刘父把车钥匙扔在他怀里。刘望海一边捡起车钥匙,一边使劲揉屁股,一溜烟走了。
“那你的腿呢?”我说。我的脑子又变得清醒起来,只是后脑勺一抽一抽地疼,就像有个订书机在里面钉我。
“我的腿呀——”刘父重新坐好,“我的腿是被石头轧的……”
刘父讲,那几年他跟老婆在厂里上班,攒了一笔钱,回老家买了一辆铲车,给人开矿。开了半年,他就又买了一辆,租给别人开。又过了几年,他已经有五辆铲车了。于是他不开了。他组了一支车队,自己当包工头。他把县里的工商局、林业局、旅游局、建设局、国土资源局等等关节打通。每年他都能揽下一两个项目。六七年时间,他就攒下了两千万的资产。
“后来呢?”我说。我刚说完,外面的公路上响起了熟悉的摩托车轰鸣声。那些摩托车的马达是改装过的,寒冬的夜晚,在这阴冷的医院里,我们都被吓了一跳。但我们很快平复下来。
“后来呢?”我继续问。
“后来我也不干活了。每个星期都要出去陪县里的领导吃饭,唱歌,按摩,洗脚,泡女人,除了这些,我就没事干。”刘父说。
“然后你就去赌博了?”我说。
“你怎么知道?”刘父说。
“这我见得多了。”我说。
“哦。都这样。都这样。”刘父说。刘父站起来,仰起脖子,盯着天花板看了好半晌。我以为他在回味赌桌上豪输的辉煌历史,发现不是。他是烟瘾犯了。他捻了一支烟,夹在指缝里。“我出去抽根烟哈。”他说。我点点头,他出去了。
输液室变得异常冷清。我走到张建跟前。
“冷吗?”我问他。我摸了摸他的手,手指是冰的,好在掌心还有些温度。
“不、不、不冷。”张建说。
“我给你倒杯水去。”我说。我走到水箱边。凉水箱是冰的,温水箱是凉的,开水箱是温的。我把最上面的一次性杯子抽出来,放到最下面,然后从上面取了两只。我倒了两杯水,一杯给张建,一杯给自己。我喝了一口。杯子里有股呛人的臭味,塑料味,或者医院里特有的化学味。我不喝了。
张建一口喝干了杯中水,喉咙里咕噜咕噜作响。我接过他的杯子,走到输液室门口。我把杯子扔进垃圾桶。垃圾桶很大,敞口的,垃圾袋又黑又厚,里面尽是针头、纱布、输液袋和沾着血的棉花。我盯着垃圾桶出神。
“他口渴了是吧?”一个声音猛地冲撞我的耳膜,嗡嗡的回音灌满了我的脑袋。
是刘父。他就坐在输液室门口的椅子上,椅子挨着垃圾桶。他是为了弹烟灰方便些,才坐在了最靠近垃圾桶的位置。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头低着,他几乎是贴着我耳朵说话的。
刘父用袖口把右边座位上的瓜子皮和指甲掸干净,邀我坐下。
我把一条腿架到另一条腿上,手揣在衣服口袋里。输液室的门口是一条幽深的走廊,走廊左边出去就是急诊大厅,进出的人不多,右边过去是诊室,里面空荡荡的,左前方是抢救室。透过一扇玻璃窗,可以看到抢救室屏风里面的内容。屏风里没人,抢救床很干瘪,心电图机的屏幕也黑着。
“你赌博手气这么差,没想过收收手?”我说。
“怎么没想过。当然想过。”刘父说,“可是赌瘾上来,忍不住啊。”
“赢了还想赢,输了还想翻本?”我说。
“也是,也不是。”刘父把烟蒂丢进了垃圾桶,但是没丢准。
“……”刘父还想说,但是医院外面的公路上响起一片尖叫。大概有什么人被打了——是喊救命声,但“命”字还没发完,声音就没了。随后是摩托车的轰鸣,忽远忽近,伴随着口哨、呐喊和欢呼。
几个医生从急诊大厅里飘出去。刘父侧转头,但是输液室的墙壁挡住了视线。刘父仿佛想到了什么,霍地跳起来,向外冲出去,像一道闪电。
我准备出去看看,想想算了。我的意识很模糊,眼睛都花了。地上的花岗岩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出颗粒感。我弯下身,用指甲去抠那些色彩斑斓的碎片。抠着抠着,刘父的影子一瘸一瘸地从墙壁的后面拐进来。他一脸松弛,把软盒中华掏出来,给我递了一支。“抽吗?”刘父说。我接过烟,咬在嘴里。啪嗒一声,蓝色的火焰从刘父的打火机上跳出来。
“没有刘望海?”我吐了一口烟,说。
“在车里呢,睡去了。”刘父说。
“车窗开条缝没有?暖气开着?”我说。我又吐了一口烟。
“没。我给开了。”刘父说。
“赢了还想赢,输了不想翻本?”我说。
“赢得少,输得多。放一起,就没赢过。读书人搬家——净是‘书’。”刘父说。
“翻不了本?”我说。
“五辆铲车,只剩一辆了。”刘父说。
“然后就自己开了?腿被石头轧了?”我说。
“百来斤重的大石头。从山顶滚下来,轧在腿上。还算好,没砸在脑袋上。阿弥陀佛,佛祖保佑。”刘父说。
我的问题全问完了。我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我只顾着吸烟,烟一下子被我吸了一半。输液室里的那对老夫妻也出来了。老头儿左手摁着右手的手背,老伴儿一手拎着药袋子,一手扶着老头儿的腰,鞋子踩在地面上,唧唧地响,远去了。我们看着他们的影子一段一段地消失,直到头也被墙角线削去了。
“能一起走到最后也不错。”刘父说。
“不知道。”我说。我努力地吸了一口烟,让自己振奋一点。
“看气色,这老头儿吃了不少营养品。”刘父说。
“不知道。”我说。我又吸了一口。
刘父把烟蒂扔进了垃圾桶,我也把烟蒂扔进了垃圾桶。刘父站起来,抖抖手,踢踢脚,舒活舒活筋骨。
“就一年时间,钱也输光了,老婆也跑了,儿子也残了,自己也瘸了,借出去的钱也讨不回来了。”刘父说。刘父看了看我,很亢奋地笑了。
我也没什么好安慰他的。并且我觉得,这些不过是他的事情。我与他如果有什么关系的话,全是因为刘望海的缘故。而我与刘望海的关系,也是偶然的,是命运强塞给我的。坦白说,我并不想要这层关系。
我给妻子发了条微信。我问,睡了吗?妻子没回。我问,女儿睡了吗?妻子没回。我问,你们都睡了吗?妻子回复:都睡着了。我回复:呵呵。屏幕上方显示“对方正在输入...”,断断续续地“输入”了一阵子,然后停了,再也不“输入”了。
我走进输液室。我看了看张建的输液袋,还有一袋没开封,在滴的这一袋还剩下一半。张建睡着了,一长串哈喇子从嘴角挂下来,忽而高,忽而低,像一个慢动作的溜溜球,落地的时候又弹回去。药液一滴一滴地落下来,让我感到窒息。
某个瞬间,我真想把滚轮拨到最大,让药液像瀑布似的哗啦啦冲下来。
“要不然你先回去吧?”我说。说完我转过头去看刘父,他已经跟进来,站在我背后。我总觉得他要偷袭我,所以我得戳穿他的阴谋。
“没事。我还清醒着呢。我们这一代,跟你们这代年轻人不一样。我们本来就是干体力……”刘父还没说完,就长长地打了个哈欠。“我还行,我还行。”刘父捂住张得圆圆的嘴巴,声音变得混沌,像闷在了海螺里。
“你还是回去吧。你不困,望海也困了。”我努力地翘了翘嘴角,挤出一点笑意,以便让他不感到歉疚。
刘父放开手,把哈欠打完整,还带点不由自主的浮夸。刘父说:“那我就不好意思了。”他说着,笑着,向后退去,然后消失在门口。但他的影子还残留着。我就盯着他的影子。他的影子被墙后面的世界吸进去,嗖嗖地消失。然后我就盯着门口的墙角线。墙角线上什么也没有,但是因为急诊大厅里来来往往的人流的缘故,墙角线的铝皮闪烁不定。
“狗崽子!我砸不死你!狗崽子!给我站住!”
一个声音在大厅那边爆开。声音来得突兀,尖利,嘹亮。整栋急诊大楼平地跳了一下。过了很久,那嗡嗡响的余音还在急救室、走廊、输液室、墙壁、吊瓶、LED灯、水龙头、椅子上颠仆,抽搐,瑟瑟发抖。我看到一个医生从走廊右边向外跑出来。接着是另一个医生。接着又是一个医生。然后是三三两两的护士,然后又是三三两两的护士……走廊右边过去,原本是空空荡荡的,没想到竟能吐出这么多人来。
我环顾四周,输液室里实在是太空了。或者说,急诊大楼里实在是太空了,这是我所能估计到的。我想大概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冲出去了吧。外面真是热闹啊。喧哗声从我背后的窗缝里打进来,一浪跟着一浪,菜市场一般。我能根据声音的高低、强弱、质地、远近,想象出外面的情形。但我一点都不想出去看。也许我太疲倦了,或者是我想不出这有什么新奇可言。
我的眼前一片迷糊,耳朵里嗡嗡作响。我的视线正好对准一面墙壁的下边。墙面惨白惨白的,上面重重叠叠地印着大大小小的鞋印。墙壁的下边是黑色的踢脚线瓷砖。瓷砖也被鞋印踩得一块一块的灰白。我盯着那些泥巴灰的鞋印,心里有种怪异的感觉。
一只蜘蛛从墙角线上爬过,钉进了我的眼帘。我的心里为之一动,血液慢慢翻上来。我悄悄地向蜘蛛走去。我蹲下来,凝视着它,它全身毛茸茸的,有着黑色和棕色相间的条纹。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见过它似的。我用力回想,试图把沉入脑海深处的那个形象打捞上来。
天啊!它果真就是我在家里见到的那只。该死的,它竟然跟到医院里来了。我感到好难受,心里麻痒麻痒的。我褪下一只鞋子,套在手上。我举起鞋子,慢慢靠近它,慢慢靠近。我想这次它死定了。“你死定了。”我的脑海里回荡着这句话。
啪——当啷啷。蜘蛛迅速爬走了。我站起来。啪——乓乓乓乓。蜘蛛又逃走一段。我向门口的方向追去。啪——咚咚咚咚。蜘蛛太敏捷了。我必须紧跟而上。啪——哗哗哗哗。蜘蛛在门轴上旋转了一个钝角,扑到了那根闪烁着白光的铝皮墙角线上。我定了定神,把另一只鞋子也脱了,套在手上。这下子,我走起路来也没声息了。我踮着脚尖靠近它,一小步贴着一小步。
“他妈的,这次非拍死你不可。”
一想到蜘蛛被我拍扁,体液沾满我鞋底的画面,我兴奋得热血沸腾。
啪、啪、啪、啪、啪——啊——
“快走开,别挡路!”
一个结实的肩膀撞到了我的胸口。我回过神,让到一边去。一个身穿棕褐相间的条纹T恤衫的少年被抬上移动担架,冲进了抢救室。他的头发上都是血,脸颊上已经全红了。我跟着跑到那扇玻璃窗后面看抢救室里的情形。冷清的抢救室瞬间变得紧张,热闹,乃至沸腾。医生在给伤者施加心肺复苏。
医生两手握住除颤仪的按压器,按压一下伤者的胸口。砰——伤者触电,上半身从床上弹起来。医生又按压一下伤者胸口。砰——伤者触电,上半身又从床上弹起来。抢救床吱嘎吱嘎地摇,但我听不见声音。那该死的玻璃真是厚,一点声音都跑不出来。
心电图机上的心电信号就像一条受了伤的小蛇,微微地颠簸,颤抖,偶尔随着砰的一声会蹿起来老高。我盯着心电图死死不放。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心电图就像一部电影,甚至比电影还要扣人心弦。它的起起落落、急急缓缓、上蹿下跳,几乎令我再次着迷,沉醉。
心电图最后颠簸了几下,变得平缓,拉得笔直,然后像一条死蛇似的软下来。但是医生还在徒劳地用功。汗珠模糊了我的眼睫毛,让我渐渐看不清眼前的景象。
我回到输液室。张建还在睡觉。他发出轻微的鼾声,地上的口水也淌到了他的鞋跟下面。再看他的输液管,黑红黑红的血液已经倒流了,在底端攒了浅浅的一层。我叫来护士,把他手背上的针头拔了。然后我叫醒他。
“老师,我想上厕所。”张建左手揉着眼,迷迷糊糊地说。
“嗯,你去吧。”我说。
“老师,能不能帮我拿一下,我够不着。”张建把右手轻轻地抬了抬。
“已经摘了。”我说。
张建看了看手背,手背上只剩下棉花和胶带了。
把张建送回寝室的时候,同事睡眼惺忪地把门上的铁链摘掉,然后打开公寓楼的玻璃门。她穿着垂坠的睡衣,在大厅铁块般的昏暗和寂静中,身子显得异常单薄。她的头发披散着,很是蓬乱,胸部也比白天瘪下去很多。她用指甲抓挠着头发,试图让自己清醒一些,但是效果并不明显。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同事说。
“嗯。”我说。
“挂吊瓶了是吗?”同事说。
“嗯。”我说。
“另外一个同学被他爸带走了是吗?”同事说。
“嗯。”我说。
“他把他爸带走了。”我纠正了我的说法。
“嗯?”同事没明白我的意思,但她也没打算明白。她把张建让进公寓楼,迷迷糊糊地关上玻璃门,挂上铁链,上楼去了。
我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台阶很冰,空气湿冷,但是能让我清醒起来。楼梯上的声控灯也熄了。我就把脚在台阶上很清脆地一跺,灯光又从门厅里面照射出来,撩过我的肩膀扑在前面的台阶上。过了一会儿,声控灯又熄了。我抬起脚又是重重地一跺。声控灯亮了,但维持了没多久。我承认,我控制不了声控灯。我作罢了。
公寓楼后面那个露天的游泳池,前天晚上我去过。池子里除了老鼠、蛾子的尸体以及白色的鸟粪,剩下的全是干泥巴块。泥巴块像蛇鳞似的爬满每一块瓷砖。
我给自己点了一支烟,默默地吸着。我想起在那游泳池里发生的另一个故事。几年前一个春暖花开的夜晚,一个数学老师在办公室里强奸了一个女学生。然而真相的败露却是在一个大雪飘零的深夜。女生独自一人躲进游泳池边的冲洗房,用墙角的安全出口指示灯照明,然后从自己的身体里拔出了一具死亡的新生命。她的事情被发现,是因为一个初三的男生。那个顽劣的男生夜里偷偷起来到阳台上抽烟,闻到了从楼下游泳池里冒上来的血腥味。
回到我租住的房子时,已是凌晨四点半了。我躺在床上,睡不着,脑子里空空的。我在家长群里艾特张建的父母。我给他们留言,我说:孩子高烧已退,并送回寝室,请放心。
我迷迷糊糊地靠在枕头上调息,床头灯亮着,一直亮到窗外蒙蒙亮。
挨到七点钟,我就起床了。我打开微信一看,家长群里有一百多条未读消息。家长们在群里炸开了锅。有的说:叶老师,您辛苦了。有的说:叶老师,孩子交给您,我们真的很放心。有的说:对待张建是这样,要是其他同学也生病了,叶老师也是会把他们连夜送医院去的。有的说:那是肯定的嘛。有的说:当老师的,哪一个不把学生当自己孩子看?……张建的父亲没有回应,张建的母亲没有回应,刘望海的父亲也是,没回应。
我打开妻子的留言。是凌晨三点半发来的。妻子说:我们已经到家了,女儿睡着了。妻子又说:你不在,我也可以带她去看的。隔了三分钟,妻子补充说:这次没有摔跤。我愣了一下。我回复说:好。妻子没回。
七点半第一节课,我站在讲台上。站了一会儿。站不稳,地心引力在拽我。
“今天我们上《秋天的怀念》,这是史铁生的……”我站不住,终于还是坐了下来。讲台上的电脑显示器挡住了我的视线。我把显示器放平了。
“把课本翻到二十八页。”我发出课堂指令。
“第几页?”几个男生开始起哄。我知道是谁在起哄。
“二十八页。”我努力地喊,但声音不大。
“老师你又没吃早饭吗?再说一遍。”那几个男生哄笑起来。
“二十八页!二十八!”我吼了一嗓子。教室里安静下来。
我捻了一根白粉笔,转身在黑板上写:“秋天的怀念,史铁生。”我一边写,一边念。写完最后一个“生”字的时候,我看到黑板的右上角粘着一块黑色。刺目的黑,依稀是一只蜘蛛。我醒了醒脑袋,试图让自己看得更清楚些。
没错,就是一只蜘蛛。
我把鞋子从脚上拔下来,握在手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我的鞋子掉在了地上。我感到天旋地转,然后听到很远的地方传来咚的一声闷响。我感到脸颊和耳朵很冰。我调整了一下脑袋的位置,尽量用头发贴着地。
据学生说,我的呼噜声特别响。好吧,天知道他们说的是真是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