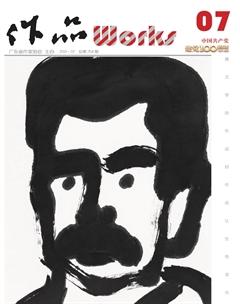老游击队员之歌(散文)
萧维民
一
我乡下称祖父为“阿爹”。我阿爹在村里人眼中是个传奇人物。曾当过“共匪”——游击队员,1944年底追随襟兄陈以铁参加革命;1945年1月游击队进攻吴川县政府所在地塘?镇;同年2月底奉命进军高州,从600多名游击队员中选120人,阿爹在列;3月初在高州木坑塘村被围歼,阿爹逃脱;1948年底阿爹以为风声已过,返乡过春节,除夕夜伪政府搜捕,阿爹的二弟被射杀,阿爹在乱枪之下又逃脱。新中国成立后阿爹任村小学校董,1952年土地改革成了地主,43天后改为中农……
1995年4月,阿爹去世。办完丧事后的一个晚上,八叔公与我父亲聊起阿爹的往事。八叔公是阿爹的四弟,兄弟感情甚笃,逢年过节,八叔公有鸡?的时候,都给阿爹送一点。八叔公沉默寡言,从不愿讲起那些苦难往事,那一次卻讲了很多。八叔公讲,阿爹为躲避搜捕,扮成樵夫,装聋作哑,睡棺材,钻墓穴,逃归村里,再逃往外地;伪乡公所、联防队隔三岔五便来搜查,曾祖父忧惧惊惶,于1946年3月逝世,阿爹不敢奔丧;1949年1月28日伪联防队射杀四叔公,曾祖母被捕下狱,八叔公与六叔公到大姊家“挨口”(投靠寄食),寄人篱下,连外甥也不待见。八叔公讲,阿爹从高州逃回来,村里有人认为带回不少财物,或许是后来当地主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家里人口多,老屋住不下,阿爹将旧宅分给了六叔公、八叔公,自己带领子女将“西头角”低洼地填平,建一间茅屋住,再用十年建了一厅两房的红砖屋,将村里人都认为“不干净”的地方建成大家炎炎夏夜都来纳凉的好居所。
八叔公的说法算是家传,我千方百计查找历史记录,哪怕有蛛丝马迹也好。《民国高州日报》1945年3月7日报道:[本报专访]本月三日,匪首陈以铁等率匪百余,由山口窜至道平乡附近。邓指挥官□□□即分饬搜捕。四日□承某,□在道平乡、木坑塘附近□围击,当场击毙陈以铁以下百余人,缴获匪枪数十。余匪三两星□,现正搜剿□行全股消灭。《民国高州日报》1945年4月17日:[本报特讯]奸匪大队长陈以铁……截获时犹改名换姓,□免一死。迨解至本城,为识者所指正,始照直供认不讳。该案□南路指挥所发查七区专署讯办,以罪证明确,依法判处死刑,电奉广东绥靖公署核准,于本月十六日下午二时,提堂验明正身,押赴风门坳执行枪决,人心为之大快,兹将布告摘录如下:案奉第四战区南路指挥所电饬□办奸匪陈以铁一案业经审明确,供认不讳,被告陈以铁甘受逆首张炎利用,充当奸匪大队长,妨害抗战,扰乱后方治安,依法判处死刑,电奉广东绥靖主任公署邓元绥法行电核准。兹于本月十六日下午二时提庭宣判,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以召炯戒,而维治安。除呈报外,合行布告,仰众周知。
我把这两则报道告诉六叔公。他是阿爹的三弟,八十七岁了,不清楚这些事。曾祖父所生四子二女,六叔公是硕果仅存的了。六叔公记不清,乡亲们自然也不知,阿爹的往事便如烟如雾一般消散在星空里了。
二
我乡下称父亲为“阿哥”。我阿哥偶尔讲过阿爹的往事。据说,当年阿爹在批斗地主时离席解手,便成了地主,受尽折磨,熬不住的阿爹拉着阿哥交代了几句便去投河,没淹死。1958-1960年期间,阿爹去高州担泥填水库,工地回荡着“水库不建成,决不还家乡”的口号,饿着肚子的阿爹将“裹腰布”缠紧干活,晚上听人私下说“工程师指一指,农民工担出屎”。修完水库后,阿爹带领阿哥兄妹担泥填“西头角”、建老屋。1974年我患重病时,阿爹想尽一切办法求医问药,还每天赶集买新鲜小海鱼给我吃……
我刚刚懂事时,阿哥便教我们兄弟俩,年初一必须早起,去向阿爹请安。天还没有亮,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小兄弟揉着惺忪睡眼去祖父母床前请安,“恭喜阿爹阿奶能能健健大发财!”阿爹便端坐在床上,手抚那山羊胡子,朗声说“你们精乖伶俐,快高长大”。我阿爹的眼里充满了幸福和陶醉……
晚年的阿爹经常生病,必要时我们父子就拉“车儿”(农用平板车)送阿爹去医疗站。夕阳暖烘烘地照着,已经忙了一天农活的阿哥在前头拉车,车上铺一张草席,阿爹坐在席子上,披着厚厚的旧衣裳,双手扶着车沿勉强支撑着,我与弟弟在车后边推。夕阳把三代四人连同那辆破旧的车儿,在地上拉成长长的一道道影子。小路两边那成排木麻黄树、水彬树的梢头上,偶尔有几只小鸟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1995年初,阿爹哮喘发作,在医疗站治不了,便到县城医院,折腾几个月,阿哥百般侍候,当时就累病了。阿爹病逝,阿哥悲痛异常,哀毁过礼,形销骨立,引发了肝病,在阿爹离世不到两年便驾鹤西去。
阿爹辞世后,阿哥曾做过一个梦,梦见阿爹端坐在一庙里,旁边坐满了和尚,都在念着经,阿爹肥头大耳,袒背合十……到阿哥去世时,我想起李密《陈情表》“慈父见背”的说法来,心戚戚良久。
其实,阿哥对阿爹多少也有微词,阿妈曾讲过在艰苦贫困的岁月里,阿爹对全家收入支出的专制,多少压抑过勤劳聪明的阿哥的积极性,甚至在阿哥兄弟分家时,阿爹倾向幼子而让身为长子的阿哥受损,但阿哥纯孝笃敬,从来没说过阿爹半句不是的话。
济民表叔讲,阿爹参加革命的时候,阿奶和阿哥是受尽苦楚的,特别1949年1月30日(旧历己丑年正月初二),阿奶哭着到梅菉镇,找舅公为无辜被杀的四叔公买棺材,之后阿奶带着阿哥到娘家“挨口”的种种往事。俱往矣,阿爹、阿哥离世后,阿奶2012年秋辞世。三位老人物故,那些苦难便如梦幻泡影了。而阿爹那一辈人修的高州水库,依旧青山绿水、烟波浩渺;我们家“西头角”那座旧砖瓦房也依然屹立着。
三
我没见过阿爹英武的样子,也没听阿爹说过那些惊心动魄。不管别人怎么说,在我心目中,阿爹不是传奇人物,也不是革命战士,只是阿爹,高高的、瘦瘦的、留着山羊胡子的、勤恳的老头儿。
秋收时,天未亮就开始劳作。待到朝阳初升,满天云朵泛着鱼肚白,丝丝风儿掠过层层稻浪,沉甸甸的谷穗密密匝匝,丰收的喜悦让人不知疲倦,一家人奋力劳动,好赶在正午前把水稻收割完毕,快快晾晒。割禾阿爹管七行,我管五行,也赶不上阿爹。那只长满了老茧的手,一把一把地抓过去,镰刀飞快,一扎一扎稻子,便满满放在身后,却从没有回过头来看落在身后的我。
阿爹终有累倒的时候,大约是六十五六岁,就不能再下地干活了。阿爹总闲不住,爱找些活干,修农具,种树苗,捡破烂,拾猪粪,等等。阿爹老病缠身,患有严重的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晚饭后,我们兄弟就为他捶背、捶腰、捶腿,姑姑们小时候也这样,因为这是多年落下的病根,阿爹老的时候让我们捶得更多、更重罢了。
改革开放后,曾有当年的战友们联络活动“复职”——请组织上解决待遇,阿爹不愿参与,虽经多次劝说也无动于衷。村干部要到县里申请“革命老区”,让阿爹讲讲当年的事,阿爹婉言拒绝,还是那句“都过去了”。阿爹最后几年,曾下功夫学习医书,记下了些偏方,为一个老妇人——那向伪联防队告密者的妻子——开过药方……或许那时已年过七旬的老翁,心境宽广来自恩仇泯灭,来自对世情洞察后的无争,来自对安静如水的晚年生活的满足。
阿爹去世时,我已是大学教师。那晚偕同在广州念书的弟弟往家里赶时,阿爹已仙游。一位在阿爹临终那晚陪伴过的堂叔公对我说:“哥三(祖父行三)走得平静,好人好报。以前我家里困难,小孩多,到处借债,借多了也没有法还,结果人人都不愿借了。但哥三从来都借,也从不问还。现在县医院一位护士,当年家里无钱交学费,还是哥三垫支的。”“哥三临终前说的不是那些心惊胆战的事,而是你的孝顺聪明,说那一本又一本的红本本和贴满墙壁的奖状,说零花钱不买零食,留着买纸笔,说读大学后从广州带回东西……说别的事时总咳嗽,但一说到你,一声儿也没咳,可惜你没见最后一面。”
近日整理旧物,发现阿爹1990年9月29日的信(那时我上大学):“孙儿:来信两封经已收阅。知道一切甚慰。说在校师长体[睇]重你的,分何等職负任,你不说明白,任職以後来说明。但你来信说要隐瞒我,知道你不应该。我知到[道]此情事,我当食参汤一样,以后再有成職[绩],切勿瞒我。你来信说不知满意不满意在此校,我看不明白了。每月菜金[是]学校公[供]应是自己负责,来信说明。你在学校要勤劳学习,又要保重身体,每日两餐不要节约太甚。我往梅菉与德民叔婶说你文科系[中文系],他说甚好,毕业后他说得回一中教书甚好,今年毕业学生无位置分配了。上课说怎么话?来信字只写分明一些,免得我看不明白了。现稻禾豐收,目前亲戚老少平安,切勿挂念。书不尽言,其餘再叙。祝你身安。祖父培森字。旧八月十一。”
阿爹写得一手好小楷,村里人给土地公披“红”,就请阿爹写上那供奉的话语,一边写“中华国广东省高州府吴川县北乡东风里大寨山东境福德振德土地”,另一边写“下居信善某某合家诚心敬奉”。那些蝇头小楷写在红布上,用墨不好把握,太少写不了,太多就漫滤开去,阿爹能写得极工整。这封信是圆珠笔写的,十六行工工整整。信封三行是鋼笔字,收信人一行用繁体。还叮嘱我“字只写分明一些,免得看不明白”,如今读来不胜唏嘘。
七十岁的阿爹用惯常口语写,夹杂着繁体字,有的地方写了错别字。信中说了三次“不明白”,两次要我“来信说明”,牵挂溢于言表;问每月菜钱是自己出还是有补贴,叮嘱“不要节约太甚”,这对艰难一辈子的老农民何其不易?还因德民表叔说读师范好,别的毕业生没包分配了,读师范起码可回县中学任教而欣喜不已……
阿爹一生的故事,必然淹没在时间的长河里。对于我,确是无尽的思念。
祖父讳培森,字宝棠,谥朴实慎直,生于民国十年十一月廿四日子时,卒于公元1995年4月11日凌晨2时许,享年七十有五。
责编:李京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