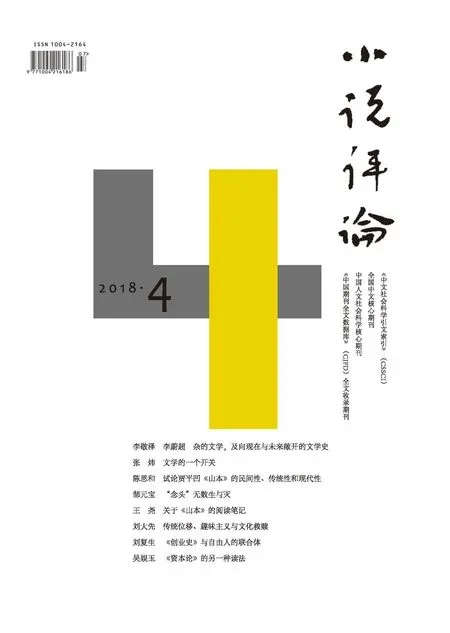经验的贫乏及其并发症
——论《平原客》《藏珠记》
吕东亮
李佩甫的《平原客》、乔叶的《藏珠记》都是2017年中国文坛值得注意的长篇小说。两部长篇在经验、结构与语言方面都呈现出相似的问题,值得作为一种写作的症候提出来讨论。
一、经验的贫乏
李佩甫的《平原客》讲述的是由一起副省长杀妻案所牵连起来的人与事,作者对这些人与事的叙述贯彻了他一直以来对于平原人精神生态的关注,作者对人与地关系的理解也秉承了一直以来的“植物与土壤”关系的隐喻。围绕着副省长杀妻案,作者倾力塑造了三个人物:副省长李德林、副市长刘金鼎以及刑案专家赫连东山。副省长李德林出身贫寒农家,凭借学业的优秀考入大学、出国留学、归国任教、破格晋升,一步步成长为主管农业的副省长。快速成长的李德林并没有快速转变为妻子所期望的优雅的、精英化的成功人士,而是由于美国苦读生活的压抑、对家乡父老的挚爱而变得不修边幅,在家乡故旧的包围与缠绕中化解着内心的焦虑,享受着虚弱的自信和荣光,进而与作为城市大家闺秀的妻子离异,与乡村女人徐二彩结婚并最终在刘金鼎、谢之长等人的帮助下杀害徐二彩,彻底陷入了乡土关系构成的泥沼。李德林这个人物形象在李佩甫小说的形象谱系里是有渊源的,他也是一个从乡村走入城市的平原客,如同李佩甫之前的《无边无际的早晨》《败节草》和《生命册》中的男主人公一样,斩不断乡土的脐带,却又为无法全面融入城市而惶恐焦虑,人物形象身上的历史牵绊感如影随形。小说对李德林形象的塑造是基本成功的,对其承载的社会历史内涵的发掘也是深入的。但也必须指出,李德林形象还不够饱满,作者对这个形象的审视还有不到位的地方,有些描写没有贴近李德林的内心,没有做到“理解之同情”。相对于李德林,刘金鼎、谢之长、赫连东山等形象则较为浮表化,刘金鼎出身花匠世家,其命运也因此带有几丝神秘色彩,从小说中对其幼年母亲失踪、少年辗转求学等经历的叙述来看,作者是有意把刘金鼎作为一种植物描写其生长的,但随着后来情节的吃紧,刘金鼎的成长实际上被搁置了,关于他的生命反思也消失了。赫连东山这个形象则流于一般,小说中关于他和儿子之间代际冲突的书写较为生涩和概念化,没有出人意表之处。小说中他唯一的较为动人之处可能是一句感慨:“这个时代已经不是我的时代了”。谢之长形象也没有生长起来,作为平原上的“跑事儿”的人物,他的复杂性以及所牵涉的社会经验显然没有在小说中呈现出来,尤其是和李佩甫之前的中篇小说《寂寞许由》中“跑事儿”的郭守道形象相比就更加苍白。整体看来,《平原客》存在故事淹没人物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作者对故事的体验不够深入、认知不够透彻。作者虽然试图写出时代对于人物的潜移默化的形塑,写出那种“麦子黄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平原生存之复杂奥妙,但呈现在作品里的却是叙述的慌乱与人物的模糊,这无疑是令人遗憾的。《平原客》的主要故事情节来自于十多年前发生在河南省的一个真实的副省长杀妻案,人物也大多有原型。在文学史上,依据一个真实的案件进行文学创作,并不鲜见。法国作家司汤达的名著《红与黑》就是根据一个真实案件创作的。从社会案件到小说情节,关键的是实现事件从新闻性到人文性的转化,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社会案件中的人心人性中去。就《平原客》而言,从小说的叙述态度来看,作者对这一案件的探究兴趣、书写兴趣是浓厚的,这一案件也刺激了作家理解新的社会经验的创作欲,同时也对作家解释新的现实的能力提出了挑战。面对新现实、新经验的挑战,《平原客》作出的回应是不能满足读者对李佩甫这一茅奖作家的期待的。《平原客》中,作者对情节的叙述兴趣过于浓厚了,有渲染之感,甚至有猎奇等黑幕式小说的倾向。尽管作者增加了一些颇有抒情氛围的书写用以烘托人物的心灵,但还是没能遮盖小说的通俗气味,没有提升小说的文学品质。总的来说,这些问题都缘于作者还没有把新的经验想透,作者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消化这些经验。
乔叶的《藏珠记》如作家自己所称是一部轻逸之作,尤其是和作者上一部长篇《认罪书》相比,就更加令人感到作品的随性随意,甚至带有游戏的意味。《藏珠记》讲的是一个千年不老的处女唐珠和一个出身名厨世家的官二代金泽的情爱故事。唐珠吞下波斯人所赠的宝珠从而千年不老,顺利穿越到当世,结识并爱上金泽后便抛开不能交欢的禁忌,以正常衰老为代价与金泽欢爱并结婚生女。与此同时,唐珠走进了金泽的名厨家族,了解了丰富的饮食文化,并与金泽联手,打败了曾为金泽父亲司机、后来成为金父腐败同盟者进而成为见利忘义者的房地产公司老总赵耀。《藏珠记》的故事情节主要是三方面的:一是唐珠和金泽的爱恋,在这些故事中,唐珠和《认罪书》中的金金等乔叶小说中女主人公一样,是一个具有强悍而热烈的爱欲的女子,小说关于其爱欲的描写一如既往地大胆暴露;二是关于饮食文化的内容,小说主要是通过金泽亲族中人物的叙述呈现的,这些内容是小说中最为出彩的部分;三是唐珠、金泽与赵耀的斗争,具有反腐败的意味,但这些情节却写得较为模式化,没有超出流俗的腐败想象。三方面的情节虽然有所交集,但内在的联系是松散的,根本原因则是这些经验是碎片化的,小说对这些经验的认知和表达也有媚俗的倾向。对世俗人情的体贴,对平民生存经验和智慧的尊重是乔叶创作的一个特色,也赋予了其作品一种可贵的非精英化的姿态和品质。但这种平民化或世俗化也潜藏着一种危险,那就是对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趋附。在大众传媒日益喧嚣的今天,真正平民经验的表达日益变得困难,媒介文化中大众已然成为被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裹挟的欲望主体,是马尔库塞所称的“单面人”,他们面目模糊、主体虚幻,无法感知到真实的利益状况,无法获得一种集体感,只能以分子化的个体形式消耗能量、透支想象。被资本利益控制的通俗文化会源源不断地向大众提供廉价的、充满快感的文化产品,这些产品大多标榜快乐至上、娱乐至死,确实具有令人“沉醉不知归路”的体验。在这样的文化场域中,乔叶的《藏珠记》因为其软性的文化质地,很容易被归并吸附到通俗文化的阵营中去,事实上也恐怕正是如此。《藏珠记》的一些套路化、鸡汤化的内容,尤其是那些讨巧的章节标题,是十分契合通俗文化的兴奋点的。如果我们将《藏珠记》与乔叶的《良宵》《月牙泉》等作品相比,就会明显发现什么是真正的大众,什么是真正的平民经验。因为作者太想走轻逸路线了,或者说过于任性了,《藏珠记》中很多有意味的内容完全可以生发出来,却被作者有意无意地抹去了、撇开了,比如关于美食的书写,尽管小说中有不少精彩之处,但还是不够,小说完全可以借鉴陆文夫名篇《美食家》的思维形式,将围绕着饮食而牵连的社会历史意蕴表现得丰厚一些,而事实上,小说中关于“守山粮”的描写就颇有值得深究的意趣。小说关于金泽形象的塑造也有可议之处。作为官二代、富二代,金泽的脾性有些抽象,其间的转换也有些突兀,小说显然没有用心解释这个人物形象,也就无法将之塑造得更为丰满。对于富贵阶层以及富二代、官二代的成功书写,在当下中国文学中是较为少见的。这也是一种新现实、新经验,对此乔叶和许多小说家一样,没有准备好。凡此种种,决定了《藏珠记》只能是一部仓促拼贴了诸般经验的小说。
如上所述,两部长篇小说都存在与时代真实经验相隔绝的问题,不仅以往小说那种常见的“自叙传”式的个人亲历经验的叙述比较少见,而且经验的浑然状态也较为欠缺。这当然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有关。我们所面临的当下社会,是典型的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所说的“景观社会”。居伊·德波认为景观社会所生产的景观“是自我与世界的边界的消除,通过世界的在场和不在场对自我进行挤压,它也是真实与虚假的边界的消除,通过表象组织所保障的虚假的真实在场,对所经历的任何真理进行压抑。”在景观社会中,文化状态则是媒介与资本高度共谋并进而牢笼一切的,在这样一个状态下,影像与现实、主体与客体、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是颠倒的、混乱的,新闻、广告、娱乐画面生成了不计其数的超现实的“景观”,“景观”代替了真实的生存经验,并以消费文化为助力,成为社会经验的主导性表达方式,甚至成为人们感知社会经验的唯一方式。景观社会里的景观生产,当然是繁多且具有吸引力的,而且优胜劣汰、花样翻新,真正是“乱花渐欲迷人眼”。景观社会中的小说创作,无疑要面临讲故事的难度。小说家作为现代社会“讲故事的人”,也要应对新的经验问题。关于现代社会小说与生存经验的关系,德国犹太裔学者本雅明认为“长篇小说在现代初期的兴起是讲故事走向衰微的先兆”,他在《讲故事的人》一文中阐释道:“讲故事的人取材于自己亲历或道听途说的经验,然后把这种经验转化为听故事人的经验。小说家则闭门独处,小说诞生于离群索居的个人。此人已不能通过列举自身最深切的关怀来表达自己,他缺乏指教,对人亦无以教诲。写小说意味着在人生的呈现中把不可言诠和交流之事推向极致。囿于生活之繁复丰盈而又要呈现这丰盈,小说显示了生命深刻的困惑。”本雅明所指的“讲故事的人”是指传统的说书人之类的民间故事传说的自然的讲述者。在本雅明看来,除了“讲故事的人”和社会生存经验具有统一性之外,“讲故事的人”所呈现的经验还具有教诲性,对听故事的人而言则是增加了一种人生经验,而小说则只能传递并且巩固现代人的孤独感,彰显“生命深刻的困惑”,因而也就面临能够为读者提供教益的经验的贫乏等问题。《平原客》和《藏珠记》,表面上讲的是似乎也是来自民间的道听途说的故事,但这些故事已经被大众传媒反复讲述过,不仅丧失了吸引读者或听众的能力,而且也不能提供教益,经验只能处于贫乏状态。在“把不可言诠和交流之事推向极致”这一小说创作的维度上,三部小说也没有显出应有的精彩来,灵魂的深度、“生命深刻的困惑”是缺失的。问题还在于,三部小说不同程度地暴露出书写时代整体经验的抱负。就本雅明关于小说家和“讲故事的人”的阐述而言,三位作家都是难以被归类的,他们都想以“讲故事的人”的身份创作小说,因而也就必然直面经验的贫乏这一时代难题。
二、结构的虚弱
在《平原客》和《藏珠记》中,经验的贫乏导致了结构的衰弱,而结构的衰弱进一步暴露了经验的贫乏。在传统的小说叙述中,浑融性的经验往往自身会提供一个合适的结构,或者依托一个人的成长,或者依托一个重大事件的起承转合,或者历史时序本身就规定了结构的样态。但这三部长篇小说,都无法再享用传统小说的结构便利,作家只能耗费心力,去尝试着搭建新的结构,然而这样的尝试由于实感经验的贫乏都显得较为勉强。
《平原客》的结构,是花开三朵、各表一枝。小说分别讲述了副省长杀妻案中的副省长李德林、帮凶刘金鼎以及刑案的侦破者赫连东山的故事,三个人的故事因为刑案而交叉融汇。应该说,这样的结构是符合事件本身的情理的。但在小说中,三人故事的黏连度是不高的,既缺乏通俗叙述所常见的环环相扣,又缺乏纯文学叙述所应该达到的从容老到。当然,作为纯文学作家,李佩甫自然不愿把副省长杀妻案叙述成一个坊间流传的凶杀艳情故事,他之所以以三个人物作为三条线索叙述,就是想呈现平原的复杂性以及平原客的精神惶惑。在作者的设计中,李德林、刘金鼎、赫连东山乃至谢之长都是典型的平原客,他们敏感地意识到社会的变动,努力地去追寻成功,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意志,并且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时代的纷乱和内心的惶惑。小说一方面想完整地讲述副省长杀妻案的全过程——这的的确确是令人震惊、引人深思的新经验,另一方面又想深入探寻三个甚或更多平原客的内心世界,于是便出现了兼顾的困难。如前所述,李德林的形象相对成功些,但还不够饱满;刘金鼎的成长过程显得有些跳跃,并且时断时续;赫连东山的形象则显得有些类型化。小说叙述常常要面临“事”与“人”之间的矛盾,重视事件的完整叙述,就会压抑人物形象的完美生成,而凸显人物的性格心理,则会影响故事的推进、淡化小说的情节感。作者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平原客》中,我们可以发现作者为了兼顾事与人而在叙述上所作的腾挪趋避以及其间的慌张,甚至有些情节更像是事后补充上去的,而这又造成了叙述的支离。在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有些情节是赘余的,游离于主线之外,而且对于人物的塑造也起不到助力,这无疑是令人惋惜的。在之前的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生命册》中,基于对大时代经验的书写,李佩甫采用的也是复线结构。因为设置了第一人称叙事人“我”来统率小说中丰富的情节片段,故而整部小说的叙述显得从容不迫。《平原客》如果也设置一个具有统摄意味的叙述人,可能会弥补一下叙述的支离和结构的虚弱,至少可以使一些情节的补叙显得自然一些,对于审视人物的内心而言则更加便利妥帖。但即令如此,《平原客》的结构可能还是存在离散性的问题。归根结底,小说结构所建基的现实经验还是太单薄了,这些现实经验用以叙述整个案件是充分的,但用以探究案件中的人物则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作者没有把这个案件背后的社会现实经验想透,也没有把副省长的生命经验与刘金鼎、赫连东山等平原客的生命经验在深层次上联系起来,故而一进入叙述,小说不由自主地被刑案奇闻式的趣味所牵引,追寻人性之变异的旨趣为社会探秘的窥视欲所冲击。
《藏珠记》的结构也是以唐珠、金泽、赵耀三个人物为线索连接而成。连接的机缘则具有巧合意义。唐珠虽然是从唐朝穿越而来的女子,行动具有自由性,但她结识赵耀和金泽,却具有偶然性,而且她所舍身相许的金泽就是自己所要报恩的名厨世家的后人。乔叶的一些小说,情节的维系往往依赖巧合,虽然有“无巧不成书”的说法,但也难免为人所诟病。因为巧合背后如果缺乏世事情理的依托,就难免令人生疑。《藏珠记》因为设置了一个既是主人公又是叙述人的穿越者唐珠,所以就冲淡了小说的机巧之感,但也同时呈现了经验的贫乏。一个按照现实逻辑行进的故事架构,却接纳了一个从唐朝穿越而来的千年处女,不正说明经验的虚空以使得外在的叙述元素可以随意嵌入吗?从这个意义上看,设置唐珠这个穿越者,可能是小说的一个败笔。当然,小说想以唐珠形象表达现代人的一个欲望困境,既想青春不老,又想尽情尽欲。这种困境也可以说是一种欲望梦想,即长久地、无风险地、高质量地满足欲望。这种梦想在现实中也只能成为困境,小说中的唐珠、金泽、赵耀也都面临这种困境。“食色性也”,《藏珠记》中,作者对饮食的书写精彩纷呈,对爱欲的书写也一如既往地大胆直露。对于欲望困境中的抉择及其结果,小说也做出了为普罗大众所认可的处理。小说以三个人的故事为线索,而且让三个人分别作为叙述人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内心生活,呈现各自的立场,既可以见出利益格局中欲望的纠葛,又可以很好地把饮食文化、反腐败、男女情爱等叙述元素连接起来。但问题在于,三个叙述元素的粘合度较低,对于欲望纠葛的描写又太过简单。饮食文化、反腐败、男女情爱都是大众文化所喜闻乐见的元素,作者统筹这三个元素的书写,很明显有取悦大众的意味,但可能是因为太过于在意读者的反应了,作者在写作时对每一个文化元素都颇费心力,反而导致了总体上的离散感。就是说,单看反腐败、饮食文化或男女情爱来说,都写得相当不错,可是三个文化元素的关联性、有机性却没有呈现出来。饮食文化与男女情爱之关系的书写显得有些牵强,反腐败与男女情爱之关系的书写显得有些疏离,而饮食文化和反腐败之间的关系则着墨甚少。作者当然也意识到了这样的缺失,所以在三个叙述人的讲述中,分别作了弥补性的交代,其中一些感慨议论的文字也不乏见地,但整体上来说,这样的弥补收效甚微,结构的虚弱无法得到大的改善。
三、语言的衰疲
经验的贫乏也带来了两部长篇小说语言上的一些问题。李佩甫的《平原客》的语言总体上显得有些生涩。这种生涩不是指作家的语言修养和功夫不够,而是相对于语言所呈现的经验而言的。相对于李佩甫之前的作品尤其是和《平原客》具有相似性的《生命册》而言,语言的那种雍容之感就减少很多。在《平原客》里,具有力道的语言、富有抒情性的语言、灵动的语言也颇多,但似乎大多没有契合小说叙事的节拍。语言的流速感觉太快了,太过慌乱了,缺乏那种让人在阅读中驻留欣赏进而回味无穷的魅力。既然小说主要是写人,写平原客,就不妨多一些抒情性的语言,经营几幅典型性的画面甚至几个含蓄蕴藉的意象,如此可能会冲淡小说的那种新闻感,提升小说的文学品质。尤其是面对一些作家自己不太熟悉的场景时,比如赫连东山和儿子之间的冲突时,不妨少一些言不及义的场景描绘——这些场景描绘流于套路化,实在也说不上有什么精彩之处——多用一些语言描写赫连东山的内心世界,充分写出他内心的惶惑,进而写出一代平原客面对时代变动的焦虑感。语言本身是有形象的,领会一种语言就是领会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存状态。巴赫金认为:“语言要成为艺术形象,必须要与说话人的形象结合,成为说话人嘴里的话语。”也就是说,小说的叙述语言自身会生成可以被感知的形象,这形象和叙述人以及叙述人所在的生活场域连接在一起,成为作品形象世界的有效参与元素。《平原客》中的故事是由一个全知型叙述人完成的。我们从叙述语言所生发的形象中可以窥测出,这个叙述人是惶惑的,内心的情绪是杂乱的,或者说这个叙述人的形象状态是模糊的、破碎的。讲故事的时候,这个叙述人时而表示了对新经验的惊异,甚至有猎奇性的欣悦,时而又有不确定、不坚定的人生感悟,甚至连抒情也无处可抒了。这些大概都是经验的贫乏所造成的。
《藏珠记》的语言流利娴熟,如山中的小溪一般欢快地流淌。乔叶在《藏珠记》的后记中说:“这个长篇,我想让它偏轻。”这轻首先就显现在语言上,具体来说就是语言的软性化、时尚化。因为将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设置成叙述人,人物的自我言说同时也是情节叙述,所以小说的叙述语言并不多,语言形象和叙述人的形象、主要人物的形象是融为一体的。而这些主要人物及其关联情节都是具有比较浓郁的大众文化特征的欲望叙事,就不能不使得小说的语言向消费文化靠近。打开小说的目录,我们会发现许多俏皮而带有强烈当下感觉的小标题,小说正文的语言也是活泼有趣的。但俏皮也罢、活泼有趣也罢,都是在大众文化的意义上被确认的,就创造有品质的文学语言而言,俏皮等等可能并不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倾向。它可能恰恰反映了作者思想的怠惰,因为袭用或化用流行文化中的语言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相对于根据自己的实感经验创造语言来说。《藏珠记》第34节标题为“性感”,里面提到唐珠对金泽的感受,有这么一段:
不疯魔,不成活。现在的金泽越来越用功,越来越专注,然而危险的是,他在我眼里也越来越性感,性感的地方简直无处不在。他穿厨师服自然是性感的,穿上普通的衬衣则是另一种性感。夹克敞着怀是撒开来要拥抱的性感,拉链合住是内敛高冷带点儿神秘的性感,卷起袖子是性感,把袖口的纽扣扣紧也是性感。他擦油烟机,擦地板,擦冰箱,擦玻璃,擦燃气灶,换灯泡,通下水道,统统都是性感,而他在做菜时准确利落的一切:淘米,洗菜,揉面,煎炒烹炸,盯着锅里的菜肴时目不转睛的样子……更是性感分值劲升到爆。
性感是大众文化所热衷的词汇,文学作品书写性感亦未尝不可。但《藏珠记》中的这段关于性感的描写,并没有将其与大众文化书写区别开来,而是认可并引用了消费文化中的表述,并且帮助扩张了那种粗糙的却是得势的生存幻觉。其实,小说完全可以去展开分析、细细阐说金泽所带给她的可以命名为性感、却有着非同寻常的韵味的生存感觉,这样一来,性感这个词就脱离了大众文化场域而得到了文学语言的救赎。《藏珠记》中的类似的段落很多,可惜大多语词没有被作者用文学语言救赎。乔叶早年写作了大量的时尚美文,对流行文化机制、对读者大众心理了然于心,对大众文化中的语言状态也有着深入的体认,但这种体认应该作为作家更新语言的背景,而不应成为作家从中征用语言的便利。乔叶近些年的小说创作,在语言的把握上是好的,她有效地采用日常化的语言对平民生存进行体贴式的书写,成功地抗衡了大众生活中愈发强势的时尚化语言表达而自立面目,实在是十分难得。但长期游走在大众文化的边缘,难免有所浸染而丧失文化警惕,进而认可大众文化的快感原则而进行无难度的语言表达。这种倾向,也反映在《藏珠记》中。《藏珠记》中的经验内容,尤其是一些美食文化和文史故事,写成一些散文是比较合适的,一定要写成小说,就必须用有力的语言去统合这些经验,而熔铸这种语言则需要更周密、更深入的思考。可惜的是,作者没有如此功夫去熔铸语言,只好借用大众文化的语言来做情节的粘合剂了。
《平原客》和《藏珠记》书写的都是当下带有总体性意味的现实经验,也都属于正面强攻的现实主义写作。面对当下变动不居的现实以及日趋膨胀的大众传媒,作家们的困境有增无减。李佩甫、乔叶如此,其他作家也一样面对经验的贫乏及相应的并发症。余华的《兄弟》上半部写改革开放前的生活写得从容,下半部写改革开放后的生活写得慌乱;格非的《望春风》也是如此,小说的后半部分写改革开放以来的生活时推进得明显快一些,经验的全面性也明显不足。这大概都是作家没有把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想深想透的结果。面对新世纪、新时代的经验,如何想深想透就是一个更加让人焦虑也更加让人着迷的问题,而具有高峰意义的作品也将在对这个问题的卓越应答中得到诞生。
注释:
①[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8页。
②汉娜·阿伦特:《启迪:本雅明文选》,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99页。
③李佩甫:《平原客》,广州:花城出版社2017年版。小说在第31页写道:“四年后,刘金鼎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已是主管农业的副省长了,那年他四十七岁。”无论从小说内部世界还是现实世界来说,这都是不合情理的。刘金鼎从大学毕业生到常务副市长,尽管有李德林的帮助,至少也要经过十多年的历练,而李德林不可能做了十多年的副省长还被刘金鼎以为有提拔至中央的可能。小说在时序上的错乱也是小说结构虚弱的一个表现。
④[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页。
⑤⑥乔叶:《藏珠记》,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年版,第258页、2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