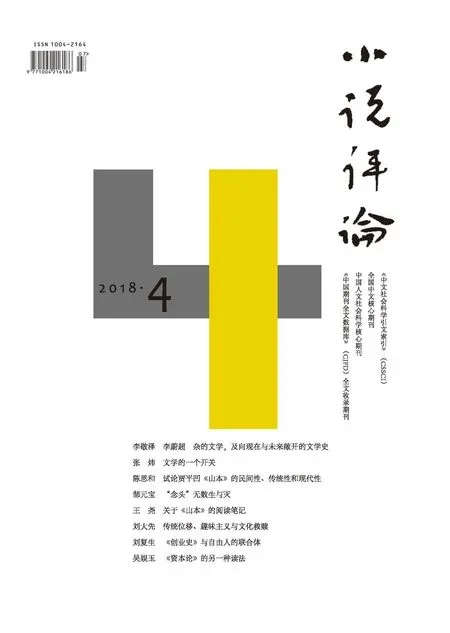李佩甫“平原系列”的灵魂叙事
沈思涵
1957年5月5日,《文艺月报》全文刊登了钱谷融先生的《论“文学是人学”》长篇论文。文中写道:“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十分明确地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他认为:艺术之所以别于历史,是在于历史讲的是人类的生活,而艺术讲的是人的生活。高尔基把文学叫作‘人学’,这个‘人’当然也并不是整个人类之人,或者某一整个阶级之‘人’,而是具体的、个别的人。记住文学是‘人学’,那么,我们在文艺方面所犯的许多错误,所招致的许多不健康的现象或者就都可以避免了。”
文学是“人”学,所要表现的是“具体的、个别的人”——钱先生的振聋发聩之说,陈晓明教授给予了高度评价:“试图用人性论与人道主义来重建社会主义文学理论,促使其体系走向开放,向着世界文学、向着中国传统文学、向着更有活力的体系建设开放。把文学纳入‘人学’的范畴,这实际上就是‘去苏联化’‘去斗争化’,也就是试图把文学重新纳入五四现代启蒙文学的历史脉络中。”这种文艺思想在改革开放之初得到了集中释放:“新时期中国文学正是以张扬人道主义开启新的征程,新时期中国文学以它辉煌的成就,证明了钱谷融先生当年的理论学说的先见之明,证明了他的非凡的勇气和洞察力。”
不过,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主流的仍然是“现实主义”,并且还时不时地呈现出复杂“症候”。譬如,“人”可以简化为“人生”,“人生”再转化为“时政”。张平当年创作《抉择》时就毫不隐晦地宣称:“一个故事有开头,有结尾,就可以动笔,(自己)写作前往往没有很细的提纲……材料准备好后,就急着把它宣泄出来。”因为,“只要能对我们现实社会的民主、自由,对我们国家的繁荣、富强,对全体人民生活的幸福、提高,多多少少会产生一些积极有意义的影响,即便是在三年五年十年以后我的作品就没人再读了,那我也一样心甘情愿,心满意足了。一句话,我认了!”
李佩甫接续上了“人学”的脉络。他显然属于另一类作家,是那种“被低估了的作家”。有论者曾经明确指出:“之所以认为李佩甫是被低估的作家,就在于他的《羊的门》没有被充分重视。它虽然轰动一时却很快就销声匿迹了,甚至被挤压到官场小说之中了。其实,这部作品足以和新时期最优秀的乡土小说媲美,足以使李佩甫从众多的乡土作家之中脱颖而出。因为,衡量一个作家的成就无需看他的所有作品,只要看他所达到的最高境界就足够了。”
那么,李佩甫又“达到”了什么样的“最高境界”呢?
李佩甫扎根中原,四十年来,推出了《红蚂蚱 绿蚂蚱》《黑蜻蜓》《败节草》《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和《平原客》等多部小说,主要围绕“中原”(一如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镇、沈从文的边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笔耕不辍。就我看来,将李佩甫有意无意纳入到“乡土作家”之列还是“低估”了他,因为李佩甫早已经超越质朴的“乡土”情怀而将笔触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骨髓之中;他的小说虽然不乏“故事”,却是以“权利”为切入点,以“平原人”的精神生活为关怀对象,审视的正是五千年历史文化浸润中的“人”的灵魂。换言之,李佩甫所坚执的,正是民族文化劣根性中“人”的灵魂叙事!
一
李佩甫非常自觉、有为而坚决地审视“人”的灵魂。从《羊的门》到《城的灯》,从《生命册》到《平原客》,他已经建构起完整的“平原人”的灵魂时空图。
《羊的门》以“中原”腹地呼家堡为着眼点,探究“在这1.5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个头矮小其貌不扬的支部书记呼天成如何成为这方土地上“唯一的主宰”,呼家堡人又为什么“早已经过惯了这种只有一个声音的日子”。
《城的灯》可以看做是《羊的门》的“续篇”——当呼家堡原始共产主义窒息人性的时候,必然有人要拼命走出这片“无骨的平原”,逃向作为现代文明集散地的“城市”,这个人就是冯家昌。冯家昌从上梁村出发当兵,抛弃了“圣女”刘汉香,而娶了又矮又胖的市长女儿李冬冬;还是为了“前程”,冯家昌主动“学习”,并总结出“两条经验”:“一是‘磨脸’,二是‘献心’”。所谓“磨脸”,就是牺牲掉人的尊严,抛弃“脸面”;所谓“献心”,就是要唯权贵马首是瞻,不择手段,不辨是非。正是凭着这种钻营精神,冯家昌一路畅通无阻,飞黄腾达,终于成为了人上之人。
其后,荣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生命册》将上梁村改换成了“无梁村”,冯家昌分解成了考入省城并作了大学讲师的吴志鹏(“我”,精神追寻者)和不断在北京上海深圳攫取金钱荣誉最终从国贸大厦十八楼跳下的骆国栋(“骆驼”,物质大亨)。《生命册》所要探寻的,正是“我”和“骆驼”的“精神之旅”。虽然“我”和“骆驼”貌似成功人士,却“已是满怀疲惫,眼里是酸楚的泪”——用“我”的话来说就是:“每每走在北京的街头上,我心里就荒。”“‘荒’不是慌。是空。”“我”是谁?“我”从何而来最终又向何处而去?
这种“无根”的状态很自然地延伸到了近作《平原客》中。何以命名《平原客》?“在平原,‘客’是一种尊称。上至僚谋、术士、东床、西席;下至亲朋、好友,以至于走街卖浆之流,进了门统称为‘客’。”然而,这只是表层含义,深层意蕴却是:“人海茫茫,车流滚滚,谁又不是(过)‘客’呢?”在作者看来,没有“精神”的平原人,无论何种背景,也不论其后发达与否——即便是黄淮市常务副市长刘金鼎,市政协副主席、“花世界”集团老板谢之长,抑或是留洋专家、政坛达人李德林副省长,都是缺少了“精神”的孤魂野鬼,是一群“过客”。作者非常反对将《平原客》看作是简单的反腐文学,或者以之为侦探小说。在“后记”中,李佩甫明确写道:“我写的是一个特定地域的精神生态”。诚哉!李佩甫筚路蓝缕,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坚决、自觉、有力地建构起了自己的“马孔多镇”,展示了从呼家堡到上梁村,从无梁村到省城这一“平原人”的灵魂时空图。
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李佩甫的“平原”系列小说,都具有直接的“历史感”和“在场感”。这不仅是因为《城的灯》《生命册》《平原客》等与时俱进,写到了省城京城,描绘了中国世纪之交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展开了光怪陆离转型期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扇面,更深一层意义在于,作者将笔触深入到了中国文化的深处,将中国文化的“恶之花”展示得酣畅淋漓。诸如官场伦理、民族劣根性、人性恶等。鉴此,李佩甫的平原系列是中国文化的“内省书”,作者对社会问题的见证与反思,对中华民族文化糟粕的批判,具有了椎心泣血的社会价值。
二
“‘平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的精神家园,也是我的写作领地。在一些时间里,我的写作方向一直着力于‘人与土地’的对话,或者说是写‘土壤与植物’的关系。”李佩甫多次强调,他是把人当作“植物”来写。我们发现,《羊的门》第三节干脆以“草的名讳”来命名,列出了二十四种“在豫中平原最普遍最常见的草”。在作者心中,“平原上的草是在‘败’中求生,在‘小’中求活的。它从来就没有高贵过,它甚至没有稍稍鲜亮一点的称谓,你看吧:小虫窝蛋、狗狗秧、败节草、灰灰菜、马屎菜、驴尾巴蒿……它的卑下和低劣,它的渺小和贫贱,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显现在外的,是经过时光浸染,经过生命艺术包装的。”
同为河南作家的刘震云多年以前的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同样赋予了其中人物如草般低贱“名讳”,诸如孙屎根、孙毛旦、锅三、冯尾巴、李葫芦、赖和尚、冯麻子、黄瓜嘴、赵刺猬、路小秃、许布袋、路蚂蚱等。如果说刘震云所为,更多地是为了突出“历史寓意”——“人物的塑造并不是新历史小说的第一要务,甚至人物只是某种‘规则’中的符号,作家们所热衷的是‘对表象的书写和表象式的书写’,由此构成这个时代的‘后人文景观’”,那么,李佩甫的平原系列小说又为什么让“平原”变成了“绵羊地”,让高贵无比的公民变成了“卑下和低劣”、“渺小和贫贱”的“草民”?
当然是权力!李佩甫的平原四部长篇,正是围绕权利政治、权力伦理来叙写精神荒原的。
李佩甫首先深刻地揭示了权利拥有者利用“法则”(制度)愚弄民众的权力伦理。呼天成何以一手遮天?就在于他善于运用“呼家堡法则”。《羊的门》写道:“‘呼家堡法则’是有关新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一步步完善的,可以说是呼天成领导艺术的具体体现。当它落实到人们头上的时候,就成了一种必须遵守的制度。”哪十种法则?一是村歌,二是村操,三是村规,四是月月“评议”,五是“干部法”,六是学习“老三篇”,七是奖惩,八是民兵巡逻制度,九是婚姻法,十是请假制。总之,推行原始共产主义“制度”,实施愚昧的个人崇拜,愚民政治,目的就是将呼家堡打造成只有“一个脑袋”的封建王朝,让公民变成草民。令人悲哀的是,呼天成成功地利用原始共产主义对抗住了现代社会制度。
其次,李佩甫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真实本质。这就是在权利膜拜下人的“主动向恶”趋势。《城的灯》中,冯家昌逃离上梁村进“城”不断“上升”的过程,其实就是冯家昌类主动向恶的过程。为了“上升”,冯家昌无情地抛弃了顶住村民口水压力与经济困窘、未过门就搬过来照顾冯家昌父亲和四个弟弟的“圣女”刘汉香,而娶了又丑又矮的市长千金李冬冬;还是为了“上升”,冯家昌竟然以李市长的风流韵事做要挟,逼迫作为岳父的他为自己铺平道路……冯家昌作为“一只狗日的虫”,在逼迫自己“忍住”“吃苦”“交心”“内敛”的过程中,不断“学习”、潜心“学习”官场游戏规则!小说写道:冯家昌“躺在床上,听着‘小佛脸儿’的教诲,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绷得紧紧的,这是一次多么难得的学习机会呀,他要张开所有的毛孔去吸收‘养分’……”“他一直在向‘小佛脸儿’学习,学习‘微笑’,学习‘柔软’,学习机关里的‘文明’”,最终,冯家昌将自己“学习”成了副厅级干部,并带动那些让哥哥拼了命也要将自己“日弄”出来的弟弟们“学习”成了“人上人”——老二“学”成了地市级公安局长,老三“学”成了上校衔的驻外武官,老五“学”成了上海一家公司董事长,资产上亿。总之,主动“学习”、潜心钻营,让冯家兄弟“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如此“辉煌”如此“成功”了。《城的灯》反讽意味耐人咀嚼。
再次,李佩甫深刻地揭示了权利的根本属性,即权利最终内化为“精神”,譬如精神尊严,精神膜拜,精神享受等。《生命册》中,同样是村支书,作为抗美援朝英雄的上尉连长蔡国寅曾经何其风光!他虽然个头矮小而且龅牙,但仍然娶了无梁村最美的姑娘吴玉花——“当年吴玉花的婚礼是十分风光的。那年月,她是无梁村第一个坐吉普车出嫁的姑娘。”然而,复原后当上村支书整天应付贫困的蔡国寅,就完全没有了当年的无限荣光,下半生就在与失望至极的吴玉花的争吵当中虚度,在对女儿蔡苇香一次次无奈的牵挂与被抛弃中老去。究其实,一米七二的美女吴玉花当年肯嫁给矮小龅牙的蔡国寅,图的是英雄光环下的精神崇拜;而没有了“父权”的蔡国寅,当然享受不到哪怕是亲生女儿的尊敬。
发人深省的是,在近作《平原客》中,李佩甫刻画了一个人物——副省长李德林的第二个老婆徐亚男。她原先只是一介农村大龄穷女子,被请去照顾腿脚不便、身在农村的李德林的父亲。当她利用身体优势成为了“省长夫人”之后,便开始颐指气使了,譬如动不动打电话给省委机关部门,开口就是“李省长家里的”;她非常享受于作为“省长太太”回到老家的风光与他人的艳羡……为了稳住自己的身份地位,她刻意地“审问”李德林与别的女人之间的关系。“在一次次的讯问中,她成功地让一个副省长在自我证明的过程里变成了一个‘说谎者’。”“只要一有机会,她就一次次地‘审’他。长夜漫漫,徐亚男在审讯过程里,终于完成了从卑贱到高贵的跨越。就此,每一次的审讯过程,都是她的精神成长过程。”笔者以为,吴玉花也好,徐亚男也罢,所争取的不过是“精神”的高地;蔡国寅是这样,李德林亦是这样,所失去的也正是精神上的高贵与尊严。这里的“权利”不是行政上的尊卑贵贱,而是精神的高扬与委顿。当生存权具备了之后,生命意志的恣意实施就成了权利的最高境界。
最后,李佩甫深刻揭示了中国文化中的“权利生态”。一是权利腐败的“渐进性”——正如《生命册》扉页所写:“麦子黄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作为小麦专家、“戴草帽的省长”李德林也是在“没有声音”的不知不觉中成为了腐败者、杀人者。小说中,刘金鼎、谢之长将自己从一介草民“跑”到了、“吃”到了黄淮市常务副市长和市政协副主席高位之时,也在将李德林慢慢地推上了断头台——李德林“觉得自己就像是温水里煮的‘青蛙’,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到了他知道‘烫’的时候,事已晚矣。”二是权利的交互式腐败。谢之长、刘金鼎、李德林等人的权利腐败并非个案,而是官场连锁反应的必然结果。这样的文化生态必然是整体塌方式的腐败,触目惊心,警钟长鸣。
三
在《生命册》“后记”中,李佩甫写道:“是啊,社会生活单一的时代,我们渴望多元;在多元化时期,我们又怀念纯粹。但社会生活单一了,必然导致纯粹。可纯粹又容易导致极端。社会生活多元了,多元导致丰富,但又容易陷入混沌或变乱。这是一个悖论。总之,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所谓的永恒,就是一个字:变。”
正是这样一个永远在“变”——变得或“纯粹”或“混沌”——的时代,让李佩甫生出了“疼痛”的感觉。“我写的平原,应该是生我养我的故乡,我对我的家乡,对这块平原,应该是有深深的情感在里面,热爱着这个故乡。(《生命册》)这本书就是映照自己,反省自己,反省这块土地,反省我的亲人们,他们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写的时候,每当写到他们,心里有点痛,当你拿笔的时候,或者打电脑的时候,真是一种指甲开花的感觉,疼。”李佩甫虽然指称的是《生命册》,其实,我们可以将这种“指甲开花”的疼痛感觉发散到他的整个“平原系列”小说创作之中。《羊的门》疼痛,《城的灯》疼痛,《败节草》疼痛,《学习微笑》疼痛,等等。作者的心,一直在疼痛。
近作《平原客》可以看做是李佩甫“平原系列”小说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作为对“平原人”的再审视,“《平原客》既是我抒写‘平原’的继续篇,也是我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平原’精神生态嬗变的一种研究。过去,我写底层人物比较多,关注的多是底层老百姓的命运,这个作品应该说是对这块特定地域‘精英人士’的一种研究。”可以说,“平原”作为李佩甫的现实故乡和生命家园,“从历史上说,这块土地不仅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也是一块灾难深重的土地。有一个词叫‘逐鹿中原’就是很好的注解。由于这里一马平川,最适于人类生活,同时又无险可守,战乱一起,杀气很重,人如草芥。……所以这里既是历史上儒家文化浸润最深的地方,也是经过历年战乱后,‘羊气’最重的一块土地。所以,我给在这里生活的人们总结了十六个字:吃苦耐劳、坚韧不拔、不择手段、生生不息。这些认知和感觉,我都用在作品里了。”
“吃苦耐劳、坚韧不拔、不择手段、生生不息”!显然,李佩甫是以一种“理解之同情”的心态来进行审视的,颇类似于鲁迅当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从本质上说,李佩甫笔下的冯家昌、吴志鹏、李德林等人都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甚至他们出身贫寒、敢于不断与命运抗争,有可取之处;如果从更高层面分析,他们由乡村到城市,由追求温饱到精神弘扬,也属于人的现代性求索范畴。从一定意义上说,冯家昌、“我”“骆驼”、李德林等人,确实是“吃苦耐劳、坚忍不拔”,即便是他们的毁灭也让读者怦然心动——譬如,李德林的堕落之路,其实也充满了无奈与挣扎,既有自身的性格与心性缘故,也是权力生态圈将其一点点蚕食的结果。
然而,“理解之同情”并不等于认同。“一个民族在行进中是需要‘灯’的。这是信仰问题,也是国民心理与国民精神走向的问题。”我们还注意到,特别有意思的是,《羊的门》中呼天成是特别注重“精神”的——譬如呼天成将犯了错误的呼国庆“保”出来,准备让其充当呼家堡的“接班人”,但是呼天成明确告诉呼国庆:“你没有信仰!”并称“我得把信仰给你种上”。而就呼天成本人来说,为了磨炼心智,呼天成在女人的胴体前练操,以求自己不为所动,李佩甫的细节设置有着“特别”的用心。因为,在呼天成看来,你“要想成为这片土地的主宰,你就必须是一个神。在这个时候(指克服常人世俗欲望——引者注),你就不是人了,你是他们眼中的神。”诚然,呼天成推崇的是愚民政策,有意将自己“神化”,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呼天成同样是一个有“精神”而且精气神十足的人。只不过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走向了人的现代性的反面。《羊的门》如此叙写,更加令人刻骨铭心!
好在李佩甫并没有丧失民族希望——他是通过“预设”来显示人类希望和未来的。具体说,就是作者对于具有中华传统美德“圣女”的一往情深。在《城的灯》中是刘汉香(“汉家之香”),作者赋予她勇敢追求爱情的高尚品质,她大力培植月亮花搞活经济努力拯救上梁村(却不幸被五个年轻盗贼所杀);在《平原客》中是王小美,这个娴静优雅的女性身上所散发出来的“神性”,让城市女郎罗秋旖和世俗村姑徐亚男相形见绌,无地自容。不过,还要说一句,《生命册》中的梅村、电视台女记者夏小羽等人皆不在其列。
“开始了。车轮滚滚向前。那只蝴蝶,卧在铁轨上的蝴蝶,它醒了么?”李佩甫忧心忡忡:平原人,你醒了么?时代车轮在滚滚向前,不可阻挡。还“卧在铁轨上”的平原父老乡亲,你们清醒了吗?
这是李佩甫所努力发出的心声。只是很疼,是那种“指甲开花”般疼痛的感觉。
注释:
①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参见冯牧主编之《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文学理论卷2》,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页。
②陈晓明:《在历史的关节点上——重读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文艺争鸣》2017年第11期。
③《永远的抉择——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人民作家张平访谈录》,《艺境(山西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④张平:《抉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529页。
⑤王学谦:《李佩甫:一个被低估的作家》,《小说评论》2013年第2期。
⑥李佩甫:《〈生命册〉是我的“内省书”》,《中华读书报》,2012年12月26日。
⑦沈嘉达《历史寓言与个人话语——评〈故乡天下黄花〉兼及其它》,《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⑧李佩甫:《文学因无用而无价》,《羊城晚报》2012年5月13日,第B03版。
⑨⑩刘雅麒:《李佩甫:广阔平原是我的领地,而那里的人物就是我的植物》,《北京青年报》2017年6月12日,第B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