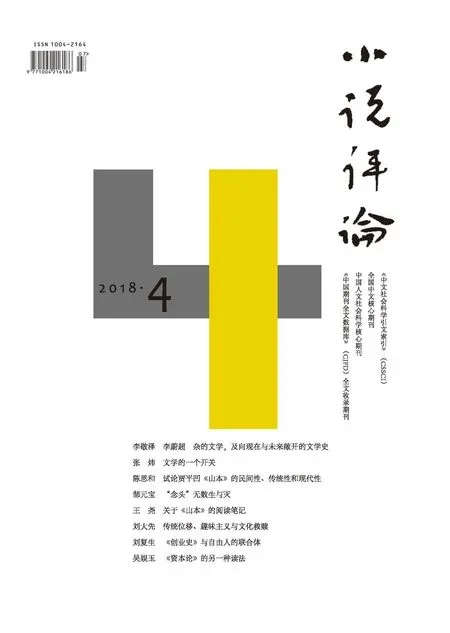李佩甫小说的时空轮转与情感历程
张喜田
一、城乡纠结成为20世纪中国作家的心病
中国的乡村及乡村叙述的问题化,是应该在乡村的他者出现之后。乡村的他者是城市。当城市出现,并发展壮大足以抗衡农村甚至压制农村时才使问题凸显。
鸦片战争之后,现代城市开始出现,现代工人、现代文明开始出现。这时的城市既是人的生活场所,又是人的工作场所,并不仅仅是消费场所和官僚场所。城市成为与农村对立或对应的一个场所,从生活环境、工作场所、生活方式、处事方式等不同于农村的传统。二者产生了一个落差,容易联想与对比,城乡具有功能作用。
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城乡叙述呈现一个历时性的变化:在五四时期,大家勇赴城市,远离乡镇(城镇);在革命文学阶段,则大多是离开、拒绝城市,走向、回到农村。1949年后,随着革命的成功,以及农民、农村在革命中的巨大作用,乡村与农民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地位达到了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地步。到了新时期,城乡发展迅速且差距也越来越大,人员迁移更大。作家由农村到城市、由小城市到大城市,或者由城市到乡村。在城乡的迁移中,伴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对城市与乡村的态度也随时变化,对城乡关系的情感与价值判断的历时性变化更明显。
在1980年代,文学渴望城市,贬乡扬城。改革开放前期,进入城市成为一种冲动,人们纷纷走出大山离开农村,走向城市。
到了1990年代,文学对城乡情感出现交融互渗,互有缺憾。城乡的对立已打破,可以互相往来,农民与知识分子、农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形成一种“互看”“互审”的关系。
到了新世纪,城乡关系的表达与情感指向更复杂一些。城乡碰撞明显,作家对城乡进行多重批判:乡村荒芜,城市堕落;城市不是理想之地,农村也不是精神的归宿。肉体与精神的撕裂更为明显。
李佩甫的创作基本与新时期同步,他的创作可以折射出新时期作家对城乡的“爱恨情仇”。
二、时空变幻,爱恨情仇,寻寻觅觅
根据当下李佩甫的创作情况,结合其对农村与城市的表现,可以把他的创作暂时分做三个阶段:抑城扬乡—贬乡进城—多重溃败。
(一)抑城扬乡
李佩甫的创作是在城市里进行的,但是,在1999年前,他重点写乡村,或者极端地说,他只写乡村。作品中虽然也有城市,但城市只是在农村后面的点缀,既没有形成城市视角来观照乡村,影响对农村的表现,又没有形成作者的生活背景,成为他生活和创作的一部分。如《无边无际的早晨》(1990.9)、《红蚂蚱绿蚂蚱》(1987.1)、《送你一朵苦楝花》(1989.3)、《村魂》(1990.10)等,城市总不在场。在城市缺席的状态下,作家礼赞着农村的朴素人性、和谐的人际关系,相应地从侧面反衬着城市的丑陋。
李佩甫作为河南作家的一员,在早期创作中,常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农村的风俗人情、山光水色,屡屡被他摹画在自己的作品中,作品显露出较为浓郁的田园风味。“他向往具有醇厚、古朴的风俗人情和清新、旖旎的自然风光的农村。笔下很愿意构造出些‘桃花源’式的景象,极力描写乡村水陬田畴的自然美,那往往是一种逃离尘嚣和纷乱的静美,一种笼罩在安谧气氛中的农村的古朴美,作品就往往含有一种隐逸、冲淡的情调。”
《红蚂蚱 绿蚂蚱》写的是动乱岁月中村里人的生产和生活。全村一家人似的和谐、融洽,充满着亲情与天伦之乐。人们之间相濡以沫,同舟共济,不存在尔虞我诈、相互迫害。人们不为争权夺势而为如何把村子搞好、填饱肚子而奋斗。在灾难的岁月中,出现了安定、自足、和谐的人际关系。《无边无际的早晨》更能衬托出农村人的朴素感情。李治国生下来就没爹没娘,但是他没有成为孤儿而乞讨飘零,而是成了大李庄的“小皇帝”,吃百家奶,穿百家衣,长大成人。乡亲们不仅供给他吃穿,而且还培养教育他,在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还总加以点拨。这些折射出了农村的安详和乐气氛,反映了宗法农村自然经济的面貌,也在互相酬答中显露了乡亲们情谊的笃厚、淳朴。
叙述者们虽然生活在城市,但是,主要回忆农村的美好,城市并没有与农村形成对话、对比。虽然他们在城市很不适应,但是如何、为什么如此并没有铺展开,这些只是若隐若现地存在,并没有形成城乡之间的碰撞与淬火,只有一厢情愿式的乡村讴歌。
这期间的两部(篇)作品,《城市白皮书》(1995)、《学习微笑》(1996),城市直接上场,但是,城市并不是作为正面形象出现,反而更印证了城市的丑陋。两部作品均是批判城市的丑恶。
《城市白皮书》中,李佩甫把批判的笔触直击污浊不堪的城市。小说通过一个有病女孩的眼睛和魏征叔叔的信,辛辣地讽刺了市场经济中道德的逐渐沦丧、机制的不合理、法制的不健全等大环境下人被异化的种种形态。作品表达了对城市人灵魂迷失状态的独特感受和深刻认识。《城市白皮书》对城市是一种批判、审视,但是,以童年的残疾审视世界,得出的必然是一个残疾的世界,不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世界。
《学习微笑》以某国营食品厂濒临破产为背景,描写女工刘小水的挣扎以及选择。小说以凄惨的笔调描写了刘小水和她的家庭及亲属为穷困所受的煎熬,这是中国成千上万下岗职工生存状况的缩影。作品也描写了工厂的领导及上级主管部门,直至副市长的腐败。而刘小水为了生存,只好接受领导的安排,走向“匪”,走向堕落。《学习微笑》隐秘地揭示了一个规律:人一旦与环境同流合污,就会“匪”,就会失去自由,而城市这个环境最容易使人“匪”起来。
作家在歌颂乡村的同时,对城市进行了批判。不过,这种歌颂和批判是单向度的,双方没有对比与对话,因为双方是单独的存在,并没有同时在场。尤其,对城市的批判往往是一种意念性、观念性的,因为没有事件,没有环境,人物也只是一个符号。
在城乡关系中,作家早期以城市的不好衬托乡村的好,而他们却忽略了他们当初为何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到城市生活一段后,似乎逐渐适应了城市的生活,这时回忆起了农村的不幸与各种丑陋、落后、卑俗,感觉到了城市的快乐与幸福,但吊诡的是,适应背后却有隐性的最大的不适应。
(二)贬乡进城
新世纪前后,李佩甫的创作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转变,不仅有叙述对象的转变,也有叙述情感、叙述态度的转变。他的叙述对象由乡村转向城市,或者出现城乡交叉与对话。
从1999年发表《羊的门》(又名《通天人物》)开始,作家对农村的态度就发生变化了,即由单纯的歌颂到反思性的批判。
《羊的门》塑造了呼家堡“四十年不倒”的当家人呼天成的形象。他成功地把村人控制在掌股之间的胆识,与他以远大的眼光经营“人场”紧密相连;他用40年的时间,营建了一个从乡到县、从省城到首都的巨大的关系网,这确保了他呼风唤雨、左右逢源的神力和“只有成功没有失败”的辉煌。而作者通过县长呼国庆在当今仕途官场上的沉浮、挣扎,更是把现实的温情与残酷、合作与较量、本真与异化、情感与利益等等,汁液淋漓地呈奉在读者面前。作品通过人物在官场、情场上没有硝烟的搏杀,以现实主义的冷峻,洞透了这块古老大地的精神内核并不只有相濡以沫同舟共济,还有尔虞我诈你死我活。农村并不总是诗意的栖居地。
从《羊的门》开始,李佩甫的乡村由原来和谐的村民关系变为对立的官民关系,村民之间仇视、猜忌。一句话,在农村,人活得不像个人!
《城的灯》中,冯家昌在农村活得最窝囊,最没有面子,从经济到身份,被人瞧不起,被人随意欺负。贫穷、卑贱是他的标签。在这个故事里,父母之爱只作为反衬穷困的无力而存在,而这种无力是被鄙视的;自然之美,只作为他站在桥上看着点心匣里的含糊背景——人可能穷到一定的分上,就不会觉得山清水秀,只觉得山穷水恶了。农村并不是前期的田园牧歌式的中国人的伊甸园。农村破败,农民欺软怕硬,家也不是力量的源泉而成了负担与羁绊。农村似乎成为了地狱,农村人总想逃离。在他们看来,摆脱贫穷的命运只能是进城,当个体面的城里人。只有离开农村到城里去,他们才能有所改变。他们就一心想到城里去。
冯家昌为了能够成为城里人,压抑人性,失去自我,在现实与情感的漩涡中挣扎。他在18岁进入部队,靠打小报告交心获得营长赏识,靠背叛初恋情人解开束缚,靠“办了”领导女儿找到靠山,靠伺候首长的“绝活”步步高升……冯家昌混进上流社会的“诀窍”是,尊严、爱情、良知这些一旦你从内心把它们抛弃,它们立刻就会变成供你向上爬的阶梯。他终于成为上流人物。
这个阶段的描写比较符合农村的现实,也符合人之生命轨迹,因为,作家本身也是由农村逃往城市的。而在早期的描写农村的旖旎风光时,却忘记或忽略了他们当初为何弃乡进城,已忘“初心”。到这时,创作主体与表现主体似乎认同了城市,然而,就在认同的同时,似乎又发现城市也不是那么美好,与当初的期望有很大的距离。
(三)多重溃败
冯家昌从社会最底层一路走来,越爬越高,整整30年,终于混成了自以为有头有脸的“人上人”。但是,他老婆骂他只是个住在楼房里穿着军装撒谎的农民,这一句话点出了他的本质:不论怎么掩饰和逃离,一个人的背景是抹不掉了,那是与生俱来的。“农村”这两个字像标签一样印在冯家昌的脸上,充满耻辱,但又去不掉。冯家昌们在城市里虽然混出了人样,但是还是被人瞧不起,自己也似乎找不到归属感,而农村又是痛苦的源头,他们不愿也不能回去了。城市与农村、故乡与他乡都与自己格格不入,心灵无处安放,陷入了全面溃败。
在作家创作的第三个阶段,在试图与城市认同的时候,也陷入了多重溃败:一是文学创作的溃败:作品明显不如早期的作品自然、厚重、圆熟。二是精神的溃败:灵魂无处安放。
突围与失败是有着乡村情结的20世纪中国作家的共性,在新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在第一个阶段的创作中,农村人想到城市的冲动是被遮蔽的。因渴望而到城里,城市却吞食了他们。因故乡不幸而来到城市,而到城市却又不是自己期望的。背后家乡的根断了,眼前又溶入不进城市。城市与乡村双双沦陷,二者都不是他们所期待的“家”,便展开了对乡村与城市的反省与批判。《城的灯》指明农村人如何到城里去,而《生命册》则说明农村人到城里又能如何?!《生命册》入城第一夜的无助、迷失,揭示了城市的浩大,将吞食、淹没外来者,这一夜似乎也成为一个谶言。
《生命册》既写出了城乡对照,又写出乡村的破败,同时也展示了进城的乡下人在城市的突围与逃逸。丢(吴志鹏)在无梁村的经历与李志国(《无边无际的早晨》)相似,也是孤儿,但是,这里却没有温暖,缺少亲情。因为在农村受到了所谓的恩惠,丢也就有还不清的债,永远“丢”不掉老家。为了躲避这份人情债,他辞掉了大学教师的工作,成了一个“北漂”:没有固定职业,不在体制内,是一个孤独的奋斗者。他既没有在城市站住脚跟,身后也失去了乡村的依靠。
“溃败”不仅是指城乡归属的失败,也是对城乡表达的失败。
对城市的叙述显示出空心化。这种空心化既表现为叙述内容,也表现为叙述本身。城市的生活、叙述者、叙述对象空心化。描写城市生活的几部长篇(《等等灵魂》《生命册》等),从小说的叙述到结构的安排都不成功,也不圆熟。情节太巧,显得虚假,长篇似乎是多个中短篇的联缀。
在早期(刚离开农村时),他们对故乡有一种亲近认同感,而对城市有一种距离、隔阂感。到后期,他们批判农村,这种批判从理性上看,应该是到位的,应该比较接近农村的真实情况。同时,对城市有了认同感,似乎深入了城市,对城市的生活与精神进行了赞同。但是,对城市的讴歌中,却显得隔靴搔痒,那种熟络那种亲近显得那么别扭和轻飘。在精神上、情感上与城市似乎有了共鸣,然而却缺乏回响。“共鸣散布于我们在世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回响召唤我们深入我们自己的生存”,而个人真正的归属感是“去社会化的”,是个人从心底自我去认同归属社会,而不是随众和人云亦云。
《等等灵魂》小说以1990年代曾风靡一时的郑州“亚细亚”商场(省外连锁店为“阡村百货”)为原型,以大都市商战为背景,描写了转业军人任秋风在情场失意之际,接手一个濒临倒闭的国营商场。凭借着大胆的创意、过人的公关能力和卓越的商业才能,以及“商学院三枝花”的鼎力辅助,令商场奇迹般崛起,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超市航母,最终这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又昙花一现般覆灭。
《生命册》从精神层面上看,主人公失去了与乡村的关联,也与城市格格不入,但是这些人似乎在城市经营得太容易了,一厢情愿地意淫城市生活,满满的自恋,包括赚钱与男女关系。骆驼虽残疾,却美女成群,丢也很容易地与另一气质美女上床。人物的经历与成功似乎没有办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并且,他们的钱来得太快,去的也太快。大起大落,转瞬即是。
从小说叙述上看,《等等灵魂》太像通俗小说,是商战+言情,情节流畅,大起大落,富有吸引力,充满阅读快感,但缺乏回味的空间。《生命册》严格来说,不是一个长篇,而是一个个中短篇联缀而成。因为没有统一连贯的情节和人物命运、性格的转变与生成。只是一些事件,通过人物连缀起来。
李佩甫的创作具有代表性,代表了一类(或一代)作家的创作共性。出身于农村(或小城镇),起初讨厌农村希望到城里去,到了城里后精神方面似乎又溶入不了城市。他们通过文学作品表现对故乡的眷恋,有着浓浓的乡愁,而城市似乎是不在场的,最多作为一种乡村叙述的背景存在,与农村形成了一场缺席的对话。等这些作家们在城市生活一段后,似乎深入了城市,这时对农村的表现似乎归于理性,既有歌颂也有批判,城市也开始出现,但对城市似乎歌颂少批判多。到创作的下一个阶段,剧情来个大反转,对农村的批判多了,对城市歌颂多了,然而,对城市的歌颂似乎显出隔膜,他们对城市似乎并不了解,并没有抓住城市的魂儿。这样,他们往往陷入多重溃败:背后失去了乡村的根,眼前又与城市处于“面和心不和”的状态。带着隔膜去叙述城乡,所以写出的作品也显得那么地隔膜生硬夹生。
三、多重溃败原因
(一)特殊出身与经历:非农村出身而热烈歌颂农村
阅读李佩甫的作品,似乎他就是农村出身的、通过写作挤进(或留在)大城市的一个正宗的农裔作家,像河南乃至中国的其他一些作家,如张宇、阎连科、周大新,还有路遥等。然而,文并不如其人!其实,李佩甫1953年出生在许昌,出身于一个工人家庭,在小城市长大。虽然在后来的访谈中,他对自己的出身并不满意,但这比那些真正出身于农村的人来说具有天壤之别。何况,许昌,并不是一个小城市,是一个地级市,不是县城,更不是镇。
对农村的记忆,是满满的诗意和田园牧歌。这源于他有一个城市出身,在乡下只是走亲戚,是“玩儿”的,一不开心可以回城市里去。并且,“城里的孩子”在农村是被人高看一眼的,有无限的荣耀与优越感。他没有受到农村的苦,农村记忆是温暖甜蜜的。而真正的土生土长的农村人是很苦的。作家记得,三年困难时期,乡下的亲戚到城里来,手里提着两串毛毛草串着的蚂蚱,很羞涩地站在门口对母亲说:“姑,没啥拿……”他是城乡差别的“受益者”。
作家也曾下过乡,他1971年下乡。他的知青生活是在汗水里泡出来的。当时他们知青队,有七八十个人,只有四个十分的“劳力”,他是其中之一。劳动强度大,吃饭常常成为问题。但奇怪的是,作家在作品中很少涉及这段知青生活。也许是因为从小有农村生活的经验,对农村生活有点适应,也不是那么痛苦,与其他的知青作家有重大差异。(其实知青在农村的苦只是与原来在城里生活相比而显示出来的,而他们与纯粹的农村人的苦是无法比的。这也就造成知青作家对下乡那段生活采取了有选择的忘却的态度。)早年的经历,让他感觉农村比城市好。这是一种独特的比较另类的想法。
知青生活结束回城之后,似乎并没有感到什么快乐和幸福,是满满的辛苦和寂寞。他曾经在一家生产“牛头刨床”的工厂里当过四年车工。开过各样车床。开车床一天站八小时,很紧张,一按电门,机器高速旋转,起步就是每分钟三千转,得两眼紧盯,搞不好,一刀过去,零件就废了!在这种枯燥、单调、紧张的工作中,觉得返城做工人,特别辛苦,不如农村生活,又留恋起了乡村,当然他还要想办法改变这种处境。
1980年代中国要走出蒙昧追求现代性,城市无疑是现代性的标杆。追求现代,走向大城市成为一种冲动。大多数人(包括农裔作家未成为作家时)希望离开农村走出大山走进城市。李佩甫想当一个作家。作家不仅使他重返精神故乡,还能带来真金白银的实惠,可以赢得尊重,并能改变人生路径与人生价值。经过努力,他终于发表了作品,成为了一个作家。
写作改换了他的身份和职业,使他从许昌调入郑州,由中等城市进入大城市,实现了早期的梦。
然而,他在行动上肉体上虽然进入城市,但是,他的精神与心理上还是眷恋乡村,这种眷恋只好通过文学创作来实现。不过,随着时间的移动,他对城市与乡村、故乡与他乡的情感也要发生变化。
(二)家宅的丧失:难以寻找的栖居
作为人类进步的标志,进入城市往往充满冲动,富有动力,但20世纪的中国作家却在此表现出较为复杂的状况,物质的“城”与精神的“城”多纠结与龃龉。同样,李佩甫进入城市之后,似乎并没有获得多少快乐与安心,进城时的冲动与进城后的不适的矛盾表现得分外激烈,正是在城乡的情感纠结中,形成了他创作的起起伏伏。
李佩甫的人物进城十分不容易便更渴望进城,但进城后又是万分不爽便又回望故乡。作家与他笔下的人物往往形成同构,有着共同的命运与心态。李佩甫第一次去郑州改稿的狼狈相便表现出这种“围城”现象。
到一个陌生世界的生存常常十分艰难。李佩甫笔下的人物虽然来到了省城,但是在这个陌生世界的孤独、隔膜将会长期存在。在《生命册》的首页便显示出了这种痛苦,“我”(“丢”)大学毕业分配到省直单位工作,本来十分高兴,但是一人首次深夜进入陌生的省城是那么孤独、无助、慌恐,并且在过了很久又明白:“要想顺顺利利地在城市里生活,你必须拥有三要素:身份,单位,关系。这三者缺一不可。如果你没有‘身份’,也没有‘单位’,再没有‘关系’,那么你就成了一个漂泊者。城市就像是一个迷魂阵,随时都会有危险。”但这些只是一种可见的需求,而不可见的、无形的更是难以寻到,也更增加城里的外来人的生存困窘与精神疏离。
这是因为找不着家了:家宅丧失了。他们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这是生人的世界,在此他们没有家的感觉了。
空间与居住、与权力相关。空间是权力,空间就是一种赋形,使人的身份成为可能。出身地的空间不仅决定了此地人的身份,而且决定了他们的心理。一些人从农村来到城市,由小城镇来到大城市,明显感觉到城市的在场与乡村(小城市)的缺席。在场与缺席使空间得以凸显。这样就造成了两个空间并存:城市与乡村,并且刺目地显现出两个空间的差别,包括文化、生活、心理、习惯、人际关系等的差别。
城市空间大而拥挤、人群稠密而陌生,形成了一种异己的、他者的力量。而二元制的城乡身份制度,固化了城市的优越感,更加重了进城后的“生人化”现象,使外来者认同城市漫长,溶入城市艰难。
在大城市,距离远、时间紧,聚会没有家乡那么频繁,人情相对淡一些。过去是乡里乡亲的熟人社会,家家户户熟不拘礼,推门就进;现在是高楼大厦的陌生人世界,人们更尊重彼此的独立和隐私,人际交往更强调分寸感。人们不禁发出感叹:“什么时候儿时玩伴都离我远去?什么时候身旁的人已不再熟悉?人潮的拥挤拉开了我们的距离?”(苏芮:《一样的月光?》)城市和路人万千的变幻早就注定重逢也只是擦肩而过,在灰暗的深夜里是寂寞的世界。
作家和人物初次到省城到大城市,具有共同的情境:他们的身子由小城市、由农村来到大城市,实现了早年的梦想,但这个大城市似乎又不是他们自己的。他们常常缺乏归属感。离家的日子,没有家宅的日子,缺乏亲近、认同感,难以寻觅到“诗意的栖居地”,从精神到肉体,尤其是精神上,日子过得艰难。
一种内在的被遗弃感,让他们往往产生一种空间的危机。空间危机,实际就是城市危机。这种危机不仅诞生于农村人身上,也产生于小城市人身上。
不过,人在一个陌生的空间里,与此空间的关系会随时间的变迁而发生着变化。同样,人对陌生空间的情感,在陌生空间的存在感,也会随时间而变化。
时间与空间的交织,形成了他乡与故乡情感的大变化。李佩甫的创作印证了城市外来人的城乡情感随时空变化而变化的现象。他笔下的人物刚到城市时,对城市十分陌生,好奇变成了恐惧,向往变成了疑虑(担心)。进城动力消亡了,内心充斥着满满的无助。这时的城市似乎并不是他们的“栖居”之地,并不是他们所向往的,只能作为“寄居”之地、暂居之地。在寄居之地便忆起了故乡的温暖,所以在离开故乡(农村、小城镇)到大城市伊始,歌颂农村,屏蔽城市。他们带着温情,带着满满的回忆,去言说故乡。故乡叙述既是他们的创作的起点,也是他们创作的高峰。
等到在城市生活一段后,逐渐熟悉了城市,享受到了都市的文明,自己又有了一定的成就,“学会”并“能够”在城市居住,就大胆地描写城市,也就诅咒起了乡村。然而,这时的情感却很微妙,他们似乎得到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曾经拥有的。这就造成他们在歌颂城市批判乡村时的“别扭”。
这些闯入大都市的作家,在创作的后期虽然在生活上、情感上似乎认同了城市,但是与城市还有种隔膜的感觉(这也是20世纪以来中国的城市文学不发达的一个原因之一)。对城市的隔膜,造成写作的“想当然”。他们看得异乡的城市似雾里看花,终隔一层。作家胸次过于狭隘,气度欠小,无感慨少悲怀,多文而少情,多咏风月时尚而少情怀抒发。作品是僵硬呆板枯涩的,而没有前期歌颂乡村时的诗意柔润温暖。作家写得声嘶力竭,但读者阅读总嫌“膈应”。
四、结语
新时期反映城乡关系的作家大多是在摆脱了与农村的基本生存联系、脱出了农夫式的与自然的原始统一后,才开始对农村进行叙述的。
空间的转移才能形成对话,但空间的迁移常造成出门在外的状态,想家、漂泊、羁旅的感觉常在。文学中的一些范畴与关系如“乡亲、异乡人”“内者、外者”“荒野、家园感”“缺席、在场”“异乡人状态”便存在于城乡发生碰撞的叙述中。还有,新时期小说在城乡关系的叙述上沉淀了一些共同的话题,如现代与传统的交融、中心与边缘的更替、家与在路上的碰撞、田园情趣的追求、地母情结的牵绊等。这些原型似的矛盾更多出现在有乡村出身背景而到大城市发展的作家身上,如路遥、贾平凹、莫言、周大新、张宇、刘震云、阎连科、李佩甫等。在他们心中,城市是现代的象征,乡村是传统的象征。在他们的作品中,追求现代文明成为一种主潮,但渴望传统也时时出现。两者常常互相作用、消耗或双赢。作家对此也常常流露出复杂与矛盾的态度,向往现代,但也不拒绝传统。以此表明,中国作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常面临着认同危机,他们在城与乡、现代与传统纠葛中总出现徘徊与迷茫。这也造成对乡村的叙述显得圆熟,而对城市的描写显得隔膜。对乡下的描写多来源于较远的距离与旁观者的身份,乡村的批判要么建立在自己屈辱的地位所造成的先入为主的“仇视”或城市即进步的现代性理念;而神往乡下着重是对农村的风习、自然风光的诗意想象,而对城市的描写总显得“隔”,这既源于作家对城市只能获得近距离的遮蔽而缺乏远距离的透视,也源于对城市情感上集体无意识似的隔膜。
注释:
①马克思认为,“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的一种无差别的统一,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看作王公的营垒,看作真正的经济结构上的赘疣”。(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0),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3页。)
②张喜田:《城乡、古今中的挣扎与修炼》,河南师范大学学学报1997年第3期,第74页。
③[法]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10页。
④⑥舒晋瑜,李佩甫:《看清楚脚下的土地》,《上海文学》2012年第10期,第108页。
⑤张喜田:《苦难的忘却——反思1980年代知青小说》,《文艺争鸣》2010年第12期,第110页。
⑦李佩甫:《生命册》,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