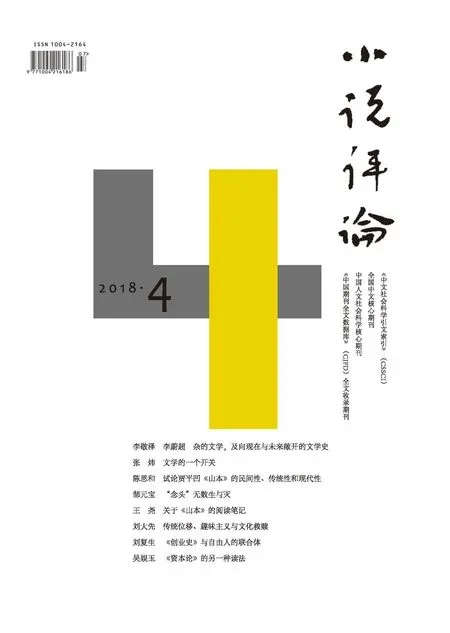论叶广芩系列小说《去年天气旧亭台》的艺术成就
王丽丽
叶赫那拉氏的出身,使叶广芩之往事追忆映衬着老北京的厚重历史与没落贵族情感的丰富意蕴。《去年天气旧亭台》由九个短篇组成,分别是《太阳宫》《月亮门》《鬼子坟》《后罩楼》《扶桑馆》《树德桥》《唱晚亭》《黄金台》《苦雨斋》。从九个题目来看,每一个短篇均以三个字命名,又形成三组字面意义相对的鼎足对,整齐而富有匠心。九个短篇看似各自独立,但其内在又相互联系,是一个精心结构的有机整体。这种联系既体现在人物的一脉相承上,如“我”、苏惠、小四儿、大芳这些人物在几个篇章中都有贯穿,也体现在作家情感与思想的融会贯通中。整部小说中篇目之设置亦有时间的先后承续性,从童年、少年到青年、中年,逐渐步入老年的时间序列中,呈现出一种流动性与整体性。本文试就叶广芩《去年天气旧亭台》(以下简称《亭台》)中诸作,从儿童视角、人性美丑、时代碰撞这三个角度去进行解读。
一、儿童视角
所谓儿童视角,吴晓东认为,即“小说借助于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讲述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的特征,小说的调子、姿态、心理和价值准则,诸种文本结构、美感及意识因素都受制于作者所选定的儿童的叙事角度”。叶广芩《亭台》中的很多篇章都是从小时候的“我”切入叙述的。儿童视角的切入让人感到小说中的“我”以一种不同于成人的新奇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儿童的视角如此美好,机敏活泼又意趣盎然,将散落于童年岁月的一颗颗记忆珍珠穿起来。用儿童的视角去感知世界和了解世界,使成人眼中有些平淡乏味的现实生活变得丰富而奇妙。
作家用儿童视角写寂寞的童年,透过儿童的心灵世界,展示出人类精神状态最底层的一部分。《太阳宫》中写“日子过得有一搭没一搭,挺憋闷,主要是没有‘事情’可干。我的活动范围就是院里,到胡同都得征得妈的许可。”没有什么干的事就唱歌,想唱什么就唱什么,最后唱累了,就趴在台阶上睡着了。无事可做,就一直“看下雨,看下雨,看得我越来越困,眼睛睁不开了……砰!脑袋撞在玻璃上。”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到作者寂寞的童年,以及寂寞童年中飞扬的想象力。其实,人性中普遍有深刻的寂寞与孤独感。也许,在成人的世界中会认为小孩懂什么,小孩不会寂寞。然而,小说正是从这样的儿童视角,让我们看到儿童的寂寞,仿佛是人类童年的寂寞,带着一种对人类与生俱来即被疏离的深沉透视,儿童的天真单纯与儿童的孤独寂寞在小说中融为一体,令人回味与深思。
在《月亮门》中,作家从儿童的视角写出了孩子对自己身体成长的懵懂与好奇。在儿童视角的关照下,对于胸罩、例假、生孩子这样一些话题,充满了新奇而又神秘的朦胧色彩。一幕幕的闹剧让人忍俊不禁,也展现出儿童世界的天真烂漫和纯真活泼,会勾起很多人对童年的回忆。《月亮门》中孩子们对苏惠妈妈的敬慕则体现出对美的向往与追求。在李立子看来,苏惠妈妈比他漂亮的演员妈妈更美,因为苏妈妈透露出娴静、淡雅、精致、从容的美,而且她总是对着他们微微笑着,有着孩子们喜欢的温柔暖意。也许,在很多人的童年中,总有一些人会带给他美的感觉,启示他引领他去感受美追求美。这也是很多孩童世界中一种很重要的记忆。
在《亭台》一书中,作家之所以采用儿童视角进行叙写的原因,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思考。
首先,在叶广芩小说中会较多运用儿童视角,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作家写作到一定阶段后表达的一种内在需求和必然选择。叶广芩不是一开始就写回忆性的家族小说的。在她的早期作品中,有《岸边》《退位》《孪生》等一些表现农村和城镇的小说。但正如作家自己所言,“我从80年代开始写小说,我写的很游离,是自己跟自己的游离,也就是说没有写进去自己生命的体验,那时候我虽然写了不少作品,但以北京文化为背景的作品从未进入过我创作视野的前台,这可能与各种条件的限制有关,我回避了个人家族的文化背景,不光是不写,连谈也不愿意谈,这甚至成为我的无意识。”但当她一旦碰触到了儿童时代的经历,作家终于以一种回望的姿态,找到了能够融入自己生命体验的适合自己的言说方式。所以说儿童视角的叙写是作家对于自我和家族重新审视的一种途径,是一次对自我和家国历史进行观照的心灵之旅。
其次,儿童视角也是展示作家诗意灵魂的一个窗口。从叶广芩的很多自叙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敏锐、善感、孤独、多思的自我形象。而童年的孤独和善感也正是很多作家都会经历的心灵体验。通过儿童视角,让我们看到作家童年的经历与心灵触角,展示出作家从童年时期即有的诗意心魂。
二、人性美丑
在《亭台》中的很多篇章都对人性的善与恶进行了探讨。作品呈现出对善的悲悯流露,对恶的痛快揭露,甚至包括挖掘出“我”的“恶”。小说将大历史、小人物,人性的丑卑、光辉及复杂都展示得令人唏嘘、感慨。
在《月亮门》中,作者塑造了郭梓仁这样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小学教师形象。他的外号叫“瓜子仁”,堪称一个人性恶的代表。在“文革”中,他成为一个上窜下跳的帮凶与小丑。他批判老七画的画时说,“什么都有阶级性,人是这样,花也是这样,牡丹、芍药代表了反动统治阶级,菊花代表了逍遥派,水仙、兰花是小资情调,喇叭花那是保皇派吹鼓手”。老七说怕晒太阳,因为对紫外线过敏,结果郭梓仁说红太阳就是毛主席,害怕太阳就是和主席作对,给老七扣上了“大帽子”,最后被关进“牛棚”。通过这些事件,郭梓仁的卑鄙的人性之恶被揭示得淋漓尽致。一个卑鄙的人却在那个时代如鱼得水,可以宣判和掌握很多人的命运,更看出“文革”的黑暗与荒诞,也反映出作者对时代、世情、社会、文化的深沉思索。
《树德桥》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叙述了历史与人性。小说中的人物都是“牛棚”中的人,作者戏谑地称这些“牛”都是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而来,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不远万里来到这片盐碱荒地。这样的戏谑里面有对荒诞历史的无奈幽默与超脱审视。主管刘队长生硬、粗暴;强大夫原来是兽医,甚至还是喇嘛;牛树德处境悲惨,饱受冤屈。牛树德刚从海外归来,中国话还没完全学好,因为说话带外国字,造反派就把他的声带用手术刀毁了,成为了哑巴。他虽是哑巴,不能言语,但他心里澄明如镜。他解剖老鼠,认真研究,终于弄清了“五七”干校无端死人的罪魁是鼠疫,用英文写出了病因,却被无知的“我”“出卖”,最后被警车带走。
小说中的主人公牛树德是爱国的,他不留恋国外的优厚条件,学成毅然回国。尽管他深受迫害,但正直善良的人性却从未泯灭,闪烁出一种高贵的人性之光。相反,“文革”的粗暴,很多人的愚弱 ,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在运动中缺乏理性与自知,对强权软弱,对弱者残忍,则显示出荒谬历史中的人性之恶。莫言说:“只描写别人留给自己的伤痕,不描写自己留给别人的伤痕,不是悲悯,甚至是无耻。只揭示别人心中的恶,不袒露自我心中的恶,不是悲悯,甚至是无耻。只有正视人类之恶,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才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悯。”叶广芩的这篇小说,就具有这种“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
《唱晚亭》揭示了人性的贪欲。金家子孙为了金钱利益,把祖先留下来的一块刻有“唱晚亭”的石头千刀万剐,等到郭老板说里面没有玉,就大骂祖先是傻帽, “太阳的余晖中,‘唱晚亭’的石头旁,同一个地点,同一个时间,一群金家子弟同样在叽叽喳喳,与他们的祖辈比,没了热闹的锣鼓经,没了悠扬的西皮流水,他们闹腾的是另一个话题——钱。”在这儿,我们看到了后代的坠落,在精神上他们没有了贵族的风雅追求,眼中只剩金钱利益。他们把祖宗留下来的一块刻有“唱晚亭”的大石“碎尸万段”。当他们见到这块石头时,想到的不是家族走过的风雨历史,也没有缅怀先人的悠远情怀。他们粗暴地让玉石厂一刀一刀切割这块大石,只盼望切出玉来发财,而最后结果出来了,玉石厂说什么都没有,而且要收一大笔费用时,他们个个都赶紧躲开了。在《唱晚亭》中,淋漓地展现了作者对一种庸俗浅薄人性的尖锐批判,他们满嘴粗话,满眼是钱。小说是对功利性生活态度的一种批判,也是对于一种矜持典雅的生活的追忆与眷恋。
不管是对人性之恶,还是人性之善的描写,我们看到了叶广芩目光穿越时代、历史的睿智,也看到了作家用心魂去感悟和触摸生命与人性的情怀。
三、时代碰撞
叶广芩在《亭台》的写作中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将儿童的“我”与现在的“我”对接起来。儿童的“我”遇到的人与事,多年以后,再次出现。作家让儿童时期隔着岁月的迷离回望和成年时期的理性审视、直面现实相遇合。不似当下很多回忆性的写作,更多的是仅停留在回忆,从而容易形成一种牧歌式的赞美或伤感。叶广芩作品的故事不停留在过往,透露出一种直面与逼视的勇气与态度。在某种程度,这既体现出作家的一种写作态度,也体现出一种生活态度,令人深思。
首先是景物的变化。在《太阳宫》中,儿时的太阳生气勃勃,作家用“跳”出树枝,“升”上天空这样的词语来形容那时的太阳。太阳给大地染上金色,风中的树叶也有了金属的声音,人在阳光与微风中,变得澄澈透明,飘然如仙。在小说中可以看到在儿童眼中的万物光辉,充满了一种圣洁、光明、诗意的生命体验。然而,几十年后再次描写北京又是另一幅图景。沧海桑田,变化迅速。“提着一兜菜我站在汽车站,周围林立的高楼让我不知身在何处。太阳从东边升起,太阳宫,太阳的宫殿,如今又有谁还知道它曾经的模样?我想起了我要为太阳宫而写的诗,几十年了,一直没有完成它,关键是再没有看过那样的日出,没有过那样的心情和感动。”
从前的日出那样壮观,那样充满诗意,而今的太阳放佛连自信都失去了,一切景物都失去了童年视角中的浑然天成与光辉动人,也许这不仅仅反映的是景物的客观变化,更是多年以后,对物非人非的一种嗟叹!而《太阳宫》最后的一句:“曹太阳,你是否还在人间?”也已经不仅是景物的变化,更是写出了作者对儿时玩伴的一种深情呼唤,对纯真的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眷恋,对人事变迁的感慨。
在《黄金台》中也有时代碰撞。有富商看中了黄金台的名字和风水,要在那里修建大型的商场会所。这些有着赫连勃勃英武祖先的刘姓后人,有的已经拿着钱走了,一部分还在高举风中飘荡的黄旗,为这美丽的村庄做最后的坚守。在这里,文化与商业对抗,祖先与后人对照,光荣与金钱决斗,展示出作家直面时代碰撞时关于英雄、荣誉、梦想、村庄式微的一种深思与忧虑。
在叶广芩的小说中,因为要写出这种碰撞,所以在很多篇什中,除了儿童视角,又会有一个成熟女性视角的展现。这样的从过去直至现在的复调视角的运用,使作品因为经过了时光的过滤,产生了厚重感与丰富性。过去与现在相碰撞,展示的依然是作家心底对于真善美的质朴追求,对于历史、对于现实、对于人性的直接面对与深沉思索。
《苦雨斋》是《亭台》中的最后一篇。虽然表面上是写有手机有现代的生活,没有很明显的对过往的描绘,但实质上它是一种寻根,是受父亲的指派,寻找一个多年失去联络的人,因此它依然是试图完成过去与现在的一种连接,依然是一种时代碰撞。
作品中所体现的这种让时代碰撞,直面现实的风格也是有原因的。在作家的生命历程中,目睹了历史与家族的巨大变迁,父亲于1956年去世,她1968年离开北京,当过护士喂过猪,经历过“中年待业”,这些生活的历练与磨难,都化成了作家生命内在的一种独特力量。她将幽默、大气与深沉、哀婉融为一体,透露出直面生活、生命的能力,也形成了其作品独特的美学风格。
注释:
①吴晓东、倪文尖、罗岗:《回溯性叙事中的“儿童视角”》,《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1期。
②③⑤⑦⑧⑨叶广芩:《去年天气旧亭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5 页、7-8页、97页、300页、51页、51页。
④周燕芬、叶广芩:《行走中的写作——叶广芩访谈》,《小说评论》2008年第5期。
⑥陈莉:《〈人生〉距离悲剧经典有多远》,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