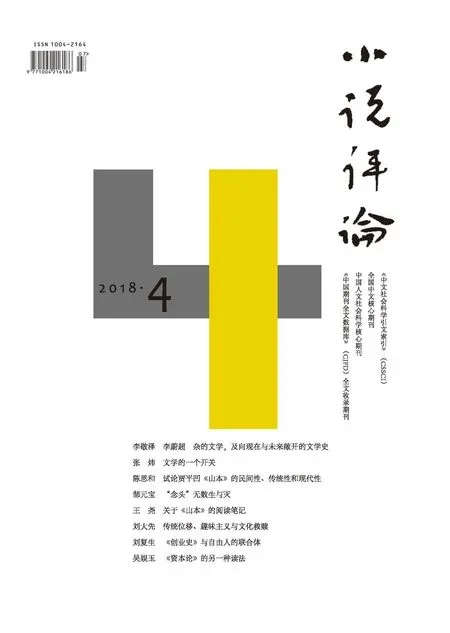莫言小说和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理论探微
张建华
莫言之小说,以其鬼斧神工的笔力,营造出一种超越文化和国界的奇谲意境和范式,在同时代的作家群体里,无疑是独树一帜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莫言小说与古典小说戏曲理论特别是李渔戏曲理论的内在联系。
周明全老师《回到文学的源头》一文说古典小说是质朴、简洁而充满想象力的,将“想象力”作为新时期文学最欠缺的东西,同时认为“当下小说要有所突破,至少在文学想象力上,应有所改变。重构文学想象力,自然有很多路径,虽然回到源头只是一种方式,但我目下的意见却是要老老实实地回到传统里,回到文学想象的源头,重新建构我们的文学想象。”在此基础上,周先生对莫言的《蛙》评价是“有一定的想象力”,然而读下来“最终给人的感觉是沉重的,想象力像是捆绑着翅膀的飞鸟。那么,是什么捆绑了他们呢?我以为主要还是他们心态的浮躁,急于批判现实,降低了文学的品质,因而在批判中抹杀或降低了文学的想象力。作家不是不能批判现实,但是作家的第一职责,是写出高质量的文学作品。批判只是作品的外延价值。”推崇文学的想象力,的确是正确的核心导向,但是周先生将想象力与批判现实的精神实质对立起来,就有一些以偏概全了。
可以说,凡是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以批判或者说内在的批判作为灵魂核心赢得文学史的赞誉,几乎没有文学作品是游离于社会和时代而永久保有生命力的。莫言的小说之所以如此动人心魄,极致张扬的想象力和隐藏在古典小说戏剧外壳背后的批判力量正是其价值核心所在。面对世界,他并没有虚伪地粉饰太平或者退缩畏惧,他是一个高举着长剑的中国式唐吉可德。
一、色彩 结构 对抗
李渔的戏曲理论煌煌大矣,然与当时文坛相较,其优势一是首重结构,二是要求“一人一事”,且要求以舞台表演为着力点,这种见地不但溉济其自身创作,亦对此后的戏曲及小说创作影响深远。莫言先生的《蛙》《生死疲劳》《檀香刑》是否与李渔理论暗合?文本回答了这个问题:古今回应,巧夺天工,二者在某种隐含的语义场景下形成同构关系。
李渔的《闲情偶寄》乃中国养生奇书。其中词曲部、演习部、声容部专讲戏曲,而词曲部则认为“结构第一”,非常重视戏剧结构布局。他说:“填词首重音律,而予独先结构者,以音律有书可考,其理彰明较著。”“至于结构二字,则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韵抽毫之始。如造物之赋形,当其精血初凝,胞胎未就,先为制定全形,使点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势。倘先无定局,而由顶及踵,逐段滋生,则人之一身,当有无数断续之痕,而血气为之中阻矣。”“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传奇亦然。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为一人而设。”此三段引文,第一是说结构布局是一篇文章之首,比之音韵辞藻更为重要;第二是说结构之外,一人一事,中心突出,不枝不蔓,是写传奇的不二法宝。
李渔关于传奇结构的理论,最突出的便是“立主脑、脱窠臼、密针线、减头绪、戒荒唐、审虚实”。李渔提出这种理论是在其写作传奇之先,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李渔是先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再据此理论框架有意识地创作传奇作品。
关于李渔戏曲理论对小说创作的影响,蔺九章早在2005年就做了二者之间的关联研究,着重强调了李渔在语言运用上的‘尖新生动’;卢旭在2007年从结构、情节、语言、戏剧性四方面对这一范畴进行了深入论述;梁鸿鹰评价《裸地》时就以李渔的戏曲理论“立主脑、密针线、减头绪、审虚实”为纲结构论文主体,以故论今,以古为新,让人不禁眼前一亮。他说:“《裸地》很容易让人们想起李渔关于戏曲结构的那些讲究,比如立主脑、密针线,比如减头绪、审虚实,小说按照这些个路数亦步亦趋,生成了格外饱满绚烂的文本。”2017年,杨昊冉再次将这一理论搬上理论舞台,认为关于这一理论“历来备受争议,许多学者在理解上也都存在着诸多分歧。”
由此梳理可见,这种戏剧理论的影响是深远而长久的,对当时及以后的戏剧创作具有无可置疑的指导作用,三十年代丁西林的戏剧创作就明显受到李渔创作理论的启发,据说其《一只马蜂》《三块钱国币》就是受李渔结构理论的启发而产生的。而值得一提的是其理论对文学殿堂其他文体的创作也具有鲜明的文学史意义,比如本文所论莫言的小说作品。
莫言的小说,获诺奖或许是偶然和必然的结合,是西方文化对中国本土文明的一次情感和价值观的碰撞交流。他运文生事,不走寻常路,每一部小说都会与以往的创作迥然有异。但是这些小说在写作过程中体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对中国古典戏剧戏曲理论尤其是李渔戏剧理论的创造性吸收,使其小说呈现出一种浓厚的戏剧舞台氛围和惊堂木插科打诨似的诙谐意蕴,以及深刻的哲思理趣。
戏剧,尤其是中国古代戏剧,往往注重声音色彩的对比和舞台氛围的营构以及冲突的集中;注重结构的精细剪裁,使其婉转低迴一波三折。总结下来,即李渔所谓“立主脑,密针线,减头绪。”
莫言的主要作品有《蛙》《生死疲劳》《丰乳肥臀》《檀香刑》《食草家族》《四十一炮》《红高粱家族》《十三部》《红树林》《红蝗》《牛》《白棉花》《透明的红萝卜》《战友重逢》《酒国》《酒神》《我们的荆轲》《会唱歌的强》《师傅越来越幽默》《老枪宝刀》,除了诺奖、茅盾文学奖,他还获得了“红楼梦奖”、法国儒耳·巴泰庸外国文学奖、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韩国万海文学奖、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巴金之外第二个获此奖项的亚洲作家),实在是硕果累累。
在这些奇花异卉的小说丛林里漫步,只要稍加留意,读者就可以发现莫言特别喜欢用漫天盖地的色彩来表达和宣泄情感,且红色是他特喜欢的一种颜色,本文提到的作品共有21部,其中四部就用“红××”冠名,使其扬名世界的电影《红高粱》,就大幅度使用充满刺激和张力的红色高粱地对观众的欣赏世界造成强烈而持久的刺激,并进而因为中国的就是世界的这种文艺理念,为中国文艺走向世界撩
开了神秘的面纱;《白棉花》楔子里,作者描写大背景的语言充满隐秘的激情和活力:“那年棉花疯长,雨水充足,花棵子足有一米半高。清晨,大雾弥漫,一块块的红太阳从雾中显出来,天地间仿佛拉起了一幅无边无缘的粉红色纱幕;《檀香刑》中,每次行刑之前,顶级刽子手“姥姥”便在脸上涂上鸡血,这种仪式里显见令人战栗的血腥的红色。而小说一开头被一个女流之辈杀了的公爹,也头戴着“红缨子”瓜皮小帽。其他如“迎着通红的太阳”“青石街上汪着一摊摊的血水”“伸着红脖子,头顶一团白花花的乱毛”“俺突然看到,爹,您的头泡在周聋子的水桶里。桶里的水,变成了红殷殷的血”……这样的语句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众所周知,红色是中国传统戏剧常用的颜色,舞台上,轻捻慢挑,长袖曼舞,惊鸿回眸,一颦一笑,都少不了用红色来铺垫和衬托。此外,白色也是莫言比较爱用的色调,《白棉花》楔子里描述了一幅如诗如画的场景:“棉花被霜打掉大部分叶片后,棉桃成熟开裂,洁白的棉絮膨胀出来,一片片的棉花,像蔚蓝天空中的片片白云。”一红一白,一热烈一沉静,可以视作是莫言对传统戏剧和传统绘画艺术的一种张扬和内在的借用。莫言还善于用各种不同的色彩比对出鲜活有趣的生活画面,“这里是成堆的白,外边有青翠的绿,鲜艳的红萝卜,金黄的豆叶,一行行耸立在渠道边像火炬般的杨树。”在这里,白色,青翠,红,金黄,火红,大自然成了一个宛如油画的天然大舞台,乡民们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表演,镜头远处,乡民们一边劳作一边诙谐调笑,镜头拉近,方碧玉从棉花田里朝我们姗姗而至。这里有一段唱词:“哎哟我的姐你方碧玉!你额头光光,好像青天没云彩;双眉弯弯,好像新月挂西天;腰儿纤纤,如同柳枝风中颤”,这是来自小调《十八摸》的词,闭目沉思,则仿佛见一长袖飘飘的绝美旦角,分花拂柳从新月斜挂的田野中袅袅步来,当真是美不胜收。侧面也证明莫言有意对古典戏曲戏剧的吸收和化用,颇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意味。
从戏剧结构这个纬度深入纵观本文所述莫言的小说,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有完全迥异于其他成果的形式和奇思妙想,绝无雷同者。莫言说:“作家抄袭自己比抄袭别人更可耻。”这种思维使他每创作一部新作品时都要努力地寻找突破和变革。莫言重视结构,重视推陈出新,这一点无疑跟李渔的理论是相符合的。
事实证明,莫言的尝试是成功的,他用无所依傍的形式和天马行空的语言创造出了奇幻诡谲的艺术世界,成了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殿堂上一道厚重的风景线。单就结构的“脱窠臼”而言,《檀香刑》《白棉花》等作品,作者有意识地采用楔子和尾声的结构模式总领全篇,这明显可以看出他对于传奇的前身元杂剧的结构特点是有意地进行了移植和吸收的。
《蛙》的结构与众不同,小说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四封长信和一部话剧共五部分组成,其中每一封信则分别由序言和十五章、十二章、八章、十二章的容量来经纬穿插,话剧由序言、人物表和九幕短剧构成。据360个人图书馆资料,莫言最初构思的结构方式是将戏剧和书信两种文体交织在一起:坐在台下的剧作家蝌蚪观看话剧时激起一段段回忆勾连其姑姑的一生——可惜由于写作过程太过艰辛而半途流产,遂采用现有结构框架,之后写作非常顺畅,莫言曾说结构变化后的写作过程有一种特别酣畅淋漓的感觉。
从莫言的这段关于创作的言论可以看出,在《蛙》的写作过程中,莫言首先注重的不是辞采,而是文章的结构。因为《蛙》的行文脱离了莫言一贯的狂狷不羁,变得平和朴素。说明不但在结构上,而且语言上莫言也在尝试“脱窠臼”。
莫言在《蛙》的前言中写道:“先生,我想写一部以姑姑的一生为素材的话剧。初二晚上在我家炕头上促膝倾谈时,您对法国作家萨特的话剧的高度评价和细致入微、眼光独到的分析,使我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我要写,写出像《苍蝇》《脏手》那样的优秀剧本,向伟大的剧作家的目标勇猛奋进。”这段话开门见山地告诉读者,莫言是以写戏剧的热情和目标写小说的,他刻意地要写出国民心底的痛和反思,包括蝌蚪的自我反思。大而化之,人的生命在历史长河中宛如一出戏,生旦净末丑粉墨登场。《蛙》就是专为姑姑所设一个从历史中一段一段穿行而过的舞台剧。这也是跟李渔认为戏剧要注重场上表演的理论是暗合的。
莫言采用第一种穿插糅合的结构方式失败了,而第二种书信体加戏剧体的结构方式却异常顺利,说明前一种方式头绪太多,要让一锅大杂烩做的色香味美,并非易事。莫言说他写作中为了避免混乱不得不用三种颜色的笔区别戏剧部分和叙事部分,以便自己回头查考,连他自己都觉得线索紊乱的话,读者更加会觉得莫名其妙;而后一种方式,脉络清晰,叙述有条不紊,正暗合了李渔的“立主脑、减头绪”之论调。改变后的小说紧紧围绕姑姑历经波折的一生展开,叙写了她悲剧而矛盾的一生,爱而不得,慈而不能,总是在一种大爱和原则之间纠结徘徊。
除了色彩的大肆张扬渲染和结构的变革更新,莫言更直接将戏剧舞台植入小说创作之中。
小说末尾以序幕和九幕剧作结。戏剧第一幕开始说:“一轮巨大的月亮在天幕上熠熠生辉。幕后传来鞭炮声,不时有灿烂的礼花照亮天幕。”可以看出莫言在以爱的色彩开启人生的大幕。第二幕伊始,作者写道:“在绿色的灯光照耀下,整个舞台像一个幽暗的水底世界。舞台深处,有一个周围生满细草的山洞。从山洞中,不时传出青蛙的叫声与婴儿的哭声。有十几个婴儿,从舞台上方垂挂下来。他们四肢抽动,哭声连成一片。”“一个身穿绿色小肚兜(兜肚上绣着一只青蛙)、头皮光溜溜犹如一块西瓜皮的孩子,率领着一群坐着轮椅、拄着双拐、前肢上绑着绷带(由儿童扮演)的青蛙,从那个幽暗的洞里钻出来。绿孩子大声喊叫着:‘讨债!讨债!’‘青蛙’们发出嘎嘎咕咕的叫声。”这两段更是从色彩、声音、意象、背景等角度将场上功夫做足了。第八幕设计更是别出心裁,其开头标识为“电视戏曲片《高梦九》拍摄现场。”这里,高梦九:“(抓起鞋底,猛拍案桌)呜呀呀呀……烦恼!”接着,有唱词和宾白,介绍了高梦九的履历和现在要审理案件的情由。这里戏中有戏,更进一步地说明莫言是在有意识地将中国戏曲和西方戏剧融会贯通,寻找一种崭新的表达模式。莫言曾经说过要学习《聊斋志异》,说明莫言对世界的理解正在浪漫唯美而且深知其痛的路径上,那么在明末清初对世界具有真知洞见的李渔很可能成为莫言的学习对象,焉知这种结构设置不是他对李渔的戏剧理论一种有意识的学习和借鉴呢?
莫言小说奇特的地方在于一种漫无边际的想象和内在的节制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在限制的刀锋上舞蹈”。莫言说:“写小说是挖空心思遣词造句,写地方戏曲文学剧本,大段的唱词,只要能够押韵,只要能够把人物的性格表现出来,还是相对自由的,当然它会受到韵脚的限制,但是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有限制才有创造,完全没有限制是没有创造的,高端的艺术创作,往往都是在限制的刀锋上的舞蹈。”这说明莫言在小说创作中对于地方戏曲的借鉴和融入是非常明确的自觉意识的,这一种自由和节制的对抗使得他的小说创作具有收放自如的内在张力和鲜明的戏曲情结,同时具备了两种文学形式的潜在优势。
二、氛围 舞台 声明
小说注重结构,本是分内之事,但是与严歌苓更注重叙事、雪漠更讲究思想的意义、马步升则比较注重历史的厚重感这些特点相较而言,莫言小说的结构特点就尤其显得别具匠心,他无所依傍也不屑于依傍的命意和辞采既体现出传统文化的内蕴又与西方现代派戏剧相呼应,就像魏晋士人,表象上是浪迹山林啸傲聚散,骨子里却是冰清玉洁,只不过将眼泪的激情以一种荒诞和滑稽的场面和文字传达出来,这种意蕴显示出一种巨大的智慧,直逼哲学层面,可以说莫言是现当代的庄子,以畸变的人物与残缺的事件与现世的冷漠笑着对抗。这种大智慧,诺奖的评委也许看到了。中国哲学在国际上的研究价值越来越高,中国的就是世界的,是中国色彩给莫言天马行空的文字游戏定了一个超越历史和国界的基调,并因之被鲜花抛中。古典戏剧舞台氛围的营造,是莫言另一个有意识的尝试。
尹林认为,“戏剧因素在莫言的小说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精彩的故事、离奇的情节是他吸引读者的首要筹码。而西方的当代小说,抒情以及哲思则占有更大的比重。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或许与中国读者的戏剧心理有关系。在此种情形下,莫言等中国作家被动地接受小说‘戏剧化’的现实,但另一方面也开始进行小说结构上的探索。他们对于小说结构的努力,未尝不可看作是对小说的复杂情节亦即戏剧因素的规避。而这种小说‘戏剧化’的倾向,有可能暗示着中西方文学抒情传统的角色互换。”这段话充分证明莫言在小说创作中有意识的形式结构革新已经被学者注意到了。
《生死疲劳》是莫言的另一部力作。著名评论家李敬泽高度赞誉之:“《生死疲劳》是一部向我们伟大的古典小说传统致敬的作品。这不仅指它的形式、他对中国经验和中国精神的忠诚,也是指它想象世界的根本方式,现代小说已经遗忘了这样的志向,而《生死疲劳》让我们记起了那种宏大庄严的景象。”这里所谓宏大庄严的景象,正是作者为了规避读者心理,有意接受中国传统戏剧的调节和干预,从而形成强烈的主观戏剧舞台效果。
大地主西门闹因历史原因含冤而死,在轮回之路上飘飘荡荡,先后经历了驴、牛、猪、狗、猴、一个无药可救的大头婴儿这诸多真幻相伴的世相,作者以大头婴儿为叙述者,喋喋不休地讲述着他化身为牲畜时的见闻感受以及西门闹一家与蓝解放一家半个多世纪的悲欢离合。奚遥认识到了莫言《生死疲劳》的戏剧元素,从戏剧语言、戏剧时空、戏剧程式和戏剧冲突四个方面阐释了其戏剧因子。她说:“戏剧时空要求剧中人活动场所相对固定,也要求剧本作者掌握好戏剧的发展节奏,太慢则嫌拖沓,太快则不利于观众理解。这一特点在《生死疲劳》这部小说中同样也有体现。”徐红妍则从民间叙事和历史意识角度分析了这部小说的戏剧意识。文章摘要开宗明义,“莫言的新作《生死疲劳》延续了他一贯的民间写作立场与历史意识,却采取了一种戏剧化与狂欢化的方式来审视民间社会与历史,看到了民间社会在主流政治入侵后所发生的改变与异化,以及荒诞的历史表面背后所折射出的巨大悲剧。”
早在2009年,毛克强就发表了这一言论,“莫言的《檀香刑》以‘戏说体’的构成方式,对历史叙事长篇进行了戏剧化演绎,突破了史诗的宏大叙事,对历史人物以戏说的描写笔触,关注历史人物的审丑评价,打破了史诗人物的英雄品格;在细节和语言方面,结合猫腔的唱腔和对细节的重彩浓墨的渲染,增加了舞台的气氛,使长篇小说的创作跨越戏剧和小说,构成了跨体写作的文学典范。”在这里,“戏说体”这个概念意味深长,它明确指出了莫言《檀香刑》的戏剧模式,插科打诨,寓庄于谐,在看似无厘头的情节和话语中寄寓着深刻的哲理和含泪的微笑。作品伊始,莫言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切入,说“我的故事,从1950年1月1日讲起。”与副末开场何其相似;作者在引戏末尾意味深长地让西门闹打翻了孟婆汤并且说:“不,我要把一切痛苦和仇恨牢记在心,否则我重返人间就失去了任何意义。”接着故事相继出现驴、牛、猪、狗、猴的短暂一生,恰似明清传奇的“出”;最后大头婴儿出现,收束全文,也恰似《桃花扇》的道士张瑶星点醒侯、李二人。这种结构形式首尾相衔,具有很强烈的戏剧意识。
从小说开篇细节审视,以阴曹地府、阎罗大殿、油锅鬼卒,炸得焦黄酥脆的死尸喷着油星子喊冤,整个画面充满了晚明时期《牡丹亭》、《十二楼》华丽荒诞的气氛和色泽。整个小说仿佛大幕刚刚开启,台上,粉墨登场的阎王、判官、鬼卒、烛火,在一个死尸的目光里形态毕肖;再看人物语言,掖了令牌的鬼卒教训年轻鬼卒时说:“妈的,你的脑子里灌水了吗?你的眼睛被秃鹫啄瞎了吗?你难道看不见他的身体已经像根天津卫十八街的大麻花一样酥焦了吗?”这里的语言并非我们日常生活用语,而是比较夸张的舞台化的语言,说明莫言有意无意将自己小说的人物放置于一种戏剧舞台的背景之中,使他们的舞台表现力充分地展示出来;色彩与声音也是舞台艺术的一种明确表征,鬼卒往西门闹炸焦的身体上刷驴血的时候,作者写到“粘稠的、暗红的血”、我听到自己的皮肉发出“噼噼啪啪的细微声响”,他形容牛头马面有着“高贵的蓝色”皮肤,他写了几乎没有尽头的幽暗隧道,写了白发苍苍的孟婆,以及孟婆白胖细腻的受,肮脏的铁锅,乌黑的木勺子,馊臭的黑色液体,涂满红釉的大碗……这种种对比鲜明且极具视觉冲击力的颜色组合在一起,和若明若暗的豆油灯一起,构成了一种十分中国化十分正统的戏剧舞台效果。对此,莫言是有艺术自觉的。仍然是第一章,他写道:“我瞥着两个鬼卒的蓝脸,恍然觉得他们很像是舞台上浓妆艳抹的角色,只是人间的颜料,永远也画不出他们这般高贵而纯粹的蓝脸。”他接着写西门闹被杀的小石桥上的狗,也是浓墨重彩,“在破败的桥洞里,聚集着三条野狗。两条卧着,一条站着。两条黑色,一条黄色。都是毛色光滑、舌头鲜红、牙齿洁白、目光炯炯有神。”这是莫言一贯的以强烈的色彩冲击读者眼眸的一种戏剧化写作手法,且这些桥和狗的形态充满了庄严的仪式化的特点,就像舞台的道具。
莫言自己就明确说道:“《檀香刑》当然是最典型的小说文本跟戏曲文本的交融。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小说化的戏曲,也可以说它是一部戏曲化的小说。”他坦言自己在写作中对人物的设定就是花旦、花脸、老生等,是脸谱化的人物。而且小说中的主人公本来就是一个戏班子的班主。
从《生死疲劳》来审视,莫言“首重结构”是有意义的。从另一维度概观,《生死疲劳》以西门闹的自叙开头,将自己依次经历六道轮回的故事娓娓道来,再辅以蓝脸一家与自己的纠葛冲突,并无多余的辐射状描述,文章紧紧围绕中心西门闹及其化身展开波澜,毫无疑问是做到了李渔所倡“立主脑、减头绪、脱窠臼”。
参考消息网2016年6月一则消息说:“此外,他(莫言)还说自己对中国传统戏剧兴趣浓厚,也希望以此为主题进行创作。”报道还称,很少在媒体露面的莫言此次是在《生死疲劳》改编成西班牙语戏剧签约仪式上接受埃菲社采访的。说明本文所述,并非空穴来风,是莫言自身有意无意地在创作中开拓和阐发了他的古典情结。
综上所述,莫言在小说写作中受到明清戏曲小说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檀香刑》和《丰乳肥臀》亦多具戏剧情调和氛围,其创作实践与李渔戏曲理论或为暗合,或为接续,看似插科打诨胡言乱语,骨子里却自有分数。与其他同时代小说家相较,这是一个较为突出的特征。当然,莫言这种学习和渗透并非唯一,我们必须看到对西方小说戏剧的借鉴和学习,莫言也是有主动意识的。
注释:
①②周明全:《回到文学的源头》,《小说评论》2018年第1期。
③④⑤李渔:《闲情偶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⑥梁鸿鹰:《立主脑、密针线、减头绪、审虚实》,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2年01月06日。
⑦杨昊冉:《中国古典戏曲编剧理论思维探微——从李渔立主脑说起》,《剧作家》2017年第4期。
⑧丁西林:《丁西林剧作全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
⑨莫言:《作家抄袭自己比抄袭别人更可耻》,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09年11月17日。
⑩莫言:《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⑪⑫⑰莫言、张清华:《在限制的刀锋上舞蹈》,《小说评论》2018年第2期。
⑬尹林:《论莫言小说被动的戏剧化》,《当代文坛》2017年第1期。
⑭李敬泽:《捍卫民族叙事的生死疲劳》,新京报2013年3月22日。
⑮奚遥:《生死疲劳的戏剧人生——试论莫言小说〈生死疲劳〉中的戏剧元素》,《北方文学》2014年第5期。
⑯徐红妍:《生死疲劳:对民间与历史的另一种把握》,《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⑱参考消息网.ucwap.ifeng.com,2016年6月0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