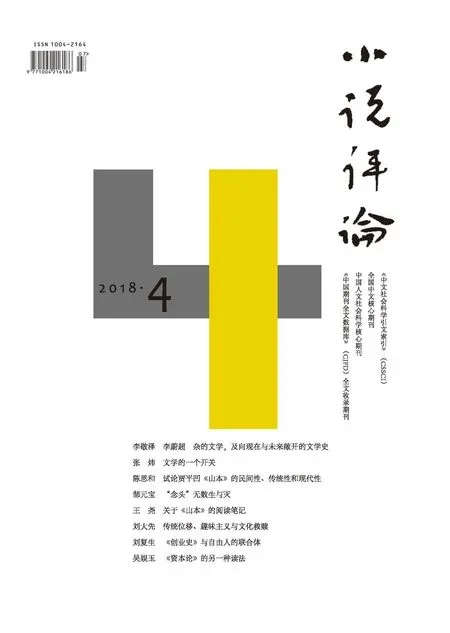互绑的个人与历史
刘剑梅
在《历史与怪兽》一书中,王德威研究文学与历史的互动,并以远古传说中的怪兽“梼杌”为象征,来勾勒二十世纪以来,历史暴力如何以不同的形式肆虐中国。他所讨论的历史暴力,不仅指像战乱、革命、饥荒、疾病那些天灾人祸,也指“现代化进程中种种意识形态和心理机制——国族的、阶级的、身体的——所加诸中国人的图腾与禁忌。”通过这个课题,他试图展现历史和“再现历史”的困境。可以说,文学对历史的再现,既是小说家见证和抗拒历史怪兽的过程,然而,又可以同时看作是小说家在不知不觉中携手制造了自己时代的怪兽的过程,这里面的矛盾全都凝聚在“梼杌”的残酷和暧昧性中。通过怪兽“梼杌”的意象来贯穿对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的分析,王德威展现了文学与历史之间复杂的对话关系,让我们看到,当历史中无处不在的暴力和创伤有形无形地侵犯和控制我们之时,小说叙事一方面是驯服这一历史怪兽的最好的手段之一,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沦为怪兽的一部分。
同样看到历史的双面性,李泽厚提出了“历史行程的二律背反”,强调历史总是在矛盾中前进,尤其表现在“历史主义”和“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上。基于李泽厚的关于历史行程的二律背反的论点,刘再复谈道:“政治家和文学家的矛盾总是从这里开始发生,文学家尊重人的情感,把个人的情感看得很重,而政治家往往是铁石心肠,为了达到一定的历史目标,他们总是说,牺牲是必要的,流血是必要的。历史学家可以歌颂拿破仑,但作为文学家的托尔斯泰,他绝对无法接受。帕斯捷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中的主角,他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去支持革命,结果最后自己被这场革命所吞没,因为革命并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铭记他当时的善良心肠,它按照自己的钢铁轨道无情地向前运行,不惜碾碎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相对历史主义的理性思维而言,文学家更重视历史进程中的伦理主义和情感真实,重视那些被历史的车轮所无情碾压的个体存在。文学最重要的存在价值,正是在于它拥抱被历史怪兽吞没的个人情感和心灵图景,并基于这一情感,不断地对历史进行批评、反思和抗争。
当我面对以历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时,我总是带着这样的一个问题来阅读:作为一个个体存在的小说家,是站在自己的家国历史或是整个人类历史的高度来观察和认知一切,重视外在的社会层面,比如不同的社会、时代、民族、阶级、阶层、集团、部落等问题,给予一个历史全景的描述,还是立足于内在的、感性的、偶然的、个性的东西,重视在历史洪流中的个体身心问题?是应该具有向外看历史行程的眼光,还是应该具有向内看个体内心世界的眼光?或是应该有效地结合二者──结合外在的社会结构和内在的个体因素?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曾经论述道:“世界历史事物并非由于历史学的客观化而具有历史性;而是:它作为那以世内照面的方式是其自身所是的存在者而具有历史性。”也就是说,海德格尔拒斥了所谓纯粹客观的历史观,而强调“人的此在是历史的首要‘主体’”,把历史还原到个人的时间体验上,把历史主体的主体性当做历史性的根本建构。阿伦特承袭了海德格尔的历史观,从历史里拨出个人的时间体验,认为极权主义和客观历史主义等都压抑了个体的存在,她则主张个人要借助思考而回到历史,不仅干预历史,而且超越历史。极权主义历史观总是强调历史的客观性,强调宏大叙事和历史规律,否定个人,抹杀个体在历史中的此在经验,而文学家最应该修复的就是个体的存在经验,恢复个体的本真历史存在。
在我眼里,萨曼·鲁西迪 (Salman Rushdie)的《午夜之子》是一部优秀的侧重于以个体的眼光,尤其是从叙述者/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存在方式出发,来重新编织历史的小说。一方面,这部小说的场面宏大,涉及到印度现当代长达六十二年的历史,从1915年开始写起,也就是印度1947年独立之前的32年,写到了圣雄甘地和印度人民为美好未来进行的抗争,然后写到赶走英国殖民者之后的印度独立、尼赫鲁总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再就是印巴分治、中印边界冲突、巴基斯坦政变、孟加拉战争、1957年印度大选以及甘地夫人颁布紧急状态等真实的历史事件,而且它所涵盖的地域也很广,包括克什米尔、德里、孟买、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并融入大量的印度传统文化中的宗教、迷信、隐喻、神话传说和风俗习惯等;另一方面,《午夜之子》并不以历史全景取胜,而是着眼于个人的成长历史和记忆,用非正式的主观语言把主人公萨里姆的成长过程跟印度的大历史紧紧结合在一起,重视个人成长的情感和经历,结合了欧洲“成长小说”和“流浪汉小说”的叙述特色,不时地叩问个体的存在问题,让个体在被历史捆绑的同时,还有回望自身的可能性。
国内外的批评家最乐于用后殖民主义理论来批评和分析鲁西迪的小说作品,因为他的移民身份,以及他自身跨越印度和英国的混杂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认同,都非常容易符合后殖民主义关于“离散”“边界写作”“混杂身份”“第三空间”等理论。这些借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对《午夜之子》的阐释,虽然是必不可少的,并且颇有见地,但是不免有些雷同。对我来说,这篇小说更吸引我的,是鲁西迪神灵活现的讲故事的方法、巧妙的隐喻和象征手段、对世界文学传统的继承与超越、流动而驳杂的语言风格以及丰富的想象力──因为正是这些出色的文学表现手法,令他成功地开创了一个独特的书写历史又同时超越历史的文学场域。
一、不同的魔幻意义
萨曼·鲁西迪的第二本小说《午夜之子》,于1981年出版后,被《纽约书评》誉为“这一代人英语世界出版的最重要的书籍之一”,让作者赢得巨大的国际声誉,获得了布克奖等英美国家的文学奖, 并于1993年再次荣获为纪念布克奖二十五周年而颁发的大奖——“特别布克奖”,1999年被美国兰登书屋评为一百部二十世纪最佳英语小说之一,2008年又荣获为纪念布克奖设置四十周年特设的“最佳布克奖”。当我阅读《午夜之子》的英文版的时候,不由自主地被他出神入化的英文所折服。他的英文不仅幽默风趣,有一种音乐节奏感,而且运用了大量巧妙的比喻和双关语,读起来朗朗上口,清晰流畅,又带着明显的异国情调,仿佛混杂着各种香料的味道,怪不得他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广大英语世界的读者,被英国著名作家普雷切斯称为是“一位滔滔不绝地讲故事的大师”。可以说,他的英文写作极大丰富了英文小说的语言和叙述,把多元的文化表象和混杂的语言叙述带入英文的小说世界里。
由于同样写漫长的家国历史和政治,同样具有魔幻的神奇色彩和大胆离奇的想象,评论家总会把《午夜之子》跟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以及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放在一起比较。《午夜之子》中有大量的魔幻色彩,比如主人公萨里姆天生拥有能够倾听和联络1001个午夜之子的心灵感应术——“洞察人的内心世界的能力”,以及他后来转换成的超级嗅觉功能,还有那1001个有超自然能力的午夜之子,个个神通广大,有的力大无穷,有的会算命,有的会隐形术,有的可以在过去和未来的时间穿越和旅行,有的闭上眼睛就可以飞上天空,有的在水里可以变幻性别等。这些神奇的想象会让人不由得联想起《百年孤独》中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魔幻故事,比如飓风刮走整个马孔多镇,俏姑娘雷梅苔丝随床单升天,人鬼对话,整个镇子突然被传染性的失眠症和遗忘症所笼罩,有预言能力的奥雷里亚诺上校,以及骨殖袋里发出的沉闷咯啦声等超自然的现象。跟马尔克斯一样,鲁西迪能够在他的叙述中自如地跨越现实世界和虚幻世界的界限,然而,鲁西迪的魔幻跟马尔克斯的魔幻显然不同。陈众议在《保守的经典,经典的保守》一文中曾经论述道,马尔克斯的魔幻是一种拉美“集体无意识的喷薄”,正因为有了马孔多的孤独和落后,才有了《百年孤独》的魔幻与神奇,最后这个代表传统社会的小镇才会被跨国资本主义侵入和毁灭,而小说相对应的叙述形式和结构形态也是比较传统和保守的,马尔克斯采用的是一位全知全能的叙述者,以及既可以瞻前又可以顾后的叙事方式,“他的方法完全可能出现在十九世纪,甚至更早的骑士小说时代、英雄传说时代,或者甚至神话预言时代”,与绝大多数追求创新的反传统的先锋的拉美作家如略萨、富恩特斯或科塔萨尔完全不同。
鲁西迪的魔幻虽然也受到印度传统文化的影响,源于许多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丰富的神话传说,但是总体来说,他的魔幻还是属于他个人缔造的现代神话和魔幻,是他自己建构的寓言和象征意象符号。他一方面用这些寓言和象征意象符号传递深邃的精神内涵,另一方面又随时解构着这些寓言和象征符号,让我们看到历史如同“多头怪兽”的多元性和多变性的本质,充满力度地叩问何为“历史真实”。比如鲁西迪关于1001个“午夜之子”的隐喻,不只是简单的魔幻描写,或对《一千零一夜》的致敬,而是他通过这一意象来描述多种族、多阶级、多神教、多文化的印度,就像主人公萨里姆所说的:“一千零一个孩子降生了,这就有了一千零一种可能性(以前从来没有在同一时刻同一地点有过这样的事),也就会有一千零一个最终结局。按照你的观点,午夜之子可以用来代表许多事情。可以将他们看成我们这个被神话支配的国家的古旧事物的最后一次反扑,在现代化的二十世纪经济这个环境中,它的失败完全是件好事。或者,也可以把他们看作自由的真正希望所在,如今这个希望已经永远被扑灭了。”这个象征着印度宣布独立后的未来希望的1001个“午夜之子”,来自不同的民族和阶级,拥有不同的宗教背景,然而,很快就处于逐渐解体的状态,无论他们天生具有多大的法力,他们的心灵逐渐被成人的偏见和世界观所影响,宗教上的对立、种族和阶级出身的差距、贫富悬殊、意识形态的不同选择、个性的冲突等等问题,使得他们根本没有办法组成一个有作为的集体──这一切都预示着印度独立的国家乌托邦的解体。通过萨里姆的心灵感应术而召开的午夜之子大会,1001个“午夜之子”讨论对国家民族的认知,在会上萨里姆提出第三条原则或第三条道路,试图克服无穷无尽的宗教、阶级、种族、贫富等二元对立──这是甘地理想化的跨越地域和阶级等差别的政治伦理乌托邦的表现,但是在会议上遭到强烈反对,最后只能不了了之,就如同印度的现实状况一样。到了甘地·英迪拉宣布紧急状态的时代,1001个“午夜之子”则被强权政府彻底摧毁和挫败了,被政府用“精神切除术”把他们神奇的法术切除,把他们代表的所有最初印度独立时的希望都切除了。印度独立之日的午夜出生的孩子们是“独立带来的奇形怪状的怪胎”,而镇压他们的甘地·英迪拉被叙述者形容为“提婆”──“神母最可怕的一个化身,众神的性力的所有者,一个头发中间分开黑白分明的千手女神。”总之,鲁西迪所建构的关于“午夜之子”的神话,有着深刻的关于印度独立乌托邦的隐喻,而最后他又通过解构“午夜之子”这个隐喻,来暗示这个乌托邦已经变成了异托邦或恶托邦。
《百年孤独》的魔幻凝聚了充满原始生命冲动的各色神话,是拉美文化的集体无意识的体现。就像马尔克斯曾经说过的,“只要逻辑不混乱,不彻头彻尾地陷入荒谬之中,就可以扔掉理性主义这块遮羞布”,所以他笔下的魔幻并不受制于从“理性主义”原则出发所设置的隐喻,而是更多地建立在原始生命意识的基础上。然而,《午夜之子》的魔幻则是鲁西迪以理性的态度来缔造的属于他自己的现代魔幻和神话故事,原本的印度神话中的神只是他借用来重新“命名”、重新书写历史的一个叙述策略和手段。叙述者/主人公萨里姆问道:“我是谁?我们又是谁?我们是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是你们从来没有的神。”虽然我们看到那么多来自印度宗教神话的“神”的名字,如湿婆、提婆、婆婆帝、象头神等,可是它们只是被鲁西迪借用来隐喻印度现代社会的现实状况——这种纯粹属于个人的神话建构(或反神话),不仅为了叩问印度现代化进程中关于“我是谁”的问题,而且为了批判印度独立后的社会政治伦理混乱的现实。
二、叙述者的内心世界
《百年孤独》和《午夜之子》最大的区别,显现在它们的叙述手法上,前者侧重于描写孤独闭塞的马孔多小镇的集体无意识,而后者在叙述上则偏重于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在小说叙事手段的师承关系上,《午夜之子》更接近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首先,这两部小说都是典型的成长小说,格拉斯和鲁西迪都采用了一个超常的个体的叙述者的视角,都用第一人称“我”以及小说中主角的名字轮流转换来叙述故事,以大历史为背景,充分展示了叙述者/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第二,两部小说中的主人公都天赋异禀,《铁皮鼓》中的奥斯卡在娘胎中就可以推测自己的未来,他三岁的时候拒绝长大,他的声音可以震碎玻璃,而萨里姆会心灵感应术,后来还拥有超级的嗅觉功能。他们神奇的能力都包含着不寻常的象征意蕴:奥斯卡的拒绝长大,象征着他对荒诞而混乱的成人世界的拒绝;而萨里姆的心灵感应术,象征着他试图构建一个超越各个种族和阶级的独立印度乌托邦的幻想。第三,两部小说中超常的既是主人公又是叙述者的个体,不仅被紧紧地捆绑在历史上,而且还会主动地“创造”历史,影响着周围的人们。奥斯卡一方面是法西斯统治下的黑暗历史的目击者,另一方面他常常把历史中突发的家人的悲剧事件归咎于自己,仿佛他就是历史悲剧的制造者:“尽管我抱憾终身,但我不能否认,我的鼓,不,我本人,鼓手奥斯卡,先葬送了我可怜的妈妈,之后又将扬·布郎斯基,我的表舅和父亲送进了坟墓。”《午夜之子》的主人公萨里姆一方面从一出生就被动地成了历史的人质:“这一来我莫名其妙地给铐到了历史上,我的命运和我的祖国的命运牢不可破地拴到了一起”;另一方面,他又总是提醒读者,他其实是在主动地“制造”历史。比如谈到萨里姆的童年时代,叙述者如是说:“有关萨里姆娃娃的最初的岁月暂时就说这些了,我的出现已经对历史产生了影响。萨里姆娃娃已经使他周围的人发生了变化。在我父亲那方面,我深信是我将他推上了极端的道路,这最后导致了冻结的可怕时刻,这一点或许也是避免不了的。”少年萨里姆把叔叔的自杀也归咎于自己,把邻居因为婚外恋产生的悲剧等都归咎于自己。萨里姆偶然说的一句话,居然也成为孟买游行队伍的口号,并最终导致孟买邦一分为二。再比如小说中的1958年巴基斯坦的政变,其实萨里姆只是在姨父和军官们的命令下,在饭桌上挪动胡椒瓶帮忙演示政变计划,可是他的叙述故意营造成一种幻象,仿佛他真正参与了这场政变。萨里姆这样分析他自己和国家的关系:“一个人的生活可能影响国家的命运,这话又如何理解呢?对此,我的回答中必须用上一连串修饰词和连词符号了:我和历史的联系既是字面意义上的,又是比喻意义上的;既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我同我的世界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这种个体与历史的复杂关系其实印证了王德威所说的历史怪兽“梼杌”的暧昧性:个体被历史所捆绑,不得不忍受历史怪兽强加给个体的种种暴力与创伤,但是个体又同时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历史怪兽的一部分而不自知,一起犯了汉娜·阿伦特批判的“平庸之恶”的罪而不自知,就像奥斯卡无意识地导致了妈妈、舅舅和父亲的死亡,荒诞地从一位反抗法西斯的“勇士”变成一位法西斯的帮凶,而萨里姆无意识地参与了巴基斯坦政变一样。
然而,最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是鲁西迪对格拉斯以个人视角为中心讲述历史方式的继承,以及他对格拉斯的叙述手段的超越。其实无论是《铁皮鼓》中的奥斯卡,还是《午夜之子》的萨里姆,都属于历史洪流中无足轻重的边缘“小人物”,他们完全不可能创造历史,只有像斯大林、毛泽东、丘吉尔等历史中的“大人物”才有真正创造历史的机会,才有影响他人和决定他人命运的能力和权力,但是,格拉斯和鲁西迪故意以文学的魔幻手法把小人物放大,把他们虚构成如同神话中的“英雄”人物,让读者对被历史埋葬和吞噬的每一个普通的个体产生同情和共鸣,达到移情作用(empathy)。格拉斯在《铁皮鼓》中借用已经住进疗养护理院的奥斯卡之口,讲述为什么他要设计这样一个超常的“英雄”人物:
“一则故事,可以从中间讲起,正叙或倒叙,大胆地制造悬念。也可以搞点时髦,完全撇开时间和空间,到了末了再宣布,或者让人宣布,在最后一刻,时间和空间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也可以开宗名义地声称,当今之日,写长篇小说已无可能,然后,比如说,在自己背后添上一个声嘶力竭的呐喊者,把他当作最后一个有可能写出长篇小说的作者。我也听人说过,若要给人好印象,谦虚的印象,便可以开门见山地说:现在不再有长篇小说里的英雄人物了,因为有个性的人不复存在,因为个性已经丧失,成为往事,因为人是孤独的,而且人人都同样地孤独,所以无权要求个人的孤独,因此组成了无名的、无英雄的、孤独的一群。事情可能就是这样,可能有它正确可信的地方。可是,就我,奥斯卡,和我的护理员布鲁诺而言,我敢说,我们两个都是英雄,完全不同的英雄,他在窥视孔后面,我在窥视孔前面;如果他打开房门,我们两个,由于既有友谊又是孤独,因此仍然构不成无名的、无英雄的一群。”
这种拒绝变成历史中“无名的、无英雄的、孤独的一群”的态度,就是格拉斯讲故事的态度,是他书写历史的态度,他要把个人的声音无限地放大,让它能够震碎玻璃,让他的鼓点能够让容易患遗忘症的人们听到,让他的鼓声与呐喊充满反抗乱世的力量。“对我来说,奥斯卡的声音是我存在的证明,永远新鲜的证明,这一点是我的鼓所不及的。只要我还能唱碎玻璃,我就存在着,只要我的定向呼吸还能夺走玻璃的呼吸,生命就还在我身上。”除了夸大奥斯卡的作为叙述者的个体存在,格拉斯在《铁皮鼓》里还运用了许多创新和先锋的叙述手法,加入了一些类似“元小说”的因素,经常插入一些奥斯卡写故事的过程,比如奥斯卡在叙述过程中对“黑厨娘”的恐惧,而“黑厨娘”有时甚至转换成代表古典主义美学的诗圣歌德——歌德成了格拉斯写作过程中的一个对话者,这一设计代表了格拉斯的现代主义美学对古典美学的解构,以及他对启蒙主义以来的理性精神的怀疑态度;再比如,奥斯卡的叙述有时会转换成由他的护理员布鲁诺来“代笔”书写。小说中的奥斯卡不是被动地被讲述,而是积极地参与讲述的过程,参与对叙述方法和叙述角度的选择,以主观的视角展现一个荒诞的现实世界。
鲁西迪在《午夜之子》中,继承了格拉斯的《铁皮鼓》以个人视角为中心的叙述方式,也把萨里姆这个叙述者的个体形象在历史中的存在夸张地放大,不过,他对格拉斯的超越,表现在他刻意放大“个体”的同时,也无情地解构着自己缔造的关于个体的“神话故事”,也许正是这一点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更加深刻的个体存在的“荒诞感”,以及他对官方或国家民族话语共同构造的所谓宏大历史叙述的怀疑和颠覆。首先,鲁西迪一方面塑造着萨里姆的作为国家寓言的英雄神话形象,另一方面又时不时把他拉下“神坛”,揭示他在历史中无奈的边缘角色,瓦解这一国家寓言。因为萨里姆恰巧出生在印度独立日,为了把他牢牢地“铐在历史上”,鲁西迪编织了一个神话,让政治家尼赫鲁写信给萨里姆的父母祝贺他的诞生:“你是印度那个既古老又永远年轻的面貌的最新体现。我们会最为关切地注视你的成长,你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我们自己生活的镜子。”萨里姆的出生和成长似乎是一个大事件,因为他代表着印度独立的国家民族的寓言,而且他天赋异禀,似乎有能力操纵历史的进程。然而,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慢慢看到这个“神话”被一点点解构。事实上,萨里姆所谓非同一般的命运只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也完全不像他自己所宣称的,有能力影响周围的人,他其实根本就没做过任何影响历史进程的事情,不仅如此,他也没有什么归属感,一直都找不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园”。因为他从小被换包,并不是他父母的亲生儿子,而是一位英国人和一位印度人的“私生子”。带着这样“杂种”的血液,他并不是百分之百纯种的印度人,他也不认同巴基斯坦,连抚养他长大的家庭都不真正属于他。开始他似乎是1001个午夜之子的领袖,但是午夜之子都不听他的指挥,后来他天生的心灵感应术,被一次鼻炎手术完全摧毁,于是他跟众位午夜之子失去了联系。整部小说中,他基本上无所作为,游离在社会的边缘,最后甚至沦落到跟德里的江湖艺人群体居住在一起。鲁西迪故意让萨里姆从一个“中心”角色游离到“边缘”角色,从一个“富家子弟”沦落成一个完全一无所有的“穷人”,通过这种个体选择的“偏岔”路径,来逃离历史的必然途径,逃离个体被历史完全捆绑的命运。
其次,鲁西迪加入了许多“元小说”的元素,把整个叙述者编写和讲述故事的过程一一展示出来,让萨里姆对着他的不识字的情人——酱菜厂的女工博多讲述他自己的成长经历与印度独立历史紧紧相连的故事,而讲述期间博多时常打断他,质疑他。这个书写历史的过程,用最终落户在酱菜厂的萨里姆的话来说,堪比一个腌制酱菜的过程:
“我已经把我特地调配出来的酱菜保存起来了。腌制过程的象征意义是,生出印度人口的六亿个卵子可以塞进一个正常大小的酱菜瓶子里,六亿个精子可以用一把汤匙舀起来。因此,每一个酱菜瓶(要是我一时变得追求华丽的辞藻的话,请你原谅我)都包含了最为崇高的可能性,那就是把历史做成酸菜酱的可行性,以及将时间腌制起来的伟大的希望!”
每一个酱菜瓶,都象征着作家和叙述者主观地“腌制”历史的过程,都是他真实的个人记忆,是他干预历史和超越历史的一个方式。也就是说,鲁西迪尖锐而敏感地看到了历史的真实面目,看清隐藏在现实层面后面的神秘构成和秩序,他不被任何官方的堂而皇之的大历史所蒙蔽,而是让叙述者萨里姆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凭着自己超人的嗅觉,把历史撕开、切碎、配上各种调味,然后重新腌制进充满了他自己主观经验的酱菜瓶里。
这种纯粹主观的个人看待历史的眼光,也通过小说里的一个“中间有洞的床单”的意象表现出来。萨里姆的外公当初爱上他的外婆,是通过一个中间有洞的床单,一次次观察外婆身体的不同部位,然后最终把碎片的、片段性的形象凭想象拼凑成一个整体而爱上她的,结婚后他才发现被这个“中间有洞的床单”蒙蔽了,他所爱上的外婆并不是他所想象的女人。外公当初不被允许看到外婆的整个身体,而只被允许从“中间有洞的床单”来观看──这其实就是历史的真相,我们所能够被官方权威允许看到的只是碎片的、片段的历史局部,是一个充满幻象和偏见的拼凑成的历史,而真相永远是被遮蔽的。不过,在叙述过程中,萨里姆告诉我们,“一条中间开洞的床单迫使我注定要过分成片段的生活”,然而,虽然他的外公一直是这条床单的受害者,“而我呢却成为了它的主人──这会儿被它迷住的人是博多。”于是,叙述者萨里姆成为了“中间有洞的床单”的主人,他掌握了叙述历史的主动权,他决定让我们看到的印度历史是完全个人化的主观的碎片化的印度历史。做为读者,我们反而像他的外公一样,只能透过“中间有洞的床单”,读着经过他主观选择和过滤后,透露给我们的点点滴滴有关他的成长故事和关于印度历史的个人记忆。
萨里姆似乎掌握了讲述“历史真相”的主动权,但是他又时不时地提醒我们,他的身体因为“受到太多历史的打击”,已经开始分崩离析了,出现了许多的裂缝,迟早他会变成碎片,“最终我会碎成(大约)六亿三千万个无名的而且一定会被遗忘的尘土似的微粒”──这些微粒象征着印度每一位普普通通的大众平民,他们总是被官方历史无情地遗忘,而萨里姆对历史的充满个人化的讲述,就是为了抵抗被历史打击并且遗忘的命运,留住这些微粒。“归根到底,我的酸辣酱和酱油同我夜里乱涂乱抹有关──白天在酱缸之间,夜里在那些床单当中,我把时间都用在腌制保持上面。记忆同水果一样,被腌制起来,免受时间的腐蚀。”不仅如此,他也提醒我们,所谓历史的真实,无非是一个视角的问题,取决于书写历史的主体──他是谁?他采取哪一个角度来看待历史?他认同了哪一个阶级、种族、社群?没有任何人可以提供一个完全真实的历史全景,唯一的真实就是个体主观感受到的真实,也就是“情感真实”和“心灵真实”──这些属于个体的本真历史存在。对为什么把“我”放在书写印度历史的中心,对这样做是否将会颠倒是非,萨利姆做了如下的回答:
“这会儿,在活动台灯灯光下,我弓着身子伏在纸上,只想成为现在的我,不想成为其他别的东西。那么我是谁是干什么的呢?我的回答:我是在我之前发生的所有一切事件的总和,是我所见所为的一切的总和,是别人对我所做的一切的总和。我是所有一切影响我也受我的影响的人和事。正因为世上有我这个人,有些事情在我身后才会发生,我便是这些事情。在这件事上我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每一个‘我’,如今六亿多人口中每一个人,都具有这种多重性。我最后再说一遍,要理解我,你必须吞下整个世界。”
比起格拉斯充满现代主义描写风格的《铁皮鼓》,鲁西迪的《午夜之子》显然更属于“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杰作,也就是说,从叙述方面,更像琳达·哈成所说的:“总体上来说,后现代主义总是采用自我意识,自我矛盾,自我解构的叙述。”在《午夜之子》中,我”既是国家民族的寓言,又同时自我解构着这个所谓国家民族的寓言;“我”既代表着印度六亿多人口,又只是一个孤独的个体;“我”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被历史摆布和侵犯的小人物,然而“我”通过自己的书写又主动地掌握着历史的命运。于是,这个“我”,在书写历史的过程中,其实是至关重要的,所有的故事都出自“我”的视角──“我在配制中能够加进我的回忆、梦想、观念”。对于萨里姆,个体通过主观经验和感情腌制历史的过程,是给予被腌制的历史“形体”,或者“意义”。“或许有一天,世界会品尝一下腌制的历史。对某些人来说,它们也许气味有些冲鼻子,也许会激得人眼泪直流。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够说它们的味道完全货真价实,反映了真相……”在此,他以个体的记忆——酸菜酱,与属于国家和集体的官方历史抗衡,与极权主义的历史观抗衡,充满颠覆意义,让我们在苦辣辛酸的味道中品尝部分关于历史的真相。但是,他也提醒我们,所有说书人/叙述者的主观记忆也有其不可靠的地方。比如,萨里姆为了排斥他的对手湿婆,可以通过心灵感应术,不让他参加午夜之子会议,可以一直瞒着关于他出身的秘密。又比如,他常常告诉我们,他的记忆可能出现误差等等,他之所以如此自我解构,是为了强调,所有关于历史的书写,都跟书写者的位置、视角、身份和认同有关,没有任何书写者掌握着绝对的历史真相。
三、以隐喻编织的“神话魅力”
借用罗兰·巴特和德里达的文学理论,王德威给予了“神话”这样的定义:“我所谓的神话魅力(myth),指的是一种叙事/或行为上的表现,它以隐喻的方式将某一社会在特定历史时间内所有的信念、不信任、欲望或恐惧加以定型。神话魅力可将特定社会/文化/政治轴线上的观念证明为表面上可号称超越时空的真理,而其存在和腐朽又总是随着历史与叙事的既定因素而行。”也就是说,神话魅力是通过隐喻的方式来表现的,虽然隐喻有其特定历史的因素,但是它可以表现出一种永恒性的超越时空的表象。林岗在《什么是伟大的文学》一文中,曾经谈到文学批评应持三个尺度:一是“句子之美”,二是“隐喻之深”,三是“人性之真”。他认为:“丰富而深刻的隐喻至关重要,它是伟大的文学不可缺少的另一项品质,隐喻性的丰富和深刻程度是衡量文本高下的又一个尺度……天才的作家总是在不经意间就在文本的具体的、形而下层与普遍的、形而上层之间搭建了绝妙的隐喻关系。”
鲁西迪的《午夜之子》就属于这样一部充满深刻隐喻的伟大的文学作品,它隐喻的方式,来连接“具体的、形而下的叙述层面和普遍的、形而上的叙述层面”,因而达到有神话魅力的效果。比如古怪的长生不老的精灵般的船夫塔伊,象征着印度被现代化入侵之前的漫长的传统;萨里姆的外公的身体中间的窟窿,代表着他对传统的宗教信仰的质疑;萨里姆众多的他自己认同的“父亲”,代表着印度传统的多样性和多元性;“多头妖怪”象征着历史的暴力以及盲信和狂热的群众;萨里姆的通灵术连接的“是所有那些所谓熙熙攘攘的民众的内心独白,来自类似群体和阶层的内心独白”;母亲的银痰盂是萨里姆失去记忆的一段时间跟过去历史仅有的一点联系;“午夜之子”象征着印度独立民族国家的希望;“酸菜酱”象征着个人的历史记忆;“中间有洞的床单”象征着看历史的视角;亲身父亲是殖民印度的英国佬的萨里姆,虽然跟来自克什米尔的外公没有血液上的联系,可是继承到了外公的大鼻子和蓝色的眼睛,意味着他跟印度的部分传统而不是整个传统保持着传承的关系……类似这样的隐喻,在小说中比比皆是,读者可以从各种角度来阐释,有时作者自己还故意解构掉这些隐喻原本的象征含义,让这些隐喻带有开放性的空间,用它们串起作者独特的对历史和记忆的书写,构成了一部后现代的“史诗/反史诗”“神话/反神话”“寓言/反寓言性”“隐喻/反隐喻”的文学经典作品。
小说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隐喻是关于“蛇梯棋”的隐喻,因为这一隐喻包含了鲁西迪书写历史的哲学观,包含了他在面对复杂的传统、历史、政治、现实时所采取的人生哲学:
“所有的游戏中都包含着深刻的寓意,蛇梯棋中包含了其他活动根本无法具有的永恒真理。那就是你爬上每一格梯子时,都有一条蛇在角落里等着你;而每当你遇到蛇,梯子又会对你做出补偿……因为这种游戏中隐含着事务的两面性,如上与下、善与恶这一永恒对立。梯子扎实可靠,是理性的代表,而蛇蜿蜒曲折,充满了神秘感,这两者之间保持着一种平衡……你有可能从梯子上滑下来,却依靠蛇的毒液登上胜利的顶峰……”
就像《午夜之子》中文版的译者刘凯芳所说的,“萨里姆将蛇和梯子看成是人生中福和祸的象征,这两者保持平衡,又互相转换,这种辩证关系与我国老子所说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很接近。”这一辩证的哲学关系贯穿在鲁西迪的书写中,所有二元对立,比如富裕与贫穷、胜利与失败、善良与邪恶、男性与女性等都是一种互相依赖和转换的关系,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就连蛇本身的意象也有其二重性,它一方面象征着死亡,另一方面又成为拯救萨里姆生命的灵丹妙药。在《午夜之子》大会上,萨里姆提出的第三种原则和第三种道路,也是出自这一哲学,试图超越阶级和种族的二元对立,找到第三条路线。这一哲学观念使得鲁西迪的写作超越了简单的黑白、善恶、贫富的对立,赋予他更加包容的视野和胸怀,也赋予了他更加超脱的视角来质疑直线性的进步时间观,逃离历史的定律和定数,逃离历史对个体的束缚,所以他的叙述经常自如地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里转换,有时他在隐喻中预示着未来,有时又在叙述中回放着过去,有时像电影镜头一样同时展示同一时间两个地点发生的事件。
萨里姆说:“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要想理解一条生命,你必须吞下整个世界。”吞下整个世界,就意味着不仅需要理解好人,也需要理解坏人;不仅需要理解幸运的人,也需要理解不幸的人。隐藏在《午夜之子》后面的“蛇梯棋”哲学,给予了鲁西迪一个既理解历史又超越历史的眼光,一个明白世界内在肌理的视野,让这部小说成了《百年孤独》《铁皮鼓》之后的又一部文学书写历史的大书。
四、历史视野和宇宙视野
刘再复在《怎样读文学──文学慧悟十八点》里谈到文学和历史、哲学的区别时,他写道:“文学体现心量,历史体现知量(识量),哲学体现智量。”他也提到文学可写鬼神,历史和哲学都没有鬼哭神嚎;也就是文学可以写魔幻,而历史和哲学则不可以。他尤其强调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文学“不设置政治法庭,也不设置道德法庭,只设置审美法庭。”也就是说,文学不做简单的非黑即白的道德判断,而是重在写出每一个个体的生存困境、人性困境和心灵困境。王国维曾经区分“历史境界”和“宇宙境界”(美学境界):“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被捆绑上历史的文学,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但成为经典的作品,总是拥有利用历史架构又挣脱历史捆绑的大手笔,而鲁西迪的《午夜之子》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它不但有历史的视野,政治的视野,国民的视野,还有宇宙的视野、哲学的视野以及文学(审美)的视野。
注释:
①王德威:《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台湾:麦田出版社,2011年,第5页。
②刘再复:《李泽厚美学概论》,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197页
③④[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北京:三联, 2014年,第432页、432页。
⑤参见Arendt, H. 1978). The Life of Mind, Vol.1: Thinking. San Diego New York London: A Harvest Book-Harcourt, Inc.pp. 202-213. 也参见 Tung Tin Wong, “Human in Historicity: Hannah Arendt on Political Experience,”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Phil thesis, 2018.
⑥陈众议:《保守的经典 经典的保守——再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 《当代外国文学》2011年第5期,第8页。
⑦⑧⑩⑫⑬⑭⑰⑱⑲⑳㉑㉒㉔㉗㉘㉙[英]萨曼·鲁西迪:《午夜之子》,刘凯芳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第254-255页、549页、549页、3页、163页、300页、300页、575页、151页、40页、41页、482页、577页、41页、178页、4页。
⑨[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阿·门多萨:《番石榴飘香》,林一安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39页。
⑪⑮⑯[德]君特·格拉斯:《铁皮鼓》, 胡其鼎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第309页、4页、465页。
㉓Linda Hutcheon, 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edn), p.1.
㉕王德威:《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页。
㉖刘再复:《怎样读文学——文学慧悟十八点》,香港:三联书店,2018年,第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