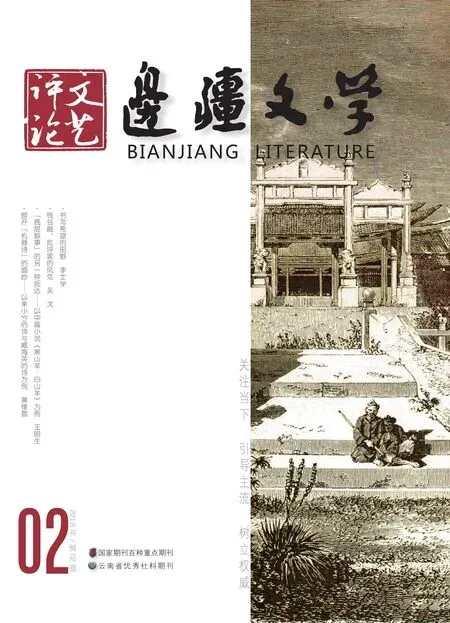郁郁涧底松, 此生何所向
——评吕翼小说《寒门》
周文英
一、痴守的梦幻
彝族作家吕翼的长篇小说《寒门》讲述的是云南高寒山区的年轻人在中国当下转型时期,企图通过发愤苦读,取得高考的成功来报答亲恩改变命运的故事。主人公冯维聪几次高考失败,最后精神失常,成为当下社会的“狂人”。
小说的故事前后有一定时间跨度,高考制度本身也经历了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到扩招的变迁,但寒门子弟的命运依然难以改变,特别是教育的产业化给寒门家庭带来的负担。坚毅、隐忍、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几乎是云南高寒山区贫困地区农民普遍的精神生活状态,高考之路的艰难坎坷更突显了贫困农民家庭仍然难以承受的教育费用。贫困在代际传承循环着,读书是冯维聪、冯天骏他们唯一的出路,他们没有任何一条道路可走。冯维聪和冯天骏的心理历程反映了恢复高考至今云南高寒山区学生的命运际遇。
冯维聪和冯天骏的命运际遇既有区域性的原因,又因为遭遇家庭变故:
碓房村是茫茫无边的乌蒙山区里一个小小的村落,虽然隔酒州县城有五十多里路,略显偏僻,周围是山,交通曲折,但怀抱着上千亩的良田沃土。那土层至少是上万年的堆积,黑得发亮,黑得发臭,以锄下去,只听得“滋”的一声,一团黑泥就起来了,随手拾起,掰开一看,里面全是植物腐朽的根叶,湿湿的,软软的,绵绵的,松松的。……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土壤的肥沃,稻谷的丰收带给人们的喜悦,对劳动的热爱,庄稼的健康成长,美好的生命力,对应的应该是青少年健康而茁壮地成长。但是冯敬谷家面临着三个孩子读书的学费,冯婶变卖了家里的草墩、谷草、辣椒、猪、牛。
冯婶摸摸头说,我的头发在上个赶场天已经卖掉了,八块。
冯家不仅变卖了家里一切值钱的东西,也变卖了人身上的头发,这个情景,与雨果小说《悲惨世界》里美丽的姑娘芳汀无路可走之后,不得不变卖自己美丽的头发是一样的画面。这里,“人”已变成“非人”,人的异化,已经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冯维聪知道父亲为他们的学费借钱被人暴打,觉得自己的生命是父母亲的累赘,喝农药自杀,后被救活。他背负着父母的期望和改变自己命运的渴望,刻苦读书。但是第一次高考失败了:
冯维聪感觉不是很好,一上考场,他就头疼。这种头疼不是第一次,早在他喝了农药,要逃离这个世界之后就有了,而且常犯,只是他不敢说,也不能说。……
考试这回事,越当回事,越紧张,就发挥不好。……整个考场里面,他大脑都是考不取大学他们一家所面临的困境,都是整个碓房是热嘲冷讽。整个视觉里,他看到的不是题目。而是爹妈头顶烈日,肩挑背驮的辛酸场面。那些场面不断再现,不断重叠,令他不安。
高考失败之后复读,学校的环境是“每个学校都剑拔弩张,每个班级都风声鹤唳”。冯维聪忘我地学习,高考之前,吃了浸满父母亲殷切希望的腊肉、六个荷包蛋。第二次参加高考,由于精神压力太大,太紧张,冯维聪在考场疯了!他不再是一个正常的人。这里,“环境要我读书”压倒了“我自己要读书”的主观意愿,冯维聪的行为愿望与行为结果发生了逆向冲突。
小说《寒门》抓住中国改革恢复高考时期“羊肠小道上的竞争让人喘不过气了”严酷现实。而在“喘不过气来”的小道上,城乡差距,家庭的经济情况、社会地位构成了当下的一幅“郁郁涧底松”的现实: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1]
诗里,“涧底松”隐喻出生寒微的人,而“山上苗”隐喻世家子弟。仅有一寸粗的山上苗遮盖了涧底百尺长的大树。地势造成了山上苗和涧底松的命运。而吕翼的小说《寒门》从反映社会转型时期的角度塑造人物,要再现的是在巨大的城乡差距悬殊之下,农民孩子奋斗的艰辛和坎坷,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是一种社会时代的常态,冯维聪和冯天骏也是复数。这里的“乡”固然名副其实,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的社会环境相比,更加偏僻、闭塞和落后;“酒州城”不是“城市”而只是“城镇”,但与碓房村相比,两者的文化落差还是十分明显。社会文明的发展变迁,总是先“城市”、“城镇”而后波及“乡村”再影响“山区”,冯维聪、冯天骏特定的高寒山区的生长环境,决定了他们成为“涧底松”,恰恰他们又不具有松树的生命力的坚韧和顽强,“贫困”不仅导致了贫困地区孩子们物质和精神上营养的不足,也导致了教育资源的不平衡、教育的不公正和不公平。
高考,是冯维聪和冯天骏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的机会。高考这种制度,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消除阶层、收入、性别、文化偏见等各种背景的干扰,让占社会绝大多数的普通家庭的子女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与阶层。而高考的行为与结果的逻辑关系是“成王败寇”。考大学从来就是冯维聪等社会底层家庭改变贫穷状况和个人前途的最主要的一个途径。碓房村里的冯家、万家、赵家等子女都会拼命努力来争取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冯维聪、冯天骏高考失败几乎等于生存机会的被剥夺。
但在教育产业化的今天,社会底层家庭及其子女普遍缺乏内驱力。因为即使他们成绩最好,他们也承受不了高额学费的负担。这些年来,考上了大学却因没有钱而无法上大学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些学生或者其家长甚至因此走上了自杀之路。
教育,要温柔对待每一个想要进步的孩子。这种教育取决于早期的家庭教育,到了冯维聪、冯天骏生理、心理急剧变化的高中叛逆阶段,“涧底松”的生长失去了土壤的养料,失去了必要的水分和雨露、阳光的保障:
冯维聪躲在屋里听到爹妈说商量钱的事。爹妈为了他们读书,这样的凑钱、愁钱,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每一次爹妈的商量、争执,以至于由此展开的争吵,像刀在他的心尖上切来割去。那刀是钝刀,或者根本没有口,划来划去,让他的内心疼痛无比。他的伤口越来越大了,越来越深,血流走的越来越多。他感觉到自觉脑袋爆裂,心脏里的血都快干了,他感觉到自己是个累赘。死死的压住爹妈,致使他们喘不过气来,过不上一天好日子。
压抑、贫困和无序的环境下成长的冯维聪,从来没有拥有过丰厚的物质基础和社会资源,自然形成了敏感、脆弱、多愁善感、焦虑、阴郁、偏狭、紧张、自卑、冲动的性格,而性格是塑造人生的最重要的一张王牌。是没有但是,社会对失败者不宽容,没有平等机会的土壤,再多努力也白费。小说家是需要大心脏的,作者心怀苍生,想呼吁的正是;让每一个孩子都有同样的机会获得成功,这是公平;为先天不足的孩子“垫高”,提供合理的便利的条件,这是正义。
二、当下高寒山区的“狂人”
鲁迅的《狂人日记》记录了中国知识分子觉醒时期的呐喊: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2]
《狂人日记》的题记里的文眼是“候补”两个字。别看狂人今天很深刻,明天狂人以恢复理性了,就“候补”去了。鲁迅把一个人的觉醒看成是一场疯狂,狂人清醒以后,又融入到这个正常的社会,这个吃人的社会秩序中,狂人也就失去了反抗性。《狂人日记》里狂人的症状表现为:疯言疯语、极度敏感、胡思乱想、常有幻觉、错觉。怀疑周围的人,不论认识与否、不论男女老幼,甚至骨肉之亲的大哥都仇视他,想吃掉他,别人一个眼神、一句话、一个动作皆包藏祸心。“鲁迅认为这些东西(金和铁,即经济和军事)是不能真正救中国的,关键还是需要‘立人’。需要树立怎样的人,那就是强调人的精神力量。他说:‘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奚事抱枝拾叶,徒金铁国会立宪之云乎?’”[3]一部《狂人日记》所记载的是狂人的心灵史。
《寒门》里的冯维聪由于高考,最后也成为了疯子,锁定贫困而封闭的云南高寒山区,这便具有了深刻而丰富的典型意义。
高考以后从冯维聪变成这样:
冯维聪抱着一堆教材,跑到小学的操场上,将书摊开,念念有词,朗朗上口。念得口干舌燥,念得满头大汗,任何人叫他停下他都不停,任何人叫他离开他都不肯。……
冯维聪失去正常思维,在水中找了快乐和自由:
他在找水的感觉,找人生流动的感觉。……他觉得整个人和水融在一起,水渗进了他的身体,他的身体溶解在了水里。或者是,他冯维聪根本不存在,他本来就是一汪水,甚至只是一滴水。是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很舒服,舒服得想死,想没有自己,想忘记了一切,想没有整个世界,或者这个世界没有他。……
鲁迅的《狂人日记》里的13则日记从社会、家庭、自身和孩子来揭示中国的吃人的历史,吕翼的《寒门》里的冯维聪,与“狂人”有着惊人的相似: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他们都是一个被迫害狂患者,从象征主义的角度看,他们又是清醒的反抗的战士。《寒门》运用了陌生的视角,刻画出正常人与狂人之间的关系,由“狂人”这一陌生视角,具体描写“狂人”的种种病状,疯言疯语、偏执、妄想等,突显出常人世界吃人而不自知的不可理喻。“陌生化”就是有意使日常熟悉的东西呈现陌生的面孔,摆脱惯性,唤起对世界的新感觉。一个真实的患迫害狂症的精神病人,而他的疯言疯语中又寓含了深刻的真理。狂人的见解越是卓越超群,在旁人眼中便越显得狂乱。
冯维聪特别怕人说话,怕炒菜时锅铲与锅底相撞的声音,怕万礼智每天早晚从门前飞驰而过的破摩托发出的油腥味和噪音。……
冯敬谷领着冯维聪从万家大门前走过的时候,万家高高的阁楼里传来一个少年的声音:疯子!疯子!
冯维聪与整个村庄隔绝了起来,与整个社会也隔绝了起来,特别是恋人冯春雨离开村庄去读名牌大学,加重了他的病情,亲人的关爱与温暖依然不能让他的病情好转起来。他只能在自己的游戏里游离着,与世人绝不相容,敏感于别人的目光,在稠人广众之中,感到更孤独。严重的自卑心理与多愁善感的气质,使他无法排解自己的心理压力。对爱情饥渴,冯维聪的性格和现状又妨碍他去获得爱情。在冯维聪的“创造机器人”里寻找到作为一个人的自由和成功的感觉,他成为了抛弃社会的人和被社会抛弃的人!
冯天骏的成长更加艰难和坎坷,他的成长背负哥哥冯维聪精神失常的心理阴影。他太渴望摆脱贫穷而落后的碓房村,太渴望过上“人上人”的生活了,从“人下人”的现实跻身“人上人”的阶层,唯一的通行证就是高考。冯天骏的理想的北大和清华,是开奔驰豪车……而亲眼目睹了万礼智因为儿子万勇迷恋网络游戏甚至堕落而发狂的夜里:
整个夜里,他都没有睡着,看着漆黑的天花板,满脑子要就是万礼智嚎啕大哭的样子,要就是大学录取通知书飞来飞去的样子,要就是爹妈在田里泥以脚水一脚的样子,要就是维聪哥神戳戳的样子……
这些描写,已经预兆着冯天骏高考的失败。他对读书从内心感到已经很厌倦:
条条大路通北京,非要和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人挤这座独木桥。给踩扁了,踏死了,落河淹死了,却还是没有实现这一目的。
冯天骏的生命不能承受考试之重,冯天骏不能安心踏踏实实做一个农民,又没有在城镇安身立命的能力,最后落为一位典型的“多余人”。在冯天骏第十五次参加高考时,大学毕业生国家不再分配工作。冯天骏最美好的人生都交给了考试,人生却不可逆转地往另一个方向滑去。作者刻意描写了个人生活及心理的压抑,冯天骏的生命过程里参加了15次高考,15年的青春就是在与高考搏斗,最后以失败告终。作者写了碓房村青年知识分子在社会底层中那种穷困潦倒的心境,无法获得生存的权利的痛苦、悲哀。
冯天骏也曾经成功过,他被省师范院校、西南农院和本地师院录取,因与他的理想北大、清华相距甚远,心里一直与冯春雨作比较,固执、偏执,只能放弃了……这里显示出个人力量的卑微和弱小,如地上的蚂蚁一样,只能蜗行,还不能站立着行走,只因为冯维聪和冯天骏的贫困家乡碓房村和更加贫困的寒门家庭,彰显了命运的强大和狰狞。他们还没有力量和资格与命运和谐相处,在与命运的对抗的生命过程里,僵硬和紧张成为了他们成长的底色,这也就是他们成为“狂人”的潜在因素。
从冯维聪和冯天骏的精神历程来看云南高寒山区的农民,祖祖辈辈的农民,贫困,愚笨,憨厚老实,知天命,积极进取,有改变自己不幸命运的强烈愿望,但与国家、时代的变化,政策法规的接受和实施方面是被动的,稍稍隔绝的,慢半拍的,被时代和社会拖着往前走的,精神能量是被动地一点点、一丝丝挤压出来的,从上往下挤压的。这样,精神方面的主观能动性、潜能还没有挖掘和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这样,人物命运与社会制度之间存在唇齿相依的关系,小说的力量也来自这里。
小说里唯一一位成功者是赵得位,他善解人意,自信,灵活,为自己活,将自己的知识化为能力,青春焕发,不去挤高考的“独木桥”,利用碓房村的天然条件,用智慧和汗水改变着碓房村的面貌,体现了“涧底松”的生命本质,顽强、坚韧,不屈不挠。在与冯维聪、冯天骏的比较中,显示出人格与风格的精彩。
《寒门》可以看成是作者吕翼成长的自叙传。“走出寒门,是一代穷孩子不懈努力的方向,走出寒门,需要的是太多的付出。他们有着不懈的追求,他们有着坚忍的意志,他们有着令人苦痛的往事,但又不得不面对令人苦痛的现实。乡下有太多的穷人,穷父母,穷亲戚,穷邻居,穷学生……这就构成了一副穷苦的世界。他们不仅物质匮乏,而精神世界也是一片苍凉。他们信佛,信神,信风水,信仰会有一双慈善的眼光在上天默默给予观照,所有尽管在那种苦难的岁月,他们依然保持着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相信美好的生活救助不远处等候着他们。”[4]真实性,决定了吕翼小说的基本的叙述内容,就是自我经历以及和自我关系密切的生活。作者追求主人公一种内在真实:孤独感,无法与人沟通的苦闷,自卑、自怜,软弱,颓唐等心理。
小说里写了一个小小的孔子像:
冯维聪双手合十,朝着孔圣人作了三个揖,磕了三个头。他站起,又照先前的样子拜了一遍。先一遍是给冯春雨拜的,后一遍是给自己拜的。他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祈求圣人保佑:圣人呀圣人,你保佑我俩考上理想的大学。我俩考上了,以后有钱了,给你修庙,要多大就多大,要多气势就多气势。如果再有钱,就给你塑身,塑金身……
冯天骏一直把孔子像看成是他的命,他的魂!这些细节既是对读书的重视与尊重,对儒家文化传统的传承,作为一种信仰,就是碓房村农民的支撑力量。另一方面,又是一种精神慰藉,因为冯家子弟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对参加高考不够自信,内心虚弱,寻求保佑,所以需要借助它安慰自己,同时它又代表着一种精神秩序。孔子像既是慰藉也是文化的象征。
冯氏兄妹三人都推崇孔子。大哥冯维聪的真正的精神支撑是冯春雨,他不能承受冯春雨的离去,爱情的幻灭其实是他陷入精神分裂的真正原因。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的痛苦,整个故事里唯有他是彻彻底底孤独的,唯有他的生存的彻彻底底的悲剧。二弟冯天骏的世界里,孔子才是他真正的精神图腾,他能够面对现实,也能够坚守理想。大姐冯天香用出卖身体的钱重修孔庙,既是非凡,亦是悲凉,更是对时代的嘲弄。
冯维聪类似于“狂人”,冯天俊近于勇士(并非完全的失败者),他们都是畸形社会的抗争者。冯维聪和冯天骏都是特定时期,“畸形的社会”里产生出来的“狂人”,作者能够从“狂人”身上发掘母胎的病源,把时代与人生紧密联系在一起,精于描绘冯维聪和冯天骏的痛苦和孤独,把“不幸的青年”的精神世界,生活经历表现给人们,创造了一个与时代相通又隔绝的艺术形象。从一个人的身上望到外面广阔世界,从一个人的脉搏揭示一群人、一类人的心灵史,表现了一种普遍人生的深沉悲剧感。“在鲁迅看来,孔乙己不过的科举制度的牺牲品。作为制度,是可恶的,但作为人,是值得同情的。”[5]暂且不议高考制度的优劣,高考多年来实为维护社会公正的底线,这一制度多少还能给予寒门弟子以希望,然而这一底线近年来也正在逐步失守,教育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制度的失衡。仅仅从冯维聪和冯天骏的命运际遇来看,他们或多或少凝聚着那一个时代的高考人的泪水、汗水和欢笑,更多的高考人是可怜的,可悲的,但又是值得同情的。这也正是中国处在时代巨变时期每一个人的喜怒哀乐的缩影和声音。
小说结尾的大团圆,显得突兀,人物形象突然拔得太高了,冲淡了小说的悲剧意蕴。权力的偶然眷顾与外国的资本也许能够能给故事中的碓房村带来经济上的改变,但改变不了整个农村与寒门的现状。农村与寒门的希望在于重建公正的社会制度。
【注释】
[1]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9月第一版,第733页。
[2] 鲁迅著:《狂人日记》,转载自严家炎、孙玉石、温儒敏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精品选读》,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3月第3版,第141页。
[3] 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第43页。
[4] 吕翼:《寒门内外,我在说些什么?》,《雨花•中国作家研究》2016年第6期第106页。
[5] 钱理群、孙绍振、王富仁著:《解读语文》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第一版第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