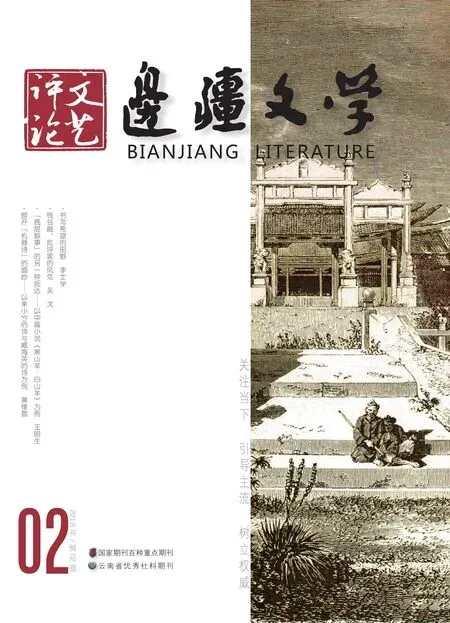异域、存在与先锋
——论段爱松的中短篇小说
唐诗奇
在云南作家中,段爱松是一个异数。他既不偏重于“边地与民族”的书写,也不虚化地域,专注于发现“城市与现代”,而是把二者结合起来,以鲜明的文学地理学的理念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文学王国,致力于在云南这一“异域之境”中写出“不一样的小说”。毫无疑问,段爱松是先锋的。他深知一个真正的先锋作家,不仅仅应当成为一个技术先锋,更重要的成为存在的先锋或精神的先锋。一方面,他承接着先锋写作形式主义的探索,在文本中重新召唤叙事与语言,把“文字炼金术”发挥到极致。另一方面,他又在广阔的时空中追问存在,在寻找“自我历史”的起源中,向形而上的层面进行开掘,拓展了小说的精神版图。在当今以故事、趣味、经验为主的文本的重重包围中,段爱松开辟出一条回归文学自性的道路。
一
段爱松是一个造梦者,读他的小说如临梦境。他曾经说过,“世界上最好的一首诗歌,就是一所绝世独立的房子;而最好的一部小说,则是一座宏伟壮阔的宫殿。”作为一个跨界写作者,他携带着诗歌浪漫、瑰丽、绵长的基因,为他的小说宫殿添砖加瓦、雕梁画栋。在这座年久岁长的宫殿里,因在底下黑暗漫长的时光而显得阴暗、古质、繁复,在时间世界的神秘力量的指引下,段爱松以鲜明的文学地理学概念,用时间的秘匙打开了时光之门,缔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学王国。
段爱松的神话王国位于昆明西南部的一个县,环绕滇池,延伸入海的栈道衬着云贵高原湛蓝的天空,被人们戏称为“小马尔代夫”。这是史前古滇国文明的遗址所在,也因盛产磷矿而闻名,现在是昆明主要高新技术开发区与生产区。这是段爱松的家乡,他生于斯,长于斯,耳濡目染的都是那些神奇诡秘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这个既古老又现代的小城让他充满无限追念与想象,成为他笔下源源不绝的灵感源泉。他以自己的故乡晋宁为据点,打通时空界限,把史前古滇国文明与当代社会连接起来,构建出“晋虚城”的文学概念。在云南,确实很少有作家像他这样拥有明确地对城市有文学地理学的概念,并如此坚定地付诸实践。在段爱松那里,时间的秩序就是心的秩序。随着前世战争片段的不断闪现,人物的身份之谜逐渐浮出水面。
段爱松在小说中不止一次提示我们古滇国与我们当代的关联——“作为某一历史时期的中心,尽管古滇国泯灭,却必然会在另一个历史时期得以轮回。”在文学晋虚城中,人物皆为古滇国亡灵在当代的重新复活,这是一种“定势的命运”,每一个人无法摆脱,亦无从改变。我们很容易注意到,段爱松笔下的人物都是天赋异禀,却又因与生俱来的残缺与社会格格不入。在这些短篇系列中,小说之间的互文性让我们知晓人物的身份与关联,“我”是古滇王国曾经的统治者;把一是我出生入死、并肩作战的好兄弟,也是我最忠诚的仆人;小滴曾是古滇国的将领,英勇无畏,为保卫家国战死沙场;老飞曾是古滇国的著名乐师,在音符中创造生命的奇迹;背果是曾经背叛过族群的罪人,今生的残疾是为他曾犯下的背叛之罪的深度救赎;巫奈是曾经背叛过族群的阴师,而这种背叛也“无声无息地落在了他现世的身上”,他最终被半人半狗的诅咒所惩罚。当我们把几个文本放置在一起时就会发现,背叛过“我”的人在今生将面临因果报应的惩罚,而他们唯有在这种惩罚中才能得到救赎,其命运终将在“非凡与丑陋的怪异结合中继续前进”。这种宿命论或者说轮回观念在段爱松的小说中无处不在地主宰着人物的命运,让小说自始至终都弥漫着一种神秘、鬼魅、惊心动魄的悬疑氛围。
值得注意的是,前世如此辉煌显赫的战争记忆,到了今生,却变得卑微、轻飘、鸡毛蒜皮。从前世到今生,关乎家国生死的战争背景变成了平凡的县城街头,国家的统治者、将领、巫师、乐师皆变为无所事事的街头少年:把一凭借着超人的天赋进行赌博,成为战无不胜的赌王;曾为保卫家国战死沙场的小滴,今生却变得胆小、瘦弱,利用自己的灵敏身型优势去糕点厂偷盗;宫廷的灵魂乐师老飞却在倒卖车票、监控室和炸洋芋中消耗着自己的生命……段爱松用这样的巨大反差似乎意在说明:一个宏大叙事的时代已经消亡,而在当今时代只剩下“一地鸡毛”。晋虚城,实际上成为个体在当代社会中难以寻求身份认同,而通过历史途经寻求寄托的精神家园,这个乌托邦不仅仅是个体的避难所,段爱松还意图把其构造成一个民族文化史诗性的寓言。在千百年浩渺的时空之中,古滇国与当代社会形成了一种隐性的对话,可以看出其构建当代民族文化寓言的野心。
二
段爱松所汲取灵感的古滇国,除了在博物馆中展示的青铜贮贝器等出土文物,甚至鲜有文字记载,实际上更像出于作者的一种想象。所以当段爱松对于“文化记忆”或者说“自我历史”进行寻根之时,这种寻根并非建立于民族集体无意识之上(因为民众对古滇国的认同非常有限,这种历史文化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潜意识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而是个人化、私密化的个人体验的集合。所以,段爱松对“晋虚城”的建构与对“我”的自我身份的探寻,与其说是寻根,不如说是对“自我历史”的重新建构。因为他所要寻找的并非广义上的民族之根,而是自我之源。
“自我”是这些小说中不断重复着的主题。寻找生命本体的真相,这个千百年来被无数人思考过的哲学命题被段爱松再次提起——“现在的我,究竟是谁?”段爱松在自己的文学世界之中,更衍生出了一套时间哲学,在时间世界里,晋虚城古今相通,只要掌握“时间的密匙”就能打通时空,寻找到生命的本源。段爱松不断追问,叙述者“我”不断从他身边的每一个人身上寻找前世的印记,从宗教的普世关照中寻找身份之谜。然而“我”永远无法找到存在的真相,正如“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预知的晋虚城”与“遥远时期突然莫名消失的古滇王国”,“不可预知”与“莫名消失”直接指向了存在的虚无。段爱松在《罪赎》的结尾处写道:“我在自己即将劈裂的身份中,并没有忘记我在寻找的真相。我突然有了某种大悲苦,不是源于自己此刻承受的罪过,而是因为那些我苦苦寻找的东西。”这个“大悲苦”即来自于虚无,所有的追问在死亡的瞬间都回到了原点。他本想在宗教中获得救赎,但无论是清真寺的诵经声,基督教堂的赞美诗,还是盘龙寺的晚钟声都无法让“我”寻找到存在的真相,三个宗教的混乱交织,正体现出了当代人的无信仰状态,或许这即是罪的根源所在。
在这套时间哲学的背后,实际上是一个当代社会中个体的身份建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段爱松的小说中,“父亲”形象是缺失的。父亲形象在我们传统文化中一直被看作“父权”的象征,自五四以来,对“父亲”的反抗在一定意义上被视为对“传统”、“权利”“制度”“权威”的宣战与摧毁。在先锋传统中,也一度以“遗忘父亲”为叙事的先决条件。而段爱松的小说中却充斥着“无父的焦虑”, 《小滴》中的小滴和《西门旅社》中的店主都在等待父亲的归来,小说人物等待寻找父亲的过程,其实也是对自我断裂的历史、对自我起源的一种寻找。与寻根文学那一批作家不同,70后出生的段爱松无法实现自我历史与现实的高度统一,只能在想象的历史中去寻找“自我历史”。然而,无论是对父亲的等待还是追寻,都是徒劳,这种徒劳的等待让人想到等待戈多到来的两个流浪汉,不同的是,段爱松小说中的等待因有明确目的性——追寻“自我历史”的可能——而被赋予了等待的意义与力量。
“和几千年前的大战不同,这次我的敌人,并不在我们之外,也不在我们之中,而在于我,在我逐渐被某个自己牢牢掌控的过程中,深感命运的沉重。就像那次和小剑在巫奈家灶房里,遇着巫奈奶奶的小脚和绣花鞋,兀自离地悬在半空中。远远看去,是那么漂亮,凑到跟前,却一无所依。”(《巫奈》)这段话可以代表段爱松小说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寻找自我的旅途中,自我的敌人恰恰是自我的存在。这成为一个悖论,在经历漫长的等待和追寻之后,最终还是指向了虚无。
在这个现实社会失范、意识形态消解、精神世界失落的时代,段爱松把形式主义策略当作与现实对话的唯一途径。通过这种方式,他一方面向历史的纵深挺进,一方面又向形而上的存在进行追问,试图通过这种美学实践完成个体在当代社会的“自我救赎”。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寻找,尽管他一无所获。正如与魔鬼缔约却得到救赎的浮士德一样,重要的不是所谓的“真相”,追寻本身已经获得了超越时间世界的力量。这或许就是段爱松悲剧精神的所在。
三
毫无疑问,段爱松是先锋的。正如安徽年度文学奖给予段爱松的授奖词中所说,“诗意的构思与非线性的叙事依然坚持和捍卫着先锋写作形式上的荣誉”。叙事和语言在段爱松这里被重新重视起来,多角度叙事则成为其形式主义探索下最基本的叙事结构。无论是《罪赎》中以亡灵的身体器官的视角分别叙事,还是《葬歌》《通灵街》以众多的家人视角叙事,或者是《西门旅社》以店主与小艮的视角交替叙事,这种叙事都分别以自身立场不断补充和再现故事的细节与真相,把一个故事不断拆分,再由读者进行重新整合。这种有意加大叙事难度的文学实践,让文本在叙事中重获新生。
其次,段爱松跨界写作的尝试,让语言获得了解放。这种叙述语言的功能不仅仅在于讲述或者抒情,而在于营造一种意境或氛围,因而常常会造成文本之间的某种“断裂”。那些古老神话传说的讲述、血腥与暴力的渲染、无边无际的想象与回忆,其实与故事进程并无事实上的关联,而是作为一种“言语的乌托邦”,成为个人言说欲望的表达。段爱松通过叙述语言的变换与堆砌,以非凡的想象力构建幽暗、古远、神秘的异域之境,进一步带来感官与感情的解放,重获一种诗性小说的审美体验。所以,在阅读段爱松小说的时候,要求读者对固有的被简化或被“养成”的思维模式进行转换,才能获得打开段爱松小说艺术空间的密匙。
当我们在确认段爱松的先锋性之后,或许随即会产生这样的质疑:这种形式主义的探索早在20世纪80年代“那个叫马原的汉人”那里就已经登峰造极,段爱松的先锋写作究竟意义何在?我想说的是,段爱松的“先锋”不仅于此。在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浪潮沉寂之后,陈晓明发出“文学颓败”的断言。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文学死亡”“先锋消亡”“理想主义的终结”之类的声音不绝于耳,正如谢有顺所担忧的那样:一方面,对存在的追问、人性的深刻剖析、人的处境的深切体察以及虚无对人精神的戕害等在文学中长久缺席。另一方面,“讲故事”文本大行其道,叙述和语言退场。这个时代更加青睐那些善于讲故事的人,而非专注于怎样叙事的人。在这一片众声喧哗之中,每年数以千计的长篇小说得以出版,故事的版图在极具扩张。然而看似文学繁荣的背后,实质上空空如也。先锋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实验性的语言游戏和叙事迷宫,而更应该注重先锋所体现的核心精神——反抗和自由。无论是反抗体制或意识形态,还是反抗旧的艺术传统,先锋精神在于自由地展示自我审美理想,表达对人类存在困境的思考和诘问。从本质上来说,一切精神上与创造性、反叛性、实验性、前瞻性相关的写作都可以归入先锋主义的范畴。
在先锋沉寂后,段爱松仍然坚持先锋写作,可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先锋派之所以受到质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过于重视形式主义的探索,而忽略了精神层面的开掘。但段爱松的小说实践不仅保持了先锋写作的“形式上的荣誉”,更拓展了先锋叙事的精神图景,对“自我历史”的追问与“自我救赎”的寻找使得小说具有形而上的张力。这种探索曾在张承志那里出现过,段爱松的追问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段爱松这一代个体的“心灵史”。所以当我们在谈论段爱松的先锋性的时候,不能仅仅从他的形式主义探索入手,而更应当关注段爱松站在时代前列时对人的存在、人性以及对历史发展衍生出来的虚无的关注和承担,并在作品中形成的独立话语空间来承载这种非凡的艺术感知能力。如果说80年代的叙事革命是为了消解文本意识形态话语的话,那么段爱松先锋的再出发,则是为了对日常和经验叙事所带来的庸常的反抗,对关乎存在与精神的那种充满力量的小说的重现。
段爱松的小说令人惊喜,但后现代语境下的先锋写作仍然面临着“无边的挑战”。如何在晋虚城的与当代社会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而不至于陷入固有的叙事套路?如何在历史关照下更有效地切入当代经验,反映当代个体的生存困境?如何在存在的虚无中重建“自我历史”,探寻生命的来路与归途?有效解决这些困境将成为段爱松小说能否走得更远的前提。无论如何,段爱松的小说让我看到文学回归自性的希望,他的创作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