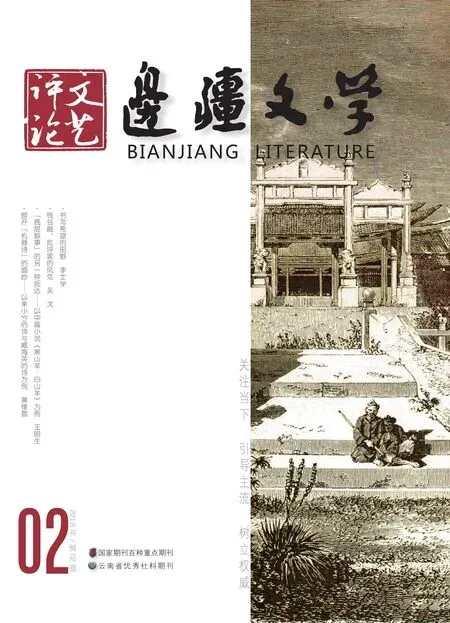段爱松小说的“异域之境”
主持人宋家宏:今天我们讨论段爱松的小说。段爱松是昆明的作家,最近几年他的小说在外面影响很大,许多重要刊物都在接连发表他的作品。昆明出的小说家不多,有影响的是张庆国、陈鹏,他们之间年龄差距很大。爱松的写作与陈鹏和张庆国都不一样。大家现在对他也有所了解了,他主要是写诗歌和小说,也写散文,可以说是全面开花。当然,他主要的成绩还是在小说方面,我们今天就以他的小说为主要内容进行讨论。
一、总体印象
主持人宋家宏:首先来说说对段爱松小说的总体印象,谁先说?
张旭(现当代文学2015级研究生):我先来说说吧。读段爱松的小说,给我最大的感觉是昏暗、晦涩、神秘。我读完一遍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没法进入段爱松的小说。为了理解段爱松的小说,我去了趟云南省博物馆以及观看了纪录片《消失的古国·古滇国》。有了文化背景,我再读了一遍段爱松的小说,我发现段爱松偏爱塑造一种阴暗扭曲人物形象,通过亡灵叙事等手法使他的大部分小说蒙上一层昏暗的色彩。另外,他小说中有很多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加大了阅读难度。
赵昕旖(现当代文学2016级研究生):读完段爱松的小说,我的总体印象是:在诗意的语言下,内容是都是源于日常生活经验。就像《滇池》文学杂志副主编、诗人李泉松简评的那样,在平实的日常中发现诗意。段爱松自己也说,“最终我们还得回到我们最有生命力的日常来,这是时代给我们的唯一选择,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无论用什么办法,努力会在繁复的日常中发现真正的这个时代特有的、被隐蔽了的诗意。”
蔡晓芸(现当代文学2016级研究生):我读完觉得段爱松的小说觉得有几点不一样。一是内容上的不一样。段爱松的小说打破了古代与现代、生者与死者、人类与妖魔、梦幻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作品透露着一股奇幻之气,并借助想象力极大地拓展了故事的叙述张力,给人以另类的阅读快感和思考空间。二是叙事上的不一样。小说作品可分为诗歌性和小说性两种类型。他不仅喜欢在小说中插入诗歌,还喜欢用诗歌的方式去写作,思绪游散自由、哲学思辨性强。三是意味上的不一样。作品中将西方宗教色彩和中国佛教思想融为一体,用宗教关怀人生,拯救人生罪过。
唐诗奇(现当代文学2016级研究生):段爱松曾说过,世界上最好的一首诗歌,就是一所绝世独立的房子;而最好的一部小说,则是一座宏伟壮阔的宫殿。我觉得段爱松小说给我的总体印象就是一座宏伟壮阔的宫殿。而且他的小说中充满了对存在的追问:我是谁,我来自何方,我将去向何处?文本因这种浓烈的哲学思辨而具有形而上的张力。
陈林(云大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毫无疑问段爱松的小说创作是非常小众的,很难让大家都喜欢阅读。但我比较肯定的一点是,他在现实语境中给古滇文化一个非常大的想象,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一种历史来读,我会把它当作一个“民族文化的寓言”,或者称作“潜意识的社会史”“感觉记忆的文明史”,或者说是一种扩大的修辞,一段虚构的历史,或饱含历史内容的诗。所以我读他的作品时会想到“史诗”这个概念。阅读的难度在于他的小说是诗化的,是跨文体的,所以他要面对的是他如何处理文化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问题。而段爱松也一直在做这样的努力——将历史文化转化为诗性叙述,他在这方面绝对体现出了他的才华。
主持人宋家宏:段爱松这样的写法在今天的小说界可以说是非常少了,这样的写法多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新世纪以后逐渐减少。或者说他是在追寻着先锋的背影,这就决定了他的小说是极为小众化的。我们当然不能否定他的探索,他的探索依然有价值,但是他也必须面对大众读者,甚至稍微具有专业眼光的读者对他作品的拒绝,这也是一个客观事实。很多先锋作家在新世纪以后都逐渐把先锋写作和现实主义结合起来了,因为中国读者习惯于现实主义作品,这样能够获得更大的读者群。这就要看段爱松要走哪条路了。
二、异域之境:晋虚城
主持人宋家宏:好的,这个问题就到这里。下面我们来谈谈你是如何理解段爱松笔下的晋虚城?
余莉(现当代文学2015级研究生):我认为段爱松有意通过“晋虚城”打造一个自己的叙事空间,有点类似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他曾说晋虚城是他生命和写作的根脉,我觉得他既是在探索作为古滇文化发源地的晋虚城的独特性,也是以文学的方式激活晋虚城的历史和现实。他把云南当作他写作的独到的异域之境,以此建构起自己的写作方式,这就包括了小说中的地理性环境、叙述视角、想象空间,通过这些来进行他对于“世界和文学神秘性”的探索。
李璐(现当代文学2016级研究生):我觉得晋虚城是段爱松创作的原点和归宿。段爱松说过,“晋虚城”于他来说,是根脉,是生命的根脉和写作的根脉。这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现实中的古滇文化核心晋城是作者的故乡,晋城给予段爱松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现实素材,以及创作背后那种强大的文化支撑力,目前读到的这些小说都与晋城相关;另一方面,一个新的“晋虚城”也由作者建构起来,是一个文学的想象的王国,里面蕴含着作者对晋城的感情,以及作者自身对文化的理解。
赵昕旖(现当代文学2016级研究生):晋虚城在段爱松小说中是一个隐形的主体。隐形是在于,在中短篇小说中,他都没有大篇幅着力刻画晋虚城的风貌,只有寥寥几笔带过,显得简练而又模糊。但是主体在于,整个小说的背景、发生地、人物等都与晋虚城相关。晋虚城不再是作为地点的一个表征,而是同个体生存状态与情感相通的纽带,并不完全是虚幻的异域之境,而是当下的现实寓意同传统的续接。
唐诗奇(现当代文学2016级研究生): “晋虚城”对于段爱松的创作来说,一方面,可以让他的童年经验有效的进入他的创作,把人物通联起来,形成了文本间的互文效果,构建属于段爱松自己的文学王国。另一方面,这个建立于古滇王国之上的“异域之境”,也为其神秘叙事埋下伏笔。
蔡晓芸(现当代文学2016级研究生):作为作者,“晋虚城”的存在是他写作的源头和动力(根脉),他曾透露将以“晋虚城”和古滇文明为核心,创作一系列长篇小说,“这可能将是我毕生最大最重要的一个写作计划,所幸已经拿出了两部,还算开了个不坏的头吧。”因此可看出,建构一座文学上真正意义上的“晋虚城”是段爱松写作的终极追求。
陈林(云大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 “晋虚城”这个名字恰好是熔铸了当代的晋城和过去的古滇国,这个“虚”字也提示了其虚构性。我特别看好段爱松的原因在于,他并不是遁入一个虚幻的古滇国的世界,而是他切实感受到了我们现在的经验世界与传统的脱离和分裂。他试图在这种脱离和分裂中为当代人的生命困境寻找依据,他在表面的经验世界的断裂之中,试图发现当代的晋城和过去的古滇国隐秘的内在关联。所以我觉得“晋虚城”恰恰不是当下的晋城,也不是回到古滇国,而是在二者之间形成一个非常巨大的、矛盾的、冲突的、悖论的世界,我觉得他正是在这种互文性关系中建构他文学的晋虚城。
主持人宋家宏:我把段爱松作品中的晋虚城看作是他的一个创作根据地,像莫言的“高密乡”,其实很多成功的作家都有他的创作根据地。昆明的作家恰好不太重视这个,我曾经说过,昆明作家没有写出昆明来,没有建立自己创作的根据地,几乎是一个普遍现象,可能他们认为写城市不是云南作家的长项。段爱松虽然没有写昆明,但是写了他的家乡。他在晋城中间加个“虚”,刚才陈林说的特别有意思,它既不是写实的晋城,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虚构,它是把历史和现实作了交融、虚化的处理,成为了他的根据地。这个跟莫言的高密乡还略有不同,莫言的高密乡写实性多一些,段爱松的晋虚城更多虚化,我们知道写的是晋城,但它又不完全等于晋城,这个小说背景处理得很好,若虚若实,我很欣赏。
三、古滇国文化的审美关照
陈林(云大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可以说古滇国文化在段爱松的小说中无所不在,尤其是在那几部重要的小说中。它的表现形式是多层面的,比如说在修辞和意象上,对青铜贮贝器的借用;在故事层面上,对古滇神话、传说、故事的援引;在观念层面上,宿命论、不可知论和一些轮回的观念也有很多表现;还有主要是小说营造的整体氛围,好像一切是浸透在古滇国原始宗教和充满着巫文化色彩的世界中;还有一个表现,就是对人物塑造有很大影响。那些人物看上去可能都不是当代人,似乎是一些奇怪的、天赋异禀的、非人化的人。
唐诗奇(现当代文学2016级研究生):古滇国文化为段爱松的小说注入了神秘的巫邪之气,它冥冥之中主宰着小说中人物的命运。但是,对古滇王国的这一异域宝库的挖掘,有同质化和重复化的嫌疑,如果成为一种固定的叙事策略或者叙事套路只会作茧自缚。
蔡漾帆(现当代文学2015级研究生):我觉得段爱松是把古滇国文化作为自己的一个精神寄托,就如同他创作过程中他需要时刻地返回到这一块领地吸取养分或者小憩一会儿,因为我们可以看出段爱松对于自己是成长在古滇国文化的土地上这一点还是相当引以为豪的,他就会把这些因素不断地注入到自己的作品里面,隐形中像是他在打一个“商标”一样,在创作中突出某种特色。
李璐(现当代文学2016级研究生):作者在面对当代经验与传统文化之间是很矛盾的,是一种又对抗又融合的方式。他在《青铜魇》里面表述现代文化蚕食冲击着古老的文化,然而古滇文化其实呈现的是一种暗自生长的态势,作者通过小说构建出人物的形象、离奇的事件,来对古滇文化进行自己所理解的阐释。
沈鹏(现当代文学2015级研究生):读段爱松的作品有些像读莫言的作品,它是带有魔幻神话色彩的,而他正好就是借助这种魔幻色彩来搭建他想象中的传统古滇文化。
陈林(云大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段爱松在处理当代经验于文化传统这个问题的时候,与现代很多作家不同于“五四”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传统一样,他不是在这种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愚昧的二元对立中来处理当代现代性与传统,而是来看他们之间存在的隐秘的关联。他的小说有的地方可能会陷入某种模式化,我认为他的写作难度就在于如何让自己的写作有着当代的丰富性,对当代社会的洞察足够多,结合古滇国文化,他进行的是一种当代和传统的格式的对话。
四、人物塑造的特点
主持人宋家宏:段爱松小说在人物塑造上有什么样的特点?
沈鹏(现当代文学2015级研究生):段爱松作品中塑造的人物都具有天赋异禀。就像《把一》中的人物把一,他擅长玩镍币;作品《背果》中的人物背果擅长于机械制造;《老飞》这部作品中,老飞又具有演奏天赋。但是,他们在拥有天赋异禀的同时,它们的身体上或者性格上又具有某种残缺。比如背果因小时候不小心摔了以后,身体成了“前鸡胸后驼背”,而小滴则是性格懦弱,胆子小。
主持人宋家宏:想过没有他为什么这样做?
蔡晓云(现当代文学2016级研究生):我认为身体上的残疾是“我”在此时这个世界上的失落或者残缺感,这种失落和残缺“我”回到古滇国文化中弥补回来,“我”其实是现实与古滇国之间的一个桥梁,通过“我”可以了解到过去同时也与现在发生着关联。
唐诗奇(现当代文学2016级研究生):其实段爱松在小说中不止一次提示我们古滇国与我们当代的关联——“作为某一历史时期的中心,尽管古滇国泯灭,却必然会在另一个历史时期得以轮回。”结合段爱松在小说中所透露出的宿命论思想和人物的命运来看,这些人物在现世的残缺都是与其前世在古滇国时期对“我”的背叛有关。现世的残缺不仅是惩罚,更是一种“深度救赎”。
陈林(云大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他的身体残缺可以说是一种人类存在的困境的表现,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小说中人物的残缺是古滇国给予他的文化基因遗传下来的,还是指我们在当代面临的困境?需要注意的是,他将对天赋异禀的世界的想象与传统的古滇国文化联系在一起,毫无疑问是当代人在对主体建构的过程中遇到极大的困难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当代不存在一种主体建构的困难,那么虚构的想象是没必要存在的。
主持人宋家宏:人物的天赋异禀与其身体的残缺是段爱松小说里人物的突出特征,除了这个特征,大家说说其他特征。
王岩(现当代文学2016级研究生):除此之外,还有人物的内在精神和现实世界之间产生撕裂的“孤独者”的想象。在《西门旅社》中,两个人实际是自己与自己的对话,某种程度是对现代化快节奏生活中人们扭曲的生活方式的揭露。《老飞》中的老飞,一方面置身于对物质世界的追求之中,另一方面常常产生精神与肉体分裂的矛盾与孤独。
陈林(云大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他笔下的人物基本上没有一个比较健全的、有现代灵魂的人,尤其是他们在人物关系上,即便他写当代世界一方面他是比较符号化的人物,写着写着就变得完全非人化。且他的人物不是独立的一个人,人物之间有一种主仆关系,尤其其中叙述者几乎就是主人,其他的人物无论他有多大的能耐他不过是“我”的一个仆从,这可能也是一种文化无意识的影响,他人就是为“我”而存在,“我”是他们存在的意义,所以小说中没有一个独立的现代人的影子。
主持人宋家宏:为什么他的小说里的人物会出现这样一个特点?
蔡漾帆(现当代文学2015级研究生):他似乎有意要体现现代人的焦虑,这些人物他不仅是外形上有些畸形,他们的心理也是畸形的,而这种畸形可能来源于外界的某些压力。比如老飞,他的一直处于漂泊的状态,从开始的倒卖车票,再到在酒店当保安,后来又在街上买洋芋,但是他始终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所以作者通过这些人物也在表现现代社会给人们带来的焦虑之感。
五、艺术特色探析
主持人宋家宏:这些小说在叙事艺术探索上有何特色?
王岩(现当代文学2016级研究生):首先从他的叙事结构来说,他采用一种非理性的叙事方式,以及创造一种空缺式结构。从叙述视角上来看,他的小说中常常出现身份不明的叙事者。从叙述时间上来看,总体来看时间变化不定,仅从一篇小说中都可以看到各种时间被穿插进去。叙述语言上,他重视语言的形式以及语言的能指。其次是巫术语言的运用,他使不合常理的人物奇特的言行和神秘事件变得合乎情理。最后,诗歌和音乐术语的运用,使作品成为富有诗性特征的音乐小说。
张旭(现当代文学2015级研究生):刚才说到对段爱松小说的总体印象时,我说到晦涩,段爱松在小说里杂糅了诗歌、音乐,在结构上也探索用音乐的方式来建构小说,比较明显地是《葬歌》这篇小说,用不同的乐章展开叙事。
陈林(云大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我也认为段爱松的写作完全不是一种炫技行为,他的每一种形式和叙事都有很深的意味在里面,包括不同视角的切换,亡灵叙事不只是亡灵叙事,《罪赎》里面甚至是身体上各个部分在叙事。《青铜魇》以青铜的视角,以梦的形式。如果《红楼梦》这部作品,他不是一人的视角,而是以楼房的视角来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青铜魇》这部作品恰巧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以青铜的视角切、以梦的形式。当他以青铜的视角来写古滇文化时,古典文明就像是一种自我呈现,因为我们从出土的文物或是文字记载无法了解真实的古滇国,青铜本身镌刻着古滇国的密码,所以通过梦的形式、以青铜的视角古滇国文化便得以呈现。
赵昕旖(现当代文学2016级研究生):还是谈谈段爱松诗歌化的语言的问题,我不认为这是刻意的炫技,他在采访中谈起过这样的写作方式,“写不一样的小说,不是刻意标新立异,而是写作独立,精神独行,发出属于自己的文本声音。”如《西门旅社》反映的希望与寻觅下的生的痛苦,《通灵街》中对死亡和欲望的坦然,还是《青铜魇》中超越时间的对话,全都容纳在像诗一样的句子里,会晦涩但更深刻,用诗歌给予了小说能给予的意蕴和思考,这样的探索方式应该值得肯定。
蔡漾帆(现当代文学2015级研究生):我想单独说一下《通灵街》。首先,在叙事层面上讲,它是一部没有介入作者太多主观感情的“零度叙事”小说,他通过亡者的亲属的不同视角的叙述完成了这部小说。其次,在内容上,我们会发现作者在小说中所叙述的殉葬是新老结合的一种殉葬方式。作者在面对传统与现代的问题时,没有明显地表露出极端的态度,而是呈现一种客观事实,用包容的眼观来看待这种文化冲突。
陈林(云大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我在读的时候发现了段爱松小说中的三个传统。一个是80年代的“寻根”传统,段爱松在寻他的古滇文化。但是,寻根传统又不能简单地把他理解为古滇文化的民族主义者,这是需要注意的。第二个是先锋传统,他在形式上、语言风格上的探索,这是非常明显的。再次,我要强调的是新历史主义的传统。他对历史的关照,不是说把历史当作我们现代以来非常流行的某种历史主义以为的那样——历史是线性的、进步的,而他恰恰是在追溯历史中的梦境化的、隐喻化的东西。
主持人宋家宏:你说寻根文学,但段爱松跟寻根文学又很不一样。因为寻根文学主要就是要寻找两个东西——一个是对今天的社会历史还有推动作用的、有价值的文化,另一个是我们传统里头和这个社会相阻碍的东西。但是段爱松的“寻根”没有很明确的价值判断,他是把他生活的晋虚城当作一个背景,且不作价值判断,而寻根传统的价值判断是很明显的,这可能就是他跟寻根传统一个根本的区别了。
陈林(云大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寻根文学可能大多都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中来思考问题,但段爱松的新历史主义的观念恰好让他超越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比如文明与愚昧、进步与落后这样的观念,搁置了价值上的选择,包括语言风格,总的来说确实和寻根文学的那代人不太一样。
主持人宋家宏:他和这三种传统都有联系,但又都有区别。包括和先锋小说,我们开始读的时候很容易觉得,这不就是先锋小说吗?当讨论起段爱松的小说时,有人就说,马原都回归现实主义了,他还搞先锋,有什么前途?从我们开始讲到的大众文学的层面上来说,确实没有前途,读图时代的来临冲击着我们传统的审美心理,谁还愿意读一部小说去猜谜?但是我们又不能否定在小说领域中,我们又不能否定有这个探索性的作家的存在。就是因为有这些小众的、具有探索精神的小说的存在,文学才会进步。我觉得段爱松小说的价值就在于此。
六、你最喜欢哪篇(或哪几篇)?为什么?
蔡晓芸(现当代文学2016级研究生):就像刚刚老师说的,中国读者可能更偏向喜欢现实主义的作品,我也更喜欢他的《西门旅社》和《通灵街》,因为他的故事性更强,“炫技”减弱了,先锋性没有那么强,让人比较容易理解。
赵昕旖(现当代文学2016级研究生):我最喜欢《罪赎》,这是我读的最慢也是思考最多的小说。晋虚城很像一个人的人生,又像整个生活的百态,在这期间,你看到的只能是“罪”本身,然后才能看到赎罪的“赎”。“赎”可能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永远在进行下去的过程,就像一直不停歇的诵经声,赎就是寻觅着往下走的过程。
陈林(云大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我也来谈谈我对《罪赎》这个作品的理解。首先,段爱松把“罪”普遍化了。当我们在阅读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们几乎看不到有晋宁连环杀人案的事实,因为这个“罪”被普遍化了,并追溯于人的一种本性,换句话说,“罪”可以理解为人的本性的一种异化。而罪赎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对人的存在,或者说人的精神历程的异化进行追根溯源的追问和还原。这一点非常重要,我非常看重他的形式也在于这一点,它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他确实模拟了杀人时对身体的肢解,另一方面,他是对身体的一种还原。罪赎如何可能?对罪本身的一种暴露,可能是得到罪赎的前提。事实上,我们当代的很多“罪”,之所以不能得到“赎”,首先就在于我们不能揭露它,“罪”不能被暴露。而段爱松就把这个罪暴露了,在暴露的过程中,我和凶手融为一体,站在一个超越道德的、超验的视角,对自身经验和精神历程做出揭露和反思。罪赎的过程,我理解为一条炼狱之路,他不停回望,不断暴露“罪”的本身,这是罪赎的前提。
主持人宋家宏:是的,这个小说非常有想象力。
陈林(云大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陈鹏的小说《第五十六个》也写过这个晋宁杀人案,但是完全不一样的写法。
主持人宋家宏:《罪赎》这个小说把晋宁杀人案完全虚化了,成为一个背景,其实是把他放到更大的当代空间里看,罪恶怎么赎?只有暴露才能赎,而在当代空间里,很多罪恶不能被暴露,所以更谈不到赎。从这个角度说,这篇小说可以说是他的小说中分量最重、最能调动想象的一篇,至少在这十篇小说中是如此。
刘敏(现当代文学2015级研究生):我比较喜欢《西门旅社》。首先在叙事形式上,这篇小说回归了传统,完全基于对真实存在的旅社的逝去年月的怀念。西门旅社好像是从这个小镇中剥离出来的一种意境。从人物形象上看,一个人的人物形象就好像包含了所有人的人生历练,作者所虚构的意境和现实就融合在一起了,读起来很有意味。
主持人宋家宏:说《西门旅社》回归传统、回归现实,也不是那么准确。《西门旅社》不是很典型的现实主义,和苏童他们后期向现实主义回归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较,《西门旅社》对形式的探索还是很明显的。说他向现实主义回归,我觉得还为时尚早。
李璐(现当代文学2016级研究生):我比较喜欢《老飞》。首先,作品的整体风格我很喜欢,作者在其中融入歌词,想象力非常丰富。其次,他身上有堂吉诃德的意味:浪漫的、理想的、荒诞的、讽刺的、不堪的。老飞是倒卖车票的,做酒店安保工作的,卖炸洋芋的。他在现实中流离,但他又是幻想里古滇国的英勇的将士。作者将老飞世俗的行为艺术化,人间岁月被演奏成一曲华美的乐章。其实作者想要探讨的还是一个文明与现代,留存与消逝的问题。
王岩(现当代文学2016级研究生):我也喜欢《老飞》。因为小说表现了物质世界生活中当代人所产生的精神困境,比较贴合当下,使人产生共鸣。“我”是一个可以跨越史前古滇国至今的虚拟幻影,是古滇国的故都晋虚城的象征。老飞是生活在现实世界的真实人物,是离开故土的流浪者的象征。因此,“我”是留在晋虚城的老飞,老飞是离开晋虚城的“我”。我在和老飞进行二重奏时,我与老飞之间琴音的冲突,实则是老飞外在与内在的自我矛盾,是老飞挣脱不开的精神困境。
陈林(云大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我可能比较偏爱段爱松的创作方式,喜欢的作品比较多,很多作品都给我带来了很多惊喜。他写到当代的作品,比如《西门旅社》《老飞》《小滴》,我们可以把它当做当代经验的寓言化书写,而不同于一般的现实主义。比如刚刚提到的《老飞》,为什么老飞一会在卖炸洋芋,一会儿在倒卖车票,其实非常明显,他写出了当代人的这种无根状态下的漂泊。写这个题材的人实在太多了,问题就在于他怎么写,写得怎么样。所以我非常看好《小滴》这个作品。他从一个最个人的童年经验写起,却写到了一个时代。首先,从个人来说,小滴表现出一种“无父”的焦虑,他一直在等待父亲的回来,联系到时代,就会让人想起一个知青回城后怎样抛弃了乡下的孤儿寡母。他从个人经验上升到了时代的隐喻性的结合,当然,最后,他还是落在古滇国,把小滴想象成古滇国的一个勇士,那么就具有了从个人到时代再到文化这样的层面。
主持人宋家宏:经过今天的讨论,大家都认为段爱松的小说很“难读”,难就难在大家习惯性地用读现实主义小说的方式去进入他的小说,老是要去想,他这样写的原意是什么?这是读现实主义的方法。读先锋小说、现代主义小说不能用读现实主义的方式去进入。它仅仅是给你提供一个基础,让你在此基础上发挥想象,调动你的参与,你读到多少、想到多少,只要你有根据,就可以成立,不需要你去作品里找生活逻辑,不存在误读,怎么解读都可以。
好的,今天讨论就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