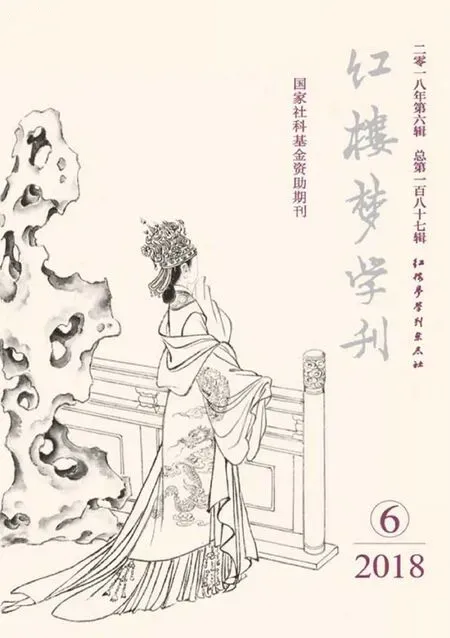贵族世家的衰颓与平民情结的生成
——管窥《儒林外史》与《红楼梦》的精神联系
内容提要:作为“世家之宝鉴”的《儒林外史》《红楼梦》,同时诞生于“康乾盛世”,同出于落寞的世家子弟之手,这决定了两部巨著必然存在多方面的精神联系。基于雄厚的历史文化修养及对时代本质和趋势的深刻洞察,两部巨著的作者在文化品味、爱憎褒贬及思维方式等方面,均存在着可以深入对话的广阔空间。两部巨著的作者对时代和人生的深入骨髓的思考,使其作品不可避免地染有浓厚的伤感虚无色彩,同时却也使他们更加认识到生活中积极力量之珍贵,那便是贵族世家的仁厚情怀与平民阶层的质朴强韧。吴敬梓和曹雪芹没有走向彻底的虚无而陷入沉沦,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幸运。
一、“世家之宝鉴”:《儒》《红》共通点略说
十八世纪中叶,我国小说史上几乎同时诞生了两部巨著,即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下或称“《外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业师张国风先生曾经指出:“正是在我国古老的封建社会回光反照的这一历史瞬间(按指康乾盛世),吴敬梓和曹雪芹更加深深地感受到一种‘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痛苦和悲哀,从而表现出现实主义艺术大师对时代本质和趋势的可贵敏感。”两部巨著的作者在年龄上相差十余岁,基本属于同一代人,两人又同样出身世家大族,同样经历过繁华到落寞的岁月,借用《红楼梦》第二回中贾雨村的一句话,吴敬梓和曹雪芹都是“翻过筋斗来的”。以上种种共同点,决定了两部巨著必然存在多方面的精神联系。仅从情感表现的力度而言,近人天僇生便说曹、吴“作此书时皆深极哀痛,血透纸背”。不过,此前对于两部巨著之间的精神联系,有的学者曾作出比较消极的论断,认为“《红楼梦》所歌颂的人物,是《儒林外史》里没有的”,“《儒林外史》所歌颂的人物却正是《红楼梦》要批判的”,“《儒林外史》总是向着上一代,对老年人有好感,《红楼梦》总是向着下一代,对年青人有好感”,“一个(吴敬梓)缅怀于既往,一个(曹雪芹)求索于未来,其思想趋势是两股道上逆向开的车,存在着回归与叛逆原则上的不同”。对于这样一种大而化之且趋向极端的观点,今天的论者是很难完全认同的。本文在择要吸取学界若干成果的基础上,尝试管窥两部巨著之间的精神联系。
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中说:“雪芹之稗官,世家之宝鉴也。”台湾学者欧丽娟教授称《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唯一一部真正叙写贵族世家的小说”。《红楼梦》中的贾家乃“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其为贵族世家自不待言。《儒林外史》中写及的世家,最典型的是“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天长杜家,这是以“五十年中,家门鼎盛”的全椒吴家为蓝本,小说中杜少卿的原型即作者吴敬梓,杜慎卿的原型即吴敬梓的从堂兄吴檠。《外史》第四十七回写到的五河县虞家也是世家,回中交代虞华轩“曾祖是尚书,祖是翰林,父是太守,真正是个大家”。李汉秋先生早就指出,虞华轩形象“是作者早年在故乡愤世嫉俗、满腹块垒的受伤心灵外射的投影”,可见虞家跟天长杜家一样,同以全椒吴家为蓝本。《外史》第八回以下所写湖州娄家也是典型的世家,书中交代娄公子已逝的祖父是太保,父亲是中堂,娄大公子现任通政司大堂。娄三公子、娄四公子虽因科名蹭蹬而牢骚满腹,但其身上却有着鲜明的世家风范的展现。《外史》第五十三至五十四回所写南京国公府的徐九公子、徐三公子,是明朝开国元勋徐达的后人,从国公府的陈设及两位徐公子的言行看,他们还是保持了世家大族的风范的。
近人解弢推崇《红楼梦》《儒林外史》善写“富贵家气象”,并引用了“三世仕宦,才晓得穿衣吃饭”的名言。《红楼梦》之善写“富贵家气象”,乃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儒林外史》所写“富贵家气象”,在精细程度上自不能望《红楼梦》之项背,但书中偶尔点染的几处,亦非世家子弟不能道。如第十回写娄府焚香,使鲁编修“飘飘有凌云之思”,娄三公子且向鲁编修道:“香必要如此烧,方不觉得有烟气。”其中的“必要”二字,使贵族生活之精致与自得跃然纸上。又如第三十一回写杜少卿招待韦四太爷,“肴馔都是自己家里整治的,极其精洁”,“内中有陈过三年的火腿,半斤一个的竹蟹,都剥出来脍了蟹羹”,席上还喝了埋在地下九年零七月的陈酒。“富贵家气象”最核心的内容,还不是上述物质层面的表现,而主要落实于“诗礼传家”或“富而好礼”。《红楼梦》第三回写林如海向贾雨村介绍贾政,谓其“为人谦恭厚道,大有祖父遗风,非膏粱轻薄仕宦之流”。同回中又以叙述人口吻称赞贾政“礼贤下士,济弱扶危,大有祖风”。第十九回中说“贾宅是慈善宽厚之家”“从没干过这倚势仗贵霸道的事”。第三十三回写贾政说“自祖宗以来,皆是宽柔以待下人”。贾府相当看重家族诗礼传家的传统,因为这是彰显家族威望和文化品级所不可或缺的,在家族教育、日常礼仪及婚姻缔结等方面,贾府一般都是奉行此原则而不敢明加违逆的,而凡违逆者即被视为异类。举例来说,第七十九回写贾赦将迎春许给孙绍祖,对于这门亲事,贾母、贾政都不赞同,贾政更是深恶孙家,因为孙家乃势利之门,“并非诗礼名族之裔”。在《红楼梦》中,贾赦是一个不孝、好色、贪婪而霸道的人,他无疑是破坏诗礼传家传统的主要责任人之一。第四十八回写贾赦强买石呆子的古扇,贾琏不忿,顶撞贾赦道:“为这点子小事,弄得人坑家败业,也不算什么能为!”结果遭到贾赦的毒打,且“打了个动不得”。由石呆子事件可以看出,贾赦身上已经完全丧失了贵族世家的精神传统,遭到贾赦毒打的贾琏在这里反而是世家传统的维护者。《儒林外史》第九回写刘守备家仆冒姓打船家,结果被路过的娄三公子当场揭穿,娄三公子说在冒姓的情况下行凶打人,“岂不要坏了我家的声名”。维护家族声名的娄府公子的心理,跟反对父亲霸道行为的贾琏毫无二致。真正的贵族必然懂得节制欲望的重要性,《红楼梦》中的贾赦则不顾廉耻,任由欲望泛滥。第四十六回写凤姐转述贾母批评贾赦的话,说贾赦“如今上了年纪,作什么左一个小老婆右一个小老婆放在屋里,没的耽误了人家。放着身子不保养,官儿也不好生作去,成日家和小老婆喝酒”。《外史》第三十四回写杜少卿认为娶妾之事最伤天理,因为“天下不过是这些人,一个人占了几个妇女,天下必有几个无妻之客”,因而他想“为朝廷立法”,主张“人生须四十无子,方许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便遣别嫁”,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称此法为“培补元气之一端”。《红楼梦》中贾赦的作为所耗损的不仅是自身的元气,整个贾府的败落他也是难辞其咎的。
贵族世家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是家族中不断有人进入仕途,即如程晋芳《文木先生传》所言:“世望族,科第仕宦多显者。”《儒林外史》第三十三回写李大人荐举杜少卿应征辟,少卿推辞,李大人道:“世家子弟,怎说得不肯做官?我访的不差,是要荐的!”此处齐省堂增订本批云:“辞严而义正,极是难得。”李大人的话之所以显得“辞严而义正”,便因世家子弟必须有人做官乃是社会共识。《红楼梦》中贾政严抓宝玉的教育,薛宝钗、史湘云等人劝其走仕途经济之路,都是出自善意的正常之举。张英(1637—1708)《聪训斋语》卷二中云:“每见仕宦显赫之家,其老者或退或故,则其家索然者,其后无读书之人也;其家郁然者,其后有读书之人也。”《红楼梦》第四十七回中写到柳湘莲“原是世家子弟,读书不成,父母早丧,素性爽侠”,故他这一支便因读书不成而趋于衰落。《外史》第三十一回中,据韦四太爷介绍,天长杜家“兄弟虽有六七十个,只有这两个人(杜慎卿、杜少卿)招接四方宾客;其余的都闭了门在家,守着田园做举业”。只要有子弟“守着田园做举业”,世家的传承便有了基本的保障。而正因世家中不断有人进入仕途,随着世代的延续,有功名者几乎成了世家的固有产出物,从而变得极为稀松平常,不会被人加意重视了。《外史》第三十一回写杜少卿蔑称王知县为“灰堆里的进士”。第四十六回写虞华轩对表兄余大先生说:“举人、进士,我和表兄两家车载斗量,也不是甚么出奇东西。”这样的话是只能出诸世家子弟之口的,因为世家中有人考中举人、进士,很难对其子弟产生强烈的刺激,像范进中举即疯那种情况,是不易发生在贵族世家中的。较之《儒林外史》所写科举世家,《红楼梦》中的贾家尚有其特殊性。第七十五回写贾赦评论贾环诗作时说:“想来咱们这样人家,原不比那起寒酸,定要‘雪窗荧火’,一日蟾宫折桂,方得扬眉吐气。咱们的子弟都原该读些书,不过比别人略明白些,可以做得官时就跑不了一个官的。何必多费了工夫,反弄出书呆子来。”贾赦讲的这番话,除了表现出他对平民阶层的蔑视外,重点强调了贾家作为世代荫袭之家,原不必跟平民子弟一样致力于科举。事实上,贾赦此论对贾氏宗族来说是极不负责任的,因为依靠荫袭得官早就难以为继了,贾家要维系家声于不坠必须教育子弟走科举之路。这个平凡不过的道理,连侍婢袭人都明白,第九回中袭人曾对宝玉说:“读书是极好的事,不然就潦倒一辈子。”第十六回写秦钟临终前对宝玉说:“以前你我见识自为高过世人,我今日才知自误了。以后还该立志功名,以荣耀显达为是。”此处庚辰本夹批云:“此刻无此二语,亦非玉兄之知己。”欧丽娟教授认为秦钟遗言“属于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由衷心声”,当可信从。贾宝玉不愿走家族寄望的仕途经济之路,并猛烈抨击科举制度的物质载体八股文,放在整个明清时期来看此类言论并不稀罕。《儒林外史》第三十六回写武书向南京国子监虞博士介绍学业情况时说“门生那文章,其实不好”“门生觉得自己时文到底不在行”,虞博士回应说自己“也不耐烦做时文”。“不耐烦做时文”的读书人在现实中大有人在,但为个人功名及家族利益起见,绝大部分人还是不得不忍苦就范。作为科举过来人的袁枚(1716—1798),在《答袁蕙纕孝廉书》中曾语重心长地劝说对方:“时文之病天下久矣,欲焚之者,岂独吾子哉”,“足下未成进士,不可弃时文;有亲在,不可不成进士”,“以至难之术,而就至狭之境。士之低首降心,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势也。势非圣贤豪杰之所能免也”,“仆劝吾子勿绝时文,乃正所以深绝之也。”欧丽娟教授谓“宝玉处处所表现的反对科第,正是陷个人与家族于败灭的不义之举”,话虽严厉,理却不错。《外史》第三十二回写娄焕文临去遗言,提及杜少卿的小儿子“尤其不同,将来好好教训他成个正经人物”。娄焕文所谓“正经人物”,一定是指走仕途经济道路的读书人,而不会是像杜少卿那样放弃科举的离经叛道之人。娄焕文的遗言与《红楼梦》中秦钟的遗言一样,都是虑及将来的肺腑之言,而吴敬梓和曹雪芹特意在书中写此一笔,正寄寓了世家子弟回首往昔时痛苦矛盾的心情。《红楼梦》第七十八回写到贾政因年迈而名利之心大灰,想到祖上“虽有深精举业的,也不曾发迹过一个,看来此亦贾门之数”,遂决定以后不再拿举业逼迫宝玉了。此处虽写贾政对宝玉的态度有较大转变,但必须看到贾政是依命数论而决定转变的,并不表明他对传统的仕途经济道路改取否定的态度。
《红楼梦》第十九回写袭人提到宝玉所说的“混话”之一,是把“凡读书上进的人”皆称之为“禄蠹”。第七十三回中又提到宝玉深恶时文八股而斥之为“后人饵名钓禄之阶”。宝玉的话当然是愤激之言,类似的言论在历史上亦不鲜见,但其意义却并不能因此而低估。宝玉的话实际上反映了作者对士大夫阶层的深刻失望,尤其是将士大夫阶层跟平民阶层对比看待时,从中体现出的极为鲜明的人文意义,更是使作品一举跃升至高品味的关键一环。《红楼梦》第四十二回写薛宝钗对林黛玉说:“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糟踏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宝钗观察现实后的愤懑由此可见。《红楼梦》中写了一个“饿不死的野杂种”贾雨村,《儒林外史》中堪与同类的是衙门里充斥“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的南昌知府王惠。与贾雨村和王惠之类官僚相比,《红楼梦》和《外史》中道德品质过硬而深具感染力的人物大都是平民,我们完全可以说,在经历了人生的沧桑巨变后,曹雪芹和吴敬梓的头脑中业已形成了稳定的平民情结。何满子先生曾经指出:“吴敬梓的平民情结,正是促使他创作《儒林外史》这样一部白话小说的动因。”近人刘咸炘《小说裁论》中揭示“儒林外史”命名真义道:
若严致中之谋产,王德、王仁之纳贿,荀玫之忘亲,匡迥之弃妻,王惠之鄙,此皆市井之行,贱恶之事,而读书识字者躬行之。匡迥之父及卜崇礼、祁太公,皆不识字之愚农,鲍文卿则一伶工,而敦厚卓绝,乃士人所不及。匡迥一身,为农则孝,为士则弃妻,则激射之意显然。书中备载杂流而独名《儒林外史》,乃深责儒者,儒者之所以卑劣若此者,功名富贵也。
贵族世家一般都有良好的家风,而家风的形成离不开创业先祖的倡导。吴敬梓的高祖吴沛便经常这样教育子弟:“若辈姿好不一,能读书固善,不然做一积阴德平民,胜做一丧元气进士。”《儒林外史》第八回中娄府两公子引用的一句俗语,其意与吴沛的教言正相仿佛:“与其出一个斫削元气的进士,不如出一个培养阴骘的通儒。”明清时期士大夫阶层在素质上的空前劣化,是一个被朝野普遍认识到的现实问题,而科举考试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则极不光彩。方苞(1668—1749)在《何景桓遗文序》中愤然言道:“余尝谓害教化败人材者无过于科举,而制艺则又甚焉。盖自科举兴,而出入于其间者,非汲汲于利则汲汲于名者也。”郑板桥(1693—1765)屡次谈及士人在农夫面前应该感到羞愧,他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中批评道:“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起手便错走了路头,后来越做越坏,总没有个好结果。其不能发达者,乡里作恶,小头锐面,更不可当。”郑板桥此处所说的“不能发达者”,所指即《外史》中横行乡里的严贡生一流人物。艾衲居士《豆棚闲话》第五则《小乞儿真心孝义》中的一段话,则是对历史进行理性反思后的见道之言:
如今世界不平,人心叵测,那聪明伶俐的人,腹内读的书史倒是机械变诈的本领,做了大官,到了高位,那一片孩提赤子初心全然断灭,说来的话都是天地鬼神猜料不着,做来的事都在伦常圈子之外。倒是那不读书的村鄙之夫,两脚踏着实地,一心靠着苍天,不认得周公、孔子,全在自家衾影梦寐之中,一心不苟,一事不差,倒显得三代之直、秉彝之良在于此辈。仔细使人评论起来,那些踢空弄影豪杰,比为粪蛆还不及也。
《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写高翰林贬斥杜少卿“是他杜家第一个败类”,说他“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却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尊卑贵贱的观念在高翰林这种人的头脑里是根深蒂固的,像他这种人恐怕永远难以理解杜少卿打破阶层界限的行为。在举世滔滔的势利世界中,贵族世家的道义担当尤显重要。《红楼梦》中的贾府虽已处于“末世”,但贵族世家怜贫恤老的优良传统仍有相当突出的表现,最典型的即是刘姥姥二进荣国府时,贾府统治层的贾母、王夫人和凤姐等人对她的真诚济助。刘姥姥得助一段当属《红楼梦》中最具人文情怀的故事之一,本文下节将对此进行专门分析。《外史》中打破官民的身份界限,读之能够让人潸然泪下的故事,是向鼎结交鲍文卿一段。第二十六回写向鼎称颂鲍文卿说:“而今的人,可谓江河日下。这些中进士、做翰林的,和他说到传道穷经,他便说迂而无当;和他说到通今博古,他便说杂而不精;究竟事君交友的所在,全然看不得!不如我这鲍朋友,他虽生意是贱业,倒颇颇多君子之行。”对官场中人的彻骨失望使向鼎更加认识到鲍文卿品质之高贵。周月亮教授曾揭示向鲍之交的精神实质之所在:“他们之间不是太守谦光、戏子得体、贤主嘉宾的问题,而是在茫茫人海中终于找到了可以兑现真诚的对象这样一个深层需要的问题,向鼎对鲍文卿不是一般的感念、还账,而是在享用着一种叫友谊的情感。”向鼎对鲍文卿的感念与回报,完全消泯了士大夫阶层对平民的优越感,向鲍之交成为全书最具感染力的故事之一,原因在此。何满子先生曾敏锐地指出,“吴敬梓所向往,情操上最契合,也即是最能代表他的价值观,堪作精神上的自况人物”,便是向鼎。而相比之下,像杜慎卿那样总是保持世家对平民的优越感,时时精于算计的人,当然就不是什么厚道人了。至于像牛浦郎那样尚未发达便鄙视同阶层平民的人,正是“世上第一等卑鄙人物”“书中第一等下流人物”。《外史》中除了向鼎以外,同具真朴的平民精神的人物还有马二先生。第十五回写马二先生资助流落异乡的匡超人,诠释了怎样的人方有资格被称为“斯文骨肉朋友”:
马二先生道:“不然,你这一到家,也要些须有个本钱奉养父母,才得有功夫读书。我这里竟拿十两银子与你,你回去做些生意,请医生看你尊翁的病。”当下开箱子取出十两一封银子,又寻了一件旧棉袄、一双鞋,都递与他,道:“这银子你拿家去,这鞋和衣服,恐怕路上冷,早晚穿穿。”匡超人接了衣裳、银子,两泪交流……又到自己书架上,细细检了几部文章,塞在他棉袄里卷着,说道:“这都是极好的,你拿去读下。”
张天翼曾用文学化的语言描述他心目中的马二先生:“我一想起马二先生,立刻就看见他站在我面前,他跟我挨得很近。我能够跟他手拉手,还感觉得到他手上的温暖似的。”马二先生能够给予读者以温暖的感觉,正是其平民精神感染人心的自然结果。
曾为世家子弟的吴敬梓和曹雪芹,晚年生活均陷入了极为困顿的境地,这不能不对他们的思想和创作产生莫大的影响。近人解弢曾经指出:“吾国昔无社会小说,故于贫家状况,多未述及,虽《儒林外史》,其中亦不多见,唯述范进家,为覶缕尽致。余则《红楼》之王狗家,《金瓶梅》之常峙节家而已。”解弢例举的《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中的贫家,当然是不够准确、不够全面的,但他将描述“贫家状况”作为“社会小说”的重要内容,却是颇具启发性的见解。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对贫家状况的描写,乃是严肃的社会写实,正如论者所指出的:“太平盛世之下,享受繁荣之果的,不是广大的农民、手工业者,也不是一般的知识分子,而是满汉地主阶级、大商人以及各级官僚。”二书对贫家状况的描写无疑是对社会不公的批判,并引导读者思考造成贫困的制度原因。《外史》第二回写周进的姐夫金有余对他说:“人生世上,难得的是这碗现成饭。”卧评说:“此语能令千古英雄豪杰同声一哭!盖不独吹箫之大夫、垂钓之王孙,为凄凉独绝人也。”《外史》中那些为了一碗现成饭而奔波的人,大都是沉沦于社会底层的秀才群体,正如台湾学者乐蘅军所指出的:“举人进士固然是糟蹋自己人格换来,但身家性命总算保住了,只有这些遍地流落的秀才,才是最彻底的沉沦:既无从以道德自守,又甚至丧失了根本的吃饱肚子的能力。”第二十八回中季苇萧所说“南京这地方是可以饿的死人的”,像回声一样弥散在《外史》全书中。其次,二书对贫家状况的描写,蕴含了对世家子弟奢靡生活的反思。则仙曾针对上述金有余的话发挥道:“恃目前有现成饭,渐至德不进,业不修,任意花消,欲吃饭而难得现成者,正复不少。愿与末世守成子弟交勉之。”《外史》第三十二回写杜少卿“不会当家,不会相与朋友”,移居南京后一家人的生活逐渐陷入困顿。第四十四回写余大先生对杜少卿说:“你这些上好的基业,可惜弃了。你一个做大老官的人,而今卖文为活,怎么弄的惯?”杜少卿答道:“我愚弟也无甚么嗜好,夫妻们带着几个儿子,布衣蔬食,心里淡然。那从前的事,也追悔不来了。”此处有黄小田评:“少卿进于道矣。”“进于道”固然表明杜少卿能够以贫贱自守,但其中未始不蕴含着对过往生活的反思。如果说《外史》中的杜少卿尚能安于贫贱的话,《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则是“贫穷难耐凄凉”的典型。第十九回写宝玉去袭人家探望她,而“袭人见总无可吃之物”,此处己卯本批云:“补明宝玉自幼何等娇贵。以此一句,留与下部后数十回‘寒冬噎酸齑,雪夜围破毡’等处对看,可为后生过分之戒。”第七十七回写晴雯逝前宝玉往其寄身的哥嫂家探望,见晴雯“睡在芦席土炕上”;家中茶壶是个“黑沙吊子”,茶碗有“油膻之气”,茶水是“绛红的”,且“一味苦涩,略有茶意而已”,晴雯喝起来却“如得了甘露一般,一气都灌下去了”。此情此景不由让宝玉想起古人说的“饱饫烹宰,饥餍糟糠”和“饭饱弄粥”。在目睹晴雯身处如此贫苦的环境之前,古人说的这两句话在宝玉脑中不过是抽象的概念,是难以引起切实的痛感的。我们可以想象,在八十回后的佚稿中,连戥子都不识的宝玉沦落于“寒冬噎酸齑,雪夜围破毡”的惨境中时,他又当如何自处?由此可见,“寄言纨袴与膏粱”当是《红楼梦》创作意图的重要一端。
二、归农:物质基础与道德精神的重建
关于《红楼梦》的思想基础问题,几十年前曾有过一场规模较大的争论。其中刘大杰先生曾提出“农民说”:曹雪芹“在他长期的穷困的晚期,接近农民的生活,受了农民生活思想的教育”,故“《红楼梦》的思想基础,是建筑在农民力量的基础上,是建筑在农民的生活思想的基础上”。在新的时代和学术环境下,“农民说”实有重新审视之必要。限于曹雪芹本身资料的匮乏,我们在考察其思想渊源时,更多需借助于间接的材料。据今存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曹寅、李煦及曹頫等人向皇上汇报的奏折中,多有晴雨、灾害、米价及谷种等项内容。曹雪芹关心农事自不应忽略先辈们的影响。较之《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之受到农民的生活思想的影响,更能得到存世资料的支持。据吴敬梓《移家赋》自注,其“曾祖兄弟五人,四成进士,一为农,终布衣”。康熙《全椒县志》卷十记载,吴敬梓曾祖兄弟五人中,唯一以务农终身的是行二的吴国器(1604—1664),他是为了保证兄弟业儒,遂遵父命而任家政的。《移家赋》自注中谓吴国器“无疾而终,人传仙去”,可见他对这位务农终身的先祖的崇仰。顾云《盋山志》记载,吴敬梓晚年“日惟闭门种菜,偕佣保杂作,人不知故向者贵公子也”,此时的吴敬梓的处境跟普通农民已无不同。乾隆三年吴敬梓在《左伯桃墓》诗中说:“亦有却聘人,灌园葆贞素。”这是立意效仿战国时於陵仲子从事田园劳动,做一个坚定的“却聘人”。
传统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亦即物质基础的最大提供者。《红楼梦》和《儒林外史》对这一基本现实的描写都是彰彰在目的。《红楼梦》中贾府经济是靠庄田地租维持的,对此第五十三回写宁府庄头乌进孝进租有明确交代。庄田收成会直接影响到贾府中人的生活水平。第七十五回写贾母吃的红稻米粥没有剩余,王夫人解释说“这一二年旱涝不定,田上的米都不能按数交”。贾府还拥有名为“园子地”的田地,第四十五回写凤姐提到李纨有“园子地”的租子收入。田地因其重要性有时几乎等同于“基业”。《红楼梦》第一回交代贾雨村出身于诗书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乡无益,因进京求取功名,再整基业”。此处所谓“根基”“基业”,便应包括田地等产业。《外史》第四十四回写余大先生对杜少卿说:“你这些上好的基业,可惜弃了。”此处的“基业”即指杜少卿以往拥有的家乡的田地。在家乡拥有一定数量的田地,往往是士大夫阶层首先要考虑的,这既是增殖产业的需要,也是致仕或进取受挫后作为退步的经济依靠。吴敬梓的高祖吴沛命其仲子在家务农,让其余四子读书进取,便是为家族发展而做出的最稳妥的安排。《外史》第九回写刘守备家仆冒充娄府装租米的船,说明娄府是有田租收入的。娄三公子、娄四公子失意于京城后退返乡里,其经济便是靠田租维持的。《红楼梦》第六回交代王狗儿祖上跟王夫人之父连宗后,到他父亲王成一代时,“因家业萧条,仍搬出城外原乡中住去了”,到狗儿便只能“仍以务农为业”了,可见狗儿的祖父辈在家乡置有田产,否则到狗儿一代便难以维持生存了。第四十二回写王夫人赠给刘姥姥一百两银子,让她拿去“或者作个小本买卖,或者置几亩地,以后再别求亲靠友的”。这是全书中表现王夫人怜贫恤老的重要一笔,而让刘姥姥置买田地显然是救穷的根本举措。《外史》第八回写蘧景玉说其父蘧祐经常讲“宦海风波,实难久恋”,因而早就有退归田里的打算,而蘧祐“做秀才的时候,原有几亩薄产”,可见为官清廉的蘧祐致仕后尚能维持一般水准以上的生活,全仗早年在家乡拥有的田产。《红楼梦》第一回写甄士隐先前能够维持观花修竹、酌酒吟诗的恬淡生活,是因为有田庄收入的支持。当他家遭遇火灾,变卖田庄投奔岳父家,耕种岳父为其置买的薄田时,便因“不惯生理稼穑等事,勉强支持了一二年,越觉穷了下去”。《外史》第四十六回写虞博士对杜少卿说,他来南京做国子监博士六七年来所得俸金,“只挣了三十担米的一块田”,他打算再用两三年为官所得“添得二十担米”,这是出身农村的赤贫之士虞博士着眼将来的理性举措。相比普通人家,世家子弟因不善经营卖掉田产,在当时人看来是标准的败家行为。《外史》第三十二回写杜少卿命管家卖掉“圩里那一宗田”,得银一千三百两。高翰林眼里的杜少卿是“杜家第一个败类”,跟其卖田行为当然是分不开的。
田地在传统中国往往是跟农业和乡村三位而一体的,而乡村在传统中是具有重要的人文陶冶作用的。跟城市市民相比,农民往往更淳朴。《红楼梦》第六回写刘姥姥跟女婿王狗儿说:“咱们村庄人,那一个不是老老诚诚的,守多大碗儿吃多大的饭。”农民的劳力直接诉诸自然,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其态度只能是“老老诚诚的”。依靠诚实劳动谋生,也是其他行业诚实劳动者遵从的基本原则。《儒林外史》第二十五回写鲍文卿拒绝赚取昧心钱,说“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得肉”。这与士大夫阶层以巧取豪夺的手段获取利益是正相反对的。古代君王作为农业国家的统治者,深知农事劳动在人的心性养成上具有无可取代的作用,故在宣示臣民时一般都会加以强调。张英《恒产琐言》对此便有深切的体会:“古人有言:‘惟土物爱,厥心臧。’故子弟不可不令其目击田家之苦。”“惟土物爱,厥心臧”出自《尚书·周书·酒诰》,其前一句为“惟曰我民迪小子”,这几句话连起来的意思是:“姬姓子孙们要教导臣民懂得爱惜地里生长的庄稼,使他们心地善良。”爱惜地里生长的庄稼,就是尊重耕植庄稼的农人。《红楼梦》第六十一回写司棋大闹小厨房,命小丫头们动手,“凡箱柜所有的菜蔬,只管丢出来喂狗”,对于如此任性破坏的行为,未始不包含作者批评的成分。《红楼梦》中备尝农民生活的艰辛,心性亦至为纯良的人是刘姥姥。《外史》中出身乡村的一批士子,如王冕、荀玫、范进、匡超人、诸葛天申、虞博士及王玉辉等,除了荀玫、匡超人最终走向堕落外,其他人基本都能保持淳朴本色。即以第二十八回写到的乡里人诸葛天申为例,吴敬梓特意写他不认识香肠和海蜇,吴组缃先生曾指出他“不肯在家好好过日子”,却为了选刻八股文章以附骥尾,把二三百两银子给穷极无聊的萧金铉和季恬逸等吃个光,“我们难道不觉得可笑,又为之惨然么?”较之长期混迹于城市的萧金铉和季恬逸,就道德水准而言,从乡村出来不久的诸葛天申显然更为淳朴。周月亮教授说吴敬梓“偏爱乡村化的道德哲学”,诚然不错。
官府为了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历代都有所谓“劝农”的官方举措。《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写高翰林贬称杜少卿的父亲是呆子,因为他在做太守期间“逐日讲那些‘敦孝弟、劝农桑’的呆话”,而这些“呆话”“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他竟拿着当了真”,结果“惹的上司不喜欢,把个官弄掉了”。杜少卿的父亲是传统的正派称职的地方官,高翰林的话则暴露了传统信仰日益崩溃的现实。当地方官唯以仕途升迁为务而弃民生福祉于不顾时,拿《红楼梦》第二回中冷子兴的话来说,整个社会便“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外史》第四十回写萧云仙在青枫城开垦田地、兴修水利、栽植花木、开办学堂,几乎将其建设为王道乐土。但随着萧云仙受屈调官,青枫城的发展是否能够持续,尚在未知之数。《外史》中除了杜少卿的父亲和萧云仙这样的地方官以外,第四十八回还写到徽州府秀才王玉辉关注乡村教化之事。回中写王玉辉平生的志向是编纂三部书,其中一部是乡约书,这是乡村儒生致力于教化工作的表现。不过王玉辉的乡约书最终未见出版,他的一片苦心也只能付诸东流了。较之《外史》,《红楼梦》中极少提及乡村的政治社会状况,不过第一回写甄士隐家遭火后到田庄上安身,却有几句话述及乡村天灾祸乱并发的情形:“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乡村社会的动荡经过层层传导,势必会影响到世家大族的生活。
《儒林外史》中占据精神制高点的人物是虞博士,《红楼梦》的第一主人公是贾宝玉。让我们感到意味深长的是,两位核心人物在各自作者的精心描写下,在跟乡村有关这一点上产生了深刻的精神联系。《外史》第三十六回写虞博士出生于苏州府常熟县一个叫“麟绂镇”的村庄。黄小田揭示“麟绂”此名蕴含的深意说:“‘麟绂’言此人,便可算得《外史》中之圣人矣。”李汉秋先生征引《孔子集语》《王子年拾遗记》等文献后进一步指出:“吴敬梓煞费苦心地以孔子降生传说中的‘麟绂’名虞博士的降生地,确是为烘托虞博士是‘《外史》中之圣人’。”虞博士这样一个圣贤之徒,出生于象征祥瑞的麟绂镇,乡村生活对他的陶冶之功自是举足轻重,这其中既包括乡村自然风光的审美养育,也有乡村仁爱互助人际关系的影响。第三十六回写虞博士去远村看葬坟毕,“叫了一只小船回来。那时正是三月半天气,两边岸上有些桃花、柳树,又吹着微微的顺风,虞博士心里舒畅。又走到一个僻静的所在,一船鱼鹰在河里捉鱼。虞博士伏着船窗子看”,明丽的自然风光对虞博士性情养成的意义不言而喻。祁太公对虞博士从小到大的热情帮助,更是使他确立了平民的质朴的人生观。虞博士中举后到山东巡抚康大人处做幕僚,不愿违心地求人荐举以获取清名,中进士后又实报年龄而失去进入翰林院的机会,这些人所难能的行为正是其平民人生观的自然表现。这种表现本质上跟《红楼梦》中刘姥姥所说村庄人老老诚诚做人是完全一致的。第三十六回中写到虞博士救助父死而无力殡葬的庄农,也是源于他感同身受的对农民生活的深刻理解与同情。而对虞博士救人义举的描写同时表明,吴敬梓跟那些始终保持理性的作家一样,并未把乡村描绘成理想化的桃花源。在一个依然充满苦难和非正常死亡的社会中如何自处、如何待人,才是吴敬梓代表那些有良知的儒者所思考的问题。
跟虞博士相比,贾宝玉的出生所具有的神异色彩更为浓厚。作为抱持受享观念来到尘世的神瑛侍者的现实化身,贾宝玉有机会见识到了乡村中从未接触的事物,从而引起了一系列的心灵震颤。不必复述刘姥姥二进荣国府时他对乡村生活无知又可笑的言谈,早在第十五回中便有宝玉接触乡村事物的一段新奇的描写。那是写秦可卿出殡前往铁槛寺途中,宝玉一行人在一庄农人家打尖,“凡庄农动用之物,皆不曾见过。宝玉一见了锹、镢、锄、犁等物,皆以为奇,不知何项所使,其名为何。小厮在旁一一的告诉了名色,说明原委”。此处甲戌本夹批云:“凡膏粱子弟齐来着眼。”庚辰本眉批云:“写玉兄正文总于此等处,作者良苦。”可见此处描写乃“玉兄正文”,不可轻忽。在了解了各种农具的名称及其功能后,宝玉不禁想起“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跟曹雪芹同时代的郑板桥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一开头便热情洋溢地说:“十月二十六日得家书,知新置田获秋稼五百斛,甚喜。而今而后,堪为农夫以没世矣。要须制碓、制磨、制筛箩簸箕、制大小扫帚、制升斗斛。家中妇女,率诸婢妾,皆令习舂揄蹂簸之事,便是一种靠田园长子孙气象。”乡村生活中生气勃勃的劳动场景,是贾宝玉这样脱离实生活的世家子弟所难以想象的。像他这样的世家子弟,应该重温《颜氏家训·涉务》中那些经验之谈:“古人欲知稼穑之艰难,斯盖贵谷务本之道也。夫食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种之,薅锄之,刈获之,载积之,打拂之,簸扬之,凡几涉手,而入仓廪,安可轻农事而贵末业哉?”而晋室南渡以来,江南朝士“未尝目观起一墢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颜之推由此指出不知稼穑所致严重后果:“故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皆优闲之过也。”“富贵闲人”贾宝玉在庄农人家的经历,又一次印证了“天天圈在家里”的生活正是造成人的封闭性和狭隘性的主因。宝玉在庄农人家还偶遇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名为“二丫头”的,她自信地为宝玉示范了如何纺线。此处姚燮眉批云:“宝玉之不识纺车与刘姥姥之不识自鸣钟,其揆一也。”护花主人评云:“写乡村女子纺纱等事,直伏巧姐终身。”可见不必等到第四十一回方明确预示巧姐和板儿的婚姻,曹雪芹在这里就已经伏下了巧姐的终身。第五回“金陵十二钗正册”预示巧姐结局的图画便是:“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人在那里纺绩。”在二丫头为宝玉示范纺线的过程中,出于狎亵心理的秦钟暗拉宝玉道:“此卿大有意趣。”结果被宝玉斥为胡说而制止。洪秋蕃评云:“乡村妇女,心地浑噩,无风月情。”宝玉制止秦钟既出于一贯的对少女的体贴心理,也体现了他对一个劳动者的基本尊重。短暂邂逅中二丫头留给宝玉的最后一个画面是“怀里抱着他小兄弟,同着几个小女孩子说笑而来”。依曹雪芹善用草蛇灰线法的写作惯例,此处描写在八十回后的佚稿中应该会有照应。
归隐是古代政治体制下必然会产生的一种观念,而归隐最彻底的一种实践形式便是归农。《红楼梦》第十七回写贾政一行来到满是田园风光的稻香村,先是肯定“此处有些道理”,然后指出此处“固然系人力穿凿”,但“此时一见,未免勾引起我归农之意”。第一百二十回续书写贾政赞成巧姐嫁给刘姥姥村中周姓财主之子:“莫说村居不好,只要人家清白,孩子肯念书,能够上进。”跟贾政赞赏稻香村的态度不同,贾宝玉批评稻香村的设置“峭然孤出,似非大观”,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宝玉此一评论?对此欧丽娟教授曾提出一种颇具启发性的解释:“宝玉的批评主要在于这所田庄失去了环境的协调性,这仅是就单一建物本身的局部现象而言;若从整个园区的全局来看,则毋宁说,稻香村之存在于大观园,正是‘天上人间诸景备’之全景组成中的必要一环。”贾政参观稻香村而兴起归农之意,跟他重视天伦之乐存在密切关系。第七十一回写他外任几年备尝骨肉分离之苦,“今得晏然复聚于庭室,自觉喜幸不尽”,故“一应大小事务一概发付于度外,只是看书,闷了便与清客们下棋吃酒,或日间在里面母子夫妻共叙天伦庭闱之乐”。第十八回写元春归省时曾垂泪对父亲贾政说:“田舍之家,虽齑盐布帛,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在这里,元春把“富贵已极”跟“天伦之乐”尖锐地对立了起来,在她看来,“骨肉各方”“终无意趣”的富贵生活,是比不上贫穷却能得享天伦之乐的田舍之家的。《儒林外史》第十七回写匡超人去参加府考,父亲匡太公无人照料,“尿屎仍旧在床上”,表现了功名追求与亲情伦理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外史》中的标杆人物王冕则主动逃避做官,在乡间度过了心魂相守的一生。虞育德在做南京国子监博士的六七年间,实际处于一种“中隐”的状态,他在离开南京前诚恳地跟杜少卿说,自己的俸金主要用来置买田地,“我要做这官怎的”,可见其为晚年所做规划即是归农。“登高必跌重”,官场的险恶必然催生归农之思,正如论者探讨贾政形象所指出的:“领教过官场险恶的人,更能体会到,农村生活虽使人远离富贵功名,却因其简单、自然,在这个世界尤显可贵。”《外史》第八回写娄府两公子失意于京城后回到乡村,才更能感受乡村景致之幽雅,其理正同。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东皋草堂记》中曾说:“仕宦,古今之畏途也”,“纡青拖紫,新人满眼,遥念亲故,动隔千里,孰若墦间之祭,挦鸡渍酒,倾倒于荒烟丛筱之中,谑浪笑傲,言无忌讳之为放适也?”几代处于特殊政治架构中的曹家,产生此类归隐之思是十分自然的。
贵族世家与农民作为社会阶层分布中的两极,除了存在一般的剥削与压迫关系外,如果有机会产生正面的交往,他们会如何相处呢?这一话题在古代小说中似罕有涉及者,《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则分别留下了经典描写。《外史》第十一回写邹吉甫的儿子小二“手里拿着个布口袋,装了许多炒米、豆腐干,进来放下”,娄府两公子说本不必带礼来,但既然带来了,“我们又不好不收你的”。邹吉甫答道:“二位少老爷说这笑话,可不把我羞死了!乡下物件,带来与老爷赏人。”于是两公子吩咐将礼收进去。此处有黄小田评云:“可知炒米、豆腐干,公子下人并不吃,但不能不如是说耳,宾主真朴可爱。”说“宾主真朴可爱”自然是对的,但说邹吉甫带来的炒米、豆腐干“公子下人并不吃”,则是自作聪明的猜测。黄评最不可取的是把两公子与邹吉甫的对话看作例行公事,从而大大淡化了主仆之间真情饱满的交流。邹吉甫之所以跟娄府公子存在正面交往,最大机缘在于他是娄家长期的看坟人。第九回写两公子问邹吉甫的儿子邹三:“我家坟山没有人来作践么?”邹三道:“这是那个敢!府县老爷们,大凡往那里过,都要进来磕头,一茎草也没人动。”邹三所说坟山中的“一茎草”,指的是坟山上的树木即所谓“荫木”。研究者告诉我们:“坟山、荫木与祖先三者在古人心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坟山是祖先的栖息之所,荫木是坟山的护羽,对于坟山和荫木的保护即被认为是对祖先的保护。”邹三说坟山上“一茎草也没人动”,反映出邹吉甫多年来尽职尽责,是一位忠实可靠的看坟人。邹吉甫乃是以农民与看坟人两重身份与娄府公子产生交往,而这两重身份又是缺一不可的:如果邹吉甫只是一位普通农民而不是娄家看坟人,他跟娄府公子产生交往的机会必定微乎其微;而一位长期的看坟人,则非当地农民莫属。尽管娄府公子对邹吉甫的尊重与感激,主要在于邹吉甫是他家长期的看坟人,但邹吉甫作为农民的身份一样得到了两公子的尊重,这是真正的世家子弟方具有的优秀品质的表现。相比娄家,《外史》所写另一世家杜家中某些子弟的品质就大大不如了。第三十二回写为杜家看守祠堂的黄大,“把坟山的死树搬了几棵回来添补梁柱”,结果被几位本家打了一个臭死。虽然黄大所搬坟山的死树属于“荫木”,故其犯错在先,但因几棵死树就把人往死里打,却明显是苛暴之举。杜家真正具有世家仁爱精神的是杜少卿一支。第三十一回写杜少卿介绍说,娄焕文负责杜家田地房产的帐目,“每收租时候,亲自到乡里佃户家,佃户备两样菜与老伯吃,老人家退去一样,才吃一样”。娄焕文跟佃户之间的关系,实际反映了杜家主人跟佃户的关系。而娄焕文那些济困扶危的义举,同样得到了老主人即杜少卿之父的赞许:“收来的租稻利息,遇着舍下困穷的亲戚朋友,娄老伯便极力相助。先君知道也不问”,“有人欠先君银钱的,娄老伯见他还不起,娄老伯把借券尽行烧去了。”韦四太爷赞叹娄焕文是“古之君子”,而作者吴敬梓让娄焕文姓娄,跟书中另一世家娄家同姓,也许不是出于无心的安排。第三十三回写杜少卿赴娄焕文之丧,“一连住了四五日,哭了又哭”,一镇上的人皆叹息说:“天长杜府厚道。”我们必须看到,杜府这份厚道不仅是针对娄焕文的,同时也是惠及娄焕文管理的佃户的。郑板桥《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中的一段话,有助于我们了解这种平等色彩颇浓的新型主佃关系:“愚兄平生最重农夫,新招佃地人,必须待之以礼。彼称我为主人,我称彼为客户,主客原是对待之义,我何贵而彼何贱乎?要体貌他,要怜悯他。有所借贷,要周全他。不能偿还,要宽让他。”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论述“乡土本色”问题时指出:“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红楼梦》中写了一位土气十足的村妪刘姥姥,将贵族世家与农民之间关系的描写一举推上了艺术的颠峰。前八十回写了刘姥姥两进荣国府,明确预伏了巧姐的终身,三进荣国府的书稿虽已佚失,但刘姥姥在小说结构和主题上的重大作用,已然是彰明较著的事实而无须质疑的了。对此王希廉《红楼梦总评》的评论最是精到:“盖全书既假托村言,必须有村妪贯串其中,故发端结局皆用此人,所以名刘姥姥者,若云家运衰落,平日之爱子娇妻,美婢歌童,以及亲朋族党,幕宾门客,豪奴健仆,无不云散风流,惟剩者老妪收拾残棋败局,沧海桑田,言之酸鼻,闻者寒心。”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写得相对简略,其性质属于典型的打秋风,不过其中却蕴含了作者本人的心酸经历,正如论者所指出的:“曹雪芹本身就有过迫不得已向人借贷的经历,故特借刘姥姥以抒心酸血泪。”一进荣国府中王夫人、凤姐对刘姥姥的关怀已经有所表现,不过较之二进荣国府所展开的全方位的艺术描写,前者的表现力显然远逊于后者。二进荣国府的刘姥姥不是再来打秋风,而是具有回报性质的串亲之行。第三十九回写刘姥姥从家里带来的枣子、倭瓜和野菜,是“头一起摘下来的”即“留的尖儿”。刘姥姥还特意强调这些瓜菜“并没敢卖”,这是表现其情意的精心之笔。回中贾母肯定刘姥姥的瓜菜好,说“外头买的,不像你们田地里的好吃”,便是对刘姥姥情意的充分肯定和赞美。刘姥姥带来的瓜菜是“留的尖儿”,此举能够让我们联想起一个历史名词“荐新”。“荐新”这一古老的礼俗从来都是被纳入官方化、制度化的体系,如昭梿《啸亭续录》卷一《荐新》所言“今奉先殿每月荐新,仍沿明制”,故个体化的情意成分是不易从中体现出来的,相比之下,刘姥姥的仿“荐新”之举则将其对贾府的感恩之情表露无遗。以贾母、王夫人及凤姐为代表的贾府上层对刘姥姥的大力济助,则充分展现了贵族世家对穷苦农民的仁厚情怀。第四十二回写平儿向刘姥姥交代送她的回礼时,为了让她安心收下丰厚的回礼,平儿说:“你放心收了罢,我还和你要东西呢。到年下,你只把你们晒的那个灰条菜干子和豇豆、扁豆、茄子、葫芦条儿各样干菜带些来,我们这里上上下下都爱吃。这个就算了,别的一概不要,别罔费了心。”平儿这番话实际代表了贾母等人对乡下人刘姥姥的充分体贴,是具有浓厚的人道主义情感的经典描写,其文化内涵诚如邓云乡先生深入腠理的分析所言:“本着‘乡人献曝’的淳厚感情,把自己晒的灰条菜、扁豆干儿、茄子干子、葫芦条儿,装上两口袋,到城里送给富贵亲戚,像刘老老一样。而城里亲戚家的人,也待她如自己人,实实惠惠接待了她,又至至诚诚地接受了她的馈赠,并赞赏这样的田家风味。这种感情的交流,是纯东方型的、是中国式的,是淳风厚俗的表现。”这种纯东方型的、中国式的淳风厚俗,同样表现于《儒林外史》里邹吉甫与娄府公子的交往中。《红楼梦》中平儿交代回礼时尤能体现贾府尊重刘姥姥的一个细节,是平儿特意点出有一口袋“园子里果子和各样干果子”。此处所谓“园子里”即指大观园,第五十六回探春理家时提到园子里的果子,第六十七回写老祝妈照料园中的葡萄。给刘姥姥的回礼中之所以包括“园子里果子”,这首先是落实贾母的吩咐,第三十九回写贾母曾对刘姥姥说:“我们也有个园子,园子里头也有果子,你明日也尝尝,带些家去,你也算看亲戚一趟。”贾母的吩咐除了是奉行礼尚往来的常礼外,尚有更深一层的心意表达。我们注意到,平儿说回礼中装“园子里果子和各样干果子”的口袋,即是昨日刘姥姥用来装瓜菜送贾府的那条,可见回礼中“园子里果子和各样干果子”,跟刘姥姥所送瓜菜具有对等的性质。贾母为何特意让刘姥姥带回园子里的果子呢?乃是因为这些果子是贾府自行管理的园子里产出的,跟刘姥姥的瓜菜一样被赋予了自主劳动的意义。综观刘姥姥二进荣国府所获回礼,有衣料、成衣、内造点心、御田粳米、成药、荷包、成窑钟子及银两等各色物事,其礼之重、情之深,自是不待言的,但若论对乡下人的真心尊重,则回礼中那袋果子却是最值得珍视的。而曹雪芹似不经意中写出的这一细节,充分表明了曾为世家子弟的他,在翻过筋斗来后其头脑中的平民情结,业已达到了怎样深刻的程度,从而产生透入心灵的感人力量的。
在刘姥姥二进荣国府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小说对刘姥姥秽物意象的描写,比如第四十一回写刘姥姥如厕时腹泻,醉酒后误入宝玉的卧室,把宝玉精洁无比的卧室弄得满是“酒屁臭气”。关于刘姥姥玷污宝玉卧室的描写,研究者已经提出两种可以融通的观点。张俊、沈治钧先生认为此一描写“或有调侃富家之意。所谓一意虚荣,幽昧未知也”,并且指出此描写“亦以照应妙玉洁癖之事,两两相形”。张、沈二先生的观点系借鉴了本回的回前总批:“此回栊翠品茶,怡红遭劫。盖妙玉虽以清净无为自守,而怪洁之癖未免有过,老妪只污得一杯,见而勿用,岂似玉兄日享洪福,竟至无以复加而不自知。故老妪眠其床,卧其席,酒屁熏其屋。却被袭人遮过,则仍用其床其席其屋。亦作者特为转眼不知身后事写来作戒,纨绔公子可不慎哉。”“调侃富家”、警戒纨绔的用意是确定无疑的,曹雪芹在书中很多场合已经表达过类似寓意。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欧丽娟教授提出的一种发人深省的观点。欧教授曾就秽物意象描写阐发其深刻的人文象征意义,认为它“呈现出一种‘溷秽恶臭的视境’(scatological-fetid vision)”,“在大观园里上演了一出去神圣化的‘脱冕仪式’,冲击了纯净圣洁等等大观园被极力彰显的价值,赤裸裸地展现出生命存在的另一面”,由此展现出刘姥姥身上充沛的生命活力,而“强韧的生命力可以延续生机,克服现实险阻,让人在‘生存’的层面上充满力量”,由此成就刘姥姥为一真正健全的、快乐的人。
如何做一个健全的人,乃是曹雪芹和吴敬梓都曾全力思考的人生根本问题。而世家子弟展现出的日见孱弱的生命力,早就在曹雪芹和吴敬梓的关注视野之内了。我们看到,《红楼梦》中的贾家乃“武荫之属”,精于骑射本是子弟们的分内之事,可是除了书中第二十六回写幼小的贾兰用箭射鹿,乃是立意演习骑射外,族中包括宝玉在内的成年子弟很少有将武事放在心上的。《儒林外史》中的杜慎卿整个一幅病弱的样子,韦四太爷说他身上带着些“姑娘气”,则正是生命力孱弱的典型症候。《红楼梦》中村妪刘姥姥身上那种丰沛的生命活力,正好可以用来对治世家子弟的衰颓。田晓菲教授在谈论《牡丹亭·劝农》出的论文中,曾指出杜宝劝农的田野跟杜丽娘的园林,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系统,而后者正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并由此引申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晚明‘情’的文化下面,隐藏着一个‘昼有公差,夜有盗惊’,充满了泥土、汗水与粪臭的现实世界。如果对‘情’的描写没有这样一个世界作为思想背景,那么,就未免简单和单薄。”田教授的观点对于理解《红楼梦》中秽物意象描写的意义,跟欧丽娟教授上述观点乃是处于同一层次上。无独有偶,《儒林外史》第二十九回写南京两个挑粪桶的人,欲到永宁泉吃水,到雨花台看落照,则不仅反映了南京的美丽离不开底层人的贡献,而且透露出吴敬梓意欲沟通形而下与形而上的主观努力。欧教授在充分肯定刘姥姥源自乡野的强韧生命力的同时,指出其“虽然具有大地的力量,却无缘于风雅精致的文化境界”,“不能提升生命品质,在‘生活’的层面上发展精神性、艺术性”,并引第五十六回薛宝钗所说的一句话加以说明:“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欧教授此一观点实难让人苟同,因为她将雅文化与俗文化看得过于对立了。其实刘姥姥具有的“大地的力量”,本身便能极大地提升贵族日益衰颓的生命品质,而贵族如果丧失了健康有力的生命品质,他们在生活层面上发展的精神性和艺术性,亦势必会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至于欧教授所引薛宝钗“拿学问提着”那句话的本意,主要指赋予世俗生活以形而上的意义,而跟风雅精致的文化境界之生成问题无涉。
刘姥姥二进荣国府中作者经常写她关注吃食的市场价值,比如第三十九回写刘姥姥说大个螃蟹值五分一斤,一席螃蟹宴需花费二十多两银子,“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了”;第四十回写到一个鸽子蛋值一两银子。这些描写孤立看是在写刘姥姥市俗的一面,可是将其置于贾府这样一个豪门中审视时,却使其获得了突出的针砭现实的意义。我们知道,第五十六回写探春改革的最初设想,系源于她对赖大家花园以承包方式获利的刺激:“谁知那么个园子,除他们带的花、吃的笋菜鱼虾之外,一年还有人包了去,年终足有二百两银子剩。从那日我才知道,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当司空见惯的生活用品与市场价值挂钩时,方使探春认识到日常生活用品之珍贵。而像此前的探春那样不懂日常生活用品的价值的人,在过着寄生生活的豪门子弟中是大有人在的。相比之下,反而是那些出身卑微的人更懂得生活的艰辛和奋斗的意义,即以启发探春进行改革的赖大家来说,他们便懂得经营花园增殖财富,赖大之子赖尚荣更在几代积累的家业支持下进入仕途,从而开启了通向上层社会的窗口。而听过探春的一番感慨之谈后,宝钗笑言探春“乃真真膏粱纨绮之谈”,并且指出探春看轻了朱子的《不自弃文》。《不自弃文》见于《朱子文集大全类编》卷二十一《庭训》,大意是天下之物即便是顽石、蝮蛇、粪便、草灰等,皆因其有一节之可取而不为世所弃。刘世南先生曾以杭世骏(1696—1772)《王佩箴刊〈不自弃文〉跋》为例,论及乾隆年间士大夫对《不自弃文》的态度,指出“当时世家大族无不习诵此文”,并推测《红楼梦》中贾政平时一定反复给宝玉讲解过《不自弃文》。红楼众钗中宝钗是深知生活艰辛且拥有出色的持家能力的人,她之看不惯宝玉悠游度日而称其为“富贵闲人”,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红楼梦》第十三回写秦可卿托梦凤姐,建议“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家塾亦设于此”,因为“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而“若目今以为荣华不绝,不思后日,终非长策”。靖藏本回前总批高度评价秦可卿的建议,谓其“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岂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者”。秦可卿建议中所说“子孙回家读书务农”,跟《儒林外史》写杜家六七十个兄弟几乎全部“守着田园做举业”,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因为二者同样是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走读书进取的道路。二者唯一的区别在于,秦可卿建议在祖茔附近所置田庄房舍地亩,乃是属于所谓的“祭田”,其收益属于特定用途的“恒产”,故可在制度上保障家族立于不败之地。何其芳曾经指出秦可卿的建议跟她的故事没有关联,故“这并不是在写她的性格,而是借这个人物写出作者的一种思想”。结合作家王蒙曾揭示出的一种具有规律性的创作现象,即“通过自己的人物说出自己想说的话,是小说家包括伟大而且客观如曹氏者很难抵挡的诱惑”,我们认为何其芳的上述见解是不无道理的。今天的论者即已直言“追忆往昔锦衣玉食,设立族田应是雪芹为家族固持所构想的方案”。有的学者曾根据康熙四十年曹寅《东皋草堂记》“予家受田亦在宝坻之西”“仆仆道途,沟塍多不治”等记述,推测曹家祖坟亦在其地,“却没有在这里经营祭祀产业,给子孙留个退步”,从而导致曹家被抄后子弟流散的凄惨结局。
结语
《红楼梦》染有浓厚的虚无色彩乃是一个有目共睹的文学事实,《儒林外史》中伤感虚无的情绪亦是愈来愈显的。第五十五回写盖宽跟邻居老爹登上雨花台绝顶,“望着隔江的山色,岚翠鲜明,那江中来往的船只,帆樯历历可数。那一轮红日,沉沉的傍着山头下去了”。天目山樵评曰:“才见东升又看西没,自古以来几千万年日日如此,无人理会,却被淡淡一语提出。圣贤豪杰,俱当痛哭。”同回中写于老者邀荆元来园中弹琴,“荆元慢慢的和了弦,弹起来,铿铿锵锵,声振林木,那些鸟雀闻之,都栖息枝间窃听。弹了一会,忽作变徵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天目山樵评曰:“此作者自评其书,所谓‘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儒林外史》其实就是吴敬梓为时代弹出的一曲“变徵之音”,《红楼梦》又何尝不然呢?而在吴敬梓和曹雪芹所处的所谓康乾盛世里,有良知的人又怎么可能避免与虚无觌面呢?这是我们思考《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精神联系时首先必须承认的一个基本事实。然而,超越上述层面的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不管是吴敬梓还是曹雪芹,他们都没有走向彻底的虚无而陷入沉沦。“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而“创作总根于爱”。吴敬梓和曹雪芹一边无情地批判着其所憎,一边执着地雕刻出其所爱,当他们从社会各阶层中努力发掘积极力量的时候,他们便历史性地看到了两方面质素的合流:贵族世家的仁厚情怀与平民阶层的质朴强韧。当我们想到现实中晚年的吴敬梓在闭门种菜,《红楼梦》小说佚稿中巧姐在刘姥姥的荒村中纺绩,难道我们还不能从中得到某种意味深长的启示吗?陶渊明《拟古九首》其五云:“愿留就君住,从今至岁寒。”毫无疑问,写出《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吴敬梓、曹雪芹将永不再孤独,因为他们毕生的心血早已汇入历史前进的滚滚洪流之中。
注释
①㉗ 张国风《〈儒林外史〉试论》,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95页。
②⑨⑩⑱㉖㊳ 李汉秋编著《儒林外史研究资料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43、357、10、373、357、68 页。
③ 张锦池《中国六大古典小说识要》,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99、423 页。
④[61] 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88、148页。
⑤ 欧丽娟《论〈红楼梦〉的追忆书写——兼及“作者原意说”的省思》,《红楼梦学刊》2015年第2辑。
⑥ 本文引《红楼梦》原文,皆见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⑦ 本文引《儒林外史》原文,皆见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⑧ 李汉秋主编《儒林外史鉴赏辞典》,中国妇女出版社1992年版,第145页。
⑪㉘㉚㉛㊺ [57] [78] [79] 李 汉 秋 辑 校 《 儒 林 外 史 汇 校 汇 评 》 , 第413、29—30、754、543、443、144、671、673 页。
⑫㊵ (清)张英、张廷玉《父子宰相家训——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 41、83 页。
⑬㉜㊽[66][72][法] 陈庆浩编著《 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增订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290、342、257、571、231 页。
⑭ 欧丽娟《大观红楼3:欧丽娟讲红楼梦》(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51页。关于如何看待秦钟的遗言,另可参见林宪亮《秦氏姐弟托梦、遗言及其叙事意义》(《红楼梦学刊》2015年第1辑)。
⑮ (清)袁枚《袁枚全集》第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 290、291 页。
⑯[54] 欧丽娟《大观红楼4:欧丽娟讲红楼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2、57页。
⑰㉓ 何满子《论吴敬梓的平民情结》,《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⑲ 陈美林《吴敬梓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8页。
⑳ (清)方苞《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版,第609页。
㉑㊾[59] 卞孝萱、卞岐编《郑板桥全集》(增补本)第1册,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244、243—244、244页。
㉒ 李汉秋、张国风、周月亮《儒林外史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402页。
㉔ 第二十一回卧评。见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第271、272 页。
㉕ 张天翼《读〈儒林外史〉》,见《张天翼文学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43页。
㉙ 乐蘅军《世纪的漂泊者——论〈儒林外史〉群像》,见氏著《古典小说散论》,台湾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155页。
㉝ 刘大杰《红楼梦的思想与人物》,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8页。
㉞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5年版。
㉟㊱㊲㊴ (清)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升校注《吴敬梓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11 年版,第4、32、4、214 页。
㊶ 李民、王健《尚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15页。
㊷ 吴组缃《〈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纪念吴敬梓逝世二百周年》,见氏著《说稗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页。
㊸ 周月亮《误解与反讽——略论〈儒林外史〉所揭示的文化与现状的矛盾》,《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㊹ 关于王玉辉编纂乡约书之事,参见拙文《王玉辉的追求与悲剧——程襄龙〈唐烈妇传〉的发现及意义》,《励耘学刊》2018年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26—329页。
㊻ 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2页。
㊼ 如何看待虞博士拒绝求人荐举及实报年龄失去进入翰林院的机会,参见拙文《读〈儒林外史〉札记三则》(《明清小说研究》2016年第3期)第三则《虞博士生平片段发微》的论述。
㊿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24页。
[51][52][53] 冯其庸纂校订定《重校〈八家评批红楼梦〉》(上),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94、301、304页。
[55] 张何斌《论贾政形象的内在矛盾——兼谈〈红楼梦〉中的“归隐”思想》,《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第13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1页。
[56] (清)曹寅著,胡绍棠笺注《楝亭集笺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576、577页。
[58] 李哲《中国传统社会坟山的法律考察——以清代为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5页。
[60]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7页。
[62] 孙雪霄《〈红楼梦〉与杜诗》,《红楼梦学刊》2010年第3辑。
[63] (清)昭梿《啸亭杂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90页。
[64] 邓云乡《葫芦条儿·山药糕·燕窝》,见氏著《红楼风俗谭》,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33页。
[65] (清)曹雪芹原著,程伟元、高鹗整理,张俊、沈治钧评批《新批校注红楼梦》第2册,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750页。
[67][68][70] 欧丽娟《大观红楼2:欧丽娟讲红楼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512、526、526 页。
[69] 田晓菲《“田”与“园”之间的张力:关于〈牡丹亭·劝农〉》,见氏著《留白:写在〈秋水堂论金瓶梅〉之后》,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59页。
[71] 刘世南《从〈不自弃文〉谈曹雪芹的思想》,《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3期。
[73] 欧丽娟《大观红楼3:欧丽娟讲红楼梦》(下卷),第904—905页。
[74] 何其芳《论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1—132页。
[75] 王蒙《“搜检大观园”评说》,见氏著《双飞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16页。
[76] 孟羽中《秦可卿的金针》,《红楼梦学刊》2018年第4辑。
[77] 陈诏《红楼梦小考》,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80] 鲁迅《小杂感》,见氏著《而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