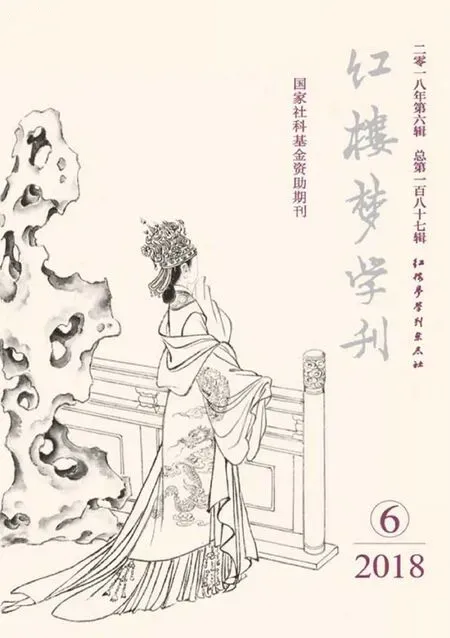首届《红楼梦》与长白山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8年9月18—21日,由长白山管委会主办、长白山管委会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和长白山红楼梦学会联合承办的“首届《红楼梦》与长白山文化研讨会”,在长白山管委会所在地二道白河镇召开,来自北京、天津、山东、吉林、黑龙江、辽宁等地近70位《红楼梦》研究者、文化工作者、媒体记者等出席会议,研讨会主要围绕“红楼梦与长白文化”“红楼梦与满族文化”展开讨论。
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先生在开幕式上致辞,充分肯定了从满族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红楼梦》的重要性。他指出过去红学界从这一角度研究《红楼梦》关注不够,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重视不够;二是对满族历史文化所知甚少;三是从这一角度的研究容易碰到诸如作者曹雪芹的旗籍、祖籍等一些敏感话题。他认为,曹雪芹的家世、人生阅历、生活环境决定了曹雪芹对满族贵族生活的熟悉并受其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从满学的角度、从满族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十分重要的。他建议不要陷入对一些具体问题的争议,而要从满族历史文化的角度深入探讨《红楼梦》的文化意蕴,诸如《红楼梦》与满族祭祀文化、《红楼梦》与满族礼俗文化、《红楼梦》与满族饮食文化、《红楼梦》与满族服饰文化以及《红楼梦》中的游艺、岁时描写与满族文化的关系,等等。
北京曹雪芹学会会长胡德平先生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研究清代的历史、研究满族先祖的历史、研究长白山的历史、无疑为研究曹雪芹的生平打开了新的视野、新的领域、新的空间,值得认真研讨。有关《红楼梦》与长白山文化、与满族文化关系的研究,只要是言之有理、持之有度,而且不断有发现,能够把满族的历史、清朝的历史和《红楼梦》中的一些文学描写文史互融,就是成绩。
长白山管委会尹涛副主任、长白山管委会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张在茂局长在开幕式的致辞中,阐述了此次研讨会在长白山脚下召开的重要意义,认为这是自《红楼梦》产生以来,关于《红楼梦》与长白山、与满族文化关系专题研究规模最大的一次研讨会,如果能在研究的层面上打开一条与长白山地域文化相连、相通的通道,即使是一条小径,都是值得尝试的。
关于《红楼梦》与长白山文化的关系的议题,主要围绕陈景河先生提出的“大荒山”是长白山等展开讨论。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赵建忠教授肯定了陈景河先生通过自己的研究,发掘出的大量的资料,丰富了对《红楼梦》的认识,但认为其基本观点还有继续探讨的空间。
首都师范大学宋德胤教授说,《红楼梦》没提长白山,因此恐怕人们接收不了大荒山即长白山的提法。曹家虽然是汉族,但久居满族高层,已经是满族化的汉人;曹雪芹没有到过长白山,但他的爷爷曹寅随从康熙东巡到过吉林,曹雪芹可以因此获得间接经验,用于《红楼梦》的创作。沈阳军区白山出版社原总编辑董志新编审认为,长白山是满族的发祥之地、清朝的肇始之地;祭祀长白山是清朝国家大典,是感恩先人不忘根本的头等大事;长白山是八旗士人心中的文化坐标。这三点决定了长白山是满族经典的文化符号。曹寅对这个符号的构建、形成有所贡献;曹寅和曹雪芹以各自的具体形式纳入了长白山文化体系。北京曹雪芹研究会副秘书长闫宽从满族发祥于东北、源头文化是入关之前的文化的角度,赞同陈景河把《红楼梦》的源头文化定格为长白山文化,认为曹雪芹在北京西山写作《红楼梦》,他的生活氛围是八旗文化;《红楼梦》的源头文化和北京西山八旗文化,是“两山遥耸峙,一水暗香流”的关系。白河林业局宣传部副部长宗玉柱说,《红楼梦》借古“大荒山”之名指代清朝满洲贵族根脉长白山,曹雪芹为盛极必衰的王朝做了一个从“大荒”来回“大荒”去的预言。吉林文史馆员、著名书画家易洪斌先生回顾了陈景河先生“大荒山是长白山”说产生初期的情况,认为他把长白山这么一块广袤的山林和土地跟《红楼梦》、跟本地传统文化联系起来,发旁人所不敢发,想旁人所未敢想,是一个非常有看点的学术事件。
陈景和先生还阐释了其他几个观点:黛玉是人参的幻化、太虚幻境是贾宝玉的成丁礼、秦可卿具有萨满的身份。对此,部分学者进行了呼应。
中国艺术研究院在读博士研究生李雨泽探讨了绛珠仙草的原型问题,认为在已经被学者提出的数种可能是绛珠草的植物当中,人参的生存环境、地面形态、生长方式、“以物化人”的特点,与《红楼梦》描写的绛珠草最为相似。曹雪芹选择人参作为绛珠草的原型的可能性更高。中国工商银行长春学院副院长秦永顺教授提出,《红楼梦》中最难理解的人物是秦可卿。她时而美丽、智慧、可亲、可爱,时而又丑陋、淫荡、可憎、可怜。秦可卿生前受家族普遍尊重和爱戴,死后葬礼又极尽奢华,与女萨满有很多相合度。
围绕《红楼梦》与满族文化关系的议题,与会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是曹雪芹的族籍问题。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满学专家赵志忠先生阐释了他的三个主要观点:第一,民族不等于血缘;第二,《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收录了曹家,清王朝已经把曹家视为满族;第三,曹家已经从昔日的包衣阿哈,变成了皇亲国戚。因此,《红楼梦》与满族脱离不了关系。民国年间的红学大家,从来没有说过曹雪芹是汉人,而是说他是旗人,胡适还直接说曹雪芹就是满人。赵教授还特别提及《红楼梦》与满族文人的关系:与曹雪芹接触的都是满族人,因为他就生活在这个圈子当中;曹雪芹身边的满族人,对《红楼梦》的创作和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卓引用通行的民族定义,赞同族属的认定不是单纯的血缘问题,也是文化认同的问题。曹家的旗籍,虽然在《清史稿》和《八旗通谱》等文献中记载不同,一种是汉军旗人、一种是正白旗包衣,但根据20世纪50年代民族调查得出的“不问满汉,但论民旗”的结论,入不入旗,文化差别很大,属于什么旗的,文化差别并不大;并引用雍正皇帝的圣旨,说明康乾时代北京的满族豪门贵族,在文化上已经满汉融合,如果立足于《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就没有必要一定要争论作者是满族还是汉族。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北京曹雪芹学会顾问张书才先生表示:我研究《红楼梦》,没讲满文化也没讲汉文化,因为都是中华民族的。研究《红楼梦》有两个问题:第一,《红楼梦》与满族文化研究。学术研究一种方法或路数是需要恢复历史的真实,最好有第一手证据;另一种是鉴赏,主要是研究者个人的认识、理解、感悟。不能以第一种路数反对第二种,也不能用第二种路数反对第一种。第二,满族文化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满族文化的根本,即狭义的是产生于满族在白山黑水之间活动时期,进入辽沈地区之后吸取了蒙古文化,入关之后,汉文化更多一些。《红楼梦》有满族的东西,也有汉族的东西,都是中华民族的东西,不要互相否定。
与此相关,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任少东先生就有关《红楼梦》的排满、反满问题发表意见:乙卯、庚辰、戚本《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宝玉为芳官梳头、改妆,起名“耶律雄奴”,几大段文字中确实有汉族正统观,而苕溪渔隐所见旧抄本,这些文字均不见了。通过对作者家世和作品内容的考察,他认为乙卯、庚辰、戚本中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文字,当系某个怀有这种民族主义思想的抄手或抄手的主人,在某次过录时添加进去的。因此《红楼梦》排满、反满说可以休矣。
《红楼梦》中的满族习俗,是与会学者关注的另一个热点问题。
山东大学文学院王平教授,代表他和他的会议论文合作者白燕,认为《红楼梦》中写到的剃发和编发发式、鹰膀褂等服饰、婚俗当中的傍晚成婚习俗、不分尊卑的敬老习俗、骑射、重女以及放鹰等游艺习俗,都很真实地表现了满族的习俗,提出《红楼梦》中有满族文化的描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关键是要挖掘出曹雪芹的用意何在。吉林省民政厅《民情》杂志原社长兼总编辑马孟寅说,《红楼梦》的最大真实是细节,举凡饮食起居、服装器具、梳妆打扮、迎来送往、宗教信仰、求医问药、风俗习惯、言语表达乃至房屋格局、花草树木、养鸟喂鱼等等,都是以一定的生活事实作为依据的;其浓郁的满族风情,使《红楼梦》新意迭出。吉林省政府文史馆馆员、吉林省民俗学会会长施力学先生例举了诸多《红楼梦》中与满族民俗相关的物品,如“悠车”,是典型的满族人的育儿工具;乌进孝进贡的东西,是典型的东北特产;“饽饽”是满族的食品等。赵志忠教授论述了《红楼梦》中“箭袖”与满族礼俗的关系、“落草”与满族生育习俗的关系以及“妞妞”等满语词汇。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文史馆馆员张顺富先生列举了《红楼梦》对东北地区民俗语言的使用,认为如果曹雪芹没有东北的文化基因,写不出来《红楼梦》这样的作品。《城市晚报》高级编辑于建清也论述了《红楼梦》与满族文化的密切关系。
此外,中国红学会副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副所长孙伟科就《红楼梦》与地域文化建设的关系提出具体建议;北京曹雪芹学会《曹雪芹研究》编辑胡鹏就《红楼梦》创作的虚与实发表意见;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学刊》编审、中国红学会秘书长张云强调,研究者要关注新材料、新成果,以免做重复劳动,甚至因为对新的研究成果不知晓而继续错误观点;长白山书院院长、吉林省周易学会常务理事鞠曦提出《红楼梦》是终结性的文学,以隐喻笔法终结了史学上的“春秋笔法”和文学上的“文以载道”;长白山红学会副会长雷广平陈述了《满洲实录》及其满族源头文化;中国红学会艺术与文创委员会主任欧阳奋强谈及87版电视剧《红楼梦》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纯净”——当时的创作者没有任何杂念。李明轩、赵德武、阚世钧等也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中国红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胡文彬先生做了最后的总结发言,他认为,陈景河先生提出的关于《红楼梦》与长白山文化的关系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他肯定说本次会议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希望通过这样的研讨能够把长白山乃至东北地方文化整体推向一个新阶段、新高度。
会议期间,还举行了长白山红楼梦学会的成立仪式和陈景河先生新著《红楼梦与长白山文化》首发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