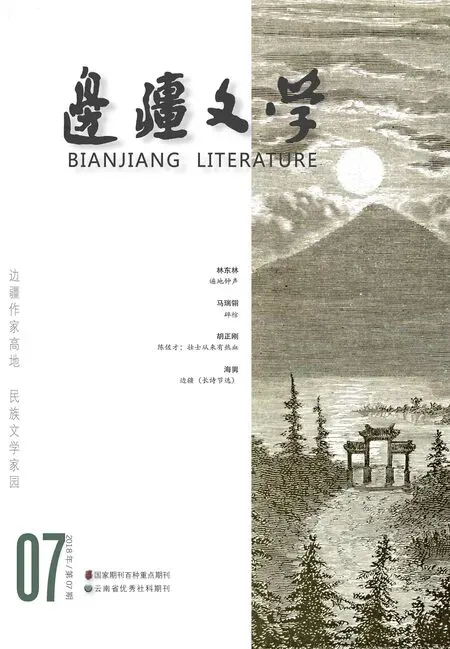冬日,我隐居在云南的天星小镇(组诗)
梁 广
我们一直在做减法
减去一秒 一分 一小时
一天被减得越来越短
减去一天 再一天
一个月被减得所剩无几
减去一个月 再一个月
一年过了 又是一年
认识的人 认识一个就减少一个
走过的路 走过一段就减少一段
有过的悲伤 欢喜 希望 失落
照例一一减少
……
我们总是被做加法的表象迷惑
其实 我们一直在做减法
下午
一个收破铜烂铁的小贩,用充满
希冀的吆喝声,牢牢地罩住
我生活的狭小范围。像是在喊魂
一个不留神,我的魂魄
就跟他飘荡出去了几百米
摸摸几年前被忧伤砸过的脑袋
这榆木疙瘩,它指使我的手
打麻将、写诗,触摸观音
和夜晚中的许多不肯安静的事物
不断地变换着面孔
总想要留住一个西斜的落日
拿着岁月的刀,我在自己的面孔上
雕凿一条又一条的皱纹
那个从内心出走的我,多年了
一直没有使风,失去岁月的痕迹
童年——题一幅画
给童年负上重量,被你见到的
不过是我童年生活中的一个
被剪辑出来的片段
窥一斑而知全豹
我拒绝那些怜悯的目光和矫情的同情
它们不能带给我,像背上的苞谷杆
所给予的温暖。我只能
把梦想装进瓶子,封住口
现在 请给我足够的力量
背着收割后的苞谷杆——
刹住从斜坡小跑下来时的前倾
跨过沟壑时的蓄势,挣上上坡时的牛劲
到了平坦的地势,我才能将头抬高一点
让你看到,一张娃娃脸上
现出的山村最美的晚归图
在劳动中成长,山村是我最好的舞台
一旦卸下童年的负重
我会轻盈得像一个失去语意的词语
我愿意背着我的乡村
像高粱一样,一节儿一节儿地长高
草书
蝉是夏天的神,掠过低空
入眼的事物,他都知了
白云有时茫然,面对无边无际的蓝
一次次遗失一丝丝的飘逸、恬淡、悠远
一个夏天的葱茏像一幅草书
在雨声的滴答中,洗去铅华、浮尘
难掩心中的苍茫
犀利的笔锋总在最后若有若无
我自问无愧于心,下笔的走势
有时细若蚊足,一种情怀也悄然流露
一个夏天,我只引用蝉鸣
对万事万物咏叹
滋生出万千悲喜
却只一味潦草
腻上与世无争的时光
冬日,我隐居在云南的天星小镇(三)
江湖不再传来告急的声息。站在桥上
我盯着冻僵的河面,没有远航而来的
船只,一个在河边垂钓时光的暗探
始终不见鱼儿上钩,一幅画面里
他手握的钓竿呈现出虚实相生的艺术
远方照旧用大雪给我传递信息
用她的雪白净化着欲望的污垢
我试了多次,终究是发不出袖中箭
在小酒馆里,呷着半斤女儿红
眯着醉眼,看南来北往的人
携带冬天的寒流消失在小镇的静谧里
堆积了越来越多的脂肪。在黑沉沉的
夜里,我无奈地藏好夜行衣
翻墙越院的本领只能传给后生了
穿一袭长衫,我扮学究
大宋的秀女,只能用婉词猎取
给一个地方冠名“开封”后,我裹紧
自己,朝内心的深处远行
我是一个有毒的人
我一直在清除所中的毒
我一直也没能清除净我所中的毒
总是清除掉一种
又莫名其妙地中了另一种
这些年 我一直
活在一种又一种的毒里
我开始沉默寡言
拒绝握手 拥抱 做爱 繁衍 微笑
尽可能地把自己装在一件黑袍子里
急急地走在
这个让我一次次地中毒的时代
我是一个有毒的人
没有亲近者 我成为纯粹的孤家寡人
死亡时 我只在人类的字典里
带走“孤独”一词
我还在深爱着这人世
乌鸦不对我哀叫了
这些给过我悲伤的朋友们
它们在河滩上空 看逝水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是一只乌鸦
怎么唱 声音里都充满悲怆
一到斜风细雨的黄昏 就爱站上
一枝斜逸的枝头
夜深人静时
我无聊地摁息星星
四处流浪的狗 会为我叫上一阵
犬吠声衬托出夜晚的静寂后
我才会像傻子一样悲伤
因为悲伤
我对人世还有深深的爱
南山我不去了 寺院我也不去了
就把我背后的山 取名终南
很多时候 我就学蝙蝠 倒挂金钩
渐渐惯用倒叙
说一些不知所云的话
虚词
梁广是一个人称代词 喜欢把字句
却常沉陷在被字句中 不能自拔
一个有着实际意义的词
时常会身不由己地虚指
有一天我看见他在落叶的树下
像极了一片落叶 像要飘飞
有一天我看见他走在路上 两旁潦草
人生跟着他 纡曲弯环
一个之字 在他的脚下 笔走龙蛇
我开始羡慕他 都不要了
一个虚词 无所指 也无所不指
看他披襟散发 一个潦草了的字
落款在千山万水的辽阔巨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