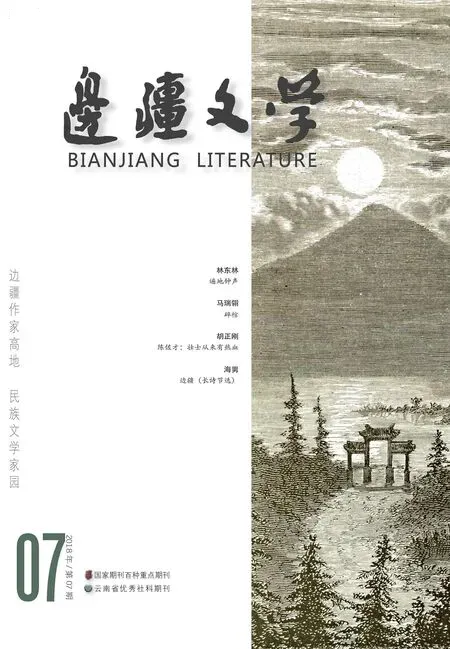谁来看管自己的灵魂
刘 莉
2012年秋冬,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时,常务副院长白描先生接近退休年龄,他说我们“鲁十八”是他的关门弟子。读白院长的文字,是从看他的博客开始的。印象最深的是《我被宣布患了癌症之后……》(后结集为《被上帝咬了一口的苹果》),一连九篇一气读完。虽然是一场虚惊,但他沉稳的笔调和深刻的生命感受,深深地打动了我,仿佛自己也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那天傍晚我在“鲁院”布满文学大师雕像的院子里独自散步。心想,我迟早也会遇到这种险境,到了那个时候,我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吗?没想到五年之后,一语成谶。2017年3月初,我被确诊为肺癌。手术半年以后,身体得到初步恢复,我写下了下面的文字。不敢与白描先生的作品相提并论,权当向老院长致意。
春天里的一声闷雷
时令已经到了惊蛰,意思是蛰伏在洞中的小兽,终于熬过漫长的冬季被春雷惊醒。这个冬天我也和小兽们一样,持续几个月的咳嗽把我困在家中,愈加期盼春天的到来。
北方管春季叫“春脖儿”,意思是从冬到夏的过度非常短暂,所以人们就更加珍惜春光。然而,就在那个春光明媚的上午,走出大庆龙南医院的我,却被卡在了春天的脖子里。这短暂的“春脖儿”对于我来说,比整个冬天还要寒冷和漫长。
2017年3月1日,吃过早饭,我就准备去大庆龙南医院,陪伴在那里输液的母亲。母亲在五年之内先后患肠癌和肺癌,但手术都很成功,这次是例行的抗癌治疗。早晨,和母亲家同住一个小区的妹妹负责把她送到医院,打完针以后我再把她送回去。
虽然开春了,但车里像冰窖一样阴冷,好不容易打着了火,慢悠悠地出了小区。一拐上大道,迎面就撞上一大片阳光。这束光像发令枪一样,使端座在驾驶台上的微型转经筒应声启动。这是几年前我从甘南藏族自治州的拉卜楞寺请回来的。喇嘛说,这个太阳能转经筒是开过光的,转一圈,相当于念一遍经,放在车里,能保估全家人平安。金光闪闪的转经筒发出微弱的沙沙声,像在为我祈福。
到了医院,进到肿瘤科病房,就看到母亲已经躺在床上,正等着护士来扎针。病房里有两张床,相邻的也是母女俩,但躺在病床上的却是女儿。等待点滴的时间里,病房就成了聊天室。那女孩看上去也就30来岁,团团脸,细高个儿,眉清目秀的,得了这病真是可惜了。那母亲是哈尔滨知青,白白净净的,也是大高个儿,像个大知识分子。躺在床上的女儿,讲起她的百岁姥姥至今还能外出旅游,并把手机里的照片调出来给我们看。我必须得承认,她的姥姥是个美丽的老人,就像微信常转发的不老神话。我说你们家一定有长寿基因,都能活过一百岁。我说完这话就觉得不妥,在患上绝症的人面前提寿命是很犯忌的。母女俩没有搭茬,我们也不再说话了。
刚入冬时我就得了气管炎,一喘气就“喉喉”响,像拉风箱似的,吃了很多药才勉强治好。这会又咳了起来。母亲说,你在这呆着也没啥事,去门诊做个CT吧。
CT结果不是当时就能出来的。做完回来的时候,病房里静悄悄的,三个人都睡着了。女孩的母亲趴在床沿上,和她患病的女儿相比,我更同情她,那是她的独生女啊!听到响声,我的母亲睁开眼睛,见是我,刚要张嘴,我就连忙说:“明天取结果”。她点了点头,又闭上了眼睛。
和母亲说好了,第二天早晨我先去取片,然后再去陪她。
我径直来到取片处,拿到片子以后,习惯性地先抽出报告单。果然不出所料,一如既往地写着:“未见异常”。每次都是这样,我有点失望,转身就走。走到门口忽然想起门诊医生说过,我的咳嗽也有可能是咽炎引起的。我的咽炎有二十年历史了,因不严重就从未治疗过。那我何不让医生给开点药呢?于是我又调头走上了扶梯。
在内科门诊长长的走廊里,我找到了呼吸科,正好还是昨天的女医生。我提着片子走进去的时候,几个病人正围着她,等她把患者都答对完了之后,我才说让她给我开点治咽炎的药。她想不起来昨天的情形,要我手里的片子。我说没事,未见异常。她执意要看片子,我就给了她。
她抽出片子扭身对着窗口,看了几秒钟,又看了看我,然后很郑重地把片子插在阅片灯箱里,又仔细地看。我有些警觉,也凑上前去,但我只能看到排列整齐的无数小方框。她指着一个方框内针尖儿大的小白点说:“这儿”。可她的手一拿开,我就找不到那个白点了。我无助地看着她,心跳莫名地开始加速。她说:“这样吧,我打电话给你联系胸外科主任,你让他看看再说。”
我心跳的速度加档了。
她说着摸出手机,在通讯录里翻找着。很快就接通了电话。我听到对方的声音说:“来吧,我在病房。”她放下手机对我说:“去吧,住院二部三楼十一病区,找张医生,胸外科副主任。”
我的脸在发烧,眼睛也好像往外鼓了。
她看我有点迟疑,就说:“去吧,没事的”,我唯唯诺诺地说了声谢谢,然后转身走出了诊室。
站在下行的扶梯上,我想,完了,直觉告诉我这次是凶多吉少了。咱跟这医生素不相识,人家凭什么给我找主任呢?我不敢想“癌”这个字,难道这种要命的病真能落到我头上吗?的确,近些年来同事好友中得这种病的消息总是接连不断地传来,人人都有“中枪”的可能。一个月前诗人老许的妻子就得了肺癌,而且发现就是晚期。去年十月份他们回大庆的时候,我们还见了面,都好好的,到了年底感觉呼吸不畅,一检查才知道病入膏肓了。
难道我现在也……又是一大片阳光像薄玻璃一样砸在我头上,希哩哗啦地洒了我一身。我下意识地仰了仰头,我穿过马路,朝住院二部走去。
张主任是个40岁左右的男人,瘦瘦的,高高的,头发有点自来卷儿,说话柔声细语,第一眼看到他,就觉得是个可以信赖的医生。他给了我两个建议,一是一个月后再来复查,小白点儿有可能是炎症,如果真是,一个月后就消了;二是现在就做加强CT,放大影像,更容易确诊。我问他能是吗?他没有正面回答。我说我母亲得了肺腺癌,会不会遗传?他脱口就说:“你就是腺癌”。
这是我第一次从医生口中明确听到的“癌”这个字眼,尽管不十分正式,但我却感到有一声闷雷在耳边滾过。我用意识紧紧抱住自己的头,不让它变大、不让它出响声,十分冷静地说:“那我还是现在就做加强吧。”张主任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走嘴,声音十分温和地说:“可以的,上午能做上,明天早晨正好有从北京来的专家,你把片子拿来,再让专家看看。”“哦,有专家来?那可太好了。”我故意很高兴的样子,想告诉他不用自责,我能承受。我还有点兴冲冲地说了声谢谢,就下楼去了。心想,这是专门为肺癌患者开刀的地方,人家见得多了。
我再次返回门诊大楼,进呼吸科诊室之前,我特意看了一眼门口的电子提示牌,我要记住这位女医生的名字,她叫王春波。王医生见我进来,就放下患者,优先听我说话。我坐在她对面的小凳上,看着她开单子,说:“王大夫,我要真是得了癌症,你就救我。”她抬起眼睛看了看我,她戴着口罩。只能看见的那双眼睛并不怎么漂亮,她看我有些小激动,就说:“没事的。”,见她安慰我,我仿佛把她当成了好朋友,内心涌上一股委屈,说:“我想哭”。
我被上帝认出来了
再次走出门诊大楼,过马路,再到住院一部,在窗口约号,我恍惚走在云朵之上。前面还有人,我坐下来,这会儿才有时间静下来想一想。我先想到了老公,应该告诉他。他现在在父母家,父亲89岁了,处于半瘫痪状态,几个月前他就回去照顾老人了,现在十点多,或许他正在做饭,听不到。再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在电话里直接跟他说,我打开微信,用语音留言的方式可能更好一些,如果他没听清,或者不相信,可以反复听。
我掐着手机对他说:“老周啊,我现在在医院,刚才大夫说我可能得了肺癌。现在正等着做进一步检查。”
没有回话,我知道他正忙着。
这时我忽然想起母亲,她还在病房里输液,这会儿也快完了,她看我这么长时间没回去,也许会怀疑,就想着如何骗她。
又想到一会还要开车送她回家,我有点害怕。我50岁才考到驾照,加上现在我被那声“闷雷”震得有些恍惚,万一出点啥事怎么办?
此刻我又想到弟弟,让他来接母亲。但整天闲在家里的我,编不出临时脱逃的理由,就坐在那里发呆。CT室厚厚的大门开了又关上,看着进进出出的人们,面无表情,动作机械。他们当中有多少是和我一样正等着判决呢?他们走进去,把自己交给那个轰然作响的庞然大物,让它检查自己的内脏,甄别出“好人”和“坏人”。“好人”就可以继续活着,“坏人”就要去死,虽然不是立即执行,但也只是时间问题了。想到这些,那声闷雷又一次滚过,这次不是从耳朵里,是从脚底下上来,一直滾到头顶上。这雷还带着电,使我的周身都麻酥酥的,这种感觉让我想到早年在变电所当变电工时,我们经常提及的“接地”现象。
我听到一个尖细的声音喊我的名字,尽管喊得那么潦草、那么不耐烦,但还是把我从电刑般的地狱里唤了回来。我定了定神,走上了“判决台”。
我躺在一个像太空器一样的机器里,两手举过头顶,像投降那样。医生关门进入操作室。检查室里只有我一个人了,随后那机器就开始运转,发出轰轰的响声,我感觉那一圈一圈划过去的亮光就是上帝的眼睛,我正在接受他的审判。我感到异常害怕,像被抛弃在浩瀚的太空里。随着扩音器里传来“吸气”、“憋住”、“呼气”的口令,我配合着做出相应的动作,同时感到一些安慰,尽管那声音依然潦草和不耐烦,但起码这是人类的声音。
从“太空器”上坐起来,还没等下地,下一个患者就被人搀进来了。我晕头转向地探出脚去找台阶,像喝醉了一样哩啦歪斜地下来了。
我抱着衣服坐在刚才等候的座位上,再让自己静一静。
要不要给弟弟打电话?我再次想起这个问题。这时,忽然有一种力量从内心升起:你不能垮啊!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呗!是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我都不能垮下去啊,接受和面对,是我唯一的选择。
我定定了神,穿上衣服,朝母亲的病房走去。
回到病房,母亲已经穿好衣服等着我来接她。邻床的母女俩不在,母亲说她们去卫生间了,然后就急切地问我结果怎么样。我张开两手满不在乎地说,啥事儿也没有!母亲不信,说那怎么才回来?我说早晨睡过头了,又堵车,来了之后又找不到车位,好不容易找到了,取片室的人又多,总之是一步没赶上就步步赶不上。母亲还是不信,要我手里的片子。我大大方方地递给她,因为这是最初的那张。母亲看到报告单上白纸黑字地写着:“未见异常”,就不再说什么了。
邻床的母女俩推门进来,要不是女儿的头发刚才躺着弄乱了,根本想不到是个患了绝症的病人,她们都婷婷玉立像姐妹俩一样。见到我那母亲也问我检查结果如何,我说没事儿。她说就是啊,哪那么容易就得上了?看把你妈吓的!我嘿嘿地笑着,连连点头。
母亲坐在副驾驶位置上,路上一直在说邻床的事。那女孩才32岁,已经扩散了,最多也就一年吧,太可惜了。我不想听这些,就把话头岔开,可母亲说着说着又说回去。她说最可怜的是那当妈的,白发人送黑发人,孩子遭难不如自己遭难,你看我都76了,根本不害怕,但要是你们得了那病可就要我的命喽!母亲絮絮叨叨地说这些,好像是对我的“未见异常”很庆幸、很得意似的,可我的心却像被剜了一样痛。
我把母亲送到楼上,本应该折返回去的。但我现在最想见到老公,打开手机一看,还是没有回话。婆婆家与母亲家相距只有几公里,我直接去找他。
进了婆婆家门,老公和父母刚吃完饭,还没收拾。婆婆吩咐再给我炒个菜,我说不用,有啥吃啥。我把他们吃剩下的半盘红烧茄子全吃了,还吃了一个大花卷。老公见我狼吞虎咽的,就问我早晨没吃饭吧?我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等桌子拣了,碗刷了,一切都收拾停当以后,公公婆婆也午休了,我才问老公,看微信了没有,他说没有,我说你现在看吧。
我们俩坐在沙发上,他打开了微信,我的声音就清晰地响了起来:
“老周啊……”
这时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眼泪无声地流下来。我扭过头去看着窗外,一片冰湖在眼前模糊着。湖面上的雪刚刚开始融化,但看上去还是成堆成堆的白……
老公说,你开玩笑呢吧?见我没吭声,就推我,我也不理他,就过来看我的脸。我把手捂在脸上不让他看,泪水却从指缝里淌出来,肩膀剧烈地抖动着,我极力压抑着没有放声哭出来,我怕公公婆婆听到。
老公搂住我的肩膀。我想不起来我们有多少年没有拥抱了,更想不起来我有多少年没有哭过了。
等冷静一些之后,我才从头到尾给他讲起上午的过程,并告诉他下午要去医院提前取片,明天早晨好让专家会诊。老公很冷静,立即电话通知妹妹下午回来照顾父母,他有事要离开一段时间。说着他就一声不响地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
我走到大落地窗前,正午的阳光像金子一样晒满我的全身。目光越过左边的大道,就是开阔的大雪野,白茫茫的。桔红色的“磕头机”错落有致地点缀其上,毛绒绒的,在阳光下放出耀眼的光芒。再往远处眺,地平线上已经出现波浪形的气体了,这是春回大地的征兆,多么美好,多么有希望啊!
可是,即使沐浴在这美丽的春光里,也无法控制我想到自己的处境,眼泪再一次涌上来。这时我想到了远在奥地利留学的儿子。我为自己到现在才想到他而惊奇。也许他是我最爱的人,是藏在内心最深处的人,而不是眼巴前抓过来就能用的人。还有虽然他也不小了,但在我心里还是个孩子,况且还是个那么善良、仁厚的孩子,这样的打击他怎么承受得了呢?一想到孩子,我的眼泪就像开了闸的河水一样汹涌而出……
下午我和老公一起去了医院,按照约定提前取出了片子。因为是刚刚洗出来的,没有报告单,我就让医生先给一个答案。他看了看片子,这回与先前的不一样了,是把病灶放大了的。一个方框里只框着一个大白点,上面还有卡尺标注着大小,差不多是1:1的比例,那医生看了看说,明早你不是找专家吗?还是让他看吧。他不想得罪人,那就肯定是不好的了,我心想。我们又拿到胸外科找张主任,可他不在,就给了一个值班的大夫。他瞄了一眼,见怪不怪地说,嗯,手术吧。我追问着他,是吗?他说,基本上吧。说完就忙活去了。
经过上午一系列的考验,我也不奇怪了,可老公还是个新人,有些不大习惯。我开始安慰他了:没事,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呗,反正也不是马上就完蛋的,怎么也得有一段时间吧。老公不是浪漫的人,也不怎么会哄人,只是一脸的焦虑。
在回家的路上,老公问我现在都有谁知道这事,我说只有你一个人,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能承受得了。他说不是承不承受得了的问题,这么大的事,应该告诉弟弟妹妹,不然他们会埋怨。我理解他的意思,心想今天不告诉,迟早也会告诉他们的。我是老大,身下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平时相处的非常好,“手足之情”正是形容我们之间感情的。但我不敢告诉他们。我坐在副驾驶上,想了一会儿,就掏出手机,时间是下午四点多,快下班了。我打开微信,尽量用平和的声音说这件事。先给妹妹和小弟留完了言,到大弟的时候,我犹豫了。半年前大弟媳突发心脏病走了,到现在他还没有走出阴影,一星期前自驾游出去散心了,说要到西藏去,现在还在路上。
我放下手机,心事重重地看着前方,车遇到了红灯,我们夹在长长的队伍里等待。这时,我突然发现驾驶台上的转经筒停了。此时尚有夕阳,我的心猛然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
我们姐弟几个都是经历过母亲两次患癌打击的人,应该有一些“免疫力”的,但是听到我的消息,依然那么震惊。妹妹最先回了话,是经过一番挣扎,冷静之后才回话的。她来了一段长长的文字,先安抚我,不要怕,妹夫已经托医院的好哥们儿找张主任了,并为我想好了下一步的打算,还说妹夫昨晚做梦感到我有什么事,今早还跟她说。小弟一直等到晚上七点多才回话,原来他的手机落到单位了,回单位取时才发现。他在电话里喊了两声“姐啊,姐啊……”就说不下去了。
第二天早晨七点半,我和老公如约来到医院的时候,弟弟妹妹们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了。见到他们,我有一种不再孤军奋战的感觉,好像苦难被他们分担了,我反倒一身轻松了,于是我笑呵呵地说“没事,没事”。我也的确觉得没事了,大姐从小就皮实,不会这么轻易就垮的。他们看到我这样乐观,也好了许多。他们今天都不上班了,专程陪我会诊。妹妹两口子工作的炼化公司,劳动纪律特别严,是刷脸考勤的。
专家是从北京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请来的,人们称他为高老师。据说这家医院的胸外科技术是国内最权威的,高老师来算是培训也算送医疗下基层吧。那天来会诊的人很多,大都是拿着父母或别人的片子,大家挤在一起,乱糟糟的。
高老师看了几秒种后就十分肯定地说,这是个不好的,马上手术吧。我站在他身旁,不想这么快就完事了,就问他这个能治好吧?他看了我一眼问,这人多大岁数?我说54岁,他略微斟酌了一下说,这必竟是个恶性的病,全世界任何一家医院都不敢打这个包票,但术后会很不错的。我看到下一个片子已经拿上来了,也就作罢。
至此,我患了肺癌,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那一刻感觉自己是混在好人当中的一个坏人,终于被上帝认了出来。
我的宗教
在弟弟妹妹们面前,我没流一滴眼泪。我还和原来一样,走路快,说话也快,我也不是故意在他们面前装坚强,我本来就是好好的一个人,是偶然发现的,这时候如果怂了,就纯粹是心理原因了。以前就听说过,人得了癌症以后,三分之一是吓死的,三分之一是治死的,只有剩下的三分之一才是真正病死的。
我不会怂。更不会被吓死。我觉得老天爷最起码还能给我五年时间吧,这就够了,干什么都来得及。这么一想,我比那些遭遇横祸的人幸运多了。
可是到了晚上,弟弟妹妹们都走了,我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还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我不想死,一点也不想。对于父母来说,没了我,虽然还有三个儿女,一样为他们送终,但是耄耋之年又重病在身的双亲,如果再经历丧女之痛,定会折寿!这是大不孝啊!对于儿子来说,我是他的唯一,他也是我的唯一。好在半年前为他操办了婚礼,感到十分庆幸。儿媳也懂事,又有上进心,是学钢琴专业的,与学萨克斯的儿子正好是琴瑟和鸣的一对,我很高兴。儿子走上艺术之路,是与我的支持与鼓励分不开的。他出国留学并不十分顺利,特别是在国内的同学都纷纷毕业回到油田就业的时候,他还在国外徘徊。老公从一开始就反对走这条路,他和大部分人一样,认为学音乐不靠谱,所以每年到了油田招工的时候,他就极力主张让儿子放弃留学,回来就业,虽然是当工人,但也是央企,即使油田前景不妙,好歹也能混口饭吃。那段时间,儿子也有些动摇了,只有我咬牙坚持着。我认为事情如果错了,就让他一错到底,不要见风使舵,到最后一定还是对的,因为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东方不亮西方亮,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给儿子打气,让他挺住,人生只要有目标,并一直去努力,终会有到达的那一天。而如果放弃留学,就会为他埋下失败的阴影,丧失梦想,人生暗淡,说不定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事实证明我们的坚持是对的,儿子不但考上世界音乐之都的著名学府,还遇到了爱情,未来已经看到了希望。据说艺术家一般都是世家出身,但总要有第一代人去闯吧,我真的很想看到那一天。
即使上帝能够慷慨地给我五年时间,那我也不到六十岁,比我预期的整整少了二十年,二十年啊!我想到了自己的前半生,上学的时候算是个好学生,从小学到高中都是班长,还是大庆样板中学第一任学生会主席。参加工作以后,自尊心很强,不想让领导说出“不”字,工作很卖力。唯一遗憾的是没上过正规大学,但单位给了我机会,让我两次参加成人高考,先后到哈尔滨和北京脱产带薪学习五年,拿到了大专和本科文凭。因为爱好文学,单位很早就把我从工人岗位选拔到机关,在宣传系统工作多年,后来又走上领导岗位。这一路走来,有烦恼痛苦,也有快乐,只是半生工作,诸事缠身,关于文学的梦想还没有实现,一心等到退下来以后当个“专业作家”,后半生好好为自己活。然而,好日子刚来,退下来还不到三年。这些日子里,我每天读书写作,享受着宁静而又充实的生活。慢慢也写出了一些作品,几个月前还加入了工人出版社的“石油作家文丛”,把几年来发表过的有“石油味儿”的小说结集出版,目前正在编辑之中,书名定为《开满鲜花的原野》。这个题材的小说是我最想写的,因为与我的成长有关,所以最先写了出来。现在这本书付梓了,没想到此刻对我构成一个大大的安慰,就像儿子结了婚一样。
上帝为什么选中了我呢?是因为我的任务到此就算完成了吗?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呢?我想起人们常说的一句话:短命的人一定是做了坏事,得到报应了;可还有另一句话:好人无长寿,坏人活千年。我到底算好人还是坏人呢?我做过的好事多,还是坏事多呢?在那寂静的深夜,我就这样拷问着自己,使我的灵魂不得安宁。
未来的路不管有多长,我该怎么走下去?心灵如何安放?
自认为不会垮的我,还是六神无主了。
我不是基督徒,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在兰州出生的儿媳,家族世代信奉天主教。第二天正是礼拜天,我让老公陪我去教堂坐一坐,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我想找一个慰籍心灵的地方。
2017年3月5日的弥撒与往日不同, 刚好是“圣灰礼”。圣灰礼是四十天斋期的第一天。听神父讲经,我才知道在基督教教义里,未来四十天,全体教徒要用斋戒的形式与耶稣共赴苦难。斋期过后就是耶稣的遇难日,他将在死后的第三天复活。那天,唱诗班还唱到:“人哪,你要记住,你原来就是灰土,将来仍要归于灰土”。
再说,这个世界缺我一个人吗?固然亲朋好友会有悲伤,但生活还要继续,不会因为我的缺席而中断,他们好好地生活下去,正是我所期望。我手机通迅录里的联系人有三四百人,这就是我全部的朋友,但绝大部分都不常联系,我活着或者死去对于他们来说有什么关系吗?但不排除他们会在某一时刻想起我来,有可能是通知我去参加他孩子的婚礼或父母的葬礼,听说我已经不在了,会感到震惊,但无非就像得知一条新闻,也有可能会在有限的范围里传播一下,之后也就该干啥干啥去了,那么缺少我一个人,孩子的婚礼或父母的葬礼也照样不会受到一点影响。
那这个世界缺我一本书吗?这就更不用多说了。
那么我的缺席会影响孙子的诞生吗?这根本就不用回答了。
我这样想,并非感到世事悲凉,这就是事实。
那天在教堂里,我虽然不是教徒,但我也和大家一样站到了队伍里。我也想被神父在前额上按下一个灰土的印记,这也仿佛代表着我的出处和归宿。
从教堂回来,我轻松了许多。
我还是想到了文学。
文学,在这里不单单指写作,而是心灵的一种寄托。心怀文学的人,也许会生出另一根神经,让你仔细体查每一个生命的过程,就如我现在这样。这不是多虑,更不是瞎想。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向死而生”吧。死亡对于我来说虽然是个可以预见的事实了,但哪怕只有一天,我也会觉得是我的未来。所以我不想这样糊哩糊涂地走过去,我要竖起耳朵,睁大眼睛,调动起各种感官,像一个非常会生活的生活家那样,认真而细致地觉察路上的风景,这个过程一定是新奇的、壮美的。这样,我还会慌乱吗?死亡,是一块石头,会镇住我的内心,使我六神归位,沉着冷静,有条不紊,这难道不是我的宗教吗?
“我”的本质是什么
确诊一周以后,高老师再次来到大庆,专程为包括我在内的四名患者手术。
提前五天,我住进了医院,开始全面检查,为手术做准备。
去医院的路上,我惊奇地发现,车载转经筒又恢复了旋转!我欣喜地打量着六年前从藏区请回的金光闪闪的装饰性法器,经筒上刻着藏语六字箴言,至今依然完好如初。自从她落座在我家的车里,六年来一直尽职尽责,三天前却莫名其妙地罢工了,现在又匪夷所思地恢复了。
无论如何,这都是吉兆。
可就在这时,传来一个坏消息。接到好友老许从威海发来的短信:“妻子小吴走了”!我一下子惊在了那里,怎么会这么快呢!从发现到离世只用了78天啊!他们本打算天暖和以后回大庆的,可怜的小吴终是没有等到这个春天。威海是他们旅居的地方,当地只有嘉男一个好友,处理后事需要人手,要不是我现在的情况,会和朋友一起赶去为小吴送行。在这个关头,小吴的离去,对我不能不说是个打击。因为我们得了同样的病。
手术的一天终于到了,我才觉得确实要动真格的了。不事到临头,不觉得紧张,到了,还真有些害怕。头天下午,主管医生把我请到办公室,为我讲解了手术原理,我这才知道人的肺是左二右三,我的病灶在右上叶。手术时先用蝎形(三角形)刀法切除病灶,然后做现场快速病理。如果是良性的,手术就此结束;如果是恶性的,就要切除整个右上肺叶。听完医生的讲解,才知道我并没有走到最后的判决,家人及朋友们也都心存侥幸。但医生说我的情况非常典型,CT片都可以当教材用了,“万一”的比率非常小。一周以后的病理报告也证明了这一点。
我把手放在右锁骨下,仔细体察病灶的位置。这里从未有过不适,所以我也从未关心过自己胸腔里的内脏,连它们在什么位置都不清楚。难道真是好好干活就不会被关注,只有“闹事了”才被重视吗?医生说右肺是主力,而右上肺是主力中的主力,我呼吸吐纳这个世界已有54年,也许是我太不讲究环境质量了,把有毒有害的东西都吸纳进自己的身体,而作为前沿卫士的右上肺拼尽全力为我过滤、抵挡,终是积劳成疾?或许是我太在意环境质量了,对有毒有害的东西太嫉恶如仇,让凝结在胸的恶气终于达到峰值,引发了这场恶变?或许,或许……
从医生办公室出来,我和老公去了六楼手术室。我想像着明天上午就要在这里开膛破肚,取出积劳成疾或忍辱负重到了极限、变成异己分子的右肺上叶。我得感恩医院,感恩医生们,他们将制止这场哗变。要不是这样,我真的很快就会与小吴会合。
3月10日上午8点半,在护士的指示下,我脱掉所有衣服,只穿一套病号服。然后披着大衣,光脚穿着拖鞋,跟着护士走出了病房。长长的走廊因为刚刚清理了陪护人员,显得异常安静。
这一刻我的心有点慌乱。
走廊尽头的玻璃门外挤满了人,我以为是患者们的陪护。推开大门,才知道全是我的家人和朋友。我看到了田明吉和朱长齐,他们是我从小学到高中的同学,几十年了,一直保持联系,是“发小”里边最要好的人,也是我有限的几位最可靠的朋友。在这个时刻看到他们,我突然想哭,就伸出两只手去抓他们。但是,护士催促我快走,浩浩荡荡的亲友也包围上来簇拥着我。我没抓到他们,溢到眼里的泪水也被众人的力量逼退了。电梯直接把我们送到六楼。手术室的门已经为我敞开,护士不给我犹豫和听亲人们嘱咐的机会,直接把我推进大门。
我回头看了一眼,大家拥挤在门外,神情庄严。
大门关上了。
我感到一个世界被分成了两半。
外面是天堂,里面是地狱。
手术以后的日子真如地狱般煎熬。从麻醉开始的,我被排在第二台手术,前面的开始以后,我就正式进入术前准备了。我看到麻醉师在我头顶忙活着,就问他需要多长时间起效,他说马上。话音刚落,我就感到从右手腕过来一股劲,“嗖”地一下就到了胸口,我想喊:“心脏好难受!”可是没喊出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这个过程大概只有两秒钟。后来听说现在执行死刑已经改用注射了,我想大概就是这样的。
我被全麻以后,其实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死亡。在这段时间里,护士把管子插进了我的气管,手术过程中我的肺被放了气,改用呼吸机代替,这在清醒状态下是不可思议的。后来我还知道,我的肺叶切除以后,医生还要把切断的气管重新固定,这些复杂的动作都是通过腔镜完成的,所以我的刀口只是腋下的三个小洞。如果不是现代医学的发展,我就会被锯开肋骨,掀开胸堂!
麻药的劲真大啊,我睡得真跟死了一样,连梦都没有了,那段时间完全是空白的。
我醒过来以后,呼进第一口空气的时候,世界突然被阻塞了。我吸不动,稍一用劲就感到胸腔里全是碎玻璃,撕心裂肺般地痛。我不能进气,只能出气,像个倒气濒死的人。我睁开眼睛看到了我的亲人们,他们的脸罩住了天花板,他们关切地问我怎么样,我有气无力地说,太疼了……不能呼吸了……我感到万分委屈。这时有一只手擦去了我淌到耳根的泪水。
我的身体被插了六根管子,胸脯上还吸附着八爪鱼般的吸盘,左臂箍了血压仪,右手食指夹着血氧感应器,全副武装地监视着我身体的各项指标。我被绑架了,一动都不敢动。特别是两根引流管,又粗又硬,从刀口插进胸腔达一尺多长,让我的每一次呼吸都要上一次刀山,连手指的位置都不敢改变一下,动哪儿都会连通胸腔里的碎玻璃开始研磨,真是万箭穿心,万劫不复啊!
这些管子和监测装置进进出出于我的身体,发出不同的信号,监视器面板上的图表、指示灯红红绿绿地闪烁,我被一个强大的外在系统严密地监视着。我忽然觉得,此时我的肉身被那些图表和指示灯照看着,已与我无关。这堆骨头和肉闹情绪不会通知我,搞小动作也不告诉我,我管不了它们。但机器不一样,它们明察秋毫,出现任何异常都立即被捕捉,再以不同的形式告发。这一切都与“我”无关,即使因那巨大的痛想抛弃这具肉体,也是做不到的。
我的肉体背叛了我,那么“我”是什么?什么是“我”?监视器上的指标都是肉体的投射,我心灵的指标呢?
再强大的系统也测不出我的灵魂,这难道就是“灵魂独立于肉体存在”的证据?进而如宗教所说:肉体归西,灵魂永生?我对人死后灵魂是否永生不感兴趣,但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的本质,就是我的灵魂。
既然灵魂独立于肉体存在,那就不应该以“肉体是否安康”来决定是否要过“灵魂生活”。身体健康,灵魂自由;身体受限,灵魂依然可以放逐。
那么在我身体健康的时候,到底过了多少关乎灵魂的生活?我不敢回答这个问题。
那么现在呢?
我是不是应该感谢这场大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