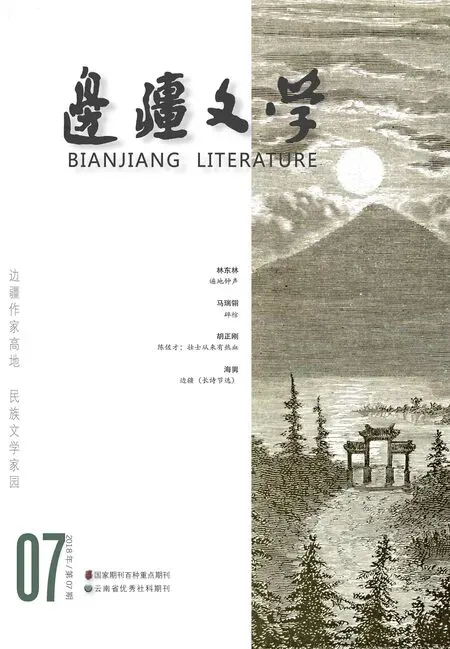截流白浪河的诗行(组诗)
师国骞
代笔
越过立冬 几个
许诺过变红的枫叶出尔反尔
这是东校区 今年最大的新闻
造物主申令 清理门户
冬风那个吹 它们面不改色
我所能做的
是在几声落地响后 给这
一目了然的死亡代个笔
虚构腹泻突袭
不出意外 卫生纸的注辞已是乌鸦
不出意外 它尖喙在那次大材小用时
抱定杀身成仁的软和
不出意外 止泻药一招制敌后
它大汗淋漓 城市的大慈悲
是一场暴雨有转机时 允许乌鸦
出现 不出意外 这是只农田的乌鸦
它用麦芒擦抹针尖 疼痛慰藉疼痛
香山寺书
因光阴社稷里古柏树的独处
香山寺始建年代不详
它像我诗一样单薄 父母遗孤
烟圈套不出寡言 神伤地皱眉后
隐于陋院 庙山香头的焰火
还是烧出了暮色 逐客令未手写成文
我已谙熟这金里发黑的哑谜
起身时疏忽 担着膝拐上的念珠
砸地一声 中殿那只檐上雀横鸣起来
它红丝丝眼球像望见久别的亲人
巴巴的声带里 我听见它叫着重修此寺
崇正和尚的大名 明朝那座忧郁的黄昏中
此僧为此鸟告辞远行落下珠子
天气晚来秋 去吧 朝西飞 安生立命
哦 我们的记性 不会遗忘古老的动容
以及那相加于命的声音
截流白浪河的诗行
1.
每回的波澜,都如
击鼓传花,恭请出祥和的
铜牛。布满水纹的目光,端平
白浪河这大碗儿女。波澜们
轻坠于牛蹄,都像安适地
匍上了老母脚跟
2.
传说中的白狼,命里
带水,图腾似的,司握
源头。传说中的白狼,举家
动迁,决绝地海居,不再过问
昌潍事。清夜寻狼不遇,心向渤海的
白浪河,从濡养着月明星稀,万家
灯火的水体,寻得沛然
3.
活成西湖模样。白浪河湿地
燕来湖,“淡抹浓妆
总相宜”。注意听了没,那桠
香肩之上的棕头鸦雀,与其他
倾慕者分野:不轻佻地开口
4.
朝北伸过去。白浪河
像左手的无名指,戴上铂金摩天轮
信物转啊,连理跳起了华尔兹
张灯结彩的黄昏旁,我们双手
合十,默诵着祝辞
5.
一步一声地,人行栈道,像敲打
木鱼,白浪河正流露
推敲声音的严静。白日
被水送入空门,却动了
托物言志的贪念。晚上,独坐的人
像卡在木板缝隙间
修行未果的肋骨;荷花收朵了,像卡在
革新不止的水流中
的怀旧主义者
螺蛳湾站到联大街站
地铁无知己 就与城区
色调最深的黑暗隔窗而坐
怔怔看 试着让厢灯虚影含羞低头
我想确认背后之人 如白纸铅字般不争
是否有石墨肤色 沃尔德曼垮掉的卷发
蚕头雁尾浓眉 顾城寻找光明的眼睛
及傲立春城的痣 滇池西岸升起
我提速尾随 几度追上回头
他又拐进另一黑穴 我听见丑陋的嘶哑
是曾与我结怨的乌鸦 有人在虚构熟人
来历不明 翅膀变得沉重 喙声渐已勒紧
终于 他为集体橱窗里的部分乘客
停在联大街 四下通明
在他隐遁的玻璃外 有无人类
意识到自己狭薄的投影
从黑暗中抽离 如此轻率地推开城市房门
独立的奶瓶(《斜阳》)
这是我见过的斜阳,最后的遗书。最后的
跳刀形同甲板,最后的奶粉由“一条红色斑纹的母蛇”
偷渡。碘溶液的天色消毒伊豆,战后“快乐阳痿者”七寸
残疾,罪责标注,“日本最后的一位贵妇人”和她的儿
支取最后的血本无还。拦腰搂抱山体的客厅,胸口
总有与海齐平的一己之见,穿堂风无赖,热衷冗余的
牺牲。怀上孩子使我发昏,“我的腹中栖息了一条蝮蛇”
黑晕里谁发号施令:成为独立的奶瓶将胜过爱一个人夫
肉身空心处(《快跑,梅洛斯!》)
“从年轻时就必须守护自己的名誉”,使一座
刑场放下屠刀,码成空心山。暴君迪奥尼斯与
不诚实的心,隔着一面刀墙。梅洛斯说刀山深处
藏有寺庙,“还有人在等着我去搭救”。脑路上
一片黄昏,动摇的门牙吞下了肚里,“快跑,
梅洛斯!”搅局的激流和山贼业已偷生。俯向
以诚信打赌的当局,人质塞里侬蒂斯如伞,盼来旱季的
绵雨。国王搂着二人,找回失散的肉身空心处隐身的神
青春策展人(《女生徒》)
馆藏的不止于妈妈的洋伞,比如:晕血的
卫生巾,“女人味的漂亮的包袱皮”……无人
光顾的展览,持刀闯入,不局限在年代久远
胸前的“一小朵白蔷薇”,哪朵腰间别着
淤血。“没有王子的灰姑娘”对水晶鞋的谤惑
已供上展台,夹心糖乱哄哄地喷薄。训诫
都是追杀,行吟才能自救。女生徒的青春
策展人,一纸空文门缝下语塞,你是怎样的
太宰治,推开门,也无济于事
还命(《维庸之妻》)
识破栾树富到滴油的骗局——“享乐主义的
冒牌贵族”。众目睽睽,暴利的黑油买卖,地面
满是公开的心理阴影,浮着溺死其中的诗行
他听见叶片窸窣,杂质琐屑,猜测不着家的诗人大谷
何处酗酒,想起遗落大谷“那间六榻榻米”出租屋
内的诗稿。这是去中野站某小餐馆的路边,栾树
膝下,携幼上班的大谷妻子将由此经过,她手里
卷轴的诗稿,将物归原主——凌晨轻易玷污她的
“大谷先生的诗迷”。就像大谷的父亲,那个写小说的
没落乡绅,芥川读者,基督教徒,走向栾树下的黑市
走向脏水潭,把命还给要光有光,说风就是雨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