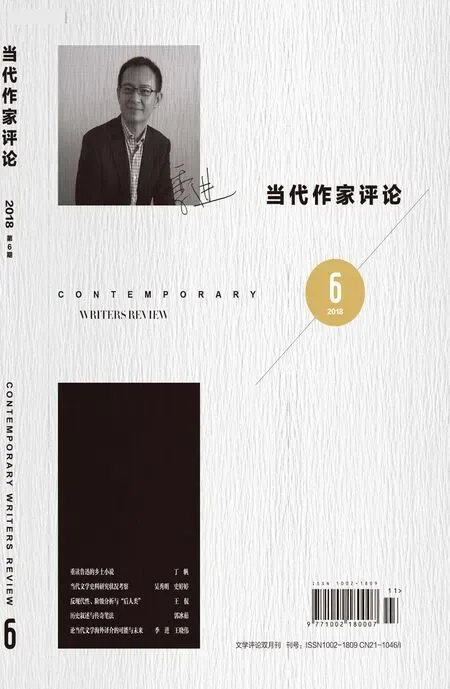大地上的逃逸者
——读鲁敏的长篇小说《奔月》
李 丹
古代汉语把不动产视同安全——兴宅娶亲、屋中有豕即是“安家”;现代汉语把不动产当作信仰——“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若如愿买到一个水泥格子,便可自立为王。对女性而言,其意义更要翻倍,世界曾把她们码在厨房里、织进卧室里、摆在客厅里,而“不安于室”则是至大的贬损。“室”的另外一个意思,不是“正室”便是“侧室”,于是到了吴尔夫那儿,“一间自己的房间”就成了必须。以至于在当下中国,男男女女、心心念念的就是一部“堡垒法”。家庭和房产二位一体,世俗主义的终点,就在家门背后,人们住在宅子里,自己当自己的看守。但是,谁又喜欢自闭、谁又爱囚笼呢?于是总有崔莺莺们的后花园曲径通幽、黑旋风们的梁山泊大旗招展。只可惜,不论是暗度陈仓还是明火执仗,也不过是在情欲和暴力间打转,哪怕春风十里排头砍去,终究还是落了下乘。
到了20世纪,人们发明了互联网,曾经最著名的一句话是“在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男男女女躲在大大小小的荧幕后面,用无数刻舟求剑的ID在现实与欲念之间荡秋千。对很多人来说,这或许就够了吧?只需带上面具,便能安全地亲历人性。另外,还给你有钥匙的门、带路标的迷宫、必有报偿的未来……这一切,只需交出你的人生。小说《奔月》只是有限地刻画了几个人物,却几乎是临摹了这个世代的众生。
一、“人设”
主人公小六的逃跑像是一个大号的嘲讽,有点儿“你把世界配给我,我拣尽寒枝不肯栖”的意思。她对“日常”转过身去,就像耶稣背对妇人,拒绝拿起石头,于是法利赛人的世界就成了一个笑话。但嘲笑世界并不是小六的本意,模特们走在T台上,把自己贬低成一具衣服架子,小六不过是把这个世界赋予的人设退货,做了一回自主维权的消费者。否则以这个世界的尿性,人类再等上两千年,怕也等不来一次主动召回。
在21世纪的中国,“人设”作为消费品早已大行其道,社交媒体上动辄某某艺人“人设卖得好”、某某明星“人设崩了”,仿佛随时循环上演“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人设”这词本是动漫业的行话,意指画师们在塑造角色时所设定的诸多标志性特征。虚拟的人物依靠发色、脸型、服装、配饰来区分角色,让观者注意和分辨。一旦失去了排他性的人设,这些人物也就只有简笔画的意义。只是,眼球经济时代了,特征就是整体、人设就是角色,世人太忙,忙到没有时间去消费一个完整的你。于是大家努力把批发改成零售,自我精简成一出戏仍嫌不够,还得像分切牛肉一样精确分割自己,点了上脑就绝不给你端上菲力。“人设”出现,几乎是个救世的一揽子方案。对明星来说,“人设”是高流动性的通货,他们被设定为老干部、吃货、好丈夫和强迫症患者,用粉丝的注意力来置换资本;对常人来说,人设是低流动性的通货,人们把自己设定为父亲、妻子、产品经理和工程师,精准运行以确保生活有烟有火。在《奔月》里,小六是贺西南的主妇、张灯的性伴、林子的恋人,以及同事、朋友、消费者。她的每一重人设都充满魅惑且精致无比,这让贺西南固执地认定她绝不会遇难死亡、让张灯对着她的浏览记录如醉如痴、让林子欲火中烧欲罢不能,也让她自己在职场上所向披靡、在日常生活中如鱼得水。“人设”是一个异常合理的定质、定性、定量系统,交通导流线一样分流辛劳、冲动和欲望,这甚至比“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更为精密、高效和有力。
从生活里逃开的意思,是说这生活是个赝品,但生活说,你才是赝品,你一户口本都是赝品。《奔月》里小六的人设维护得太好,好到自己的人生其实摇摇欲坠,别人还觉得你不动如山。
小六可以细腻地回忆起与贺西南婚姻生活的细枝末节——“衣柜里的十三条领带;冬天一起泡脚;清晨刷牙洗手间镜子里一对满口泡沫的人;阳台上的衬衣在滴水;卡通杯里的茶垢”,但也能更加坚决地说出:“老实讲,我好像谁都不爱的。”她与张灯无缝对接,器官咬合吸吮,“那种直冲天灵盖般的嚣张气焰常使他们理智尽失”,但从头至尾,小六又“淡然于此、视若无物,如口渴即饮、伸手摘果般的平常”,张灯与小六的初次性爱甚至“还不如丰水梨与创可贴值得一提”。她和林子两人操练了由情至性、从求欢到交配的几乎全过程,从常态到变态一一历练,但小六始终都是一个旁观者,“感到自己像是《一千零一夜》里的枕边人,没有任何威胁,却比山鲁佐德更为卖力。她既置身舞台中心,又是帷幕后的操纵者。她带着双重的视角与罪恶感,旁门左道地无耻创新,揭露和剥落出那个万劫不复、暗无天日的自己”。至于在职场和日常生活中,小六更是一个杰出的伪装者,连“嗜吃醉泥螺”这样的小细节也只是人设之一,“是她在某个场域里的习惯性装备,用以区别于他人、用以确认自个儿”。
而所有伪装的意义,不都在于撕破伪装的一瞬吗?这个世界的上限,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个世界下限,则是“一种幸福,各自表述”。而无论上限与下限,又如何有小六的空间呢?容不下啊,实在是容不下!于是小六就只能用一种冒犯的方式,把生逢人世变成一次长达28年的潜伏。
无论如何也不肯把自己交出去的执拗,或者说,在世间行走而委身不得的孤独,让小六踏上了逃出南京的旅程。小城乌鹊算是一座逃城,但随机就会比命定好吗?要是逃跑就能赢得解放,阮籍又何必“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监狱若是大起来,整个世界都流放地。小六从南京跑到乌鹊,也就相当于从宁古塔跑到沧州。摩西领犹太人出了埃及,却还祈祷“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小六的日子是无可数算的,“南飞有乌鹊,夜久落江边”,漂泊于小城终归还是不得已。小六引爆了“人设”,世界却又给你重造一个。在乌鹊,小六虽然隐遁藏匿,却无力阻止这世界依照前定的逻辑螺旋回升。
二、“降维”
刘慈欣在《三体》系列小说中创造了一个“降维打击”的概念,原指高维空间生物对低维宇宙空间降维,从而导致低维空间的文明彻底毁灭。对低维生命来说,“降维”意味着基本规律的颠覆,它并不针对某个特定对象,而是使整个低维世界的秩序和法则完全失效。借用这个说法,小六从南京潜入乌鹊,多少有些符合“降维”的定义,虽然其意不在“打击”,但她的存在对于乌鹊居民来说,却永远超出服务区。如果说小城乌鹊里的林子、聚香、籍工和钱助理都是一部电视剧里的角色,那么至少在这出戏的开头,小六就是那个执掌遥控器的人。
不论对南京还是对乌鹊,小六都是一件凶器,就像《三体》里的一片“二向箔”,不仅让你的世界粉碎,还让你的世界观崩溃。孙悟空在地上画个圈,说里面是安全外面是恐怖;孔夫子在地上画个圈,说里面是内圣外王外面是无君无父;世上的可怜人在地上画个圈,说里面是爱外面是恨,小六却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仅拒绝缴纳投名状,还说你们画地为牢的勇气其实都是空无。
在《奔月》中,小六的乌鹊生活占据了重要篇幅,作为对比,她曾不无冷酷地道破自己南京生活的可怜本质——“我与楼底的这位主妇,或其他任一主妇,可以分饰A、B两角,交叉运行不同的家庭。我和她,都能够在对方床头找到睡衣,很快掌握不同型号的数字洗衣机,准确地从冰箱下层找到不够新鲜的冻带鱼扔到油锅里准备当天的晚饭。丈夫们也一样。”“这种替代性可以类推到各个方面——父母与孩子、上级与下级、人与某个角落、人与某年某日。一切都是七巧板式的,东一块西一块,凑成堆便完事。你辛辛苦苦像燕子衔泥一样搭建起小窝,你与这个小窝的隶属关系,只是玩偶及其舞台”。
“现代性在鲁敏那里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肉身化为小说主人公的某种执念,某种怪癖”。曾不止一个作者勘破这种生活的虚妄,君特·格拉斯笔下的奥斯卡·马采拉特终身不肯长高,卡尔维诺书中的柯西莫男爵一辈子活在树上。小六的逃亡、侏儒的身高、男爵的树木都是扔向这世界的二向箔。他们从时代的种种定义里脱身潜逃,顺便几乎是残忍地宣告:你们心心念念的秩序,不过是精神桑拿和灵魂按摩。只是,没人愿意接收那些他们不知道的好消息,在未知与故作不知之间,大多数人软下腰去,按部就班完成一段“玩偶及其舞台”的关系。
所以,小六对来到乌鹊时第一份和光同尘的工作极为满意,“如果天底下真有一份最适合她这种情况的职业的话,无疑就是这‘卡通人’了:她能看别人,所有人。所有人也能看她,但看到的并非她本人,只是‘二熊’。但除了很小的孩子会把她当作‘二熊’外,大部分人又知道她连‘二熊’都不是。这就非常有效地避免了一切的社交”。大隐于市,曳尾于涂,小六打扮成卡通人的样子几乎有些庄子的味道了。只是,这被中国人用了两千年的手段,真的就万试万灵吗?
日子就像西西弗的石头,依然无可避免地沉重起来,乌鹊生活几乎就是南京生活的微缩加速版,从男欢女爱到职场斗争,那些被一笔勾销的故事再次固执地找上舌头。天上星河转,却还是旧时天气旧时衣。乌鹊在短短两年内迅速南京化了,让人不禁对马克思那句“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击节赞叹。“没有盼望的生活”是对一切人类的总拷问,从“有所待”到“无所盼”是小六这场乌鹊历险记的全部内容。
那些虚拟但又真切的社会关系顽强地生长起来了,在乌鹊生活中,小六很快就有了准父母关系(籍工、舒姨)、恋人关系(林子)、闺蜜关系(聚香)、同事关系(钱助理等),这些人和她南京生活中的母亲、丈夫、情人、同事没有任何区别,而种种社会关系所衍生出来的理解与误解、无情与嫉恨、认同与攻击再次呈现。逃亡其实带不来拯救,忙碌抵消不了怨怼,硬起心肠来却还是走回到老路上。张爱玲和毛姆表示,拯救爱情需要一场战争,至少也得是一次霍乱才行。而寻找人生的意义却比拯救爱情还要难得多。
我们是有一些老路的,世事嚣嚣红尘滚,中国人厌了,就熟门熟路地把终点站定在桃花源,然后梅妻鹤子一下,也无风雨也无晴,心里就太平。若是好风凭借力就立德立功,若是行路难多歧路就山林田园。就算无所获,至少也落个乘兴而来兴尽而返,总归是不执拗。但小六却不,她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委身的每一个人都是俗人、自己栖身的每一块地都是飞地,她绝不会像贫穷的家庭教师简·爱那样对主人罗切斯特说:经过坟墓,我们将平等地站在上帝的面前。在小六的维度里,别人的咽喉才是敞开的坟墓,那些社会法则、道德律令甚至爱情都是诅咒。《奔月》里有一种纤巧敏锐的见异思迁,《圣经》上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大部分人舍不得让这出戏演完,而小六却能背对电视,狠心按下遥控器。
三、“男女”
对相当数量的男性读者而言,《奔月》带来的阅读感受恐怕都骨鲠在喉,一部把菲勒斯中心主义打在尘土里的小说,怎么会令男人愉快呢。唐代女诗人李冶有诗: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溪。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若是男人读到这首诗,大概都会在心里偷笑吧,婚姻是多么好的捆绑啊,哪怕不是一段彼此祝福的关系,仍然会让那么多女性如醉如痴、趋之若鹜。
若以男权中心的角度来看,婚姻与其说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约”,莫若说是男人与男人之间的“约”,用盖头和戒指、誓言与蜜月,一个男人向其他所有男人宣示和落实主权。红尘男女奉行的神圣法则,不过是一次情欲和财产的包产到户。
鲁敏的笔,对男性见骨剥皮,令人击节赞叹。身为丈夫,贺西南在我们这个缺乏理想主义的时代里也称得上典范:小六生死未卜,他不抛弃不放弃,只要婚姻还在持续,他就坚持身体忠贞,哪怕一颗心另有所属也要先在程序上履行一次恩断义绝;作为情人,张灯足够奔放而能满足小六内心的情欲,也足够无耻而能使她不必考虑道德束缚;作为男友,林子朴素实诚还带着点青春期的莽撞冲动,有痴心便能绝对,为了一点幻想就愿意把全身心都交出去。这几个样本,差不多就可以涵盖当代女性对男性的全部想象了。就算站在女人这边儿,男人也会禁不住问:女人啊,最坚固的相守、最蓬勃的情欲和最好的日月都给你,你还想怎样?
小六的回应羚羊挂角:你们愿给的我都要,要了之后还都扔掉。
男男女女之间有很多逻辑,通常小于生死相依、一般大于始乱终弃,大部分情况,是一不小心就爱了、一不小心就信了、一不小心就婚了。又因了这些“不小心”,这些“爱、信和约”很快就变成守不住的围城。耶稣有句语录刻薄见骨,却又直逼人心——“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说得虽是男子,其实却男女通吃。你的身体是清白的又能怎样呢?见了孙大圣,还不是白骨精?这种决绝的态度令追随者们望而却步:救主啊,你这样的言辞又让何人可奉、何人可行呢?幸好另一位语录大师出来和稀泥,说是“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把人性转换到礼制,把决绝也调整成修行。人们趁势定了些“论迹不论心”的律令,以虚晃一枪的姿势,把敷衍进行到底。只是,爱得蹩脚,必然活得心虚,人若非寿数有限,其实大抵混不过去。
鲁敏“迷恋于‘家庭’所透露出的复杂的、动态的、没有终点的但又能够准确找出人的形象的功能”。这在其长篇小说中多有呈现。而《奔月》的出色,在于跳出了痴男怨女、冤冤相爱,也跳出了尔虞我诈、一地鸡毛。无论情感还是事功,小六均无有亏亦无有得,没有波澜起伏,更无关山飞渡,心动指数一直为零。“驱赶苍蝇、清理排泄物、疏通积堵,把污水溢流的地面擦洗得光亮可鉴。她有种奇特的快意,越是低劣、污秽,越能得到一种无目的的满足感”。把日常需要降低到厕所里,小六就变成了一个长发的甘地。任何一个男性伴侣和她都建立不起超出荷尔蒙、内分泌和器官的联系。至此,男男女女这点事儿也不过是蛇蜕蝉皮罢了。
《奔月》里的三位主要男性角色几乎是依照一种不高于神经反射的逻辑行走坐卧——贺西南无法抗拒地回到了安逸温馨的家庭生活,恩断义绝和浪漫求爱都只围绕这一所需;张灯则意识到了自己的情感饥渴症,用小六的“QQ空间、微信微博、浏览历史、观影记录、购物车、豆瓣评论、邮箱附件”捏造了一个灵魂伴侣,至于这个伴侣是否还叫“小六”其实已经无关紧要;而林子还是个懵懂男孩,嚷嚷着他一知半解的一切,却在小六真要坦白自己的身份时落荒而逃。这种性别关系的重构,有力地击破了一切庸俗故事,让《奔月》获得一个非比寻常的位格。小六和这些男性角色的塑造,几乎称得上是女性主义的一次成功逆袭,“玩偶及其舞台”还在装模作样,观众却已悄然退场。看似七宝楼台的庄严叙事被戳破,露出锦灰堆的本相,以至于小说在文末激情饱胀——“她总算是实现她的妄想了啊,随便哪里的人间,她都已然不在其中。她从固有的躯壳与名分中真正地逸走了。她一无所知,她万有可能。”
在物理学定律里,一个物体若要离开某颗星球,需要达到一个“逃逸速度”,否则强大的万有引力将使其不可抗拒地落回地面。这世界上,人们挣扎在自己的躯体里,被延伸而出的理性、忧伤、爱情捆绑在大地上,难以脱离。而《奔月》在故事结尾则用“奔跑”的意象和“摇摇晃晃迈开步子”喻示了小六的离去。很多逃亡故事讲述的主题是由残缺而至圆满的成长,但《奔月》却以一种孤芳自赏的完成时态,令小六从这世界僭越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