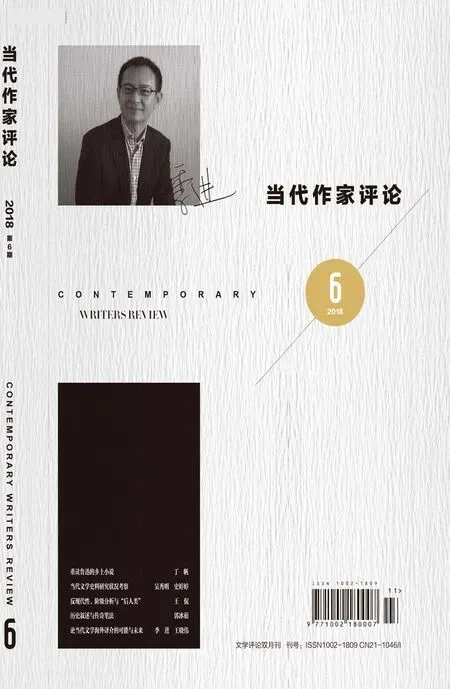诗歌报纸在1986年
贺嘉钰
对诗歌本体的阐释性研究、对诗人与流派的探源性描述以及对诗歌史的分段体察基本建构起新诗研究的骨骼,不同论者的审视角度与论述风格又逐渐丰满着新诗研究的血肉。但一个问题不容忽视:拥有话语资源的研究领域因为具有较高“可阐释性”始终热度不减,偏门冷门的领地却常年无人问津,长此以往,文学史的建构就有可能因为研究者的“有意规避”或“无意绕道”形成“坍塌性”硬伤。“诗歌报纸”或可位列其中。有关报刊的跨学科研究近年来颇为热闹,具体到一份报纸或一种报业现象,已有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但对诗歌报纸形成、发展与呈现的关注,还较为少见。
就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看,目前对当代诗歌报纸仍缺乏最基础的整理工作,有关诗歌报纸整体及个体化面貌的诸多基本信息依然空白,当代诗歌报纸的整体生态与存在状况在研究领域仍然未获关注。而诗歌报纸资料的获得与阅读更具难度,笔者在国家图书馆查找当年由安徽省文联主办、正式公开发行,在其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诗歌报》,也只能查到1984年9月创刊号至1985年全年,以及1989年全年报纸,无法窥其全貌。本文意图,在初级整理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以观察到的历史面貌和觉察到的问题对80年代诗歌生态的某一切面做尝试性解读,集中到1986年这一具体时段,力图呈现出一个时代段落里诗歌的丰富面貌。
之所以截取一个特定年份为考察对象,有两点考虑:一是1986年的转折意义与反映于诗坛的复杂状态使其具有深入探讨的价值,二是鉴于资料庞杂和个人能力有限。1986年之所以特殊,不仅表现为这一年集中创刊了几份有影响力的“诗歌质报”、发生了轰动诗坛的“1986年现代诗群体大展”事件,还表现为以此为节点,80年代诗歌再一次显示出更迭与分化。
一、1986年的诗歌现场与诗报生长
朦胧诗潮自身的渐退与后继者们入场的意愿共同滋养着诗歌领地的生长,“盛世”降临于1985年。散落在全国各处的文学青年以刊物为“据点”,渐渐编织起规模颇为庞大的诗歌网络。这张隐形、自由、充满弹性的“诗网”在自发生长的同时刺激并网罗更多爱诗者入场。“入场”是他们冲动的表达与实践方式,也是对“在场”的自我要求与期待。官方与民间,主流或小众,参差样貌的小诗场逐渐组构出“诗歌盛世”的一种模样。
(一)《中国》[注]《中国》筹办于1984年,创刊于1985年1月,终刊于1986年12月,共出刊18期。与1986年诗歌
文学刊物《中国》的出现、发展与停刊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曾聚集起一群“左派”,却以“激进的启蒙精神”、“新锐而富有朝气的个性”和对无名后生的“倾心扶掖”,对“那些将文学视为生命体验的作品的推崇与鼓励——而给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象”。笔者此处只探讨1986年它与诗歌的一些交集。
自1986年,《中国》每期封二位置都刊出一首诗歌,而诗作者往往还不为人知。“它们是我们从读者来稿中选出来的,在这个显著的位置上,刊登这些正在成长的文学爱好者的诗歌比刊登那些有名气的或老前辈的诗歌或名言要有意义,当然比刊登广告更有价值,这是我的建议。《中国》一向重视对年轻人的扶植和发现新作者。我曾在《中国》与部分地方文学期刊联谊会上的发言中说过:我感到这些年轻的作家和诗人是许多老作家无法比拟的,他们身上体现着中国文学的可以预见的希望。对我们来说,就应该责无旁贷地为他们提供创作的条件和机会。”
除了封二显著位置的奖掖,1986年第1期始,刊内固定刊出青年诗人诗作,配以“编者的话”解读,笔者所见包括1986年1月至8月、11月、12月几期。《中国》1986年第2期于2月18日出刊,牛汉、冯夏熊“编者的话”中介绍了对“新生的诗”的关注:“不完全是因为巧合,本刊上一期的全部作品,都是青年人写的,他们中的年龄最大的不超过三十四岁。这一期的主要作品仍然是年轻人写的。……我们注重发表新诗领域中新生的诗,还将发表更新一代的新诗。”3月18日,第3期刊有牛汉诗论《诗的新生代——读稿随想》,他将80年代青年诗人的投身热情评价至一个新高度:“诗的时间概念是飞速的。今天这一代新诗人,不是十个、八个、几十个(像‘五四’白话诗时期和‘四五’运动之后那一段时期),而成百上千地奔涌进了坑坑洼洼的诗歌领域。即使头脑迟钝的人也会承认这是我国新诗有史以来最为壮观的势态。这个新生代的诗潮,并没有大喊大叫,横冲直冲〔撞〕,而是默默地扎扎实实地在耕耘,平平静静、充满信心地向前奔涌着。”是否“最为壮观”还有待历史的检视,但新生代诗人所昭示的群体性真诚与诗歌耐磨度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
《中国》对青年诗人的持续关注与扶持是一种眼光的体现,这与副主编牛汉本人的诗人身份不无关系,“进入新时期以来,诗歌创作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我们感觉到:继北岛和舒婷等新诗人之后,诗歌领域又出现了更为年轻的‘新生代’。本期发了十位作者的诗作,目的在于表明我们对于这‘新生代’出现的喜悦和支持,我们希望大家也予以关注”。在推介作为“群体”的这一新生代诗人之外,《中国》的编辑还沉潜入作品内部,以细致精微的审美感受给予这些年轻诗人诗作富有张力且真诚的评介:“又来了一群年轻可能也是陌生的诗人,于荣建、刘晓波、柯平……他们从城市来,带来中国最前沿的城市意识,有一切焦灼、困倦、神秘、荒诞的感受构成的审美心态。他们触到城市的每一个细节,每一根敏感的神经末梢,既有痛感又有快感,他们既能抒情又会嚎叫!中国的城市诗虽未成气候,自有其原因,但所谓成熟不一定就是好诗,不成熟则预示发展。”阶段性展示之后,也会进行回顾与反思:“新生代的诗已形成强大的势头。一代诗人正在崛起。包括本期在内我们连续推出他们的作品。新生的是稚嫩的,富有生命力的。这些作品中体现出的深度与力度,显示了他们的顽强与自信。”
至1986年12月18日《中国》1986年第12期终刊,《中国》对新生代诗歌给予了“很高的礼赞”,认为新生代诗歌的范畴冲破了朦胧诗所生发的“小圈子”,以不可阻挡的势头在全国各地生长起来。也正是80年代自身的“气场”,形成了诗场得以开疆拓土的氛围,正是80年代自身的创造力与吸附力,为诗歌生长与遭遇的各种可能性提供了契机与环境。
(二)1986年的诗报诗刊
如果说诗歌书籍的出版是对前期的总结与检视,那么以诗报诗刊为主体的现在时记录则取消时间的延滞,更“逼真”地呈现出诗场即刻的发生与关注所在。
1986年6月6日,《诗歌报》第42期刊出“崛起的诗群”专版。在翟永明的诗前登有《诗之我见》:“正如我不久前写到过:‘诗作为一种暗示贯注我全身’,我希望我内心的语言和我的诗的语言最终融为一体,并使我面对现代世界更加深思熟虑。”个体态度的累积或可聚合为时代的气场,从翟永明的表述中可见,一些诗人对待诗歌态度真诚,将诗歌创作视为勾连心灵的通道而非一种单纯“手艺”的训练。一种理想的诗场氛围是:诗人内向地深掘拓展诗歌的可能,公共媒体外向地敞开提供展示的平台,这两点在80年代的诗歌场域实现过一些真诚的互动。在1986年第7期《当代诗歌》中,编者专门发文《设“新诗潮”专栏以来》表明立场:“我们想:当代中国诗歌是多元的,既有当代现实主义的,也有当代现代主义的。大圈圈里套着小圈圈,小圈圈里又满是骚动的‘点儿’。既然面对着多元化的诗歌态势,《当代诗歌》理应呈现这态势。为此,我们不想关闭这个窗口。”《诗刊》也在1986年7月号上首次刊出“大学生诗座”专栏,《飞天》杂志设有“大学生诗苑”栏目。
9月30日,《深圳青年报·两界河》副刊刊出“86’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大展”预告。10月21日,“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第一辑)”在《诗歌报》第51期第2版、第3版上刊出,第二辑在《深圳青年报》第2版、第3版上刊出。10月24日,第三辑在《深圳青年报》第2版、第3版、第4版上刊出。《星星》诗刊1986年11月号“中国诗歌社团诗选专号”中刊出的《中国诗歌社团诗选专号编辑小记》上记载:“中国究竟有多少诗歌社团,谁也说不清楚。估计是三百至五百个之间吧。”
《诗刊》1986年9月号卷首语上有这样一段值得揣摩的表达:“本刊8月号发表了《关于设立文化大革命国耻日的建议》和《天安门广场》受到读者注意,这期我们又推出了张志民的长诗《梦的自白》。它以直朴的语言,写得真实到令人颤栗的程度,相信会引起当代人的沉重反思,为什么这样的诗在十年后才出现,恐怕也正是改革所带来的宽松气氛的结果。这种宽松使得人能纵深地思考历史和现实,也给了诗人敢于正面抒写的勇气。”作为最具权威性的国家级诗歌刊物,《诗刊》在传播优质诗歌的同时还发挥着身份性文艺导向功用,诗歌的发表与点评的偏向,特别是卷首语的表达,与现实社会的情绪往往保持一种密切关系。
撷取诗报诗刊1986年进程中几个片段来观察,笔者有四点感悟:一是个体书写的真诚与努力是80年代诗场蓬勃的原动力;二是官方诗媒的敞开与提携为新人进入诗场和受到公众关注提供平台;三是基于诗场自身资源,媒体的自我策划与造势“合谋”了80年代诗歌在整个文学场的风生水起;四是在时代个性与社会氛围的浸润中,“文化场”、“诗歌场”所抵达的开放自由程度让诗人有“条件”创作具有“经典”品格的作品。
(三)对几份1986年创刊诗报的观察
以“创刊”为遴选条件,笔者试将研究样本锚定在创刊于此年的部分诗报上。与只是“存在”相比,“创刊”的标志性与时间性更为突出,可视为1986年诗报存在中“凸起”的骨节。以笔者所见为样本,以期纵深地进入,从中清理出一种可能的观察路径。
1.有关16份创刊诗报的基本信息:

报刊名称创刊时间创刊地点主编备 注文学创造1月武汉谷未黄编辑:王家新、王建浙、王大鹏、方方、马竹、邓一光、古远清、刘富道、刘益善、舟恒划、谷未黄、陈应松、邹建军、周忠良、洪烛、南野、胡发云、郭良原、饶庆年、赵国泰、高伐林、徐鲁、雪村、程光炜、董宏猷、董宏量、楚良、鄢元平、熊召政、管用和出版:由武汉市汉南区文化馆中国大学生诗报1月福州邵长武沈雯雷主办:中国大学生诗协诗中国2月武汉熊召政饶庆年编辑:江苏省南通市诗歌学会苏中青年诗社《青年诗作》编辑部、南通市苏中青年诗社联谊会青年诗作2月南通徐泽曹剑任编委:曹剑、徐泽、万川、葛洪、顾耀东、海燕、杨建、郁斌、王彬彬、顾来红顾问:牛汉、公刘、夏阳、沙白、张松林、曾卓、丁芒、忆明珠、朱先树、马绪英、邓海南、陈敬容、朱红、赵恺、王辽生、黄东成、潘洗尘、冯新民备注:江苏第一家青年诗报*中国当代诗歌报3月四川王琪博尚仲敏编委:徐梅、肖红、王琪博、卢泽明、李明、夏阳、杨涌、尚仲敏
* 《青年诗作》创刊号标注。
续表:

报刊名称创刊时间创刊地点主编备 注中学生校园诗报3月大兴安岭姜红伟顾问:臧克家、张志民备注:创刊号发行16000份,其他两期共计发行八千份。发表了21个省、自治区的94位中学生诗歌作品100余首*非非评论8月西昌周伦佑主办: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现代文学信息研究室备注:5月,《非非》杂志出刊,为“非非主义”诗歌运动内部交流资料之一松花江诗报10月松花江于金廷副主编:于富、战林、柘子编委:于金廷、于富、王昭全、孙玮、李锡洪、宋永学、季家骧、战林、柘子顾问:胡昭、阿红、芦萍、上官缨报头题字:胡昭诗10月福州福建《诗》报编委会编编委:蔡其矫、舒婷、孙绍振、刘登翰、田家鹏、蒋庆丰、王性初、宋瑜、廖一鸣、林祁、陈志华、苏小玲、李闽山、缪又凌、王欣报头题字:陈奋武存在客观主义诗歌资料10月南阳编辑:中国现代诗歌信息交流中心中国高校诗报11月淮北宁敬张佑兵编辑:郭传火、潘小平、刘海洋、易海明、山风美编:罡夫主办:淮北煤炭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会中国诗人11月重庆夏阳燕晓冬编委:王琪博、楼刚、卢泽明、何芝琼、燕晓冬、夏阳主办:现代派诗歌研究学会赞助单位:楚天业余诗人协会、拉萨晚报社、香港新穗出版社、重庆青年翻译出版公司、重庆环球轮船公司赞助人:熊衍东、洋滔、陈煦堂、肯斯勒、王德川中国诗歌天体星团11月备注:刊有黄翔《狂饮不醉的兽形———“诗学选集”断章》和哑默长诗《飘散的土地》节选等存在客观主义诗歌导报12月南阳皮客主办:河南省现代诗歌信息交流中心、存在客观主义诗歌研究中心备注:刊有《存在客观主义诗歌第一号公告》世纪末诗人12月开封孔令更副主编:齐遂林、李锐锋编委:孔令更、尹清轶、齐遂林、李锐锋、杨超、陆健、易殿选、郎毛、周保生、徐勤、常崇光、程光炜、墨桅主办:河南青年诗歌学会开封分会顾问:公刘、苏金伞、青勃、舒婷
* 姜红伟:《“改革开放30年中国民间诗歌报刊备忘”民刊收藏家系列访谈录之姜红伟篇》:“创刊号发行一万六千份,其他两期共计发行八千份。发表了21个省、自治区的94位中学生诗歌作品100余首。”,引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10c6890100cnr5.html。
2.试析诗报的基本特征与属性
作为媒体,无论影响力大小,“存在”即是对公共文化空间的进入,对诗人而言,无论“场”的大小,发表作品即是“在场”。由于缺乏必要的训练与自觉,对“诗报”本身界定的不清晰,专凭诗人(或称诗报人)对诗歌热忱的“非制度性”因素,诗报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与复杂程度大大增加,一些诗报还显现出狭窄、稀薄,甚至局促的面貌,在呈现丰富与自由的同时造成一种乱象。
1)诗报基本特征
尽管以“报纸”这一媒介形式为承载,但诗报所表现出的时效层面的“非及时性”、传播内容方面的“非信息性”、受众层面的“非大众性”、发行数量层面的“有限性”、经营层面的“非盈利性”、社会影响方面的“小众性”等,似乎对普遍意义上的报纸特征表现出全方位的“颠覆”。同时,在自我预期与成品展现上,诗报还往往表现出一种“断裂”,由于众多诗报都逃避不出“短命”这一显性宿命,发刊词的阔大与现实诗报格局的狭窄便形成一种鲜明的反观对照。
2)诗报属性
就自觉生长而拥有的属性看,创刊与存在于80年代的大部分诗报都体现出“青年性”、“自发性”、“起步性”、“地域性”、“非职业性”、“非制度性”、“非盈利性”、“圈子化”与一定程度的“江湖”气质。
以笔者所见“1986年创刊诗报”为样本,16份诗报中:《中国大学生诗报》《中国当代诗歌报》《中学生校园诗报》《中国高校诗报》《存在客观主义诗歌导报》《中外诗歌交流与研究》均依托于高校或以校园为背景创办,《诗中国》《世纪末诗人》的编辑成员均有当地青年诗歌学会的参与,大多数诗报的主编与编辑由高校学生担任。正由于大多数办报人“经营”诗报为一项“副业”,诗报也因此处在“不独立”、“边缘化”的地位。由于诗报主办者往往就是诗人,而“诗人”身份的非独立性影响着诗报存在的非独立,笔者欲将此定义为“非制度性”,即缺少某种制度化的保障与约束力整饬诗报内部事务,使其免于频繁的人为与人事因素干扰而保证诗报正常印行出版的条件。但诗报的创办常常是一个诗人或一个诗歌小圈子的“冲动”行为,即便“缔结”共同认可的章程,也由于群体与追求本身的自由而不具强制性。
在“非盈利性”方面,以经费来源为例,一般谁出资谁就会影响报纸性质与办报方针。一部分诗人所拥有的天然追求“民间”的心态使其对官方资助抱持自觉的疏离甚至抵制,诗报上基本鲜见广告,笔者猜测原因有二:一是办报人不求广告,以保证报纸的纯文学性;但更有可能的是无广告青睐投放于诗报,毕竟诗报受众有限。若无官方资金注入,诗报一般会呈现出“小规模”、“少资金”与“短存在”的现实状态,这导致了诗报的创办与停刊此起彼伏、旋生旋灭的生存状态。但是,一味将历史分类归纳其实是一种简化,我们不能忽视偶然性因素在其间发挥的作用。
在“报纸”与“诗歌”之间,本身就存在一种“悖论”关系。通常而言,报纸“过日即废”,但诗歌却具有应被反复琢磨与思索的质地,对与时间保持紧张关系的报纸而言,诗歌更体现出对时间的消解甚至取消。应该说,用报纸表达诗歌是一种“形式”上的错位与背离,但诗报为何会如此广博地存在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出版报纸相较于书籍刊物,经济成本低廉,这对于大多数缺乏资金支持的诗报创办者应是最实际的影响因素;再者,“报纸”在出版物中比较“易成”、“入门”,在设计排版上拥有更自由的发挥空间,且更易被赋予一些“江湖气”,容易短时间形成特定“氛围”,更易吸引想要进入“诗场”的初级选手,对他们而言,发表就是意义,作品的留存似乎还未进入考量。同时,一部分诗歌实践者在经历过“诗报”、“诗刊”、“诗集”等多种出版形式后,当反思作为出版“初试”的诗报,会认同在创办经验的累积中为日后更“长存”形式的诗歌出版物打下了坚实底基。无意中,“办报”的经历成为具有深刻影响性的中间过程。不仅在于围绕诗报所形成的诗歌圈、生长于诗报的诗歌场,办报过程中约稿、组稿、编辑、印刷、出版等细节工作增益着直接着手刊物与书籍创办的诗歌实践者无法接触并内化的诗歌训练。诗报作为“中间过程”,它的存在价值可能更多并不体现于“展示”,而是提供了创办者与诗人快速进入诗歌场域的“途径”,给予了他们“在场”的心态,将其实质性地结构进公共诗歌领域。报纸天然的引导舆论与造势功能将诗歌场具体化,落实在一份可观可感的报纸之上,为“在场”留下证据的同时将生长出更为自觉的诗歌出版面貌。
当前,关于学习平台的研究层出不穷,商业化的直播APP也数见不鲜,但从零开始搭建起一个个性化的班级甚至校本使用的移动学习平台仍旧需要克服很多的技术难点。本研究主要基于当前云技术的发展情况下,利用各大运营商提供的公共云云服务平台,如何快速地搭建一个属于学校或班级私有的移动微课直播平台。随着研究的深入,用户还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在系统中集成更多插件和功能,搭建出个性化的微课直播平台,帮助教师更加高效地开展教学活动。■
3)诗报的“合法化”策略
在整个社会文化氛围开放活跃、诗歌场域热闹积极的80年代,年轻人的集合活动常常自赋使命。在进入官方话语体系受阻、民间大规模的同质化存在又将导致被遮蔽等多重因素挤压下,寻找“权威性”与“创新点”,成为诗报“合法性”的有效支撑。此时,以高校文学社为主办支持或挂靠当地文联、诗歌协会,邀请著名诗人担任诗报顾问、编委,请知名书法家为诗报报头题字,成为了底层诗报“入场”自寻“合法性”的主要方式。仍以16份1986年创刊诗报为例,除前面谈到的6份诗报具有校园背景,《文学创造》由武汉市汉南区文化馆出版,整个80年代及其后依托于当地文化馆建设的诗报不胜枚举。
在诗报内容之外,“名人”出场往往是报纸获得权威认可的重要砝码,但顾问、编委的效用往往止步于名气的借挂,并不会对报纸内容本身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在笔者统计的1986年创刊诗报中,《青年诗作》的顾问有牛汉、公刘、夏阳、沙白、张松林、曾卓、丁芒、忆明珠、朱先树、马绪英、邓海南、陈敬容、朱红、赵恺、王辽生、黄东成、潘洗尘、冯新民等;《中学生校园诗报》的顾问有臧克家、张志民;《世纪末诗人》的顾问有公刘、苏金伞、青勃、舒婷。
“归来”诗人基于在诗坛的威望作为权威的代表以顾问、编委的身份被编织进诗报的“影响结构”,诗报创办者在这里采取“诉诸权威”的传播手法,而权威在诗报中的真正地位却是非常边缘化的。虽然代际之间的诗歌追求、诗意表现已大为不同,但诗坛似乎历来认可老诗人对新诗人的举荐。
由于1988年以前,我国的报刊刊号未做统一规定,各省市、自治区以及直辖市的报刊出版管理仍由当地宣传部门负责管理,故对报刊刊号的研究梳理未进入笔者考察范围。
二、诗歌报纸的显在与隐在:从“1986诗歌大展”谈开
1986年,一次衍生于报纸的事件完成了被诗歌史铭记的“井喷”式能量释放——“86’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大展”,这年10月由《深圳青年报》与《诗歌报》联合推出。
1986年9月30日,《深圳青年报》刊出由徐敬亚执笔的大展公告,宣布《深圳青年报》、安徽《诗歌报》将于10月隆重推出新中国现代诗历史上第一次规模空前的断代宏观展示,并提出三点举办“大展”的合法性依据:一是从新诗扮演了民族意识演进探索先锋的视角,回顾与呈现1976年至1986年中国与“新时期文学”如何还原和再生了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二是反思朦胧诗“大论战”本身的丰富深邃而历史记录的贫瘠匮乏,所产生出保留现时诗歌现场的冲动;三是基于展现“后崛起”诗群所形成的艺术与出版繁荣所怀带的欣喜与焦灼。1986年10月21日,安徽《诗歌报》大展第一辑展示诗群20家,同日,《深圳青年报》大展第二辑展示诗群23家,10月24日,《深圳青年报》大展第三辑展示诗群22家。“‘大展’是中国新诗出现以来,第一次如此集中地把青年诗人集合在现代主义旗帜下的壮举,也是上个世纪末中国诗坛最有价值的活动盛事,它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一个多元化的阶段。”
报纸发行量是其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此,大展策划者徐敬亚回忆:“至当年末,总订数已达到15万份!”“非非”诗人杨黎也谈及《诗歌报》“发行在十万份左右”。
在朦胧诗诉诸政治且追求语言革新之后,“崇高和庄严必须用非崇高和非庄严来否定——‘反英雄’和‘反意象’就成为后崛起诗群的两大标志”。“后来者开始轻率地否定新诗潮的经验”,“革命性迫使有些人必须要灭掉先行者的背影,以便‘替代’得更合情合理一些”。于是,大展将“两反”以集体面目推到了历史的前端。然而,此次狂欢的单薄化与盛世景观的自我命名“嫌疑”使这一集体亮相在历史的反思中收割了赞誉,也招致了诟病。例如就有徐敬亚在《中国诗歌流派2011宣言》中的表述——“中国现代诗‘86大展’,冲决了一统天下的诗坛格局,打破了中国人对艺术集结的传统恐惧,促成了第三代诗人群体式登上诗歌舞台的历史转化。从社会学的意义认定,‘86大展’是一次中国人在诗歌范围内自由结社的经典范例”与“六十几块尿布膨胀式的自我欢呼”这样的两极对照的评价。
(一)两份报纸与“大展”的因缘
纵观当事人与学界回忆与讨论,争锋大多聚焦于此次大展在诗歌史的开拓意义,而鲜有从“报纸”与“诗歌”,“媒介”与“内容”的角度对“大展”进行的解读。笔者无意从其诗歌史意义做深入评判,而更倾向于探索此次“诗歌事件”与传播媒介之间存在的或许偶然或许必然的联系。
“大展”得以举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80年代诗歌的“土壤”与“果实”客观上提供了可供展示之内容,“至1986年7月,全国已出的非正式打印诗集达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其中,以四川‘非非主义’为代表的诗歌探索群体,已向体系化、流派化方向发展。1986年9月在兰州召开的‘全国诗歌理论讨论会’上,无论是自囿于沉寂原序的中老年批评家,还是呈挑战者姿态的青年理论者,都对纷纭庞大的诗坛现断面,发出了驾驭的困惑。”而考虑“大展”为何由这两份报纸连袂举办,就不能忽视人为的“偶然性”因素。
《深圳青年报》为共青团深圳市委员会的机关报,创刊于1984年2月2日。这一份着重特区经济、政治改革的报纸在展现城市青年精神面貌的同时积极推进并传播文化。《深圳青年报》设有“短波发射台”、“记者来信”、“周五特写”、“名人说世态”、“警世录”、“体坛纵横”、“人·岁月·生活”、“内地人看深圳”、“海外趣闻”、“缤纷世界”等栏目。每周二、五出版,公开发行。
1983年,徐敬亚发表于《当代文艺思潮》的《崛起的诗群》作为“三个崛起”之一,引发了中国文坛一场大震动,并经历了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浪潮。1985年,徐敬亚南下,任《深圳青年报》副刊部编辑,而作为诗人、诗评家的他与其时诗坛也保持着亲近的关系。他常常收到诗友寄自全国各地的诗集、诗报、诗刊。“应该有一个实体的呈现,来代替人们茫然的思考和谈论”,基于对诗坛整体风貌的判断与预感,徐敬亚意识到新诗需要整体地向诗坛展示发展的成果并着手落实。1986年7月5日,徐敬亚向全国几十位诗歌朋友发出名为“我的邀请·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的信,告知他欲在《深圳青年报》副刊上举办一次“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或称“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雏展”的整版专辑。对于徐敬亚此举,时任《深圳青年报》总编辑的刘红军、副总编辑曹长青给予极大的赞同与支持。为了落实版面,徐敬亚与安徽《诗歌报》主编蒋维扬和编辑姜诗元商议共办“大展”一事,《诗歌报》欣然应邀。此次“大展”得以举办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核心人物的组织与动员能力。
(二)诗歌对报纸功能的有意搭乘
无论发表作品,还是推动诗歌事件,“办报”是一种相对低成本易操作,甚至带有艺术化的行为实践,同时契合一部分诗人通过将私人行动链接进入公共空间,实现对诗歌圈内某种话语权占领的愿望。
将“86’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大展”视为一次“诗歌事件”,“大展”操办者在“地利”优势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报纸特性,扩大了影响。
1.形成引导诗歌事件的“舆论流”
首先,传播媒介共有的天然属性——制造舆论、引导舆论的功能伴随信息的送达过程常常作用显著,特别是当其具有官方认可的“合法”背景,或恰好在此对立面时,就更有可能在大范围内实现“舆论”的抵达。就1986年“大展”而言,《深圳青年报》与《诗歌报》本身就拥有庞大而稳定的诗歌读者市场,在传播平台与受众参与度的双重保障下,“舆论流”的形成与流动完成了对大展的“造势”。
从传播学进入,1986年“大展”作为传播事件也具有诸多可探讨之处,以时间节点来呈现诗歌的信息传播模式与舆论体系过程将是一次有意义的探索性研究,对具体历史细节的打捞将组构起“大展”如何组织、如何动员、如何发展,又在何种程度上完成了“神话”这一完满的过程。笔者在此提出这一进入问题的视角,而结论还需建立在确凿的数据基础上由命名衍生出的诗歌“大展”范式。
“86’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大展”广泛与深远影响力的又一表现是,其后诸多发表于报纸的诗歌登展都选择以“大展”定名。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其后以“大展”为名称的诗歌展示活动就包括:“1988年中国首届高校诗人诗歌大展”、由《新诗报》举办的“中国新诗1988:内蒙古青年诗人群体大展”、《大陆诗报》于“1989年春·创刊号”推出的“江西青年诗人现代诗大展”、《锋刃》于1993年9月30日登载的“中国民间先锋诗群实力大展(第一辑)”、《浣花》于1993年推出的“中国现代诗大展诗专号第一辑”、《江南诗报(浙)》于总第20期1997钢铁号第三版推出的“青年诗人陈超作品大展”等。
“86大展”之后,这一命名似乎得到规约,无论登展规模何如,都会冠以“大展”的头衔。而“86’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大展”之前,笔者却未见诗歌展示活动如此表述。尽管“86’大展”是否真正为命名的滥觞无法确切考证,但它的存在一定大大拓展了这一命名的流通性,并使“大展”的表述与诗歌产生某种亲近的联结。
在此,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徐敬亚在“大展”的邀请信中曾明确提起过此次活动的名称为“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或“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雏展”,现实征用中,举办者选择“大展”弃用“雏展”,或可视为一种微妙的取舍,从命名上就自我赋予某种强势心态。
小到一张具体诗报,大到八九十年代蔚为大观的诗报生态,是诗报的“显在”;诗报背后的人缘网络、诗报之上的诗意追求以及诗歌对报纸功能有意无意的“搭乘”,则都可归为诗报的“隐在”。“隐在”是根,是原因,“显在”是根部以上的茎叶和果,是表现。
当对所掌握到的诗报做细读与梳理后,会不由得产生一个疑问:出版发行如此活跃、整体数量如此众多、地域散布如此广泛的当代诗歌报纸,为什么大多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为什么诗歌报纸在诗歌史中几乎不占席位?这一“缺项”的客观原因可能包含三点:一是选题缺乏研究价值,二是研究者仍未探寻到其学术支点,但更有可能的原因是,诗歌报纸全貌史料的难以获取造成了研究缺位的天然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