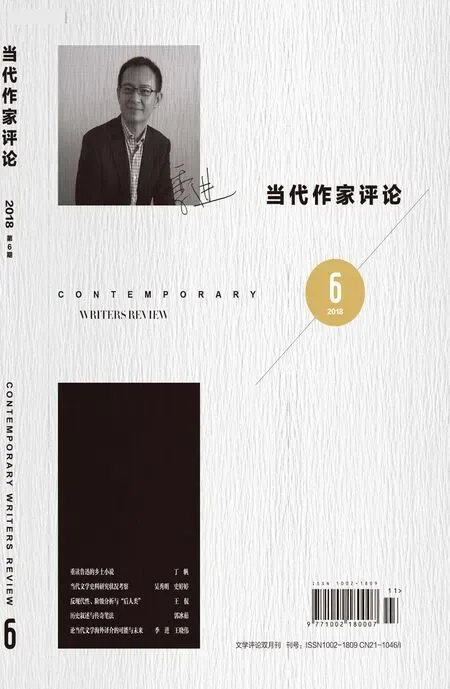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中的乡村想象
——论《皖北大地》兼及乡土小说的新可能性
彭正生 方维保
一、引论:乡土小说的现实情境与新可能性
从鲁迅的《故乡》开始算起,中国乡土小说的历史已然百年。总览百年乡土小说的发展历程,其中最突出的现象是乡土小说与时代演进的共振与互动关系,具有极其鲜明的历史参与意识和人文关怀精神,这主要表现在:特定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和人的精神变化会深刻影响并改变乡土小说的风貌,乡土小说的演化也反映和折射着政治、经济、文化和人的精神的时代面貌与历史表情。比如,20世纪20年代,鲁迅及其影响下的乡土写实派小说家,怀着对民族觉醒和文化复兴的期望,在启蒙现代性思潮感召下,关注并剖析乡土中国的衰颓景象和国民精神的黯淡世界。30年代,沈从文和“京派”小说家以审美现代性目光凝视乡土世界,他们吟唱的是对传统中国的怀想与眷念之情,包蕴着浓厚的古典人文情怀,始终保持着远离激进时代风潮的姿态。40年代到70年代,古老的乡村不再是沉睡、沉默的土地,它是革命精神的发源地,也是革命与反革命力量话语权的角力场,在革命现代性思想的召唤下,周立波、丁玲和革命作家们的乡土小说成为革命合理性和胜利必然性的文本象征载体。80到90年代,在改革现代性话语的洗礼中,路遥、贾平凹等人的乡土小说一方面寄托着对乡土中国在改革中完成蜕变和新生的积极期待与想象,另一方面又表达出在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社会和乡土文明遭遇的挑战与困境、隐痛与忧思。
一般来说,从历时性维度来透视和概括创作主体与创作对象的关系,以及小说家处理乡土题材的视角立点与思维方式,20世纪乡土小说大致表现为启蒙现代性、审美现代性、革命现代性和改革现代性四种形式,并由此显现出不同的思想观念、情感姿态与价值立场。而从共时性维度来看,20世纪乡土小说的潜在结构表现为现代性/反现代性的矛盾意识,显在的文本形态则表现为城市/乡村的对立模式,正是在这种二元观念影响下,那些现代性文本里的乡土世界代表着不堪回首的历史遗存,现代化的都市代表着令人憧憬的文明未来;而反思现代性文本中的乡土世界象征着人类曾经美好的“伊甸园”,城市社会则似乎是堕落无望的“索多玛”。
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结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在加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发生着相较于既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为深刻的变化,乡土小说的创作也一改90年代的萧条局面,迈进又一个新的收获时期。尤其近年来,一批有影响的作品相继发表,颇有乡土小说再度繁荣之气象。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尽管乡土题材的小说对农村社会、农业现状和农民生活进行了多方面表现与思考,但是在总体上没有超越和突破既往乡土小说的视野、思维和境界。面对正在发生的史无前例的伟大变化,以及城乡日趋同化与融合的崭新时代面貌,小说家们似乎仍然在现代性/反现代性的二元对立框架内来思考与书写,从而使乡土小说陷入千篇一面的重复之嫌。难怪有学者表示出对乡土小说的不满,甚至断言“乡土小说面临终结”。
不可否认,虽然农村的面貌、农业的观念和农民的生活必将随着时代的改变而发生深刻变化,但是在可预见的较长时期内,农业仍将会是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社群仍将在历史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作为稳固社会形态之重要构成的农村社会也不可能消失。只要乡土世界不会消失,乡土文学就不会消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乡土小说面临终结”实际上是一个“杞人之忧”的伪命题。真正有意义的新课题是:如何书写出新时代农村社会的现实与真实,探索乡土文学的表现形式,拓展乡土文学的审美视域。因此可以说,乡土文学不是面临着终结,而是充满了新的可能性。
二、新时代的乡土景观,以及第五种类型的乡村形象
谈到《皖北大地》的创作动机,苗秀侠坦言这部源自挂职经历的小说,意在“书写土地”,反映“中国农村发生的大变化”,表达“现实乡村的另一面”。尽管这样的自我言说不乏宣传意味,但是对于一位拥有扎实的写作经验且专注乡土叙事的优秀小说家来说,也至少表达了一种自觉意识、价值取向和叙事雄心。同样,这样的自我言说所透露出来的自信心似乎也表明,苗秀侠已经意识到中国农村社会正处于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并及时地捕捉到了中国农村社会的改革趋势,敏锐地洞察到了新时代农村旧貌换新颜的变化实质,因此,她要通过《皖北大地》描绘一幅完全不同于既往乡土小说的乡土景观,展现一个迥异于既往的乡村形象,以探索乡土小说表现的新空间、新领域。
乡土小说中的乡村形象,本质上是小说家的文学想象,既是小说家思想观念、情感方式与价值立场的形象载体,也是时代影像、历史面孔与社会心态的话语符号。有论者曾将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划分成“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主义”和“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两种类型,并相应地用“落后”“愚昧”“野蛮”与“唯美”“诗意”“和谐”来概括两种不同的乡村形象。不过,这种结论显然是片面的、以偏概全的。细致考察百年乡土文学的发展历史,笔者发现,小说家主要描绘和提供了“生死场”、“桃花源”、“角力场”和“空心村”四种不同类型的乡村形象。具体来说,第一种类型是启蒙现代性视角下的村庄形象,其代表主要有鲁迅小说中的“鲁镇”(《祝福》)与“未庄”(《阿Q正传》),以及乡土写实派小说家笔下的皖西、浙东等村庄。此类文学村庄的出现与五四思想革命与文化批判的启蒙话语语境密切相关,它们落后、封闭、破败,是命运轮回、希望微茫的“生死场”。第二种类型是审美现代性视野中的乡村形象,其代表主要有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茶峒”(《边城》)、废名笔下的“陶家村”(《菱荡》)等。此类文学村庄的产生则与反思现代性价值观与都市文明,张扬生命精神的文化观念紧密联系,它们自然、优美、宁静,是理想的、与世隔绝的“桃花源”。第三种类型是革命意识形态视角下的乡村形象,它们主要存在于延安时期到十七年时期的“红色经典”和革命文本,其代表有周立波笔下的“元茂屯”(《暴风骤雨》)、柳青笔下的“下堡村”(《创业史》)等。这些文学村庄所承载的是以政治意识形态话语规范来塑造和想象乡村的使命,它们是革命与反革命、先进与反动力量斗争的“角力场”。第四种类型是改革与时代转型中的乡村形象,它们是小说家对改革以来加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境遇的文学想象。这些村庄是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日趋凋敝、衰败的“空心村”或“荒村”形象,显示出小说家对乡村命运的关切,正如贾平凹所言,“我关注的是城市怎样肥大了而农村怎样凋敝着,关注的是农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同时也抒发了他们对乡村消逝和乡土文明消亡的担忧之情。于是,人们自然会追问:乡村的未来与出路究竟何在?
《皖北大地》中的安大营村是一个崭新的乡村形象,它的主要特点可以用“四新”来进行概括,即:新的大农业观念,新的土地经营模式,新的现代农民形象和新的生态居住环境。首先是新的大农业观念,它的内涵是农民已不再固守单纯粮食作物种植和家禽粗放养殖的传统农业观念,而是自觉秉持和遵循“种植、养殖业的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和“现代农业联合体”,以“循环农业”为核心的大农业观念,坚持走集约型、科技化和可持续的现代农业之路。其次是新的土地经营模式,它的要义是通过积极探索与尝试土地流转、集中生产的方式,在不改变现有土地制度和所有权结构的前提下,激活农业生产力,提高土地贡献率,增加农民收益和改革获得感。再次是新的现代农民形象,小说塑造了安玉枫、杨二香等具有革新精神、创新意识和现代思维的新型农民,他们开放、进取,也更有自信、更有魄力。他们不再是土地的奴隶,而是土地的主人,是一群“直立行走”在乡村大地上的现代农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论者准确地指出,《皖北大地》重新建构了“中国现代农民的主体性”。最后是新的生态居住环境,安大营村已经不再是一个被城市挤压、匍匐在都市面前凋敝的灰头土脸形象,而是一个生态和谐、风景迷人又充满了生机活力的新农村。在这里,“湖中有亭,水里有鱼。烂泥坑样的南湖,成了一个景观湖。”所以,在乡土小说的乡村形象谱系与流变的图谱上,《皖北大地》的意义在于为我们创造出了新的乡村形象——新时代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城乡融合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形象。它不再局限于现代性/反现代性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也不再强化与凸显城市/农村两种生存空间和文明形态的矛盾与冲突,而是抹平它们之间的差异因素,表现为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形象。
可能有人会说,这样的乡土想象多少带有虚拟现实的意味,不过毫无疑问,小说家也是清醒的。小说中,苗秀侠同样理性地面对土地上发生的一切,冷静地凝视并书写着安大营村仍然存在的痼疾与新伤。在安玉枫的归乡途中,其目之所见的是大量抛荒的土地,在他的印象中,安刘河镇就像“一片荒凉的麦子地,一堆发呆的老人脸,一溜溜没嘴没牙的大杨树”。同样,在这块土地上,还有刘东强这样靠欺骗、破坏和捣蛋为生之人,还有像跑反这样强占了别人土地却倒打一耙的无赖之徒,也还有像刘学习这样见利忘义、见风使舵的小人……此外,这里也仍然存在着逼婚、上访等令人沉痛的乡村隐疾和暗伤。凡此种种,皆显示出作家真诚的态度与直面现实的勇气。同样,可能有人也会质疑安大营村的真实性与普遍性,质疑它是否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实际上,小说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因此,小说家的文学想象也便天然具有恩格斯所说的“倾向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重要的是小说家在文本里关注、呈现与表达了什么。对于苗秀侠来说,乡村社会仍然存在诸种不理想现象,她也写出了这些“内心的冲突与忧伤”,但是,她有意识地虚化、弱化了现实乡村世界里的隐痛与暗疾,强化和突出了它的繁荣与美好;她把现代农村中的黯淡景象隐去,却凸显出它的明亮色彩。总而言之,她希望表达的是一种理想,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和升腾的情感。
如前所述,中国现代文学想象中的“村庄”形象,或是沉睡的土地,或是沉默的他者,或是阶级角力的生死场,或是时代转型的空心村。《皖北大地》值得赞许的地方在于,它提供了乡土文学想象中的第五种“村庄”形象,一个充满活力,朝气蓬勃的希望之地。苗秀侠超越了城乡对立、文明冲突、城乡割裂的固有理念,她建构起来的乡村已经不再是“血与泪”、“剑与火”的旧世界,而是城乡融合、工农商一体化的新世界。
三、乡土小说的结构模式与情感形式
任何在乡村世界诞生的生命个体,除非固守土地而终老,否则在其成长到死亡的人生旅程中,必然总是不断地出走与回归故乡。如果将乡土小说中的故乡视为一个原点性的地方,那么主人公在文本结尾的行动方向——尽管这种方向可能是自愿行为,也可能是被动行为——与故乡的关系,也必然呈现为“归来”或“离去”两种情形。具体表现在叙事结构上,便是还乡(归乡或返乡)与离乡两种结构模式。同时,对于所有从乡土世界启程跨入城市的知识分子,且又以乡土为对象进行创作的小说家,小说中人物的出走或回归行为所关涉的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物理位置变化,身体的腾挪与空间的转换总牵连着复杂的内心情感。而这种情感,大致不过非为“恋乡”,即为“怨乡”。恋乡文本里,故乡具有一种情感向心力,是情感的守望和归宿,承载着怀想和眷恋;怨乡文本里,故乡表现为一种情感离心力,是亟待告别和疏离的对象。当然,不论结构模式,还是情感形式,其所涵盖的乃是这个相对性标准之内的大部分乡土小说文本,而非绝对与机械。以情感形式为例,就像永不可能踏入同一条河流,没有人能在面对故乡的时候只产生单向度的情感,正如季红真在《白狗秋千架》中读出了莫言“恋乡与怨乡的双重情结”。
同样,通过认真梳理百年中国新文学史中的乡土小说,笔者发现,若按文本结构模式(返乡/离乡)与情感取向(原乡/怨乡)进行交叉组合,则这些作品可呈现为四种不同类型的文本形态。具体类型与典型文本图示如下:

图中,以故乡为空间和情感原点,横轴所标识的是人物/主人公与故乡的空间位置关系,其区分的是人物/主人公在文本结尾离开还是返回故乡,左向为返乡结构文本,右向则为离乡结构文本。纵轴所表示的是叙事者/隐含作者对故乡的情感立场与态度,其区分的是叙事者/隐含作者是亲近还是疏远故乡,向上为怨乡情结文本,向下则为恋乡情结文本。如此,就形成如图所示的四个象限、四种类型的小说及其典型性文本。
通过对四个象限、不同类型文本的分析,又可进一步发现:结构模式与情感形式并非彼此独立、相互分离,而是彼此联系、相互渗透。离乡或返乡不仅只是结构模式,它勾连着对故乡或厌倦或眷恋的情感。怨乡不意味必须离开故乡,恋乡也不必然定能返回故乡,情感形式与结构模式呈纠结状态。再往前一步,由表及里,由形式而至内容,四个象限与不同类型的区分又不仅仅是一种结构主义的形式研究,它实际更深入地区隔着小说家不同的立场、观念。以怨乡型的两类文本为例,《故乡》中的怨乡情感产生于鲁迅基于启蒙现代性视角审视乡土中国国民精神问题而获得的认知与思考,在故乡这一乡土中国的镜像里,他看到的是被传统文化与思想囚禁的心灵无光、精神黯淡的人们。而对于《人生》中的高加林来说,他不惜背负“丢了良心”之名决意离乡,却非因为他“鄙视农民”——路遥甚至还借由德顺爷赞美刘巧珍有一颗“金子一样的心”,而是他绝不想“像父亲一样一辈子做土地的主人”。他辜负了刘巧珍而选择了黄亚萍,与其说他选择的是一个人,毋宁说是选择了与农耕的乡土生活相对应的现代城市生活,以及与农民相对的市民身份。因此,他的怨乡情感非关乎故乡的文化与人的精神状况,而是源于乡土在改革现代性的想象图景中乃是经济落后、物质贫乏的象征。
同样,恋乡型的两类文本亦是如此。《丈夫》是沈从文不怎么受关注的一个短篇小说,在其压抑却余味流长的结尾中,丈夫终于还是带着妻子“回转乡下去了”。小说通篇笔墨节制又情感内敛,却写尽也写透了探望妻子的丈夫在“城里”所遭受的内心委屈和心理凌辱。但是,沈从文亦是清醒的,现实的乡土并非纯粹的乐土,它与文学的幻化想象不同,“自然越是平静,‘自然人’越显得悲哀”,他希望读者不要忽视“故事的清新”和“文字的朴实”背后“蕴藏的热情”和“隐伏的悲痛”。这里,可见沈从文恋乡情感的复杂状态,在理性层面,他并不单纯是反现代性的,也是反思乡土文明的;但是,在感性层面,他的情感天平却完全是失衡的,他将几乎全部的爱都给了“乡下人”和乡土世界。《大风》中的张文亮没有终点可以抵达的寻根之旅中,他的返乡行动与其说是在向精神故乡的漫游,不如说更像是一种文化凭吊仪式,在这个意义上,他执迷的恋乡情结所暗含着的恰是对正在消失的乡土中国的文明的感伤之情。
《皖北大地》讲述了两个归来者的返乡故事,其显性的叙事结构采用的是“返乡”模式。一个是农民农瓦房的返乡故事:天性喜爱种植庄稼的农瓦房与王彩芹青梅竹马、两情相悦,因家境贫寒而无力负担彩礼,只能选择私奔南方。王彩芹被安三虎夺走之后,农瓦房漂泊异乡,先后靠在城市的建筑工地、城郊的蔬菜大棚打工和看相算命谋生。源自对故乡和庄稼的执恋,他辗转回到大龙河湾,在安守信的帮助下实现承包土地种植庄稼的夙愿。另一个是商人安玉枫的返乡故事:青年时,他将好吃懒做的父亲赶走,独担养家重任,却遭遇养鸡鸡舍被烧、养鹅鹅被冻死以及女友与人偷情的打击,于是出走故乡。在城市,他先后做过贩卖蔬菜、皮鞋生意,并靠物流生意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但是,故乡却始终让他魂牵梦萦,他说服妻子温晓莉,返回家乡创建蔬菜种植合作社,创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克服水患、火灾和资金链断裂等危机,最终实现了他立志带领同乡科技致富、共同富裕的梦想。但是,苗秀侠显然并不满足于按照传统观念讲述老套的返乡故事,她志在写出别样的乡土小说。《皖北大地》虽亦属返乡型小说,但它并没有将对乡土的眷恋之情与对城市的厌倦情感对立,安玉枫甚至在城市也收获了同样精彩的人生。在此,苗秀侠显示了她的叙事雄心,她以更加包容、开放和自信的心态处理城市与乡村之关系,城市不是吞噬乡村的野兽,乡村也不是满目疮痍的废墟,乡村完全是与城市平等的自信形象。在《皖北大地》里,城市与乡村不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乡村与城市也不再是对立的文明形态,在安玉枫与村支书安云礼的畅想中,“农村变得像城里一样好看,一样方便”,也有敬老院、幼儿园、路灯、花木带和大电视幕墙等城市生活设施。于是,返乡不再是在城市遭遇失败后无可奈何的归返,恋乡既不因对城市的厌弃与憎恶,也不是对虚幻精神故乡的虚妄怀想。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问题的复杂性,或者说在面对乡村与城市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冷静与理性,在处理乡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时候,同样不可能机械与片面。毕竟,广袤的沉睡的土地是走出乡土世界的知识分子的曾经的根基,而古老的淳朴的乡土文明也奠定了他们的精神底色。因此,事实上,任何关于中国乡土小说的阐释在某种意义上又都不可能是没有缺憾的,所有的解释与分类也都是为了理解的需要。单纯地将某个小说家或某部作品纳入到现代性或反现代性的视野都是出于理论与批评体系的考虑。
四、“传奇+小说”型的乡村罗曼史文体形态
如果说西方文艺理论强调小说和传奇的区分,我国的文体观念则体现出一种融合观,它把小说与传奇、神话等幻想文学统统整合进叙事性文学。正如论者指出的,“我国虚拟一脉小说,发展源流可大致为:从神话到传说,再到先秦寓言,再到唐宋传奇、《西游记》《聊斋志异》等,到了现代则以鲁迅的《故事新编》为代表。这一脉小说体可用传奇文体概括之:乃小说之一种,想象奇特、虚构情节和情境超出物理时空逻辑、形象超越现实世界。”可见,传奇不再是与小说相独立的文体,而是小说的一种亚文体。
在《中国乡土小说史》中,丁帆创造性地运用“三画四彩”概念来统摄中国百年乡土小说的文体特征、美学品格和艺术精神,显示出深广的学术视野、深厚的理论功力、深刻的历史洞见和独览众山的思想境界。他认为“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乃“现代乡土小说美学品格的最基本的艺术质素,赋予了乡土小说区别于其他文类的美学风格”,而“作为‘三画’内核的自然色彩、神性色彩、流寓色彩和悲情色彩这一美学基调,便是现代乡土小说的精神和灵魂之所在”。在“三画四彩”共时性的概念框架之下,他描述并阐释了从乡土写实派、乡土浪漫派到乡土先锋派百年乡土小说的发展变化。不过,显而易见的是,百年乡土小说始终保持着独立自足的文体意识。尽管我们可以看到,乡土浪漫派小说积极吸收了佛教传说、民间故事等奇幻因素,寻根乡土小说和乡土先锋派也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现代派手法融入文本,不过,合乎历史逻辑与真实仍然是乡土小说的基本遵循,它坚定地保持着小说的文体界限与疆域。
然而,《皖北大地》却似乎刻意打破这样的限制与约束,努力突破和拓展乡土小说的文体疆域。它如同一部乡村罗曼史,不只积极地吸收与融合了传奇的元素,更是以传奇的方式来叙述故事、结构小说、组织人物命运,从而使小说呈现为“小说+传奇”的文体形态。具体表现在:首先是故事情节令人惊奇。《皖北大地》将巧合、偶遇、误会等能够增强戏剧效果的手法融为一炉,让故事的发展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农瓦房化名“赛诸葛”在宁城算命看相,为了谋生曾欺骗一位大娘,当他再次遇见大娘,发现原来她是安玉枫的母亲。而安玉枫年轻时在火车上偶然邂逅一位长着“狐媚的眼睛”的活泼少女,多年以后,他们再次重逢,这位传奇女子杨二香已经成为他的合作伙伴。这些传奇般的情节不仅增强了小说的吸引力与可读性,而且它还让主要人物之间发生联系,使故事线索不至松散、零乱,严密和稳固了叙事结构。其次是人物命运不可思议。《皖北大地》将民间传奇与传说中惯用的“善人有善报”“有情人终成眷属”等人物命运模式发挥至极致,小说的结尾,所有的人物最终几乎都喜剧般地实现了“愿望的达成”。比如王大鹏从省农业科学院调到皖北县挂职,随即转任靳沟口镇任职党委副书记,只为与靳小兰结婚。安三虎最后也放弃了王彩芹,农瓦房在历经人生的千曲万折后终于和王彩芹结合。这些人物命运百转千回又不可思议,但是也正是这种传奇,让小说摇曳多姿又波澜迭起。此外,《皖北大地》还将神奇的传说插入故事,比如关于大龙河、宝灵泉和孝灵泉的传说,有关安息国和安姓家族与安大营村的谱系与溯源,这些神话元素使小说变得神秘而超越。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皖北大地》的主调仍然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乡土小说,或者确切地说,是一部结合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乡土传奇小说——乡村罗曼史。因为,苗秀侠本就不是去写一部传奇,而是要记录改革以来乡村社会的发展,为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画像。
应该说,《皖北大地》里的场景生动、对话传神、叙事酣畅,较为成功地描绘出新时代乡村世界宏阔的历史场景和时代画卷。然而,小说家对矛盾情境中人物的精神世界及其变化着墨有限,核心人物形象没有性格发育和内心发展,在故事的起点就已固定,这无疑削弱了文本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审美张力。但是,如前文所述,《皖北大地》超越了既往乡土小说中城市/乡村、现代性/反现代性的二元对立的惯性思维和结构模式,以城乡融合的新观念理解和表达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世界,提供了文学思考乡土的新视角和文学想象乡土的新方式,标示出乡土文学的新的可能性。就此而言,它无疑也是一部具有突破性意义的乡土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