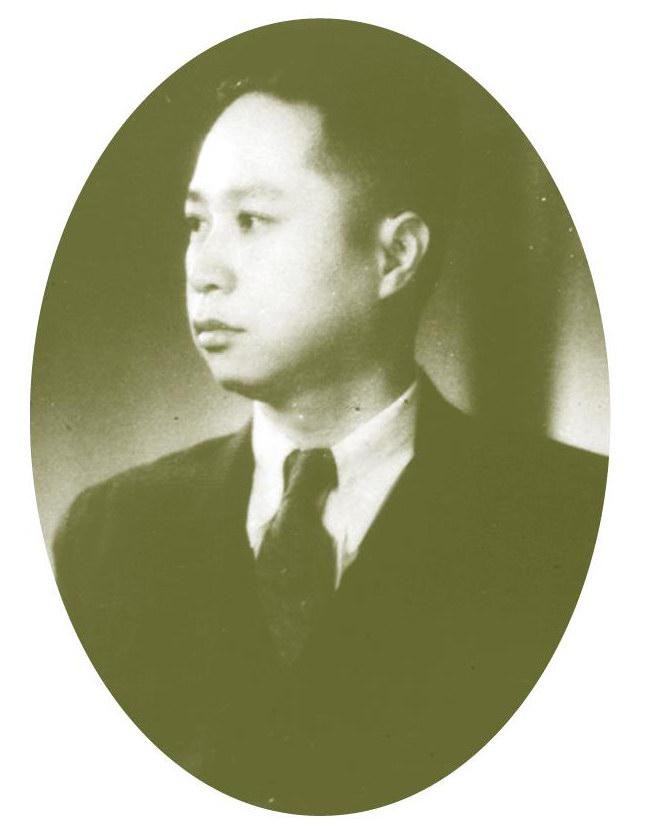叶挺离党期间与共产党人的交往
蔡长雁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等起义领导人受到广东省委的处分。此后,处分虽然撤销,但对叶挺在起义中表现消极的指斥却未改正。并没参加起义的王明写了篇《广州起义纪实》,攻击叶挺“于暴动前6小时始由香港到广州”,“对于军事计划不甚熟悉,遂致表示出消极怠工”,特别批判了叶挺将起义部队转移到农村去的主张。叶挺到了莫斯科也无处申辩,负气赴德国,结果“暂待”党外,这一待就是十年。就是在“暂待”党外期间,叶挺仍然保持着共产党人的情怀,千方百计靠拢党组织。
欧洲期间:从消沉走向振作
当时正是欧洲危机前夜,前些年的无产阶级革命也相继失败,种种不顺让叶挺心灰意冷,于是他在柏林加入了德国的一个提倡素食的流派——国际社会主义斗争团,打算远离政治,放弃军事,转而从事德文著作的翻译,希望在文化交流方面为国家做些贡献,同时也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
1930年4月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途经欧洲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在柏林他与叶挺作了一次促膝长谈。周恩来是叶挺最为敬重的中共领导人。广州起义失败后,李立三处分起义领导人,黄平不服,去上海向中央申诉,周恩来根据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精神起草了致广东省委的指示信,指出省委会的根本错误在于太侧重主观上的责备而忘记客观的困难,表现出一个极不正确的指导和估量。如此为起义领导同志说了公道话。1928年2月,中共中央将李立三调离广东后,派周恩来前往香港,主持召开广东省委扩大会议,纠正李立三对广州起义所作的错误结论和惩办做法,宣布撤销原来省委对起义领导人的处分决定。这次周恩来到柏林,令叶挺十分高兴,但两人交谈时,周恩来对叶挺进行了批评,周恩来说,干革命不能只承认成功、不承认失败,尤其个人受点误会和冤屈是总会遇到的,这个时候既不能意气用事,更不能消极沉沦。“我们总不能放弃革命不干呵!干革命,成功不必在我。”
在叶挺看来,周恩来不仅仅与自己有着深厚的个人感情,心心相通,更是正确路线的代表,面对周恩来入情入理的批评,叶挺心悦诚服,甚至把周恩来的批评当强心针兴奋剂,重新振作起来。虽然欧洲经济危机,叶挺生活困难,找个地方打零工都不如意,但他积极想办法克服困难,在柏林工人区,与一些生活困难的人一起合股开了一家小饭馆,自己当厨师,并为二三十个中国留学生办理包餐,以此解决生活问题。此后,他边开饭馆边抓紧学习考察德国新的军事科学,学习研究有关工兵方面的新知识,研究爆破技术,对德国陆军特别加以重点考察,忙得不亦乐乎,期待学有所用。
涉险上海,寻找组织
随着与自己一道谋划组织第三党的同志们先后从欧洲回国,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加紧侵华,叶挺在欧洲待不住了,于1932年秋回到澳门,一边继续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一边积极寻找党组织,期望与党建立联系。
1933年春,叶挺终于打听到阳翰笙在上海的地址,就写信给他,希望他从上海来澳门看看自己,自己有很多心里话想要与他倾诉。阳翰笙是叶挺的老部下,此时正担任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职务,全力领导左联。他说,“1929年秋,我奉党组织之命,参与发起组织‘左联,是12名发起人之一。”显然,阳翰笙在上海无法脱身。叶挺于是决定亲自去走一趟,寻找党组织。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虽是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但是鱼龙混杂。英、法、美、日等国在上海划割租界,实行殖民统治;国民党军警宪特机关密布,流氓、地痞等黑帮势力与帝国主义、国民党相勾结,触角伸向上海每个角落;还有各界各家特工在上海尤其在上海租界互相渗透获取情报,进行潜伏与反潜伏的斗争。面对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共六届四中全会(193年1月)上台的王明,推行第三次“左”倾路线,导致党的力量日益萎缩。直接要命的则是1931年4月24日具体负责党的保卫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被捕叛变,他是少数熟知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共领导人住址及中共秘密工作方法的人之一。
正是在这非常时刻,叶挺于1933年夏奔赴上海,显然时机不好,中共中央已经撤离,相知甚深的周恩来也奔赴中央苏区了。但让叶挺想不到的是,与自己迫切希望相比,对方显然过于“淡定”,几乎是直接把自己关在了“门外”。阳翰笙没有出面会见叶挺,更没有派比阳翰笙负更重要责任的领导干部出面,叶挺只是在上海法租界自己的公寓里见到了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的刘仲华和毛齐华。他们俩人的到来,没有特别令叶挺惊喜,他们之间只谈了爆破方面的问题,而叶挺最为关心的找党问题并没有涉及。
无疑,王明时代的中共中央对叶挺并没有多少兴趣。
港澳期间:与共产党并肩作战
叶挺从上海返回澳门后,自己的一帮老朋友们正在谋划福建事变。1933年11月上旬,蒋光鼐把叶挺请到福州住在自己的家里,担任军事顾问,帮助策划福建事变。本来是想请他公开活动的,但许多人认为叶挺共产党的色彩太浓,表示反对。在这里,叶挺碰到了自己的老部下梅龚彬。叶挺详细介绍了自己广州起义失败以来的遭遇,表明了抗日反蒋的立场及盼望与党组织早日联系,争取党的教育与帮助的心情。但是,随着福建事变的失败,叶挺归党之事不了了之。
此后,叶挺离开福建,返回澳门,但常到香港与反蒋抗日人士走动。在宣侠父、梅龚彬、陈希周等共产党人的协助下,李济深等人于1935年7月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同盟成员主要由原参加福建事变的各派民主人士和原十九路军中上层军官组成。宣侠父、陈希周和梅龚彬等共产党人,分别担任了同盟的不管部长、群运部长和宣传部长。叶挺是同盟军事委员,与这些共产党人成为同事。梅龚彬实际上是同盟的灵魂人物,他在香港铜锣湾的寓所,成为中共反蒋抗日联合战线的一个地下机关。
叶挺到香港一度住在九龙通菜街,曾找到同住九龙的宣侠父,反映自己的情况,但没有下文。在九龙时,叶挺与陈希周比邻而居,经常带着夫人和两个儿子到陈希周家会面和谈心,共叙国内外时局。后来陈希周参加新四军,担任叶挺秘书。1936年4月,文学家、共产党人丘东平抵达香港,住在九龙,也加入到反蒋抗日联合战线中。丘东平认识了宣侠父,宣侠父这时正需要人手帮助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于是丘东平先后把陈子谷、陈辛人(两个此时还不是中共党员)介绍给宣侠父和梅龚彬,因此丘东平、陈子谷、陈辛人等又与叶挺相识,后来他们都参加了新四军。丘东平还到通菜街专门拜望过叶挺,讨论联合戰线等方面的问题,以后两人又多次会面,叶挺还答应在澳门给丘东平找间合适的房子。丘东平还活动翁照垣和罗吟圃两人出资在九龙办了一个“半岛书店”,发行《在抗战旗帜之下》《大众动向》等刊物,宣传同盟主张。由于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香港当局封闭了半岛书店。为了宣传同盟主张,梅龚彬与叶挺商量后,由叶挺主持在澳门板樟庙街办了一家小印刷厂,印制同盟的报纸杂志,代行半岛书店职能。
这时,由于日本发动华北事变,进而准备灭亡全中国,蒋介石开始谋求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并以改善国共关系作为姿态。为此,从1935年秋天起,蒋介石就通过各种途径与中共联系。1936年年初,中共代表团指定潘汉年为与国民党谈判的联系人。潘汉年5月初到达香港,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上层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还特别会见了叶挺,宣传了八一宣言精神,告诉他中共政策已由过去推翻国民党统治,转变为联合国民党一道抗日,希望叶挺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做一些国共联合抗日的工作。叶挺完全同意中共的政策主张,并乐意接受潘汉年的建议。这是叶挺自离开党的组织在国外流亡多年回国后,第一次同中共的重要干部面谈,中共党员柯麟当时陪同潘汉年参加会见。柯麟也可算作叶挺的战友、部下,曾在第四军作医务主任,并随叶挺参加了广州起义。因此,柯麟随后被派到澳门以开诊所为掩护,担负中共同叶挺的联络员。此后,叶挺心情舒畅,情绪很高,遇到熟人常常高兴地说:“我现在好了,和那边(指中共)联系上了,再也不是孤家寡人了!”
叶挺按照潘汉年传达的团结抗日的政策精神,访问了在苏州、嘉兴、常熟、江阴一带建设防御工程的国民党部队中的老朋友。1936年11月叶挺还偕同中共华南工委书记宣侠父等人到广西苍梧李济深老家,向李济深和住在他家的抗日反蒋人士转达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叶挺立即要求在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工作的梅龚彬,陪同去上海会见潘汉年。潘汉年当时携带《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和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在上海沧州饭店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谈判。叶挺正是想通过潘汉年了解党对西安事变的真实态度,再利用自己熟悉国共双方的有利条件,为和平解决事变共同抗日尽点力。1937年5月中旬,奉中共中央命到华南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张云逸到达香港,他在柯麟陪同下专程赴澳门会见叶挺,向叶挺介绍了中共处理西安事变及拥蒋抗日的方针政策、国共谈判的进程及趋势。叶挺表示愿意随时响应中共号召,返回内地,投身抗战。有此背景,在国民党内老朋友帮助下,叶挺举家迁往上海,住在静安寺路一座庭院式的小洋房里,与国民党方面的陈诚、张发奎、黄其翔等多有来往,交谈时事,等待报效祖国的时机。
抗战爆发:终于重回党的怀抱
1937年,為了尽快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推动国民党在政策上进一步转变,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国共之间进行了多次谈判。2月下旬至3月上旬,周恩来、叶剑英代表中共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进行了第一次谈判,谈判的中心是红军改编和苏区政府问题,也涉及南方各边区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张冲提案有“其他边区地方队改为团队”的条款。对此周恩来建议中共中央,“其他边区,过千人者集陕甘,以下者改为团队。”毛泽东、洛甫则提出:“陕甘以外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一律改民团或保卫团,千人以上者亦然,绝不宜调来陕甘集中。”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的议案,这个“就地分散改编”的办法由国民党方面提出,被共产党方面所接受。7月18日,周恩来上庐山与蒋介石谈判时,就南方红军游击队问题,提出:国共双方派人分赴闽浙赣、闽粤赣、湘鄂赣、鄂豫皖等地传达国共合作新方针,对南方红军游击队实行改编。8月中旬,周恩来同何应钦商谈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何应钦答应中共可派人到南方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协助红军游击队进行改编。
显然,南方红军游击队就地分散改编曾是国共双方的共识,中共方面也一直这样认定。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还对就地分散改编提出了具体要求。但把各边区武装适当集中却是周恩来挥之不去的心愿,虽然这一建议一提出来就被中央否决,但随着时机的成熟,最终还是为中央所接受。叶挺也因此而出山,实现重回党的怀抱的愿望。
1937年7月7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离开西安飞抵上海。在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等陪同下,周恩来会见了叶挺,周恩来请叶挺出面活动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毫无疑问,周恩来是让叶挺出面“集中改编”,而不是“分散就地改编”,因为那样就不需要叶挺了。所以叶挺自7月上半月会见周恩来后,就开始为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而奔走,他与正在上海参加淞沪会战的陈诚联系,声称自己愿意出来集合仍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开赴前线抗日,请陈诚帮助活动,并建议改编后的部队名称就叫新编第四军。同时叶挺在上海还抓紧招兵买马,比如从香港回到上海的陈辛人、丘东平,年轻的医学博士沈其震等都立即投到叶挺的旗下。8月叶挺即带着他们到南京活动,筹建新四军。在叶挺的活动下,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通报,蒋介石核定,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改编与指挥闽赣边游击部队。
由于国民党方面对叶挺的这一任命,推翻了国共双方达成的共识,中共不能不对国民党保持警惕,同时对叶挺也产生了不信任情绪。10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云逸南杰博古剑英同志并告周、朱、彭、任及伯渠(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方针的指示),认为“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国民党企图拔去这些战略支点。在西安事变后,还用了全力,用屠杀方法拔去他们。在这个方法失败之后,现在却利用抗日题目,想经过叶挺把他们拔去,方法不同,目的则一。”“把各区游击队完全集中,对于我们是十分不利的。”并特别要求:“叶挺须来延安,在行营他完全同意中央的政治军事原则后,可以去闽粤边(或闽浙边)指挥张鼎丞部(或刘英部),以此为基础,扩大部队。”10月5日,叶挺在南京与叶剑英、博古接洽,但未得中共同意的明确结果,于是找潘汉年,让他致电毛泽东、洛甫(张闻天),请求中央意见。中共这边还未答复,10月6日,熊式辉转蒋介石电,将叶挺职权加以扩大。10月12日,国民党政府正式颁布了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命令,以叶挺为军长。
面对国民党方面的一意孤行,中共方面着实为难,公开反对未必有利(政治被动,难以争取民众),就此承认,也有风险,毕竟不知道叶挺与国民党关系密切到什么程度。如果叶挺能接受中共的领导,事情就简单了:同意国民党的任命,国民党得面子,共产党得里子。于是中共中央与在南京的中共代表电报往返多次,反复调查核实相关情况,最后终于弄清楚了这几个关键问题:第一,叶挺出面改编部队并不是国民党提出的,而是共产党自己提出来的,是周恩来第一次在沪时向叶挺提过这个办法,故叶挺才敢活动。现已委任为新编四军军长,拨发了5万元活动费。叶挺表示如共产党方面不赞成,仍可辞职。排除了叶挺是国民党安插之人的嫌疑。第二,南方各游击队分散坚持事实上难以为继,以集中改编为有利。第三,叶挺表示完全接受共产党领导,并决定立即来延安接受中共中央的当面考察,等延安会见有结果后再决定是否呈报就任新四军军长职。搞清楚这些情况后,毛泽东等表示,如此则可经过叶挺整理南方游击队。
11月2日,叶挺到达延安,与毛泽东长谈。可以说,以前毛泽东与叶挺之间相互了解都不深,经过这次面谈,毛泽东消除了对叶挺的疑虑,叶挺一再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军事策略,考虑到留在党外便于同国民政府打交道,故“表示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中共中央对叶挺的这个决定表示尊重和理解,同时作出决定,同意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
抗战全面爆发后,因为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系,南方红军游击队成了国共之间绕不过去的一道坎;而由叶挺出山,则能顺利越过这道坎,其重要性凸显出来、急迫起来,于是叶挺成为两党共同的选择。叶挺本人也终于如愿以偿,被共产党中央接纳。
显然,叶挺在历史上组织上虽然一度离党,但在思想上、情感上和行动上几乎一直没有切断与党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