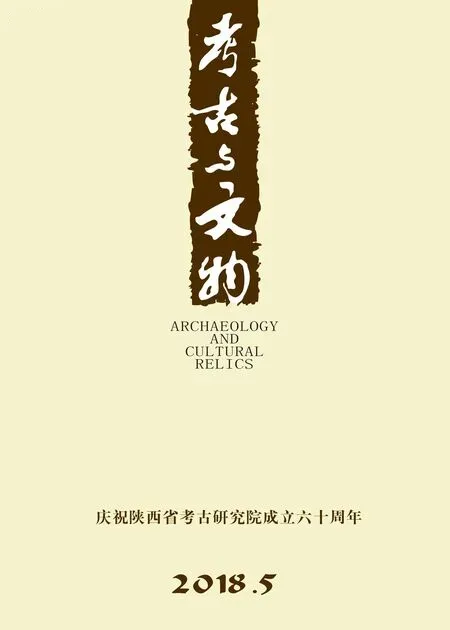2008~2017年陕西三国隋唐宋元明清考古综述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隋唐考古研究室
在三国到明清近1700年的历史长河中,曾经有八个朝代在陕西建国立都,其中有民族大融合时期的西晋、前赵、前秦、后秦、大夏、西魏、北周,还有繁荣辉煌的隋、唐时代,即使宋元明清时代,陕西依然是经济文化发达、军事地位显赫的重镇。此期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一直是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的主线或重要组成部分。从上世纪20年代始,唐代陵墓和隋唐长安城的调查发掘是这一时期考古研究的中心内容,取得了很多令人瞩目的成果。2008年以后的近十年来,陕西地区三国至隋唐明清考古,不但隋唐时代大中型墓葬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继续有新的收获,以往不被关注的十六国—北朝时期,乃至宋元和明等各时段都涌现了很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在考古的理念、综合记录手段以及研究方法上都有很大突破。
始于2006年的唐代帝陵大遗址考古项目,创建了地毯式全面深入调查、大面积普探、关键部位试掘以及全方位测绘、高精度数字采集的全套田野工作方法,在这种工作理念和方法的主导下,唐代帝陵考古从宏观的陵园布局的演变到具体的陵前石刻文物保护复原、建筑构件编年,乃至唐代帝陵制度的内涵研究都取得了丰硕成果。这是十年来陕西隋唐考古工作的重大收获。
在墓葬考古方面,比较突出的是十六国—北朝墓葬的发掘收获。在咸阳北原一带及西安南郊集中发现的十六国—北朝高等级墓葬,填补了这一时期考古发现的空白。十六国—北朝处于汉制向唐制的过渡期,这些考古资料将是研究历史变革时期文化交流融合、新旧制度交替的重要资料。
隋唐墓葬的考古新发现,尤其如唐上官婉儿墓、韩休墓、李道坚墓等一批墓志和壁画保存较好的大型唐墓,备受各界关注,在唐代毁墓习俗、历史史实复原、美术考古、尤其是中国早期山水画研究方面引起了广泛讨论。
北宋吕氏家族墓是陕西地区首次发现的大型高等级的宋代贵族墓葬,其随葬品中成套的茶具、酒具和文房用具以及青铜器等藏品,反映了北宋士人的精神追求和生活方式,而陕北宋金画像砖墓则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这些宋金贵族和平民墓葬的发掘,为研究区域墓葬习俗制度和唐宋墓制的转变提供了详实资料。
在城址考古方面,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隋唐长安城考古工作,在大明宫等宫殿遗址区、里坊区和东、西市遗址,都有了新的考古发现和认识。同样为大遗址项目的统万城遗址考古,确定了东西城、外郭城的分布格局和年代,通过周边的墓葬及祭祀遗址的发掘,对统万城的生活群体葬俗葬制及延续时期有了一定了解,同时积累了沙漠考古的工作方法和经验。
历史时期考古是传统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的相互渗透、结合,二者互为印证、解读。其内涵丰富、物质文化面貌复杂、门类繁多。既有城市考古、帝陵大遗址考古等综合性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又有与其他自然或社科门类的交叉结合形成的专题类研究,诸如陶瓷考古、美术考古、宗教考古、建筑考古。10年来,陕西三国—隋唐宋元明时代考古,正是由于考古理念的更新、多学科研究的紧密结合以及资料采集和记录手段的大幅度提升,拓展了学术视野,推进了学术研究的深入,从而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和收获,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规划的制定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为这一时期城市历史风貌的复原积累了资料。
本文试对近10年来这一时期考古发现和研究做一概述,以城址、陵墓、宗教、手工业考古的发现和研究为重点,并将工作内容较多的长城调查和西藏考古单列介绍。
一、城址
近年来,城址考古的理念已经进化为城市考古。城市考古虽仍是以古代城址为对象,但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其目的是“为了掌握古代城址不同时期的遗迹现象,复原古代城市不同时期的形态结构,认识古代城市社会生活的空间场景,从而为研究城市发展的历史、开展历史城市保护奠定基础”[1]。所以,城址本身的布局、结构,城址周边的环境变迁,城市居民的墓葬分布及城市的兴衰,都是其研究的主要内容。近十年来,陕西城市考古以统万城遗址、隋唐长安城遗址考古新发现最受关注[2]。
(一)统万城遗址
统万城遗址考古近十年来主要着眼于城市布局、周边墓葬、祭祀遗址等方面的考古勘探与发掘研究。
城市布局方面,首先是外郭城的确认。统万城外郭城呈曲尺形,周长13865.4米,面积7.7平方公里,西北部凸出,城垣走向与东西城城垣基本一致[3]。
其次,经发掘确认统万城东西城门外均有瓮城。西城西门瓮城位于西城西垣偏南处,瓮城南北长38.5、东西宽22、高10米,城垣宽3.8米。瓮城门面南,紧贴西城西垣。西门平面呈“亞”字形,门道内外两侧均有凸出的夯土台,进深20.6米,单门洞,门道宽6.5、长19.5米。从地层堆积看,唐代西门瓮城废弃后,西门内侧人为修筑夯土,隔断城内与瓮城的联系[4]。
第三,对东城建筑基址的发掘,为确定东城的建筑年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这组建筑基址东西宽96、南北进深48米。从其所处位置来看,应该是东城的主体建筑之一。中心夯土台东西宽28.3、南北进深26.7、面积755平方米。夯土边缘与城垣方向一致。东南部夯土厚度达2米。南面有两个斜坡漫道,长6.8、宽4.4米,北面及东西两面各有一个斜坡漫道。南面漫道两侧及夯土台外侧有砖砌散水。南北中心夯土台外有“U”字形夯土带,与中心夯土台相隔2.2~2.6米。中间形成凹槽,凹槽内发现近40个柱洞。夯土台外地面出土数十件兽面瓦当,另外有沙石雕刻的莲花座、浮雕壸门、佛头像的石刻残块等。夯土台叠压唐代晚期地层,其建造年代当在晚唐五代时期[5](图一)。

图一 统万城东城建筑基址
第四,经过对统万城的钻探和发掘,基本搞清了马面的规模及功能。统万城西城城垣外、东城南、东、北垣外均建造有马面或垛台,每面8~10个。这些凸出的马面或垛台,将城垣外广场分成若干区域,便于守城将士从多面居高临下用弓箭、擂石等武器抗击攻城之敌。另外,还在城垣外设立虎落,地面撒铁蒺藜防范敌骑兵入侵。
在统万城周边的考古工作主要是其墓葬区和祭祀遗址的发掘与统万城有关的墓葬群分布南至华家洼、波罗地梁、周家梁墓群,东南至尔德井墓群,西至敖包墓群、北至瓦渣梁墓群。整体范围南北约10、东西约20公里,面积约200余平方公里。共发掘北朝、唐、五代、宋代墓葬40座,基本搞清了与统万城有关的墓葬年代、形制及各时代墓葬形制的演变序列[6]。在统万城周围还发现了疑似祭祀遗址的夯土台。西梁夯土台基址位于统万城遗址东南,隔红柳河与城址相望,距统万城直线距离约2公里。主要由围墙及围墙内的南墩台、中墩台和北墩台等部分组成。三座墩台形制大小相近。南墩台平面近方形,南北长37、东西宽36米,中部距底部深约8.8米。夯土基础部分深约4.8米。地表部分夯土略呈覆斗状,残高约4米,顶中部较平坦,墩台四周均有斜坡漫道。
中墩台、北墩台规模与南墩台相当,只中墩台形制如龟背,东、北两面设漫道;北墩台形如覆斗,东、南、西三侧设漫道。
查干圪台位于统万城遗址西城西北、外郭城内,东南距西城距离约2.3公里。查干圪台共发现三座夯土台,发掘了1、2号夯土墩台。
1号夯土墩台主要由西、南、东三条夯土道路、中部平台基础和外围覆土等组成。其构筑方法是先夯筑呈矩尺形的西、南两条夯土道路,然后夯筑东夯土道路,三条夯土路相交呈“T”字形,之后以三条夯土路为中心夯筑方形平台,最后于方形平台基础外缘再夯筑护坡。墩台平面整体呈南北长、东西短的圆弧形,且西、南两侧坡度较缓,东、北两侧坡度较陡,墩台主体部分南北残长27、东西残宽20.5、厚2米,西侧夯土路超出墩台主体部分,总长79.5、宽1.1~1.5米。三条夯土路和中心平台部分夯层清楚。护坡为青白色夯土(图二)。
2号夯土墩台平面近方形,方向35°,墩台长约6.8~6.9米,边缘夯土厚0.18~0.3米,中部夯土厚0.4~0.5米,中部高出现地表约0.3米。同样是在“斗”形方坑内起夯。
西梁和查干圪台两处夯土遗址均被隋唐时期墓葬打破,因此其时代应当早于隋唐时期,结合统万城历史沿革,我们认为其建造年代应与统万城同期,为两组礼制性建筑,可能与大夏国时期统万城的祭祀活动有关。

图二 统万城查干圪台夯土基址1号墩台(西城西北部,东俯瞰)
(二)唐长安城
唐大明宫的持续考古发掘是这一时期隋唐长安城最重要的考古工作之一。2007~2010年,为配合大明宫遗址保护及国家遗址公园建设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大明宫宫墙和北夹城、含元殿南水渠、太液池西池北岸及玄武门南侧的两处道路过水涵洞、宫廷膳食灰坑、宫城东北角墩台等遗存进行了全面的勘探与局部清理发掘[7]。重点发掘了兴安门遗址。门址分为早、晚两期,早期门址有三个门道,晚期门址有两个门道,晚期门址由东、西墩台、门道、隔墙以及东西两侧的城墙和马道等组成。出于遗址保护原则,只发掘了晚期门址,发掘面积2939平方米。早期门址的发掘采用小型探沟、钻探等方法进行探究。出土遗物有建筑材料和日用品陶瓷器等[8]。
在城市改造和基建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遗址。2009年9月,在西安市碑林区边家村、黄雁村改造过程中,发现了大片唐代遗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做了发掘工作。遗址位于唐代通义坊范围内,发掘面积约500平方米,揭露出通义坊内东西向道路及其南侧排水沟遗迹,出土了陶瓷器残片、骨器、钱币、建筑材料、善业泥、经幢等文物[9]。2012年2~7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发掘了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遗址,揭露出朱雀大街、安仁坊坊墙墙基和第七横街等遗迹[10]。2014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了唐长安城东市遗址,发现了道路、水沟、店肆后作坊、水井、窖井、渗井、灰坑、活土坑等遗迹[11]。
此外,在隋唐长安城周围,还发现了两处陶窑遗址、一处粮仓遗址,这些遗址当与长安城内人们的生活有关。2011年,我院在西安市未央区大白杨村发掘唐代陶窑16座、水井3座[12]。2011年底~2012年初,西安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在西安市昆明西路与团结南路十字路口西北角处发掘陶窑9座[13]。这些陶窑均成组分布,每组2~6座不等。成组陶窑在操作间之外有供出入的过洞与斜坡道相连。2012年7、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西安市未央区梨园路北侧发掘了4座粮仓遗址。根据其排列规律,推算这一带至少存在3排21座粮仓,东西成行、南北成排分布。粮仓内发现大量炭化的谷物堆积,另外还发现有“开元通宝”钱、手印砖等。粮仓位于西安北郊龙首原的高爽地带,并在唐都长安之北的禁苑之内,而且靠近漕渠,十分有利于粮食的运输、保存及安全[14]。
这一时期出版了3部与隋唐长安城有关的重要考古报告。关于唐长安城醴泉坊三彩窑址[15]和醴泉坊遗址[16],报告对1999和2001年发掘的唐长安城醴泉坊遗址全部成果予以阐述。历年来对唐长安城青龙寺和西明寺调查和发掘的全部资料也已公布。另外,还有张建林、田有前对2012年之前的隋唐长安城的考古发现进行了 梳理和介绍,对隋唐长安城的相关考古研究的综述[17]。
(三)陕北麟州故城
麟州故城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店塔镇杨城村西北部的杨城山上,城址依自然山势逶迤而筑,高差约200米。2009年7~10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榆林市考古队对麟州故城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与测绘。整个城址呈不规则长条形,面积约为1.12平方公里,城周长约5.4公里。分别由东城、西城和紫锦城组成,三个小城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城内皆发现建筑遗迹,以东城最密集。城防工事中瓮城、城墙、马面、角楼等均保留很好,尤其是位于城址中部的紫锦城,有一残存20米保存非常好的夯筑墙体,墙体上部为麟州城的最高点。
麟州城始建于唐代开元十二年(724年),废弃于明代正统八年(1443年),历时719年。五代麟州刺史杨宏信及其长子杨重勋和其孙杨光,世代守卫麟州,抵御契丹、西夏。而杨宏信的次子杨业和其孙杨延昭均为宋代名将,在山西朔州北拒契丹,称雄一方。由于麟州故城与杨家将的渊源关系,后代人们怀着对杨氏英雄的崇敬心情,将此城称为杨家城,延续至今。
二、帝陵
十年来主要对隋文帝泰陵、唐帝陵、明藩王陵进行了考古勘探与试掘。
(一)隋文帝泰陵
泰陵为杨坚与文献皇后独孤氏的合葬墓,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杨陵区五泉乡双庙坡村。现陵前立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书“隋文帝泰陵”石碑。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扶风县博物馆罗西章曾对泰陵做过多次勘察[18]。为配合隋文帝泰陵保护规划的制定,2010年5、6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陵园遗址和隋文帝庙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与勘探,取得了重要收获。
现已探明陵园遗址周围有平面呈长方形的城垣,南北长约628.9、东西宽约592.7米,墙基宽约4.4米,陵园总面积372749平方米。陵园四面各辟一门,南门门址保存较完整,门外分别有一对门阙,门阙平面呈梯形。陵园外环绕有围沟。陵园中部偏东南部筑有覆斗状封土,现高约25.1米。封土顶部南北宽约33、东西长约42米,底部南北宽约153、东西长约155米,基础部分呈倒“凸”字形、覆盖墓道。封土南部发现两条东西并列的墓道,形制和结构相同,东西间距23.8米,均为7天井、7过洞,西侧墓道(包括天井、过洞)南北长约78.7、宽约3.4~5.6米,东侧墓道略短,也稍窄。
“隋文帝庙”遗址周围有长方形垣墙,南北长约384、东西宽约354米、面积135936平方米。其中南墙宽10.1、东墙宽16.4米,南北两面的垣墙分布有马面6处,南墙正中有门址一座。在城址内偏南部有《大宋新修隋文帝庙碑》。
此次调查和勘探进一步确认了陵园遗址和“隋文帝庙”遗址的准确位置和布局、范围。探明了主要建筑基址及陵墓玄宫墓道部分的结构,探出两个墓道,证实泰陵确为文献记载的“同茔而异穴”[19]。
(二)唐代帝陵
2006年,陕西唐代帝陵被国家文物局正式确定为全国100个大遗址保护项目之一,这对唐代帝陵考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在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我院对关中21座唐代帝陵(“唐十八陵”加上永康陵、兴宁陵、顺陵)开展了系统的田野考古工作。截止2017年底,已完成21座唐陵的考古调查、勘探和测绘工作,其中对16座唐陵的部分陵园建筑和神道石刻做了考古发掘和清理,搞清了这些陵园的基本布局、陵园石刻的分布规律及数量、相关遗迹的分布及保存现状、陪葬墓的数量和分布情况。
经过详细地调查、勘探、发掘和测绘,对唐代帝陵的陵园结构与布局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唐代的帝陵陵园坐北朝南,地势北高南低,以南北为中轴线,呈东西对称布局。各陵园的规模差别较大,据宋敏求《长安志》记载,昭陵和贞陵周围一百二十里,乾陵周围八十里,泰陵周围七十六里,定、桥、建、元、崇、丰、景、光、庄、章、端、简、靖等13陵周围四十里,献陵周围二十里。

图三 唐元陵下宫正视影像图
在陵园布局方面,各陵虽构筑方式不同,有些陵园垣墙因山势而稍作曲折,但整体上陵园平面大体呈方形。玄宫所在之封土或陵山为整个陵园中心,四周筑垣墙,四面垣墙正中设门,门外各有门阙一对,围墙四角各有角阙。南门为正门,南门外为神道(又称司马道),南门之外、神道北端,有蕃酋殿与列戟廊遗址。神道南端,有门阙一对,在其南又有门阙一对,加上陵园南门,共有3对门阙。其中第1对门阙与第2对门阙距离较远,第2对门阙与第3对即南门门阙之间为南神道,神道两旁列置石刻。此外,又有寝宫与为数众多的陪葬墓。
初唐时期的高祖献陵、太宗昭陵,布局设计“斟酌汉魏”制度,同时吸收南北朝帝陵的传统,试图探索建立唐代帝陵的新形制。献陵墓上筑覆斗形封土,封土现高约18米。周环方形墙垣,四面辟四门,陪葬墓分布于陵园东侧及东北,这些特点与汉陵相同,惟陵园四门及神道石刻为汉陵所无[20]。四门所立石虎取站立姿势,造型与西魏永陵之神兽类似;神道所立石柱则明显仿照南朝陵墓造型,石柱座上雕刻两条盘绕的龙,石柱顶部雕刻蹲兽等,这些特征无不与南朝陵墓石柱相仿[21]。献陵陵园北部偏东钻探发现的建筑遗址紧邻陵园,坐北向南,周环墙垣和围沟,整组建筑呈轴对称布置:中轴线上安排两进院落,并有大型建筑基址,应该是礼制建筑。遗址出土的砖瓦、瓦当等建筑材料与献陵南门遗址完全一致,说明建造年代相同。推测此处建筑很可能是献陵最初的寝殿建筑群。这种将陵寝建筑紧邻陵园的做法也与汉陵相仿。唐太宗昭陵开唐代“因山为陵”之先河,在具体的设计和布局上多有创新,与献陵几无相似之处。因山势在九嵕山南面悬崖开凿玄宫,南北山梁上分别建造南北司马门,东西不设门,也没有环绕的城垣。西南面的平缓开阔地带建造寝宫。北司马门从外向内(从北向南)依次为三出阙、列戟廊、殿堂式大门。寝宫宫城的平面布局刻意仿照长安城的宫城设计,南面为宫城正门,北面有夹城,形成两道北门,主体建筑沿南北中轴线依次排列,布局与大明宫极为相似。陪葬墓主要分布在南面及东南面。陵园石刻完全不同于前朝,北司马门矗立具有纪念碑意义的“昭陵六骏”石屏,前无古人。写实性的“十四国蕃君长像”石人具有纪功宣威的功能,有学者认为此种做法可能源自突厥陵墓石人[22]。
盛唐时期的高宗乾陵、中宗定陵、睿宗桥陵是唐代帝陵形制确立的阶段。自乾陵开始,陵园环绕陵山一周修筑平面方形的城垣(唐代文献称之为“壖垣”或“行墙”),四面辟四门。由南向北布置三重门阙,第1对阙台(宋代称之为“鹊台”)通常距第2对阙较远,相距1000~2000米,有些超过2000米,其间中轴线的西侧建造下宫,东侧分布陪葬墓。第2对阙(宋代称之为“乳台”)距离南门阙一般不超过1000米,两者之间的神道两侧对称排列石刻。陵园四门由外及里依次筑三出阙、列戟廊和殿堂式大门,南门外还修建放置蕃酋像的建筑(蕃酋殿)。需注意的是蕃酋殿的位置曾发生变化,乾陵将之安排在南门与南门阙之间,桥陵及以后则将其移至南门三出阙以南。寝宫(后称下宫)位于第1对阙(鹊台)与第2对阙(乳台)之间的西侧,宫城规模较大,乾陵下宫面积145000平方米、桥陵下宫面积206515平方米;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有内外两重城垣;较大的建筑基础为数条平行的夯土基构成。陵园石刻从乾陵开始形成定制,四门外各立石蹲狮1对,北门阙以外再立石马和牵马人各3对(乾陵北门外还有石虎1对、尚不明确的石刻1对),南门阙以外神道两侧由南向北依次立石柱1对、翼马(或麒麟)1对、鸵鸟(或鸾鸟)1对、仗马和牵马人各5对、石人10对以及数量不等的蕃酋像。石刻体量高大,如门外石狮高达2.7~3米,石人高达4米左右。以上可以看出,乾陵—桥陵的总体设计布局和石刻组合分别吸收献陵、昭陵两者的设计理念,基本呈方形的陵园墙垣、神道石刻最南端为1对石柱、四门外设置1对石狮等源自献陵(献陵为1对石虎);因山为陵、北门外设置6匹石马、南门外设置蕃酋石像(昭陵蕃酋石像设在北门内)、门外设三出阙及列戟廊等均源自昭陵。还有学者认为高宗太子李弘恭陵的神道石刻组合和造型对乾陵神道石刻制度有很大影响[23]。无论如何,乾陵陵园形制标志着唐代帝陵制度的正式形成,此后的唐代帝陵陵园基本按照这一布局设计建造。

图四 唐光陵东门及南列戟廊遗址
中唐时期的玄宗泰陵、代宗元陵(图三)穆宗光陵(图四)延续盛唐帝陵形制,略有变化。仍然是“因山为陵”,但陵园平面多随山势,平面形状多不规则。东西两门以及东北、西北角阙的地点选择只能依据不同地势。下宫规模减小,如泰陵下宫宫城面积23100平方米,崇陵26800平方米;宫城平面多为长方形,不再是内外两重城垣,北面不设门。陪葬墓急剧减少,甚至没有陪葬墓。从泰陵开始,石人体量变小,分为左文右武,东侧为手持笏的文官,西侧仍为手拄仪刀的武将。鸵鸟不再采用写实方法,逐渐失去鸵鸟原型,颈、腿变得粗短,或许这一时期的应当称之为“鸾鸟”更为合适。翼马定型化,不再出现兽头的麒麟。蕃酋像更为注重表现不同民族的服饰差异,在建陵陵园城垣附近发现的马头人身石像和猴头人身石像,显示着这一阶段还曾流行在陵园周圈埋设十二生肖石像的制度。
晚唐时期的敬宗庄陵、僖宗靖陵,陵园形制与前一阶段相比变化不大,但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有3座陵园即敬宗庄陵、武宗端陵、僖宗靖陵采取久已不用的封土为陵的设计。陵园规模逐渐变小(贞陵是一个例外),尤其是3座“封土为陵”的陵园,边长仅500米左右,“因山为陵”的章陵边长也不过800余米。陵园石刻的种类未减少,但在数量上有减少、体量上有变小的趋势。到唐末的僖宗靖陵,石人高度不足2米,与前一阶段的蕃酋像大小相差无几。或仅有1座陪葬墓,或没有陪葬墓。这一阶段中,贞陵是一个特例。陵园规模巨大,南北门之间的间距达3500米,在所有唐代帝陵中是最大的。下宫宫城规模也较崇陵要大些。陵园石刻出现一些不同于其他陵的种类,南门门址残存4个石座,从石座的结构分析,其上原可能是4个守门武士的雕像。南门外两侧还发现一个较大的石座,座上正中残存有榫眼,座上原来的石雕应为一形体高大的雕像。蕃酋像重新变得程式化,服饰不再多样,稍显雷同。
据历年来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资料,可将唐陵陵园形制的发展演变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初唐两座帝陵,属于借鉴汉魏帝陵制度的探索阶段。这一时期陵园布局尚未形成定制,两座陵园采用截然不同的形制。
第二阶段的乾陵、定陵、桥陵,标志着唐代帝陵陵园形制的正式形成。这一阶段最初的乾陵最为重要,是唐帝陵形制变化的一个转折点,形成的“乾陵模式”对后来诸帝陵影响深远,为此后诸唐陵设计的楷模。
第三阶段基本沿袭盛唐时期的陵园布局—“乾陵模式”,又发生一些调整和变化。从某种意义来讲,泰陵也是唐代帝陵形制的一个转折点。从泰陵开始,陵园平面不再追求方形布局,因地势调整,往往呈不规则形状。神道两侧的石人分为左文右武。石刻个体变小,下宫规模减小,陪葬墓数量减少。
第四阶段唐代帝陵制度逐渐走向衰微。除贞陵外,陵园规模逐渐变小。门阙等阙台不再使用三出阙形式。石刻组合基本稳定,石刻体量更趋变小,陪葬制度渐趋消失[24]。

图五 明愍王陵前石麒麟
(三)明秦藩王陵考古调查
明代200余年间,先后有13位藩王、30余位郡王及其夫人、子孙等埋葬于今西安南郊的少陵原、鸿固原、高望原、凤栖原等地,其中明秦藩王墓葬13座,被称为明秦藩十三陵。2006年5月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考古调查发现7座陵园,结合文献记载,应该分别为第一代愍王朱樉陵园、第二代隐王朱尚炳陵园、第三代康王朱士契陵园、第四代惠王朱公锡陵园、第五代简王朱诚泳陵园、第八代宣王朱怀埢陵园、第九代世子朱敬鉁陵园。
第一代愍王朱樉陵陵园位于整个秦藩陵园区中部偏北,东与西汉宣帝杜陵相距2000米。平面长方形,方向355°,南北长430、东西宽370米,占地面积15.6万平方米。由陵墙、主墓、陪葬墓、陵园内建筑基址及神道石刻五部分组成。陵园南墙墙址东西走向,全长369米,东段保存较好。陵园东、南、西面中部各发现一座门址。南门门址位于陵园南陵墙中部,东西长23、南北宽12米。主墓朱樉陵位于缓坡地至高点,9座陪葬墓分布于东南、西南两侧,目前有封土者5座,推测M2、M3当为朱樉两妃王氏、邓氏的墓葬。上世纪70年代在陵区地表仍可见到朱樉妃邓氏墓碑。
2010年考古调查时发现第三代秦僖王朱志堩墓志石,据村民介绍其墓葬为朱樉陵园带封土墓葬之一,后来封土被夷平,M11当为其墓。
朱樉墓M1墓道南端发现一座建筑基址,整体呈方形,由四座房址及通道五部分组成,四座房址围成一个院落,南北、东西对应。南房址位于陵园内中部神道正北端,东西长23、南北宽11.5米,夯土距地表0.7~1.5米。东房址平面长方形,南北长20.8、东西宽15.9米。建筑基址南端10米处,发现一残石龟座,当为石碑基座。其南为陵园神道,神道为南北走向,通至南陵墙中部门址。神道两侧当有9对石刻,目前东侧9件、西侧8件。由南向北分别为华表东西各1、石虎各1、石羊东1、石麒麟各1、石马各2、石文官像东西各1、石武士俑东西各1、石狮东西各1件(图五、六)。
第二代隐王朱尚炳陵园,位于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办东伍村北,陵园呈南北方向,平面长方形,南北长336、东西宽192米,占地面积64512平方米。陵园内现存3座圆丘形封土,现存石刻12件,位置被移动(图七)。

图六 明愍王陵前文官像
第三代康王朱士契陵园,位于长安区大兆乡康王井村东,南北长276、东西宽170米,占地面积46920平方米。地表封土破坏严重,墓前尚存神道碑龟座、石马、石文武官俑、石狮计10件。第四代惠王朱公锡陵园,位于长安区大兆乡庞留井村东,方向348°,南北长326.8、东西宽170.1米,占地面积约55588.7平方米,地表残存圜丘形封土两座,墓地尚存“大明宗室秦惠王神道碑”(残)及“秦惠王暨妃王氏合葬墓”碑各一通,其他石刻14件。第五代简王朱诚泳陵园,位于西安市长安区杜陵乡韦曲街道办,陵园平面长方形,坐北面南,南北长约334、东西宽约179米,占地面积约59786平方米。陵园内尚存封土3座,神道石刻尚存华表、石虎、石羊、石马、文官俑12件,另有3件位置被移动等。

图七 明隐王陵前石刻
第八代宣王朱怀埢陵园,位于长安区杜陵乡三府井村东,南北向,尚存封土2座,高约7米。神道石刻11件,由南向北,依次为华表1对、石虎1对、石羊1对、牵马人及马1对、文官俑1对。另外尚可见到石龟座1件。宣王墓石刻肥胖臃肿,形体不似前几陵高大雄伟。
第九代世子朱敬鉁墓,位于长安区杜陵乡世子井村东北,封土被毁,地表尚存墓碑一座,立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螭首龟座,碑高3.2、宽1.15、厚0.3米,碑额刻“赐嫡子敬鉁墓”[25]。
据研究,明秦藩王王位受封者1位、袭封者8位,嗣封者2位,进封者3位,追谥者5位,除过追谥者计有14位,加追谥者计19位[26]。据明史最后一位秦王是景王朱存枢(第十一代秦王),朱谊漶子,袭封,崇祯末陷于贼,不知所终。梁志胜、王浩远依据发现的朱存枢、大明秦世子暨妃张氏合葬圹志、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博物馆院内的大明宗室秦景王圹志认为《明史》记录有误,朱存枢为世子时已薨,秦景王当为朱存机,最后一位秦王当是朱存极[27]。但是目前考古调查只发现了7座陵园,其原因可能是未生子而卒的秦王附葬其他陵园,比如第三代秦僖王朱志堩附葬愍王陵园;也可能有如明史记载明末战乱秦王不知所终,未建陵园;还有一种可能是至今未发现。依据调查数据,秦藩王陵园基本是正南北方向,第一代愍王陵园面积最大,接近正方形,往后陵园面积变小,也变得狭长。陵前石刻配置当有9对,目前所见没有完整的,在第八代宣王陵前首次发现马及牵马人,但是低矮臃肿。陈冰对秦藩陵园内的墓冢分布特征所反映出的丧葬礼制等规律、历史文献、地名学及守墓制度等相关问题展开探讨,提出了六条保护建议[28]。

图八 咸阳机场二期M54出土的陶九枝莲灯
三、墓葬
2008年以来,墓葬考古从西晋到宋元时期,均有数量不等的发现。西晋、十六国时期墓葬发现百余座,西魏墓葬发现较少,但多为纪年墓,特点显著。北周墓葬数量不多,但等级较高,隋唐墓葬数量较多,贵族平民均有。宋金墓葬极具时代特点,出土的瓷器、画像砖及壁画为以前少见,元代墓葬的壁画是一大特色,明代墓葬以家族墓葬为多,多石室、石棺。
(一)西晋墓葬
1989年在东郊田王发掘一批西晋墓,其中M426前室有 “元康四年” 墨书题记,结合该墓出土新莽钱币和东汉五铢钱,可确定墓葬年代为西晋惠帝元康四年(294年)[29]。以此为标准,确定了关中西晋墓的特点:墓葬形制有单室、双室、多室几种,西晋早期墓葬形制继承东汉之制,其后开始变化。甬道劵顶较平,前后室之间设后甬道,一般前室放置器物,后室葬人。多室墓侧室也会葬人。随葬器物中出现了陶俑、多子格等典型器物。近十年来,西安发现的西晋墓如下:2007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南郊庙坡头村南发掘1座[30],2012年,在长安区茅坡村发掘西晋墓1座[31],2009~201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机场二期扩建工程中,在底张、西蒋村发掘西晋墓9座。值得注意的是墓葬中出现了新的器物—空柱盘,关于其用途,有灯台、帐座、盛放实物等说法[32]。
(二)十六国墓葬
关中地区发现的十六国墓葬约70余座,多数位于空港新城的洪渎原、咸阳北原以及西安市近郊。1995~2001年,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在咸阳市北部的头道原一带发掘24座十六国时期墓葬[33],其中文林小区9座墓出土刻铭砖6件,有前秦建元十四年(公元378年)纪年砖1块,为关中地区首见。岳起、刘卫鹏根据新发现的纪年墓,对关中地区十六国墓葬进行了初步梳理和认定,确定了十六国墓葬的形制、出土器物等特点[34]。
十六国墓葬多以家族墓地的形式出现,排列有序。均为带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墓道平面均呈较长的长方形,以南向、东向居多。流行在墓道壁设置1~5个生土台阶,以两级台阶最常见。少数墓葬带1~2个长方形的天井。墓道斜坡前段平缓,后端陡深。部分在墓道北壁、过洞口上部生土上雕刻有门楼。绝大多数墓葬在墓道终端的甬道口设有封门。封门分砖质和土坯两种,以砖质封门常见。砖质封门以小砖为主,也有一部分用空心砖或空心砖与小砖混用。封门绝大多数为一道,设于甬道口的墓道末端,墓室口基本无封门。甬道平面多呈长方形,也有一部分呈梯形。梯形甬道一般口小里大,均为土洞弧顶或平顶,以弧顶为主。
墓葬形制有单室、单室带耳室、双室、双室带耳室几种。主室平面均为四边形,四边长度相等或相近,顶呈四面起坡式的攒尖顶或穹隆顶。侧室平面呈长方形或梯形,弧顶或平顶。
一般情况下墓室葬具为木质单棺,仰身直肢葬,以多人合葬为主,盛行祔葬;随葬器物一般陈放于主室的两侧、四隅和墓主的头部附近。单室墓的随葬品主要陈放于墓室东西两侧,前后室(或带侧室)墓随葬器物一般陈放于前室,侧室、后室一般用来葬人。

图九 咸阳机场二期M298出土女乐俑

图一〇 咸阳机场二期M298出土马俑
出土器物有武士俑、乐俑、具装马、鸡、狗、猪等;生活明器有罐、仓、灶、井、碓、磨、连枝灯等;实用器有铜釜、鐎斗、熏炉、铜尺、铜(铁)镜、叉、簪、镯、指环及铜钱等。其中武士俑、乐俑、牛车和九枝莲灯最具时代特征。
十六国墓葬主要分布在咸阳北原一带及西安郊区,近十年来发现的主要有以下几处:
1.洪渎原墓葬区
2007年,我院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专用高速公路发掘9座[35]。2008~2011年,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中在底张、北贺、西蒋村发掘17座[36](图八),其中M298为坐南朝北的双室土洞墓,墓葬全长75.25米。墓道带四个台阶,宽6米。有2个天井、2个过洞。过洞口上方有在生土上雕刻的阙楼,甬道口上方也雕刻有门楼。墓室内绘壁画。该墓是关中地区目前所见规模最大的十六国墓葬(图九、一〇)。2012年,在空港新城空港花园小区发掘4座,2014年,咸阳市文物考古所在泾阳坡西发现1座[37],2017年,在空港新城窦家村发掘6座。在秦汉新城摆旗寨发掘1座[38]。
2.西安郊区
2007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南郊凤栖原杜陵乡焦村发掘1座[39]。2011年,西安东郊灞桥区洪庆街道办纺织工业新园发掘1座[40]。2017年,在西安市汉城南路发掘1座[41]。
随着十六国墓葬资料越来越丰富,相关的研究也在展开。对墓葬形制、出土陶俑、骑马俑、乐俑、釉陶罐等也有专门的讨论[42]。
十六国墓地的分布,与十六国都城的位置有极大的关系。前赵、后前秦、后秦均在长安建都,都城使用了西汉长安城东北宫城的一部分。十六国、北朝时期,只对局部进行重建、维修,北周延续使用。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汉长安城考古队在西汉长安城东北部勘探发现了东西并列的两个小城,具体位置在宣平门大街与洛城门大街围成的区域内。经对小城的城墙局部试掘,发现墙体建筑于西汉文化层之上,而墙体北侧地层堆积情况为:最下为西汉文化层,出土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材料。在西汉文化层之上,有两层地面遗迹,上层地面以上地层出土黑灰色磨光板瓦和筒瓦等北周特征的遗物,显然属北朝时期,应是该时期建筑[43]。201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调查发掘了5座古桥。其中4座位于西席村北,正对汉长安城北墙中间的城门—厨城门,称“厨城门桥”。另外一座位于高庙村北,正对汉长安城北墙洛城门,称“洛城门桥”。此桥便是北周的“宣平门桥”,通过此桥十六国北周时期渭河南北两岸畅通无阻,故作为十六国、北周都城周边最近的高原,洪渎原是十六国贵族最理想的埋葬之地[44]。
(三)北魏、西魏墓葬
1.北魏墓葬
近十年,关中地区发现的北魏墓葬,多见于西安南郊[45]和咸阳北原[46]上,墓葬均南向,斜坡墓道,带天井,墓室为方形或长方形穹窿顶,有的带有后室或者侧室,出土器物以俑最有特点,另外还见有牛车以及少量青瓷器等。
陕西地区发现的北魏墓葬数量很少,很难概括出一个清晰的特征。陕西地区北魏墓葬很大部分仍承继了西晋、十六国的因素,包括墓葬形制、随葬品的类型等。随葬品中陶俑占比很大,颇具自身风格特点。倪润安通过对关中地区发现的北魏墓葬综合分析,认为关中地区北魏墓葬文化正处在逐渐接受洛阳地区文化的过程中,同时也显现出地方特色[47]。张全民则对关中地区的北魏陶俑从制作方法和演变方面做了研究,认为北魏前期,陶俑基本上延续了十六国时期的工艺和风格,到了北魏晚期,才逐渐形成了组合完整、特点较为鲜明的陶俑群,同时兼有分模制作和单模制作两种工艺[48],前者至西魏后不再使用,后者则被西魏北周沿用,最终形成了当时关中特有的一种陶俑形制。
除了关中地区之外,2011年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在陕西靖边距统万城约3公里处清理了5座北魏晚期至西魏时期墓葬,这批墓葬墓室均在生土上雕刻出仿木结构的柱子、斗拱等,墓葬的主人应为北朝时期统万城居民,其中M1墓主或为粟特人,壁画题材包含有浓厚的佛教因素。这批墓葬的发掘对研究中国北方地区特别是统万城周边地区北朝墓葬的葬俗及统万城居民的构成与宗教信仰具有重要意义[49]。
2.西魏墓葬
近几年陕西地区连续发掘了6座保存较好、并有纪年的西魏墓葬。2014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南郊韦曲北原上发掘大统六年(540年)娄氏和大统十四年(548年)长孙俊合葬墓[50]。2015年在长安郭庄发现2座西魏墓葬[51],或为乞伏氏家族墓葬,其中M2墓志记载为大统七年(541年)茹茹族乞伏孝达和吐谷浑晖华公主的合葬墓,M3则为西魏末废帝元钦时期茹茹族乞伏永寿妻临洮郡君墓葬。2017年7月在咸阳摆旗寨清理大统四年(538年)陆丑墓[52],同年8月在咸阳西郭村发现大统十五年(549年)袁纥頠墓[53]。
西魏墓葬的研究囿于发现数量少,认识尚较模糊,学界多将其做为北魏和北周的中间阶段,并未截然分出。张全民对关中地区北魏和西魏墓葬中出土的陶俑做了分析和研究,并且把西魏陶俑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基本概括出了西魏陶俑的特点,北周陶俑群正是沿着西魏的传统继续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特征。直到隋代统一以后的大业年间,关中地区才在北周、北齐俑群特征的基础上,融会形成了隋代陶俑的特征[54]。赵强通过对姬买勖墓和邓子询墓与已发表的西魏墓葬的对比分析,认为西魏国祚短暂,尚未形成严格的墓葬制度,姬买勖、邓子询墓葬的形制,更多的受到西晋方形单室砖墓的特征的影响,其墓葬形制具有过渡性。同时文中还对姬买勖、邓子询墓志做了释读[55]。
(四)北周、隋墓
1.北周墓葬
在配合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一期建设的考古工作中,我院等发掘了一批有明确纪年的北周墓,确定了洪渎原为北周的贵族墓地之一。北周墓葬形制以斜坡式土洞墓为主体,竖穴次之,少见砖室墓。墓道修建规整,天井数量不等,有的墓葬天井长度不一。墓室有单室、单室带耳室、双室、双室带耳室数种。有的墓葬还开有小龛。随葬器物以陶器为主体,骑马出行仪仗是常见的配置。仓、灶等庖厨用具齐全,男女侍俑较多。但个体较小,制作粗糙。高等级墓葬有少量青瓷及青铜药具。
2007年在咸阳市渭城区底张镇龙枣村发掘北周独孤宾墓[56]。独孤宾原名高宾,由北齐投奔北周,依附于独孤信门下,赐姓独孤。其子高颖为隋代名相。在渭城区正阳镇柏家嘴村发掘郭生墓[57],该墓使用石门、石棺。石棺四周有线刻,棺盖为太阴、太阳,左右两侧为青龙白虎,前档上部朱雀下为石门图案,两侧有柱剑门吏线刻。后档为玄武。前档座上刻一组六人的乐舞图。2009年,在长安区夏殿村发掘莫仁相、莫仁诞父子墓[58],是近年在西安南郊发现的规模较大的北周墓。2010年,在机场二期建设的布里村发掘拓跋迪夫妇合葬墓[59]。2010~2012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长安区高望堆村发掘4座北周家族墓[60]。其中3座有纪年,为天和二年(567年)张猥墓、建德元年(572年)张政墓和天和六年(571年)张盛墓。2013年在空港新城邓村发掘2座古代墓葬[61],其中一座为北周新昌公宇文某夫人拓拔氏墓。201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空港新城陶家寨西北发掘北周建德六年晋顗墓[62],出土玉佩2组、东罗马金币3枚及色彩鲜艳的陶俑70余件。
2.隋代墓葬
近十年来,隋代墓葬发掘40余座,其中纪年墓较少。根据以往的发现,多位学者对其进行研究,申秦雁的研究范围为中原地区。刘呆运根据新出土的资料对关中地区隋墓形制和葬地进行了研究。张全民对隋代陶俑的演变进行了研究[63]。关于隋墓特点可总结如下:
墓道:平面形制多呈长方形或梯形,上口略大于下口。斜坡地面经踩踏较平整,东、西两壁一般都经铲平修整,表面均光滑。
过洞和天井:过洞平面呈长方形或方形,土洞式拱顶。多数过洞入口处两壁稍有收分。地面为斜坡,坡度同墓道,壁面光滑,起券处较高,拱顶弧度大小各异。天井平面均呈南北向纵长方形,早期的天井南、北两壁从开口至过洞顶的高度处逐渐斜收,天井东、西两壁基本竖直。隋代后期,天井四壁均较竖直,天井开口已逐渐变短,与初唐墓葬天井趋于一致。隋墓天井四壁表面一般不作修整,壁面略显粗糙。

图一一 咸阳机场二期唐墓M92及围沟全景
甬道:其水平进深大小不一。平面呈纵向或横向长方形,均为拱顶土洞式,起券高度、拱顶高度一般与过洞相当,而低于墓室顶部高度。大多数甬道地面与墓室地面高度相平,两壁面均作铲平修整,平整光滑。早期甬道位于墓室南壁的中部或偏西,晚期开始向东部偏移,使墓室平面成刀把形。
封门:封门一般位于甬道入口处或墓室入口处。土坯或砖砌,土坯多为草拌泥制作。一层顺平、一层顶向错缝平砌。石门一般见于双室土洞墓、单室土洞墓中。
墓室:墓室一般修建的不是很规整。平面形制多样,有长方形、方形、梯形、平行四边形、不规则方形等。墓顶多数为拱顶式,个别为四角攒尖式。
棺床:有砖棺床及石棺床,砖棺床均用条砖平辅,砌砖方法丁、顺错杂,随意性很大。棺床早期多为东西横向设置于墓室北部,晚期南北纵向置于西侧的较多。没有棺床的棺木也基本按照同一规则放置。高等级墓葬中出现石棺。
随葬器物分为镇墓类、出行仪仗类、庖厨用具类、家禽家畜类、生活用具类。镇墓类的武士俑及镇墓兽来自两个系统:继承北周风格的个体略小,继承北齐风格的个体略大。随葬品中的釉陶和白瓷是这一时期的特色。特别是白瓷,胎质细腻光滑,做工精细,尤其透影杯更是少见,工艺水平极高。
十年来发现的隋墓主要有下面几处:
200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边方村、布里村发掘隋墓4座。其中鹿善夫妇墓[64]与元威夫妇墓[65]较为典型。墓建造规整,墓外建有兆沟。对研究墓葬制度尤为重要。元威夫妇墓内出土一组白瓷,出土的方镜也较为少见。同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长安区韩家湾村发掘隋苏统师墓[66],出土瓷器5件,其中透影杯器壁最薄处仅厚1毫米左右,杯体上半部分胎釉融为一体,如玻璃般呈半透影状。
2010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长安区何家营村发掘隋开皇十八年韦协墓[67],墓葬为斜坡墓道带三个天井的土洞墓,在三个天井下绘有列戟、仪仗图,墓室四壁绘女侍及内侍,惜只存西壁及北壁局部下半部分。
201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枣园西路三民村发掘隋代小型墓30座[68]。这批墓葬结构特殊,墓室地面也为斜坡状。每墓葬一人,头向南。随葬器物较少,多为小瓷盒、小罐和五铢钱。发掘者认为应该是隋代宫人墓地。
(五)唐代墓葬
陕西地区的唐墓,集中发现在唐都长安及其周边区域。围绕西安周围的黄土台塬分布。北至渭河以北的底张湾,南至长安县韦曲镇之南的神禾原、少陵原;东至浐河两岸的龙首原、长乐原、白鹿原、铜人原、洪庆原;西至长安县西北的高阳原、细柳原等范围内,均有唐代墓葬被发现。尤其地处唐长安城东以及东南近郊的龙首原、白鹿原、铜人原、洪庆原,之南的凤栖原、少陵原、毕原等地,分布更为密集[69]。
2007~2017年,陕西省内共发现唐代墓葬500余座,分布在西安西郊、南郊及西咸新区周围,多为配合基本建设、少量为主动性发掘项目,配合基本项目主要有2007~2017年咸阳机场二期项目,共发现唐墓60余座,其中纪年墓30余座(图一一);2008~2010长安区韦曲街道办韩家湾村西,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1000兆瓦太阳能光伏电池项目一期工程”建设项目用地共发现唐墓30余座,其中纪年墓8座;2008年,枣园三民村清理唐墓22座,4座纪年;2009年西安烟草物流项目发掘的唐纪年墓,为清河房氏成员;2010年灞桥枣园村墓,发掘唐墓7座,其中纪年墓4座;2011年长立丰惠泽苑项目发掘唐墓25座;2012年长安万科二期项目,共发现唐墓百余座,其中纪年墓十余座;2014年,西安西郊金色悦庭项目清理唐墓7座;2014~2015年,泾阳太平堡遗址墓群清理唐墓30余座。主动性项目有2008年的西安庞留唐武惠妃墓、2014年的长安郭庄韩休墓、2014年的华阴唐宋素墓、2016年富平献陵陪葬墓李道坚墓等。大量实物资料的出土,推动了唐墓相关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如墓葬形制、墓内随葬品、墓葬壁画的研究及墓葬的文物保护工作,尤其是关于墓葬壁画和墓志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细致。正如陈寅恪所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70]。

图一二 唐窦希瓘墓出土壁画
上述唐代墓葬中,壁画墓中保存较好的有唐韩休墓[71]、唐李道坚墓[72]、唐武惠妃墓[73]、长安航天城M13(诸葛芬)和M4[74]、长安韩家湾村M29和M33[75]等。这几座壁画墓的时代从初唐延至晚唐,内容丰富。尤其以唐韩休墓墓室内的山水图和乐舞图最为完整。出土三彩器的墓葬有唐杨贵夫妇墓[76],墓内出土了三彩侍女俑和模型明器等;西安杨家围墙唐墓[77]内出土的三彩扁壶,保存较好。此外,还发现了一批唐代名人墓葬,如唐昭容上官氏墓[78]、唐执失思力墓、唐窦孝谌墓及其子窦希瓘墓[79](图一二)、长孙无傲夫妇墓[80]、户部尚书李承嘉墓[81]、殿中侍御医蒋少卿夫妇墓葬[82]、司农卿秦守一墓葬[83]、兵部尚书戴胄夫妇墓[84]、凉国夫人王氏墓[85]、泾原镇海节度使周宝之妻博陵郡夫人崔氏墓[86]等。任职县令的墓葬有敦煌县令宋素墓[87]、洛州密县令冯孝约墓[88]等。唐代家族墓地新发现有郭子仪家族墓地[89]。目前,已发现的郭氏家族成员包括郭暧和升平公主墓、郭曜和王氏墓、郭仲文墓、郭仲恭和金堂公主墓、郭锜和卢氏墓、郭钊和沈素墓、郭锷墓、郭在岩墓等,郭子仪家族墓中出土了诸多珍贵的墓志以及丰富的随葬器物。唐代令狐楚家族墓成员墓,包括令狐缄墓和裴氏墓[90]。两墓均为竖穴墓道单室土洞墓。据墓志记载,令狐缄为唐代文学家令狐楚侄,葬于唐咸通六年(865年);裴氏丈夫为令狐均,葬于乾符四年(878年)。
另外,还有两处外来人群墓葬。一处是唐代百济国遗民祢氏家族墓地[91],共发现3座墓葬,出土了2合墓志,可推断3座墓为祢氏祖孙三代,为探讨唐代百济国祢姓的渊源提供了重要证据。另一处是唐代突骑施王子光绪墓[92],墓中出土了各种类型的陶俑和墓志。墓志所载内容,为我们研究西域历史、西突厥史、突骑施活动都提供了重要资料。
此外,在配合基本建设考古中,发掘出土了一批特殊人群的墓葬,如唐代女官墓[93]和宫女墓[94]。女官墓墓主为宫廷五至七品女官,官职司正等,墓志未载墓主年龄及籍贯。宫女墓形制较简单,为木棺单人葬,均有漆盒等漆器出土。
在发现的众多唐墓中,以韩休墓、窦孝谌墓、昭容上官氏墓最具代表性。现简介如下:
1.唐宰相韩休墓 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大兆街办郭新庄村南100米处。该地在杜陵东南2公里的少陵原上,是唐代重要的墓葬区之一。在该墓西侧有著名的韦氏家族墓、郭子仪家族墓、长孙无忌家族墓,该墓南侧为武惠妃敬陵,东侧为唐代宰相杜如晦家族墓葬。该墓为长斜坡墓道单室砖室墓,平面呈“刀把”形,坐北向南,方向175゜。南北水平总长40.6米,由墓道、5个过洞、5个天井、6个壁龛、砖封门、石门、甬道、墓室、棺床组成。墓内共出土随葬品186件(组),多发现于西二龛内,其余散布于甬道和墓室内,包括陶俑、陶器、瓷器、铁器、石门及墓志等。在墓室入口放置有两合墓志,载其墓主为唐玄宗朝宰相韩休,开元二十八年(749年)八月葬于少陵原,夫人为河东柳氏,天宝七年(757年)十一月合葬于此。墓葬内甬道和墓室绘制有精美的壁画,是本次考古发掘最重要的收获。甬道两侧为侍女图、宦官抬箱图。墓室顶部为日月星象图,南壁为朱雀图,北壁西侧为玄武图、东侧为山水图。西壁为树下高士图,东壁为乐舞图(封三,2)。
2.唐豳国公窦孝谌墓 位于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二期工程新修停机坪内偏北中部,原属咸阳市渭城区底张镇西蒋村农耕地。2009~2010年发掘,该墓被盗严重,墓上分布有封土、祭祀坑、石刻。现存封土底径约23、顶径约4、残高10米。封土东北约0.3米处有一长方形祭祀坑,坑内殉葬动物。封土以南从北向南,立石羊、石虎、石人各一对。封土下为斜坡墓道多天井双室砖券墓室,平面呈刀把形,坐北向南,方向180゜。墓葬水平总长74.2米,由墓道、5个过洞、5个天井、2个壁龛、前甬道、前室、后甬道、后室等部分组成。壁龛开于第三过洞两壁。后室西侧以砖砌棺床,其上置石椁,人骨多已无存。墓内绘有壁画,墓道两壁为祥云、导引人、青龙、白虎,北壁绘门楼。过洞天井两侧壁绘有侍女、牵牛图、宝相花等,墓室壁画保存较差。共出土随葬品77件(组),有武士俑、骑马俑、侍女俑、风帽俑、三彩盒、三彩马头、玉珠,鎏金铜泡钉、鎏金铜马镳以及石人、石虎、石羊、石门残块和华表、墓志等。
3.唐昭容上官氏墓 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北杜镇邓村。墓主为唐中宗昭容上官氏,即唐代著名女政治家、诗人上官婉儿。该墓系斜坡墓道多天井和小龛的单室砖券墓,坐北向南。由墓道、5个天井、5个过洞、4个壁龛、甬道和墓室等部分组成,全长36.5米。壁龛内放置彩绘陶俑,未被盗掘扰动,保存较好。甬道内放置墓志一合,盖题“大唐故昭容上官氏铭”。志文为楷书,近千字,记载上官昭容的世系、生平、享年、葬地等信息,依此可确定墓主人的身份。
除大量的考古新发现外,唐墓发掘报告的整理出版也有很大收获,如唐懿德太子墓、唐顺陵、唐武惠妃墓、唐韦贵妃墓、唐嗣虢王李邕墓等[95]。同时,关于唐代墓葬的综合性研究专著也涌现出来。包括对整个陕西地区唐墓综述性研究,关中地区墓葬的分区分期研究,墓葬壁画研究[96]等方面。如墓葬形制与分期、壁画、随葬品、丧葬制度和习俗、墓志、文物保护等。同时,对墓葬中所包含的宗教文化因素也开始了广泛的探讨[97]。而墓葬出土遗物的现场保护和提取也越来越科学有效,更多更先进的科技手段不断被应用到考古现场信息资料的采集工作中[98]。
唐墓壁画的研究包括壁画的分期、题材、布局、风格、形式及意义、局部内容的考释、制作工艺、文物保护等方面。发表的论著有《唐代墓室壁画研究》[99]《唐墓壁画研究综述》[100]《唐墓壁画中周边民族文化因素及其反映的民族关系》[101]此外还有一些壁画图录等。
墓志类研究近年来颇受学界的关注。墓志研究主要从志文记载的墓主生平经历、相关历史事件、家族谱系、宅地葬地、墓志撰文书写、墓志纹饰研究等方面补史证史。关于家族墓地研究,重要的有郭子仪家族墓志研究[102],百济移民祢氏家族[103];墓志中史学、文学研究,以唐上官昭容氏墓志、唐李建成墓志、唐韩休墓志、李应玄墓志和姬揔持墓志为代表[104]。
同时,各类墓志[105]汇编等综合性研究成果也纷纷涌现,《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誌》[106]将同一墓地考古发掘出土的墓志按照古籍整理的标准结集刊布,并附出土现场信息和照片,大大拓展了碑刻文献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是考古与历史文献研究紧密结合的有益尝试。
在唐墓研究方面,一些以往不被关注的方面,如墓葬建造过程和技术、墓葬壁画的多学科研究、陶器随葬品的研究等,都有了一定的进展。发掘窦孝谌墓、韩休墓时,由于仔细记录了墓葬筑造时留下的痕迹,为复原墓葬建造的过程、探讨唐墓建造技术积累了珍贵的资料。墓葬壁画研究中,检索历史文献,将出土壁画放到当时社会大环境、墓主地位和家世的小环境以及绘画史发展大框架中进行探讨,拓展了唐墓壁画研究的空间和深度。在唐墓随葬品研究方面,迄今对出土陶俑、唐三彩、金银器的研究较多,《隋唐五代时期灰陶制品》则是关于唐墓出土陶器演变专题研究的有益尝试[107]。
总之,唐墓的考古发掘工作更加科学规范,研究视角更加客观、开阔和深入。
(六)宋金元墓
相较于汉唐,陕西宋金元时期墓葬发现数量较少,但近年吕氏家族墓、甘泉金墓、刘黑马家族墓、横山罗圪台壁画墓、蒲城洞耳壁画墓重要发现,为宋金元时期墓葬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1.宋代墓葬

图一三 韩城宋氏壁画墓北壁下部墓主图
陕西地区宋代墓葬按照建筑材质可以分为土洞墓和砖室墓,其中土洞墓较多。根据目前公布的材料,土洞墓主要发现于关中地区的西安市周边[108]、蒲城[109]、蓝田[110]、凤翔[111]等地。墓葬形制基本一致,墓道为竖穴土坑或斜坡带台阶,墓室基本呈长方形土洞,有的带有小龛,既有单人葬,也有多人合葬,出土随葬品除吕氏家族墓特例外,大多较少,一般为数件瓷器和陶器,最常见的是铜钱。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葬,该墓地共清理墓葬29座,有规划完备的墓地。墓地周绕平面如长颈瓶形的围沟。家庙遗址1座,位于“瓶颈”处,29座墓葬则分布于“瓶底”部位。出土文物700余件组,砖、石墓志铭24盒。墓葬排列规划整齐,约呈横向三排、纵向南北成轴的布局。南端为长,中轴线上自南向北纵向排列长子长孙墓;横向则按辈分分排布置。墓地使用时间为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至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共埋葬五代吕氏族人。墓葬皆为竖井墓道土洞墓室,坐北朝南,深7.5~15.5米,形制分为单室、前后双室、并列双室、单前室双后室、主室带侧室五种,顶部近平或略拱。其中有5座墓葬主室上部纵向叠置1~2个空墓穴,其作用应属防盗设施。葬具已朽,仍可辨有木棺或棺椁,人骨基本为仰身直肢。随葬品有丰富精美的瓷、石等遗物[112],且多为成套的餐具、茶具、文房用具、酒具等,是研究宋代士人生活和北宋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
陕西地区发现的宋代砖室墓较少,但是分布范围较广,见于陕西全境。按照墓室形制,大致可以分为长方形券顶墓和方形穹窿顶或攒尖顶墓葬两种,前者见于西安市和韩城市,在西安市西南乳驾庄发现1座,墓葬为竖穴墓道长方形砖室墓,墓室内砌出仿木结构及门窗等,并施彩绘,出土陶器、瓷器及铅器等[113]。2009年韩城宋代壁画墓,该墓为单墓道长方形砖室夫妇合葬墓。墓室东、西、北三壁绘满壁画,色彩鲜艳,保存完好。墓室北壁正中为坐于书法屏风前的墓主人画像,墓主像左右两侧为研方备药场景的画面。整个画面暗示墓主生前应有从医的经历(图一三)。东壁为佛祖涅槃图,西壁壁画为北宋杂剧演出场景[114]。
方形砖砌墓见于渭北和陕北地区,墓室内均有简单的仿木构,墓壁有壁画及砖雕等[115]。2010年在合阳县王村镇蔡村发掘2座宋墓,为长方形竖穴墓道八边形砖室墓,攒尖顶,墓室内有仿木结构的砖雕斗拱、屋檐、柱子,墓壁镶嵌佛教和世俗图案的砖雕。该墓除发现1枚牡丹纹铜镜外,未发现其他随葬品[116]。2012年统万城遗址东南发掘北宋墓葬3座,墓道为带有台阶的斜坡式,墓室为砖砌,基本呈方形,内设棺床,叠涩顶或穹隆顶,四壁用砖砌出门窗,随葬品极少,有铜钱、铁器、瓷器等[117]。2008年8月在陕西西乡县发现1座宋墓,墓葬未公布详细资料,但是从图片大致可知墓室为长方形砖室墓,墓壁用砖砌出仿木构斗拱,墓室内设有棺床,随葬有精美的瓷器[118]。
目前对于陕西地区宋代墓葬的研究,多集中在墓志考释[119]和器物[120]研究上,对于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葬[121]和韩城北宋壁画墓[122]的专题研究较多。
2.金代墓葬
陕西地区金墓较有特色集中发现于陕北和关中两个大的区域。陕北地区金代墓葬主要发现于延安市甘泉县[123],墓室为砖砌单室或多室,墓室内装饰砖雕仿木构等。主要的壁面装饰可以分为砖雕画像和壁画两类,前者内容主要表现颇具地域风情社火场景(图一四),孝行图比较少见[124];壁画则多见孝行故事[125]。另外在富平、甘泉、合阳等地还发现了一批佛徒火葬时使用的陶棺,灰陶,质地坚硬,在棺挡地方写有“大师父”等题记[126]。

图一四 陕西甘泉县金墓出土彩绘砖雕
关中地区金代墓葬可分为砖室和土洞墓两种,砖室墓又有券顶墓和穹窿顶墓两种。穹隆顶墓发现4座,位于渭南市靳尚村,墓道为带台阶斜坡形,其中M1墓室内绘有伎乐类壁画,壁画直接绘于砖壁上,没有地仗层[127]。券顶墓在西安市曲江发现1座,为竖穴墓道长方形砖室,墓室后部设棺床,随葬品较多,有耀州窑酒具、钧窑食器、金属器、买地券等[128]。土洞墓发现较多,多位于西安市南郊,多为竖穴墓道,随葬有铁猪、铁牛等[129]。
3.蒙元墓葬
陕西地区发现的蒙元墓葬主要分布于陕北和关中地区,且两地葬俗葬制有着明显的区别。
关中地区发现的蒙元墓葬20余座[130],大部分位于西安南郊[131],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在曲江夏殿村发掘了12座蒙元时期刘黑马家族墓葬,该墓地布局完整,随葬品组合清晰,为关中地区同期墓葬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132]。此外在西安市东郊十里铺和高陵泾河工业园也有个别发现。这批墓葬均为土洞墓,墓室多为方形,少量近圆形,尸骨葬为主,随葬品仍然以灰(黑)陶俑和陶器最富有特色,另外还随葬有瓷器、金属器等。
以灰(黑)陶器作为随葬品的习俗目前只发现于陕西、甘肃、河南三省,杨洁认为,其中陕西关中地区在这种习俗中起着主要作用。
在陕北地区发现2座元代壁画墓,分别位于榆阳区[133]和横山县[134],这两座墓葬均为八边形石室墓,墓室内通绘壁画,内容主要有夫妇并坐图、孝行图、伎乐图、出行图等,同样的墓葬形制之前在蒲城地区也有发现[135],但这三座墓与西安市韩森寨发现的元代壁画墓[136]风格有着明显的区别,前三者有着浓厚的蒙元特征,后者则为汉地风格。
虽然此期榆林地区与关中地区在墓葬形制和随葬传统上有着巨大差别,但双方也存在一定的交流和融合。1987年在延安市南柳林乡虎头峁村发现的2座元代石砌墓葬,形制均为抹角八边形穹窿顶单室墓,并随葬有黑陶俑及黑陶器。其墓葬形制为陕北地区的传统,并有一定的改变(由直角多边形变为抹角多边形),而随葬品则当为关中地区因素,因此虎头峁元墓是蒙元时期陕北和关中二区域墓葬文化势力共同结合的产物,两种墓葬文化在位于二者之“中”的延安地区“合二为一”。
近年陕西多座蒙元墓葬的发现,推动了蒙元时期考古的研究。除了对于关中地区蒙元墓葬的综合研究[137]之外,主要集中于陶俑研究[138]和墓志释读两个领域[139],也有学者对于早年发掘的蒲城洞耳村墓主族属进行了考证[140]。
(七)明墓
十年来,陕西地区发掘的明墓超过80座。墓主身份上至明藩王家族,下至一般平民,时代大多为明中晚期。
小型墓发现范围广、形制单一,大多为竖穴墓道土洞墓,如澄城县善化乡明墓、咸阳西石羊庙墓群、黄陵西寨子明清墓地、汉中勉县老道寺杨寨墓、西安新筑西坡墓地、长安南留墓葬等。
大中型墓葬主要分布在西安南郊、泾阳、三原、高陵等,尤以高陵县最为集中。西安南郊明墓以明藩王家族墓为多,高陵县明墓为张氏等几大家族墓地,这一区域明中晚期流行石椁或石券墓,墓门上部多有仿木构的额枋等石雕刻,颇具地域特色。
大中型墓以万历十年为界,成化至万历十年以前为明中期,万历十年以后为明晚期。明中期墓葬相对较少,代表性的有以下几处:
西安南郊明上洛县主墓,为阶梯状斜坡墓道的单室砖券合葬墓,墓室东、西、北壁各有一座砖券壁龛,墓门上有仿木结构砖砌门楼。葬具为一棺一椁。出土有彩绘木俑、木器、铜钱、幽堂(买地)券、墓志等。墓主为明保安王嫡长女,逝于明成化六年(1470年),明成化七年(1471年)葬于此地[141]。
铜川市未来新城小区明墓,为斜坡墓道带天井、过洞的单室砖券合葬墓。出土有釉陶器、瓷器、玻璃器、木器、织物、宋金旧钱等陪葬品。买地券记载墓主为任福,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年下葬[142]。
西安南郊曲江观邸明墓,为斜坡墓道的单室砖券合葬墓,墓室三面各有一个壁龛。出土有陶俑、铜钱等,并有墓志两盒,墓主为明嘉靖年间抚宁知县郭涞世及其夫人合葬[143]。
西安市广电中心基建工地共发现4座明墓,为秦藩王朱秉橘家族合葬墓,有3座为明正德、隆庆和万历初年,形制为斜坡墓道单室砖券合葬墓,单棺或多棺合葬。以砖室墓M26为例,墓门上部砖砌门楼,墓志放置于墓室顶部填土中,墓室内有砖砌祭台,左右两壁及后壁设有壁龛,红底花草、翔龙的彩绘漆棺椁出土有玉器、陶器、锡器、铁器等器物以及10件陶俑[144]。
西安南郊翠竹园二期项目,共清理明墓20座,多为弘治到万历以前。墓葬形制有竖穴墓道土洞墓、斜坡(有的带阶梯)墓道砖券或土洞墓,均为单墓室的单人或双人合葬。出土遗物较少,主要为铜钱及墓志,另有锡器、铜质佛像、冥币等[145]。
高陵徐吾村泾欣园住宅小区三期工地发掘25座明墓,均为平面甲字形的墓葬,以斜坡带阶梯墓道的单室土洞墓为主,并有少量砖券单室双人、三人合葬墓,砌仿木结构门楼。随葬品有瓷碗、铜钱、饰品等。根据出土墓志,为明中期隆庆、嘉靖、万历初年张氏家族墓地。
明代晚期墓发现较多。
西安市广电中心基建工地M25(1621年)为斜坡墓道单室土洞墓,墓室平面为梯形。墓门处有砖砌门楼,木质棺椁表面髹有红漆,绘有龙凤、花卉等图案。出土器物有瓷罐、铁器等。
三原县王徵家族墓,共清理3座墓葬,呈“品”字形分布,M23为带有长斜坡墓道的单室土洞合葬墓,墓室内并排置棺,中间墓主王徵木棺高于两侧木棺。墓室出土有玉瓶、玉香炉、砚台、黑瓷罐等物。其余2座晚到清代,均为多洞室合葬墓[146]。
高陵地区发掘的明墓有院张村明代家族墓及姬家安置区明墓、杨官寨明墓等。这三处墓葬均位于高陵县姬家乡附近。
院张明代家族墓,共发掘26座,从出土墓志可知,绝大部分为万历十年以后。墓葬可分为东、西两区,在西区发掘出土了一座完整的有夯土围墙的墓园,内筑三座呈“品”字形分布的墓葬。墓葬为斜坡带台阶或竖穴式墓道的多室合葬墓,由墓道、前庭和砖(石)砌仿木构门楼及砖砌或石砌墓室组成,其中两座石券墓分别有4个和2个石室,另外一座为砖券3室。出土的1块买地券和4块墓志表明墓主为明秦藩知印张栋(1535~1585年)及其子孙的家族墓。东区发掘19座墓,墓葬形制与东区基本相同。是以斜坡墓道为主,个别为竖穴墓道的券顶(或洞室)墓,多为并列双室或三室,砖、石门楼上雕出仿木构门脊、瓦当、滴水、斗拱及花卉装饰图案。出土随葬品以瓷器、锡器、墓主随身金银首饰为主,数量较少。
姬家安置区发掘有两处共7座墓葬,分属两个家族。根据出土的墓志记载,M5为山西省左布政使王翼明及其4位妻妾合葬墓。王翼明为晚明时期官员,去世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M4修建于天启二年(1622年),为明代奉政大夫工部管缮善司郎中王伊菴及其妻妾李氏田氏合葬墓。
彬县东关村明墓,为短墓道石砌双室夫妻合葬墓。主墓室三壁及顶部均绘有壁画,内容以人物、花卉、瑞兽为主。墓葬出土有铭旌、朱书镇墓砖、墓志、买地券等遗物,根据墓志记载,墓主纪泰葬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其夫人葬于崇祯三年(1630年)。在纪泰墓附近有其家族成员的墓葬[147]。
总结明中晚期大中型墓资料,在墓葬形制演变、随葬品、葬俗等有以下特征。
1.明代中晚期墓葬多为夫妻妾合葬墓,墓葬形制可分同穴单室合葬、同穴多室合葬两大类,有砖券、石砌及土洞墓。明代中期,中型墓多见斜坡墓道(有的呈阶梯状)砖券的单室合葬墓,长方形墓室的中后部棺床上,置一具或多具棺木,也有单室土洞墓内置多具石棺的。规模较大的墓葬,在墓室两壁和后部皆设壁龛,一般的仅在后壁开壁龛。明代晚期,单室合葬墓依然存在,但较少带壁龛,墓道多成斜坡带台阶状,而同穴多室合葬墓逐渐流行,土圹内并列多个砖券或石砌墓室,或直接掏挖成并排的土洞墓,墓室的数量依男墓主妻妾多少而定,墓室间隔墙上,往往开挖方形通道连接;墓室前部共用一个前庭,最前部一般为竖穴墓道或斜坡台阶墓道,墓道均较短。这种形制的墓葬一直延续至清代。无论中期或晚期,规模较大的砖、石墓,在墓门上部都砌出仿木构的额枋、屋檐等雕刻,晚期因多墓室并排,上部额枋瓦檐连成一体,更宽阔华丽,其前庭两壁也多砌出带滴水瓦檐的院墙。
2.葬具多为木棺,规模较大的墓葬有石椁。出土陪葬品以2~3件黑釉瓷碗、钵或罐较多见,丰富者还随葬有小件青花瓷器、锡器或铅器及墓主随身首饰,个别明藩王家族墓或品官命妇墓中见有彩绘陶俑、彩绘木俑、木器、玻璃器。此外,买地券、墓志也较多见,墓志有置于墓前庭、墓室内的,还有埋于墓封门上部填土中的。
四、陕西长城资源调查与研究
长城由墙体、单体建筑、关堡、营堡及相关遗存等组成,是一个由政府主持修建的军事防御工程体系。对陕西长城的研究,早就有学者开始关注,择其要者,有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对陕西境内的长城遗址进行了调查,对于长城的位置和保存状况有大致的描述[148],但是语焉不详。史念海从历史地理的视角,依据文献资料,结合实地调查,考证了长城延伸的方向和位置,但对一些遗迹的定性与断代缺乏考古学依据[149]。彭曦对战国秦昭王长城进行了全线考察与研究,详细记录了调查所见长城的分布,但对部分分布于河流山谷北岸或西岸的长城遗迹没有发现,在长城分布上也有一些误判[150]。艾冲对于陕西长城曾做过研究,指出隋长城被后来的明长城沿用叠压,但没有发现具体的隋长城遗迹[151]。通过前述的调查与研究,可以了解陕西长城的大部分遗迹的大体分布情况,由于缺乏全面系统的实地调查,对长城的认识,无法具体到每一个单体建筑或一段墙体的分布保存状况,对全部的长城遗迹分布、走向也没有宏观的认识和把控,未形成成熟、完备的长城研究体系。
2007年以来,长城遗址的实地考古调查全面铺开,对各时代长城遗址的具体长度、各类遗迹的数量、分布位置等方面的信息有了较详细的了解,尤其是对明长城遗址的精确测绘,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详实的基础资料。
陕西境内的长城主要有战国魏长城、战国秦长城(秦汉沿用)、隋长城和明长城等,长城墙体遗迹总长度是1802公里。
(一)隋长城
隋长城墙体遗迹全长18公里,由墙体和单体建筑组成,墙体都是堆土筑成,保存程度差;单体建筑为夯土筑成,但也圮毁严重,多数坍塌呈一个圆形土包[152]。
由于隋长城堆土而筑的特殊建造方式,加之修建过程短促,其后又被明长城沿用,一直未能被辨识。2007年以来调查发现的隋长城遗迹,分布在神木县、靖边县(图一五)、定边县。三个县区的隋长城由于大量被毁,现已互不相连。神木县段隋长城分布在明长城西北侧,靖边县隋长城与明长城相交,定边段的隋长城东与明长城相交,西接宁夏盐池县隋长城,再向西连接内蒙与宁夏境内隋长城,直抵黄河东岸。崔仲方所修筑的长城,就分布在今陕西北部向西经内蒙古南部与宁夏交界附近直达黄河岸边,可知隋长城的本来面目是同于后来的明代延绥镇长城“横截河套之口”。这种情况说明隋长城所选定的修建位置基本被后来的明长城所延续使用,这也正是隋长城比战国秦长城的进步之处。
(二)明长城
陕西省明长城即明代延绥镇边墙的大部分,墙体遗迹总长达1170公里,有单体建筑(马面、敌台、烽火台)1151座,关堡112座[153]。
墙体 全线土墙夯土土质以黄土为主,全部土墙现状基本呈脊状锯齿形或驼峰形。有少量墙体是以石构筑而成,大部分是纯以片石垒砌,有一段墙体是用片石垒砌两侧,内部用石块或片石堆砌填充。
还有利用自然险要经人为加工而成的墙体。称为山险墙。或是山险加以人工铲削而成,或是山险加以人工增筑补缺而成,增筑部分所用材料以片石为主。
还有利用自然河流而成的防御,称河险墙。
单体建筑 是单独建筑为防守、传信目的实体建筑,共调查到1286座。依据其功能可分为三大类别:马面、敌台、烽火台。
营堡 指规模较大的军事性驻军据点,营堡遗址现共有46座,部分是由于迁建造成,在明代同时存在作为军事驻地的约为36座,所以俗称为“三十六营堡”[154](图一六)。
明长城是为了防御北方的蒙古势力而修建的[155],整个长城系统包括大边、二边和三十六营堡。大边位于该防御带的北侧,主要防御外来的侵扰;二边位于南侧,是为控制内地军民不得出境;营堡分布其中,作用为屯兵驻守之处。大边和二边共同构成“夹墙”,形成延绥镇的纵深边防工事。
延绥镇明长城经过数次修建、不断完善充实形成的防御系统,最初是守在天险,又发展为守在界石,再发展为守在营堡,再发展为守在墩台、界石、营堡,再发展为守在边墙,最后发展为守在互市与边墙,至此长城系统臻于完备[156]。但此后再无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工程,并且长城在边防上的重要性逐渐降低,直至后来逐渐颓弃。

图一五 靖边隋长城-银湾村长城(由西向东)
考古调查资料,也为探索不同时代长城的发展演变规律打下了基础[157]。目前长城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尚需更全面深入的调查和研究。
五、陶瓷手工业遗址考古
陶瓷窑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是手工业考古的重要门类。近年来,随着聚落考古、城市考古理念逐渐完善,做为聚落或城市中手工业区重要组成部分的陶窑、陶瓷器制品、工艺技术的研究,逐渐被重视起来[158]。
陕西地区陶瓷手工业考古可分为陶窑和瓷窑作坊、窑炉两大类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陶窑有位于城之内的,兼烧砖瓦建材和陶器的,也有纯粹为陵墓建造服务的陶窑,二者的一致之处在于,制陶原料门槛较低,不像瓷窑对原料和燃料环境依赖性大,制陶技术的流向和陶窑的位置均主要因生产和消费需求而转移。一些为大型建筑服务的陶窑,往往建前设窑烧制,完成需求后随即毁窑平地。故陶窑大多延续时间相对较短,很少像瓷窑那样动辄延续百年以上。这也是虽然陶窑曾普遍存在,但遗址常难发现且保存不好的原因之一。陕西近十年发现的陶窑大多比较零星,唯独唐陵附近的陶窑,因其位置偏僻,故保存较好。
瓷窑遗址考古,主要为铜川耀州窑遗址的研究和澄城尧头窑址的勘探发掘。

图一六 定边明长城-安寺村营堡
(一)陶窑
1.桑园窑址 位于渭南富平县宫里镇涧头村,距唐定陵约1000米,是目前发现的最大的一处唐代砖瓦窑址,有个体窑炉545座,分16组分布,整体范围达0.9平方千米(图一七)。
据勘探发掘结果显示,每组窑均生产某一类产品。该窑场可分为五个功能区,有两个砖窑区、两个瓦窑区和一个特种窑区(产品为兽面砖、鸱尾等特种建材)。
每组窑炉分两排相对分布,共用一条兼做操作间的南北向通道,单组窑长度300米左右,窑炉最多达83座。各组窑平行呈北南向分布,间隔均匀,为60米左右,相邻窑组长度相当,两端基本平齐。
窑炉全部是平面马蹄形的半倒焰式窑,由窑门、火膛、窑床、烟囱几部分组成。窑门里是平面扇形的火膛,窑床近方形,窑床后壁底部有三个或五个吸烟孔通向后部烟室,由烟室顶部烟囱排出。大部分窑炉窑壁及以下部分为生土掏挖形成,窑顶砖砌,另有一部分窑炉包括窑顶全部在生土中掏挖,窑炉顶部完整,呈微弧形。
窑炉尺寸较大,如第四组Y261,是砖窑,窑床宽3.6、长3.4、火膛深1.5米。窑室两侧壁下部有引火槽,从火膛引至吸烟孔,后壁下部有五个吸烟孔通向烟室,由1个烟囱通向地面。
桑园砖瓦窑址位于唐定陵陵区附近,产品时代和种类与定陵陵园遗址出土物吻合,是专为唐中宗定陵建材生产开设的官方砖瓦窑场,隶属唐甄官署管辖。唐十八陵中有十一座唐陵都发现有附属的砖瓦窑,从数座到十数座乃至数十座不等,而桑园窑址是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一处,再现了唐代陶业的盛况,说明制陶业在唐代仍是比肩瓷器制造、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手工业门类。
2.小土门村陶窑遗址 位于西安市莲湖区小土门村以南,时代为唐代。共清理窑炉9座,均为平面马蹄形的半倒焰式窑炉,分为3组,第一组是6座,两两相对,共用一个操作窑道。出土有砖瓦残块等建筑材料、碗罐类生活器皿,还有镇墓兽、陶俑类等丧葬明器残块。
3.西郭村陶窑遗址 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底张镇西郭村,分布范围大约1000平方米,目前探明有10多座,发掘区共清理陶窑9座。其中有6座陶窑南北两排相对、分别共用一操作间,从出土砖瓦等建筑材料以及陶窑的形制来看,应属于隋唐时期。
4.银沟村陶窑遗址 位于富平县银沟村,此处曾是富平县唐—元代县城所在,分布着数十座陶窑,或呈“品”字形分布,或双排两两相对分布。经发掘的两座显示,窑炉为半倒烟式窑炉,时代为唐代,产品包括生活用品陶器、砖瓦建材、丧葬明器,但未见陶俑。
5.西安西郊窑头村陶窑遗址 位于唐长安城延平门西侧,共有陶窑9座,有多个窑室共用一个操作间的对窑、两个一组的陶窑和单体陶窑,时代为唐代中晚期。出土物以条砖、方砖、瓦当、筒瓦、板瓦等建筑材料为主,其次为盆、钵、罐、陶炉等日用器皿,另有少量陶拍、马头残块等[159]。
以上发现的唐代陶窑遗址,或为陵墓建材和随葬品烧制服务,如桑园窑址、小土门村陶窑、西郭村陶窑;或为城市建筑建材或日常用品生产服务,如银沟村陶窑。说明唐代陶窑生产,砖瓦建材和日用(随葬用)品是在同一类陶窑中生产。窑场布局模式分两种,窑炉个体数量多的成双排分布,窑炉个体数量少的或并排或呈“品”字形分布,均共用操作间;窑炉形制相对固定,仅个体尺寸和烟囱部分的局部结构略有不同,这一点与唐之前陶窑形制多、差异大的情况有别,说明唐代的建窑和烧成技术更稳定、成熟。唐代瓷器的生产处于起步和发展时期,陶器在日常生活中占比仍较多,银钩遗址陶窑中众多的陶器类型,为研究此期陶器发展提供了资料。

图一七 陕西富平县唐桑园窑正射影像图
(二)瓷窑
1.耀州窑址 2016年,为配合耀州窑遗址公园游客服务中心项目的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遗址区的北部进行了局部勘探,了解了黄堡中心窑场的北边缘区域的堆积分布情况。确认了黄堡窑场的北部边界。
调查勘探发现,在南距耀州窑博物馆2公里处、漆水河与312国道之间,地层堆积以宋金文化层为主,在中区范围内可能有五代文化 层的存在;地层堆积西高东低,南厚北薄,尤其南部仍有较密集的瓷窑、作坊和灰坑遗址分布。崖壁断面可见的作坊为窑洞式,与以往发现的形制相同。采集瓷片以青釉为主,尤其是金代翠青釉瓷器较多,另有少量黑釉、姜黄釉、月白釉瓷器残片等,可辨认出土器形以碗、盏、碟为主,另有少量的壶、器盖等器物残片。
近十年来,耀州窑考古发掘虽然很少,关于耀州窑的研究,近10年来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首先关于五代耀州窑青瓷的性质,自禚振西提出耀州窑五代青瓷产品是中国古陶瓷史上的柴窑后,引起了学界高度关注,学界同仁从文献记载的柴窑特征、地望和耀州窑及越窑、河南一些瓷窑产品特征等方面进行正反两方面的讨论和激烈争论,中国古陶瓷学会分别在2010年和2014年两次举行了围绕柴窑和耀州窑的小型研讨会和考察,民间收藏界也数次召开会议讨论,虽然至今并无确定的结论,但五代—宋初耀州窑天青釉瓷的工艺成就和意义也被学界所广泛认可[160]。同时,王小蒙对五代耀州窑与越窑、邢窑等工艺的对比研究,认为五代耀州窑青瓷以北方瓷器工艺为基础,融合南北瓷窑工艺精髓,最早创新了薄胎厚釉的天青釉瓷器,开启了中国官窑体系天青釉瓷的发展序列[161]。王芬等对五代—宋初天青釉瓷的胎釉成分进行了测试,归纳出了天青釉的呈色机理,认为天青釉瓷的烧成是当时的刻意追求[162]。彭善国和易立等通过对内蒙、东北及中原地区墓葬出土耀瓷资料的梳理,认为《五代黄堡窑址》中部分青瓷器应该属于宋代早期[163],张红星、穆青研究文章也持同样观点。
其次,耀州窑各时期造型、装饰工艺的特征及与同期中外其他瓷窑工艺交流的研究;耀州窑青瓷与金银器造型装饰的对比研究;通过研究,对耀州窑各期的风格特征、工艺来源有了更清晰深入的认识[164]。第三,窖藏、居址、墓葬出土耀州窑资料的梳理归纳,馆藏耀州窑瓷介绍,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耀州窑产品的流布研究[165]。
另外,陕西富平银沟遗址发掘出土了大量耀州窑各时代瓷片标本及其他窑场陶瓷、金属日常用品遗物和宗教遗物,结合银沟遗址附近曾经是唐富平县城—义亭城这一文献记载,这一区域很可能是分布着丰富手工业遗存的县城遗址。因距离耀州窑仅30余公里,故出土有大量耀州窑瓷器。至于此地是否有瓷器生产,并进而是否有可能和文献记载中的鼎州窑相关,目前考古工作还在进行中,有待于新资料的发现。
2.尧头窑遗址 位于渭南市澄城县尧头镇,是一处规模宏大的瓷器民窑遗址,因独特的黑釉剔花工艺与粗犷大气的器形装饰,且窑火不熄至今,被誉为“瓷窑活化石”。据考古调查、发掘和民间藏品判断,尧头窑瓷器最晚元代始烧,上世纪80年代前后逐渐停烧。产品种类丰富,以黑釉瓷最多,有“黑珍珠”之美誉。
201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第一次对窑址区做了大范围的、系统的调查,调查可见古瓷窑炉、作坊等遗迹点共有319处/组,其中窑炉遗迹130处,整个遗址范围分布达8平方公里。
2016年发掘了1000平方米,揭露出窑炉、作坊、加工原料的耙泥池等遗迹。发掘出土的文化堆积和遗迹、遗物可分为三期,早期包含物以M形匣钵窑具为代表,产品以黑釉碗盘类器为主,时代可早到元末明初;中期以支柱、搁板窑具为代表,产品以黑釉的碗盘类为主,并有青釉器,出现盆缸类大型器。发掘揭露的有Y5、Y6两座瓷窑,在Y5的窑壁上可见有利用废弃的搁板砌筑的迹象,窑室内也有搁板、支柱及黑釉涩圈碗等出土。这一时期对应的历史时代为明初至明代中期;晚期以直筒形匣钵窑具为代表,产品以黑釉、白釉、青釉器为主,器类更趋繁复。发掘的窑炉有Y1~Y4,以煤为燃料,此期对应时代相当于明代中期以后至解放后。解放前后尧头窑的产品以盆、瓮、海子等大型器为主,所以瓮窑区占整个窑区面积约三分之二,尧头窑地面可见的窑炉多属此阶段,发掘揭露的一处耙泥池,也属此期。
尧头窑是元代以后渭北地区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窑场之一,其元代受耀州窑青瓷影响较多,明代以后,与铜川陈炉窑、山西窑瓷器生产也有很多交流。
3.安坪村窑址 该窑址是调查所见,位于宁陕县安坪村。遗址面积约3600平方米。地表分布有大量匣钵,有几处较为集中的红烧土区域,偶见瓷片。初步判断,该遗址为宋元时代民间瓷窑遗址。
陕西古代瓷器手工业一直以来都是耀州窑生产一枝独秀,元代以后,耀州窑黄堡中心窑场的生产逐渐没落,周边自金代以来开始的瓷业则不断扩张。各窑场产品从以青瓷为主,向青瓷、黑瓷、白瓷、白釉黑花等多品种过渡。陕西瓷器生产“青”一色的格局被打破了。关中西部和秦岭以南等地瓷窑遗址的发现,填补了这一区域瓷器生产的空白。尧头窑遗址的系统调查和考古发掘,为了解渭北地区这一最大的窑场提供了资料。
六、佛教考古
陕西地区的古代佛教遗存主要包括佛教石窟、土窟以及寺院遗址三类。此外,还有少量出土于墓葬和其他遗址中的佛教遗存。其中,石窟遗存的数量最多,主要集中在铜川、延安、榆林三个地区,其余四类遗存的数量相对较少,陕北、关中、陕南地区均有分布。
石窟 7处。分别为2007年发现的延安市安塞县大佛寺石窟[166],2008年发现的宝鸡市岐山县宋家尧石窟[167]、2009发现的汉中市留坝县武关河佛教造像龛[168]及榆林市神木、府谷两县2015年发现的4处藏传佛教遗存[169]。其中,大佛寺石窟保存了典型的北朝佛教雕像与树下诞生、步步生莲、出游四门等佛传故事。宋家尧石窟造像均为石胎泥塑,题材以佛、菩萨、弟子为主,时代从北朝时期延续到盛唐时期。武关河佛教造像龛时代为隋唐时期,造像题材为一佛二菩萨、一佛二菩萨二弟子。神木藏传佛教遗存共计3处,分别为喇嘛庙石窟、庙沟石窟、王乐沟石窟;府谷县藏传佛教遗存1处,为石窑沟石窟。遗存主要为藏传佛教高僧造像、佛塔与六字真言、观音菩萨心咒等藏文经咒。
土窟 1处。为2017年发现的榆林市绥德县圪针湾佛窟遗址[170],6座洞窟均坐北面南。K1为僧房窟。K4为塑像壁画窟,塑像为三佛、二弟子、二胁侍菩萨、文殊、普贤的组合,壁画内容为药师佛与十二神将及炽盛光佛与九曜。此外,还发现有画像石、石柱、瓦等遗物。K5亦为塑像壁画窟,塑像为地藏菩萨与闵公、道明,壁画内容为地狱十王。此外,还发现有石贡器、瓦等遗物。K2、K3、K6均为小型龛式窟,后两者内发现有石造像龛、圆雕石造像等。该遗址洞窟组合完整,遗物丰富,时代跨度大,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化遗产价值。
寺院遗址 2处。分别为2009年发现的延安市富县广家寨寺院遗址[171]和2016年发现的商洛市镇安县毗卢寺遗址[172]。广家寨寺院遗址残存遗迹主要为两道南北向的石砌墙基和一道南北向的走廊(过道),遗物主要为北朝至宋代的石刻造像(或残块)300多件,数量大,风格多样,延续时间长,对于研究陕北地区的佛教传播、宗教信仰等具有重要的意义。毗卢寺遗址系一座元代密宗寺院遗址,发掘四边形石塔1座,建筑遗迹1处。出土石刻文字记载该寺建于元末明初,石塔修建于明弘治六年(1493年),对研究秦岭山区寺院结构以及明清宗教兴衰有重要意义。
与佛教相关的墓葬发现 5处。分别为2009年西安市南郊翠竹园二期明墓M36出土鎏金铜佛像和西安广电中心明墓M26西棺头挡板红漆描金佛像[173]、2010年咸阳市机场十六国墓M54出土彩绘九盏佛像莲花灯[174]、2011年榆林市靖边县八大梁墓地M1出土佛教壁画与雕刻[175]、2014年渭南市蒲城平路庙墓群M22出土砖雕佛传故事——涅槃图像[176]以及2017年西安市长安区大居安唐墓M2出土两件小型鎏金彩绘金铜佛教造像[177]。翠竹园二期明墓M36鎏金铜佛像火焰纹背光,高圆肉髻、双手合十、结跏趺坐于莲台上,穿通肩袈裟。西安广电中心明墓M26西棺头挡板红漆描金佛像穿通肩袈裟,结跏趺坐于须弥莲花座上,两侧侍立童子。机场十六国墓M54彩绘九盏佛像莲花灯由灯座及九个灯盏组成。在圆筒形灯架柄上,贴塑有两层8个佛教造像,禅定印、结跏趺坐于双层覆莲台上。八大梁墓地M1甬道入口处两侧于生土上雕刻柱式尖拱形仿石窟窟门。墓室东壁南、北两侧分别绘制一尊力士;北壁西部为主要表现胡僧礼拜舍利塔的场面。西壁南侧为一跪于绳床上的僧人与一立姿僧人。南壁壁画中可见跪姿僧人跪于绳床上的形象。
其它相关遗址 2处。分别为2016年发现的西安市雁塔区马腾空遗址出土的1件唐代泥塑佛头部[178]和2017年发现的空港新城遗址2号窑址内出土的65件北朝时期的彩绘泥塑佛教造像[179]。
考古发掘之外,陕西佛教考古近十年来在田野调查、资料刊布与相关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
2012年至2014年,陕西省文物局组织专业团队对陕西省铜川市[180]、延安市[181]、榆林市[182]三个地区的石窟遗存开展了专题调查,共计发现石窟遗存664处。调查结束后,及时整理公布了调查成果,用统一体例对每一处石窟进行了全面介绍。
此外还相继出版了1987年法门寺唐代塔基与地宫遗址发掘[183]、2012年至2014年药王山摩崖造像田野调查[184]、1973年青龙寺遗址发掘、1985年西明寺遗址发掘成果的考古报告[185]。同时,还对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收藏的百余件佛教造像精品[186]以及1985年田野调查所获药王山碑刻实物照片、测绘图、碑文拓本以图示、碑文著录[187]以图录的形式进行了介绍。
研究方面,马世长、丁明夷对陕西延安地区石泓寺等几处石窟进行了介绍和分析[188],冉万里用考古学方法对唐代长安地区佛教造像进行了综合研究[189],程旭对陕西馆藏造像资料进行了收集整理和初步分析[190],介永强对唐代长安城的佛教寺院建筑进行了综合研究[191],常青对麟游蔡家河石窟与喇嘛帽山千佛院石窟开展了综合研究[192]。
综上所述,2007年以来,陕西佛教考古在田野发掘与调查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新发现很多,遗存的类型与特征进一步丰富。一批考古报告、考古简报的出版刊布为今后的田野工作和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为下一步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专题或相关研究专著及论文的发表充分表明陕西佛教考古研究工作已逐步走向系统化和深入化。

图一八 2013年发现的西藏阿里日土洛布措岩画
七、青藏考古
自2007年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继续组队参加文物考古援藏工作,这些工作均与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合作进行。同时,在西藏自治区之外的其他藏区,也开展了一些相关的考古调查工作。
在结束了连续三个年度的西藏萨迦北寺的考古工作之后,2007~2008年,先后派出两批次专业人员,参加了西藏自治区7个地市的“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试点及技术指导工作[193]。
2009年,对芒康、察雅两县已知的5处吐蕃石刻遗存做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并新发现2处吐蕃石刻遗存,取得了重大收获[194]。此次调查是迄今为止对藏东地区吐蕃石刻遗存所做的首次全面考古调查,成果丰硕,为研究吐蕃时期佛教史、佛教艺术史、唐蕃关系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195]。同时,还对芒康澜沧江两岸的盐井、盐田等进行了调查[196]。
2012年9、10月,我院应邀与西藏山南地区文物局联合组队,对位于洛扎县的吉堆墓地进行全面的考古调查和测绘。新发现墓葬20、条状殉牲坑3、方形殉牲坑7座。与此同时,考古队还调查了与墓地相关的两处吐蕃摩崖刻铭[197]。
2013年7、8月,对阿里地区日土县热帮乡洛布措进行了环湖考古调查。共发现岩画618组(图一八)、墓葬57座、祭祀坑24座、大型石片图案1组、石构遗迹4组、石墙4道[198]。同时,还对日土县多玛乡乌江村丁穹拉康石窟群及其壁画进行了全面的测绘、拍照与记录,对窟形、组合、壁画内容与制作技法等进行了详细的观察[199]。
2014年8、9月,对阿里地区古格王国时期的遗址进行了调查。札达县象泉河及其支流的河谷台地和土林崖壁上密集分布着城堡建筑、窑洞居址、寺院建筑(图一九~二一)、石窟遗址、佛塔遗址等各类古格王国时期的遗存。共调查遗址近10处。
2015年7、8月,对阿里琼隆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测绘。共计发现洞室742座,院落105座,房址45座,护墙29道,墙体25道,碉楼1座,玛尼墙13道,塔20座,其它遗迹2座,发现陶、铁、铜、石、骨角、木、玻璃、毛织物、擦擦、经书残页、唐卡残片、塑像残块等遗物以及木、碳、谷物样品等近400余件(组)。此外,还对曲龙村境内的3处相关遗址进行了调查[200]。

图一九 2014年调查发现的阿里札达热尼拉康东壁北段早期壁画献乳糜与藏文题记
2016年7、8月,对阿里象泉河流域进行了考古调查。主要围绕象泉河上游曲龙段及中游托林段的干流与支流开展,共计调查遗址16处,遗迹类型十分丰富,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元明时期,表明象泉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发展具有多样性和延续性。而三普新发现后首次做全面调查的遗址点有8处,其中对度日坚岩画做了全面调查,发现651组画面,确认了迄今为止西藏地区数量最多、车辆和图案岩画最典型的一处岩画地点,首次确立了象泉河流域古代岩画在西藏岩画中的重要地位[201]。
2017年7、8月,主要参与了阿里札达县格布赛鲁墓地的考古发掘工作。共发掘墓葬9座,除M6为带封堆的异穴合葬土坑墓外,其余8座均为墓室底部有涂红迹象的小型土坑石室墓。出土各类遗物300余件(组),采集人骨和动物骨骼约100余个个体。根据出土物特征初步推断,8座竖穴土坑石室墓的时代约为公元前3~7世纪,M6的时代可能晚至汉晋时期。这两类墓葬的结构、葬俗与随葬品特点既显示出了浓郁的北方草原文化因素,又体现了与中亚、南亚、新疆等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联系,是西藏西部高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物遗存。
在西藏自治区之外其他藏区开展的工作:
一是2013年5月,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故宫博物院等单位,联合对西藏、青海、四川三省交界区新发现的吐蕃石刻造像进行了考古调查。新发现吐蕃石刻造像多处,填补了从青海西南部到四川西北部再到西藏东南部这段古代交通要道上的缺环,为吐蕃佛教史和唐蕃交通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图二〇 2014年调查发现的阿里札达县麦隆沟佛寺遗址主殿局部
二是2014年5、6月,与西藏等五省区文物机构联合组队,对唐蕃古道进行了全程考察。行程6500余公里,考察相关文物点56处。这次考察扩展了唐蕃古道所涉及的地域范围和文化内涵,使得各省区唐蕃古道考古工作能在一个完整的时空框架和相互联系的文化背景下展开[202]。
三是2014年4、9月,参加了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热水乡哇沿水库淹没区的考古发掘及整理工作。发掘区以察汗乌苏河为界,分为南岸区和北岸区。北岸区包括房址9,灰坑14座、灶31、墓葬3、石堆3座、寺院遗址1处;南岸区包括房址1、灶1、墓葬22、殉牲坑及殉人坑6座。其中25座古墓葬尽管遭到严重盗扰,但结构类型完整,营建方式多样,出土的墨书古藏文卜骨、带古藏文编号的椁板及棺板、“开元通宝”等表明这批古文化遗存的主人应该是唐代吐蕃统治时期活动在该地区的吐蕃人或吐谷浑人。出土的镶嵌玻璃珠则是汉晋以来通过丝绸之路自西向东传播的重要物品。
三国隋唐宋元明时代考古,时间跨度近2000年,历史进程起伏跌宕,文化面貌复杂多变,重要考古发现层出不穷,研究内涵丰富、门类繁多,远超过其他时期。上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综述,仅仅是择其要对一些基础性的工作进行归纳,城址、陵墓、手工业、宗教考古中的任何一个门类都有若干个独立的专题性研究课题。总之,10年来陕西三国隋唐宋元明时代考古无论是理念方法,还是田野工作实践,都取得了卓著的成果,同时,也有多方面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
第一,加快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出版迫在眉睫。近年来,考古发掘尤其是基建考古任务繁重,资料整理时间被严重压缩,成果发表出版滞后,不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应在这方面加大经费和人员支持力度,扩大合作,推进考古发掘成果的迅速转化。
第二,基本建设考古工作仍需重视。西安及周边基建勘探中发现最多的是汉唐时代墓葬、居址等遗迹,并且很多是高等级墓,尤其是唐代贵族墓高度集中于两京地区。近10年甚至20年,城市建设还在高速行进,汉唐墓葬发掘仍处于高峰期,以后,随着基本建设工程的减缓和地下墓葬资源的减少,这种情景和机遇也不会再有。所以,一如既往地重视基建考古中的墓葬发掘,严格按照田野操作规程发掘每一座墓葬,详细采集和提取墓葬信息,建立墓葬考古的数据库。
第三,着力推进本时期城市考古工作开展和研究进度。西安地区城址考古中,东汉之后、隋大兴城之前长安城考古发掘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历史考古研究相对薄弱;隋唐长安城除宫殿遗址之外,里坊格局、东西市和城门遗址考古,由于现代城市的叠压,很难展开,唯有抓住城市基本建设的机会,艰难推进;此外,唐宋县城遗址考古,陕北宋金古城考古等都是今后城址考古方面的课题。

图二一 2014年调查发现的阿里札达县热尼拉康南壁西段下部早期菩萨塑像
第四,加强十六国—北朝和宋金元明时代墓葬考古的研究。隋唐时代墓葬分期、制度和葬俗等的研究做为隋唐考古的重大课题,一直备受关注,研究成果丰富,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序列;十六国—北朝时期以及宋金元明时代墓葬考古研究则较为薄弱。十六国至北朝曾有7个政权在陕西建都,近年在西安周边发现了大量的这一时期的贵族墓,对其分期及丧葬制度文化研究尚需深入。近年的陕西宋金元明墓葬的考古发掘,显示了这一时期墓葬的区域化特征较为突出,分区、分期及与周边同期墓葬的比较研究应进一步展开。
第五,以城市考古的理念,整合数十年来汉、唐长安城及周边发掘的城址、墓葬、手工业遗址等资料,从宏观的角度审视以汉、唐长安城为中心的都城圈的文化生态模式,设立基于考古资料基础上的关于城址、墓葬、生产、生活的系统化综合研究和各项专题研究课题。
第六,广泛开展多学科结合的专题研究。本时期因遗存类型丰富而在此方面大有可为,如历史、美术和科技测考古相结合的壁画研究,考古和历史地理及科技测试等相结合的古陶瓷生产工艺和贸易流通综合研究;美术、宗教、考古相结合的石窟寺考古研究;分类细化深入的墓志碑刻研究以及以丝绸之路沿线为代表的中外文化交流研究等。可以肯定的是,新的研究方式和多维的研究角度必然带来新的研究成果。
占据考古学研究“半壁江山”的三国隋唐宋元明时代考古,以其文献和实物双重丰富的特征,在考古学人的努力下,未来必将展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面貌。
执 笔:刘呆运 邢福来 田有前于春雷 王小蒙 赵占锐苗轶飞 李 坤 席 琳肖健一
统 稿:王小蒙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现长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成立六十周年纪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2]同[1].
[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统万城遗址近几年考古工作的收获[J].考古与文物,2011(5).
[4]同[1].
[5]邢福来.关于统万城东城的几个问题[J].考古与文物,2014(5).
[6]邢福来.关于统万城周边墓葬的几个问题[J].考古与文物,2013(3).
[7]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第一工作队.西安市唐大明宫遗址考古新收获[J].考古,2012(11).b.龚国强,李春林,何岁利.唐长安城遗址[C]//留住文明—陕西“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及课题考古概览(2006-2010).西安: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2012.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西安市唐长安城大明宫兴安门遗址[J].考古,2014(11).
[9]a.田有前.西安市唐长安城通义坊遗址[C]//中国考古学年鉴2010.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446-447.b.田有前,张建林.西安唐长安城通义坊遗址[C]//留住文明—陕西“十一五”期间基本建设考古重要发现(2006-2010).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
[10]张全民,辛龙.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遗址[C]//中国考古学年鉴2013.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456.
[11]张佳.大唐东市或有商铺七万多间与西市并列唐长安城CBD[N].西安晚报,2015-11-19(4).
[12]王志友.西安市未央区大白杨汉墓与唐代陶窑遗址[C]//中国考古学年鉴2012.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416.
[13]张翔宇,高博.西安市昆明路唐代陶窑[C]//中国考古学年鉴2013.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457-458.
[14]徐龙国,刘振东,张建锋.西安市未央区梨园路唐代粮仓遗址[C]//中国考古学年鉴201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449.
[15]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唐长安醴泉坊三彩窑址[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1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醴泉坊遗址2001年发掘报告[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
[17]张建林,田有前.隋唐长安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C]//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六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
[18]罗西章.隋文帝陵、祠勘察记[J].考古与文物,1985(6).
[19]张建林.隋文帝泰陵[C]//中国考古学年鉴2011.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481.
[20]虽然《封氏闻见记》载:“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垄,如生前之象仪卫耳。”一些学者如宫大中也推测在洛阳等地发现的石刻可能属于东汉陵园,毕竟未得到证实,见宫大中.东汉帝陵及神道石刻[C]//中国古都研究(第四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21]朱偰.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2]葛承雍.唐昭陵、乾陵蕃人石像与“突厥化”问题[C]//欧亚学刊(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2002.
[23]沈睿文.唐陵的布局—空间与秩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12-224.
[24]张建林.唐代帝陵陵园形制的发展与演变[J].考古与文物,2013(5).
[25]a.徐卫民等.陕西帝王陵墓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7.b.陕西省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卷[M].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9.
[26]肖健一.明秦藩家世谱系与墓葬分布初探[J].考古与文物,2007(2).
[27]梁志胜,王浩远.明末秦藩世系考[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
[28]陈冰.西安明秦王墓的考察与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3.
[29]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东郊田王晋墓清理简报[J].考古与文物,1990(5).
[30]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曲江雁南二路西晋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0(9).
[31]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茅坡新城西晋墓清理简报[J].文博,2014(6).
[32]王辉.西晋墓葬的美术文化考古思索—以偃师杏园墓出土的陶空柱盘为例[J].中华文化论坛,2014(10).
[33]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阳十六国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34]岳起,刘卫鹏.关中地区十六国墓的初步认定—兼谈咸阳平陵十六国墓出土的鼓吹俑[J].文物,2004(8).
[35]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专用高速公路十六国墓发掘简报[J].文博,2009(4).
[3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待刊.
[37]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泾阳坡西十六国墓发掘简报[C]//文物考古论集(二).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
[3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待刊。
[39]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凤栖原十六国墓发掘简报[J].文博,2014(1).
[40]李维,杨军凯等.西安灞桥发现十六国墓首次惊现彩绘铠甲俑群[J].收藏界,2012(1).
[4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待刊.
[42]a.岳起,刘卫鹏.关中地区十六国墓的初步认定—兼谈咸阳平陵十六国墓出土的鼓吹俑[J].文物,2004(8).b.韦正.关中十六国考古的新收获—读咸阳十六国墓葬简报札记[J].考古与文物,2006(2).c.韦正.关中十六国墓葬研究的几个问题[J].考古,2007(10).d.董雪莹.十六国北朝墓葬出土鼓吹俑的类型与分期[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12).e.易立.魏晋十六国墓葬中“降釉小罐”初探[J].中原文物,2008(1).f.周扬.关中地区十六国墓葬出土坐乐俑的时代与来源—十六国时期墓葬制度重建之管窥[C]// 西部考古(十四).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g.刘卫鹏,张淑娟.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女乐[C]//碑林集刊(十四).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
[4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长安城宫城遗址的钻探与试掘[J].考古,2008(9).
[44]刘呆运.鹿善墓葬地研究[J].考古与文物,2013(4).
[45]a.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韦曲北塬北朝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5(5).b.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韦曲高望堆北朝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0(9).c.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南郊北魏北魏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9(5).
[4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0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调查发掘新收获[J].考古与文物,2010(2).
[47]倪润安.光宅中原—拓跋至北魏的墓葬文化与社会演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254.
[48]张全民.关中地区北魏西魏陶俑的变化[J].文物,2010(11).
[49]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靖边县统万城周边北朝仿木结构壁画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3(3).
[50]同[48].
[51]刘呆运.长安新发现两座西魏墓葬[C]//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年报(2014年).西安: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5.
[5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内部资料。
[5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内部资料。
[54]同[48].
[55]赵强.西魏两座纪年墓葬及相关问题探讨[J].考古与文物,2015(4).
[5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周独孤宾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1(5).
[57]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周郭生墓发掘简报[J].文博,2009(4).
[5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周莫仁相、莫仁诞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2(3).
[59]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待刊.
[60]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北周张氏家族墓清理发掘收获[N].中国文物报,2013-8-2(8).
[6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咸阳邓村北周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7(3).
[6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资料待刊。
[63]a.申秦雁.论中原地区隋墓的形制[J].文博,1993(2).b.刘呆运.关中地区隋代墓葬形制研究[J].考古与文物,2012(4).c.刘呆运.关中地区隋代墓地分布研究[J].考古与文物,2015(5).d.张全民.略论关中地区隋墓陶俑的演变[J].文物,2018(1).
[6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咸阳隋鹿善夫妇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3(4).
[65]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隋元威夫妇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2(1).
[6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隋苏统师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0(3).
[67]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隋韦协墓发掘简报[J].文博,2015(3).
[6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西郊三民村隋代墓葬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5(5).
[69]程义.唐代长安城周围墓葬区的分布[J].唐史论丛,2011(13).
[70]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J].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册,1930.后收入陈寅恪著.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36.
[7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待刊.
[7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待刊.
[73]200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陕西历史博物馆合作发掘了庞留唐墓,即唐武惠妃墓。目前,较为详细的资料介绍可见程旭.皇后的天堂—唐敬陵贞顺皇后石椁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74]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航天城两座唐代壁画墓发掘简报[J].文博,2015(2).
[75]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韦曲韩家湾村两座唐代壁画墓发掘简报[J].文博,2017(5).
[7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唐代杨贵夫妇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6(11).
[77]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市西郊杨家围墙唐墓M1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3(2).
[78]李明.论唐代的“毁墓”—以唐昭容上官氏墓为例[J].考古与文物,2015(3).
[79]200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阳机场二期建设项目中,发掘了执失思力墓,编号M117;唐窦孝谌墓,编号M151;东为其第三子窦希瓘墓,编号M152。资料未刊布。
[80]宁琰,辛龙.唐长孙无傲及夫人窦胡娘墓志的发现与考释[J].文博,2017(5).
[8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资料未刊布.
[82]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唐殿中侍御医蒋少卿及夫人宝手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2(10).
[83]张小丽.郭永淇.西安东长安街唐代石椁墓[C]// 2009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84]张小丽.朱连华.唐太宗民部尚书戴胄夫妇墓的新发现[J].文物天地,2015(12).
[85]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唐凉国夫人王氏墓发掘简报[J].文博,2016(6).
[86]郑旭东.西安曲江唐故博陵郡夫人崔氏墓相关问题略论[J].文博,2017(3).
[87]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华阴唐宋素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8(3).
[8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户县兆伦遗址隋唐墓葬发掘简报[J].文博,2015(5).
[89]a.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凤栖原唐郭仲文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2(10).b.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唐郭仲恭及夫人金堂长公主墓发掘简报[J].文博,2013(2).c.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唐太府少卿郭锜夫妇墓发掘简报[J].文博,2014(2).d.郭永淇.新出土郭子仪孙郭在岩墓志考[J].文博,2014(6).其他资料均未公布,保存在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90]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长安区晚唐时期令狐家族墓葬发掘简报[J].文博,2011(5).
[91]张全民.新出唐百济移民祢氏家族墓志考略[J].唐史论丛,2012(14).
[92]a.柴怡.西安西郊唐代突骑施王子墓[J].收藏界,2012(2).b.葛承雍.新出土《唐故突骑施王子志铭》考释[J].文物,2013(8).
[93]200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为配合“长安万科”项目基本建设,在西安枣园三民村发掘22座唐代小型墓葬,其中4座纪年墓墓主均为女官。
[94]201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为配合“长乐盛世”项目基本建设,在西安西郊枣园西路与枣园北路交汇处发掘了16座唐墓,其中7座纪年墓墓主皆为宫女,时代为唐中宗景隆三年(709年)至唐睿宗景云元年(710年)之间。
[95]a.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著.唐嗣虢王李邕墓考古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b.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顺陵文物管理所编著.唐顺陵[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c.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著.唐懿德太子墓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d.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昭陵博物馆编著.唐韦贵妃墓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e.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周原博物馆编.周原汉唐墓[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f.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编著.陕西凤翔隋唐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96]a.冉万里编著.隋唐考古[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b.程义著.关中地区唐代墓葬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c.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壁上丹青—陕西出土壁画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d.陕西历史博物馆编.唐墓壁画珍品[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e.程旭.丝路画语—唐墓壁画中的丝路文化[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f.程义.20世纪关中唐代墓葬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唐史论丛,2008(10).
[97]唐墓中道教文化因素研究的文章主要有:a.程义.关中唐代墓葬里的道教因素钩沉[J].唐史论丛,2011(12).b.尹夏清.从守门与镇墓之制看汉唐丧葬文化中的道教因素[J].宗教学研究,2007(3).唐墓中佛教文化因素研究的文章主要有:c.霍巍.唐宋墓葬出土陀罗尼经咒及其民间信仰[J].2011(5).d.郭晓涛.陕西凤翔唐墓出土陀罗尼经咒的图像解读[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8).e.冉万里.略论佛教地域观念对隋唐时期丧葬习俗的影响—以各类追冥福行为为中心[J].西部考古,2009(四).f.杨洁.唐代镇墓天王俑的世俗文化因素考略—兼谈两京地区的差异[J].四川文物,2009(5).
[98]唐墓中有关文物保护研究的文章主要有:a.杨忙忙.唐墓壁画环境监测与分析研究[J].考古与文物,2010(3).b.杨文宗.陕西历博壁画保护工作的回顾与展望[C]//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c.2016.杨文宗.我国墓葬壁画的保护方法[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7(4).d.梁龙.基于样本的图像修复算法在唐墓壁画上的应用[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13.
[99]李星明.唐代墓室壁画研究[M].西安:陕西美术出版社,2005.
[100]郑以墨.唐墓壁画研究综述[J].艺术设计研究,2009(3).
[101]程旭.唐墓壁画中周边民族文化因素及其反映的民族关系[D].兰州大学博士论文,2012.
[102]a.荣新江,李丹婕.郭子仪家族及其京城宅第—以新出墓志为中心[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b.杨军凯.杨洁.唐郭仲文墓志及其家族葬地考[J].文物,2012(10).
[103]张全民.新出唐代百济移民祢氏家族墓志研究[J].唐史论丛,2012(13).
[104]a.李明,耿庆刚.《唐昭容上官氏墓志》笺释—兼谈唐昭容上官氏墓相关问题[J].考古与文物,2013(6).b.李明.论唐代的“毁墓”—以唐昭容上官氏墓为例[J].考古与文物,2015(3).c.贾二强.释唐李建成及妃郑观音墓志[J].唐史论丛,2014(18).d.赵占锐,呼啸.唐宰相韩休及夫人柳氏墓志考释[J].唐史论丛,2016(23).e.王其祎.周晓薇.应予关注的中晚唐文学研究新史料—新见张籍撰《唐阳城县主李应玄墓志铭》[C]//唐研究(十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f.仇鹿鸣.新见《姬揔持墓志》考释—兼论贞观元年李孝常谋反的政治背景[C]//唐研究(十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05]a.胡戟,荣新江.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b.赵力光.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c.西安市长安博物馆.长安新出墓志[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d.西安市文物稽查队.西安新获墓志集萃[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e.故宫博物院,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三)[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f.胡戟编著.珍稀墓誌百品[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6.g.陕西历史博物馆.风引薤歌: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墓志萃编[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106]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著.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
[107]王小蒙,陈力.隋唐五代时期的灰陶制品[J].文博,2015(1).
[108]a.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孟村宋金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0(5).b.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北宋范天祐墓发掘简报[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6).
[109]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调查发掘新收获[J].考古与文物,2015(2).
[110]a.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蓝田县五里头北宋吕氏家族墓地[J].考古,2010(8).b.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调查发掘新收获[J].考古与文物,2011(2).
[111]a.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凤翔孟家堡唐、宋、明墓发掘简报[J].文博,2012(6).b.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凤翔孙家南头墓地宋元明墓葬发掘简报[J].文博,2014(3).
[112]a.张蕴等.九泉之下的名门望族—陕西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地[N].中国文物报,2009-9-11(4).b.张蕴,卫锋.蓝田五里头北宋“考古学家”的家族墓地[J].中国文化遗产,2010(2).c.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蓝田县五里头北宋吕氏家族墓地[J].考古,2010(8).d.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调查发掘新收获[J].考古与文物,2011(2).e.张蕴.北宋名门的悲与喜—陕西蓝田吕氏家族墓园发掘记.中国文物报[N].2013-9-5(3).f.张蕴.陕西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园考古北宋金石学家的长眠之地[J].大众考古,2015(2).
[113]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乳驾庄宋代砖雕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3(8).
[11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0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调查发掘新收获[J].考古与文物,2010(2).
[115]王沛,王蕾.延安宋金画像砖[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
[11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调查发掘新收获[J].考古与文物,2011(2).
[117]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调查发掘新收获[J].考古与文物,2013(2).
[118]秦育春.陕西西乡县宋墓新出土瓷器[J].收藏,2013(21).
[119]a.魏军.北宋吕倩容墓志考释[J].考古与文物,2016(3).b.郭永淇.北宋范天佑墓志考释[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6).
[120]a.程义,程惠军.汉中宋代镇墓神物释证[J].四川文物,2009(5).b.秦育春.陕西西乡县宋墓新出土瓷器[J].收藏,2013(21).c.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等.陕西华县南宋铜钱窖藏[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10).
[121]a.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异世同调.陕西蓝田吕氏家族墓地出土文物[M].北京:中华书局,2013.b.张蕴.古砚遗芳—记蓝田北宋吕氏墓出土文物[J].收藏家,2014(9).c.蓝田墓地与北宋藏家吕大临的《考古图》[J].美成在久,2016(1).d.刘涛.吕氏家族墓出土的北宋耀州瓷[J].收藏,2016(5).
[122]a.姚小鸥.韩城宋墓壁画杂剧图与宋金杂剧“外色”考[J].文艺研究,2009(11).b.周华斌.乞儿驱傩与宋杂剧—韩城“北宋杂剧图”壁画读解[J].中央戏剧学院学报(戏剧),2015(5).c.康保成,孙秉君.陕西韩城宋墓壁画考释[J].文艺研究,2009(11).d.延保全.宋杂剧演出的文物新证—陕西韩城北宋墓杂剧壁画考论[J].文艺研究,2009(11).e.杨效俊.陕西韩城盘乐村宋墓壁画的象征意义[J].文博,2015(5).
[12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发掘调查新收获[J].考古与文物,2014(2).
[124]王沛,王蕾.延安宋金画像砖[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
[125]a.王勇刚.陕西甘泉金代壁画墓[J].文物,2009(7).b.袁继明.陕西甘泉城关镇袁庄村金代纪年画像砖墓群调查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4(3).c.王勇刚.陕西甘泉柳河渠湾金代壁画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6(11).
[126]王保东.富平发现金代陶罐[J].考古与文物,2015(5).
[127]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渭南靳尚村金末元初壁画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4(3).
[12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曲江金代李居柔墓[J].考古与文物,2017(2).
[129]a.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孟村宋金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0(5).b.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等.西安南郊黄渠头村金墓发掘简报[J].文物春秋,2014(5).c.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铜川阿来金、明墓葬发掘简报[J].文博,2015(2).
[130]李举刚,杨洁.陕西地区蒙元墓葬的发现与研究[C]//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十八).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
[131]a.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皇子坡村元代墓葬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4(3).b.张小丽,袁长江.西安雁塔南路发掘一元代墓葬[N].中国文物报,2009-10-9(4).c.张全民,郭永淇.西安长安凤栖原墓葬发掘[C]//2009中国考古重要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d.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大朝刘黑马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5(4).e.成立.一夫三妻元代合葬墓惊现罕见瓷器:看,这是珍贵的元青花[N].西安晚报,2011-6-21(3).f.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曲江元代张达夫及其夫人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3(8).g.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曲江缪家寨元代袁贵安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6(7).
[13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大朝刘黑马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5(4).
[133]榆林榆阳区的元代壁画虽然为征集品,但是根据与相关材料的对比,可以肯定其墓葬应该为八边形穹窿顶单室石墓,与横山县罗圪台村元代墓葬形制相同。姬翔月.陕西榆林发现的元代壁画[J].文博,2011(6).
[13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横山县罗圪台村元代壁画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6(5).
[135]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蒲城洞耳村元代壁画墓[J].考古与文物,2000(1).
[136]a.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东郊元代壁画墓[J].文物,2004(1).b.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编.西安韩森寨元代壁画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137]袁泉.洛渭地区蒙元墓随葬明器之政治与文化考[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10).
[138]a.杨洁.陕西地区出土蒙元陶俑类型分析[J].文博,2013(5).b.杨洁.陕西关中蒙元墓葬出土陶俑的组合关系及相关问题[J].考古与文物,2015(4).
[139]a.李举纲.西安南郊新出土《刘黑马墓志》考述[J].考古与文物,2015(4).b.李举纲.元刘天与墓志及相关问题探析[J].文博,2015(2).c.段毅.元代医学教授武敬墓志考略[C]// 碑林集刊(二十).西安:三秦出版社,2014.
[140]侯新佳,李根枝,张芳.陕西蒲城洞耳村元代壁画墓墓主族属浅析[J].华夏文明,2016(3).
[14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明墓[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
[142]铜川市考古研究所. 陕西铜川新区未来城明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6(2).
[14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明墓[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
[144]同[143].
[145]同[143].
[14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留住文明[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
[147]刘卫鹏.陕西彬县东关村明代石室壁画墓的发掘[J].苏州文博论丛,2010.
[148]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M].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5、9、70.
[149] 史念海. 黃河中游戰國及秦時諸長城遺跡的探索[J]、鄂爾多斯高原東部戰國時期秦長城遺跡探索記[J]、洛河右岸戰國時期秦長城遺跡的探索[J]、再論關中東部戰國時期秦魏諸長城[J]、西北地區諸長城的分佈及其歷史軍事地理[J],见史念海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50] 彭曦.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
[151] a.艾冲.明代陕西四镇长城[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b. 艾冲.中国古长城新探[M].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6.
[15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省早期长城资源调查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15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省明长城资源调查报告(墙体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15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省早期长城资源调查报告(营堡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155]于春雷.“新修龙泉寺碑记”与延绥镇长城[J].文博.2012(6).
[156]于春雷.从点到面:明代延绥镇长城的形成与演变—兼谈延绥镇的边防理念[C]//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157]于春雷.长城的进化—以陕西长城为例[J]. 文博.2016(4).
[158]白云翔.手工业考古论要[C]//东方考古辑刊,2012.一文中认为,手工业考古研究不能等同于手工业制品的研究,其主要内容有:原材料的研究,生产工具和生产设施研究,工艺技术和生产流程研究,产品研究,产品流通和应用研究,生产者研究,生产经营方式研究,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研究,社会经济研究,社会文化研究十个大的方面;将其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一个“产业系统”和“一个文化因子”进行研究。
[159]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西郊窑头村唐代陶窑发掘简报[J].洛阳考古,2009(2).
[160]a.陆明华.陕西出土耀州窑青瓷考察记[N].中国文物报,2010-8-4;b.钱冶.探寻柴窑之旅—五代耀州窑天青釉瓷考察散记[N].中国文物报,2014-6-4.c.高功,张继开.探索千年之谜—柴窑—聚焦中国柴窑文化论坛[J].收藏界,2010(10),C.岳岩,王学武.第二届中国柴窑文化高层论坛在京举办[J],收藏,2013(1).这两次以收藏界为主的论坛,展开了柴窑产地的讨论,其中,《收藏界》2010年11期,集中刊登了会议论文。
[161]a.王小蒙.模仿与创新—唐至宋初耀州窑与越窑青瓷的影响和互动[C]// 中国古陶瓷学会.中国古陶瓷研究辑丛编(越窑青瓷与邢窑白瓷研究).北京:故宫出版社,2013(10).b.黄堡窑装烧工艺的发展演变—兼谈黄堡窑与越窑、汝窑及高丽青瓷的关系[C]//北京艺术博物馆编.中国耀州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10).
[162]王芬,施佩,朱建峰,林营,王学武.耀州窑五代天青瓷的研究[C]// 2016中国硅酸盐学会陶瓷分会年会会刊.
[163]a.易立.试论五代宋初耀州窑青瓷的类型与分期—以墓葬塔基出土文物为中心[J].考古与文物,2009(3);b.彭善国,刘辉.东北、内蒙古出土的耀州窑青瓷—以墓葬材料为中心[J].考古与文物,2015(2);c.同[a];d.张红星.内蒙古地区出土耀州窑瓷器[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9(12);e.穆青.河北出土的耀州窑青瓷—兼谈五代至北宋早期青瓷与白瓷上的深剔刻装饰[C]//北京艺术博物馆编.中国耀州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10).
[164]a.禚振西.黑釉耀瓷的装饰艺术[J].收藏,201(13);b.王小蒙.唐耀州窑素胎黑彩瓷的工艺特点及其渊源、影响[J].考古与文物,2013(6);c.杨俊艳.析唐代金银器对十世纪耀州窑青瓷的影响[C]//北京艺术博物馆编.中国耀州窑[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10).d.徐仙女(韩国)[C]//北京艺术博物馆编.中国耀州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10).
[165]a.杜文.窖藏及墓葬出土耀州窑瓷器问题探讨[C]//北京艺术博物馆编.中国耀州窑(图录).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10);b.冯小琦.故宫博物院藏耀州窑瓷器[C]//北京艺术博物馆编.中国耀州窑(图录).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10);c.耿东升.析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宋金时期耀州窑青瓷[C]//北京艺术博物馆编.中国耀州窑(图录).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10);d.张蕴.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出土耀州窑瓷器[C]//北京艺术博物馆编.中国耀州窑(图录).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10).
[16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延安市考古所,安塞县文物旅游局.陕西安塞县大佛寺石窟调查简报[J].文博,2013(12).
[167]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队,岐山县博物馆.陕西岐山蔡家坡石窟考古调查报告[J].考古与文物,2009(5).
[168]杨一苗,耿凌楠.陕西留坝县发现隋唐佛教造像龛[N].新华每日电讯,2008-10-09(8).
[169]李俊,乔建军.陕西榆林市藏传佛教石窟及摩崖石刻调查[J].考古与文物,2016(3)
[170]席琳.绥德圪针湾佛窟[C]//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年报(201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8.
[171]张建林,田有前.陕北富县发现一批北朝至宋代佛教造像[N].中国文物报,2010-02-26(4).
[172]a.韩宏,陈永辉.陕西镇安发现元代寺院遗址[N].文汇报,2017-03-28(5).b.刘呆运.镇安毗卢寺遗址[C]//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年报(201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7.
[17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明墓[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41,88.
[174]赵争耀.西咸机场二期考古重大发现[N].西安晚报/三秦都市报,2010-12-10.
[175]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榆林市考古勘探工作队,靖边县文物管理办公室,靖边县统万城文物管理所.陕西靖边县统万城周边北朝仿木结构壁画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3(3).
[176]肖健一.空港新城杨家村遗址[C]//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年报(201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5.
[177]邢福来,苗轶飞.长安大居安村唐代墓地[C]//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年报(201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8.
[178]王志友.马腾空遗址[C]//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年报(201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7.
[179]肖健一.空港新城杨家村遗址[C]//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年报(201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8.
[180]《陕西石窟内容总录》编纂委员会.陕西石窟内容总录·铜川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2017.
[181]《陕西石窟内容总录》编纂委员会.陕西石窟内容总录·延安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2017.
[182]《陕西石窟内容总录》编纂委员会.陕西石窟内容总录·榆林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2017.
[18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法门寺博物馆,宝鸡市文物局,扶风县博物馆.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184]铜川市考古研究所,西安美术学院中国艺术与考古研究所.药王山摩崖造像考古报告[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
[18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龙寺与西明寺[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
[186]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文物精华·佛教造像[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187]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省铜川市药王山管理局.陕西药王山碑刻艺术总集[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
[188]马世长,丁明夷.中国佛教石窟考古概要[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189]冉万里.唐代长安地区佛教造像的考古学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190]程旭.陕西馆藏造像概述[J].敦煌学辑刊,2014(3).
[191]介永强.唐都长安城的佛教寺院建筑[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4(2).
[192]常青.蔡家河与喇嘛帽山千佛院—陕西麟游的两处佛教窟龛造像调查[J].考古与文物,2016(3).
[193]席琳.高原上的文物考古工作者—西藏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2008年试点工作散记[J].中国西藏,2008(6).
[19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西藏芒康县扎进玛尼石刻造像与达琼摩崖造像调查报告[J].西藏研究,2017(1).
[195]席琳等.西藏昌都地区芒康、察雅两县考古调查新发现两处吐蕃石刻遗存[N].中国文物报,2009-11-13(4).
[196]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等.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芒康县盐井盐田调查报告[J].南方文物,2010(1).
[197]席琳.洛扎县吉堆吐蕃墓地调查[C]// 中国考古学年鉴2013.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423.
[198]席琳,何伟,张建林.西藏日土洛布措环湖考古调查取得重要收获[N].中国文物报,2013-10-18(1).
[199]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西藏日土县丁穹拉康石窟群考古调查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4(6).
[200]于春等.西藏阿里琼隆银城遗址考古手记[J].大众考古,2015(12).
[201]席琳等.西藏札达度日坚岩画考古调查取得重要收获[N].中国文物报,2016-11-18(8).
[20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从长安到拉萨:2014唐蕃古道考察纪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