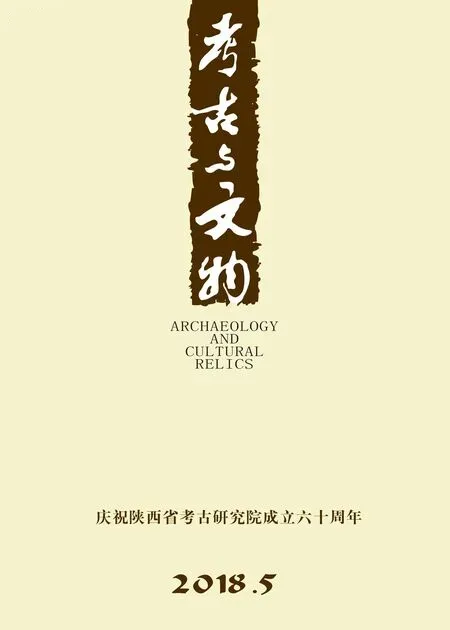2008~2017年陕西秦汉考古综述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汉考古研究室
陕西是秦汉历史文化的重要分布地区,这里不仅有大秦一统至西汉王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之积淀,还有早期秦国辗转东进的蓄势历程。陕西的秦汉考古工作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又肩负巨大的历史重任。近十年来,陕西秦汉考古工作秉持“传承既往、与时俱进、着眼当下、开拓未来”,以及以“项目(课题)为依托,科研为主题,协作为力量,服务为宗旨”的理念,围绕秦汉各时段相关城址、陵寝、聚落、中小型墓葬、祭祀遗址、秦汉交通等方面开展各项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并取得了重要收获。在大遗址考古工作中业绩尤为显著,如对秦汉诸城址的调查与发掘,在秉承传统工作方法同时,又融入创新理念,既注重对各类文化遗存点状的全面发现,又加强对城址线和面的整体性对接,尤其增加对城址所依存自然环境的分析研究;对秦汉陵墓考古
调查、勘探工作的大遗址考古工作以及对大、中、小型秦汉墓葬的发掘工作成果丰硕,从制度层面探索出陵墓的时代特征与发展轨迹。此外,在祭祀遗址、离宫别馆、交通道路、水利工程、手工业作坊遗址的考古工作也取得诸多新发现。这十年来陕西秦汉考古工作所取得的各项收获,不仅仅是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对各类遗存的布局、架构、内涵有了更清楚地认识,也为新形势下大遗址保护利用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保护、展示与科学研究“三位一体”的新格局。
一、秦汉城址考古与研究
陕西秦汉时期的城址均以独具特征性的大体量、丰富的内涵以及所处环境构成了考古学意义上的大遗址文化遗存,亦成为近年来陕西考古工作的重要目标。本世纪初,随着国家推动大遗址保护工作的深入以及对具体项目强力支持,十年来陕西大遗址考古平稳深入推进,文化遗产保护成绩突出。以秦汉时期秦都雍城、栎阳、秦咸阳、汉长安城、西汉帝陵为主要工作对象的田野考古工作获得了科学详实的考古数据,对各遗址保护范围及外围环境、布局结构、文化内涵和历史沿革也逐步厘清,这不仅是对历史考古学的贡献,更重要的是为大遗址保护规划和考古遗址公园的编制和建设提供了权威科学依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大遗址保护、展示与科学研究“三位一体”的新格局。

图一 秦雍城遗迹分布图
(一)秦雍城
位于陕西凤翔的秦雍城,作为秦国“九都八迁”过程中建置时间最长的的国都,也是秦国在此蓄势,逐步走向强盛的里程碑。秦国在雍城发展军事、构筑城防体系、提升经济的支撑力。如果说当初秦国在陇东地区拉开了自身发展的历史序幕,那么后来东出陇山,向关中挺进,尤其在经过反复选择定都雍城后才有了统一六国的强国梦想。20世纪30年代考古人进驻雍城,直至今日历经了工作启蒙、初期探索、全面辉煌及巩固转型等几个时期,几代考古学家鼎力传承,才逐渐揭开了这座古城的神秘面纱[1]。在全面回顾既往前贤于雍城大遗址所获得考古工作成就的基础上,近十年来拟定了从传统“宏观”到当今“微观”转型,即以“全面调查,重点勘探,选点发掘”的工作规划,并取得了各项重要收获。
1.遗址整体布局的基本确认
通过在城址区“拉网式”的调查勘探和小面积发掘,包括城墙遗迹、道路、宫殿、聚落、作坊等遗存数量以及自然水域环境信息大量增加,由“点”形成的“面”则显现出这座城市所具备的多功能化城市面貌及特征,它既体现了早期城市以自然环境作为适从条件的普遍原则,又反映出秦国面对复杂外部袭扰环境而以完备城防设施作为首选的自身特征。之后考古工作逐步由城内转到对整个51平方公里遗址区调查,现已基本确认秦都雍城由城址、秦公陵园、国人墓葬、郊外礼制建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国家祭天场所及远郊“野人”聚落形成的总体格局,以及各自的布局规律[2](图一)。
2.遗址水系环境与“城堑河濒”的城防体系
近年来雍城考古工作中,将自然环境因素纳入到考察这座都城何以长久置都的重要因素之列。中国古代社会水与城的关系非常密切,雍城亦如此,水系自然环境为秦人当初择都雍城的主因之一。在雍城以北的雍山,水蕴藏量丰富。由于西北的水源地高,向东南流经雍城城址所在区域位置较低,环围雍城四周的大河形成了在秦人早期不筑城墙的背景下,城防设施则以周边河谷、陡崖环护,这一发现也印证和再现了文献中“城堑河濒”的场景[3]。除城外大河之外,还发现从城外大河引水并穿城而过的小河,以及保证城内供水而在大河上筑起的围堰遗址,使雍城成为“水”中之城,城内形成“顺河而建,沿河而居”的情景。河流成为当时城内便捷的水上通道,河堤沿岸往往有临河道路,同时城内各条陆路之间纵横交错、相互连接。调查发现当时临河而建的聚落形成多个相对集中的片区,沿河而居则方便地利用了向河中自然排洪的功能,同时通过地下引水管网将河水引向城中各个区间,用于诸如作坊生产、农业灌溉、聚落生活以及苑囿池沼用水等[4]。
3.都城扩改建的发展序列
在秦“九都”中,按照各自所蕴含文化遗存的量化标准及其层次结构与功能化比较研究,雍城是一座正式都城[5]。雍城置都三百余年间,历经由南向北改扩建过程,功能逐步完善。根据城址区遗存分布状况与年代关系,依据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原理,将城市扩建与沿革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为“初居体验”与“城堑河濒”期,第二期为正式规划营建与“城郭结构”期,第三期为雍城后期的正式筑城与城市功能由防御到大都市格局形成期[6](图二)。
4.城市聚落结构与沿革
以大型宫室群、贵族建筑群与平民聚居区三个层次结构构成的城市聚落群分布,按照早晚关系可确定为三处遗址中心聚落,即瓦窑头宫区、马家庄宫区、姚家岗—铁丰—高王寺宫区。瓦窑头宫殿区系最早城市聚落,大型宫殿、贵族居所、平民聚落处于无间隔的“和谐”分布形态;马家庄则显现出内外城之分,国君和贵族在城中心,平民则在外城。平民聚落遗存内涵则表明“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场景。作坊是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以不同生产门类而划分不同城市聚落人群和社会组织的聚居场所,透过每一处作坊内的文化遗存可以梳理出当时集生产、居住与生活于同一聚落的场景。在雍城城址内外发现各类手工业作坊多处,冶铜作坊在史家河、马家庄、高王寺和今凤翔县城北街一带;炼铁作坊在史家河、东社、高庄一带;制陶作坊发现于城内豆腐村、铁丰、瓦窑头以及城外的姚家小村、八旗屯等地;陶质生活用器则发现于邓家崖东岗子一带。作坊一般分布于靠近城墙的内侧,附近为工匠栖身之地。城址区各聚落之间形成广阔的空隙,除道路遗迹外没有发现雍城时期的人群居住、作坊或其它活动遗迹,推断其用途当为农田区域。此外,城外及穿越城内的多条河流,提供了丰沛的水资源,加上城外植被茂密的林区环境,为雍城提供了富实的渔猎经济,所以城内还应该生活着一定数量从事农耕、渔猎、山泽木业方面的聚落人群。这种多元性经济结构壮大了秦国实力,成就了秦国在雍城蓄势之后继续东扩的愿望[7](图三)。

图三 秦雍城瓦窑头大型组合型宫室平面图
从都城个案考量,则呈现其早期所具有单一考古学文化属性、同一谱系、同一时代的城市聚落形态、布局、结构的特点;而从都城沿革与扩建过程观察,则显现了它从早期传承周制,到后来包容政治自主创新背景下形成的同一空间、不同时间、有谱系或无谱系关系城市聚落布局与结构之变化,反映了秦雍城时期由单一“秦人”到后来与周余民、戎狄等构成的社会组织形态[8]。
(二)秦汉栎阳城
栎阳城是秦汉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都城,位于西安市阎良区。秦献公二年(公元前383年)秦国都城由雍城迁至栎阳,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在此实施了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商鞅变法”,使秦国强大起来,为统一中国打下了基础。秦末项羽三分关中,栎阳曾作为塞王司马欣的都城;汉高祖刘邦也曾以栎阳为都城,整顿军队,向东挺进,逐渐完成统一全国大业。栎阳城考古工作始于上世纪60年代,80年代开展了系统的考古勘探与发掘,确定了栎阳城遗址的南墙、西墙,在城中发现了大量建筑遗址及道路。
为了进一步确定栎阳城遗址的保护范围,为遗址保护规划的制订提供科学资料,2013年栎阳城遗址考古工作重新启动。五年来,先后确定了三座古城,并在三号古城内试掘确定了多座大型宫殿建筑,确定三号古城的时代为战国中期至西汉前期,即文献所载的秦至汉初栎阳城。同时对栎阳城附近的2座西汉大墓和汉唐白渠遗址进行了勘探与试掘。
一号古城发现于上世纪80年代,此次工作在局部地段发现了城址北墙,城址南北约2430、东西约1900米,时代为秦汉时期。二号古城位于一号古城东北,南北约3800、东西约3100米,时代为西汉中晚期。
三号古城位于二号古城西。勘探发现前后两期北墙、西墙,前期北墙已勘探长约440、西墙长约180米;后期北墙已勘探长约105、西墙长约200米;南墙、东墙尚未发现。城址范围发现大型建筑遗址5处,院落1处,手工业生产区1处。为了确定三号古城的时代,先后对一至六号建筑遗址进行了试掘。确定了一、二号建筑的宽度;在三号建筑夯土台基西部发现长5.6、宽4.8米的地下建筑;四号建筑为东西向排房式建筑,清理了3个房间,西部房间为浴室,中部房间东北角设有壁炉;五号建筑东部清理了5个房间,在南侧、北侧房间内分别发现了为浴室排水的大型地漏,房间地面铺砖、墙壁贴砖,建筑南侧有预设于台基下的与浴室地漏相连的排水管道和渗井设施;六号建筑内外清理出5个灶和疑似厕缸的遗存。试掘中出土了大量的筒瓦、板瓦、瓦当等建筑材料,时代特征明显,显示其上承雍城,下接秦咸阳,并延续到西汉早期。遗址中还出土了长73、最大径63厘米的巨型筒瓦及大瓦当残片、空心砖踏步等遗物。出土器物上有“栎阳”“宫”等刻划文字和大量的“栎市”陶文。根据发现的遗迹、遗物,发掘者认为发现的夯土遗存是秦最高等级的宫殿建筑,为文献所载栎阳的建筑遗存,时代从战国中期延续到西汉早期[9](图四)。

图四 秦栎阳城遗址三号古城2017年发掘现场
栎阳城遗址范围内分布多座古城的原因,与石川河多次泛滥改道对城市的破坏有直接关系[10]。栎阳城遗址考古获得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三)秦都咸阳城
从秦孝公于公元前349年从栎阳迁都,直至公元前206年子婴降汉,咸阳为都共历九世144年。作为完整的都城概念,“咸阳城”一词代表的是渭河南、北广大地域。
经过50余年的努力,咸阳城渭北区的考古工作取得初步成果,宫殿区、手工业区、陵区、平民墓地等空间布局基本明确[11]。2006~2014年,借助国家大遗址保护政策支持,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为契机,继续开展了大范围调查、勘探。2016~2017年,在“咸阳宫”西的胡家沟地点,进行了总面积约3000平方米建筑遗址和4座古墓葬的主动发掘。此外,在配合基本建设过程中,司家庄秦陵周边以及一些平民墓区也有发掘。
寻找咸阳城城域地标即夯墙,是多年来一直困扰学界的问题。事实上,夯墙并不是城界的唯一表现形式。众学者基本都以《秦都咸阳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简报》附图为蓝本,讨论咸阳城的四至问题[12]。在近年的调查和勘探工作中,发现在西部地区、北部地区遗存类型变化存在一些规律,据此推测咸阳原海拔420米左右可能是咸阳城北至的“边线”之一。尤其重要的是在现高干渠以南、海拔420米左右存在的东西向的沟渠,经勘探证实与汉成国渠窑店段由西向东的走向相抵牾,这为咸阳城北界所在提供了新线索[13]。咸阳城西界也应该不是一条南北直线[14]。
尽管发现的城域地标还达不到完全闭合的程度,但咸阳城北区整体面貌和空间布局并不存在异议。在海拔420米以南,自西向东依次有手工业制作、府库、官署、宫殿等不同功能的大型建筑40余处,仅西部的聂家沟和胡家沟区就有14组建筑明确是与国家级府库和手工业制作有关。这些建筑规模宏大,其中一组基址东距“咸阳宫”西墙26米,平面呈长条形,南北总长约142、东西宽约37米,内部有三个单元,外部东、南有夯墙和踩踏面[15]。
从建筑的体量上可以看出,“咸阳宫”西部不仅是手工业生产场所,还有官署管理机关。2016年发掘的府库遗址,东西长约110、南北宽21米,土木结构,毁于烈火(图五)。出土了大量石编磬, 30余件残块上发现刻文,内容为“北宫乐府”“乐府”及“右四”“八”“三”等数字编号,这些文字验证了2015年采集石磬的属性,确定了秦置北宫并设乐府的历史事实,同时对判断该组建筑的用途提供了证据(图六)。这是秦都咸阳城考古中第一次可明确用途和名称的建筑遗址,对研究咸阳城北区布局有重要的意义[16]。

图五 秦咸阳城府库遗址发掘现场
随着以阿房宫为重点的渭南区考古工作的深入,有关秦帝国时期的咸阳城轴线问题形成了一些新认识。阿房宫是秦始皇时期帝国的新政治中心,向南正对秦岭沣峪口,向北延伸正对关中平原北部前沿的最高峰嵯峨山,处在贯穿秦朝的东西、南北向轴线的近乎三分之一的位置。这体现了秦始皇在阿房宫选址时对国家整体的把握与控制[17]。《阿房宫考古发现与研究》一书汇集了多年来阿房宫遗址文物考古和历史研究相关文章,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其研究现状,对于今后相关研究具有指导性意义[18]。

图六 秦咸阳城遗址出土石磬残块
(四)西汉长安城
汉长安城是西汉的都城,具有中心性、威严性、礼仪性、安全性和时代性等特征,是西汉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汉长安城利用秦在“渭南”的宫室改建而成,自西汉建都后,新莽、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相继沿用旧城营建新都,东汉、西晋、隋也将此作为临时之都,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有重要地位。汉长安城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基本搞清了汉长安城的城壕、城墙、街道、给排水系统等城市结构和格局,并对未央宫、长乐宫、桂宫和北宫等主要宫殿区以及武库、手工业作坊区、南郊礼制建筑区等进行了全面勘探和重点发掘,对十六国和北朝时期长安城的宫城也做了初步探查,为汉长安城考古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近十年来,汉长安城考古工作主要围绕大遗址保护和未央宫遗址区申遗开展的。发掘工作主要有:西安门外大型建筑遗址[19]、西安门遗址、直城门遗址[20]、未央宫南宫门遗址[21]以及十六国北朝长安城宫城的宫门遗址[22]等。同时在长安城内外开展了大规模考古勘探和试掘。勘探主要有:城壕、城墙、城门、城内大街、未央宫、明光宫、武库、“北第”、“东第”、北宫、市场、建章宫、太液池、南郊十四号礼制建筑、上林苑钟官铸钱遗址等;试掘有:城壕、章城门、安门、宣平门城墙外凸部分、直城门大街、安门大街、未央宫西宫门、南北路、东西路、沧池以及其他建筑遗址。这些考古工作为研究长安城提供了新资料,获得了新认识[23]。
随着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城郊相关遗存得到了更加重视[24],墓葬[25]、桥梁的考古发现更丰富了对汉长安城的认识。
2012年以来,在汉长安城北发现3组7座渭桥,其中厨城门四号桥为战国晚期修建,厨城门一号桥经西汉及东汉至魏晋两次修建,洛城门桥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所建,厨城门三号桥为唐代所造。厨城门一号桥规模巨大、布局完整、是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秦汉木梁柱桥,附近还出土了大量石构建材,表明其可能还是一座木、石构结合的大型桥梁(图七)。遗址中出土的古船以实用船只显示出的成熟木板船类型,是我国古船考古资料中的首次发现,填补了汉代船舶发现的空白。发掘表明,至迟到康熙时期渭河河道未大规模北移。渭桥遗址的发掘,不仅对了解汉长安城周边交通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研究渭河河道变迁及古代桥梁技术提供了新资料[26]。汉长安城渭桥遗址被评为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近十年来,汉长安城遗址研究著述颇丰。学者们在对汉长安城的特征[27]、机构设置[28]、朝向及宫室设置[29]、设计思想[30]、城郭[31]、城门[32]、公共空间设置[33、34]、城市水利[35、36]及水环境利用[37、38]等诸多方面有着深入的研究,对认识汉长安城的城市布局、规划设计及城市发展等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五)眉县柳巷城遗址
柳巷城遗址位于宝鸡市眉县渭河一级台地、渭河北岸台塬南侧。城址为正方形,边长160米、面积25600平方米。城址仅设一门,位于南城墙略偏东位置。在每面城墙正中有一凸出方形夯土马面,城墙四角有角台。城外距城墙约8米处建有护城壕。
柳巷城遗址出土遗物以砖、瓦等建筑材料为主,陶器等生活器物较少。陶器以罐为主,纹饰素面较多,另有少量瓶、盆、釜等器物。还发现了数十枚五铢、剪轮五铢等铜钱,以及铜权、石质夯头等工具。
柳巷城遗址为一处东汉晚期坞堡建筑,城墙、城壕、马面、角楼等防御设施齐全。就其地望而言,柳巷城距秦汉郿县县城较近。根据城址内出土的遗物判断,城址大约始建于东汉末年,废弃于北魏时期。依据柳巷城址的地理位置、形制、规模、年代等特征,结合《后汉书》《三国志》等文献资料判断,柳巷城即为东汉末年董卓所建郿坞。眉县柳巷城遗址是黄河中游地区汉魏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一座防御性坞堡[39]。

图七 汉长安城厨城门一号桥遗址
二、秦陵与西汉帝陵考古工作
自东周至两汉,从国君到帝王,“陵随都移”和“视死如生”的葬俗观念贯穿于陵墓制度始终。多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各时段陵墓发现与研究方面逐步形成了从本体到对整个陵区布局功能设施的全方位考察,从单一陵墓到不同时段陵墓发展演变的比较性研究。
(一)秦公王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秦人在其五百年以上的发展历程中,先后营建了西垂、衙、平阳、雍、栎阳、咸阳、芷阳、杜东、韩森寨及丽山等十个陵区,这些陵区的发现和研究使原本了无踪迹、散见于历史文献只言片语中的一座座秦人陵区逐渐清晰,连缀成一条基本完整的古代陵墓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链条,是研究中国古代陵墓产生、发展、演变历史的最系统、最完整的实物资料。通过这十个陵区可以看到秦陵在陵园、墓葬、封土、礼制建筑、陪葬墓、陪葬坑、门阙等形制要素方面的渐变,这些渐变逐步强化,最终造就了从“集中公墓”到“独立陵园”的制度巨变,并由此奠定了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基础[40]。
1.宝鸡太公庙秦陵
宝鸡市陈仓区的太公庙村,上世纪80年代因发现春秋时期秦公镈、秦公钟祭祀坑而举世瞩目。从铜器铭文得知秦公镈是秦武公祭祀祖先的礼器,铭文中提到了秦襄公、秦文公、秦静公、秦宪公四代世系,着重讲了秦襄公被“赏宅受国”之事[41]。这一考古发现为寻找秦平阳城址及其附近的秦公陵园提供了重要线索。
其后在礼县大堡子山M2和陕西凤翔南指挥秦公一号大墓的西墓道南侧相继发现乐器坑和车马祭祀坑,按照这一规律分析,太公庙乐器祭祀坑的东北方向应该有秦公大墓存在的可能。2013年,在太公庙村勘探发现了大墓和车马坑,其东西两侧发现了疑似陵园的兆沟设施。发现的“中”字形秦公大墓、车马坑和陵园兆沟设施,形制和已发掘的凤翔秦公一号大墓基本一致,应为一处秦公陵园,推断墓主可能为秦武公。根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述,秦平阳宫城系秦宪公新建之都,陵园也随之附设,葬于此地的当有其后4位国君,即秦武公、德公、宣公和成公。目前虽然未发现其他秦公大墓的线索,但在墓葬附近发现了城址的线索,时代和性质都指向秦的第5处都邑—平阳城[42]。
近年来,多位学者围绕秦平阳城址与陵墓探索,做了多角度的分析研究。太公庙至平阳镇一带的秦文化遗存,从春秋晚期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期,西边的早,应为秦平阳城故址;东边的晚,当属秦汉平阳亭和东汉时期郁夷县之所在[43]。通过该区域秦墓分期的比较,认为早期的国人秦墓应距西侧的太公庙较近[44]。太公庙和大堡子山两次考古发现,前后相隔近三十年。大堡子山乐器坑发现以前,研究者多与传世的秦公镈、秦公簋进行联系,诸如作器者及其相关问题虽有争议但并不那么突出。大堡子山乐器坑发现后,发现二者在埋藏方式、器物造型、时间衔接、人物关系上都有着紧密的衔接关系。由此确定太公庙出土秦公乐器的地方不是“窖藏”,与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子乐器坑”一样,都附属于大墓的祭祀坑。两处所出镈、钟器物风格酷似,差异主要在带铭文的“秦子镈”上。礼县“秦子乐器坑”的时代稍早,可隶定在宪公时代;太公庙秦公乐器的时代稍晚,可隶定在出子、武公时代。作为祭祀坑,“秦子乐器坑”的对象当是静公,而太公庙秦公乐器祭祀的对象当是宪公[45]。
2.雍城秦公陵园
雍城南郊三畤塬上的雍城秦公陵园是目前所知最大的秦国国君陵寝之地,该陵园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布局规整,它与其它秦陵园形成了具有持久性、继承性、完整性、独特性的秦国陵园体系,展现秦陵制度从早期集中公墓制即所有墓葬均集中于规划的陵区之内,向着独立陵园制及各陵园以兆沟相互隔开的发展过程。自上世纪80年代起,对雍城秦公陵园进行了三次大规模调查与勘探,已确认51座包含丰字形、中字形和甲字形大墓,凸字形、刀把形、目字形、圆形等外藏坑。近十年来,在传统工作认识基础上进一步以“微观”方法对雍城秦公陵园进行细部调查与勘探,是新时期雍城大遗址考古工作目标之一,工作初期随机选择14座秦公陵园中的一、六号陵园进行实验性复探,在每一座分陵园东北方向都发现有隶属的陪葬墓区,均为秦公的“族人”,该发现为进一步研究雍城国人墓葬分布和下一步针对秦公陵园的考古工作提供了新方向[46]。研究方面,探讨了雍城秦公陵园的墓主及排序,认为每一座陵园只对应一位国君,一座陵园内的多座大墓,反映了一代秦公与其夫人、次夫人的并穴合葬关系,同时确定了陵园的布局规律,秦公墓在陵园内西南,秦公夫人、次夫人在陵园内东北,而陪葬墓区则分布在陵园外东北[47]。
3.咸阳原秦陵
近年来,在秦都咸阳城的西北部,发现并确认的战国秦陵有咸阳塬上的“周王陵”、司家庄、严家沟战国晚期大型秦陵园3座。
咸阳周陵镇的“周王陵”有内、外两重陵园。外陵园由墙垣和外围沟两部分组成,外陵园南北长835、东西宽528米;围沟南北长954、东西宽639米;园墙四面各有一门阙遗址。内陵园,园墙南北长423、东西236.5米;围沟南北长431.8、东西246.5米。陵园在两陵墓道正对处分别设有门阙。内陵园将南、北二陵界围其中,两陵位于一条南北轴线之上。南陵封土外形为“覆斗状”,现高14、底边长约100、顶边长40余米,墓葬形制为“亞”字形。北陵南距南陵145.8米,封土外形为截锥体,现存高度17.5、底边长60米左右,顶边长约10米,墓葬形制为“亞”字形。陵园内共发现外藏坑27座,建筑遗址探明6处。内陵园遗址分布在北陵西北和东南部,外陵园遗址分布在北部和东部。小型墓葬共发现168座,分别位于外陵园内西北角、东北角、东侧外围墙、外壕沟之间中部偏北处,各区的墓葬成行、成列有规律的分布[48](图八)。

图八 “周王陵”陵园布局图
司家庄秦陵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周陵镇司家庄村北。陵园由三道围沟围绕而成。第一道围沟之内的区域为内陵园,南北长约560、东西宽536米;第二道围沟位于第一道围沟之外,平面南北长663、东西宽约631米;第三道围沟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南北长1285、东西宽1038米。三道围沟的北、东、南三面与墓道对应处均断开形成通道。主陵居内陵园中部,现存封土形状不规则,底部东西长80、南北宽63、高约15米。墓葬形制为“亚”字形,四面各有一条墓道。“甲”字形大墓位于主陵北侧,无封土,坐西面东,通长94米。发现陪葬坑6座,其中主陵周围4座,甲字形大墓南侧2座,均为竖穴长方形。建筑遗址发现5处,分别位于内陵园东部、西南部、西部。小型墓葬发现较多,除了主陵园内,三道围沟之间,在陵园东南部也发现了大片小型墓葬[49]。2015年,咸阳市渭城区大石头村北发掘马坑11座,均为竖穴土坑,南北两排,东西向,各埋有一马,时代为战国中晚期[50]。马坑发掘地点距离司家庄秦陵较近,可能属于陵园的祭祀坑或陪葬坑。
严家沟秦陵位于汉成帝延陵东北部,现存两座封土,世传为汉成帝嫔妃班婕妤等的墓葬。勘探发现双重园墙,外园墙外侧有围沟环绕。陵园整体呈南北长方形,内园墙南北长473、东西宽236.5米,设有6处门址。外园墙保存状况较差,复原南北长1043、东西宽526米。西墙与内陵园门址对应处也发现了门址。外园墙之外还设有围沟,南北长1154.6、东西宽约630米。陵园内现存两座封土,南封土破坏严重,仅余高4~5米的平台,底部范围东西长123、南北宽约90米。北封土呈“覆斗形”,底部边长73~79、顶部边34、高约15米。两座墓葬形制均为“亞”字形。陵园共发现陪葬坑12座,建筑遗址1处,位于内陵园南墙外侧,似为一东西长方形院落。发现了300余座小型陪葬墓,大多分布在围沟与外城垣之间,部分位于陵园外西、南部区域[51]。
“周王陵”两座“亚”字形陵墓的主人,诸学者分别提出为秦惠文王和秦悼武王陵[52]、秦惠文王与惠文后之公陵[53]、秦悼武王及其夫人的永陵[54]、汉元帝皇后王政君和王莽妻子之墓葬[55]等诸多观点;而严家沟秦陵所葬之主人,分别有秦惠文王与惠文后之公陵[56]、秦悼武王及其夫人的永陵[57]等认识;司家庄陵园虽没有明确认识,但是上述三座陵园当均为战国晚期秦陵,为战国晚期秦人的咸阳陵区[58]。
4.秦芷阳陵区
芷阳陵区位于临潼县斜口镇韩峪乡骊山西麓的塬阪上,即学术界所称的“秦东陵”。上世纪依采集“芷”字印记的陶器以及4座陵园和多座大墓的发现,判断是秦芷阳陵区所在。
2011年开始,对秦东陵进行了大范围的考古勘探,一号陵园内除以前发现的2座“亚”字形大墓、2座陪葬坑、2处陪葬墓区、11座小型墓葬及4处建筑遗址外,新发现了陵园四面壕沟,陪葬坑12座,小型陪葬墓区3处共计161座,建筑遗址11处等遗迹;二号陵园在以前发现的1座“中”字形大墓、3座“甲”字形大墓、2处陪葬墓区的基础上,新发现了“甲”字形大墓2座、陪葬坑9座、小型墓葬区1处等遗迹;三号陵园除以前发现的1座“中”字形大墓、1处小型陪葬墓外,新发现1座“中”字形大墓、6座陪葬坑、围沟1处、小壕沟3处、小型陪葬墓106座等遗迹;四号陵园除以前发现的1座“亚”字形大墓、2座“甲”字形大墓外,新发现了陵园内残存的围绕“亚”字形大墓的东、南、北三段内壕沟,围绕“甲”字形大墓的内外壕沟4段、“中”字形墓葬1座、小型墓葬125座,其中与陵园相关的小型墓葬123座、陪葬坑3座、建筑遗址3处(图九)。对四号陵园M130南面的J3建筑遗址进行了试掘,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发现J3残存平面呈“凹”字形,面积达2230平方米,时代为战国晚期,当为“中”字形墓葬的享堂类礼制建筑。

图九 秦东陵四号陵园K10正射影像图
2010年,公安机关破获一起盗掘秦东陵的盗墓团伙,缴获高柄漆豆1件、残漆豆足座3件。高柄漆豆盘底有针刻文字两处,足座底部有烙印文字一处,针刻文字一处。这件带铭文的漆器出自秦东陵一号陵园南侧“亚”字形大墓M1,由此判定一号陵园被盗墓葬为秦昭襄王陵墓,与其相邻的另一座“亚”字形大墓为昭襄王妾唐八子,即孝文王母唐太后之墓,一号陵园即为昭襄王与唐太后之合葬陵园[59]。
研究认为,二号陵园为悼太子之墓,另外三座“甲”字形大墓为太子嫔妃之墓;三号陵园“中”字形大墓为唐太后之陵墓所在;四号陵园为宣太后之骊山陵园[60]。
近年来秦东陵的考古工作深化了学术界对秦芷阳陵区的认识,使秦公、王至秦始皇帝陵的发展序列日趋完善,同时,一号陵园南北向长方形围沟与秦咸阳陵区战国秦陵相似,弥补了秦陵研究的缺环。
5.西安东郊“韩森冢”战国秦陵考古发现与研究
2011年,对位于西安市东郊的“韩森冢”进行了考古调查与勘探,发现封土下为带四条墓道的“亞”字形墓葬1座,陪葬坑2座。由封土、方形墓圹、斜坡墓道和龛组成,全墓东西长146.9、南北宽119.2米;墓圹为方形竖穴土坑,口大底小,开口边长约45米。四条墓道平面均呈梯形,底为斜坡状。龛位于墓道右侧,平面略呈方形或长方形,为竖穴土圹结构,边长8~9 米。墓葬形制与秦东陵中主墓的形制结构较为相近,尤其与四号陵园的主墓几乎完全相同,推测“韩森冢”应为战国秦王陵级墓葬[61]。
关于“韩森冢”墓主,学界有汉刘康的恭皇陵[62]、汉史皇孙冢[63]、秦悼太子陵[64]等观点。
(二)秦始皇帝陵
近10年来,秦始皇帝陵园考古调查和发掘成果丰硕。2009年,陵园勘探工作主要集中在陵园南、西、北内外城垣之间。发现陪葬坑2座及陵园外城垣北门遗址;了解了陵园内城北侧2座门址的形制及结构。一座陪葬坑位于陵园南内外城南部偏西区域,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8、南北宽6、深5.2米。底部有朽木及红烧土等,坑的具体形制及结构尚不清楚。另一座陪葬坑位于陵园西内外城垣之间,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长34、宽7.6~10米,底距地表5.4~5.6米[65]。
随着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成立,启动了一号兵马俑坑的第三次考古发掘工作[66]。这次发掘找到了俑坑被扰时间的地层学依据,可确定为西汉早期甚至更早;首次提出陶俑制作存在缺陷和破损修补,以往所认为的“物勒工名”手工业管理制度,实际上并不适用于作为明器的陶俑生产;在科技考古方面也收获颇丰。在柲、车、皮等不同胎质漆器的漆膜底层发现有青灰色漆灰,主要成分是人为加工的石英颗粒和云母类黏土矿物,也存在骨质成分,应属灰糙;测出的织物包括平纹、交编组织及S捻向的纱线。3例夹紵胎的笼箙制作工艺,一号车的笼箙胎为斫制,二号车的笼箙,虽然胎体为梓木,但却是用了类似竹垒胎的工艺。在笼箙器壁的朽迹中发现了丝织品,判断是绉纱或者是比纱较重的穀[67]。
对秦始皇帝陵园内城西北部区域进行了详细的考古勘探。该区域是由九条通道分割的东西对称的十进式建筑群。建筑遗址在东、西、北三侧各有一道宽3米的夯土墙,将整个建筑围就在独立的墙垣内,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南北向长方形建筑群。建筑遗址的北墙中部有一门道通向内城北墙西侧门址,北侧为9个南北向通道连接起来的东西对称的建筑遗存,最南侧为主体建筑、侧殿及廊道式建筑等结构形式组成的复杂建筑结构,周围用夯土墙围就共同组成十进式的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布局严谨的建筑群。这一建筑遗址保存较好、布局严谨、结构复杂、规模宏大,在中国古代帝陵建筑遗存中不多见,是研究秦始皇帝陵园及中国古代帝王陵墓陵寝制度极为重要的新材料[68]。对该建筑遗址复探中,在建筑群南部勘探出大型夯土台基式建筑,并认为该建筑群南至秦陵封土边缘北至内城北墙,是由台体建筑与院落式建筑组成的十一进结构[69]。对陵园地面暴露出的遗迹进行了考古调查,及对陵园墙垣进行了再次调查勘探[70]。对陵园外城以北偏西侧、内城东西向墙垣门址进行了考古勘探,发现62座古墓葬、7座窑址和灰坑等遗迹,其中8座疑似为战国至秦的小型墓葬,7座窑址可能是与秦陵有关的遗存;在封土北边缘勘探发现陪葬坑1座,平面呈“凹”字形,南北长35.4、东西宽21.5米,为地下坑道式的土木结构,主体为6个夯土隔墙包镶的长条形过洞。同时对封土西侧三号陪葬坑、铜车马坑进行了复探[71]。
对K9901(百戏陶俑坑)陪葬坑进行了全面发掘,出土铜器8、铁器5、石器3、陶器残件4件,27或28件陶俑个体的陶片。确定了该坑的平面形制、组成部分以及建筑结构,确认北侧第三过洞为排列规律的陶俑,丰富了秦陵陶俑的类型,为研究该坑的性质及内涵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同期,在陵园外城东北方向勘探发现一座陪葬坑,该坑东部被古代河流冲毁,现存平面为甲字形,为地下坑道式土木结构,坐东面西,由斜坡门道和主室两部分组成。对内城北部东区曾勘探发现有34座中小型墓葬的区域进行了再次勘探,确认该区域分布着99座大中小型墓葬及建筑遗址、道路等与陵园有关的遗存,是秦始皇帝陵园制度研究的突破性发现[72]。在陵园外城西侧勘探发现与陵园有关的古河道3条、陶窑4座、取土坑58个,均为陵园建设过程中形成的遗存[73]。
2012年,对封土西北侧的一座“甲”字形大墓进行了复探,确认该遗存为一座带有斜坡通道的外藏坑。对内城中部夹墙内的道路遗存进行了勘探,发现了大规模的踩踏路面与铺石遗存,为认识秦始皇帝陵的道路系统提供了新资料。对陵园西内外城之间建筑遗址的勘探,确认为其复原面积达12万平方米的庞大建筑群,性质超出以前所认识的“飤官”建筑,当为陵园礼制性建筑。对陵园北内外城之间建筑遗址的勘探,确认该区域南北可分为三排建筑,总体结构为门阙建筑,是秦始皇帝陵特有的门阙结构形式。在霸王沟勘探发现陪葬坑1座[74]。对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内建设区域进行的勘探,再次确认了三号兵马俑坑西侧“甲”字形大墓,新发现了9座战国秦墓。
对陵园外城北墙北约380米的区域进行了考古勘探,发现一条可能与陵园有关、通往陵园外城北门的古道路[75]。
近年来,还对陵园内建筑遗址、内城东北部部分小型墓葬进行了发掘,对陵园外城西墙西侧发现的“中”字形墓葬区域进行了考古勘探,新发现了多座“中”“甲”字形墓葬,并对一座“中”字形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
秦始皇帝陵的考古研究成果丰硕,除对勘探与发掘成果进行公布外,相继出版有《秦始皇陵二号兵马俑坑发掘报告》[76]《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9~2010)》[77]。研究专著有《秦始皇帝陵园考古研究》[78]《礼仪与秩序—秦始皇帝陵研究》等[79]。
近十年来,秦始皇帝陵园微观研究成果迭出,有关陵园方向、新发现建筑遗存性质、陵园建设等内容,诸多学者进行了多角度探讨,可以说,秦始皇帝陵园的考古研究开始在大规模考古材料的支撑下,对以前的认识进行不断地修正与总结,将会使秦俑秦始皇帝陵研究走向科学、严谨与系统化。
(三)西汉帝陵考古与研究
西汉王朝历时214年,先后有11位皇帝,他们的陵墓均分布在京师长安周围。除霸陵、杜陵分布在汉长安城东南的白鹿原、杜东原上外,其余9座帝陵均分布在渭河北侧的咸阳原上。
从2006年开始,在国家文物局政策及经费支持下,对西汉帝陵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工作。此次工作采取“全方位调查、大面积普探、重点地区详探、关键部位试掘、高精度测绘及资料数字化”的工作思路,田野工作与资料整理齐头并进,取得了较大成果。
工作开展以来,完成了除阳陵以外的其它10座西汉帝陵的考古调查与勘探工作,对霸陵、阳陵、茂陵、渭陵部分建筑遗址、外藏坑进行了考古发掘。累计调查区域255平方公里,勘探面积7000万平方米,发掘面积3200平方米,发现陵园31座,确定陵邑6座,修陵人墓地1处,探明建筑遗址132处,外藏坑1845座,古墓葬1250座。确定了所有帝陵陵区范围和基本布局,探明了各个陵园的结构、封土、墓葬形制、外藏坑、建筑遗址、陪葬墓等,发现了诸如多重陵园、陵区道路系统等新的遗迹现象,了解了文物遗存的性质、内涵。对研究中国古代帝陵,特别是汉代帝陵制度具有重大意义。
工作过程中,在传统考古调查、勘探的基础上,积极尝试新技术、新方法的使用。通过不同时期航空照片的对比判读,确定因人为活动消失了的地面遗迹(如陪葬墓封土等),并对遗址整体和细节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在地面勘探的同时,还与德国美因茨博物馆、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浙江大学等机构合作,运用探地雷达、成像光谱仪等现代科技设备对安陵、杜陵陵区进行了探测,将无损伤探测新技术在考古工作中的运用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研 究。测绘方面建立了各个陵区的三维测绘坐标系统,设立有多个测量控制点,通过测绘部门的控制点,将测绘数据与国家地理坐标系统建立起有效关联。测绘方面,对调查、勘探成果及时采用电子全站仪、RTK等专业测绘设备进行测量,及时成图。积极尝试考古资料的数字化管理,各项记录完成后,及时对资料进行数字化,逐步建立起各个帝陵的考古资料数据库和GIS系统,为考古资料的后期利用和信息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长陵位于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窑店街办三义村北。陵区由陵园、陵邑、陪葬墓区三部分组成,陵园位于陵区西南部,陵邑位于陵园北侧,陪葬墓大多分布于陵区东部,绵延约7.5公里。长陵陵园平面呈长方形,除西墙址外,其余三面墙址共发现门址四处。帝、后陵分别位于陵园东南部、中部偏西处,封土均为覆斗形,东西长约160、南北宽约135米,墓葬形制均为“亚”字形,各有四条墓道,东墓道为主墓道。陵园内发现建筑遗址6处、外藏坑285座,分布在帝、后陵周围。长陵邑遗址平面呈长方形,未发现东城墙,南北长2170.5、东西宽1359.2米,墙外设有壕沟。确定门址2处,位于南、北城墙中部偏东处。陵邑遗址内发现道路、建筑基址、灰坑等遗迹。长陵陵区发现、确认陪葬墓123座,南北向成排分布。地表现存封土41座,16座封土下有两座墓葬,此类墓葬多为夫妻异穴合葬墓。陪葬墓周围设有围沟,部分墓葬周围有夯土墙围绕(图一〇)。

图一〇 汉长陵陵邑西墙(部分)
安陵位于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正阳街办白庙村南。陵区由陵园、陵邑、陪葬墓区三部分组成,陵园位于陵区西南部,陵邑位于陵园北侧,二者相邻,陪葬墓区位于陵区东部。安陵陵园平面呈长方形,周围有园墙围绕,东、西墙中部偏北处各设一门,位置对应,二者之间有道路相连。帝陵位于陵园东南部,墓葬形制为“亚”字形,四面各有一条墓道,地面有高大的封土堆。后陵位于帝陵西侧偏北处,墓葬形制为“中”字形,东西各有一条墓道,封土规模小于帝陵。陵园内发现建筑基址4组、外藏坑168座,建筑基址分布在陵园北部,外藏坑大多分布在陵园北部,少量分布在帝陵周围。安陵邑遗址位于陵园北侧,二者共用陵园北墙,平面形制不规整,东西长1664.7、南北宽1000.4米。遗址周围有城墙、壕沟围绕,北墙、东墙各发现门址1处,遗址内发现道路、建筑基址、陶窑等遗迹。陪葬墓分布在陵区东部,东西分布范围长906.2米,陪葬墓25座,其中13座地面保存有封土,10座墓葬周围有园墙。
霸陵位于西安市灞桥区狄寨街办沟泉村南。陵区由陵园、陵邑、陪葬墓区三部分组成,陵园位于陵区东部,陪葬墓居于陵园西北侧,陵邑位置尚未确定,陵园与陪葬墓分布范围东西约5、南北约1公里。在传统认为帝陵所在地凤凰嘴未发现汉代遗迹,确定了窦皇后陵和江村大墓的墓葬形制,发现墓园1座、门址2处、外藏坑134座、陪葬墓8座。
阳陵位于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正阳街办马台村北。陵区由陵园、陪葬墓区、阳陵邑、刑徒墓地和修陵人居址五部分组成,东西长7、南北宽1~2公里。阳陵陵园位于陵区中部偏西,陪葬墓区位于陵区中部偏东和偏北处,阳陵邑位于陵区东端,刑徒墓地和修陵人居址位于陵区西端。阳陵陵园平面为东西向长方形,长1820、宽1380米,陵园内分布有帝陵陵园、后陵陵园、南区外藏坑、北区外藏坑及3处礼制性建筑遗址。帝陵陵园、后陵陵园均有园墙围绕,每面园墙中部设置有门,封土位于陵园中部,墓葬形制均为“亚”字形,墓室周围有外藏坑114座。陵园北侧有陪葬墓2座,东侧陪葬墓区东西长2350、南北宽1500米,中部有东西向道路1条,道路两侧人工壕沟纵横,将墓区分割成排列整齐的墓园16排107座。阳陵邑遗址东西长4.3、南北宽1公里,整个遗址以1条东西向道路为轴线,两侧有东西向道路11条,南北向道路23条,将遗址分割成面积不等的里坊100余个。2011~2016年,先后对阳陵帝陵陵园东门遗址、东司马门道建筑遗址、陪葬墓外藏坑进行了考古发掘,深化了对西汉帝陵的认识。阳陵帝陵陵园东门遗址位于帝陵陵园东墙中部,南北长135、东西宽11~28米,遗址地面保存有南北对称的2个高大夯土台。发掘部分位于南夯土台的西半部分,清理出的遗迹有:南侧内门塾、主阙夯土台、夯土墙、柱槽及大面积的草拌泥墙皮等。根据发掘情况确定,东门址的形制为古代最高等级的阙——三出阙,使用过程中曾经大规模维修或重建,火灾致使其损毁[80]。

图一一 汉阳陵东司马门道建筑遗址发掘现场
阳陵东司马门道建筑遗址南北宽约107米,分为南北两部分,间距15.4米,中间有宽11.6米的道路,南北两部分以道路中线为轴相互对称。2013年对遗址的北半部分进行了发掘。揭露出的建筑基址平面呈曲尺形,南北长45.8米。南段南北长21.9、宽4.3米;与北段连接部分南北长4.8、宽2.6米;北段为曲尺形,南北长19.1、宽6.7~6.9米;向东曲折部分东西长18.3、宽6.55米;东段东西长14、宽3.3米。基址上部破坏严重,残存深度0.35~0.5米。出土有较多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材料。根据遗址所处位置、规模、形制判断,初步认为其为阳陵陵园东门前的阙。该遗址的发掘对了解、研究西汉帝陵中的司马门、陵园门等各种门址提供了新材料(图一一)。
阳陵陪葬墓外藏坑位于一座陪葬墓的墓道内,长30.4、宽5~5.8、深6米。坑内有大型木椁两具。东椁长13.92、宽3.4、残高0.57~0.76米。椁内出土有骑马俑、木马遗迹、木车遗迹、着衣式陶俑、木俑遗迹等。盗洞内出土有石磬、乐器构件、着衣式陶俑及大量的车马器、兵器等。西椁长11.22、宽2.9、残高0.8~1.54米。椁内出土有罐、仓、茧形壶等陶器及耳杯、盘等漆器遗迹,部分陶器中残留有动物骨骼。外藏坑出土器物多数与汉阳陵帝陵外藏坑中的出土器物一致,属于皇帝特赐之物,由此可见外藏坑所属墓葬墓主人地位之显赫。这座外藏坑的发掘,对于西汉帝陵的陪葬制度研究及高等级墓葬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图一二)。

图一二 汉阳陵陪葬墓外藏坑出土石磬、陶俑
茂陵位于陕西省兴平市南位镇策村南。陵区由陵园、陵邑、陪葬墓区及修陵人墓地四部分组成,东西约9.5、南北约7公里。茂陵陵园位于陵区的中央,陵邑位于陵区的东北部,陪葬墓分布在陵园的四周,其中东侧墓葬较为集中,等级较高,修陵人墓地则位于陵区的西端。陵园内分布有汉武帝陵园、李夫人墓园、11处建筑遗址、244座外藏坑及9座中型墓葬。帝陵陵园平面近方形,边长约430米,四周有园墙围绕,园墙中部各设一门,帝陵封土位于陵园的中心,墓葬形制为“亚”字形,墓室四周呈放射状分布有150座外藏坑。陵邑平面为东西向长方形,长1844.5、宽1542.7米,四周以壕沟为界。陵邑内道路纵横交错,主干道为“三横七纵”,将整个陵邑划分为约30个矩形区间。陵园外陪葬墓分布规律性不强,东侧较为集中,规模较为宏大,大中型墓葬数量多,南侧、北侧、西侧大中型墓葬数量较少。修陵人墓地分布在一条南北向冲沟两侧,小型墓葬排列密集,数量多,面积约4万平方米[81]。2008年,对茂陵二号建筑遗址进行了小面积发掘。二号建筑遗址位于茂陵陵园西南部,平面为东西向长方形,长540、宽493.6米。发掘面积为200平方米,发掘出水渠3条、湖泊遗迹1处,出土了建筑材料、陶器、钱币等遗物。初步推测二号建筑遗址是茂陵陵园内一处园林式建筑遗址。此类建筑遗址在西汉帝陵中系首次发现,对研究西汉帝陵制度具有重要意义。2009~2010年,对茂陵帝陵陵园内2座外藏坑进行了发掘。K15由斜坡通道与坑体两部分组成。坑体内有上棚木、立柱、侧枋木、铺地板、木封门等组成的隧道式木结构,陪葬物品放置在木结构内。北部有一木质隔断;北段为完整的马骨,共7排40具;南段放置10辆木车(图一三)。K26由斜坡通道、坑体及洞室三部分组成,坑体东西两壁下部各开挖10个窑洞。窑洞口部均有木质封门,每个窑洞内放置两具马骨,马头均朝向洞口,马头附近有1~2件陶俑。茂陵2座外藏坑的发掘一方面验证了茂陵大遗址考古勘察工作的成果,同时为了解茂陵外藏坑的形制结构、内涵提供了基础资料,对研究西汉帝陵外藏坑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82](图一四)。

图一三 汉茂陵外藏坑K15出土马骨

图一四 汉茂陵外藏坑K26出土陶俑
平陵位于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双照街道办互助村北。陵区由陵园、陵邑、陪葬墓区三部分组成,东西长约6500、南北宽约6500米。陵园位于陵区中部,陵邑位于陵园东北部,陪葬墓分布在陵园、陵邑周围。陵园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长2096、宽1397米。陵园内分布有帝陵陵园、后陵陵园、袝葬墓8座、外藏坑1238座、建筑遗址7处。帝陵陵园、后陵陵园平面均为方形,周围有各自独立的园墙,每面园墙中部设有门,封土位于陵园中部,墓葬形制均为“亚”字形,陵园内有外藏坑54座。平陵邑遗址平面不规整,南北长4523、东西宽2798米。遗址内3条南北向道路和6条东西向道路将遗址分隔为28个里,每个里有独立的围墙、围沟。陪葬墓分布在平陵陵园周围,原有封土近百座,绝大多数已被平掉。
杜陵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曲江街道办事处三兆村南。陵区由陵园、陵邑、陪葬墓区三部分组成,东西长约4000、南北宽约4000米。陵园位于陵区西南部,陵邑位于陵园北侧,陪葬墓分布在陵区东部。陵园园墙保存较差,帝陵陵园、后陵陵园位于陵园南部,礼制性建筑遗址位于陵园南部、东北部,陵园北部有外藏坑48座。帝陵陵园、后陵陵园平面形制均为方形,四面有园墙围绕,每面园墙中部设置有门,封土位于陵园中部,帝陵墓葬形制为“亚”字形,后陵只发现了西墓道,陵园内有外藏坑41座。杜陵邑城址平面为东西向长方形,长2100、宽500米。杜陵祔葬墓、陪葬墓已探明140座,62座地面保存有封土。
渭陵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周陵街道办事处新庄村南。陵区由陵园与陵园外陪葬墓两大部分组成,陵园位于陵区北部,陵园外陪葬墓分布在陵园西、南、东三面,东西长约3000、南北宽约3500米。陵园内分布有汉元帝陵园、王皇后陵园、傅昭仪陵园及外藏坑16座、礼制性建筑遗址4处、祔葬墓及完备的道路系统。汉元帝陵园、王皇后陵园位于陵园中部偏南、偏西处,平面均为方形,四周有园墙环绕,每面园墙中部各辟一门,覆斗形封土位于陵园中部,墓葬形制均为“亚”字形,封土周围有外藏坑10座。傅昭仪陵园位于渭陵陵园中部偏东处,平面近方形,四周有园墙环绕,每面园墙各辟一门,墓葬形制为“甲”字形。祔葬墓位于渭陵陵园东北部,排列整齐,5排32座,现存封土12座,墓葬形制均为“甲”字形。渭陵陵园外陪葬墓共26座,大部分封土仍存,分布较为散乱,部分墓葬成组分布[83]。
延陵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周陵街道办事处严家沟村西北。陵区由陵园及陵园外陪葬墓两大部分组成,东西长约4500、南北宽约4000米,陵园位于陵区中部,陵园外陪葬墓分布在陵园西、南、东三面。延陵陵园平面形制为东西向不规则长方形,西北角内收,东南角外凸,这种特殊的陵园形制与其避让平陵陪葬墓及陵园东侧的严家沟战国秦陵园有关。陵园内分布有帝陵陵园、后陵陵园、6处建筑遗址、17座外藏坑、祔葬墓等。帝陵陵园位于延陵陵园中部偏东南处,平面为南北向长方形,四周有园墙环绕,每面园墙和封土正对位置设有门,帝陵封土位于陵园中部偏南处,墓葬形制为“亚”字形,封土东、北侧有外藏坑3座。后陵陵园位于延陵陵园西部,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四周有园墙围绕,东、南墙辟有门,北、西墙留有缺口,应为门道。陵园南部一道东西向隔墙将陵园分隔为南、北两个院落,后陵封土位于北院中部,墓葬形制为“亚”字形。建筑遗址分布在陵园东南部、北部,外藏坑分布在帝陵陵园东西两侧。袝葬墓位于陵园西北部,共4排19座,13座保存有封土,每排3~7座,排与排之间有道路相隔,墓葬周围绕以园墙、围沟形成墓园。陵园外陪葬墓确定36座,28座保存有封土,墓葬形制多为“甲”字形。
义陵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周陵街道办南贺村东南。陵区由陵园及陵园外陪葬墓两大部分组成,东西长约2800、南北宽约3100米,陵园位于陵区西北部,陵园外陪葬墓分布在陵园南侧、东侧。陵园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长1857、宽1540米,周围设有园墙、壕沟。陵园内分布有汉哀帝陵园、傅皇后陵园、外藏坑、建筑遗址及祔葬墓。汉哀帝陵园平面呈方形,四周有园墙围绕,中部各设一门,封土位于陵园中部,墓葬形制为“亚”字形。傅皇后陵园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四周有垣墙围绕,中部各设一门,封土位于陵园中部,墓葬形制为“甲”字形。帝陵陵园周围分布有17座外藏坑,北侧及东北部分布6处大型建筑遗址。祔葬墓位于陵园东北、西南部,共7座,1座封土尚存,东北部祔葬墓的西侧、南侧,设有园墙、围沟。陵园外陪葬墓分布在义陵陵园外东、南侧,确定的陪葬墓16座,12座保存有封土,封土形状有覆斗状、圆丘状和不规则状三种,墓葬形制均为“甲”字形竖穴土圹墓[84]。
康陵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周陵街道办事处大寨村东。陵区无陪葬墓分布,主要为康陵陵园及相关遗迹,东西长2200、南北宽1700米。康陵陵园将汉平帝陵园、王皇后陵、2处建筑遗址等界围其中,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周围有园墙、壕沟环绕,南墙中部设置有门。汉平帝陵园位于康陵陵园中部偏西处,平面近方形,四周有园墙围绕,中部各设一门,封土位于陵园中部,墓葬形制为“亚”字形。王皇后陵有内、外两重陵园;外陵园平面近方形,边长约830米,四周有园墙围绕,辟有5门;内陵园平面为南北向长方形,四周有园墙围绕,中部各设一门,封土位于陵园中部,墓葬形制为“亚”字形,北墓道两侧有外藏坑7座。汉平帝陵园与王皇后陵园外有一条围沟环绕,围沟区域平面呈“刀”形,东西长908.4~1500.5、南北宽619~866.5米。康陵陵区还分布有建筑遗址10处及完备的道路系统。康陵陵区这种复杂的陵园关系是在西汉晚期政权更迭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85]。
除上述诸帝陵外,还对按照帝陵、皇后陵规制修建的汉太上皇万年陵、汉薄太后南陵、汉钩弋夫人云陵、汉许皇后少陵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与测绘。
万年陵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振兴街道办事处昌平村东北。陵园平面近方形,周围以围沟为界,未发现园墙。太上皇陵位于陵园中心,封土呈覆斗形,边长约60米,墓葬形制为“亚”字形。夫人墓位于太上皇陵西北,封土呈馒头形,墓葬形制为“甲”字形。陵园内还发现建筑遗址1处、外藏坑6座。
南陵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狄寨街道办事处鲍旗寨村西北。陵园平面近方形。南陵封土呈覆斗形,底部南北171、东西153米;顶部东西长47、南北宽35米;高约24米。墓葬形制为“亚”字形。陵园内发现外藏坑15座、建筑遗址3处。南陵邑的位置尚未确定。
云陵位于陕西省淳化县铁王镇大圪垯村北。陵园平面近方形,周围有夯土园墙围绕,四面设置有门。云陵封土呈覆斗形,底部边长约150、顶部边长约50、高约31米。在封土南部发现墓道1条。陵园内有外藏坑26座,陵园外有建筑遗址2处。云陵邑位于陵园西北,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长708、宽349米。
少陵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大兆街道办事处大兆村南。陵园有内外两重夯土园墙,平面均为东西向长方形,四面各辟一门。许皇后陵封土为覆斗形,底部边长97、顶部长35、宽29.7、高14.8米,封土东侧发现1条墓道。陵园内有外藏坑17座、建筑遗址2处。
十年来,西汉帝陵考古在资料整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长足进展。《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是对2001~2005年工作成果的介绍[86],是西汉帝陵研究较为全面的基础资料。茂陵、渭陵、义陵、康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介绍了这4座帝陵最新的考古成果。焦南峰等还对西汉帝陵大遗址考古的工作思路、方法及效果进行了总结[87]。阳陵帝陵陵园南门遗址[88]、东门遗址[89]、茂陵帝陵陵园外藏坑发掘资料的公布,为研究西汉帝陵制度、内涵增加了新资料。
综合研究涵盖了西汉帝陵选址、布局、营建、丧葬思想等内容。包括对西汉帝陵分布与昭穆制度之间的关系[90]、西汉帝陵布局与汉长安城、自然环境、皇权传承的关系[91],西汉帝陵选址[92]、形制要素[93]、封土[94]、“夫人”葬制[95]、道路[96]、门阙制度[97]等多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是将陵区组成由多个遗址、遗迹提高到陵园、陵邑、陪葬墓的层次,使学界对西汉帝陵认识上升到了新的高度。对西汉帝陵皇后陵的方位、外藏坑[98]、祭祀制度[99]、陪葬墓、制度变化[100]、丧葬思想[101]、陵寝[102]、墓向[103]、修建过程[104]、陵庙及庙制[105]、陵邑功能与营建[106]、皇后葬地[107]等问题或专文探讨,或在相关研究中有所论述。综述性文章有对秦汉帝陵制度研究综述[108]。
对单个帝陵、问题开展的研究有:对长陵邑[109]、茂陵陵园布局[110]、“次冢”[111]、康陵布局[112]、霸陵帝陵墓葬形制[113]、阳陵帝陵陵园南门遗址[114]、义陵“董贤墓”[115]、阳陵帝陵陵园设计[116]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与探讨。综述性文章有对阳陵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117]。
器物研究主要集中在阳陵出土器物,诸多学者对铜印、封泥[118]、刑具[119]、陶俑[120]、陶仓、陶羊[121]、武士俑[122]、陶牛[123]、铜镜[124]进行了介绍、考释与研究,此外,焦南峰等对西汉帝陵陶俑[125]、刘云辉等对杜陵玉杯、玉舞人[126]进行了介绍与研究。
科技考古、文保保护方面主要以阳陵出土物、遗址为研究对象,在动植物遗存[127、128]、文物保护[129、130]与展示[131、132]、文物保护环境监测[133、134]及危害预防处理[135]等多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对于西汉帝陵尤其是阳陵出土文物的保护、研究与展示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西汉帝陵考古工作全面了解、掌握了各个帝陵陵区范围、布局及结构,为西汉帝陵的保护、研究、展示提供了科学资料,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较大的社会影响。该项目入选“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获得国家文物局2009~2010年度田野考古奖一等奖。
三、中小型墓葬发现与研究
(一)中小型秦墓葬考古发现与研究
1.中小型秦墓的考古发现
宝鸡地区:该地区是秦墓分布的密集区,近年秦墓发现、发掘数量丰富。为了了解中小型秦墓和秦公陵园之间的关系,对雍城六号秦公陵园中兆沟外侧发现的708座中小型墓葬及车马坑进行了选择性发掘,共发掘墓葬1座,车马坑3座(图一五)。该墓地的墓葬较多配有车马坑,表明墓主人具有贵族身份。但此次发掘无法判断墓地与六号陵园的关系,根据秦人西为上的原则,这批墓葬和车马坑可能属于四号或十号秦公陵园[136]。凤翔翟家寺两座小型秦墓均为竖穴土坑墓,带有生土二层台和脚窝,出土器物较少[137]。凤翔雷家台墓地发掘的5座小型秦墓均为竖穴土圹墓,出土器物有陶、铜、铁、玉石器等,时代为战国中期前后[138]。以往发现的秦墓均位于雍城城址外,翟家寺、雷家台两处新发现的秦墓位于秦雍城城址内北部,对于研究秦雍城布局、沿革提供了新依据。凤翔六道村战国秦墓地位于秦雍城城址东侧,为一处具有特色的国人墓地,整个墓地范围较大,对墓地局部进行了发掘,共23座,墓葬排列较整齐有序,多为偏洞室墓,仅个别墓葬为竖穴土圹墓,这批墓葬资料提供了秦雍城周边秦墓地聚族相葬布局的线索[139]。凤翔路家村墓地发掘8座墓葬,其中5座战国秦墓,1座汉墓及2座晚期墓葬,均属中小型墓葬,墓葬形制较完整,随葬器物特征明显,为凤翔地区墓葬研究增加了资料[140]。宝鸡市洪塬村发现春秋中期秦墓1座,出土遗物约10件。该墓放置棺椁的方式在宝鸡地区是首次发现。这种墓室形制或是竖穴土坑墓向偏洞室墓的过渡形态,为了解宝鸡地区秦墓形制的发展演变提供了新材料[141]。

图一五 雍城六号秦公陵园外侧中型墓葬车马坑
咸阳地区:咸阳、西安地区在配合基本建设的过程中发掘了大量的秦墓,主要分布在秦咸阳城的西北部。坡刘墓地发掘战国秦墓108座。墓葬形制主要有竖穴土坑墓、竖穴墓道洞室墓两种类型,洞室墓又分单室和双室两种。随葬品共741件(组)。坡刘墓地出土陶器特征与塔尔坡秦墓、任家咀秦墓相比较,初步判断墓地时代为战国晚期至秦统一,墓地主人是秦人贵族[142]。关中监狱新征地共发掘古墓葬310座,出土文物700余件(组)。其中战国秦墓278座,分布密集,排列有序,有的区域墓葬间距仅0.4米,个别墓葬有相互打破现象,表明了墓地延续了较长时间。278座战国秦墓中,竖穴墓40座,洞室墓236座,瓮棺葬2座。该墓地的发掘,基本上可以把以前发掘的任家咀春秋战国秦墓群和塔儿坡战国秦墓群连成一片,也就是说,从任家咀到塔儿坡,东西2、南北1公里的庞大区域是秦都咸阳西郊一处大型公共墓地[143]。花杨墓地发掘秦墓68座,竖穴墓道洞室墓占绝大多数。花杨墓群与塔儿坡秦墓、关中监狱战国秦墓群时代相同,应为战国晚期秦墓。花杨秦墓群的发掘对研究秦咸阳城周边秦墓提供了新资料[144]。咸阳市渭城区贺家村北发掘战国秦墓163座,墓葬大部分为竖穴墓道直线洞室墓,少数为竖穴土坑墓,3座墓葬周围设有围沟。墓葬陶器组合分为仿铜陶礼器组合和日用陶器组合,此外还有数量较多的陶蒜头壶和铲状袋足鬲1件。揭露出一条与墓地同时期的道路,对研究墓地布局、结构、形成等具有重要的作用[145]。上述几处秦墓的发掘,为研究秦咸阳城城市布局、咸阳原秦陵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夹道村秦墓发掘在乾县尚属首例,填补了该地秦墓空白,扩大了关中地区秦墓分布范围。4座小型秦墓年代从战国早期至晚期,M3“同穴合葬”为研究战国时期葬俗制度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这批墓葬的主人很可能与战国秦置“好畤邑”的历史背景有关[146]。杨凌区柔谷乡尚德墓地发掘的300余座墓葬中,大多为东周、秦汉时期的中小型墓。从墓葬规格看,墓主人的身份多为一般平民。此外还发现了多道封闭或半封闭的围沟。通过此次发掘,为厘清不同时期聚落的内部结构、性质提供了有力依据[147]。西安临潼清泉发掘秦末汉初竖穴土圹砖椁墓1座。从秦陵周围已发现的秦墓来看,类似墓葬比较少,其性质的认定有待于更多的考古发现。这些墓葬为秦始皇帝陵周围秦墓与秦陵营建人员构成、秦汉墓葬发展演变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148]。
渭南地区:既往秦墓发掘主要集中在关中中西部,近年来在关中东部地区陆续发现、发掘了一批秦墓,充实了该区域秦墓资料。据《史记·秦本纪》等文献记载,战国中期以后,秦与三晋在关中东部曾有过持久的拉锯战。一般认为随着战争的持续,秦文化才得以逐渐在关中东部扩张开来。通过华县东阳、华阴市沙渠村、蒲城永丰、白水西章等墓地的发掘,秦文化东进的时间上限已经推前到春秋早期。
渭南阳郭战国秦墓地共发掘战国秦墓32座,均为中小型墓,墓葬形制有竖穴土坑墓、平行线洞室墓、直线洞室墓3种。M58墓室底部有0.3米厚的积石,在秦墓中少见。随葬器物有陶、铜、铁、料器等。墓葬时代为战国中晚期[149]。东阳墓地位于华县西南,有上千座西周早期至东汉时期的墓葬。2001年发现秦墓69座,发掘38座,时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150]。2014年,东阳墓地发掘秦墓18座、灰坑9座、灰沟1条。类型学研究结果表明,18座墓葬可分为四期。第一期的M3,使用一棺一椁葬具,有荒帷,3件铜鼎形制与陇县边家庄春秋早期秦墓出土列鼎有相似之处,所见的重环纹带及垂鳞纹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时代特征。第二期10座墓葬中出土的喇叭口罐等典型秦文化器物,与宝鸡西高泉、陇县店子等地春秋早期器的特征非常接近,不晚于春秋中期[151]。华阴市沙渠村发掘秦墓11座。墓葬形制皆为竖穴土坑结构,葬具一般棺、椁齐备。葬式为仰身或侧身屈肢葬。随葬器物主要为陶器,多放于椁里棺外,头厢或头顶位置。多数墓葬随葬有羊骨,一座墓葬填土中发现有殉狗。墓葬时代主要集中在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152]。
蒲城县永丰镇以北洛河东岸发现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古墓群。这里在战国时期曾一度为魏国占领,是秦魏两种文化的交融地带。经局部勘探,确定26座墓葬并发掘其中4座。墓葬结构为竖穴土圹墓1座、竖穴墓道土洞墓3座。出土器物有陶器、铜剑柄、玉璧等。该墓北部发现3个祭祀坑,坑内有幼犬骨架、陶罐等。墓室西壁龛内有大量的殉牲,种类有牛、马、羊、鸡、狗、兔等。墓葬的时代为战国晚期至秦代[153]。在白水史官乡西章村发掘东周墓20座。均为竖穴土圹结构、一棺一椁葬具,墓主仰身屈肢葬、头西脚东。绝大多数的陶器组合为一鼎或二鼎、二簋、二壶、二豆,少数为罐、盆、鬲或仅有罐、鬲。尽管墓葬形制及器物组合与宝鸡地区东周墓葬类似,但仿铜陶礼器器形差别较大,日用陶器制作粗糙,明器化特征明显,发掘者将其年代判断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从M13出土的喇叭罐、甗等器物看,时代可早到春秋中期,日用陶器制作粗糙具有明器化特征,或许是受当地经济水平的影响[154]。
2013年在澄城县居安墓地探明了墓葬和城址的基本情况。城址位于西北部,是一处沿沟而建、居险设守的军事堡垒,东、南、北三面城墙与西边自然沟合围,面积逾20万平方米。墓地长约1600、宽约1000米,北部、东部时代早,南部、西部晚,墓葬数量达3211座。重点发掘了2座墓葬,均为竖穴土坑结构,葬具为一棺一椁,仰身屈肢。出土器物多在头箱处,有陶、铜、玉、石及煤精制品等。两墓均出有典型秦人器物,时代为春秋中晚期,其中M158出土陶鬲有周文化因素,时代可能略早于M8(图一六 )。

图一六 澄城县居安墓地M8墓室情况
关中东部地区秦墓的墓主人身份以平民居多,早期少有随葬兵器,应该是一种和平状态的下的自然移民。战国早中期开始,秦墓数量突然增加,陶质随葬品的多寡与兵器的有无存在一些关系,其中一部分墓主应该属于战争性移民。作为文化过渡地区,这些墓地中也常包含三晋及楚的文化因素[155]。
陕西地区中小型秦墓分布区域广,数量多,内涵丰富。学者依据丰富的考古资料,从多角度对秦墓葬进行研究,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
《临潼新丰——战国秦汉墓葬考古发掘报告》是关中地区迄今为止一次性发掘的数量最多的秦墓,同时又是关中东部地区首次发掘的大规模秦汉墓群。594座墓葬分为战国中期晚段、战国晚期、战国末期至秦代、秦末汉初四段。报告详细介绍了各个墓葬的资料,并对墓葬形制、葬具、葬式、随葬器物、墓葬分期、年代及相关问题进行了综合讨论[156](图一七、一八)。
2.秦人秦文化源流研究
从墓葬信息分析秦文化的源流,是中小型秦墓研究的重要内容。早期秦文化是指西周至春秋前期,或公元前677年秦德公居雍以前的秦文化。秦文化的很多特点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秦文化的来源即商文化、周文化和西戎文化[157]。从秦人早期考古资料来看,西首葬、屈肢葬与直肢葬及殉人与腰坑是秦人早期最主要的丧葬习俗。西首葬与太阳崇拜的宗教习俗密切相关。采用直肢葬的人群为贵族、国人,采用屈肢葬的人群多为墓主的家奴或身份低贱者(平民)。殉人既有自愿殉葬的贵族,丧葬形式多采用直肢葬;也有墓主家年轻的家奴或被杀殉葬的人。腰坑很可能是当时的祭祀坑[158]。史党社以文献与考古材料互证的角度,提出了如何界定各个时期“秦人”的标准[159]。认为秦文化在春秋早期得以初步形成,之后曾向境内的异姓族群传播,政治、军事力量是传播过程中最重要的推手。文化传播对秦人族群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导致了异族间“秦人”认同的产生,族群认同反过来又作用于文化的传播,最终使不同的人群形成了相对同质的“秦人”共同体。这种传播持续到战国—秦时期,并最终导致西北戎狄趋于消亡与新“秦人”共同体的诞生[160]。陈洪以大量秦墓葬材料分析为中心,研究秦人社会发展变迁之轨迹,提出了秦文化遗存之分布与时间框架的建构、秦文化的传统与变革、秦文化的传播与六国社会的变迁等学术思考[161]。从葬俗的角度对中型秦墓墓主族属、身份进行了探索,认为直肢葬的中型秦墓墓主与大型秦墓墓主出自同一个族群,这个族群在秦人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属于贵族阶层。秦贵族阶层的直肢葬来自周文化,下层平民采用的屈肢葬式源自西北甘青地区古文化,两者渊源不同,族属各异。屈肢葬中型秦墓的头向具有多样性,墓主身份、籍贯均较复杂,西头向者应是西北诸戎部族及其后裔,北、东、南头向者来自秦以外的其他地区[162]。滕铭予通过对宝鸡建河墓地环境观察,以及与相关文化遗存的比较,提出了秦文化居民中某些处于低阶层的人群进入汉代以后,仍然保留了自身传统的文化习俗[163]。张寅对东周时期关中地区西戎遗存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基本厘清了关中地区西戎遗存的年代,指出其来源于甘肃东部地区,是东周西戎考古学文化的一个次生类型,进而认定其应与迁徙到关中居住的西戎移民有关[164]。孙占伟对清涧县李家崖东周秦墓重新分析探讨,认为墓地以战国晚期为界可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墓地性质为晋系文化遗存。第二阶段为战国晚期至秦统一,墓地性质为秦文化遗存。这一现象与文献记载也相吻合[165]。

图一七 临潼新丰墓葬群M7随葬陶器组合

图一八 临潼新丰墓葬群M91随葬陶器组合
秦人族源是秦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观点有西来说、东来说和北来说三种,而争论焦点主要在东、西之争。近百年来的争论以20世纪70年代为界,分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主要是依据文献资料和民俗资料展开的研究和争论,可称之为传统的东来说与西来说之争;后一阶段则在文献和民俗资料的基础上,广泛运用考古学资料展开综合研究,可称之为新东来说与西来说之争。近几年来,超越东、西之争的新成果开始出现,推动秦人族源问题的讨论走向深入[166]。文化传播与交流方面,段清波认为秦文化中的兵马俑、铜车马等文化因素,不是从固有文化中发展演变而来,而可能是通过丝绸之路由西亚传播到东方的,与此同时,秦统一时期,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制度也传入东土,并对秦始皇帝的改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167]。
周原遗址及其周边发掘的秦汉墓葬不仅有助于了解周原地区商周时期以后的聚落形态演化过程,而且对探讨秦汉时期京畿周围地区普通民众丧葬习俗及社会生活状况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168]。关于秦墓葬在获得更多新材料的情况下,重新检索沿用多年的分期标准,依据凤翔孙家南头春秋秦墓的重要考古新发现,即由于该墓地处于秦“九都八迁”的“汧渭之会”一带,对于探索秦东迁路径、城邑、地望和早期秦文化区域特征有重要关系,也因其特殊地理位置关系,以及随葬铜器墓中有陶器共出的现象,为多年一直沿用传统且各自独立的铜器与陶器分期标尺提供了相互比照的实物资料。有学者关注到一个现象,即若将该墓地与其周边同类、同期墓葬比较,二者虽有共性,但自身特征也较为明显,体现早期秦国多元文化特征及其复杂群体之间相互融合的历史背景[169]。
3.中小型秦墓葬俗研究
屈肢葬是关中、陇东地区秦墓的重要特征,这一地区秦墓中还有一定数量的直肢葬。由于两种葬式同时并存,屈肢葬多见于小型秦墓,直肢葬多见于大、中型秦墓,有关学者多以为秦人葬式与社会等级密切相关,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收集分析秦人葬式资料发现,这种象征意义只延续到春秋战国之交。战国早、中期后,小型秦墓中直肢葬的增加,秦人葬式中的等级色彩逐渐消失[170]。关于屈肢葬的源头和独特的方式,早期秦文化在葬式、出土陶器等方面兼具辛店、寺洼文化要素,辛店、寺洼文化的屈肢葬都可能是秦人屈肢葬的源头[171]。葬俗具有很大的延续性与保守性,在同一考古学文化之下,不同的葬俗可能就反映了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别,这一点在早期秦文化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近年西汉水上游早期秦文化项目的开展,发掘了一批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秦墓,对于历年西汉水上游、宝鸡地区汧河、渭河流域春秋早期及以前的秦墓资料的梳理和对各类墓葬所代表的人群的分析,对于揭示早期秦人的人群来源和结构有着重要意义[172]。
秦人的殉葬传统一方面是由秦人传统的丧葬习俗影响所致,另一方面,是与羸秦早期居于戎狄之地所形成的落后生活所决定的[173]。有学者通过对东周齐、秦殉人墓之比较研究来探讨其文化内涵之嬗变[174]。总结春秋至战国早期秦人车马殉葬方式,并上溯到西周和商代,认为殷人、西周殷遗民和秦人的车马殉葬方式同属于一个前后发展的系统[175]。
有学者通过收集关中地区秦墓头向数据,分析秦墓头向空间分布特点,从而研究秦的移民结构。秦地外来移民的埋葬地或应有固定的区域,但是各种头向墓群相互间隔很近,侧面反映了当时咸阳城居民的居住状况,即外来移民与当地秦人曾经在咸阳周边混居杂处,不存在地域、空间的隔阂[176]。
葬俗研究方面,春秋时期三晋与秦的葬俗不同,战国时期三晋的葬俗文化开始与秦趋同,战国晚期随着秦灭六国战争的推进,各地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秦文化,同时,秦文化也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而产生融合[177]。葬具研究方面,研究者认为由秦墓葬具的数量、尺寸、形制和饰件,基本上是依据“周礼”所记载的程序进行的,但在公级葬具的饰件上有越礼的现象[178]。
4.中小型秦墓出土器物研究
目前发掘的楚墓、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遣册,而秦墓中却很少发现。究其原因,遣册是周代丧葬制度的内容,秦未从根本上接受周的礼乐文明,未严格遵循周礼关于丧葬的繁琐规定,故秦墓很少有遣册出土[179]。
秦镜出土时残损比例超过80%以上,秦墓对随葬铜镜位置的讲究、对铜镜残片有意识的分别摆放,显示出秦镜的残损很可能是在随葬时人为打碎的,推断秦人在使用铜镜随葬时有毁器的习俗。毁镜习俗与地域和民族有关,流行于秦文化崛起的过程中,随着秦亡汉兴,这种古老的习俗也渐行式微。这种习俗在北方的匈奴、鲜卑民族中也能见到[180]。通过对西安尤家庄秦墓出土镜的观察和研究,认为铜镜从时间和空间看,铜镜出土的地理位置越偏东,数量越多;从种类看,时代越晚,其种类越丰富[181]。
铜带饰是渭河流域秦墓中的常见器物,其时空分布与秦国的发展史相吻合。从秦的数次迁都、与戎狄的战争、秦墓中戎狄文化因素来看,在秦与戎狄部族长期的互相影响下,这种具有强烈戎狄风格的饰品在秦国获得了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秦人的生活[182]。S形饰也是一种带饰,最普遍的使用方法是用于系结纺织物的腰带。由于其实用性不强,到汉代后随着秦文化的消亡而消失[183]。
秦式玉器造型极富特色、纹样独特、雕琢工艺别具一格,不同历史阶段其器形、纹饰及工艺制作特点也有所不同。秦、楚两地文化交流与传播也对秦式玉器有所影响[184]。在全面收集了关中地区秦墓出土的玉器资料,分析了秦墓出土葬玉的特点及随葬情况,认为自战国中晚期开始,随着国势的逐步强大秦国逐步摒弃西周礼制[185]。
新近发现的几件秦式青铜器和梁带村芮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有很多相似之处,对春秋时期秦芮关系的研究有一定的价值[186]。凤翔小沙凹村春秋时期窖藏青铜器发现于2006年,从器形、纹饰、铭文来看,并非秦文化器物,是典型的中原文化风格,应该是从中原流传到秦国的青铜器[187]。这批器物是秦人与东方交往的物质见证,反映了秦人崛起的历史事实。另外春秋时期的秦人器用制度具有较为独特的特点[188]。
陶囷模型最早出现在春秋晚期秦墓中,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数量最多,战国中期到秦代明显减少。陶囷模型器的流行有着独特的社会背景,对于秦汉文化的传承关系的探讨有重要意义[189]。陶囷与秦国的农业发展和秦人的价值观及丧葬习俗分不开,而陶囷和陶仓的流行时间的不同与它们不同的文化内涵有很大关系[190]。
铜器铸造方面,对陇县边家庄M12出土春秋早期秦式铜戈铭文的重新考释表明,铭文与铜戈铸造有关,铭文前四字指用于铸造铜戈的金属原料:铜和锡铅[191]。
西周、春秋时期秦人较多使用黄金饰品并可能掌握了提炼水银工艺,甘肃东部地区早期秦人很可能较早使用了鎏金工艺,而后随着秦人东进此技术传播到中原地区。战国时期王畿洛阳地区较多使用了鎏金工艺[192]。秦金银器的出土地点主要集中在甘肃、陕西,在全国其它地方也有零星出土。
以秦人由封国向帝国的转变为历史背景,着重分析了秦代社会生活中饮食具的多元类别与其特定的社会功能。从生活日用与祭祀礼仪这两个主要方面入手,详细列举了从封国时期的关中地区至帝国时代的朝野内外丰富而多元饮食具的历史演进[193]。甘肃东部地区应是铲足鬲的原生地,铲足鬲来源于西周至春秋早期分布于甘肃东部的寺洼文化[194]。来源于寺洼文化的还有戎式陶罐,作为西戎遗存的代表性器物,是战国时期迁居关中地区的西戎移民的遗物[195]。秦代关中地区随葬品出现了反映现实生活的仓、灶等陶制明器,不同于同时期其它地方的随葬品制度,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秦国统一全国的政治因素,为研究秦国的随葬价值观提供了重要的线索[196]。
秦出土漆器的研究成果较多。通过对秦生漆资源分布及利用、漆器手工业生产与管理、制作工艺及艺术风格等问题的研究,初步梳理了秦漆器发展的历史脉络,彰显了秦漆器艺术的基本特征[197]。对秦漆器手工业相关问题的研究分析进一步表明,以中央直属、地方官府经营与小规模私人经营并存的漆器手工业在技术创新发展、生产工艺流程、生产经营管理及产品质量监督等方面逐步走向规范化、条理化。充分彰显了秦漆器手工业的发展特色与经营理念[198]。对秦纪年漆器铭文中有关制地、职名等问题的分析,探讨了战国晚期至秦代漆器手工业的性质及督造、监造、制造等管理流程的发展演变[199]。在秦人发展的各个阶段均拥有一定量的生漆资源。特别是战国晚期至秦统一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土面积的扩大,生漆资源的拥有量也在不断递增。当漆器制造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规模经营。随着漆器手工业的发展,社会对生漆资源的产量、质量需求也在逐渐提高。顺应这一形势,开始出现了以官府为主体的漆园经营[200]。对秦漆器胎骨和胎骨制作工艺的分析研究,进一步表明漆器胎骨发展演变的轨迹。对推进漆器制造工艺的改进、漆器艺术风格的演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01]。秦代漆器艺术风格的地域特色较为明显,这种文化层面上的差异与秦统一的文化政策及相关手工业的法律、法规存在一定的迥异[202]。釦器法是战国中期出现的一种新型漆器制作方法,发展于战国晚期和秦代,成熟于两汉时期。从战国至两汉时期,釦器漆器的类型由相对比较单一向多元化发展;釦器的材质由铜、错金铜、错银铜、镀银铜、鎏金铜向银釦、金釦发展;釦器由最初的实用性向艺术性发展;制作工艺由简单化向复杂化演变。各个时期的釦器漆器均有较为鲜明的时代特征[203]。秦东陵出土漆豆的制作工艺、彩绘纹样均运用了最基本的制作方法和彩绘艺术,与楚式漆豆有相似之处,漆豆的铭文风格充分彰显了秦漆器的艺术特色,对研究漆器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从随葬器物组合来看,秦墓中随葬漆豆却非常少见,这种现象可能与当时的社会因素有关联[204]。通过秦东陵出土漆豆铭文的考证,考定漆豆制作于秦昭襄王八年,“薛君”即孟尝君,“殳”为文献中的“金受”,亦即“金投”。出土漆豆的M1极可能是秦昭襄王墓[205]。
秦国是东周时期最早使用铁器的诸侯国之一。从春秋到秦统一,秦人铁器历经了初创、缓慢发展和快速发展三个阶段,铁器在秦国社会发挥作用首先从农耕开始,随后发展到手工业领域,各种木作铁工具被广泛运用。从关中地区秦墓出土铁器观察,早期来源于戎,而晚期受中原地区影响较大[206]。为讨论秦国铁工业发展的脉络,林永昌等人收集了关中东周到秦统一时期出土的铁器资料,考察铁器种类的年代变化、与相关随葬品的共存关系以及使用背景。指出秦国铁器的普及化过程在多方面表现出不平衡性。最后,铁器的普及程度也显示出地域性特点。在战国中晚期,距离都城越近的墓地,随葬铁器和其他金属制品的比例越高,可能说明中心与地方在手工业生产与产品流通的差异[207]。
5.中小型秦墓科技考古研究
体质人类学方面,研究者以关中地区出土人骨为基础,从人口的死亡年龄结构、平均身高、肢骨粗壮指数及病理四个方面出发,对秦人平民阶层与劳工阶层间体质的差异进行了研究[208]。通过对凤翔孙家南头春秋时期秦墓的9例人骨标本的观察和测量,研究者将孙家南头秦人归入“古中原类型”居民。与典型的“古中原类型”比较,孙家南头秦人上面部偏高、颧宽绝对值偏大,这些特征或许受到了来自甘青地区“古西北类型”因素的影响[209]。临潼新丰秦墓人骨标本与相关地区的的比较研究发现:新丰组颅骨在人种分类上属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范畴,其基本的种系成分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中的东亚类型最为接近,其次为南亚类型。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若干近代组的比较表明,新丰组在颅骨的基本形态特征方面与近代华北组最为接近,其次为华南组。与新石器时代各组的比较结果显示其与陶寺组、仰韶合并组最为接近。与夏代至汉代相关颅骨组的比较结果显示新丰组与游邀组、乔村A组最为接近[210]。
人体骨骼中的微量元素与其生前的食谱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分析人骨中的微量元素可以揭示古代先民的饮食结构。近年,这一领域做了大量的分析研究工作。孙家南头春秋战国秦墓人骨中稳定同位素组成测试分析表明,春秋战国时期陕西凤翔地区秦先民是以C4类植物为主食、辅以少量肉食的杂食性食谱;经济模式可能为农业与畜牧兼营,以种植黍、粟类等旱地作物的农业形式为主,并辅以驯养牲畜;殉人可能是与墓主饮食方式较为相近的姬妾或仆从之类的人;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秦先民的食物结构较为稳定,C4植物比例与δ15N发生变化的原因可能与当时历史的变迁与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211]。利用等离子体质谱仪测试分析了宝鸡建河墓地出土战国时期秦人骨中与食谱有关的元素,结果表明战国时期宝鸡地区秦先民的食谱结构主要是以植物类食物为主,肉类为辅;经济模式可能以种植黍、粟类等旱地作物为主,并辅以畜牧为生[212]。将线性回归分析方法运用于古食谱研究中的δ13C、δ15N数据分析,可以揭示更多的食谱信息。宝鸡建河秦墓素食中有一定量的C3成分,推测不应是采集所得,而是小麦的体现,肉食则由于自然或社会条件的限制,C3类型的野生动物可以忽略不计,几乎全部属于C4家畜[213]。
出土金属器物分析方面,研究者对新丰秦墓青铜文物通过光学显微镜、电子显微镜/能谱分析、X-射线衍射分析和拉曼光谱等方法,研究了青铜器残片的锈蚀特征,为了解北方地区青铜器腐蚀情况提供了参考[214]。新丰秦墓青铜器科学分析表明,新丰铜器的成形工艺包括铸造和锻造两种,以铸造为主;铸造铜器的材质以高合金量的铜锡三元合金为主,而锻造铜器则为低铅青铜;铜垫片为热锻而成,材质为铜锡二元合金或低合金量的铜锡铅三元合金,明显不同于器物基体。研究结果为全面揭示战国晚期秦国乃至秦代的青铜器制作技术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资料[215]。刘亚雄等人对新丰秦墓的23面铜镜进行了金相组织观察和扫描电子显微镜能谱成分分析。结果表明,这批铜镜均为铸造而成,未普遍经淬火、回火等热处理,与同时期其他地区的铜镜相比,铅锡含量较高且成分波动较小,表明这一时期关中地区铜镜制作技术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秦镜中较高的锡含量导致其脆性增加,可能是出土秦镜多已破碎的原因之一[216]。
(二)中小型汉墓考古与研究
1.关中地区中小型汉墓的发掘及研究
2009~2018年,关中地区中小型汉墓发掘与研究取得长足进展,《周原汉唐墓》[217]《西安东汉墓》[218]《西安北郊郑王村西汉墓》[219]及其为数不少的发掘简报,结合前几年出版的《西安龙首原汉墓·甲编》《白鹿原汉墓》《长安汉墓》《宝鸡建和墓地》等报告,全面展示了陕西及其关中地区中小型汉墓的面貌,完成、完善了关中地地区中小型汉墓的发展序列。10年来西安地区新发现的西汉列侯级的墓葬有3座,其余绝大部分墓主为汉长安城的一般居民,有一处为杜陵邑的,有一处为上林苑的,但是出土器物有九鼎,也有石椁发现。富平侯张安世家族墓地的发掘获得了2013年十大考古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以及媒体的追踪报道,形成了墓地布局、构成要素、出土器物、张安世个人作为、家族谱系等研究热点。
《周原汉唐墓》介绍了2005年在宝鸡扶风、岐山县发掘的纸白墓地、七里桥墓地及历年在周原遗址范围内抢救性清理的秦汉、隋唐时期的墓葬资料,探讨了秦汉墓葬年代及分期,对家族墓地的分布排列有独到的研究[220]。《西安东汉墓》对西安地区近100座东汉墓葬材料结集出版,并且将出土的釉陶、铁器及粮食等进行现代科技分析[221]。《西安北郊郑王村西汉墓》以墓葬为单位介绍了80座中小型西汉墓葬资料,对墓葬形制、出土陶器、铜钱等作了比较系统的类型学研究[222]。
富平侯张安世家族墓地位于西安南郊凤栖原。墓园平面近方形,东西长约195、南北宽约159米,由甲字形大型墓M8及其从葬坑、高规格祠堂建筑基址以及兆沟等构成。墓园周围祔葬十数座中小型墓,与墓园一起构成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墓园四围有兆沟。M8位于墓园的中心,长65、宽24.5、深15米,北向斜坡墓道。墓内前后分置砖椁、木椁两重结构的椁室和3个土圹木椁结构的耳室,推测墓主为汉宣帝时大司马卫将军、富平侯张安世。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铜钱,该墓地从西汉中期一直延续到王莽时期,出土重要文物1800多件,其中700多件彩绘陶甲士俑和多件鎏金银、错金银青铜器,学术意义重大[223](图一九)。
石家街汉墓也是一座列侯级墓葬。2012年在西安市新城区石家街发掘,墓葬形制为斜坡墓道土圹砖、木椁墓,坐北向南,平面呈“甲”字形,由封土、墓道、墓室及陪葬坑组成。现存封土近椭圆形,底径约45、顶部宽约28、高约7.5米。墓室为竖穴土圹砖、木椁结构,墓圹东西长30.4、南北宽24米。墓圹东、西、北三面各有四层台阶,每层平台之间以“之”字状的阶梯相连。平面呈东西横长方形, 东西长19.3、南北宽约15.2、砖椁高约6.3米。发现有墓上建筑,及3座陪葬坑,随葬品等级较高,尤其是陪葬坑K3内出土的数量众多的裸体着衣式陶俑,在质地、大小及形制均与汉阳陵陪葬坑出土的裸体男、女陶俑极为相似。推测时代应在西汉中晚期,墓主为列侯级别[224]。
支家沟墓地位于蓝田县华胥镇,为长斜坡墓道的竖穴土圹墓,总长53米,地表存留有高达10米的封土,并发现有墓园墙垣遗迹。前室的车马坑随葬有真马一具和大量的车马器,墓道和前室的12个放置随葬品的壁龛,构成了具有特色的外藏椁系统,随葬品中有“太官”“内者令印”“元年右工”等官职与纪年文字(图二〇),结合2件宦者俑的出土,推测墓主与西汉皇室有着密切的关系,墓主身份应不低于列侯。通过对支家沟汉墓所处的地理位置、墓葬形制、随葬品及其出土文字材料的分析,并对《汉书》中葬地与蓝田密切相关的文献梳理后认为墓主与昭帝时期的鄂邑长公主吻合[225]。

图一九 富平侯张安世家族墓地墓园平面图
西安地区西汉墓发表的简报资料还有:辛家庙井上村发掘了13座汉墓,形制多竖穴墓道单砖室墓,出土有陶器、玉器、铁器、铜镜、铜钱等。从铜钱“货泉”“货布”等,时代为西汉晚期[226]。张家堡东发掘了一座新莽时期墓葬,出土器物丰富。形制为长斜坡墓道竖穴土圹砖室墓,由墓道、南北耳室、甬道、墓室等部分组成,出土器物204件(组),铜鼎和大釉陶鼎以及九鼎组合属首次发现,对新莽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227]。张家堡广场西南发掘墓葬33座,形制可分为土坑墓、土洞墓和砖室墓三类,以土洞墓和砖室墓为主,出土随葬器物100余件,时代分为两期,第一期不晚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第二期约为西汉晚期和新莽时。推测墓主为长安城内的普通平民[228]。大白杨村附近发掘清理了汉代墓葬14座,形制为竖穴土坑墓,个别为竖井式墓道土洞墓、竖井式墓道砖室墓和斜坡式墓道土圹墓。出土的随葬品有陶器、铁器、铜器和五铢钱等,年代推测多在西汉中晚期,墓主为长安城的平民[229]。凤城三路百花家园小区发现一座大型汉砖室石椁积沙墓,规模宏大,尤其是发掘出土的石椁为西安地区汉代墓葬中所罕见。西安地区的西汉石椁墓,目前已公布的仅有两座,而百花村M6的砖石混合结构,前室砖室,后室内为石椁,外为砖室,对长安地区汉代墓葬形制、丧葬制度及汉代石作手工业发展状况的了解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230]。未央印象城清理9座小型汉墓,形制有竖穴墓道砖室墓和竖穴土洞墓两种,出土了较为丰富的陶、铜及玉器,时代为西汉早中期到新莽时期。墓葬位于西汉长安城东,推测为汉长安城居民的葬地[231]。太华路万达广场发掘多座汉墓,形制多为竖穴土圹砖椁墓,大部分带有小龛,个别土圹内积沙。M5规模较大,形制为斜坡墓道砖室墓,出土31件器物,尤其是其耳室出土的11件硬釉陶器十分珍贵;M16、M18各出土一套石磐,M24出土10件釉陶壶及1套铁铠甲。年代为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墓主当为汉长安城内的居民[232]。张家堡村旺景国际大厦清理西汉墓葬42座,形制以竖穴墓道土洞墓为主,个别为竖穴土圹墓;葬式多为仰身直肢单人葬,大部分墓葬有棺椁痕迹。该墓地墓葬规模较小,排列密集,方向以西向和北向为主,时代自西汉早期至中晚期,应为一处汉长安城内居民墓地。出土的彩绘铜镜直径超过27厘米,为研究西汉彩绘铜镜提供了新材料[233]。在西安市长安区西甘河村、张王村及南堰头发掘的14座西汉墓,形制分别为竖穴土坑墓、竖穴土洞墓、斜坡墓道洞室墓,出土器物210件。推测墓主人可能是生活在上林苑的居民[234]。西安南郊羊头镇发掘了35座汉墓, M3、M20、M68墓葬规模较大,形制分别为长斜坡墓道土圹木椁墓、土圹砖室墓,共出土器物302件。墓地东南距杜陵3公里,推测墓主人可能是杜城或杜陵邑内的高级贵族或官吏[235]。

图二〇 支家沟墓地出土“内者令印”封泥
西安地区东汉墓葬也有一些发现。西安南郊潘家庄,第169号东汉墓保存较好,出土器物丰富。形制为长斜坡墓道穹隆顶砖砌多室墓,共出土器物60件,其中“黄神之印”陶印、陶牛车,较为少见[236]。雁塔区西京社区清理2座东汉墓,均为斜坡墓道砖室墓,出土有盘口罐、陶仓、铜盆、铜襟钩、铜钱。出土的铜器制作较为精湛,陶仓及铜镜纹饰时代性明显[237]。陕西师范大学雁塔校区二期清理2座东汉墓,均为长斜坡墓道砖室墓,共出土器物108件。两座墓葬南北并列,方向一致,距离较近,年代相当,推测应为家族墓[238]。大明宫汽配城滹沱村安置楼工程中清理7座东汉至北朝时期的古墓葬,出土了一批重要文物,尤其是M3出土的4块镇墓石非常少见[239]。西安市北郊北辰大道西侧西距汉长安城约7000米,清理墓葬8座,均为斜坡墓道洞室墓。墓室有单室、双室、三室和四室等,共出土器物120件,铜钱50余枚。8座墓葬的年代可分为两个时期,7座为东汉中至晚期,1座为北朝时期。7座东汉墓,方向一致,排列有序,东西三排,为一处经过严格规划的家族墓地[240]。
咸阳地区:咸阳市渭城区民生工程项目清理围沟1条、汉墓8座、唐墓1座,其中4座汉墓位于围沟内,出土器物100余件。时代集中在王莽时期和东汉中期两段,两座带有纪年材料的墓葬,有助于推进东汉墓葬分期与年代的进一步细化[241]。恒兴公司清理了一批古代墓葬,其中两座规模较大,M6为长斜坡墓道土坑墓,且墓内积沙积灰;M12竖穴墓道空心砖墓,从墓葬形制看咸阳地区空心砖墓主要流行于西汉晚期,为研究汉代墓葬形制补充了新的资料[242]。
宝鸡地区:路家村墓地发掘8座墓葬,其中1座为汉墓,属中小型墓葬,墓葬形制较完整,随葬器物特征明显[243]。西白村墓地发掘清理墓葬9座,其中汉墓4座。出土器物有陶器、铜器、铁器等。M2出土的多枝灯,器表彩绘云气、龙纹来表现,在汉墓中发现较少[244]。纸白墓地共清理墓葬25座,包括西汉墓18座、东汉墓6座。18座西汉墓均为竖穴土洞墓,随葬器物有陶器、铜器、铁器、玉石器等多种,随葬的彩绘人俑以及彩绘马、牛等动物俑较多[245]。凉泉汉墓发掘墓葬8座,时代为西汉中期偏晚至晚期早段。墓葬成组分布,部分墓葬为共用墓道的连体结构,均为长斜坡式墓道和土洞墓室结构,随葬品114件。部分墓葬连体共用墓道的情形、以及发掘出土的秦式玉人等,反映出墓主人生前的社会组织与家族关系[246]。
渭南地区:蒲城县永丰镇发现4座战国秦汉时期的家族墓葬。其中3座的时代为秦代或汉初,皆为中小型竖穴墓道土洞墓。该墓地的发掘为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的历史考古以及丧葬礼俗等提供了宝贵资料[247]。
墓葬研究以《西安龙首原汉墓》《长安汉墓》《白鹿原汉墓》等考古报告及已发表的相关资料为依据,西安地区西汉中小型墓葬进行了墓葬形制、出土器物的类型学研究,墓葬的分期与年代问题也进行了梳理[248]。在西汉中期之前西安地区汉墓主要表现出对“周”“秦”“楚”等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对“周”文化的继承是框架性的、间接性的,主要体现在礼制方面,如棺椁、礼器、乐器、车马等,对“秦”“楚”文化的继承则是直接的、具体的,如墓型、器类、器形、装饰等方面。西汉中期以后,逐渐形成了独具特征的汉代葬制,如砖室墓、釉陶器、礼制方面衰弱、生活明器盛行等[249]。
2.陕北汉代墓葬、城址,陕南崖墓的发现与研究
陕北榆林地区是全国著名的画像石产区之一,不仅数量众多,内涵丰富,而且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米脂官庄画像石墓》介绍了米脂官庄发掘的3座汉代画像石墓的考古资料,并收入榆林地区历年来出土和征集的汉墓画像石,是研究汉代画像石乃至汉代历史、汉代艺术的重要参考资料[250]。在神木大保当镇发掘了3座汉墓,其中2座墓出土了画像石。画像石均为浅浮雕,局部涂有黑色和红色,内容主要有车马出行、神仙羽人、祥禽瑞兽等。这3座墓的时代应为东汉早中期[251]。绥德县四十里铺镇后街村发现一处汉代墓葬,墓内发现了3块石板,经初步认定,这3块石板应该为东汉时期画像石,对研究汉代的建筑、雕刻、绘画具有重要价值[252]。画像石墓葬的相关研究多关注于画像石图像,集中于画像石的题材、风格、来源等内容的研究。
老坟梁墓地是陕北地区一处规模较大的汉代墓葬区,也是目前陕北地区发掘数量最多,随葬品最丰富的一批汉代墓葬。《陕西靖边老坟梁汉墓发掘简报》介绍了7座墓葬材料,其中4座砖室墓和3座土洞墓,墓室结构均较简单,随葬器物以彩绘陶最具特色。老坟梁墓地为研究汉代北方边疆地区的墓葬分期和文化面貌提供实物资料[253]。作者将其与同时期长安地区的中小型汉墓进行比较,指出老坟梁汉墓表现出明显的地方特征,与当时的区域历史背景相符,反映出汉、匈两种文化势力在这一地区的此消彼长[254]。并且对老坟梁墓地出土粮食做了鉴定与分析,为当地饮食结构提供了证据[255]。
瓦渣梁城址位于靖边县杨桥畔,遗址内出土戳印“阳周塞司马”陶器、“阳周宫”瓦当,并发现铸币遗址。与阳周故城相关联的“奢延水、走马水、帝原水、黑水”等诸古水系、地理名,与郦道元《水经注》所记录描述的“阳周故城”地理位置和水系之名称及流向高度吻合,证明此地为先秦时的政治、军事重地。专家普遍认为瓦渣梁所发现的古城遗址与史料所记载秦汉时期的阳周故城基本吻合[256]。
陕南崖墓是陕南地区汉代墓葬的主要形式。南郑县苏家山村发现了3座东汉墓[257]。商洛崖墓是近年陕南地区考古的重要发现,经过针对性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在商洛丹江、乾佑河等流域发现了3000多座崖墓,推测为东汉时期流行于我国西南地区的一种特殊墓葬,以石室、石穴的形式修建于河流两岸的陡坡峭壁上[258]。
3.汉代壁画墓的发现与研究
目前陕西地区的汉代壁画墓主要发现在西安与陕北榆林地区。在曲江新区翠竹园小区发掘西汉时期墓葬4座,其中一号墓规模较大,为斜坡墓道砖室墓,由墓道、甬道、耳室、墓室组成。墓室内有彩绘壁画,内容丰富,色彩艳丽。根据墓葬的形制和出土器物,此墓的年代应在西汉晚期。壁画遍及墓壁以及券顶,内容为生活场景与天象图[259]。在靖边县杨桥畔渠树壕发掘一座汉代壁画墓,形制为长斜坡墓道、砖券拱顶前后室结构,壁画总面积约20余平方米,内容有星象图、持铩门吏、车马出行、侍女、宴乐等,星象图是中国考古首次发现的四宫二十八星宿,具有星形、星数、图像、题名四要素的天文星象图。为准确地认识二十八宿及中外星官提供了科学依据,壁画星象图表示了三垣、中外星官以及黄道和日月相对位置,也为汉代建筑、服饰、兵器以及风俗、神话、宗教、美术绘画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经对星象图和壁画车马出行图的初步研究,时代为东汉中晚期[260](图二一)。

图二一 靖边杨桥畔渠树壕壁画墓星象图
关于壁画墓研究,杨泓提出西安新发现的两座汉墓壁画绘制技法有明显的差异,理工大墓壁画受楚风影响明显[261]。贺西林梳理20世纪以来汉墓壁画发现与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运用分期、分区的方法对汉墓壁画的演变过程进行了探索,同时对部分图像重新进行了考辨[262]。黄佩贤以墓室壁画作为随葬品在汉代丧葬文化中角色的视角,对汉代壁画墓的源头地区以及汉代墓葬画像的历史作用等进行探讨,提出壁画墓是汉墓的一种形式,出土壁画墓的区域,必定也同时出土有不带壁画的汉墓,两者的整体发展情况应该是同步的[263]。程林泉、张翔宇对关中地区汉代墓葬壁画的题材、布局、分期及区域特征等问题进行总结,分析技法的差异[264]。后晓荣、陈晓飞就关中地区目前所发现两汉壁画墓的考古发掘资料,结合史实,概括关中地区的两汉壁画墓的性质特点、历史地位等[265]。还有学者对单幅壁画[266]、壁画的色彩[267]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四、离宫别馆、交通道路与水利工程考古研究
(一)关中地区离宫别馆调查
陕西关中是秦汉王朝统治的核心地区,营建了大量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离宫别馆是古代帝王出巡时居住的宫室,秦汉时期关中离宫四百余,由此可见其规模,这也成为考古学研究宫室及其相关建筑的重要对象。关于“行宫”和“离宫”称谓的区别,祈远虎从它们兴建的目的、用途、规模、分布特点,以及对两词渊源的探究与学界对这方面已有的成果分析,认为离宫和行宫是有差异的,可以对两者进行区分,认为离宫多拥有地理优势和资源优势,被帝王用来避暑或者避寒,并且长期驻居;而行宫是在一些重要的道路上设置,供皇帝往返经过时进行临时地驻跸和休息[268]。
对关中地区秦汉时期离宫别馆进行全面考古调查,旨在摸清那些久已消失的秦汉离宫别馆遗址的数量和分布,确定具体遗址的年代、规模、结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秦汉宫室苑囿建筑艺术以及相关礼制思想。近十年来关于关中离宫别馆的考古工作,如“陕西关中地区秦汉离宫别馆调查研究”项目,对千河下游地区进行了全覆盖式调查,发现东周、秦汉时期遗址40余处。这些遗址的遗物以砖瓦等建筑材料为主,且多发现有夯土基址,说明千河下游在东周至秦汉时期集中分布着性质单一且文化内涵有明显特征的一些遗址,这些遗址很可能是当时离宫别馆一类的建筑遗迹[269]。千阳县冯家堡村尚家岭发现的两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是一处始建于战国晚期的离宫别馆遗址,沿用至西汉中期。遗址出土了大量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瓦当、板瓦、筒瓦、空心砖等建筑材料,为研究战国秦汉时期建筑提供了新资料。该遗址位于古汧水道,应是位于关陇交通要道的一处兼具驿站或军事功能的建筑。该遗址的发现,使我们对秦汉离宫别馆的布局与功用又有了新的认识[270](图二二)。
王子今新著《秦汉交通考古》中对直道、驰道、阁道、栈道、复道、甬道等的考释和实地勘察,详细介绍了道路建筑,为秦汉帝国发展史和交通道路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借鉴[271]。

图二二 千阳尚家岭Ⅰ区夯土建筑基址北侧结构
(二)甘泉宫遗址考古与研究
甘泉宫遗址,地处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北部,泾水之阳,南接北仲、嵯峨二山,北枕子午岭余脉甘泉山。现存遗迹有西城城墙、门址以及东城大型建筑夯土台基等。据2014年调查遗址总面积超过1000万平米。发现甘泉宫遗址可分为西城、东城两部分,西城北、西、南三面城墙保存较为完整;东城城墙被确定为几处建筑遗址。厘清了遗址的整体范围,发现围绕一号、二号墩台(通天台)分布有5处大型建筑遗址。通过重点勘探首次明确了二号墩台(通天台)为东西向长方形、高12米的三层夯土台基结构,顶部台基中央有最长11.5、最短8、深约2米的椭圆形红烧硬结块范围。三层台基上共发现柱础石18处,东侧、北侧发现曲尺形的石砌基址。顶部、周围发现红烧土深厚,推测二号墩台毁于大火[272]。考古工作又进一步验证了西城西墙年代及门址结构。虽然发掘时在晚期地层及灰坑中发现少量秦汉时期云纹及仅存“长”字的瓦当残片和货泉、布泉等铜钱,在考古调查时也发现完整云纹瓦当及半两铜钱。但是解剖城墙后发现叠压于城墙下时代偏晚的粗绳纹陶片,西城的年代可能是南北朝时期,与汉甘泉宫遗址无关。
对甘泉宫遗址的研究中,姚生民提出益延寿宫是汉武帝为求仙于甘泉宫所建的宫观,益延寿宫应在甘泉宫遗址内。云阳宫即秦之林光宫,汉之甘泉宫,在云阳县西北,在甘泉山下[273]。梁云对甘泉宫上世纪70年代的调查结论提出质疑,认为遗址应由东、西两城构成,二者之间有驰道、直道南北贯通。东城为汉甘泉宫,西城有林光宫、云阳县城、驻军阅兵场所三种可能。甘泉苑的范围东至铜川,西至彬县,甘泉宫是甘泉苑的中心,甘泉苑内外的离宫别馆及建筑遗址分布颇有规律,并揭示了甘泉宫与京师长安之间两条重要的交通路线[274]。郭霖锋探讨了甘泉宫位置地望,秦甘泉宫、林光宫、汉甘泉宫的变化过程。认为汉武帝两次扩建甘泉宫,使其成为仅次于长安未央宫的重要活动场所[275]。周晓陆等对名品“宫”字瓦、甘泉宫三字瓦进行释读,认为是西汉武帝前后的重要文物[276]。

图二三 秦直道-南桂花探沟的道路四叠层
(三)秦直道考古发现与研究
秦直道考古调查、发掘在2009~2018年取得了重大成绩,不仅收获了2009年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也在道路本身的建筑方法、方式,道路主体线路走向、沿线建筑遗址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对陕西富县桦沟口秦直道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路面、车辙、路面脚印、建筑遗迹、靠河护坡、“之”字形盘山道、人为破坏现象等,遗物有钱币、铜镞、筒瓦、板瓦、陶器。发掘者认为桦沟口段直道及其附属建筑,始建于秦代,沿用至两汉之间,或稍晚废弃。下层路面的时代约为秦代和西汉早期,上层路面约为西汉中晚期[277](图二三)。富县、甘泉县秦直道调查路线约150公里,调查覆盖范围为道路两侧各一公里,发现秦汉建筑遗址6处。在以前实际踏查的基础上,对直道主体线路勘探验证,首次获得详细的直道走向图(图二四、二五)。在多处建筑遗址采集到大量的外饰粗、细绳纹内饰布纹或大麻点纹的筒瓦、板瓦残片,在安三遗址采集到羊角云纹瓦当[278]。在甘泉县桥镇乡安家沟村发现了一处秦汉建筑遗址,位于洛河南岸的台地上,南临洛河,与北岸当地人称“圣马桥”的秦直道引桥遗址隔河相望。遗址东西长约150、南北宽约80米,总面积约12000平方米左右[279]。
秦直道研究中,张在明提出秦直道地层的四叠层说,指出修筑于秦代的直道,自起点向北,经兴隆关向东,直至终点。使用200多年后,即在两汉之间或东汉早期,兴隆关以东的秦直道经人为破坏后废弃。后改走兴隆关以北的子午岭主脉,向西转了一个大弯后至终点,直至宋明时期[280]。王子今认为安塞、庆阳、鄜州、合水等方志资料所见“圣人道”、“圣人条”为秦始皇时代开筑的说法,是有一定可信度的。所见“迄今坦然周行”等说法,也值得研究者重视[281]。高子期、周晓陆认为秦直道作为军事运输工程,主体是道路,其沿线还有关隘、桥梁、阙台、烽燧、城镇、驿站等各类建筑。这些共同架构成直道的立体军事防御网和军需供给网,成为当时南北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融汇的桥梁和纽带。对直道沿线建筑的研究,有助于揭示其战略地位,也成为确定其走向的有利证据[282]。姚生民认为呼韩邪、王昭君当由秦直道出塞无疑[283]。曾磊认为秦直道可能不是秦王朝全新开辟,而是通过对前人道路的拓宽和改造而成[284]。尹亚萍对秦直道是否经过上郡进行了详细地论述。明确了秦直道的走向,对研究直道所经郡县及直道的历史文化价值意义重大[285]。喻鹏涛认为秦直道作用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原王朝与匈奴交恶时期军事作用占主导,和平交往时期和平功能占主导地位[286]。

图二四 富县秦直道远景

图二五 富县秦直道近景
(四)秦蜀古道考察研究
秦蜀古道是经关中通往巴蜀,穿越秦巴山地,由多条主道路组成的一系列道路的统称。被称为“秦蜀古道”,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从长安出发,分别从长安子午古道、周至傥骆古道、眉县的褒斜道、宝鸡陈仓道出发,到达汉中,再由汉中到达成都。近年来,经过调查,陕西省境内共发现313处道路文物本体遗存,主要由栈道、栈桥和碥道三部分构成,还包括驿站、关隘、寨堡、城址、隧道等。
这些文物全部是实地踏查的成果,范围广,数量大,具备一定的规模,遗存的保护环境真实,说明秦蜀古道不仅仅只是存在于文献中和地图上,作为秦蜀古道线路的主省份,陕西是秦蜀古道文物遗存的最主要地区。秦蜀古道在历史上先后被称为“周道”“秦道”“蜀道”。这条古代大道,由7条主道路组成,包括由陕西关中通往汉中的“故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4条道路,以及由汉中通往终点站四川盆地的“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3条道路,它们或以途经水和山谷命名,或依道路走向方位命名,或依据历史故事命名[287]。
在对秦蜀古道调查中,首次系统绘制完整秦蜀古道线路图。围绕秦蜀古道的“申遗”建立联合机制。 陕西、四川、甘肃三省开展协作,相互配合,加快秦蜀古道的调查研究工作[288]。
(五)其它交通道路考察成果
陕西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西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通了中国与亚欧大陆间的贸易通道,并使之成为当时东西联通的“国道”。以此为契机,运用考古学方法,通过整合考古资料,对秦汉交通道路进行线性考察研究,探讨丝绸之路之文脉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和发展进步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从长安方向出使分别向北、西北和西的三个方向的道路为主干道,即陕西境内丝绸之路的北(沿秦直道方向)、中(沿泾水方向)和南线,其中南线也被称为溯汧渭古道。
溯渭河从长安出发经“汧渭之会”处到达陇山段是陕西境内丝绸之路南线主干道路,早在东周时期,秦国翻越陇山向关中迁徙时该线路走向已基本确立,西汉以来,随着皇帝巡幸和郊祀活动的频繁,对道路的修筑规格和线路拓展进一步上升。2008年以来,在中国城科会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丝绸之路文化研究中心的支持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溯渭河长安至陇山段路线进行了考察研究工作,得出了重要认识,即区间干通道、秦汉道路的沿用与拓展、水路与陆路的相辅相成、道路与离宫别馆的关系,以及“大震关”的具体地望等[289]。
(六)水利工程考古
郑国渠考古调查取得新收获。郑国渠是秦王在公元前230年采纳韩国水利专家郑国的建议开凿的,系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条灌溉渠道。修筑郑国渠的初衷原为韩国疲秦之计,后来却变成了强秦之策。自秦国开凿以来,历经各个王朝的建设,先后有白渠、郑白渠、丰利渠、王御使渠、广惠渠、泾惠渠的贯通,至今造益当地。近年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分别围绕郑国渠渠首遗址、走向、相关设施进行考古调查;社科院考古所秦栎阳考古队还对白渠进行了解剖性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在相关发表的认识中,有李岗对泾阳明代洪堰制度碑的分析[290]、张维慎对秦汉时期水利工程的综述[291]、王子今等对郑国渠命名提出了新的认识[292]、以及关于郑国渠与白渠渠线分析[293]。
昆明池是汉武帝在元狩三年和元鼎元年于上林苑中先后两次兴建而成的大型湖泊,它除在当时训练水军外,还实际性的成为了汉长安城的调蓄水库,较稳定的解决了都城长安的蓄水供水,并兼有了防洪排涝等作用。2012~2016年,采取大范围调查、全区域勘探、全探孔记录、小规模试掘相结合的考古方法,逐步确定了昆明池池岸的位置与池深、昆明池进水渠与出水渠道等重要发现[294]。
五、手工业作坊遗址
(一)眉县尧上遗址考古
尧上遗址位于陕西省眉县常兴镇东北,北依台塬,南临渭水。2010~2011年,对该遗址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揭露面积约650平方米,发现灰坑10座、窑址2座,出土物包含有砖瓦等建筑材料以及少量陶器残片等。建筑材料以板瓦为主,筒瓦较少,出土器物以及建筑材料年代以西汉时期为主。初步认为这里是秦汉时期陶器作坊区遗址。
尧上遗址出土陶器种类繁多,以罐、盆、甑、釜、椭圆形槽等器物居多。遗址同时出土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板瓦、筒瓦以及回纹铺地砖及空心砖等建筑材料,极具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发掘中还发现了一些带有陶文的陶器残片,有“南舍”“斄亭”“日利”以及“霸陵过氏□”等陶文。此次发掘还有数百面瓦当出土,以云纹瓦当居多。还出土有“长乐未央”“千秋万岁”及“利”等文字瓦当。建筑材料的集中出土及陶文暗示着当年此处可能有大型建筑遗址。
历年考古调查及发掘证明,以尧上遗址为中心,周边直径约3~4公里方圆分布着大量的秦汉时期墓葬,其中心区域基本不见墓葬。这一现象表明,以尧上遗址为中心的区域当为秦汉时期眉县县治所在,其周边发现的秦汉墓葬当为秦汉眉县城内居民的墓葬区。从地形地貌看,这一区域具备承载一个汉代县城的地理优势。丰富的建筑材料及成片夯土遗迹也为上述推断提供了实物证据。另外,发现的秦汉聚落遗址出土了一批秦汉时期遗迹及遗物,对研究秦汉时期的中小型聚落的特征、辨析汉代普通人群的物质遗存、了解秦汉时期普通人群使用的日常生活器物的特征及建筑材料特点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根据尧上遗址出土陶器及建筑材料的特征初步判断,“郿县故城在今县东北15里。”唐代以后的郿县县治在渭河以南,斜水之东,与今日眉县县城基本为同一地点。据此推断,位于其东北15里的两汉眉县县治就更应该偏东,恰合于现在考古发掘所在区域[295]。
(二)杨凌邰城遗址
秦汉时期邰城遗址位于杨凌揉谷乡法禧村周围。在以往考古调查与发掘中发现有大量秦汉粗绳纹砖瓦、云纹瓦当、五角水管、铸铁作坊和墓葬,还出土了刻有“邰”字铭文的秦代铜鼎和铜温壶等。这与史书记载的“邰城”相吻合。
2010年,为配合杨凌“古邰国遗址公园”的建设规划,在梳理以往考古工作背景的基础上,采取“聚落结构调查法”,两度对邰城及其周邻10余处遗址进行了详细的考古调查。累计调查面积达30余平方公里,GPS测点定位,采集遗迹500余个,种类有墓葬、陶窑、夯土、灰坑等,获得了大量各时期的陶器标本,内涵主要为史前、商周、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遗存。其中,战国秦汉时期遗存最为重要,墓葬数量多,尤其是砖、瓦、排水管等遗物的发现,说明建筑规格较高,且具有一定规模。
初步构建了“邰城遗址群田野考古调查GIS”系统,为动态分析区域聚落兴衰演变,结构布局等提供了技术支撑。确认了战国秦汉邰城的位置和范围,厘清了布局结构的线索。以法禧为中心,包括周邻的疙瘩庙、尚德、殿背湾、杜家坡等遗址,战国秦汉时期为同一聚落,其规模与结构与县治相符。以往曾在此范围发现有城墙、铸铁作坊及大型建筑等遗存,或为县治所在。为进一步了解冶铁作坊的特征与性质,随后根据钻探结果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发现了陶范与芯,铸器类别可辨者达数百件,同时发现了炉壁与鼓风管残块,炼渣、炉渣、残铁块与木炭块等。根据共存陶器与“半两钱”范的特征判断,该作坊的使用年代应在西汉前期。从出土的炼渣外部特征观察,与熔炼渣较为接近,而有别于冶炼渣;鼓风管的管径,也明显比冶炼炉鼓风管要细。凡此表明,该作坊很可能是以熔炼技术为主的铸铁作坊。就产品构成而言,其主要是以生产农具为主,或可能兼铸铜钱。就所出残铁块与炼渣特征判断,其技术体系很可能铸造与锻造兼而有之。炼渣包含有木炭屑,表明作坊是以木材或木炭为燃料进行生产的。这是迄今陕西唯一正式发掘的同类作坊,为今后探讨西汉都城附近铁器工业形态提供了新的素材[296](图二六~二八)。

图二六 杨凌邰城遗址出土范与芯

图二七 杨凌邰城遗址出土半两钱石范

图二八 杨凌邰城遗址出土鼓风管
六、祭祀遗址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古代通过祭天活动以达到“与天滋润,强国富民”之祈福。雍地具有悠久的祭祀传统,而秦汉时期在雍城郊外创制的畤祭则对中国古代祭祀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凤翔雍山血池遗址是目前我国秦汉时期“祭天”遗址中,与文献记载完全对应,由选址与地貌关系、坛场、祭祀坑、建筑、道路等内涵构成的完整的“畤”文化遗存。被评为“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遗址位于陕西凤翔县柳林镇血池村,东南距秦雍城遗址约15公里。整个遗址区背靠一道东西向大山,分布于东西排列、南北走向的三道峁梁的阳坡一面。
2016~2017年,发掘面积4000平方米,发掘祭祀夯土台、祭祀坑、建筑基址等各类遗迹250余处,出土玉器、青铜车马器等各类器物2600余件,同时也结束了数年来对这处总面积达470万平方米的大型遗址的考古调查工作,目前共确认相关遗迹包括各类建筑、场地、道路、祭祀坑等遗迹3200余处,取得了重要收获(图二九、三〇)

图二九 凤翔雍山血池遗址2016年发掘现场

图三〇 凤翔雍山血池遗址出土玉器组合
雍山血池遗址是关于“畤”遗存完整功能结构的首次发现,它以实际文化遗存印证了雍城这座从秦国迁都之后,历经秦代至西汉武帝时期,它仍继续作为秦皇汉武时期 “圣都”,以举行国家最高祭天礼仪活动之功能区的存在,填充了既往整个雍城遗址唯缺郊外以畤祭天遗存的空白,进一步明确了雍城遗址各功能区的空间分布与文化内涵。
据《史记·封禅书》记载,雍地的祭祀传统可以追溯到黄帝时期,一直到西周晚期在此还有郊祭活动举行。春秋战国时期,秦先后在雍地建立了包括鄜畤、密畤、吴阳上畤、吴阳下畤的雍四畤祭祀系统,使雍地不但成为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而且成为国家最高等级的祭祀“圣都”。汉承秦制,西汉早期汉高祖刘邦在继承秦人雍四畤基础上增设北畤,即形成完整的雍五畤祭祀五帝系统,以郊祀雍畤作为王朝最高祭礼。汉帝先后十八次郊雍,场面非常隆盛和壮观。据出土器物初步研究判断,血池遗址很可能即为西汉初期汉高祖刘邦在雍城郊外原隶属秦畤基础上设立的国家最高等级,专门用于祭祀天地及黑帝的固定场所——北畤。该遗址是继礼县鸾亭山“西畤”相关遗迹后,首次在雍城发现与古文献记载吻合、时代最早、规模最大、性质明确、持续时间最长,且功能结构趋于完整的国家大型祭祀遗址。
对血池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不仅是正史记载中关于在雍地开展的一系列国家祭祀行为之印证,而且成为从东周诸侯国到秦汉大一统国家祭祀活动的最重要物质载体和实物体现,从“透物见人”的角度,此次考古发掘出的实物资料,对于深化秦汉礼制、秦汉政治、中国古代礼制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于此同时,通过今后以雍山血池遗址考古成果为契机,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对于当代树立文化自信、增强对中华文明的自豪感与认同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297]。
近年来,与畤祭相关的研究论述如包括秦置畤制度、畤祭与秦“天下共生”理念、秦到汉畤祭形式的变化、畤与地名考,以及与秦汉畤祭制度变革有关联的泰山封禅等[298]。
七、问题与思考
回顾陕西秦汉考古走过的历程,从城址、陵园、中小型墓葬、离宫别馆、交通、长城、作坊,到祭祀遗址与出土文献的发现,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每一个时段的工作都留下了每一代考古人的足迹,他们为当代中国考古事业和历史研究筑起赫赫丰碑。我们一方面在不断总结和回顾以往工作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同时也感受到未来陕西秦汉考古的历史重任。
首先,与时俱进的考古学理论、方法及其应用是陕西乃至中国秦汉考古科学研究发展的基础。就我国考古学发展历史看,从最初以人文观察手段去探究方法已得到逐步的改变,在坚持运用“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将所有人类相关遗存置于一定的时空范围内,运用多角度、多层次、多学科、多领域协作的原则,去达到考古学研究的终极目标,即“透物见人”[299]。要步入这一境界,要做到三个结合,即考古学要和历史文献相结合,自觉形成“历史考古学”的有机“合作”,二者相辅相成,共同究明历史时代人类社会的历史[300];要与多学科相结合,如环境科学、社会学、民俗学、哲学等;要与自然科学技术方法相结合。“从历史和考古学的性质、任务及其特点出发,根据考古材料,运用考古学的理论以及相关学科方法和手段,对秦汉时期的社会历史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古学研究”[301]。
其次,从东周至西汉,陕西是秦国、秦帝国、西汉王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以文化遗存的实证资料来还原这一历史辉煌时期的面貌,是考古学的神圣职责。由于时代跨度大,属性流变、制度衍生,如何在“汉承秦制”的传承与发展模式下,探索秦汉历史文明,这是留给陕西秦汉考古工作的使命。我们的工作理念必须适应于这一要求,要将每一处遗存点连成一条线,形成一个面,建立一个“共时性”与“历时性”特定时空关系中,探寻秦汉社会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
再次,陕西秦汉考古工作在未来的重大命题中,新的考古材料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研究契机,如早期秦文化课题中关于嬴秦西迁路线及对应遗存等;秦“九都”之功能化与层次结构的认识也是在对相关遗址的考古工作中,以量化的标准和各自比照的方法来确定其都、城、邑的属性;秦汉聚落社会的研究等,今后通过全国性、跨区域的各方协作单位之间的精诚合作,持续不断努力来完成[302]。在获得相关资料过程中所采用的科学方法和手段是非常关键的。随着国家层面颁布新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构建考古管理体系,规范资料记录方式及记录内容,提升考古发掘质量,采取新的纪录方式,是主导考古工作逐渐向着规范化、标准化方向迈进重要力量,将对考古资料的管理、保存和系统广泛研究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不仅如此,在新时期秦汉考古工作中,在文献背景下,以人文学传统方法是基础,而对于多元化的新技术采用则是必然的选择。只有不断采纳新技术、新方法,未来的考古工作才能继续深入。在当前弘扬传统文化的背景下,陕西秦汉考古工作必须树立新形势下“保护、展示、研究三位一体”工作理念,这对于大多数考古项目来说,其前置条件也必须是配合保护和利用,因此考古工作的社会服务意识至关重要。
执 笔:李 岗 田亚岐 肖健一许卫红 杨武站 孙伟刚
统 稿:田亚岐 杨武站
[1]田亚岐.秦雍城遗址考古工作回顾与展望[C]//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
[2]田亚岐.秦都雍城布局研究[J].考古与文物,2013(5).
[3]杨永林,张哲浩.陕西秦雍城“微观”考古新发现“城堑河濒”实景[N].光明日报,2013-1-8(9).
[4]同[2].
[5]田亚岐.秦雍城沿革与历史地位研究[C]//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
[6]a.田亚岐,任周方.秦都雍城功能与格局的典型性特征[C]//嬴秦溯源—秦文化特展.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2016.b.田亚岐等.秦雍城城郭形态与演变的新观察[C]//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5.c.田亚岐,郁彩玲.秦都雍城城市体系演变的考古学观察[C]//辉煌雍城—全国(凤翔)秦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17.
[7]同[2].
[8]田亚岐,王炜林.秦都雍城聚落结构与沿革的考古学观察[C]//庆祝张忠培先生八十岁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9]刘瑞等.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考古取得重要收获[N].中国文物报,2018-2-23(8).
[10]刘瑞等.西安秦汉栎阳城考古新进展[N]. 中国文物报,2015-9-11(8).
[11]a.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都咸阳考古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b.焦南峰等.陕西秦汉考古五十年综述[J],考古与文物,2008(5).
[12]刘庆柱,陈国英.秦都咸阳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简报[J],文物,1976(11).
[1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渭城区秦遗址沟壕遗迹调查简报[J],待刊.
[14]许卫红,苏庆元.秦都咸阳城北区西界点的分析[J],北方文物,2016(1).
[15]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调查新收获[J],考古与文物,2014(2).
[1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6年考古年报.
[17]刘瑞.阿房宫:从考古学开展秦统一研究的核心遗存[N],光明日报,2017-7-17(14).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阿房宫考古发现与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等.西安市莲湖区三民村西汉大型建筑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2017(1).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汉长安城直城门遗址2008年发掘简报[J].考古,2009(5).
[21]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学年鉴(2014)[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22]刘振东.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长安城宫城2号建筑(宫门)遗址发掘[C]// 200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23]刘振东.汉长安城综论—纪念汉长安城考古工作六十年[J].考古,2017(1).
[24]刘振东.简论汉长安城之郊[J].考古与文物,2016(5).
[25]a.柴怡,等.西安东郊石家街发现汉代列侯级别墓葬[N],中国文物报,2013-8-16(8).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等.西安市大白杨村汉墓发掘简报[J].考古,2014(10). c.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西安富力赛高城市广场汉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7(3).
[26]a.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西安市汉长安城北渭桥遗址[J].考古,2014(7).b.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西安市汉长安城北渭桥遗址出土的古船[J].考古,2015(9).
[27]同[23].
[28]同[24].
[29]刘瑞.汉长安城的朝向、轴线与南郊礼制建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30]段清波.汉长安城轴线变化与南向理念的确立[J].中原文化研究,2017(2).
[31]许宏.大都无城—论中国古代都城的早期形态[J].文物,2013(10).
[32]徐龙国.中国古代都城门道研究[J].考古学报,2015(4).
[33]王子今.西汉长安的公共空间[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1).
[34]徐畅.西汉长安城未央宫北阙的地理位置及政治功用[J].四川文物,2012(4).
[35]张建峰.汉长安城地区水系设施和水利系统的考古学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36]潘明娟.古罗马与汉长安城给排水系统比较研究[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4).
[37]李勤.汉长安城水环境研究[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
[38]于志飞,王紫微.经纬圆方—汉长安城及其近畿空间尺度设计研究[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5(3).
[39]孙周勇.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提要集,2016.
[40]焦南峰,等.秦的十个陵区[J].文物,2014(6).
[41]卢连成,杨满仓.陕西宝鸡县太公庙村发现秦公钟、秦公镈[J].文物,1978(11).
[4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3年考古年报.
[43]张天恩,庞有华.秦都平阳的初步研究[C]//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5年).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5.
[44]田亚岐,刘爽.试论孙家南头秦墓相关问题[J].考古与文物,2014(4).
[45]田亚岐,刘明科.宝鸡太公庙与礼县大堡子山乐器坑比较研究[C]//陕西历史博物馆编.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24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7.
[46]a.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雍城一、六号秦公陵园第三次勘探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5(4).b.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雍城十四号秦公陵园钻探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5(4).c.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雍城六号秦公陵园兆沟西南侧中小型墓葬与车马坑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5(4).
[47]梁云,田亚岐.试论雍城秦公陵园墓主及其葬制[J].考古与文物,2015(4).
[4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周王陵”调查钻探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1(1).
[49]焦南峰等.秦的十个陵区[J].文物,2014(6).
[50]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5年考古年报.
[51]a.同[49]. b.刘卫鹏、岳起.咸阳塬上“秦陵”的发现和确认[J].文物,2008(4).
[52]a.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 [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b.徐卫民.秦都城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53]a.王学理.咸阳帝都记[M].西安: 三秦出版社,1990.b.丁岩.咸阳原两座秦陵园主人之揣测[J].考古与文物,2015(2).
[54]a.同[51]b.b.焦南峰等.咸阳周王陵为战国秦陵补证[J].考古与文物,2011(1).
[55]段清波,朱晨露.咸阳“周陵”属性研究[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
[56]同[51]b.
[57]同[65]b.
[58]同[49].
[59]王辉,等.八年相邦薛君、丞相殳漆豆考[J].考古与文物,2011(2).
[60]a.孙伟刚,等.新发现秦漆器及秦东陵相关问题探讨[C]//人类文化遗产保护(5).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b.梁云.战国王陵形制的东西差别[J].社会科学战线,2013(6).
[61]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东郊“韩森冢”考古调查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5(2).
[62]王学理.张冠李戴“韩森冢”实属西汉“恭皇陵”[C]//碑林集刊(十四).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
[63]辛玉璞.也谈韩森冢的冢主[J].文博,2002(3).
[64]耿庆刚.韩森冢为秦悼太子陵说[J].文博,2016(4).
[65]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09年度秦始皇帝陵园考古勘探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0(5).
[66]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兵马俑坑考古队. 一号兵马俑陪葬坑2009-2011年发掘简报[J],文物,2015(9).
[67]王树芝,等.秦兵马俑一号坑笼箙木炭分析的收获[N],中国文物报,2014-3-20.
[6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0年度秦始皇帝陵园礼制建筑遗址考古勘探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1(2).
[69]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秦始皇帝陵内城陵寝建筑勘探简报[C]//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2年).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
[70]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秦始皇帝陵园暴露遗迹调查报告、秦始皇帝陵园城垣遗迹调查勘探简报[C]//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1年).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
[71]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秦始皇帝陵陵区北部I区2010年度钻探简报、秦始皇陵园内城东西向墙垣城门勘探简报、秦始皇帝陵K201002陪葬坑勘探简报、秦始皇帝陵封土西侧三号陪葬坑勘探简报[C]//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2年).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
[72]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秦始皇帝陵陵区北部II区2010-2011年度勘探简报、2011-2012年度秦始皇帝陵K9901考古简报、秦始皇帝陵陵区K1201陪葬坑勘探简报、秦始皇帝陵园从葬墓园勘探简报[C]//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3年).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
[73]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秦始皇帝陵园西侧I区2011年度勘探简报[C]//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4年).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
[74]同[72].
[75]秦始皇帝陵博院.秦始皇帝陵园内城北部道路遗存勘探简报[C]//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4年).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
[76]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陵二号兵马俑坑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77]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9-2010)[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78]段清波.秦始皇帝陵园考古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79]张卫星.礼仪与秩序—秦始皇帝陵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80]阳陵考古队.汉阳陵帝陵陵园东门遗址2011~2012年考古工作收获[C]//汉阳陵与汉文化研究(第二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
[8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汉武帝茂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1(2).
[82] 201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8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汉元帝渭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J].考古,2013(11).
[8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汉哀帝义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2(5).
[85]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汉平帝康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J].文物,2014(6).
[86]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87]焦南峰,等.西汉帝陵园:新视野下的再发现[J].中国文化遗产,2013(2).
[8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汉阳陵帝陵陵园南门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1(5).
[89]阳陵考古队.汉阳陵帝陵陵园东门遗址2011~2012年考古工作收获[C]//汉阳陵与汉文化研究(第二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
[90]a.朱峰,杜忠潮.论西汉帝陵位次排列中的昭穆制度[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1).b.梁安和.简析西汉帝陵昭穆制度[C]//梁安和,徐卫民.秦汉研究(第十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
[91]a.杨哲峰.渭北西汉帝陵布局设计之观察[J].文物,2009(4).b.刘尊志.西汉帝陵分布及相关问题浅析[J].中原文物,2010(5).c.崔建华.论皇权传承规范对西汉帝陵布局的制约[J].考古与文物,2012(2).d.颜永杰,徐卫民.渭北西汉帝陵的营建与自然环境关系研究[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5).
[92]焦南峰,马永嬴.西汉帝陵选址研究[J].考古,2011(11).
[93]焦南峰.西汉帝陵形制要素的分析与推定[J].考古与文物,2013(5).
[94]焦南峰.秦、西汉帝王陵封土研究的新认识[J].文物,2012(12).
[95]焦南峰.西汉帝陵“夫人”葬制初探[J].考古,2014(1).
[96]a.焦南峰,等.神道、徼道、司马门道—西汉帝陵道路初探[J].文物,2008(12).b.焦南峰.宗庙道、游道、衣冠道—西汉帝陵道路再探[J].文物,2010(1).
[97]焦南峰.西汉帝陵的门阙与“门阙制度”[C]//徐苹芳先生纪念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98]段清波.外藏系统的兴衰与中央集权政体的确立[J].文物,2016(8).
[99]徐卫民.秦汉帝陵祭祀制度研究[C]//秦汉研究(第四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
[100]马永嬴.从“将作大匠”看西汉帝陵的变化[J].考古与文物,2009(4).
[101]刘尊志.两汉帝王陵墓反映的丧葬思想浅论[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
[102]刘尊志.试论西汉帝陵的寝与相关建筑[J].中原文物,2015(5).
[103]丁岩.先秦两汉帝陵墓向问题初探[J].华夏考古,2014(1).
[104]梁安和.浅谈西汉帝陵的修建过程[C]//秦汉研究(第九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
[105]梁安和.西汉帝陵陵庙与庙制研究[C]//秦汉研究(第十一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7.
[106]a.杨武站,王东.西汉陵邑营建相关问题研究[J].文博,2014(6).b.杨武站.论西汉陵邑的功能[J].考古与文物,2017(3).
[107]杨武站.西汉皇后葬地研究[J].文博,2016(3).
[108]高凤,徐卫民.秦汉帝陵制度研究综述(1949-2012)[C]//秦汉研究(第七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
[109]喻曦,李令福.西汉长陵邑的设置及其影响[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
[110]马永嬴.汉武帝茂陵陵园布局的几点认识[J].考古与文物,2011(2).
[111]马永嬴.汉武帝茂陵“次冢”名位辨[J].中原文物,2012(4).
[112]马永嬴.汉平帝康陵布局试析[J].文物,2014(6).
[113]杨武站,曹龙.汉霸陵帝陵的墓葬形制探讨[J].考古,2015(8).
[114]杨武站.关于汉阳陵帝陵陵园南门遗址的几点认识[J].考古与文物,2011(5).
[115]朱晨露.汉哀帝义陵“董贤墓”名位考释[J].考古与文物,2016(2).
[116]石宁.西汉五行思想与汉阳陵帝陵陵园设计[J].文博,2013(5).
[117]晏新志,等.汉景帝阳陵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文博,2009(1).
[118]a.闫华军.汉阳陵馆藏“熊相胜胡”铜印印文的姓名学探析[J].文博,2010(1).b.闫华军.汉阳陵馆藏“车骑将军”龟钮金印与西汉车骑将军[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3).c.杨武站.汉阳陵出土封泥考[J].考古与文物,2011(4).d.张琳.汉阳陵博物馆馆藏印章考释[J].文博,2014(6).e.杨武站.汉阳陵出土封泥研究[C]//西部考古(第8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f.曹发展,闫华军.汉阳陵博物馆馆藏“东织染官”铜印印文考述[J].文博,2016(5).
[119]程艳妮.汉阳陵馆藏西汉刑具概述[J].文博,2009(3).
[120] a.石宁.汉阳陵博物馆藏陶俑概述[J].文博,2009(2).b.李库.西汉景帝阳陵随葬陶俑研究[J].荣宝斋,2016(3).
[121]石宁.汉阳陵出土陶羊与西汉时期的羊[J].农业考古,2015(4).
[122]石宁,等.汉阳陵南区从葬坑出土武士俑和兵器浅析[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5).
[123]李曼丽.汉阳陵出土陶牛的葬仪内涵[J].考古与文物,2011(4).
[124]张琳,程艳妮.汉阳陵馆藏铜镜[J].收藏,2014(19).
[125]焦南峰,杨武站.宫廷生活的缩影,西汉帝陵中的陶俑[J].收藏,2010(6).
[126]刘云辉,等.汉杜陵陵区新出土的玉杯和玉舞人[J].文物,2012(12).
[127]杨晓燕,等.汉阳陵外藏坑农作物遗存分析西汉早期农业[J].科学通报,2009(13).
[128]胡松梅,杨武站.汉阳陵帝陵陵园外藏坑出土的动物骨骼及其意义[J].考古与文物,2010(5).
[129]王惠贞,等.汉阳陵出土陶质文物保护研究[J].文博,2009(6).
[130]张益,等.汉阳陵文物彩绘的结构观察及颜料成分分析[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3(3).
[131]a王保平.论北方黄土地区大遗址的保护与展示—以汉阳陵博物馆为例[J].四川文物,2010(5);b王保平.汉阳陵—北方黄土地区大遗址的保护与展示样本[J].中国文化遗产,2010(6).
[132]李库.汉阳陵帝陵外藏坑出土动物骨骸的保存与展示[C]//人类文化遗产保护.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133]a.李库.汉阳陵地下博物馆遗址区域环境状况调查[J].文博,2013(2).b.李库,等.汉阳陵外藏坑遗址环境监测系统布置方案[C]//西部考古(第8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c.姚雪,等.汉阳陵外藏坑遗址监测系统优化研究[C]//西部考古(第9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134]姚雪,等.汉阳陵帝陵外藏坑遗址温度变化规律及预报模型[J].敦煌研究,2014(6).
[135]a.王永进,等.汉阳陵地下博物馆遗址表面白色物质分析研究[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1(4).b王永进,等.汉阳陵地下博物馆遗址表面硫酸钙(CaSO4·2H2O)形成原因探析[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6(4)
[13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雍城六号秦公陵园兆沟西南侧中小型墓葬与车马坑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5(4).
[137]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凤翔翟家寺两座小型秦墓的清理[J].文博,2013(3).
[13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凤翔雷家台墓地发掘简报[J].文博,2013(5).
[139]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凤翔六道村战国秦墓发掘简报[J].文博,2013(2).
[140]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凤翔路家村墓葬发掘简报[J].文博,2013(4).
[141]王志友,董卫剑.陕西宝鸡市洪塬村一号春秋秦墓[J].考古,2008(4).
[142]周艳涛.秦都咸阳首次发现一处大型秦国贵族墓 地[OL].[2012-01-11]. http://news.hsw.cn/system/2012/01/11/051211763.shtml.
[143]a.刘卫鹏.关中监狱战国秦墓群的发掘[C]//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2年).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 b.刘卫鹏.关中监狱战国秦墓群发掘概况[C]//秦汉研究(第六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
[144]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阳花杨战国秦墓群发掘简报[J].文博,2017(1).
[145]田亚岐,耿庆刚.咸阳“周陵”发现一批战国秦墓[J].大众考古,2014(5).
[14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乾县夹道村秦墓发掘简报[J].文博,2014(1).
[147]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0年考古年报.
[148]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临潼清泉秦墓清理简报[J].文物世界,2011(6).
[149]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考古研究所.陕西渭南阳郭庙湾战国秦墓发掘简报[J].文博,2011(5).
[15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著.华县东阳[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376.
[15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4年考古年报.
[15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4年考古年报.
[15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1年考古年报.
[15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1年考古年报.
[155]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调查新收获[J].考古与文物,2014(2).
[15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著.临潼新丰—战国秦汉墓葬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157]a.梁云.论早期秦文化的来源与形成[J].考古学报,2017(2).b.梁云.关于早期秦文化的考古收获及其相关认识[J].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4).c.梁云.早期秦文化探索历程[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7(1).d.梁云.从秦墓葬俗看秦文化形成形成[J].考古与文物,2008(1).
[158]高士荣.试论秦人早期丧葬习俗[J].兰州学刊,2016(11).
[159]史党社.日出西山—秦人历史新探[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
[160]史党社.从墓葬中的“异例”看秦文化的传播[J].中原文化研究,2017(3).
[161]陈洪.秦文化之考古学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162]陈洪.中型秦墓墓主族属—以渭河流域中型秦墓葬俗为视角[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
[163]a.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建河墓地[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b.滕铭予.宝鸡建河墓地的年代及相关问题[C]//边疆考古研究(第8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164]张寅.东周时期关中地区西戎遗存的初步研究[J].考古与文物,2014(2).
[165]孙占伟.陕西清涧李家崖东周墓地性质分析[J].南方文物,2015(3).
[166]雍际春.近百年来秦人族源问题研究综述[J].社会科学战线,2011(9).
[167]段清波.从秦始皇陵考古看中西文化交流[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
[168]a.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编著.周原汉唐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b.郑红莉,孙周勇.周原秦汉墓葬葬俗与特征研究[J].文博,2014(4).
[169]a.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凤翔孙家南头—周秦墓葬与西汉仓储建筑遗址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b.田亚岐,刘爽.孙家南头秦国春秋铜器墓的相关问题[J].考古与文物,2013(4).b.田亚岐,陈洪.再论孙家南头秦国春秋铜器墓的相关问题[J].考古与文物,2013(4).e. 陈洪.关中秦墓青铜器编年研究[J].文博,2012(5).f.陈洪.关中秦墓陶器编年研究[J].考古与文物,2014(6).
[170]陈洪.秦人葬式与社会等级的关系及其演变[J].考古与文物,2016(2).
[171]陈洪,等.再谈秦墓屈肢葬渊源及其相关问题[J].文博,2014(1).
[172]王志友.早期秦人构成探析[J].敦煌学辑刊,2014(3).
[173]郑红莉.秦墓殉葬现象再考察[C]//碑林集刊(十五).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
[174]印群.东周时期秦齐殉人墓的比较研究[C]//东方考古(第9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175]刘婷,梁云.秦人车马殉葬方式及其渊源[C]//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5年).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5.
[176]陈洪.从头向看本土秦人与外来移民的数量比例及葬埋地[J].中原文物,2017(4).
[177]滑宇翔,宋杰.秦与三晋战争对中原葬俗的影响[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3(3).
[178]郑红莉.秦墓棺椁制度试探[C]//碑林集刊(十六).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
[179]杨志飞.试论秦墓出土遣册量少的原因[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180]马利清.出土秦镜与秦人毁镜习俗蠡测[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
[181]马利清,宋远茹.尤家庄秦墓出土铜镜的初步研究[J].考古与文物,2010(2).
[182]张正原.秦墓出土铜带饰相关问题研究[J].保定学院学报,2013(5)
[183]于焕金.秦墓中出土的S形饰研究[J].考古与文物,2013(5).
[184]刘云辉.陕西出土的古代玉器—春秋战国篇[J].四川文物,2010(5).
[185]a.朱歌敏.宝鸡地区秦墓出土玉器初探[J].文博,2014(3).b. 朱歌敏.关中地区秦墓葬玉探析[J].文博,2016(4).
[186]王宏,权敏,向丽君.浅谈新发现的几件秦国青铜器[J].文博,2013(4).
[187]景宏伟,曹建宁.陕西凤翔小沙凹村发现春秋时期窖藏青铜器[J].考古与文物,2016(4).
[188]王宏.凤翔小沙凹窖藏青铜器研究[J].文博,2017(2).
[189]武丽娜.秦墓出土陶囷模型研究[J].农业考古,2010(1).
[190]吴晓阳.秦汉墓葬中随葬陶仓、囷现象浅析[J].古今农业,2012(2).
[191]李建西.陇县边家庄秦墓出土铜戈铭文新释[J].文博,2017(5).
[192]高西省.战国时期鎏金器及其相关问题初论[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4).
[193]宗椿理.民以食为天,饮当器以用—秦代饮食器具的多元类别与特定社会功能解析[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5(4).
[194]张寅.铲足鬲的分布、年代及其相关问题研究[J].文博,2014(2).
[195]张寅,等.关中地区东周时期“戎式陶罐”及相关问题研究[J].文博,2017(5).
[196]方喜涛.秦代随葬实用明器意义初探[C]//秦汉研究(第九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
[197]朱学文.秦漆器研究综述[J].华夏考古,2013(1).
[198]朱学文.秦漆器手工业研究[J].文博,2012(1).
[199]朱学文.秦纪年漆器铭文及其相关问题研究[J].考古与文物,2014(2).
[200]朱学文,朱宏斌.秦生漆产地与漆园经营[J].农业考古,2012(4).
[201]朱学文.从考古资料看秦漆器胎骨及制作工艺[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
[202]朱学文.从考古资料看秦代漆器艺术风格的相关问题[J].文博,2011(4).
[203]朱学文.试论釦器法在战国秦汉漆器制作中的应用[J].文物,2014(7).
[204]朱学文.秦东陵出土漆豆研究[J].文博,2013(2).
[205]王辉,等.八年相邦薛君、丞相殳漆豆考[J].考古与文物,2011(2).
[206]邸楠.关中地区秦墓出土铁器初步研究[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
[207]林永昌,等.论秦国铁器普及化与关中地区战国时期铁器流通模式[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3).
[208]熊建雪,等.秦人平民与劳工阶层体质差异研究—以关中地区出土人骨为例[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
[209]陈靓,田亚岐.陕西凤翔孙家南头秦墓人骨的种系研究[C]//西部考古(第三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
[210]邓普迎.陕西临潼新丰秦墓人骨研究[J].文博,2016(5).
[211]凌雪,等.陕西凤翔孙家南头秦墓出土人骨中C和N同位素分析[J].人类学学报,2010(1).
[212]a.凌雪,等.宝鸡建河墓地出土战国时期秦人骨的元素分析[C]//西部考古(第五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b.凌雪,等.宝鸡建河墓地出土战国时期秦人骨的稳定同位素分析[J].考古与文物,2010(1).
[213]舒涛,吴小红.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在碳、氮稳定同位素食性研究中的应用[J].文物世界,2015(4)
[214]付倩丽,等.新丰秦墓出土青铜器腐蚀状态初步研究[J].文博,2011(6).
[215]邵安定,等.陕西临潼新丰秦墓出土青铜器的初步科学分析研究[J].文博,2017(2).
[216]刘亚雄,等.陕西临潼新丰秦墓出土铜镜的科学分析[J].中原文物,2015(4).
[217]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周原博物馆.周原汉唐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218]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东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219]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北郊郑王村西汉墓[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
[220]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周原博物馆.周原汉唐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221]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东汉墓 [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22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北郊郑王村西汉墓[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
[223]a.张仲立,等. 西安南郊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2010年度获重要发现[N].中国文物报,2010-4-16.b.丁岩.西汉一代重臣张安世家族墓考古揽胜[J].大众考古,2014(12).c.丁岩.西汉富平侯张安世系年述略[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3).d.申超.汉代张安世家族兴盛考[J].南都学坛,2013(11).
[224]柴怡,等.西安东郊石家街发现汉代列侯级别墓葬[N].中国文物报,2013-8-16(8).
[225]a.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蓝田支家沟汉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3(5).b.段毅.蓝田支家沟汉墓墓主身份蠡测[J].考古与文物,2013(12).
[22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北郊井上村西汉M24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2(6).
[227]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张家堡新莽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9(5).
[22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西安富力赛高城市广场汉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7(2).
[2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等.西安市大白杨村汉墓发掘简报[J].考古,2014(10).
[230]a.柴怡,张翔宇.西安北郊发现大型西汉积沙石椁砖室墓[N].中国文物报,2012-05-11(8).b.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北郊百花村汉代石椁墓(M6)发掘简报[J].文博,2013(5).
[231]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未央印象城汉墓发掘简报[J].文博,2017(2).
[232]a.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北郊万达广场五号汉墓发掘简报[J].东方博物,2013(1).b.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北郊万达广场汉代砖椁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7(2).
[233]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张家堡村汉墓群[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4).
[234]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市长安区西甘河村古墓葬发掘简报 [J].东方博物,2013(4).
[235]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曲江羊头镇西汉墓发掘简报[J].文博,2013(6).
[236]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南郊潘家庄169号东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8(6).
[237]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电子三路西京社区东汉墓清理简报[J].文博,2010(4).
[238]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陕西师范大学雁塔校区东汉墓发掘简报[J].文博,2012(4).
[239]张翔宇,等.西安北郊滹沱村安置楼工地发掘七座古墓[N].中国文物报,2013-01-04.
[240]张翔宇,等.西安北郊香树花城工地发掘八座古墓[N].中国文物报,2012-12-21.
[24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咸阳渭城区民生工程汉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7(2).
[242]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阳崔家村汉墓发掘简报[J].文博,2016年(4).
[24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凤翔路家村墓葬发掘简报[J].文博,2013(4).
[24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凤翔西白村秦汉墓葬发掘简报[J].文博,2010(4).
[245]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扶风纸白西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0(10).
[24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宝鸡凉泉汉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3(6).
[247]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蒲城永丰战国秦汉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6(5).
[248]韩国河,张翔宇.西安地区中小型西汉的墓葬的分期与年代研究[J].考古学报,2011(2).
[249]张翔宇.西安地区西汉墓文化因素分析[J].考古与文物,2013(5).
[250]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米脂官庄画像石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12).
[251]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等.陕西神木大保当东汉画像石墓[J].文物,2011(12).
[252]赵建兰.陕西榆林出土一汉墓[N].中国文化报,2013-7-11.
[253]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靖边县文物管理办公室.陕西靖边老坟梁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1(10).
[254]王天佑,马明志.陕北、长安地区中小型汉墓的比较研究—以老坟梁汉墓为例[J].中华文化论坛,2017(1).
[255]王天佑,等.陕西靖边老坟梁出土的粮食鉴定及其初步分析[J].农业考古,2011(1).
[256]陆航.陕北靖边发现阳周故城遗址[OL].[2016-11-07].http://ex.cssn.cn/zgs/zgs_jl/201611/t20161109_3270484.shtml.
[257]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汉中市文物考古工作队.陕西南郑苏家山汉墓发掘简报[J].文博》,2012(2).
[258]a.王昌富.考古队初步揭开陕南三千崖墓的神秘面纱[N].北京科技报,2004-05-31.b.王昌富,杨亚长.陕富水汉代崖墓考古发掘获重大发现[N].中国文物报,2009-05-29.
[259]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曲江翠竹园西汉壁画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0(1).
[260]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靖边县渠树壕东汉壁画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7(1).
[261]杨泓.观陕西汉唐墓室壁画札记[J].文博,2011(3).
[262]贺西林.古墓丹青:汉代墓室壁画的发现与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
[263]a.黄佩贤.汉代壁画墓的分区与分期研究[J].考古与文物,2010(1).b.黄佩贤.近年关中地区出土西汉壁画墓的启示[J].文博,2011(3).
[264]a.程林泉,张翔宇.关中地区汉代墓壁画浅析.[J].考古与文物,2006(3).b.张翔宇.西安地区汉代壁画墓特点浅析[J].文物,2012(10).
[265]后晓荣,陈晓飞.关中地区两汉壁画墓初探[J].中国历史文物,2006(4).
[266]叶磊,高海平.汉墓丹青--陕西新出土四组东汉墓室壁画车马出行图比较浅析[J].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10(4).
[267]龚晨.汉代墓室壁画色彩研究[D].上海大学博士论文,2015.
[268]祈远虎.离宫、行宫辨[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269]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09年千河下游东周、秦汉遗址调查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5(3).
[270]a.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千阳尚家岭秦汉建筑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0(6).b. 田亚岐.千阳尚家岭秦汉建筑遗址初识[J].考古与文物,2010(6).
[271]a.王子今.秦汉交通考古[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b.赵瑞民.讲述秦汉帝国交通的故事—《秦汉交通考古》序[N].中国文物报,2016-5-10(6).
[272]肖健一,等.陕西咸阳秦汉甘泉宫遗址调查获重要发现[N].中国文物报 2015-12-18 .
[273]a.姚生民.益延寿宫考略[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3).b.姚生民.西汉甘泉宫在甘泉山下[J].秦汉研究,2012.c.姚生民.甘泉宫泰畤考[J].秦汉研究,2014.
[274]梁云.汉甘泉宫形制探讨[J].考古与文物, 2015(3).
[275]郭霖锋. 秦汉甘泉宫的演变[J].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4).
[276]a.周晓陆.西汉甘泉宫三字瓦当跋[J].考古与文物,2008(1).b.八岭.西汉“甘泉宫”瓦当[J].四川文物,2008(5).
[277]a.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直道考古队.陕西富县秦直道考古取得突破性成果[N].中国文物报,2010-01-01.b.张在明,喻鹏涛.陕西秦直道遗址调查发掘简报[J].秦汉研究,2015.
[278]肖健一,等.陕西富县、甘泉县秦直道考古调查成果[N].中国文物报,2015-9-25.
[279]王勇刚,等. 陕西秦直道甘泉段发现秦汉建筑遗址[N].考古与文物,2008(4).
[280]张在明,等.秦直道发现道路四叠层与东西线之争[N].中国文物报,2011-08-12.
[281]王子今.说“圣人道”“圣人条”:秦始皇直道研究札记[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2).
[282]高子期, 周晓陆.秦直道建筑探究[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
[283]姚生民.昭君出塞经地考[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1).
[284]曾磊.秦直道为重修说[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8(7).
[285]尹亚萍.论秦直道是否经过上郡[J].鄂州大学学报,2016(5).
[286]喻鹏涛.秦直道若干问题研究[D].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287]赵静.子午道名称的科技认识探讨[J].文博,2016(1).
[288]赵静.陕西秦蜀古道遗产[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
[289]a.田亚岐.陕西境内丝绸之路南线走向考察及其相关问题研究[C]//湖南吉首“2014年国际考古遗产管理科学委员会(ICAHM)年会”论文.b.田亚岐,等.秦汉时期长安至陇山段丝绸之路考察研究[C]//早期丝绸之路暨早期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290]李岗.陕西泾阳发现的明代洪堰制度碑[J].农业考古,2017(2).
[291]张维慎.浅谈秦汉时期陕西的水利建设[C]//秦汉研究(第十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
[292]王子今,郭诗梦.秦“郑国渠”命名的意义[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11(2).
[293]赵艺蓬,陈钢.郑国渠与白渠关系浅析[C]//秦汉研究(第八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
[294]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西安市文物保护所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西安市昆明池汉唐遗址区西周遗存的重要考古新发现[J].考古,2013(11).b.张宁,张旭.汉昆明池的兴废与功能考辨[J].文博,2013(3).
[295]孙周勇,李坤.陕西眉县尧上遗址[C]//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296]a.种建荣,等.试谈铁作坊中废弃冶铸遗物整理的理念与实践[J].南方文物,2013(3).b.林永昌,等.试论汉代关中地区铁器生产原料的来源与流通—邰城铸铁作坊出土铁遗物的冶金分析[J].考古与文物,2015(6).c.林永昌,等.西汉地方铸铁作坊的技术选择:以关中邰城作坊冶金陶瓷科技分析为例[J].南方文物,2017(2).d.林永昌,等.论秦国铁器普及化与关中地区战国时期铁器流通模式[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3).e.种建荣,等.试论陶器生活遗存所见西汉铁器手工业作坊的性质—以邰城铸铁作坊为案例[J].考古与文物,2018(1).f.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邰城铸铁[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297]田亚岐,等.陕西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C]//2016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
[298]a.梁云.鄜畤、陈宝祠与汧渭之会考[C]//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1年).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b.赵东.畤祭:从秦国到西汉的重要祭天形式[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1).c.刘再聪.畤祭与秦人“天下共生”意念的萌芽[J].青海社会科学,2009(1).d.徐迎花.秦代以畤祭为特色的郊祀制度考[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e.徐卫民.秦始皇泰山封禅的原因新探[C]//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1年).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f.何平立,沈瑞英.秦皇汉武封禅与礼仪、思想、文化变迁[C]//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1年).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g.臧知非.封禅与文化认同:秦始皇封禅的政治文化学分析[C]//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2年).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
[299]张忠培.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300]a.王子今,吕宗力.《中国考古学.秦汉卷》评价[J].中国历史研究动态,2011(4).b.高崇文.读《中国考古学·秦汉卷》[J].考古,2012(8).
[30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302]梁云.早期秦文化的探索历程[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