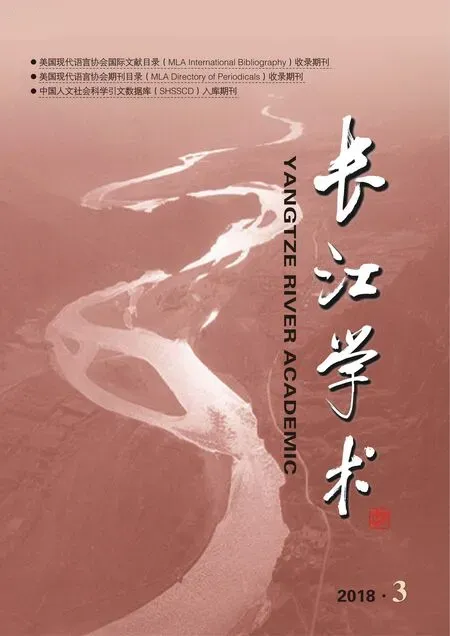白话书写的音乐性实验:鲁迅的《野草》和《好的故事》※
〔美〕安敏轩著 郑艳明译
(1.康奈尔大学 亚洲研究系,美国 纽约 14853;2.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五四”时期,鲁迅和同时代的作家用现代汉语创作出一批新文学作品。散文诗作为一种新的文体,顺应了早期诗人建构白话诗学的需要。鲁迅对语言在政治和美学方面的未来十分关注。本文通过重读他的散文诗集《野草》,考察《好的故事》的视觉、听觉韵律,分析鲁迅如何以波德莱尔式的散文诗作为自己语言创造的起点,探索白话书写的音乐性。
一

“散文诗”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适应了民国早期诗人创造白话诗学的需要,它的名称与外国散文诗的译介相关。在1920年代,如果把散文诗这一独特体裁视为语言和韵律试验的动力,则有助于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更深入地理解散文诗的特点。1915年,刘半农翻译了四首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当时列入“小说”栏)发表在《中华小说界》上,此后五年,他和周作人等《新青年》中的部分作者开始创作散文诗。散文诗受到了广泛关注。1923年,郭沫若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以一段散文和韵文的论争作为开头,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下文将论析鲁迅在《野草》中梦想通过散文诗为白话创造一种新的韵律的原因和过程。
诗歌形式有两个特征:它受到形式本身的限制和传统的影响。因为形式是诗歌创作中的工具,而不是用来分析诗歌的首要凭借,所以个别诗歌常常或遵守,或抬高,有时甚至违背、贬低形式的限制和传统的影响,然而形式依旧是有用的原材料,是艺术家和读者阅读诗歌的出发点。以英国的十四行诗为例,它由十四句诗句组成,常在第八行或第十二行后有一个概念上的转变或跳跃,对爱进行冥想和沉思。读过十四行诗的人可能会举出一些反例:从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全集第94首中对自我控制的欣赏到乔治·梅瑞迪斯(George Meredith)的诗集《现代的爱情》中的十六行诗,都突破了这一形式要求。在散文诗最受欢迎的1920年代,它的特别之处在于,作为一种诗歌形式,它并未受到传统的严格限制。周作人《小河》的序言中写道:“有人问我这诗是什么体,连自己也回答不出。法国波特莱尔(Baudelaire)提倡起来的散文诗,略略相像,不过他是用散文格式,现在却一行一行的分写了……或者算不得诗也未可知;但这是没有什么关系。”郭沫若在上文提到的《序引》中谈到,最近有关诗的论争在押韵的诗与散文诗之间越陷越深,应该把讨论的重点放在这种诗歌观念“何以竟能深入人心而牢不可拔”。另外,贺麦晓(MichelHockx)指出,和郭沫若一样,捍卫散文诗的人把它定义成不押韵的分行诗。作家和批评家们对散文诗的形式似乎都有不同的理解,人们普遍认为散文诗的特点是不押韵,但创作出的散文诗却常常是押韵的。只有一些人意识到了西方的散文诗最普遍的特点是不分行。虽然有关用韵问题的论争一度激烈,但作家和批评家们却并没有为散文诗确立形式的限制。和对散文诗进行定义相比,五四作家们更热衷于对这一文体进行实验。
人们对散文诗这一诗歌类型的期待源于它的历史。“散文诗”一词最初是由西方术语“prosepoetry”的字面意思翻译而来,即传统的“没有韵律的散文”加上“抒情的诗”。在中国,“散文”和“诗”这两种文体已有较长的历史,而它们的历史却和英语的“prose”和“poetry”不完全一样。虽然“词”似乎更口语化,也更适合白话文运动,但称其为“散文诗”,暗指曾最受欢迎和最为推崇的“诗”,似乎在尝试为这种还未成熟的诗歌形式确立权威地位。当然,除了只能选用这些术语外(“诗”已经被白话借用指代“诗歌”),命名的人也希望将这种诗歌类型与过去辉煌的诗歌传统放在同等的位置进行评价。此外,“散文诗”与外国文化间的密切关系也赋予了它特殊的价值。奚密写道:“对现代汉诗来说,‘西方’在很长时间内一直都是‘先进’、‘现代’的同义词,并被视为主要的模式。”从这一角度来看,“散文诗”在很多方面都是令人满意的:它的命名既结合古典的纯文学与西方的进步意义,再造了一个经典的名词来实现现代性的需求,同时也可视为将传统的因素结合起来发明新的白话文词汇的实践。
不同的主体对散文诗的具体特点有着不同的阐释。周作人在谈论散文诗时经常提到法国的波德莱尔,散文诗的作者、和鲁迅同时代的刘半农则认为“法国之诗,则戒律极严。任取何人诗集观之,决无敢变化其一定之音节,或作一无韵诗者”。和周作人、鲁迅一样,刘半农也不会法语,但他似乎没有读过1890年以后的法国作品。这个例子也说明西方散文诗传入中国的方式多以译介为主。郭沫若在其翻译的歌德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中介绍了散文诗,曰:“如果有人从头到尾都不了解散文诗的意思,我请他们读这部作品《少年维特之烦恼》!”他眼中的散文诗是一种超凡的文学现象,而不是一种作家故意使用的文体。正如在英语中,人们听到自己喜欢的语言时,常会说“听起来像一首诗”,郭沫若所要表达的似乎也是如此。鲁迅对散文诗的看法和郭沫若有些相似,他在介绍《野草》时写道:“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不过,在这段话中,他似乎在避免用散文诗来抬高自己的作品。作家和批评家们阅读了散文诗作品,却很少有人了解它的相关研究,且缺乏对散文诗传统的讨论,对散文诗的理解不尽相同。在散文诗被人们广泛了解,成为中国人书写和表达情感的方式,并且有足够的本国作品作支撑之前,人们对这一概念当中所包含的部分外国传统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作者使用的语言、感兴趣的国家的文学,以及如何定义这部分传统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作家的需求。
散文诗这一形式的最大好处可能在于它的自由,它没有限制作家的具体创作,却不乏内在对美的追求。作家们对散文诗的解释和定义都没有错。正如波德莱尔在散文诗《窗户》中写道:“‘你能保证这传说是真的吗?’如果我的想象能帮助我生活、帮助我感觉到我的存在和我是什么,那么我自身之外的真实是什么有何关系呢?”中国的散文诗并不是西方的散文诗,很多人也并不关心西方散文诗的含义,读者因此得以直接与这种诗体交流,而不用在意它所代表的传统。散文诗没有统一的定义,写作散文诗的人将有机会承担起为新一代白话诗人、读者、评论家创造更多诗性语言的任务。
二
前一章描述了民国时期人们对散文诗的态度和在当时讨论这一形式的难度。这一可塑性很强的诗歌类型,使批评家们在讨论它的形式和传统时,常常要和这一时期的作家那样通过它的各种定义来完成他们的批评任务。前文提到,郭沫若将其作为一种美学价值评价;孙玉石在1980年代引用波德莱尔对散文诗的定义,并且只列举了符合这一定义的一些作家作品。虽然这些观点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正确的,但也可能对读者造成误导。因为有关这一诗歌类型的一些初步想法,被应用到具体作品时,将会对诗歌作品、诗集的接受和理解产生影响。

李欧梵谈到,鲁迅1924年开始投入《野草》的创作时,正好在阅读和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其中包括波德莱尔的散文诗《窗户》的日文翻译,上文已经有部分引用到。在这本书译文的第二部分第二节以“自己发见的欢喜”命名的译者附记中,鲁迅写道:
波德莱尔的散文诗,在原书上本有日文译;但我用Max Bruno德文译一比较,却颇有几处不同。现在姑且参酌两本,译成中文。倘有那一位据原文给我痛加订正的,是极希望,极感激的事。否则,我将来还想去寻一个懂法文的朋友来修改他;但现在暂且这样敷衍着。

法国的波特莱尔,谁都知道是颓废的诗人,然而他欢迎革命,待到革命要妨害他的颓废生活的时候,他继续憎恶革命了。所以革命前夜的纸张上的革命家,而且是极彻底,极激烈的革命家,临革命时,便能够撕掉他先前的假面,——不自觉的假面。
鲁迅所描绘的波德莱尔是一个懦弱、滑稽、有种优越感的精英人物形象,这一说法当然不是崇洋媚外,但也不是客观地陈述历史,他在情感上所在意的是波德莱尔对政治的态度。鲁迅在给年轻作家萧军的回信中写道:“我的那本《野草》,技术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我希望你脱离这种颓唐心情的影响。”颓废不仅指颓唐的,也指沮丧和难过——他们共有的词根“颓”,含有堕落和崩溃的意思,这些都表明,白话中由它构成的复合词的含义并不是固定的。对此我的理解是,鲁迅将颓废视为失败主义的一种,这种感受对于那些没有为生存和未来奋斗的人而言是体会不到的。回避和避免跟世界接触可能是波德莱尔想法中的一部分,但在鲁迅看来,回避是“碰钉子”后产生的想法,是虚伪的、暂时的。也许对他而言,他和弟弟周作人之间的交恶,国家政治局面的恶化,以及他在内的革命者们的活动对国民生活难以产生影响的现实,这些都只是外部影响,思想变化似乎并没有影响他的情绪。鲁迅更在意的是创造了什么,对《野草》而言,正是它的写作技巧。鲁迅似乎设想自己在这些外部阻力影响下,以想象中波德莱尔的思维方式(或许和波德莱尔本身的想法有些出入)苦苦挣扎;在失败后受到打击,并因此退回到追求个人的小的快乐,正如他在《呐喊·自序》中所描述的抄写古碑拓片一样。鲁迅在给萧军的信中提到《野草》的“技术不算坏”,他并没有从政治参与和思想正确的角度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而是将它的“技术”和写作方式放在第一位。
当然,仰望天空并不是现代现象。早在汉代,诗人扬雄作《反骚》以回应屈原的《离骚》。在讨论诗人之间的这种对话时,读者面临的问题可能来自“影响”之类的术语,其“受影响”或“顺应”的消极内涵似乎在暗示:有互文关系的作者可能在进行一种非创造的行为。而像普实克和李欧梵等这样对他们的对象非常有热情的评论家,则更倾向于从作家的独立性、独特性和天才的创作等角度来论述。在讨论“影响”的过程中,面临的另一问题来自国家民族主义:如方志彤认为庞德是中国1917年文学革命的教父,而罗威尔则是教母。周质平从影响的角度质疑美国诗歌孕育了中国诗歌这一观点,指出:“我所不能同意的是……似乎没有这两位美国诗人,中国的文学革命就要流产,至少也要延缓”。他并未从“影响”的事实这一角度提出质疑,这些事实本身值得怀疑。笔者认为,思想不是孕育出的,不论一本书受到另一本书的多少影响,作品本身都还是作家的产物。国家文化也是如此,它无法创造文学,无论国家文化的影响多大,文学作品还要靠作家们将其书写出来。这或许是方志彤用“父亲”“母亲”这一表述的原因。文学一旦被定义为民族精神和互相影响的直接产物,我们在阅读过程中也就失去了重要的分析方法和工具。正如奚密指出的:“把本土和外国截然两分的思维模式显得简单化和可疑了。‘五四’以来汉语诗歌的现代性应视为诗人在多种选择中探索不同形式和风格以表现复杂的现代经验的结果。”当一种艺术形式,尤其是散文诗这样开放性的试验形式跨越边界时,不同地方、不同语言的读者读到的感受会变得完全不同。因此,一部作品对另一部作品的影响并不代表他们是同一种艺术,或是通过对前者的机械模仿而衍生出来。当我们认同这些看法时,就会发现鲁迅的美学观念和他对中国语言文学的期待,而如果仅把鲁迅想象成一个盼望外国传统的人或者独自创造新文学的天才,将会对这种期待视而不见。
在相隔很远的作家之间,翻译是最直接、专业的沟通方式。鲁迅主张“硬译”,目的是丰富和改造汉语,通过外语中新的结构补其不足,以容纳更多的想法和更丰富的句法,使汉语拥有更强的表现力和生命力。鲁迅说:“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这并不是空想的事情。”鲁迅将自己和他这代人视为创造白话的一代,所以很自然地专注于语言能为说话人做些什么。而身份、传统、版权和“中国性”的问题似乎都与此无关。正如刘禾在《跨语际实践》中写道:“对我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出于何种实践目的或者需要,文学人类学家才孜孜不倦地从事文化的翻译。”当散文诗这一概念进入到中文的语境中,鲁迅认为它是我们自己的概念,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被绝大多数不会说外语的人来谈论。鲁迅的目标是革新中国的语言,使它更有效地涵盖西方的想法和经验。面对这一巨大的挑战,鲁迅希望通过使用各种工具来充分发挥和利用这门语言。“但精密的所谓‘欧化’语文,仍应支持,因为讲话倘要精密,中国原有的语法是不够的,而中国的大众语文,也决不会永久含胡下去。”鲁迅在使用“欧化”一词时的不情愿显而易见,但我们仍能感受到他似乎在试图表明自己对这种语言变化的信心:即使是在民族主义者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人面前,他也将支持这一语言。总而言之,不论鲁迅受到了多少影响,不论他受到的影响来自哪里,鲁迅做的选择基本来源还是他自己的意志。鲁迅在翻译中的这一意图使白话文得以发展和完善。
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太过重视鲁迅的“独立创造”,常常会忽略鲁迅付出了多少辛苦的劳动和他的学问有多大力量,他精通五种语言(绍兴方言、文言文、白话、德语和日语),熟悉英语和俄语,在广泛深入地阅读大量作品的同时,他翻译了很多有难度的作品,并且以之为己任。在翻译《死魂灵》的时候,他描述自己“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一面也自然只好怪自己语学程度的不够格”。鲁迅从他自己心中庞大的图书馆所精选出来并与之进行对话的《小散文诗》这类作品,可以视为鲁迅另一种形式的自我表达。在他看来,翻译外国作品有时是不那么愉快的斗争,鲁迅对自己的能力不甚满意并且希望能做更多的事情,他眼中的白话文更具包容性。鲁迅并不满足于刘半农和其他人的作品中已经存在的散文诗传统,希望通过演说的方式来丰富和改善白话文。
鲁迅和波德莱尔一样,向往一种更好的,更清晰、灵活和美妙的语言。波德莱尔写道:“我们当中谁没有在那雄心勃勃的日子里梦想过一种诗意的散文的奇迹呢?它富有音乐性,却没有节奏和韵脚,相当灵活,对比相当强烈,足以适应灵魂的抒情性的动荡、梦幻的波动和意识的惊跳。”因为这一梦想在当时并未实现,于是鲁迅选择了牺牲翻译作品的流畅性。然而伦德堡格(Lundberg)得出以下结论:“鲁迅的‘翻译语言’和他自己的‘创作语言’显然不同……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以他自己为主。”和小说相比,《野草》更能代表鲁迅在白话的美和音乐性上的执着追求。它的形式、风格多样,包含诗剧《过客》和被鲁迅称之为“拟古的新打油诗”的讽刺诗《我的失恋》,以及寓言体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等。《野草》中至少出现了八次有关梦的叙述,绝大多数都是以“我梦见”作为开头。限于篇幅,本文不能一一分析其中的类型,但这些梦的叙述正好与散文诗所代表的自由相契合。虽然这些梦境所反映的是在醒着的世界所经历的事物,然而每一个梦,都像是不同诗人眼中散文诗的规则与传统,创造着独特的诗歌美学。此外,《野草》中的梦境叙事似乎都提供了一个可以自由地进行美学创造的空间,这一点在《好的故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鲁迅通过叙述人将梦到的美好故事直接叙述出来,没有重新编排任何内容或涉及政治方面的表述。在不把它们置于人与世界的任何固定关系的情况下,他试探着象征性地将这个故事讲述为最好的故事。
梦的自由与散文诗的自由,二者相互补充,似乎是鲁迅这一时期的合理选择:莫里斯·布洛克(Maurice Bloch)在书中写道,“如果我们面对一种语言,它的语法不能清晰自由地表达,那么这种语言所带来的争议就会降低,它所携带的命题也将会改变。”古典诗的形式对句子的长度、助词和其他指示词的省略有强制要求,讲究押韵与平仄。鲁迅和其他二十世纪早期的作家,都认为这些规则限制了表达。正如布洛克所言:“虽然这些限制通常都被认为用来限制形式而不是内容,但和直接批评内容相比,它们在限制内容方面却更有效。”
具体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野草》中,鲁迅写了一首讽刺诗,名为《我的失恋》,副标题是“拟古的新打油诗”。这首诗是叙述“我”给爱人礼物,爱人不理解的故事,采用的是古诗中每句七字的形式。例如“金表索”,三个字组成的宾语对七言的句子而言正好合适,主语和动词占据前四个音节的位置,在第四个音节后通过句中的停顿来获得对美的期待,在一句中完美地实现了用形容词修饰名词。爱人所赠的礼物都是三个音节,并且都有古典的含义,如“百蝶巾”“双燕图”“玫瑰花”,而叙述人回赠的礼物都违反了传统诗歌的形式要求和期待。在第二节中,他回赠的礼物是“冰糖葫芦”,虽然在情感上是可以接受的,但这一表述采用了口语,且不是由三个音节构成,这样句子就超出了七拍。这只是布洛克(Bloch)指出的格律限制了口语入诗、用新词及押新韵并最终限制了内容的一个方面。绝大多数古典诗歌中,如果诗人找不到符合结构的“冰糖葫芦”的表达,他们会用另一个名词来替换。在英语的十四行诗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例如绝大多数情况下,和“potassium carbonate”(碳酸钾)这个词相关的内容将被排除在十四行诗之外,因为这个词有太多的音节而不能适应十四行诗的音节要求。除此之外,“carbonate”(碳酸盐)也不符合抑扬格。鲁迅的《我的失恋》似乎表明,除了一些技术专有名词外,现代生活中很大一部分感受和事物不能用古代汉语来表达,并因为形式的限制不能进入到古典诗歌当中。作者们梦想的写作内容的自由,需要和形式的自由结合起来,这也可能促使他在创作《野草》时选用散文诗这一形式。
三
鲁迅在《野草》中尝试建立了一些结构,旨在创造和改善白话文。具体而言,他通过《好的故事》营造了一个将诗的音乐融入白话的自由空间。已有部分研究者开始注意到《野草》和《好的故事》中的音乐性,并达成了一些共同意见。例如孟瑞君写道:“《好的故事》的意境更是富于通感音乐美的典型。”李天明同意这一观点,认为《好的故事》“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它的音乐性。”然而这首诗的音乐究竟是什么,如何设置的问题,仍有待考察。虽然部分读者已经意识到,人能感知声音中意愿结构的存在,就像耳朵能将电视信号不良的声音与海潮发出的嘶嘶声区别开来,但仅凭直觉并不足以开始讨论这首诗的韵律模式。由鲁迅的作品可以得出,他并未像下文分析的那样定义他作品中的诗体,他所用的方法我们并不能使用(也许他凭直觉感知到的这些诗的韵律模式正如我们听到这些诗被朗读出来时感受到的一样)。因而在讨论《好的故事》中多样的韵律结构时,我们的分析方法有时甚至是矛盾的,下面谈到的一些方法还只能构成一种对话的尝试。当我们进一步展开有关《好的故事》韵律问题的对话,这些分析工具或许将提供最佳方式。
上文所涉及的有关押韵是否存在的激烈论争很自然地与诗的节律结合起来,尤其是这一历史时期,押不押韵作为一种音乐特征都同样重要。从研究方法来看,辨析《好的故事》中的韵律却十分困难,其中最大的障碍来自鲁迅的背景: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绍兴人,从小就说着当地方言,绍兴方言虽然和该地区的吴方言、上海周围的方言有关但却完全不同。鲁迅在1912年搬到了北京,并开始了《野草》的创作,那时他对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白话文并不熟悉。1933年,上海《出版消息》刊登了一则匿名作者所描绘的鲁迅素描,说道:“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而且是‘南腔北调’。”这个四字成语字面上的意思是“南方的口音北方的语调”,或者是指说话的口音不纯,夹杂着方言。这个小小的刺激(在接下的内容中对鲁迅有一些称赞)激发鲁迅在年底写了一篇文章,回应说他“喜欢演说,有些口吃以及夹杂着口音”的人,并将其作为杂文集《南腔北调》的前言。曰:“前两点我很惊奇,后一点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这缺点还有开拓到文字上去的趋势。”他没有继续为这种趋势定义,而是将其归因于《语丝》的停刊;他选择用“南腔北调”这个词来为他的杂文集命名,或许是因为他在1933年写作的杂文也拥有这种混合性,这使他再一次认识到作品中结构的缺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的艺术中缺少严格的限制。
有评论者认为《好的故事》中的一些乡村场景来自鲁迅的故乡,鲁迅的语言夹杂着绍兴方言和北方官话,因而在讨论韵律时需要分析诗中方言的影响。绍兴方言和吴方言有着直接关系,是越国语言的直系后裔,而越国最终被楚国吞灭。它们之间有着漫长的分化历史,包括绍兴方言在内,和吴方言相关的很多方言特征之一是拥有一套和文言、古典完全不同的表述。比如第三人称代词表单数时为伊,表复数时为耶。鉴于此,我们并不能像分析那些缺乏书面表达,语法和词汇的差异被隐藏在对更常见的古典词语的重新解释以及交叉应用中的方言那样,通过追述特殊的方言字来帮学者直接认出方言在书面文学中的存在。通过对鲁迅作品中的词汇进行统计分析,徐士文(Raymond Hsü)发现鲁迅只使用了几次方言词汇,并得出了这些分散在他大量的作品当中的表述很可能是无意中被使用的结论。而在《鲁迅作品方言词典》中也只有一处涉及《好的故事》中出现的绍兴方言,即第七段中与蜀葵有关的比喻。徐士文还发现鲁迅比同时代人更多地使用白话,他注意到“读者们往往被鲁迅丰富的表述,尤其是文言的表达所吸引,认为和其他作家比起来,鲁迅使用白话要少一些,而忽略了鲁迅对白话的大量运用。”
虽然鲁迅的确想用白话的词汇和结构来进行创作,但他所听到的这些词是否能够表达读者经验的问题却依然存在。在无法获得任何鲁迅阅读相关作品的录音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弄清楚这一问题,而尝试用今天的绍兴话来朗读他的作品,或许可以暂时得出一些结论。今天的绍兴方言是为数不多的我们能听到的和鲁迅所听到的相似的声音,虽然在《野草》创作完成后的80年里,绍兴方言也发生了一些我们很难感知到的变化。通过分析用今天的绍兴话朗读的《好的故事》,我们发现这首诗用绍兴话读起来比普通话的韵律更多一点。在第一段中,“的(地)”与“了”之间有一个有很轻的押韵(它由很小的助词结构组成,而不是语气更强的名词、动词或形容词),这只有在普通话中才很明显。接下来的两个句子在句法上刚好相对,两句分别以“近”和“边”这两字作为结尾,不仅用绍兴话读起来押韵,用普通话读起来和前一句中的“暗”字读音更为相近,“an”在绍兴话中听起来则更像“gnin”。这个例子虽然并不十分精确,但它的结论和上文中徐士文的观点大致相符合,即这首诗的韵律模式在白话当中通常是可以听到的,其中的一些例外则可能是无意中产生。
《好的故事》中押韵的频率和排列一方面表明作者对韵律的关注,另一方面也表明作者也许忽略了批评家提到的有韵诗和无韵诗之间的巨大差别。这首诗中的押韵分别出现在第一段和第一次列举梦中所见场景的段落中,有利于抒情。作者并没有拒绝押韵,而是反对每句用韵。韵律从诗的结构中被解放出来,因此可以专门用它来吸引读者的注意或者起强调作用。这在《好的故事》中尤为重要,因为它以最普通和最不起眼的场景,即主人公睡着了开始做梦作为开头。当声音成为听者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押韵将成为一种很好的宣告方式,另外它也可以勾起读者的兴趣,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在《死火》这样的诗中,场景框架被作者浓缩成简单的事物,如开头“我梦见自己在冰山间奔驰。”《好的故事》缺乏这种对奇特的感官经验的即时反应,但它在开头搭建的声音结构使叙事人所处的由昏暗的灯光和烟草的烟雾构成的氛围变得有些抒情。第五段中出现了很强烈的押韵,和古典诗歌比起来,韵脚隔得更近,押韵的次数也增多了,强调了在这首诗反复出现的“一一看见,一一知道”的基本经验。虽然波德莱尔诗中的韵律在日语的翻译中也很难保存下来,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罗列以及其他情况下也强调押韵,并且保留了押韵的用法。他写道:“Il n’est pas d’objet plus profond,plus mystérieux,plus fécond,plusténébreux...”诗人在开头通过一系列较长和较复杂的形容词,组成了简短而又紧凑的ABAB式的押韵。虽然(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散文诗)最大的自由一开始看起来是不押韵的自由,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现在可以承认他们更大的自由是随心所欲地用韵。
古诗的押韵和格律之间很难分开。整齐的押韵增强了韵律和节奏,二者相互促进。在高度凝练的古诗当中,格律是一首诗在格式、音律等方面应遵守的规则,代指节奏、韵律,我将其定义为诗与时间的关系。《好的故事》中的格律形式很难辨别,但它有大量精心组织和听得见的韵律。因为《好的故事》采用了西式的标点符号,这些停顿将在文本中直接展现,避免了通过语法分析将古代汉语划分成短语。为了形象系统地描述这些韵律,我选择了通过断句将书面语划分成句的方法。汉语的音节持续的时间虽不完全相同,但大体相似,因此通过标点符号之间的音节数可以粗略估计在每个停顿之间说这些话的时间。具体来看《好的故事》中的韵律:诗中押韵和相同长度的短语集中出现在第一、五、七、八和十一段。以第五段为例,其中出现了四个连续的四字短语,紧接着是一个两字的短语和三个以上的四字短语。相比之下,《呐喊·自序》中的前两段只有一个有韵律上的重复,出现在鲁迅与母亲分别,描述母亲对他选择去学洋务感到失望,并为他的未来感到焦虑的这一场景中。作者在这里采用了传统的抒情方式,而传统的七个音节形式的运用似乎是非常合理的。不论是不是有意用韵,这样的押韵在《呐喊·自序》的600多个字符中只出现了一次,但在《好的故事》的550个字符中反复出现。每个段落中几乎都有两个到三个音节的押韵出现。
《好的故事》与中国传统诗歌在韵律方面的一个关键不同,是重复押韵的多样性。正如《我的失恋》中绝大部分句子那样,古典诗歌每句通常由四个、五个或七个音节构成。《好的故事》中押韵的句子则多为四字、七字组成的短语,另外还有一些八字和十字的短语。这是非常重要的,正如上文讨论《我的失恋》时已经提到的,诗行的长度可以限制句中的词汇与内容,古诗中由文言文的单音节词构成的句子在语义上刚好符合七言的句子。当古汉语中的单音节词变成了白话中的双音节词,原先符合七言诗的节奏开始反抗最后突破这一形式的限制。此外,古代汉语中助词和代词的省略,对鲁迅这样支持白话并且致力于将语言表述得更加精确的人而言,他们不仅仅希望白话文比文言文多出一些字词,而是希望通过加入更长的短语来丰富这门新语言的节奏模式,最终使说话人可以完整、清晰地表述自己的想法,并获得白话的音乐。
CharlesAlber在197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认为“鲁迅在《野草》中使用的最耐人寻味最有效的文学手段是排比”,即句子中一些重复的韵律结构。如果不去讨论哪种手法更有效,在《好的故事》中有一个十分独特的排比(另外还有一些容易识别的排比,它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手法之一)是值得特别注意的。在第七段中,叙述人说:“带织入狗中,狗织入白云中,白云织入村女中……”古诗中的排比和骈文的排比说到底和韵律有关,通常构成排比的两句诗或散文的短语字数相同并且呈平行排列。因为文言词汇常用一个字表示一个动作或事物,白话中则加入了现代汉语中的双音节词,所以在没有重复用韵的情况下,白话将更容易保持句子的平行。散文诗并不需要每句都有相同的字数和韵律,相同的句法也不用出现在一起。在上文所引的例子中,两句的交织和混合实现了扩展,句子并没有失去“名词+织入+名词+中”的结构。白话的这种双音节结构不需要诗的这种灵活性,这个特殊的句子本来可以用古代汉语甚至白话当中的单音节词来表述,如带织入狗中,狗织入云中,云织入人中,用白话表述也是非常清晰的。和古代的作家相比,用白话写作的现代作家运用排比所带来的韵律变化会更容易实现。
讨论《好的故事》时,在列举事物时用逗号分隔的地方是音乐产生的重要地方,然而将段落和句子划分成短语的方法并没有很好地描述这一点。因为在《好的故事》中所罗列的和透过叙述人的视线反复看见的场景中,并没有一定的规则,不论是有意制造一种声音,表达一种情绪和想法,或者只是为了使读者感到惊讶,他们都可以被安排到不同种类的结构当中。需要注意的是,《好的故事》中列举的事物随着叙述人的视线在移动,例如从“丛树和枯树”到“茅屋,塔,伽蓝”,叙述者的视线好像在抬起,随着树木延伸到地平线。不可否认的是,和视觉相比,作者列举这些事物时更加强调听觉。例如在看到“伽蓝”后,叙述人原本可能会看到僧人,虽然的确看到了,但却是在“晒着的衣裳”后,才引入了“和尚”,“裳”与“尚”构成押韵关系。这种情况不仅常出现在列举中,也常重新排列点缀在诗中。作者似乎在强调这个叙事人梦到的不仅仅只是愿景,而是在脑海中形成并在人与人之间通过语言传递的东西,即梦到的不是一个“好的地方”,而是一个“好的故事”。
对《好的故事》以及所有诗歌而言,诗歌媒介的特征不仅仅体现在听觉韵律,也体现在视觉韵律中。如果创作《野草》的目的之一是创造白话的音乐,那么印在书页上的这些字符就成为准确表达与之相关的声音和想法的说明。《野草》最初发表在《语丝》杂志上,代表了白话文的一种新的印刷和排版趋势。其中最重要的是前面提到的把标点符号运用到诗歌或散文中的做法。在刘半农、胡适、鲁迅等人早期发表于《新青年》的一些重要作品中,人们并不需要通过标点符号来阅读散文诗,他们被用来帮助读者和分类文本,就像清朝时通过加点和下划线来标记名称或书名一样。《语丝》通过引入标点符号并将其置于竖排的文本中间,进一步影响到眼睛扫描阅读这一列文本的时间。鲁迅在《好的故事》中充分利用了这种新的视觉结构,他对标点符号的重视和运用尤为引人注目。特别体现在其中两个标点符号的使用上:一种是将省略号和其他的标点符号结合起来的用法,它显示了省略号表示暂停的性质,但在西方从未见过这种用法。例如,在第五段将罗列的事物先介绍完后,逗号后面是一个省略号,似乎在分析和暗示省略、列举的内容还在继续。第七段的“我就要凝视他们”后,紧跟省略号的是一个句号,表达的或许是叙述者片刻的停顿,记起了当时的情形,又或许是在回想起《好的故事》消散的那一瞬间停下来。尽管在英语当中,省略常常是通过语境来解释的,但鲁迅在使用时还有另外的指导意义,就像管弦乐队的指挥者那样,用有力的、突然的或者渐渐的、流动的手势来示意休息,乐队的沉默给了它额外的意义。第二个可以感知到的特征是,鲁迅使用了特定数量的标点,这使我们很容易把鲁迅的散文诗和其他的散文作品区分开来,因为在《语丝》的页面上,这些句子特别短小。对《好的故事》而言,这一点尤为适用。在传统的诗行外,作者可能在表明其控制阅读速度的愿望,也可能反映了作者“一一看见,一一知道”的创作方法。还有一点疑问是,《好的故事》中韵律的用法和故事本身,和鲁迅所描绘的田园场景与理想社会,感觉之间的融汇与流动,以及最终在黑夜中失去梦这一诗的结尾有什么联系。当我们阅读《好的故事》时,不论是否重视音节,总有一种很强的仪式感,就像祷告时的颂词但却包含了更多含义。然而这种来自音乐语言的影响并不只是词汇或者思想上的,更多的是语气上的。《好的故事》中体现的韵律对感觉经验及其表达的增强在诗歌当中很常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诗歌当中,这些被强调的工具逐渐固定下来成为通行的格律,直到受过教育的听众能够在不给予其他任何内容的情况下将诗识别出来。在散文诗这一体裁被广泛运用的前30年,白话中并没有这样的传统,鲁迅等一些作家对简单引入经典结构和工具并不满意,试图再造一个传统,他在《好的故事》和《野草》中的发明非常有影响力。不仅如此,《野草》的创作同样也是鲁迅对他杂文风格的发展和完善。李欧梵对鲁迅的杂文评价是“一种狂热的创造性……他对僵死的体裁区别规定的蔑视还导致了一种创造性的混合;他的散文中有诗,诗中有散文。”鲁迅在散文诗中建立起的结构可以运用到白话的其他方面。即使只是因为它的形式让他看到了一些值得完成这本集子的东西,鲁迅仍然坚持《野草》的创作是有价值的。
此外,《好的故事》和《野草》的韵律向我们展示了鲁迅的创作美学和他对现代汉语的期待。在《怎么写》这篇文章中,他大体上写到了散文:“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与其防破绽,不如忘破绽。”形式的松散、自由,包容差异与外来事物的能力,对个人意志和客观现实世界的回应:这些形式和语法追求通过散文诗的选择表达出来,并由诗中对文言、白话和绍兴方言的组合变化,不同种类的韵、节奏、标点符号——南腔北调体现出来。《野草》中所倡导的白话的音乐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适应性的、流动的、跨文体的和多变的。即使知道他的尝试逐渐也会成为白话的一种历史,鲁迅似乎没有试图“避免错误”或将诗歌作品完美化,而是寻求更多自由的空间,更多选择来创造意义。鲁迅的创作并不是为了寻找一种永久的解决方案或建立新的经典形式,而是一个首先需要暂时生存下来,并通过“野草的生长”,实现继续创造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