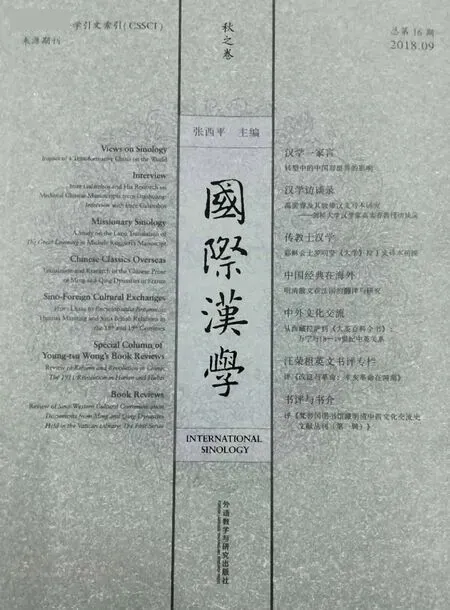《远东杂志》及其所构建的晚清图景*
□
《远东杂志》(The Far East, Illustrated with photographs)是晚清一份重要的英文期刊,该期刊由早期著名的报业人约翰·布莱克(John Reddie Black,1826—1880)创办,在中国、日本以及欧洲流传广泛。杂志上刊载的数量丰富的照片使《远东杂志》脱颖而出,成为西方人认识、见证,并塑造其“中国形象”的重要途径。因此,《远东杂志》上刊载的照片引起了海内外学者极大的兴趣,如泰瑞·贝内特(Terry Bennett)撰写的《中国摄影史:西方摄影师(1861—1879)》(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 Western Photographers 1861—1879)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远东杂志》所刊登的照片及其摄影师在中国摄影史上的地位。①泰瑞·贝内特著,徐婷婷译:《中国摄影史:西方摄影师(1861—1879)》(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 Western Photographers 1861—1879),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3年。此外,论及《远东杂志》照片的还有网上发表的文章《晚清的〈远东〉杂志和它的摄影师》《〈远东〉杂志上的晚清中国》等。此外,萨米尔·科金(Samuel Cocking)的《1869—1909:早期赴日远游者记》(“1869—1909: Philosophies of an Early to Japan’s Shores”)、②Samuel Cocking, “1869—1909: Philosophies of an Early to Japan’s Shores,” Yokohama Rover Semi-Centennial. Yokohama:Japan Gazette Press,1909, p. 39.泰瑞·贝内特的《摄影在日本(1853—1912)》(Photography in Japan 1853—1912)③Terry Bennett, Photography in Japan 1853—1912. Singapore: Tuttle Publishing, 2006, p.149.等著述亦曾谈及约翰·布莱克。但目前学术界关于《远东杂志》的研究仅聚焦于其所刊载的照片,而对《远东杂志》的整体关注则较少。事实上,《远东杂志》不仅刊登了大量在中国实地拍摄的照片,亦译介了相当数量的中国传统文学作品。此外,二者之间又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互文”关系,从而共同构建起新旧交替时期“多面性”的晚清图景。本文即以《远东杂志》,特别是在上海刊印的《远东杂志》新系列为研究对象,拟在厘清《远东杂志》概貌的基础上,探究作为上海侨居地的汉学杂志④关于“侨居地汉学”,可参考王国强:《“侨居地汉学”与十九世纪末英国汉学之发展——以〈中国评论〉为中心的讨论》,《清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51—62页;孙轶旻:《近代上海英文出版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跨文化传播(1867—194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远东杂志》所秉承的独特属性及其所构建的晚清图景。
一、《远东杂志》概况述略
《远东杂志》是苏格兰人约翰·布莱克于1870年5月起在日本创办的英文期刊,起初《远东杂志》以日本为主题,主要介绍和刊载在日本发生的时事、日本的历史、外国人在日本的活动等相关内容。自1876年7月起,因约翰·布莱克迁至上海而对《远东杂志》的内容和主旨做出了较大调整,不仅加入并偏重中国主题,而且将《远东杂志》刊印地从日本横滨转移至中国上海。《远东杂志》,特别是1876年以后在上海刊印的《远东杂志》新系列成为19世纪中叶以中国为主题的一种重要的英文期刊。
1. 《远东杂志》的编辑
《远东杂志》的创办者约翰·布莱克,同时兼任《远东杂志》编辑。他是19世纪著名的报业人,曾先后参与或创办了《日本捷报》(Japan Herald)、《远东杂志》《日新真事志》(Nisshin Shinijshi)、《万国新闻》(The Bankoku Shimbun)及在上海发行长达40年之久的《上海信使》(The Shanghai Mercury),对日本和中国的西文报刊出版业做出了显著贡献。同时,约翰·布莱克还是一名业余摄影师,在足迹所到的东京、横滨、上海等地拍摄了大量珍贵的老照片。
约翰·布莱克创办和编辑的《远东杂志》采用以插页粘贴蛋白照片的方式出版发行,不仅实现了他职业兴趣和业余爱好的完美结合,而且在杂志创办之初即赋予《远东杂志》图文并茂的鲜明特征。《远东杂志》在文字内容之外,穿插有700余幅照片,其中亦包括约翰·布莱克自己拍摄的作品,如“上海西门及城墙”“中元节祭奠亡人的祭台”等。这种照片和文字相辅相成的方式又在一定程度上使《远东杂志》脱颖而出,成为晚清新式期刊的典范。
对摄影的嗜好还促使约翰·布莱克创办了《远东杂志》的附属机构“《远东杂志》艺术代理 ”(The Far East Art Agency)。 该 代 理 于 1876年9月在上海河南路5号正式开业,主要出售约翰·布莱克及其他西方摄影师在上海、北京、厦门等地拍摄的照片或相册,如托马斯·查尔德(Thomas Child, 1841—1898)拍摄的“京城及近郊风物”、圣朱利安·休·爱德华兹(St. Julian Hugh Edwards, 1838—1903)的“厦门和台湾景色”摄影作品等。西方摄影师在中国实地拍摄的照片借此广为流布,《远东杂志》及其艺术代理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晚清中西方视觉文化传播的一种重要途径。
2.《远东杂志》的出版发行情况
《远东杂志》于1870年5月创刊,1878年12月停刊,共刊出12卷100余期。其中,1870年5月至1873年5月为双周刊,1873年7月至1875年10月则调整为月刊。此间,《远东杂志》以日本为主题,在日本横滨刊印。1875年11月至1876年6月期间《远东杂志》暂时停刊,并于1876年7月重新开始发行。复刊后的《远东杂志》新系列仍为月刊,直至1878年12月停刊,《远东杂志》又刊出5卷25期。约翰·布莱克于1879年又开始着手《上海信使》的编辑出版工作,该期刊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并延续了《远东杂志》,加之约翰·布莱克健康状况不佳,于1879年6月赴横滨修养,翌年病逝于日本。《远东杂志》亦因之最终停刊。然而在《远东杂志》新系列复刊期间,约翰·布莱克曾一度侨居上海,他对《远东杂志》的内容做出了较大调整,不仅加入中国主题,而且有意识地增加了文学在杂志中所占的比重,刊印地也从日本横滨转移至中国上海。在上海、香港和东京同时发行,并在北京、宁波、神户、纽约和伦敦等地拥有专门的代理商。(见表1)

表1 《远东杂志》代理商一览(载《远东杂志》1878年1月第1期)
约翰·布莱克期望《远东杂志》成为同时期所有东亚英文报刊中发行量最大、流通最为广泛的英文期刊。自创刊起,《远东杂志》即不负众望,不仅创刊号全部售罄,而且成功获得了读者的钟爱。很多读者将杂志装订成册收藏,甚至愿意额外添价购买杂志副本。随着《远东杂志》的持续刊行,其订阅者亦稳定增长。截至1876年9月,《远东杂志》的订阅者已超过300人次。约翰·布莱克在该期扉页明确指出:“复刊后的第1期(1876年7月)印制了300本,但全部售罄,因此又增订了第2版。”并刊登广告要求订阅者预付资费,以一季度4美元,半年7美元,全年13美元的价格订阅。之后,为了进一步扩展中国和日本之外的市场,约翰·布莱克从1877年5月起将杂志订阅费下调为一季度3.5美金,半年6美金,全年10美金。这无疑又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远东杂志》订阅者的逐步增长,最高或曾逾1,000人次,而且据编者所称,《远东杂志》的绝大多数订阅者会将杂志在朋友间传阅,甚至将杂志寄回本国,所以《远东杂志》的实际读者更为广泛,远远超出了同时期的大多数杂志。
3.《远东杂志》的主要内容和栏目设置
约翰·布莱克创办《远东杂志》的初衷“旨在世界与古老帝国之间建立起美好的情谊”。①John Black, ed., The Far East, Vol. I. 1870, p.1. Reprinted by Yushodo Booksellers LTD. Tokyo, 1965.创刊时,约翰·布莱克正旅居横滨,因此《远东杂志》最初以日本为主题,并试图兼顾中国及其他远东地区。但是,1875年前受客观条件的限制,除刊登了上海河口、中国陵寝、香港公园、广州天坛与市集等寥寥几幅照片之外,《远东杂志》很少涉及中国主题。这种情况随着约翰·布莱克侨居上海而发生了改变。这种调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新系列在维续日本主题的同时,明显向中国主题偏移。如《远东杂志》新系列创刊号采用的几乎全是在中国拍摄的照片,日本照片的数量反而锐减。第二,尽力改善文字,期望为当地文学期刊添一份力。正如约翰·布莱克在复刊号中所指出的,如果有一个人对日本文学感兴趣,那么就会有十个人对中国文学感兴趣。因此,《远东杂志》新系列相应地加大了中国文学的比重,特别是加大了对中国文学译介的力度。
改版后的《远东杂志》新系列以中国为主题,兼顾日本和其他远东地区。内容以照片和文字相辅相成的形式呈现,涉及中国的文学文化、社会习俗、历史地理与时事热点等诸多方面。在约翰·布莱克勤勉推动之下,《远东杂志》吸引了在华西方摄影师、传教士及汉学家并热情赐稿,在上海定期刊印发行,并在对中国和远东地区感兴趣的西方读者间广为流传,从而成为上海侨居地重要的汉学杂志。现如今,《远东杂志》不仅成为现存的研究早期中国和亚洲摄影史的最为珍贵的刊物之一,而且也是探究晚清中西文学文化交流及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的重要史料。
二、《远东杂志》刊载的中国照片与“远东漫游”
得益于摄影技术的发展,约翰·布莱克可以多方搜罗在远东地区实地拍摄的照片为《远东杂志》添加插图。1870年至1878年间,《远东杂志》共刊载700余幅照片,其中与中国相关的照片集中刊载于《远东杂志》新系列,大抵有158幅。这些照片从内容上可以分为民风民俗、社会生活、人物肖像、社会纪实和城市景观五类。
民风民俗类指记录民间风俗、习惯、信仰和庆典活动的照片有18幅。如《远东杂志》新系列1876年第1卷刊载有一组约翰·布莱克和他的团队拍摄的与中国祭奠亡人风俗相关的照片。这组照片拍摄的是每年依照惯例举行的祭奠亡人的仪式。仪式在中元节举行,中国各地都有此习俗,因此,约翰·布莱克得以有机会前去观看,并拍摄照片以作纪念。
社会生活类指反映社会各阶层个人或群体的社会活动和社会现象的照片,有31幅,如“趴活儿的苦力”“中国演员”“乞丐”“田地里的女性劳作者”“中国士兵与长官”“穷人的居所”“流动小吃铺”“湖面上的冰橇”等等,这些照片真实记录了晚清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百态。其中,“湖面上的冰橇”由著名摄影师托马斯·查尔德拍摄,照片中人们头戴冬帽,身着棉衣,以简易的冰橇在冻结的湖面行走,冰橇用人力拉动。
人物肖像类是以人物为拍摄对象的照片,有头像、半身像与全身像等。《远东杂志》新系列刊载的人物肖像照片有23幅,包括裕禄、李鸿章、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及上海商妇、北京仕女、苏州女子等肖像照。其中,李鸿章的照片为全身像,由洛伦佐·F.菲斯勒(L. F. Fisler,1841—1918)摄于1875年。约翰·布莱克认为李鸿章的肖像照定会广受欢迎,因此将这一消息置于《远东杂志》1876年第2期的扉页广而告之,期望借此吸引读者,扩大杂志的流布。
社会纪实类指真实反映具有时效性的人、事、灾难、战争或贫困等社会状况的照片,有10幅。如“日本使臣森有礼访华”“中英混编洋枪队”“宁波‘常胜军’”“昆山水门”“吴淞口‘纽卡斯尔号’”“上海传教士大会”等。其中,“宁波‘常胜军’”由亨利·查尔斯·坎米奇(Henry Charles Cammidge, 1839—1874)拍摄。“常胜军”又名“洋枪队”,是1860年至1864年间由清政府与外国势力联合组建的一支雇佣军,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军队装备了枪炮等先进武器,战斗力极强,故称“常胜军”。
城市景观类包含历史建筑、民居、公园、雕塑等人造景观以及城市夜景、城市鸟瞰等各类和城市相关的照片。《远东杂志》刊载的城市景观类照片数量最多,有76幅,如“上海外滩”“苏州虎丘”“昆山内城”“宁波余姚”“广州市集”“厦门客家土楼”“北京天坛”等等。这些照片涉及上海、苏州、宁波、广州、厦门、台湾等几乎所有通商口岸,见证并再现了当时鲜活的城市景观。
《远东杂志》新系列刊载的照片以城市景观类所占比重最大,而城市景观类中又以上海的照片为数最多。诚如约翰·布莱克在复刊号上所宣称的:“开始发表一系列关于上海的照片,并将继续着力刊登在中国拍摄的照片”,①The Far East, New Series, Vol. I. 1876, p. 1.诸如“上海西门及城墙”“上海豫园”“上海文庙”“上海天主教堂”“上海警察局”“上海海关”“上海跑马场”“上海锚地”“上海公园”“上海综合医院”“上海天文台”等照片在《远东杂志》陆续刊登,一幅幅精心拍摄的黑白照片,将晚清上海的图景定格在永恒的光影之间。如“上海西门及城墙”由约翰·布莱克拍摄,上海西门即仪凤门,照片中的上海城墙乃明朝中叶为抵抗倭寇而建,城墙上张贴着许多告示,城门口还有正在趴活儿的苦力。该城墙于1911年被拆毁,但是这些照片却将那些曾经真实存在过的城市景观纪录封存,从而联通起古今,使今人可以借此窥得历史的雪泥鸿爪,不仅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而且也成为收藏家看重的藏品。
此外,《远东杂志》还通过其艺术代理机构出售一系列以城市景观为主题的照片或相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托马斯·查尔德拍摄的“京城及近郊风物”。这组照片共131幅,每幅照片的尺寸为10英寸×8英寸,以每幅50美分的价格出售。《远东杂志》曾于1877年4月和1878年4月两次刊登这组照片的广告,并附有详细的照片目录,共分为“万寿山风光”“玉泉山风光”“北京古观象台”“北京城墙”“紫禁城”“天坛”“长城南口”和“明陵”8个系列。其中“万寿山风光”包括“佛香阁”“铜亭”“石舫”“十七孔桥”“铜狮子”“铜牛”等19张照片。这些以城市景观为主题的照片随着《远东杂志》及其艺术代理流布开来,不仅为当时的读者提供初步的视觉印象,而且又在某种程度上激发起读者亲临其境的愿望。一旦愿望得以实现,这些照片又能作为游历的导览图。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这些以城市景观为主题的系列照片与19世纪西人的“远东漫游”相互促进,成为中西双方交流的一种独特的文化产物。
所谓19世纪西人的“远东漫游”指的是19世纪欧洲兴起的一股到中国、日本、印度等远东地区漫游的风尚。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18世纪欧洲贵族青年壮游的遗响,但商人、传教士和外交官成为19世纪“远东漫游”的主体,他们或出于商业利益的考量,或受到宣教热情的驱动,或得到外交使命的派遣,纷纷踏上遥远而神秘的古老帝国,开始或辉煌或冒险或新奇或震撼的远东漫游。
19世纪恰逢摄影技术出现并取得迅速发展的时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托马斯·査尔德、洛伦佐·F.菲斯勒、圣朱利安·休·爱德华兹与约翰·布莱克等既掌握了摄影技术,又参与“远东漫游”的西方摄影师得以通过照片纪录“远东漫游”的所见所闻、所经所历。于是“京城及近郊风物”“厦门与台湾景色”等系列照片便应运而生。
三、《远东杂志》译介的中国文学
《远东杂志》译介的中国古典文学囊括了小说、戏曲、诗歌等多种文学作品,成为中国古典文学西译的重要载体。
《远东杂志》刊载的翻译成英文的中国古典小说有《好逑传》《薛刚反唐》《粉妆楼》《俞伯牙摔琴谢知音》《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二度梅》和《说唐后传》。其中,《好逑传》《二度梅》为才子佳人小说,《薛刚反唐》《粉妆楼》和《说唐后传》为英雄传奇,《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和《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为拟话本。就才子佳人和英雄传奇等章回小说来讲,采取的多为节译,或以人物为中心,或以情节为标准,节选相关的内容进行翻译,拟话本则往往省略了入话,仅将正话翻译成英文。
《好逑传》的英译文刊载于《远东杂志》1876年新系列第 1 卷第 3 期,题为“The story of Tit Cheong Yok,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即《铁中玉的故事,译自中文》,为《好逑传》第一回至第六回中与铁中玉相关内容的译文,包括铁中玉智救韦佩、义助水冰心、水冰心俏胆移花、搭救铁中玉于危难及铁中玉水冰心结成连理好逑等故事情节。《二度梅》的英译文刊载于《远东杂志》1878年新系列第4卷第5期,题为“Leong Yok, a Chinese Tale,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即《良玉的故事,译自中文》,译文以梅璧(字良玉)为中心,翻译小说中与之相关的情节内容,该译本比由帛黎(A. ThéophilePiry, 1850—1918)的法译本《二度梅》(Erh-tou-meiou les pruniersmerveilleux)还早两年,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二度梅》最早的西译文。
《薛刚反唐》的英译文刊载于《远东杂志》1876年新系列第 1卷第3期,题为“The Story of Mow Ying, from the Chinese”,即《武曌的故事,译自中文》。该译文是目前所知《薛刚反唐》最早的西译文。《粉妆楼》的英译文载于《远东杂志》1876年新系列第 1卷第5期,题为“The Story of Puk-yok-shong, from the Chinese”,即《柏玉霜的故事,译自中文》,是《粉妆楼》主要故事梗概的翻译,亦是目前所知《粉妆楼》首次被译介成西文。《说唐后传》的英译文载于《远东杂志》1878年新系列第4卷第5期,题为“The Fung Hwang’s Nest”,即《凤凰巢的故事》。译文为《说唐后传》第30回“尉迟恭囚解建都薛仁贵打猎遇帅”、第31回“唐贞观被困凤凰山盖苏文飞刀斩众将”中与“凤凰巢”相关情节的翻译。译者署名为R。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与《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的英译文刊载于《远东杂志》1877年新系列第3卷第2期与第5期,由费理雅(Lydia Mary Fay, ca. 1804—1878)翻译。前者省略了“管鲍相交”的入话,而着力将“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正话译成英文。后者亦删除了“朱买臣妻子自休”的入话,直接翻译正话。二者均选译自明末抱瓮老人辑录的话本选集《今古奇观》。
《远东杂志》译介的中国戏曲为《刘玄德醉走黄鹤楼》,由司图特(G. C. Stent, 1833—1884)翻译成英文,译文载于《远东杂志》1876年新系列第 1 卷第 3 期,题为“The Yellow Stork Tower,A Chinese Historical Drama, in Two Acts”,即《黄鹤楼,一部两幕的历史剧》。译文讲述了赤壁大战后,周瑜在黄鹤楼设宴款待刘备,企图伺机擒获刘备,幸得诸葛亮神机妙算,命姜维改扮渔翁,救刘备脱险的故事。
《远东杂志》刊载的翻译成英文的中国诗歌有署名为W. R. K.翻译的白居易之《琵琶行》,①The Far East, New Series, Vol. V, 1878, p. 108—110.以及司图特翻译的《夫人游街》(Dame Kuo’s Visit to His-ting Fair)、②Ibid., Vol. I, 1876, p. 15—18.《慎勿与寡妇成婚》(Don’t Marry a Widow)、③Ibid., p. 34—37.《反语》(Inverted Facts)。④Ibid., p. 123—125.这三首滑稽感伤的诗歌或译自民歌,具体底本不详。
上述这些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文虽然译自中文,却又或多或少地对中文原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编,这种改编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故事单元的重新组合。如《薛刚反唐》由清代如莲居士撰写,全书共100回,主要描述薛刚推翻武周政权,中兴大唐的故事。《远东杂志》所刊《薛刚反唐》英译文则以武曌为中心人物,节选与之相关的情节内容,并相应地对故事单元做出调整。译文共分为三个章节。第一章为《薛刚反唐》第一回至第五回的节译。译文跳过第一回中“两辽王安葬白虎山”的情节,直接以“狄仁杰拒色临清店”的情节开篇,以武曌为中心人物,描写了武曌从入宫至贵为中宫之主的故事。第二章为《薛刚反唐》第6、9、10、11、12、15、18、19、20、21、22、23、24、25、26 回 的节译。译文围绕薛刚,叙述了薛刚大闹花灯、踢死皇子、惊崩圣驾后畏罪潜逃,在卧龙山与峦英结亲,后因祭奠铁丘坟,被朝廷缉缴、投奔薛义被囚、押解途中获救的故事。第三章为《薛刚反唐 》 第36、37、38、39、40、54、60、61、100回的节译。这段译文以李旦为中心,讲述了李旦避难通州,与胡凤娇联姻,又联合忠臣义士兴兵攻入京城的故事。虽然译文的第二、三章分别以薛刚和李旦为中心,然而,“武曌”始终作为其敌对面而贯穿并衔接起全文,而《黄鹤楼》英译文则将之改写为一部两幕的历史剧。
第二,人物形象的动态改写。如《薛刚反唐》译文不仅将小说的中心人物从“薛刚”改为“武曌”,且译文所塑造的“武曌”的形象也和中文小说出现了偏离和不同。译文既有意识地将小说里风流淫冶的武曌改写为译文中纯洁可爱的武曌,而且又添加笔墨详细勾勒出武曌从温婉宜人到暴戾残忍的性格转变。如:
Mow Ying have a son. On hearing of the birth of the young prince, the joy of Kow Chong exceeded all reasoned bounds. He promoted all the relations of Mow Ying to the highest ranks;and no longer held an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true Empress. All this acted very prejudicially on Mow King. She had been a good, gentle woman,and had captivated the two Emperors, father and son, as she would have fascinated any one with whom her lot was cast, by her virtues as well as by her genius and her loveliness. But now ambition and jealousy took possession of her,and she began to cherish against the Empress.①Ibid., New Series, Vol. I, 1876, p. 54—55.(武曌诞下一子。听到小皇子出生的消息,高宗喜不自胜。他赐封武曌的所有亲属,并且不再召见皇后。这一切却引发了武曌的偏执。她曾经是善良、温柔的女子,德行、才能和美丽为她赢得了父子两位帝王的爱情。但是,如今野心和嫉妒控制了她,武曌开始设法与皇后为敌。)
译文中武曌从“善良、温柔的女子”变为“被野心和嫉妒控制的女子”,谱画出武曌性格发展变化的轨迹,并强调境遇、地位和时机等因素对一个人性情转变的激发作用,从而呈现出曲线的动态的“武曌形象”。
第三,剔除有涉艳情的描写。受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语言环境的影响,《远东杂志》往往剔除了译文中有涉艳情的描写。如《薛刚反唐》有颇多涉于艳情的描写,或以之塑造武曌淫冶的性格,或描摹武三思、韦后等人的荒淫,或通过对美色诱惑的抵制而赞扬狄仁杰的高尚品质等。译文则往往直接删去小说中的艳情描写,尤其是与武曌有关的私情,从而将武曌塑造成纯洁美丽的女子。另外,虽然译文保留了《薛刚反唐》第一回中“狄仁杰拒色临清店”的情节,却将女子色诱狄仁杰的意图改为单纯的请求庇护,亦将小说里女子进入房间后,对狄仁杰的挑逗及狄仁杰三番五次的挣扎改为译文里狄仁杰在门口态度坚定地拒绝女子,在情节和语言上有意净化中文,剔除小说里关于艳情的描写。
第四,加入西化的元素。将西方的行为规范、婚姻观念、地理知识与先进武器等嵌入中文的故事情节,在一定程度上连接中西文化,消弭二者之间的隔阂与距离。如《粉妆楼》和《二度梅》的译文皆将中文里的“一夫多妻”改为“一夫一妻”,这无疑更符合西方人的婚姻观念。又如原文:
小的适在城外北平山梅花岭下经过,真正是雪白梅香,十分可爱!我们长安这些王孙公子,都去游玩。有挑酒肴前去赏雪观梅的,有牵犬架鹰前去兴围打猎的,一路车马纷纷,游人甚众。①竹溪山人:《粉妆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页。
译文:
After a time they went out to see the people amuse themselves in rolling the snow into huge balls and making gigantic snow man or other effigies with it.②The Far East, New Series, Vol. II, 1877, p. 116.(不久,他们出去看雪中游玩的人们,有的在滚雪球,有的在堆雪人或做雪雕。)
译文将中国传统的“赏雪观梅”“兴围打猎”的雪中娱情玩兴的活动改为“滚雪球”“堆雪人”等为西人喜闻乐见的雪中娱乐。又如原文:
……观望良久,猛得一阵怪风,震摇山岳。风过处,山岙之中跳出一只黑虎,舞爪张牙,好生厉害。二位公子大喜。大公子遂向飞鱼袋内取弓,走兽壶中拔箭,拽满弓,搭上箭,喝声“着”,飕的一箭,往那黑虎顶上飞来,好神箭,正中黑虎顶上!那虎吼了一声,带箭就跑。二公子道:“那里走!”一齐拍马追来。只见那黑虎走如飞风,一气赶了二里多路,追到山中,忽见一道金光,那虎就不见了……在四下看时,原来元坛神圣旁边,泥塑的一只黑虎,正是方才射的那虎,虎脑前尚有箭射的一块形迹。③《粉妆楼》,第6—7页。
译文:
One of them had carelessly seized his matchlock as he passed out; and as they crossed a field, seeing, as he believed, a tiger prowling at no great distance from them, fried at it, and caused it to run into a temple close by. They followed, but on entering saw nothing inside but a wooden tiger which had the appearance of having been shot by a gun.④The Far East, New Series, Vol. II. 1877, p. 116.(他们经过时,看到一只老虎在不远处游走,一人掏出火枪,朝老虎射击。老虎逃向附近的寺庙。二人追踪而至,庙里只有一只木虎,虎面却有一块被枪击的痕迹。)
译文不仅将小说里的“泥虎”改为“木虎”,而且将罗灿射虎的武器,从“箭”演进为“火枪”,将原文中主人公使用的比较落伍的武器改成19世纪西人熟知并使用的先进兵器。
综上所述,通过翻译和适度的改编,《远东杂志》陆续将《好逑传》《二度梅》《黄鹤楼》《琵琶行》等十余部中国文学作品介绍给西方读者。其中,《薛刚反唐》《粉妆楼》《二度梅》《说唐全传》《黄鹤楼》等中国小说戏曲是首次被翻译成西文。《远东杂志》作为中国文学西译的重要载体,不仅丰富了中国古典小说西译的篇目,而且促进了中国古典文学的西译进程。
四、“互文”与“多面”:《远东杂志》所构建的晚清图景
《远东杂志》新系列不仅刊登了大量在中国实地拍摄的照片,成为早期中国本土出版的最有代表性的画报之一,而且译介了相当数量的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促进了中国古典文学的西译进程。此外,二者之间又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互文”关系,这种互文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图文并茂,即图文对应,相互阐述。《远东杂志》卷首目录分为文字目录和照片目录两部分,而照片目录又将照片出现的页码和相应文字描述的页码并置。这种独特的编排方式体现了《远东杂志》以照片和文字相互映衬又相互阐述的理念,并成为《远东杂志》一以贯之的体例。如《远东杂志》新系列卷一所刊载的元杂剧《黄鹤楼》译文中即穿插有一幅中国戏曲演员的照片,照片附有文字说明,指出中间的演员扮演蜀帝刘备,其左右两侧的演员则分别扮演孔明和赵子龙。三人端坐于舞台正中,刘备身着蟒袍,诸葛孔明手执羽扇,赵子龙则白面无髯,做武生装扮。这幅照片与译文相呼应,生动再现了中国戏曲的舞台表演艺术。《远东杂志》新系列卷三所刊载《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的译文中附有两幅照片,其中一幅为北京仕女,照片中盛装女子倚立于花架一侧,花架上放置着花瓶、茶杯、书册和烟枪。编者有意将这幅带有典型中国元素的仕女照片衍射小说女主角的形象,使读者对金玉奴生出一种直观而鲜活的视觉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照片又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插图功用。因此,可将之视为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一种新式的独特的插图形式。
第二,文实互补,即文学书写与照片纪实互为注脚,又相互补充。如《远东杂志》编辑约翰·布莱克曾特地派遣一名中国摄影师前往扬子江拍摄照片,经过长达七个月的等待,终于收获若干照片。扬子江美轮美奂的风光本能孕育出许多照片佳作,但是中国摄影师却不善选景,拍摄的照片质量颇令人失望。因此,《远东杂志》仅挑选刊登了少数几张扬子江照片,如“扬子江上游重庆”“杨子江上之安庆”等。这些照片真实记录了扬子江当时的风光,却偏向于一种静态的客观的再现。相比之下,《俞伯牙摔琴谢知音》译文中对扬子江风光的描绘则更趋于一种动态的抒情的描写:
楚王特赐恩待,命俞伯牙水路返回,并赠以大船二只,使其得以悠然欣赏扬子江两岸的风光与层峦叠翠的青山……扬帆起航时,和风宜人,船首迎着扬子江的碧浪而进,两岸美景层出迭起,俞伯牙及随从瞬间忘却了时间和距离。俞伯牙仿佛回到了孩提时代,驾着一叶小舟崎岖蜿蜒于波光粼粼的江面,远山如岱,气势磅礴,令人敬畏。”①The Far East, New Series, Vol. III, 1877, pp. 18—19. 小说原文为:“张一片风帆,凌千层碧浪,看不尽遥山叠翠,远水澄清。”译者在翻译时有意识地进行了增饰。
这段文字着眼点在顺流而下、不断变化着的两岸景色及其为观者所带来的内心愉悦。文字和图片一动一静,既有客观纪实,又有主观抒情,二者之间相互印证,又互为补充,有助于捕捉完满又立体的扬子江景色。又如《远东杂志》1877年新系列第四卷刊载有一幅中国乞丐的照片。照片中的乞丐是持有官方许可证的,依旧衣衫褴褛,境况窘迫。而《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的译文则讲述了即便乞丐的物质条件有极大提升,甚至变得富甲一方,却仍然难免受到士人根深蒂固的蔑视。士人与乞丐之间有如云泥之别,有着难以跨越的鸿沟。乞丐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这种身份地位世代沿袭,延及子孙。小说中的金玉奴正是因为乞丐女儿的身份遭到莫稽的薄情抛弃,而只有金玉奴被淮西转运使收为义女,获得了新的社会地位时,才能与莫稽再结连理。照片真实记录了乞丐穷困潦倒的物质状况,小说译文则着重叙写乞丐卑微沉沦的社会地位。二者之间相互注释,又互为补充,有益于形成对乞丐较为全面而整体的理解。
《远东杂志》刊载的中国照片与其译介的中国文学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既图文并茂、又文实互补的“互文”关系。而这种“互文”的关系又促使二者相互融合,相互支撑,共同构建起新旧交替时期“多面性”的晚清图景。
首先,这种“多面性”的晚清图景指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是一种“全景式”的晚清各阶级社会生活的图景。就政治方面而言,《远东杂志》1876年新系列卷一刊登了李鸿章、威妥玛和森有礼的肖像照,他们都是活跃在当时远东政坛的风云人物,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威妥玛为驻华英国公使,他们作为中英双方的代表正在就中英和谈进行会晤。森有礼为日本使臣,访华期间曾与李鸿章就朝鲜局势进行磋商。这些照片及其相对应的文字追踪报道了当时的政治热点。就经济生活而言,《远东杂志》新系列先后刊载有“上海茶馆”“中国商铺”“洋泾浜的中国店铺”“流动小吃摊”“台湾的制糖厂”“出售柳编品与席子的店铺”“广州的外国工场”等照片,生动再现了晚清上海、台湾、广州等通商口岸的经济场景。就军事方面而言,《远东杂志》刊载有“中英混编洋枪队”“宁波‘常胜军’”“昆山水门”“中国军官”等照片。其中,“昆山水门”照片中,城墙上的损坏清晰可见。这些损坏即是1863年戈登率领常胜军攻打昆山所造成的。就文化生活而言,《远东杂志》所刊载的“上海文庙”“亲王遗孀的书法作品”“中国木刻画”“中国戏台子”等照片及其文字说明,较为详细地阐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宗教方面而言,《远东杂志》刊登了一系列与中元节祭祀相关的照片,诸如“中元节祭奠亡人的年祭”“中元节祭奠亡人的祭台”“Fêng的葬礼”等,并以相应文字介绍了中国的祖先崇拜与殡葬习俗。
《远东杂志》所构建的“多面性”晚清图景不仅在横向上渗入晚清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在纵向上贯通了晚清社会的各个阶层。《远东杂志》一方面报道了李鸿章、裕禄、安庆道台等朝廷贵介叱咤风云的生活;另一方面通过《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好逑传》《二度梅》等小说译介描画出中国传统士人的风雅生活;而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远东杂志》十分关注平民大众的市井生活。如约翰·布莱克拍摄的著名的“上海西门”,照片中城门前衣衫简朴的独轮车夫正在趴活儿。托马斯·查尔德拍摄的“湖面上的冰橇”,照片中的冰橇则由苦力拉行。其他诸如“中国独轮车”“流动鞋铺”“趴活儿的苦力”“作针线的女人”“乞丐”“穷人的居所”等照片,真实摹画出晚清市井生活的百态。此外,《远东杂志》又不仅仅局限于叙写男性的社会生活,而且亦深入到女性的闺阁世界。如“上海商妇”“宁波女子”“广州仕女”“年轻的苏州女子”等照片,呈现出晚清女子的生活图景。
其次,《远东杂志》所构建的晚清图景既有传统的一面,也有落后的一面,同时又有试图革新的一面,描绘出19世纪后半叶新旧交替时期“多面性”的晚清图景。关于传统的一面,多表现为具有典型中国元素的标签式题材。这种标签式题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先行者所塑造的“中国形象”的影响,纷纷将镜头聚焦于宝塔、亭台、瓷器、香炉等具有典型中国元素的事物,形成了一系列被多次拍摄或叙写的标签式题材。如《远东杂志》刊登的宝塔照片就有“龙华塔”“苏州宝塔”“北京大理石宝塔”与“文昌宝塔”四幅,也不乏诸如“苏州虎丘”“永乐大帝陵寝”“北京天坛”“中国长城”等典型的人文景观。此外,《远东杂志》还通过《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小说译介讲述了中国传统的器物文化,特别是士人对古琴的痴迷。译文不仅将俞伯牙和钟子期因古琴而谱就的千古高谊娓娓道来,而且不厌其烦地将古琴的起源及其六忌、七不弹、八绝等与古琴相关的艰深知识都翻译成英文,从而彰显了古琴对中国传统士人的魔力,古琴也因之成为传统高雅文化的典型代表。
关于落后的一面,则重点突出了吸食鸦片、女子裹足与迷信活动等晚清社会的陋习。《远东杂志》1878年新系列卷4刊登有一幅“吸食鸦片”的照片,并撰文披露了晚清社会普遍弥漫的吸食鸦片的恶习及其对人的精神和身体造成的双重伤害。又《远东杂志》1877年新系列卷2登有一幅“三寸金莲”的照片,“三寸金莲”特指中国女子裹足而形成小脚,其实是一种残疾,反映了中国病态的审美趣味。而《远东杂志》刊载的仕女肖像照片中,亦时可窥见三寸金莲,如“年轻的苏州女子”,照片中年轻的女子左手执书,右手持扇侧身端坐于桌子旁,桌脚边一双三寸金莲隐约可见。桌子上遵其要求摆放着花瓶、茶杯及其日常使用的香水瓶和纤长的烟枪。此外,约翰·布莱克在其《方兴未艾的中日文学研究》一文中活灵活现地介绍了民间盛行的扶乩和通神这两种迷信活动。
关于晚清社会试图革新的一面,《远东杂志》并没有忽视,如《远东杂志》报道了中国首条铁路的通行:“(1876年)6月30日,吴淞铁路上海段通车……这是中国第一条营运的铁路,它满载乘客,于午后五点半驶离上海站……车上载有约150人,皆为受到邀请的淑女和绅士。”①The Far East, New Series, Vol. I, 1876, p. 48.而且威廉· 桑 德 斯(William Thomas Saunders,1832—1892)和洛伦佐·F.菲斯勒还在火车行驶前,为大家拍照留念,记录下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远东杂志》还刊载有“上海法国神父天文台”“上海综合医院”“中国学校”等照片,反映了清廷在内力和外力的共同激励下,引进先进的科技,借鉴西方的医疗机构,吸收新的教育理念进行革新的努力。传统、落后与革新的种种面貌交织融汇出新旧革新时期“多面性”的晚清图景。
综上所述,作为上海侨居地重要的汉学期刊,《远东杂志》不仅具有时效性与大众性等近代期刊的一般特征,而且凭借其地缘优势,一方面可以在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另一方面,又能使用西方先进的摄影技术,《远东杂志》因之刊登了大量在中国实地拍摄的照片。同时,《远东杂志》还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学的译介,《薛刚反唐》《二度梅》《说岳后传》《黄鹤楼》等中国小说戏曲通过《远东杂志》首次进入西方人的视野,从而促进了中国古典文学的西译进程。此外,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远东杂志》所刊载的照片与译介的文学作品又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图文并茂、文实互补的“互文”关系。这种“互文”不仅赋予《远东杂志》图文相得益彰的显著特征,使《远东杂志》在同时代的期刊中脱颖而出,成为晚清新式期刊的典范,又共同构建起新旧交替时期“多面性”的晚清图景。
意大利汉学家焦仰先(Fortunato Margiotti)
意大利籍方济各修会会士焦仰先(Fortunato Margiotti, 1912—1990)是研究中国传教史的专家,国内外有关他的研究,至今未得见,甚为遗憾。焦仰先神父曾与他人一道,编辑整理了不少西班牙方济各会士的书信。1958年,他在罗马出版了《山西天主教史:从起源到1738年》(Il cattolicismo nello Shansi dalle origini al 1738)。这是一部有关山西天主教史的重要著作,研究的范围从传说中的关羽拥抱天主教到方济各会士助理宗座代牧弗朗切斯科·玛利亚·加雷托(Francesco Maria Garetto)于 1738年在山西逝世为止,内容十分丰富,叙述了天主教传教士入晋传教之艰难过程,也有大量篇幅用于讨论当地文人,特别是段氏和韩氏两大家族,如何帮助西方传教士在山西开展天主教传教事业。
在结构上,《山西天主教史:从起源到1738年》一书的设计非常清晰和明了,它包括了“索引”(Indice)、正文和附录。其中,正文为全书之主体,分为四部分,分别是:“传教史”(Storia dell’Apostolato)、“传教方法”(Metodo di Apostolato)、“传教阻碍”(Ostacoli dell’Apostolato)和“传教成果”(Frutti di Apostolato)。焦仰先神父尽管是方济各修会的会士,但在“传教史”部分,则将大量笔墨给予了在山西传教的耶稣会士,比如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金尼阁 (Nicolas Trigault,1577—1628)和高一志(Alfonso Vagnone,1568—1640)在该地先后传教的经历。作者通过梳理众多的西文年报和信件,建构了这段基于西方记忆的历史,对于补充彼时的中国史研究,殊为可贵。
作者的“附录”设计也颇为用心。在文献选择方面,作者选取了不少中文史料,并将其译成意大利文,以飨欧洲读者,而在文末所附的两份列表:“山西省天主教共同体”(Comunità cristiane dello Shansi)和“在晋传教士(1620—1738)”(Missionari dello Shansi, 1620—1738),尽管篇幅短小,但为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了查阅的捷径。(木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