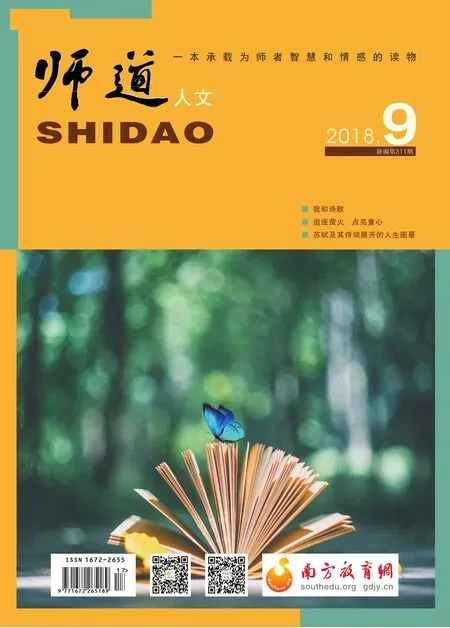苏轼及其诗词展开的人生图景
武 琳
就像传记电影 《黄金时代》《挚爱梵高》的叙事那样,我们也来用倒叙的镜头隔着这近千年的时光瞻观这位伟大的文人。
从一段公案讲起:
据苏辙 《墓志铭》记载,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 (公元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病热转剧。
临危,维琳方丈叩耳大声说:“端明宜勿忘西方!”
“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苏轼回答。
钱世雄也凑近耳畔大声说:“固先生平时履践,至此更须着力。”
轼答曰: “着力即差。”
世雄还要再问: “端明平生学佛,今日如何?”
轼曰: “此语亦不受。”
语绝而逝!
也许命运就是这样,当年苏轼奔波劳徙,前往岭南瘴疠之地,历尽艰辛尚安然无事,而当人生发生转机,在家人、朋友和百姓的一路护拥之下北还,却不幸止于常州,留给后人无尽的叹惋。
苏轼内心或许也闪过不甘,这是人之常情,但对于一个早已看透命运的人来说,当死亡降临的刹那,就像当初直面诸多坎坷一样,淡然从容的人生态度从未改变。苏子坦然平静,随性无为,临命不苛求 “外力”。
一个人,怎样死无所谓,重要的是如何活着。从当年初出眉山的那个才华横溢的少年,到后来旷达乐天,依然执着民生不忘初心的老人,苏轼的一生高低起伏,急流浅滩,历经辉煌磨难,苦中寻乐,天然绚烂。
苏辙 《栾城集·伯父墓表》中记述: “苏氏自唐始家于眉,阅五季皆不出仕。盖非独苏氏也,凡眉之士大夫,修身于家,为政于乡,皆莫肯仕者。”不求仕途似乎是偏居于眉山的士大夫后裔的传统。但自北宋开国后,贬抑武人参政,要建立一个士大夫政治制度。重视科举,提倡读书,读书人登仕成为时代风尚。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中年奋发的苏洵带着两个儿子出蜀进京了。
苏轼21岁进士及第,并为主考官欧阳修所激赏;后又应直言极谏策问,25岁制科入第三等,名噪京城。少年得意,踌躇满志。但苏轼骨子里终究是个文人,他不属于朝堂。26岁任凤翔签判跻身官场之后,苏轼的人生便充满了变数。
新党变法期间,他上神宗书《谏买浙灯状》,批评官府 “以耳目不急之玩,夺民口体必用之资”,后再上神宗书,论朝廷得失。面对有损民生的政治现实,苏轼有着与权力对垒的浩然之气。强烈的正义感和是非之心在最现实的政治社会必然是异端,苏轼自知不能见容于朝堂,主动避祸,力求外补,出为杭州通判,后改知湖州。但四月到任,七月就被御史李定等人罗织罪名弹劾,苏轼终究没能逃脱党争小人的攻讦。

苏轼 《黄州寒食诗贴》
元丰二年即公元1079年,苏轼经历了人生第一次大的劫难——“乌台诗案”,之后被贬官黄州 (今湖北黄冈)。苦难的影响是复杂的,它折磨人的同时也成就了人生向更高境界的蜕变,黄州五年,让苏轼走向了苏东坡。
数年之后虽又被起用,诏回京城,授予官职,有了元祐八年的得承恩宠,但在新旧党争的裹挟中,苏轼早有归意。无奈,一代文宗的名望让他终不能隔离于争斗之外。在哲宗对元祐党人的清洗围剿中,绍圣元年 (公元1094年),苏轼经历了人生第二次大的劫难,以 “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知英州。对这次劫难,苏轼和当年去黄州的心境已大不相同, “累岁宠荣,固已太过;此时窜责,诚所宜然”, “瘴疠炎陬,去若清凉之地”,恳切洒脱,外物已然放下。即便如此,那帮奸佞之徒对年已衰暮的诗人也没有丝毫的怜悯,利用一切可能置他于死地。英州贬所未至,八月再贬惠州。绍圣四年再贬儋州。七年的外放流离之后,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诗人奉诏北归,止于常州。
王国维在 《文学小言》中写道: “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文章者,殆未之有也。”给东坡作传的林语堂先生也曾说:“在今天看来,我觉得苏东坡伟大的人格,比中国其他文人的人格,更为鲜明突出。”
历代文人对苏轼的尊崇,让东坡居士成为了一个几乎不可逾越的标杆典范。他的才情,他的风骨,无不令人景仰膜拜。即便在人生低谷,他也不曾抱怨、抑郁、自怜,反而定下心来检省自身,反思自身鲁莽无知之不足。无论多么艰难的时刻,苏轼总能安放自己的心灵,让郁闷困蹇得以消散。
其实看一个人的品性为人,他人亦是参照坐标。朋友故交,前辈后学,兄弟子嗣,在与他人往来的映照中,我们可以了解一个更加丰富立体的苏子形象。流放儋州,他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尚有此身付与造物者,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故人知之,免忧煎”,透露的都是豁达与豪迈;提携后进,不光在学问器识上点拨,还会在物质上周济,他赠予门生李廌马匹,还甚为体贴仁厚、措辞委婉地写了《马券》,方便对方买卖而不伤自尊;即便是曾经陷他于死地的政敌章惇落难岭南,他也不曾落井下石,而是施之与温暖的体恤和安慰。
苏轼一生坎坷,所幸身边总是有温暖人情的滋养。这也缘自他宽厚豁达、乐观自适的人格魅力和泛爱世人的秉性。苏轼自言 “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所以每到一处,总有新交补充故友。在苏轼一生众多的亲朋故交中,有一个人是绕不过去的,那就是其胞弟——苏辙(人称小苏)。
当年苏洵为两个儿子取学名一为轼,一为辙。精明的父亲是希望苏轼可以学习蕴藏才华, “若无所为”,不受这浊世的伤害;苏辙敦厚朴实,能够有用于世而不必居其名。
父兄三人创立了苏氏蜀学,这家学本就深厚。想那苏轼苏辙兄弟仁宗朝嘉祐二年同年进士,在当时已是众人口中了不起的谈资,连苏洵这个做父亲的都感慨二子登科如“拾芥”般容易。等到了嘉祐六年制科 (“六科举士”,北宋天子特诏的特试,须由大臣奏荐,天子亲自策问拔擢,制科得隽者比出身进士更为矜贵),同年应试四人中取三人,苏氏兄弟二人占了两席,即便是在文才济济的北宋,苏氏也星光璀璨,成为世人仰望的门庭。
苏轼明敏好文,旷达恣肆,才华横溢,接了欧阳修的衣钵,为一代文宗。一生坎坷大半缘由是其光芒四射的才名太盛。苏辙静厚内敛,性情沉静。文章气势宏大淡泊,文采略逊于兄长但也能独树一帜,保有自己的锋芒。当年苏辙制科的对策文章,因 “极言尽谏,语甚切直”差点被考官以 “出言不逊”黜落,多亏司马光爱才,想尽办法奏报给皇上才得免。后人赞他的文赋 “俊秀高超,大致与苏轼相近”。其文如其人,论事精确,修辞简洁,晚年更加不求文工,但求明理,处事低调,不愿人知之。恰恰是苏辙 “临变故纷纭,举止安徐若素”的谨慎稳重的性格每每为命途多舛的兄长托底。苏轼乌台诗案落难时,苏辙 “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这等奋不顾己也是难得。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苏的坎坷人生也多半是心甘情愿受兄长拖累。 《宋史·苏辙传》中称 “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
苏轼从政四十年,多少受出身蜀地的影响,在朝堂多被孤立,但好在有一个好兄弟风雨陪侍。他们虽性格迥异,但彼此之间的情谊不仅是兄弟的血脉亲情,还是志趣相投的相知相遇,是完全彻底的交托信任,是毫无怨忿的护持给予。“四海多兄弟,愿得一子由”,苏轼对弟弟的倚重可见一斑。
兄弟自小在老家眉山,无忧无虑,闲居读书,都向往 “水竹村居”的日子,即便初至京师,尚在应举阶段,就已思想及早退休还乡。无奈家业凋零不得不求仕谋生,为人子须尽了光耀门庭的责任才行。当年在汴河南岸的怀远驿刻苦读书备试制科的时候,兄弟曾做“雪堂风雨夜,已作对床声”的约定,待尽了义务,寻一处景丽人淳的乡野安度余生。但可惜造化弄人,兄弟二人最终未能实践这四十年的宿约,甚至雷州一别四载至苏轼临终,二人都未及见最后一面,弟为兄撰墓志铭成为他们人生最后的交汇点。在二人坎坷的仕宦生涯中,不能共处久待,诗文应和是兄弟互通情谊、寄意相思的主要方式,历史上很少有哪家兄弟之间在精神上有这份相知了。
观仰一个人,体察他一生行走的姿态,作品又恰恰是另外一个切入点。作品是人生的真实记录和映射,是作者某一阶段的情感、心迹。人生是发展的、变幻的,不同时期的作品反映了作者人生变化的轨迹,有理性抑或感性的生命底色的呼应。在诗中,诗人书写自己的性灵,诗人与朋友亲人应和。一生虽为文所累,但仍笔耕不辍,诗人留存在作品中的生命气息与光泽才是永恒之物。
让我们把镜头一帧一帧地扫过去,竭尽我们的想象去展开、还原诗人人生的零星图景。
其一 《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
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
路长人困蹇驴嘶。
本诗写于嘉祐六年 (公元1061年)冬,苏轼初仕凤翔,苏辙送至郑州分手,回京侍父。苏辙与苏轼当年赴京应试路经渑池,同住县中僧舍,同于壁上题诗。如今苏轼赴凤翔做官,又要经过渑池,因而苏辙作 《怀渑池寄子瞻兄》寄怀:
相携话别郑原上,
共道长途怕雪泥。
归骑还寻大梁陌,
行人已度古崤西。
曾为县吏民知否?
旧宿僧房壁共题。
遥想独游佳味少,
无方骓马但鸣嘶。
苏轼和诗的才情和对人生的思考深度是明显高于苏辙原作的。诗中透露出对人生变幻的感慨:不过如鸿鸟在雪地上留下的爪印,终究是离散无踪迹,连五年前兄弟题壁的奉闲精舍也僧死壁颓,无字迹可寻。这人生的孤旅才刚刚开始,兄弟俩二十余年的生命中未曾有过这样的分离,苏轼心中的茫然怅惘可以想见。末联回忆了 “往岁马死于二陵,骑驴至渑池”的困窘,是否也昭示了兄弟二人日后崎岖的人生路途?
其二 《琴诗》
若言琴上有琴声,
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
何不于君指上听?
宋神宗元丰四年 (公元1081年)作于黄州。苏轼自认此诗为偈语。诗作体现了诗人探究事物真谛的兴趣。诗人思考于黄州贬所。困境最能考验人,泥泞之中如何自处,如何生存,如何寻找人生可以依傍的价值和乐趣。
其三 《东坡》
雨洗东坡月色清,
市人行尽野人行。
莫嫌荦确坡头路,
自爱铿然曳杖声。
写于元丰六年 (公元1083年)。东坡是黄州的一个地名。老朋友马正卿看不过苏轼生活困窘,帮他从郡里申请下来一片撂荒的旧营地,供其一家躬耕以解决生计。诗人在此不只经营禾稼果木,还筑起居室——雪堂,亲自写了“东坡雪堂”四个大字,并自称东坡居士了。
从 “野人”身上感受到一股幽人守志僻处而自足于怀的味道。可贵的精神与客观风物交融为一,句句均是言景,又无一句不是言情,寓情于景,托意深远。同一时期,诗人有 《定风波》词,写在风雨中的神态: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又有 “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虽是咏定惠院海棠的,实际是借海棠自咏身世。
其四 《别子由三首 (兼别迟)》
(一)
知君念我欲别难,
我今此别非他日。
风里杨花虽未定,
雨中荷叶终不湿。
三年磨我费百书,
一见何止得双璧。
愿君亦莫叹留滞,
六十小劫风雨疾。
(二)
先君昔爱洛城居,
我今亦过嵩山麓。
水南卜宅吾岂敢,
试向伊川买修竹。
又闻缑山好泉眼,
傍市穿林泻冰玉。
遥想茅轩照水开,
两翁相对清如鹄。
(三)
两翁归隐非难事,
惟要传家好儿子。
忆昔汝翁如汝长,
笔头一落三千字。
世人闻此皆大笑,
慎勿生儿两翁似。
不知樗栎荐明堂,
何似盐车压千里。
元丰七年 (公元1084年)端午节,苏轼移官汝州任团练副使,从九江登庐山赴筠州探弟,在筠州驻留十日时所写。
前两首,兄弟不忍相别,聊以安慰的是,此别非为他,而是北上汝颍故地。先君苏洵最爱洛阳,我这次要到嵩山去,要到汝水伊川之间买田卜宅,今后我们兄弟二人相扶相持,归隐于此,遥想期待一下:清澈的水池映照着茅轩,轩里坐着两个清瘦如鹄的老翁,谈诗论文喝酒品茶,那日子多逍遥洒脱!最后一首充满了自嘲调侃:归隐倒不是难事,重要的是诗书传家要有好儿子。子侄们,想当年,你们的老爸如你们这般大时,文思如泉涌呀,下笔就三千字。世人听说后都大笑,生儿子可千万别像那苏氏兄弟,潦倒落魄。甚至诗句终了还大发牢骚,那些如樗栎般的无用之才都被推荐到朝廷,位高权重,我们兄弟这般千里马却还在被盐车所累,疲惫不堪。
其五 《洗儿戏作》
人皆养子望聪明,
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
无灾无难到公卿。
也作于元丰六年 (公元1083年),看起来观点荒谬,实际上是反讽,沉痛愤懑,自我揶揄,是饱蘸泪水的 “游戏之作”,因为在苏轼看来,当时的公卿宰相,都是一些只会保持权位,毫无治国才具的人。虽然后人对此诗褒贬不一,我却从中看见一个充满温情的父亲。
其六 《和陶饮酒二十首其一》
道丧士失已,出语辄不情。
江左风流人,醉中亦求名。
渊明独清真,谈笑得此生。
身如受风竹,掩冉众叶惊。
俯仰各有态,得酒诗自成。
作于元祐七年 (公元 1092年)。苏轼所生的时代比陶潜身处之东晋乱世要幸运得多,但士大夫汲汲于名利以至斯文扫地、廉耻皆无的情形依旧。此时已有一些人生阅历的东坡居士已不像元丰年间对陶诗的理解,深浅有别。当年不明白陶潜作 《饮酒》诗, “正饮酒中,不知缘何记得此许多事”,此时已经以渊明的精神为榜样,其委时任运的姿态支撑着苏轼以后更坎坷苦难的命途。
其七 《蝶恋花》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作于绍圣元年 (公元1094年)闰四月,罢定州责知英州,南下途中。对立意象结构全篇。一首伤春伤情的词作,缠绵悱恻,一唱三叹。那世事无常,命运难以把握的烦恼与感喟啊。唯有大家,才会一身而兼具多副笔墨。
其八 《六月十二日夜渡海》
参横斗转欲三更,
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
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
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
兹游奇绝冠平生。
于元符三年 (公元1100年)六月,自海南岛返回时所作。该诗回顾了诗人被流放到南方的经历,表现了他北归的兴奋之情,九死不悔的倨傲之心和坚强自信、旷达豪放的襟怀。全诗多次运用 “比”的手法,韵味深远。
其九 《自题金山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
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
作于公元1101年。苏轼一生不论出处穷达,始终有四不变:“辅君治国,经世致用的抱负不变;怜恤生灵,为民造福的思想不变;襟怀坦荡,独立不阿的品节不变;乐观豁达,幽默风趣的心性不变。”苏轼一生那么多可圈可点的功业声名,他却独独选了最不堪的贬地荒境,格调立见。
其十 《南乡子·和杨元素时移守密州》
东武望馀杭。云海天涯两杳茫。何日功成名逐了,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
不用诉离觞。痛饮从来别有肠。今夜送归灯火冷,河塘。堕泪羊公却姓杨。
“醉笑陪公三万场/不用诉离觞”,熟悉吗?在 《致青春》中的青春别离中,被悲情豪迈地吟诵,古代诗词与现代场景毫无违和的引用、辉映,诗人余响已越千年犹铿然不绝。
再有,
“此心安处是吾乡” (《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
“有生何处不安生” (《山村五绝》),
“腹有诗书气自华” (《和董传留别》)等等,熟悉吗?
就在千年之后我们日常的交流中,就在我们对人生的探问解读中,苏子已经渗透在我们的血脉中了,像是文化密码,会被一代代人意会、传承。
“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林语堂先生如是说。
从诗人经历潜入诗作,再从诗作到对诗人心迹的探寻,反复循环,你才能读懂一个伟大的灵魂,你才能在某一个时刻被一句诗,一首词击中,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