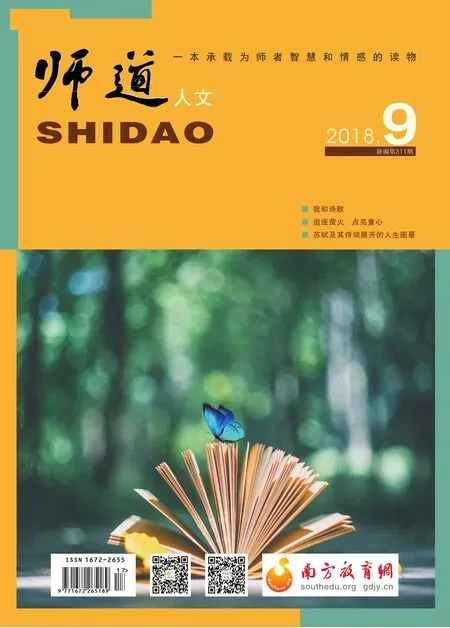秋日的里尔克
冯俊意
此时坐在窗前,北风从屋子的另外一边进来,吹着我的肩背,感觉有点冷。我正沉浸在里尔克的世界里,快收尾了,已经是书的尽头了。
这几天都在翻读冉云飞先生的《里尔克:尖锐的秋天》。窗外,喧嚣的校运会广播正闹着,那里有一个青春运动的世界。而喧闹从来都跟我无缘,那样的境况下,我只会更觉自己是孤独的。读里尔克的诗恰好,读他本人更合适,因为对于诗自己不一定读懂,常常是依着自己的理解从自己的方式去解读,也就只能永远在渺无际涯深不可测的诗海里吸取极微小的一点作为自身的营养。很多人说诗不容易看懂,是啊,有些诗确实写得晦涩又难懂,但是在我看来,与小说散文相较,好的诗歌更直接地触碰到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感动和温润我们日益麻木和硬化了的心。诗人于坚说得很对: “读一首诗就是被击中。而不是被教育。”

莱内·马利亚·里尔克 (1875—1926年),二十世纪著名德语诗人
万事万物都要有缘,没有缘分,东西再好,也只是它们而已,关卿何事? “我们相知不深,因为我不曾与你同在寂静之中。” (梅特林克语)常常慨叹,这世上好书太多,可很多都跟自己没缘,或是缘分未到。什么人读什么书,什么时候读什么书,什么地方读什么书,或许是冥冥中上苍安排的,不然我们为何总会为寻寻觅觅而烦忧,而无奈。在我自己有限的阅读里面,外国诗歌读得并不多。同很多人一样,我也认为我们作为普通读者跟外国诗歌还隔着一层翻译。翻译难,诗歌翻译尤难。或许,诗人翻译诗歌,诗人谈诗歌,这样的书会更好看些。所以,我个人非常偏爱穆旦、冯至、王佐良、北岛、王家新、黄灿然他们的译诗,因为他们本人就是非常优秀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认为,译作应能同原作平起平坐,它本身是无可重复的。是的,这样的译诗才是真正的诗。王家新好像也说过,一个优秀的译者不是 “翻译机器”,他应该是诗的 “分娩者”和创造者。
冉云飞先生这本谈诗人里尔克的书我至少是读进去了,且为之深深吸引,因为作为学者的冉云飞早年也写诗,后来又出过一本好看的谈唐诗的书 《像唐诗一样生活》。北岛说: “一个好的译本就像牧羊人,带领我们进入牧场;而一个坏的译本就像狼,在背后驱赶我们迷失方向。”许多伟大的外国诗之所以进不了我们的内心,实是译本不佳。坏的译本横在我们面前就是一堵墙,我们终是不得其门而入。说来好笑,大学时代由于能读懂一些简单的英文,我曾读到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The Road Not Taken,当时非常感动,背诵后黯然落泪,这或许是我唯一能读懂原文且非常喜欢的英文诗了。相比之下,该诗的汉译,无论如何都没有了原诗的意境和神韵。反之,是否亦然?世人都知唐诗宋词不可译,不仅不可英译,亦不可今译。
其实,里尔克的诗,稍有阅读的人都不会陌生,他最为我们熟悉的 《豹》好些人都读过,但我也只是匆匆而过而已。不应该错过的,茫茫书海,与你有缘分的东西本就不多,该反思自己的阅读方式和途径了。怎么会错过呢?深受里尔克影响的中国诗人冯至,也是他把这位伟大诗人的诗翻译到中国的土地上得以传播的,当年我从图书馆几把冯先生的诗都看完了,而冯先生的诗公认的深印里尔克的痕迹。我应该从冯先生那里溯源而上,或许能有机会看到更广大的风景。很遗憾,没有。不过,或许是里尔克的诗本身就不太易为人理解,没有一定的年龄和人生阅历,他的诗是不易被我们接受的。这也正是里尔克的诗 “凝重苍凉” (北岛语)的原因吧。
寂寞和孤独是里尔克诗的常见主题,其实也是诗人们共同的主题,只不过对于里尔克是永恒的,伴随一生,不仅仅浸透在诗歌里面。诗人自己这样说: “我是孤独的但我孤独的还不够,为了来到你的面前。”你是谁? “你要爱你的寂寞,负担那它以悠扬的怨诉给你引来的痛苦。”这痛苦,最终也将结晶为艺术,为诗歌。里尔克在写给青年诗人的信里一再讲到寂寞,实是诗人自道: “我们最需要却只是:寂寞,广大内心的寂寞。走向内心,长时期不遇一人——这我们必须能够做到。居于寂寞,像人们在儿童时那样寂寞……”寂寞,这个永恒的话题,道出了人存在的本质。我喜欢这一句: “孤寂好似一场雨。/……这时孤寂如同江河,铺盖大地……”诗人冯至的名作《蛇》也为我们留下了一条寂寞的长蛇的意象。由诗人冯至来翻译诗人里尔克的诗是最恰当不过的。
最喜欢 《秋日》这一首短诗,在这样的秋日里,读它恰好:
主啊!是时候了。夏日曾经很盛大。
把你的阴影落在日晷上,
让秋风刮过田野。
让最后的果子长得丰满,
再给它两天南方的气候,
迫使它们成熟,
把最后的甘甜酿入浓酒。
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
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就醒着,读着,写着长信,
在林荫道上来回
不安地游荡,当着落叶纷飞。
诗人北岛因这首 《秋日》把里尔克列为20世纪最伟大诗人之一。而对于中国当下的译诗,北岛同样颇为担忧。他的 《时间的玫瑰》就是一本谈诗人、谈外国诗歌、谈诗歌翻译的随笔,所选的九位20世纪西方诗人,作者认为称得上是最伟大的诗人。其中很多选诗由于不满前人的译本,北岛都亲自再翻译,即便承认冯至这首 《秋日》译得比较好,他还是再次参考其他译本在冯译的基础上再修改 “攒”成另外一首,读者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翻翻看,我个人感觉确实比冯至上面这首译诗更简洁有力,节奏感也更好。但我仍认为冯至这首已是相当精彩了,而且冯至懂德语,译诗是从德语直接翻译过来的,北岛是参考英译在冯译基础上略作修改而已。
“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多么决绝,多么令人绝望。但是,这孤独对于人类而言实在是永恒的,因而也就 “不必”那么惧怕,尽管是 “不安”的, “当着落叶纷飞”。这种孤独不是在寒冷衰败的冬日,而是在最佳的秋日,秋风,秋实,秋叶,这是一种怎样纷繁的意象呀?虽孤独,而不孤寂。里尔克深知其理,所以他也主张 “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诗人懂得 “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便懂得了承受,一往而前。如诗人自己所说的, “因为在根本处,也正是在那最深奥、最重要的事物上我们是无名地孤单。”

我也喜欢冯至 《十四行集》中的一首:
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
我们都让它化作尘埃:
我们安排我们在这时代
象秋日的树林,一棵棵
把树叶和些过迟的花朵
都交给秋风,好舒开树身
伸入严冬;我们安排我们
在自然里,象蜕化的蝉蛾
把残壳都丢在泥里土里;
我们把我们安排给那个
未来的死亡,象一段歌曲;
歌声从音乐的身上脱落,
归终剩下了音乐的身躯
化作一脉的青山默默。
读完此诗,我也仿佛自己身上有什么东西在脱落,在这样的秋日。我甚至怀疑,冯至是翻译 《秋日》之后,意犹未尽,又作了这首属于他自己的 “秋日”之诗。
诗人也有流浪和漂泊的一生。作为出生于布拉格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主要是德语诗人,也用法语写作,长期生活在德国柏林和慕尼黑,旅居意大利、法国等地。里尔克说: “我属于这么一种人:他们只有在以后,在第二故乡里才能检验自己性格的强度和载力。”漂泊不安的人生,是现实使然,也是诗人自己的抉择,他们总在寻觅,探求,追逐。人都在追求自身的安身立命之所在,可要命的是,我们永不可能找到,人永不会有自己真正的故乡。故此,痛苦也就是永恒的。冯至先生除了翻译里尔克的一些经典诗歌,还翻译了里尔克的 《给青年诗人的信》这本了不起的小书,这本小书对于了解里尔克关于诗歌关于诗人有非常直接而重要的帮助。比如他给学写诗的青年建议: “只有一个唯一的方法:请你走向内心。……你要躲开那些普遍的题材,而归依于你自己日常生活呈现给你的事物;你描写你的悲哀与愿望,流逝的思想与对于某一种美的信念——用深幽、寂静、谦虚的真诚描写这一切,用你周围的事物、梦中的图影、回忆中的对象表现自己。”这已经是诗人自己很具体而微的写诗经验之谈了,对我们读他的诗也有莫大的帮助。
小心翼翼合上书,读这本书的时候也是战战兢兢的,在图书馆二楼找出这本满是尘埃的书,或许多年来都没什么人动过它,它的装帧也太差了,一翻就脱,后来翻读它时不敢翻得太开,惟恐弄散弄坏了。合上书,意味着读完了,其实远没有读完,更没有读懂。只不过完成了一个过程罢了。 “伟大的诗歌如同精神裂变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其隆隆回声透过岁月迷雾够到我们。” (北岛)但诗歌永远不会是大众的,可又有什么关系呢?诗本不可言,不可教,不可解,或者说各有各的读法。这么多天,我都浸淫在里尔克的诗海里,它让我多了一些感知,多了一些思索,也多了一些对孤独的爱。于我而言,这就足够了。
抬头望见窗外,明黄的阳光照射在室内深红的帘子上,窗外的花坛还是绿的,我眼睛一亮,多么强烈的色彩对比啊!不过,在阳光斜照的窗玻璃上,留下的是防盗网斑驳的影子,我仿佛看到了一只豹子挪动的身影,渐渐地令我昏眩。这或许就是里尔克的豹?好在这样的秋阳暖暖的,也很是舒适。如此,诗歌也不只是冷色的,生活也应还有暖阳。